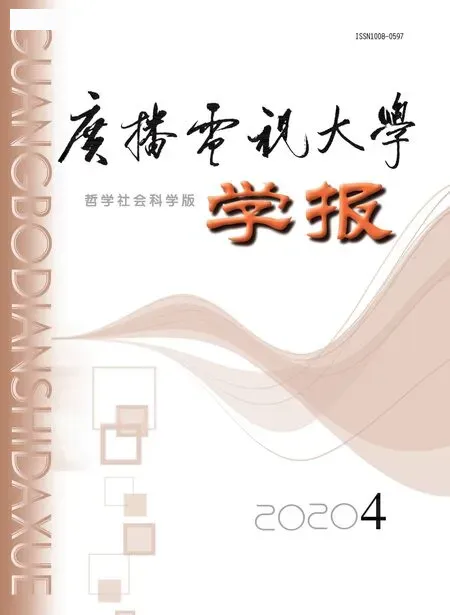从作为环境的意象到作为意象的环境
——以《诗经·蒹葭》为例
2020-03-03刘圆婧
刘圆婧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环境史研究有许多著名的对象,如:大象(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老虎、稻米、丝绸、淤泥(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竹子(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作者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对象入手,以小见大,揭示出环境变迁与人类发展的历史。而《蒹葭》所描绘和塑造的一种环境,及诗中的“露”“霜”和“蒹葭”诸意象,似乎俯仰皆是,并不具有作为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典型性。然而考察后世人们对这样一种作为环境的意象本身行诸文字的运用,可以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环境观,体现出上古人们对在特定场景下对环境的记忆于后世人们的影响,乃至环境本身都上升成了一种意象,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交互诠释。当前的环境史研究,在对待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但注意和承认自然环境及其变化会影响人类的历史,而且更注重人类的活动如何改变了自然界,进而反过来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和未来。
探讨《诗经》中篇什的主旨,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读《诗》,什么是《诗》的本来面貌?历代学者积年累月地对《诗》中的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求,试图对诗旨进行最大限度上的还原。经典诠释,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对经典的尊崇与虔敬、对经典传承的自觉与共识,是此种诠释传统植根的土壤。正因为经典在中国士人群体中具有的至高地位,思想的流变往往以经典为载体,以治经、解经为方式,以期实现思想的孕成、破茧与传承。经典诠释,是中国士人传扬前贤的方式,更是他们表达自我的途径。上迄先秦,孟子诠解释经,便以“以意逆志”四字概而括之。先秦以降,所谓经今古文学之争,无非诠释角度之牴牾。诠释不仅是对文本意义的如实描摹,更是对文本的重新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达成对文本的全新解读。不同的诠释角度和诠释方式,是诠释者也即解经者个人志趣的展现和时代学术风貌的缩影。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解经作为解经者思想表达的途径,承载着时代思想的变化。
宋代学者试图跳出这个圈子,对经学文本进行直接研究,诗句说什么就理解为什么,在经学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疑经改经”之风。但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探求《诗》之本义已十分困难,所有的判断都只是更为接近事实的假说。所有研究都要归于“经学解释体系”和“文本解释体系”两个语境下,而所有的探究又都是针对“《诗》体”的还原,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的《诗经》解读,清人大都已经进行了总结性的回顾,难有突破。跳出现有“解释体系”,或许不仅能为《诗经》研究另辟新路,更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诗经》其实从来都是体用二分的,从春秋时起,贵族士大夫注重《诗》的学习就是立足其应用性,徐复观认为六经一开始就是“寓于教诫的经典”[1]。孔子出生之前,西周以来的诗已有了“诗三百五篇”的通行文本,崔述《读风偶识》载:
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也。[2]
《诗》以文乐合一的方式广泛流行于上流社会,贵族成员普遍接受了《诗》的教育。但士大夫并不太关注其审美功能,而是重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属性。鲁釐公二十三年,秦伯享重耳,是对《诗》断章取义应用的最早记载,《左传》和《国语》都有提及,《国语·晋语四》:
秦伯赋《采菽》,子馀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馀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馀使公子赋《黍苗》。……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馀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馀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3]
《左传·襄二十八年》卢蒲癸更是直接说出了:“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4]毫无疑问,在周代礼乐文化的背景下,《诗》自然成为公卿及士人君子参政议政、讽喻谏诤、抒怀达意的特定方式和表达程式[5]。而从历代文人对《诗经》所塑造的一个个深入人心意象的应用,较“赋诗断章”实际上更近了一层。程俊英在研究《诗经》时,常常运用“(先)细玩诗意,再同后世诗词加以比较”[6]P65的方法,这是立足于《诗》的应用性。
一、多种解释体系下的《蒹葭》
关于《蒹葭》的主旨,向来聚讼纷如,莫衷一是。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立足于传笺的“未能用周礼”说,《小序》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7]P601同属“《诗经》汉学”体系下的《郑笺》《孔疏》也是这么解释的。二是由传笺生发出的“求贤慕贤”说。三是“怀人”说。四是爱情说。前人对多种说法的研究已论之甚详,在此不必赘述。唯一要提及的是后世文人用典时,不可能完全脱离经学或文本解释体系,这两种解释体系多少会对他们的用典产生影响,不过就是多少深浅的差别,故我们在讨论文人用典时也要兼及文人所属时代对《蒹葭》的解释情况。
细玩诗意,《蒹葭》主要描绘了一个思慕、找寻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艰难。“溯洄从之”言逆着河流向上游找寻,“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写道路难行;“溯游从之”言顺着河流向下游找寻,似乎快要找到了,但也只是“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很明显,诗中的主人公最后是没有找到自己想要找寻的那个人的,对此历代学者大都无争议,除了清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云:“盖言逆流从之则随水出其右而难至,顺流从之则可自右而左,至其沚也。”[8]似有最后要找的人就在水中的小沙滩,顺流而从就可找到的意思,但也不十分明确。进一步分析诗中的诸意象,很明显“露”“霜”“蒹葭”等起兴之物对塑造全诗的意境起了重要作用,而要寻找的那个“伊人”,更是重中之重。从后世文人用《蒹葭》诸典考察,大致围绕着这几个意象展开。植物自身的意象、植物与自然结合的意象、植物与人形成的意象,三者交织成为《蒹葭》之大环境的意象,又在创作者的手中与后世的流传和诠释中成为了作为意象的环境。
二、成为典故的《蒹葭》意象
(一)“露”和“霜”
诗经中涉及“露”的诗有五首,《召南·行露》《郑风·野有蔓草》《秦风·蒹葭》《小雅·蓼萧》和《小雅·湛露》。这五首除《蒹葭》外,各诗主旨均无较大争议。在除《蒹葭》外的四诗中,“露”大多以一种起兴的物象呈现。《湛露》是宴饮诗,“露茂盛貌”,借露水非阳不干,兴宴饮不醉无归。《野有蔓草》是一首恋歌,“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春草青青、露水晶莹,在清晨的田野里男女相会,《孔疏》说:“毛以为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陨落之露,漙漙然霑润之兮,以兴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泽之化,养育之兮。”[7]P444《孔疏》中对《蓼萧》中的“零露”的解释,较《野有蔓草》相似,“此萧所以得长大者,由天以善露润之,使其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故得其长大耳”[7]P880。《行露》可归为弃妇诗一类,女子十分强硬地对欺骗她的男子表示了严厉的拒绝,开头所描绘道路上潮湿的露水,给人以阴冷不适感,程俊英认为是“用它(露)象征强暴之男”[6]P41。综上分析,“露”不足以自成一典故,因为露水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小水球,不同人关于露水因为情景的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解释。唯有将“露”和“霜”置于一处,才几乎可以算是一个从《蒹葭》中生发出的典故。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所收作品上至先秦,下迄梁初,收录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史、子书。故主要以《文选》所收考察魏晋以前关于《蒹葭》的用典。张平子(衡)《思玄赋》有: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袭温恭之黻衣兮,被礼义之绣裳。辫贞亮以为鞶兮,杂伎艺以为珩。昭彩藻与雕琭兮,璜声远而弥长。淹栖迟以恣欲兮,耀灵忽其西藏。恃己知而华予兮,鶗鴃鸣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时亹亹而代序兮,畴可与乎比伉?咨姤嫮之难鎫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彰。[9]
据《后汉书》记载,“(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10],《思玄赋》主要是关于作者感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自己政治上不得志,被奸佞所谗讥。“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一句,据《六臣注文选》注云:“言以才艺之美而不见用,为邪佞所夺。如灵芝一年三度秀茂,而乃迫于霜露不得茂盛也。”[11]以芝迫于霜露则不能秀茂,喻贤才被谗,与《蒹葭》的“未能用礼说”“未能用贤说”颇近,我们可以认为张衡作为一个天才文学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从传、笺中直接汲取了养料。魏文帝曹丕《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12]卷二十P1283-1284
全诗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突出特点是写景与抒情的巧妙交融。此诗与《蒹葭》颇有联系,都是描写一种求而不得的痛苦,不同的是此诗多直抒胸臆,情感表达更为浓烈直白。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13]和《蒹葭》的“白露为霜”共为“草木零落露为霜”一句所用典故的滥觞,曹子桓此处应将“白露为霜”所反映的《蒹葭》主旨,理解成一种悲清凄凉的情感。左太冲(思)《杂诗》:
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明月出云崖,皦皦流素光。披轩临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12]卷二十九P1376-1377
全诗的诗眼是末二句,表达了作者感慨时间飞逝,惜己壮志未酬的情感。“白露为朝霜,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主要是写时间逝去之速,与《燕歌行》相似。
其实在西汉初年,《薤露》作为一首著名的挽歌,其中“露”的含义已颇为明确。据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言:“丧歌旧曲,本出于田横门人。歌以葬横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14]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像薤上的露水,到太阳升起时就会慢慢晞干。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薤露》一篇的“露”与《蒹葭》有直接关系,但“薤”和“蒹”“葭”同属草本植物,凝结在它们上的霜露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后世文人在运用“露”,特别是“霜露”的典故时,还是与《蒹葭》的“白露为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蒹葭
“蒹”“葭”并称在《诗经》中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在以“蒹葭”为题目的《秦风·蒹葭》中。《毛传》云:“蒹,薕。葭,芦也。”[7]P601“蒹”“葭”应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故分别考察“蒹”“葭”在《诗经》中的出现,除《蒹葭》一篇外,还有七处。分别是《召南·驺虞》《卫风·硕人》《卫风·河广》《豳风·七月》《大雅·行苇》《王风·大车》和《小雅·小弁》,通过对以上各诗的分析,“蒹”“葭”在以上各诗中的地位,远没有《秦风·蒹葭》一篇重要,加之这些篇什都不似《蒹葭》著名,故可认为后世对“蒹葭”之典的运用,都可以远祧《蒹葭》。
最早以“蒹葭”为典故的文人是东汉的蔡邕,他在《释诲》一文中说:
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萌,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15]
但他仅仅把“蒹葭苍而白露凝”理解成自然现象,是寒暑交替、阴阳变化的标志,并未对“蒹葭”的内涵展开发挥。曹子建《盘石篇》:
磐石山巅石,飘飖涧底蓬。我本泰山人,何为客淮东?蒹葭弥斥土,林木无芬重。[16]
据孙明君的说法,诗人幻想自己走出蒹葭丛中,走向大海,这是一首想象中的游历诗。[17]蒹葭在曹植笔下,也只是作为自然界中的单纯草木而已。及至魏明帝曹叡时,在《世说新语·容止》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18]
“蒹葭”被当作一种常见值贱的水草,用来反衬玉树的秀美挺拔。到了唐代,文学创作迎来了新的高潮,诗歌创作更是达到了巅峰。唐代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为《诗经》的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诗经》作为五经之一,以其流利上口,在唐代多用于启蒙教育;科举中进士考试考诗赋,诗赋注重文采,而《诗经》往往作为文采的标准。从唐代许多诗人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诗经》不同程度的接受[19],也即对《诗经》的应用。杜甫便有题为《蒹葭》的诗作:
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沉波。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20]P613
这首诗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关于《秦风·蒹葭》主题意象用典的一次总结,杜甫借蒹葭抒情,表达了自己唯恐年岁蹉跎的心情,也塑造了一种四时变化、万物生灭的苍凉夐远之意境。虽未及《秦风·蒹葭》寻人不遇的主旨,但对《秦风·蒹葭》中所营造的意境有了改造和转化,把原诗中一日之间时间的变化,改写成一年之间的四季变化,“咏秋日蒹葭,而兼及四時。苗早言春,露多言夏,后落又涉冬矣”[20]P613。杜甫还有《渼陂西南台》一诗,虽有“蒹葭离披去”句,但较此诗来说“蒹葭”作为一个典故的地位就不是那么突出了。白居易也有《寄微之三首·其二》:
君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襄阳九里郭,楼雉连云树。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苍茫蒹葭水,中有浔阳路。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21]
“苍茫”二字与《蒹葭》全诗的意境十分相似,而这首诗本来就是一首寄人感怀之诗,也有几分“友人难寻”的韵味。同时代的储光羲、韩昌黎、杜樊川、柳子厚也都在诗中运用了“蒹葭”这一典故,但均未超过前人,以蒹葭起兴其他的感情。
(三)“伊人”“依人”与“秋水”
“伊人”是《蒹葭》一诗中作者反复寻找的人,是全诗中最主要的意象,是重中之重。“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句,更是一般人对《蒹葭》一诗的最直观印象。《毛传》:“伊训为维,笺云伊,当作繄,繄犹是也。”[7]P601陈奂《毛诗传疏》:“伊、维一声之转。伊其即维其,伊何即维何,伊人即维人。”“维,是也,犹言‘是人’也。”[22]《诗经》中还有《小雅·伐木》《小雅·白驹》二首谈及“伊人”,按一般解释,在这两首诗中,伊人一为“朋友”,一为“贤人”。因为《小雅·伐木》《小雅·白驹》都是诗经中影响较大的诗,不能简单地把“伊人”这个典故归结成《蒹葭》所有的。加之“伊人”本来所指的就是“那个人”的意思,谁都可以用“伊”这个指示代词。
但到了《诗经》宋学的时代,朱熹的《诗集传》第一次将“秋水”“伊人”并提:“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23]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从朱子说[24],这里所指的“秋水”虽出自《庄子·秋水篇》,但在与“伊人”结合起来之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又因朱子的《诗集传》是元、清二朝科举考试的官方教科书,故对文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中收录了一篇《奉答新喻张克隽明府》:
微生夙婴患,趋庭迫章句。披襟未穷历,吟讽已入趣。稍涉王覇术,妄意清时遇。逶迤江海心,蹭蹬风云路。得贫还自骄,夫官非我素。断汲移沙井,休车倚庭树。常恐交知绝,不获赏心晤。长天纡物色,空谷知人处。客言神仙尹,振舄龙池墅。秋清散明月,春阳霭芳露。琴歌纷有适,简书澹无虑。高情难闻寥,雅意在延伫。倾风有近远,赏气无新故。直以微细质,侧承君子顾。仪文牣兼金,惠心深尺素。徒知私自怜,何期远相慕。白露滴秋水,伊人宛洄遡。聊用倚逍遥,相于及迟暮。[25]
这首诗是与新喻知县张克隽相互唱和诗篇的一首,“白露滴秋水,伊人宛洄遡”二句表达了对朋友的深切怀念,写自己命途多舛,对友情就更加重视。愿意如《蒹葭》中的伊人一样,徘徊洄遡,期待着与朋友的再次相遇。
《汉语大词典》“秋水伊人”一条,认为是“对景怀人”的意思,并引《雪鸿轩尺牍·答许葭村》:“登高望远,极目苍凉,正切秋水伊人之想。”词典的解释大体不误,但未认识到“秋水伊人”一词真正的出处应该是朱熹的《诗集传》。而台湾“教育部”所编的《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认为“伊人”多指女性,或许和人们把“伊人”和“依人”的混淆有关。“依人”一词据《辞源》(第三版),典出旧题为汉代郭宪所撰的《洞冥记·三》:“有远飞鸡,夕则还依人,晓则绝飞四海”。“伊人”是与人亲近的意思,另有飞鸟伊人、小鸟依人的成语,在后世也多用来形容女性情态可爱。“伊人”“依人”音同,我们可以推测,在《蒹葭》传播过程中,人们把“伊人”“依人”相混,渐渐认为“伊人”是指女性而言的,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蒹葭》诗旨的理解,《蒹葭》是一首爱情诗的说法渐渐为人们接受。
三、从文人用典综合分析诗旨
通过对文人用典的考察,我们发现对《蒹葭》主旨的解释是在不断地层累中形成的。由最初的《毛传》《郑笺》的解释,到文人对《蒹葭》中典故和其他文献中相关典故的组合,进而生发出众多解释,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文人自己自觉地、不受现有解释体系限制的创作,就是古人对“蒹葭”“露”“霜”“伊人”的诸多意象怎么用,我也怎么用,是意象的用法,而不是典故的用法;也有基于解释所赋予诗旨,进而细化到意象的创作,即典故的用法,对典故的用法一般是层累的,因为对于某个意象来说,总有多种经典文本对其作出不同的阐释,这些阐释共同构成了典故本身。
在人类文明初期,自然崇拜无处不在。在周代,人们与自然事物的关系已相当亲密,然而由于最初的审美经验是物质需要的产物,因而审美对象便是与人类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动植物。然而在《诗经》文本中,对自然力量的顶礼膜拜已然开始让位于对自然事物的客观描绘。随着人与自然的联系日渐复杂多样,人们对于自然的观想,不再为物质功用所局囿,自然景物开始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活动相缔结。人们开始发现自身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对应关系,借助自然的“对应物”,内心世界也找到了表达的窗口,这也是“比兴”的始作。从原始宗教、物质功用到精神功利,《诗经》反映了审美意识的层累与跨越。
在原始巫术、原始宗教时代,凡巫术活动与祭祀仪式,往往伴有原始意象与神话故事,日月山川以至动物植物皆是意象。每个意象又都有其内涵丰富的神话故事。这对当时的先民们来说是人人了然于胸的集体意识;然而对于后人来说,它们的原始的意义逐渐模糊,鲜明耀眼的环境退隐成为诗词歌赋里悠远缥缈的意象。原始的环境“意象”经过《诗经》的始作,在继续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社会意蕴的基础上,又生发出了先民借以抒发个人情感与意志的功能。这两者的结合,就完成了由神话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过渡,集体观念开始了向个体意志的转化,客观的环境拥有了人文化的表达。而在后世两千多年的《诗经》诠释史上,政治教化、道德教化、历史训诫的视角逐渐成为主流。《蒹葭》的场景及其蕴含的主旨,因为《诗经》的原典性而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接受,“露”“霜”“蒹葭”(乃至“伊人”)从作为环境的意象上升成作为意象的环境,将自然环境与人类情感相结合,赋予了自然环境超越了时空的力量,我们也能从中反观《诗经·蒹葭》一篇的原旨所在,为其解释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仅就《秦风·蒹葭》一篇来看,它的主旨就应该是一个寻而不得的过程,这样来看无论是寻找贤人、朋友还是恋人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