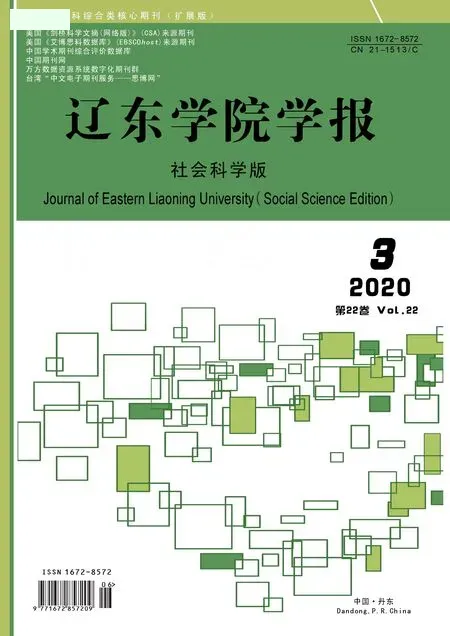数字经济测度困境与核算建议
2020-03-03宫春子
宫春子,黄 俭
(1.南昌工学院 财富管理学院,南昌 330108;2.豫章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南昌 330103)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数字经济更是推动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2016年9月,我国在杭州G20峰会上首次提出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中国创新增长的主要路径;2017年3月,我国正式将发展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利用互联网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传统产业,大力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近年迅猛发展。200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4.80万亿元,占GDP总值的15.2%;2011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9.49万亿元,占GDP总值的20.3%;2014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16.16万亿元,占GDP总值的26.1%;2015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18.63万亿元,占GDP总值的27.5%;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22.60万亿元,占GDP总值的30.3%;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27.20万亿元,占GDP总值的32.9%(1)数据来源:各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31.30万亿元,占GDP总值的34.8%[1]。但作为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统计范围界定、数字经济的总量测度、数字经济的调查方式方法、数字经济的核算原则、数字经济的统计和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等都还没有跟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即传统度量方法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经济的度量。本文针对数字经济统计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界定数字经济的内涵,解析数字经济在测度和核算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数字经济测度的调查方式和核算方法,同时提出设立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统计指标体系的建议。
一、数字经济的范围界定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分享经济、虚拟经济、互联网经济等一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的经济形态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因此,要准确界定数字经济的统计范畴,必须先厘清各种经济形态。
信息经济,也称资讯经济、IT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关键是创新能力,知识经济有两大突出特征:首先,先决条件是人的素质和技能;其次,基础是研究开发,核心是信息与通信技术,主角是服务。因此,知识经济集中突出人的智能。
分享经济是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的资源,通过平台化达到供需匹配,以新形态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它是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并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包括金融业的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也包括房地产业、体育经济、博彩业、艺术品收藏等。
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经济活动总和。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主体的经济行为,其交易行为大多直接在网上进行。
以上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分享经济、虚拟经济、互联网经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数字经济在不同视角下的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在我国虽然产生时间较短,但数字经济的提法在发达国家由来已久,只是至今仍没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塔普斯科特。1994年,数字经济刚出现时,塔普斯科特就出版了专著《数字经济》(近年又出版了《区块链革命》《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范式转移》等著作),塔普斯科特被称为“数字经济之父”。之后,伴随着美国大学教授卡斯特尔于1996年出版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和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数字经济概念逐渐在世界流行,并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力度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和生活。但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没有统一的界定。
当下,学者们通常认为: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互联网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业等;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它是指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提升了传统产业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而新增产出的部分。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年4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将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扩展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2],即将数字经济由“两化”扩展到“三化”。
综上,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数字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数字经济使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之间通过网络以数字化进行交易、沟通和管理。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关键是资源整合。简言之: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高效率平台、大规模生产、个性化服务、数字化治理为特征的经济形态。
二、数字经济测度的困境
我国原有国民经济核算内容主要关注市场、商品和服务价格,而数字经济具有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和新价值产出,这使传统的测算体系无法完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法,即在界定范围内统计或估算出一定区域内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二是对比法,即基于多个维度指标,对比不同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得出数字经济发展数据。
虽然直接法和对比法都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仍不能准确反映数字经济的全部情况。此外,一些数字经济现象也超出了测度范围,使传统的核算方式方法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形态内容:一是许多新经济活动目前无法纳入统计核算中,而要纳入核算,首先必须先鉴别这些新经济活动的性质,即明确哪些属于生产,哪些属于服务,哪些收入应该纳入统计。例如,近年来网络直播发展迅速,成为一种新的互联网文化业态。例如:网络直播行业在经济收入、用户人数等方面都发展较快,2015年我国国内网络直播市场规模约为90亿元,平台数量近200家,直播平台、用户数量约2亿个,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近400万,直播房间数量超过3 000个(2)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年到2020年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发展规模更大。其中,网络广告规模近4 000亿元,在我国广告市场中占比达50%以上。受网民人数增长、数字媒体使用时长增加、网络视听业务增长快速等因素影响,电视、报纸、杂志广告持续下滑,网络广告速度持续迅猛增长(3)智研咨询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网络直播行业市场分析预测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而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媒体形态,其打赏收入、广告收入等应如何统计?再比如,娱乐圈中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现象居多,以草根出身歌手“大衣哥”朱之文为例,一夜成名,身价倍增。其妻子、儿子、女儿都以发朱之文照片或直播朱之文生活赚钱,而且同村的一些年轻人也不外出打工,辞职专门在家靠直播朱之文及家人的生活在网上赚钱,赚钱额多于打工收入。其中,一小哥仅出卖其成熟的“公众号”就赚得60万元,比其10年打工收入还多[3]。这种经济现象应该如何统计?
二是传统企业与数字经济企业不断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产生和消亡快速,另一方面新状态花样翻新,界定难度加大。例如,单车生产本来是传统企业业务,但单车却走向了共享经济。但曾被誉为“新四大发明”之一、风光无限的共享单车行业,2018年底又陷入困境中,大批ofo用户聚集在总部排队退押金。ofo半年报负债表显示:ofo整体负债为64.96亿元,其中,用户押金为36.50亿元,供应链为10.20亿元[4]。共享单车模式经营数额之大不容忽视,但共享单车经济商业模式应如何统计?再比如,居民自有小客车参与共享营运,事实上从事了运输服务,应如何统计?如果将其计入生产活动,则会改变居民购买小客车作为耐用消费品的统计,如果不作为生产统计,又无法反映全社会的服务总量。
三是一些科技企业服务的消费者遍及全球,企业常设机构动态性强,使得数字经济规模测度难。由于数字经济主要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这使企业服务的消费者不受地域限制,企业常设机构也会根据有利于企业的原则经常变更,企业地域经济总量难测度。例如,2019年6月9日,欧洲G20财长就加征数字税主题召开会议并达成共识:将制定相关法规加增数字税,堵住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等全球科技巨头为降低企业所得税而利用的漏洞。因为根据现行规则,拥有活跃用户群体不构成企业的常设机构,所在国难对跨国高科技企业相关利润征税。而即使有常设机构,相关国家也只能对常设机构的经济活动和资产产生的利润收税。由于科技服务企业多提供线上服务而非实体产品,其价值创造地和缴税地不关联、不匹配(因为企业可以选择在税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公司,以此规避税务压力)。例如,2017年谷歌公司通过一家荷兰空壳公司将227亿美元转移到了百慕大;同年,苹果、谷歌、脸书、思科和微软在英国的营业收入大约为234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 072亿元),产生的利润约为66亿英镑,依据英国现行税率税收负担为12.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11.6亿元),实际上在英国综合税负仅为1.91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6.9亿元)。再如,根据欧盟执委会的数据,传统行业企业需缴纳的有效税率为23.3%,而大型跨国科技企业因为跨国经营,选择利于避税地设立常设机构,平均税率只有9.5%。欧盟报告显示,谷歌在海外地区缴税占其营收的9%,但在欧盟地区缴税只占其营收的0.82%以下[5]。因此,2019年欧洲G20财长会达成共识:加征数字税。而常设机构活动性强,这同样增加了数字经济的统计测度难度。
三、数字经济测度的建议
“世界正在迎来新时代、新机遇,数字经济将重塑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将会有新的模式,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6]从数字经济规模统计数据上看:2018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1.2万亿元,占GDP总值的33.3%。这无论从总量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数字经济增速都很快。其中,2018年数字产业化部分为6.4万亿元(2017年数字产业化部分规模为6.2万亿元);2018年产业数字化部分为24.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7.6%[2](2017年产业数字化部分为2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5.4%(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虽然快速,但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数字经济均占GDP比重在50%左右。以2016年为例,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0.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6.9%;英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8.4%;日本数字经济规模为2.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7.5%;这些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在GDP中占比均接近或超过50%(5)③ 数据转引自李金昌《数字经济向我们快速走来》,《中国统计》,2018年第4期。。2018年从总量上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31.2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为4.7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3.3%。以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占比上看发展空间都很大。
毋庸置疑,数字经济规模本身重要,准确统计测度数字经济规模同样重要。因为无论“高估”还是“漏统”,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都有重大影响。针对我国目前数字经济测度的困境,笔者建议:
(一)明确数字经济的统计范畴
2017年7月,我国出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指出要尽快建立数字经济核算制度与统计分类,但我国目前与数字经济相对应的数字产品(服务)却五花八门,不尽统一。学者们通常将数字产品基于用途分为内容型、交换工具型和数字过程与服务型③。但数字经济不仅包括信息、通讯和技术产业自身的产值,也包括信息、通讯和技术产业带动工业、农业、服务业及相关行业产值增量的贡献,还包括由于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带来产值增量的贡献。只统计数字经济基础产业部分和融合部分,将效率提升和福利影响排除在外,数字经济规模总量必然被低估。因此,笔者认为数字经济的范围应该包括四大类内容:数字经济基础产业部分、数字经济技术型部分、数字经济融合部分、数字经济服务部分。
(二)建立科学的统计调查方法和核算方式
我国原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统一的定义,具有严谨性,要求用户按事先统一定义应用核算体系提供数据,但缺乏灵活性,不能满足用户新需求。因此,数字经济核算可以通过卫星账户形式,即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建立数字经济附属核算体系,使数字经济核算既以中心框架为核心,又有别于中心框架。
建议通过设立卫星账户,对普通居民、个体户、企业、政府使用数字产品和进行数字产品投资的情况,在统一口径后开展专项调查,并填制供给表和使用表,依据表中数据进行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计算。
同时建议卫星账户形式中的专项调查,可以通过在各项常规调查中增加数字经济调查的内容获得数据,即:一是与一套表的调查相结合;二是与规模以下的企业、个体户的抽样调查相结合;三是与住户调查相结合。同时,可选取重点行业、典型样本企业开展信息技术渗透率调查。总之,结合原有的调查形式和调查方法,增加数字经济调查项目,辅之以专项调查,可以取得数字经济的准确数据。
(三)构建科学的数字经济统计指标体系
统计指标体系是由表征评价对象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联系的多个指标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将数字经济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后,只计算数字经济总规模、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不能全面反映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效益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因此,必须建立反映数字经济活动的指标体系和指标评价体系。
在建立反映数字经济活动的指标体系时,首先要遵循系统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简明科学性原则和可比可操作可量化原则;其次,参考欧盟、美国商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赛迪网的经济指标体系,设立反映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从大的方面讲,可以设立四个一级指标,即基础型数字经济指标、技术型数字经济指标、融合型数字经济指标、服务型数字经济指标,再根据各一级指标设立若干个二级指标。例如,针对服务型数字经济指标,可以设立即时通信(微信用户分布)、生活服务(大众点评网与美团网用户分布)、网上购物(网络零售额)、互联网金融(支付宝与蚂蚁金服用户分布)、旅游(携程用户分布)、娱乐(爱奇艺用户分布)、教育(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互联网医疗(平安好医生用户分布)、出行(滴滴出行用户分布)等二级指标。通过多个指标,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我国数字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情况。
总之,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准确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强化数字经济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发布工作,完善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建立数字经济统计调查和监测制度,对提高数据质量,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优化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