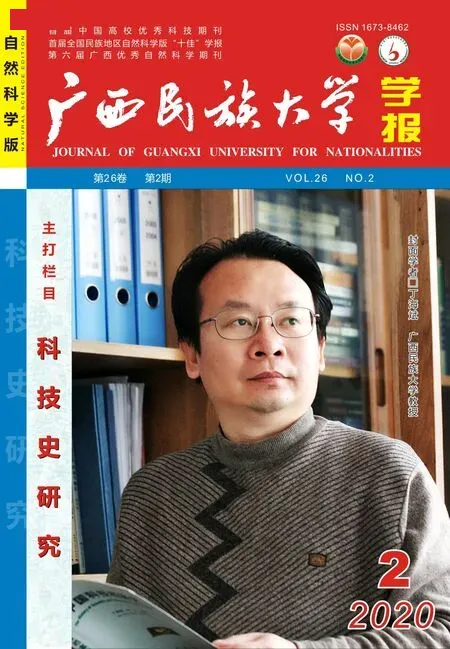宋代天文官员观念变化对改历的影响*
2020-03-03赵帅军
赵帅军
(1.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最为频繁的时期.前人对宋代历法改革因素的探讨多聚焦于历法的数理结构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在数理层面,前辈学者钱宝琮认为宋代历法在技术层面多沿袭唐代历法,没有做出太大的创新;[1]尔后陈美东认为,宋代历法在精细化程度上走得更远,而在技术上并未有重大突破.[2]这就使得后继学者把焦点放在社会层面上来探讨,胡静宜从政治、文化、经济角度论述了社会大环境对于频繁改历的影响;[3]康宇从一般性天文观念的变革探讨宋代历法的变革;[4]谢海金、徐刚则从官方与民间之争、华夷之辨、理学与历学之争三方面入手,对宋代历法变革的整体因素进行讨论.[5]但是学界关于改历人员的研究,少有涉及.笔者以宋代前五部历法为例,探讨天文官员观念的变化在历法改革中的影响.
1 宋代天文官员的政治地位
1.1 宋代天文机构设置
改历活动参与者的活动时间及行政范围,主要在元丰改制前的司天监.宋初承唐制,唐初司天监名为太史局,唐肃宗乾元二年改名为司天台,后梁改为司天监,宋朝承袭后梁之名,所以谓之司天监.
据《宋会要》载:“太史局旧名司天监,元丰改制行,改今名.《两朝国史志》载:司天监,监、丞、主簿、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监及少阙,则置判监事二人,以五官正以上充.礼生五人,历生一人.丞、主簿及五官正以下,皆守其职.掌察天文祥异、钟鼓刻漏、写造历书、供诸坛祀祭告,神名位版,画日.天文院,掌浑仪台,昼夜测验辰象,以白于监.测验注记二人,刻择官八人.监生无定员,押更十五人,学生三十人.钟鼓院,掌钟鼓刻漏、进牌之事,节级三人,直官三人,学生三十六人.”[6]3803《宋史》载:“司天监:监、少监、丞、主簿、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各一人.掌察天文祥异,钟鼓漏刻,写造历书,供诸坛祀祭吿,神名版位,画日.监及少监阙,则置判监事二人.以五官正充.礼生四人,历生四人,掌测验浑仪,同知算造、三式.元丰官制行,罢司天监,立太史局,隶秘书省.”[7]
可以看出,司天监是元丰改制前的天文机构.除了司天监之外,它还有天文院和钟鼓院两个附属机构,这是它的整个组织架构.司天监的主要职责就是察看异常天象、钟鼓刻漏、写造历书等.值得注意的是,写造历书是其任务,而编制历法不属于例行公事,编制历法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所以这是它的职责,而不是日常政务.对于司天监的内部结构,在《宋会要》宋神宗五年是这样记载的:“五年六月十六日,诏司天监历算、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并简罢”.[6]3805以此看出它应该包含这几个方面,在历算上,它有相应的机构和人才储备.司天监在北宋政府机构设置中属于行政机构,属于九寺五监系统,不隶属于其他任何机构.元丰改制之后,司天监才隶属于秘书省.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
另一个则是关于官员的组成.其主要有司天监、少监、司天监丞、司天监主簿、司天五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礼生、历生、刻择官、监生、押更、节级、直官、鸡唱、学生等.宋代在机构设置中,施行差遣制,所以在主要官员的实际任命上,需要细加斟酌.《宋会要》记载:“监及少阙,则置判监事二人,以五官正以上充.”[6]3803在司天监和少监缺位的时候,需要置、判监事两人来维持司天监实际运作,主要是以五官正及以上的官员来补充.但置、判司天监事的官员只是负责司天监和少监的工作,但不等同于这两个职位,实际是低于少监的.
1.2 宋代天文官员的地位及权责
天文官员在宋代属于“伎术官”.《宋会要》载:“和安大夫至医学,太史令至挈壶正,书艺、图画奉御至待诏,为伎术官.”[8]在元丰改制前,太史局即为司天监.有学者研究认为,天文官员等“伎术官”在宋代地位很低.[9]自隋唐以来,中国从士族门阀政治开始转向官僚政治,随着科举制的施行,也形成了日益庞大的科举官僚群体.经过唐朝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宋朝日臻完善,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宋朝整体的官僚分为文武两套班子,“伎术官”区别于此,属于杂流.从唐代开始,官吏开始分途,从事具体行政事务的吏群体逐渐从官僚队伍中分离出来.“伎术官”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分离出来的,成为一个有别于科举官僚队伍的群体.但是“伎术官”又和吏不同,它内部也是有品级的,宋朝的官品只是一般寄禄官而已,而不代表实际的权责.但它的官品和朝位是联系在一起的,表明官员在朝中的地位,朝位的重点是“人”.我们从现有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对于天文官员的限制是日益严苛,更多是在任官资格和升迁方面做出限制,更加多数的禁令是禁止司天监内部的“学生”,“学生”本身也是一种吏,而对于官员相对宽容.
宋代司天监监正的品位一般是从三品,少监是从四品.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官品丧失了其原有的意义.而差遣制是真正体现其权责的重要标志,所以确定其实际职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朝通过比品、序班等手段,建立了新的职官秩序.朝仪制度的排位则体现出其身份性质.根据学者的研究,在朝位的设置上,并没有把司天监排除在外.作为一种“伎术”机构,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限制其活动范围,另一方面仍然给予其特殊的地位,使其权责不相匹配,这是在皇权不断加强的趋势下,逐步弱化其他权限.[10]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往往和政治以及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所以对其限制会越来越严格.同时这也是皇权不断加强的一种体现.天学机构的管理日益加强,充分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当把知识视为一种权力,在管理限制上必有一些特殊.
1.3 宋代政府对天文官员的管束
宋太祖从开宝五年,就开始陆续颁布禁令.到了开宝九年,下诏“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11]385宋初开始收缴天文、图谶等书籍,并开始禁止私习天文,这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侧面反映.因为这些知识在古人的知识体系中,一方面被认为是“奇技淫巧”,另一方面却是通“天人之学”.所以当皇权强大的时候,势必会对其进行管控.而后宋太宗正式颁布了天文禁令.太平兴国二年“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十二月丁巳朔,诏以六十有八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12]416司天台即是司天监,是它的另一个名称.在《宋会要》中记载“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召司天台学生郑昭晏、石昌裔、徐旦、史序、束守吉等五人试于殿前,并授司天台主簿.”[6]3801这些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中也有记载,都是属于司天监的官员,所以他们应该属于同一机构.这些禁令使得天文学的权力正式收归中央,司天监成为主管天文学的主要机构.
除了设置司天监以外,宋代还设置了翰林天文院以制衡司天监.在管理上,则是愈加严格.在至道元年,十一月八日诏“司天监五官正磨勘,非次(至)改官至殿中丞(正)[止],以后只加检校官.”[6]3801这限制了天文官员中“磨勘”的职位,同时也限制了附加身份的给予.当然这主要是指五官正,而非限制司天监和少监.真宗时又限制“司天监、翰林天文院职官、学生、诸色人,自今不得出入臣庶家课算休咎”,[6]3801这对其活动和交流进行了范围限制,使得这个团体的人员更加禁锢自己的身份.
乾兴元年九月,司天监丞徐起上奏,希望以后天文官员的升迁可以依照京朝官的办法,但被驳回,并诏罢告示:“今后司天监及诸伎术官等,并不得依京朝官例磨勘”.[6]3802十二月又下诏:“司天监五官正不得依京朝官例差监库务.”[6]3802这两个诏令禁止了司天监按照京朝官的“磨勘”体系升迁,但两个诏令又有细微的差别,主要是限制五官正及其以下的官员,而司天监和司天少监不在这一禁令之下.然而这两个职位在宋朝又不常设置,而多以他官兼任,特别是以五官正为主.因此可以说,这基本上断绝了司天监官员转入京朝官的行列.这反映了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不断成熟,其他选官途径逐步断绝.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机构设置日益封闭化.
天文官员身份限制不仅愈加严格,而且其所掌握的权力也有所限制.对于司天监的官员,要求其“司天知星与气朔三式、周易等学”,[6]3801这是他们必备的一些知识.但仍然要求他们“仍令常勤学业,务在精通.”[6]3801更为重要的是精通.这项技艺较为特殊,所以在应对一些事项时,仍旧“承前有事,都令集议.”[6]3801要求他们集体商议,这也限制了个人的权力,加强了对天文官员的管控.而在另一条诏令中,更加严格控制解释权,诏“司天监自今后每详定公事,须依经据,不得临时旋有移改,仍取知委状以闻”.[6]3802对于特殊的事情,要言而有据,还要从经学中寻找相关的论据,从而限制了天文官员的解释权,同时也加强了管控.
宋朝政府在机构设置上,更加趋向职业化和技术化,这也是官僚政治体系逐渐成熟的一个必然趋势.对于其机构的官员来说,这也限制了他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制度层面已经对于其思想进行了规范,使其趋于理性化思考.
2 宋代天文官员的天文观念
2.1 宋代天文官员对历法的认知
我们不能探究到每一个人对于历法的认知,但通过这些人的观念可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特征.根据史书中留下的记载,通过分析这些人的认知,来构建一幅认知的图景.
宋朝的天文知识是承袭五代的,在思想史的发展上,五代和宋也是一脉相承的.宋初沿用的是后周王朴的《钦天历》.在《新五代史·司天考》中详细记载了王朴关于历法的一些认识.
王朴在他上表《钦天历》的奏折上谈道:“臣闻圣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变者也.人情之动,则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13]670天人感应仍是皇帝与上天沟通的渠道.如果与人沟通,用言语则可探知.而对于天道的变动,仍需用数来探究,这是圣人观天道的必经途径.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历法具有的神圣性,但同时又为皇帝沟通上天提供了渠道.所以他又谈到“是以圣人受命,必治历数.”[13]670这是历法制作的必要性.而后他在谈完历法的政治性功能后,开始对历法的组成部分进行谈论,从日月五星的运行、天文常数的设置到圭影的测验都有一一交代.
而与其同时代的王处讷,在后周时期曾有一次政变,周世宗要杀一些政敌,王处讷此时进谏“汉历未尽,但以即位后仇杀人,夷人之族,怨结天下,所以社稷不得久长耳!”[14]9443王处讷将历与国运联系到一起,以达到劝谏的有效性.历的社会功能性深入人心,则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历的认识.
在端拱二年的时候,《乾元历》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舛误.宋太宗下诏翰林张玭来禁中测验,经过一番测验,他回答道:“臣占荧惑明润轨道,兼前岁逆出太微垣,按历法差疾者八日,此皆上天祐德之应,非历法之可测也.”[15]1594他认为历法之所以预测不准,是因为上天的德祐非历法可以探知.
韩显符是制造浑仪的专家,在淳化的时候奉命制造了一台浑仪.制成之后,在书的序言中他谈到“是知浑仪者,实天地造化之准,阴阳历数之元”.[16]浑仪是探究天地阴阳历数之源,这是对于历数的一种可视化表示,是历代帝王知晓天意的重要帮手.而自伏羲以来上千年的历史中,“致使天象无准”,[16]主要是因为浑仪的制作不精良而导致的.于是“且历象之作,非浑仪无以考真伪”,[16]天文历象的变化,通过精密的仪器可以探知.
《崇天历》施行不久之后,便出现误差.周琮则认为“古之造历,必使千百年间星度交食,若应绳准,今历成而不验,则历法为未密.”[17]1678历法若有预测不准,则是历法设计还未精密.而后在神宗熙宁三年,因为望日应该定在哪天而发生了冲突.“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由于月球绕地球的公转轨道是椭圆的,加上太阳和其他大行星的扰动,所以“有时十六、十七圆乃至十四圆”,这都是有可能的.而周琮则认为“古今注历,望未有在十七日者”,[18]5200定在十七是不符合以往惯例的.这也反映了他观念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认为“天”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预测到的,但同时又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下周琮《明天历·义略》,从中可以探知周琮关于历法的认知.他交代了各种天文常数和一些测算方法,基本符合他的观点:“夫天有常运,地有常中,历有正象,表有定数.”[19]他认为天象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当遇到日月运动发生异常时,“则舒亟之度,乃势数使然,非失政之致也.”[19]这是规律使然,不要归罪于其他.但在关于日月交食的问题上,他则认为“交会日月,成象于天,以辨尊卑之序.”[19]这仍然是受到了传统天人观念的影响.
在天文官的观念中,关于历法精确性的认知,始终处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之中.一方面,在宋人追求“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宋人对于自然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接受专业技术知识训练的官员,对于自然的认知更加精确,认识到天是有规律可循而且是可测的.通过对“术”的推演而探知天意,成为这个时代天文官员的普遍心态.另一方面,传统的“天人感应”观念依旧是他们知识体系下的重要基础.对于自然的认识仍然逃脱不了束缚,一些反潮流人士提出的观念终究是少数,并不能成为把握这个时代的主流.徐凤先曾指出“宋代非常重视异常天象,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天人感应回潮.”[20]21-34而将历法与天人感应观念相结合,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这对于历法改革来说,无疑是添入了更多的非科学因素.
2.2 天命观下的历法改革
宋初刚开始用的是《钦天历》,这是王朝过渡性的产物.但很快就被《应天历》所取代,理由是“推验稍疏”.[21]此次参与历法改革的主要天文官员是王处讷,在后周时他便在一场政争中,利用“历数”的观念来劝谏周世宗,历法与正统是新王朝确立权威性重要的一步,王处讷也是深知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下,《应天历》应运而生,其在术法上,没有太大的改变.陈美东指出,“对王朴的若干创新点并未予理睬”,[15]这部历法没有继承前部历法的创新之处.更加表明这部历法是应政治需要而诞生的.王处讷也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制历的,追求的是王朝政治的合法性,而并不是历法创新和改进.
施行没几年之后,《应天历》“气候渐差”.[21]下诏经过四家制历和两轮测验,《乾元历》遂正式颁布.端拱二年宋太宗下诏让翰林张玭来禁中测验,由于五星校验中有一定误差,张玭则认为“此皆上天祐德之应,非历法之可测也.”[15]历法的社会化功能仍是它的重要特性.这部历法在术法上依旧没有进步,只是在数据上进行了优化.宋太宗是僭越上位的,颁布历法确认其权威性是他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天文官员,为了迎合皇帝的需求,只能进行改历.
真宗即位之后,命史序等人“考验前法,研覈旧文,取其枢要,编为新历.”[22]《仪天历》遂替代了《乾元历》,它在制定上,没有太多的创新成果.宋真宗年少即位,为了稳固皇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塑造皇帝的权威性.颁布新的历法遂成为其确立权威的一个重要手段.史序等天文官员仍然在数据和细节上进行了优化,这也是在“天命”观下的历法改革.
乾兴末年,《仪天历》见算又差,改历之议又起.张奎制定的历法由于真宗的驾崩而未颁布.与此同时,下诏楚衍和宋行古制定了《崇天历》.《崇天历》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前部历法的失误而颁布的,但也和真宗驾崩及新皇帝的即位有关.《崇天历》由于制定仓促,颁行当年便预报日食失误.周琮因此上言:“古之造历,必使千百年见星度交食,若应绳准,今历成而不验,则历法为未密.”[19]1694周琮深刻揭示了历法校订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尔后宋仁宗又下令对历法重新修订,经过五年的校验,使之正式颁行.
皇祐四年,《崇天历》月食不效,改历之议又起.在刘羲叟的反对后,此事不了了之.在英宗即位后,命周琮等人制定新历,三年后制成上奏.周琮指出“旧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23]周琮指出旧历的缺失,来说明此次历法改革的必要性.除了历法本身的问题,还有英宗的即位也是颁历的重要因素.英宗并非仁宗的儿子,继承皇位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所以确立权威性也是他很重要的任务.所以历法的改革也是受到“制天命而用”的影响.而后历法进行了四家竞争,经过了严密的校验,《明天历》最终胜出.
3 结语
五次历法的改革都是有明确的技术因素,但同时也掺杂着复杂的非技术因素.一方面,由于皇权不断地加强,对于历法这种特殊的知识把控愈加严格,其社会性功能愈加受到重视,“制天命而用”的思想成为历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面,天文官员对于“天”的认识愈加趋于理性,认为“夫天体之运,星辰之动,未始有穷,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则差,差则敝而不可用,历之所以数改造也.”[19]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将历法改革视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使得更加理性对待其出现的误差,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来使得“合天为历本”.在这两种观念的交织下,使得宋代天文官员在历法改革中反复踟蹰不前,既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又认识到历法改革的必要性.科学的进步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频繁的改历使得历法的科学性无法提高.但为了应付改历,只能在数据上进行优化,使其有所进步.当然,宋代历法缓慢的进步为之后元代《授时历》的成功制定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