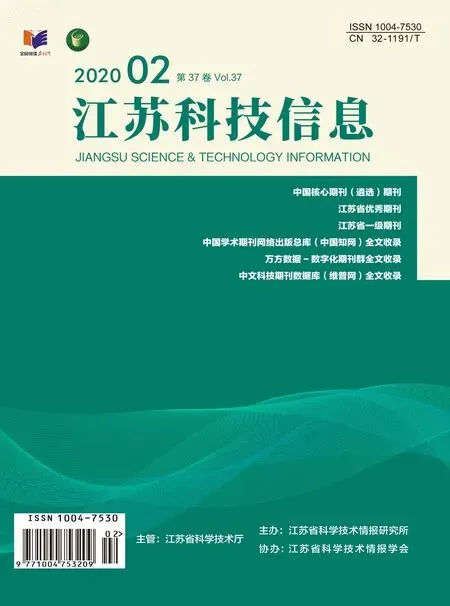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研究
2020-03-02木丽迪尔阿哈提
木丽迪尔·阿哈提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1 我国著作权归属的现行规定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著作权人包括:(1)作者;(2)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然人是作者最基本的形式,而具有作者资格的常见种类还有法人等其他形式。在法人工作的概念层面,有必要主观和客观地参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作品创作。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作者的身份越来越复杂,但第一个标准是作品的署名。著作权归属的问题我国著作权法有明确规定,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此外,我国还规定了特殊的版权所有权,如委托作品和合作作品。一般来说,我国的著作权所有权是基于作者和签名,并以作品的创作为基础的。但是创作背景的差异直接影响创意主体的定位和人工智能创作环境中著作权所有权的识别。
2 人工智能对现有著作权制度的挑战
2017年机器人阿尔法狗连胜围棋界诸多高手的事情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机器人阿尔法狗不败的战绩不禁让人感叹人工智能的强大,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特别广,不仅在围棋领域可见,而且在音乐、文学、艺术领域中也可见其身影,甚至在医疗卫生、人脸识别、数据分析领域都承担极为重要的责任。腾讯公司的“Dreamwriter”可以在不到1 min的时间内完成超过900字的新闻稿。在接受一张图片之后,微软的小冰可以快速地结合图片表达的意思完成一首诗[1]。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完全与人类分离仍然是不确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创造中人类的辅助色彩更为鲜明。其次,人工智能创作内容是特殊的。在工业革命期间,人类用机器取代了人力资源,以加速材料的生产。今天,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人们用高科技设备取代了人工分析和处理信息,更有效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法人被写成“人”,那么人工智能著作权的内容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外,目前人类创造的速度无法与人工智能创造的速度相比较,因为人工智能创作的速度也比较特殊。人们担忧如果赋予人工智能创造版权,人类创造会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并且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3 人工智能主体成为独立法律人格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应当满足两个条件:分别是社会存在和法律确认。这就要求人工智能作出表示,不仅要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且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要对现有的人工智能进行分类,第一类是人类的工具,它们是以人类算法为依据,完成特定任务的人工智能软件;第二类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是否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人工智能,因为它具有自主创作的能力。学术界的熊琦教授[2]认为,人工智能中的“智能”指的是通过机器学习,从数据中整理和发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并以此作为未来内容生成或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人工智能应当体现价值判断和推理[2]。由此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具有超越人类的计算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但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因此,人工智能代表设计者的理念,不能作为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存在。著作权法中,作品判定的条件和权利归属的定位都具备作为人的权利主体的要素,因为权利客体的源自权利主体。在作品判定要件中,著作权法要求作品必须是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的独创性表达。郑成思先生认为《伯尔尼公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版权作品限于人类创作的作品,但其提及“作者”的各个条款都暗指自然人[3]。简言之,作品须为人类的智力成果[4]。
4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著作权的相关认定
4.1 域外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著作权的相关实践
日本著作权法将著作物定义为“思想和感情的创作性表现”,当人工智能创造出几乎没有人类参与创作的作品时,力量很难保护。考虑到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可能受到侵权等因素的影响,阻碍人工智能投资者进行投资,日本将研究并且制定新的法律。在日本,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人工智能著作权属于谁,只是说这些作品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
在美国虽然著作权局将程序员列为著作权所有者,但它将计算机软件列为作者。换句话说,美国将人工智能创作的版权归功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而在1993年之前,至少有两个由计算机软件创建的作品已经由美国著作权局注册和保护。就现实而言,如果美联社的新闻是通过人工智能完成的,则表明该报告是由人工智能产生的,然而著作权属于人工智能的开发者。
4.2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著作权的相关认定
人工智能是第一次权利分配,而人工智能生成物是第二次权利分配,二者概念不同,差异巨大[5]。假如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构成独创性的作品的可能,那么著作权应当如何归属,学者们众说纷纭。研发者、使用者、拥有者、共同作者、对工作中创出的作品各抒己见。第一种观点提出,设计者投入脑力劳动然后使用计算机等智能机器创造出了计算机程序,此项设计为人工智能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生成物的著作权应当属于设计者。第二种观点提出,计算机等智能机器仅对创作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它没有主观能动性,所以没有自己独立自主创作作品的能力,因此,操作它的人才具有生成物的著作权。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将人工智能视为意志创作的人,可以从法人工作系统中学习到,所以著作权属于人工智能的拥有者。而第四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设计者和操作者共同创作的作品,因此著作权属于二者所有。还有一些人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觉得把作者当作人工智能的主体与人工智能创作出来的生成物有理念和制度的冲突和困境。“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说”得出结论:除非著作权法有特别规定,反之谁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有了作品,那么谁就是作者并且享有著作权[6]。“著作权归属创作者说”从具体法规中认识到,谁创作了作品则谁为作者并且享有著作权,除非有其他的规定。如果没有反驳此理论的依据,则作者是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于人工智能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因此只要操作人参与了生成过程,不管参与了多少,尽管只是简单地启动人工智能操作程序,也应该把这个生成物看作操作者的创作物来处理。因为目前为止还未出现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创作的人工智能。还有与上述那些观点截然不同的情况,就是如果在自己职务中创作的作品和在别人委托下创作的作品应当如何归属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职务作品如何归属著作权“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简单来说,如果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作者的身份定位是使用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工作人员,他创作作品是一个工作任务,那么生成的作品则属于职务作品[7]。我国著作权法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委托作品如何归属“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根据上文提出的第一种观点,笔者持怀疑的态度。如果没有基础数据和原材料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是无法自动创作任何东西的。虽然人工智能设计者提前设定了计算机程序的一切数据,然而像数据和要使用的材料是时刻处在变动状态的,人工智能设计者不可能预测所有产生的结果,因为这不符合作品创作的基本规律。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会变化的,例如新闻事实、新的图像等一系列新的事物,所以要杜绝一成不变,学会创新、与时俱进,否则生成物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归根结底,设计者所创作的产物仅仅是他人创作时使用的机器。设计者虽然可以对设计的人工智能通过取得著作权,回收当时设计时所花费的成本,但却也阻断了其他使用人工智能创作后可以获得的权利。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操作者和所有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在雇主合同关系或者委托合同关系中他们的身份会发生改变,以致于著作权归属于雇主或者委托人。原因在于他们只把人工智能当作工具来使用,这样的想法太片面。同样有片面之处的是人工智能的投资者,人工智能的投资者投资了人工智能开发和其生成物的创作[8]。当投资者身份定位发生改变为委托人身份或者雇主身份时,可以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确定其身份,无需大费周章。不仅人工智能的共同作者有设计者的缺陷,而且投资者也存在不足之处,对于这种情况,应当明确其身份定位,针对自己的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的法律规定认定著作权的归属。
5 结语
人工智能是有利有弊的。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能够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它不但可以进行文学、音乐、艺术方面的创作,还能进行发明创造。这个现象已经对人类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的位置,并且已经对人类的著作权制度造成极大的冲击。但是如果不对人工智能进行制约,任由其发展,失控的人工智能会打破稳定的社会环境,冲击著作权。笔者认为,虽然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水平,但是实际上体现出的仍然是人类的价值观。不管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工智能著作权制度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制定时,应当把人工智能当作工具来看待,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提倡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如果出现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著作权问题时,要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合法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