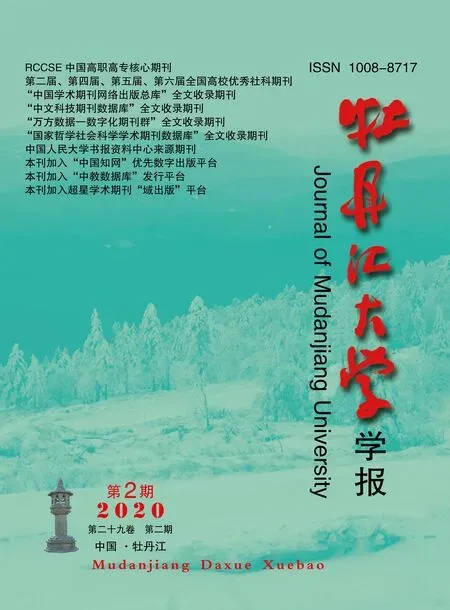“美”与“善”并存
——关于审美无功利性中的功利性思考
2020-02-27吴迪迪
吴迪迪
(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在西方美学史上,审美的功利性和无功利性一直是各家争论的焦点。审美作为一种包括感知、想象、情感、理解在内的复杂心理活动,亦称“审美活动”,就其本质而言,它确实是超越一切利害关系的纯粹精神活动,是不涉及概念和目的的,是无功利性的;但是人作为审美活动的主体和参与者,审美活动即有关“人”的审美和情感体验过程,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审美活动,是因为人与审美对象之间建立了“诗意联系”,没有这种“诗意联系”也就没有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当然也就没有美。而这种“诗意联系”的建立,不管是来自于对物质利益的驱使,还是来自于对精神世界的关照,都包含有一定的目的性在其中。也就是说,审美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因为有主体“人”的参与,所以必然有功利性存在。因此,完全不关乎功利的审美活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功利性只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初衷和最高理想,而实际的创作必然是夹杂着各种功利性的目的在其中,即审美活动就是人的功利性活动。
一 、无功利的“美”
审美的无功利性作为康德美学的重要思想,它是康德在继承并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康德认为“美”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审美情感的无利害性,而所谓无利害性就是无功利性,它是不与对象实存相结合的愉悦情感。这种愉悦情感不是以存在为依据,也不是以概念为目的,它不同于感官上的享受,也不同于道德上的满足,是一种纯粹的超乎官能和理性的无利害的愉悦,无关乎人的实际欲望。因此,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摒弃了对物性的占有欲望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审美只有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获得,并且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内在关照而获得,而是通过其外在的客观形式所获得,即形式是使审美主体产生美感的核心。例如绘画、雕塑或建筑,它们的美不在于本身是什么或者内在传达了什么,而是在于它们通过色彩、线条或造型展现出来的给人以直接的、纯粹的审美视觉上的冲击感,不需要借助思考和想象,是主体自动化地生发美感。显然,康德的这种美只能局限于类似于绘画、建筑和雕塑等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而自然美和文学作品等的美则显然被排除在外。同时,对于形式的过分推崇,而忽视内容,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的误区。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和行草书法可以说是对形式美的艺术实践的尝试。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人生悲剧最多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的精神最自由、最解放、最浪漫的时期。即使贵为王侯,生命也可能会受到威胁。为了排解内心的苦痛,人们选择许多“外化的形式”,其中“有药”,“有酒”,有玄谈,有艺术。晋人对美的“一往情深”的追求,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形式美的“标本”。[1]注重内容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主流美学思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追求形式美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取代,但是这种唯美的艺术形式和非功利的美学思想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很快就受到来自正统儒家思想的各种声音的排挤和反对,最终失去了主流地位。诚然,形式对于艺术很重要,尤其是对于类似绘画、建筑和雕塑等的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而言,形式美是使观赏者获得美感的直接且重要途径,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形式,而是艺术家通过色彩、线条亦或文字等“有意味的形式”向欣赏者所传达的思想。创作者创作作品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在自然或不自然地渗透自己的思想和意识的过程,而欣赏者或读者的接受作品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借创作者的思想寻找共鸣或获得精神的释放和灵魂的升华,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善”,是关乎利害的。也就是说,审美的本质和创作者的初衷是实现它的超功利性,但是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却总是直接或间接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和功利相关,即完全无功利倾向的审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审美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之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它具有充分实现人的心灵解放的效果。就其本质而言,审美是对“人的存在”之“审”,质言之,它是人的体验外界客体的一种感悟过程,是审美主体即人对“美”的一种领悟过程,其发生前提是审美主体的独立存在,而后才有可能使审美客体即“美”的对象“主体化”,经过审美体验后的主体因此得到自由的提升,其生命也得以“美化”。审美主体这种经由审美而转化为“诗意栖居”的生命存在的过程,就是一种基于现实功利又终于超越功利的体验活动。[2]实际上,审美的无功利性是对其功利性的一种反思、拓展和超越。审美的无功利性强调的是对审美现实功利性的超越而绝非对审美自身内在的功利性的否定。
二 、有功利的“善”
在康德看来,“美”是纯粹无利害的,而“善”则是利害的。无论是间接的善,还是直接的善,其中都包含有一定的目的性在其中,即利害关系,审美活动作为主体人参与的活动,它包含着人的各种欲望,因此是一种有功利的“善”,而人们通过艺术不仅体现出对精神的需求、对政治的反映,还可以间接地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可见,审美实际上就是有功利的各种“善”的融合。
(一)精神的“善”
人作为一种有思想有意识的高级动物,他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就在于,他不仅有对物质需求的欲望,也有对精神需求的欲望。也就是说,人需要面包,但又不止需要面包,人在面临生存问题之外,还面临着诸多精神世界的问题,而艺术一定程度上正是人们这种需要的解决,艺术的审美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之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它不仅具有充分实现人的心灵解放的效果,还能唤起审美主体的内心意志和希望。正如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和庄子的“乘物以游心”,虽然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大美”境界,可也有功利性的目的,就是从道的观点,争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艺术的美就是功利的“善”,它不仅是我们生存的需要,更是我们生命的需要。相对于物质的直接功利性而言,艺术审美的间接功利性使它在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上显得不那么重要,因此一些人认为“没有艺术也照样生存,人类在没有艺术的情况下将不会失去很多”[3]。人们一再地强调物质的重要性,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却从来不敢去想象没有精神、没有艺术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一直知道,音乐所不能预防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世界里没有音乐将会是怎样的。”[4]艺术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它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我们没有去感受也并未意识到,但这却并不影响它的存在。物质需求固然重要,但精神需求也必不可少。尤其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在享受物质带来的刺激和快感的同时,也在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的挑战,孤独、恐慌、暴躁、消极、沉沦等成为当下人的共同精神状态。身处这个消费时代,表面上我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束缚,通过各种形式来寻找生存的意义和美的价值,但实质上现代文明所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快节奏的生活本来就使人紧张忙碌、疲惫不堪,来自现代文明下的住房压力、结婚压力、升职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诸如此类的烦恼、恐惧、忧愁的层出不穷加剧了现代人的心理失衡,加之各种原始野蛮和暴力变相显现出来,在这个消费品充斥的市场,人们渐渐迷失了自我,找不到生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相比物质匮乏所带来的肉体上的饥寒交迫,精神和心理的极度空虚和无助更让人痛苦,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找寻各种方式的艺术,并借艺术的内在审美来缓解和释放内在的紧张、恐慌和寂寞等情绪。因此,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艺术形式,之所以被欣赏者所青睐就在于审美主体从中可以找到共鸣或者得到精神和心灵的抚慰。
(二)政治的“善”
中国文化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同时也是最讲求实际的,具有高度的社会意识性,这就要求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学、艺术等,都要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道德价值,本质上都是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反映。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绘画等艺术都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一时期的政治生活状况。例如从杜甫的“三吏”“三别”《丽人行》以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当时人民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侧面也暗含了社会的黑暗不合理和国家的岌岌可危。北宋张择端的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表面上看它描绘的是都城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依曹星原的看法,在这盛世图像之下,却暗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用意,创作者之所以选取一条即将穿过虹桥的船作为整幅画的中心,就在于想通过把撞船的危机植入其中,来揭示出在向皇后秉政时期大家要同舟共济的主题。不仅绘画,服饰也是某一时期政治生活的晴雨表。唐代女子的着装“慢束罗裙半露胸”,以及“浑脱帽”和“时世妆”的流行,这不仅展示了唐朝人的思想开放,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唐朝当时的对外开放和兼收并蓄政策。文学艺术有时又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反映,它更要为政治服务。《诗经》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是从最初编纂和收集的目的来看,它只是统治阶级为了解民情和进行歌功颂德的一种手段,最终服务于政治。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以及“文艺为千千万万工农兵服务”的观点,更是明确表示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红色文学”正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且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虽然这些作品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甚至文学性不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士气,鼓舞了信心,是当时特殊时期的精神支柱,也是当时政治局势下的必然选择。当然,文学艺术替政治代言,这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西方也如此,贺拉斯提出诗要寓教于乐,即不仅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柏拉图从国家利益和人生的角度出发,要求文艺作品要有益于国家和人生,只能表现真、善、美的东西,禁止有害的文艺作品在社会上流传,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等。可见,文学艺术不仅是有功利的“善”在“文以载道”和“寓教于乐”的传统思想的统治下,它还往往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连。
(三)物质的“善”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一种,它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直接实用性,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间接精神性,即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安慰和满足。正如创作者在创作之初本是想表现纯粹的无功利的审美,但在创作的过程中却总是无意识地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文学艺术本身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它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但它却可以变相地带来经济利益,即它的存在本身是直接精神性,但却间接地产生了经济利益,即间接物质性。从文学的起源来看,一般认为劳动是文学发生的起点,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5]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了原始歌谣的产生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在产生之初,只是原始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发出“杭育杭育”的声音来摆脱沉重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的一种情感发泄,而情感的发泄则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劳动的继续。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可见,文学艺术从产生之初就不是单纯的精神性的产物,它是劳动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当下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更是把文学艺术也纳入到了商品市场的体系中来,文学艺术已不单纯是创作主体或审美主体的精神依托,它也是商品,供人们消费,对消费主体而言,他们消费金钱以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不同于以往的消费有形的物质商品,现代人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去消费感情、消费希望、消费梦想、消费寄托,因为艺术可以让他们从中找到共鸣,获得情感上的发泄和精神上的安慰。对创作主体而言,艺术已不是独属于艺术家的艺术,它不仅需要欣赏者,也需要消费者,艺术家的创作经过商业市场的运作,获得了一定的受众,也就等于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获得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创作主体的创作积极性。因此,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类似于绘画、音乐、电影、服装等艺术,都不仅讲求内在的思想价值,也注重外在的商业包装,因为被纳入市场体系中的文学艺术活动实质上就是买卖双方的交易活动,商业包装作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商品的知名度,进而使其获得更多的受众,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交易活动,一般的交易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它则更多是为人们的精神需求服务,因此艺术创作既不是文化商贾借助艺术的外衣赚取商业利润的手段和途径,也不是专属艺术家的被束之高阁的精神替代品。真正的艺术应该是精神的“善”和政治的“善”以及物质的“善”的融合。
三、关于审美趋势的思考
审美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它不仅如康德所说是纯粹无功利的,同时也包含着诸如精神性、政治性和物质性等各种功利性在其中,它是“美”与“善”并存的综合体。它是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的精神家园,反映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同时它也无意识地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当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业成分的注入,人们对物质的重视远高过对艺术的关注,艺术所带给人的精神价值已被经济效益、娱乐效果所取代,商业成分的加入使它逐渐地去精神化而呈现出物质化的特征。诚然,审美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政治、经济等密切相关,但是过重的商业包装和娱乐色彩却使它沦为艺术的空壳,毫无思想而言,没有思想的艺术就不是好的艺术,这正如现代雕塑之父罗丹所表示的:不仅在艺术中一切都是思想,艺术的整个美来自思想,来自作者在宇宙中得到启发的思想和意图。而且整个审美文化都以思想为核心,就像“美丽的风景所以使人感动,不是由于它给人以或多或少的舒适的感觉,而是由于它引起人的思想。”[6]可见,艺术之所以是美,不是因为形式,而是因为所传达的思想。裸体艺术的盛行不在于它满足了观赏者的性欲和冲动,而是在于它打破了世俗的审美传统,表现了对身体和性的关注,传达了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思想。而如今人们对于审美活动的认识则完全流于形式层面,忽视了审美精神层面的重要性。例如很多人穿衣打扮追求时尚,甚至为了时尚去一味地复制和效仿,但这显然不是真正的时尚。真正的时尚是审美的时尚,是包含主体内在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感受以及审美判断的特殊审美现象和审美行为方式。例如旗袍在中国叫时尚,走出中国就不一定是时尚了,同样,比基尼在西方叫时尚,在中国却不一定是时尚。时尚有一定的文化生存背景,它包含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审美思想传统,旗袍的温婉典雅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内敛含蓄的传统思想,而比基尼则体现了西方人的热情大胆。显然,艺术不是简单地复制模仿,但它也不是一味地“泛个性化”,文学作品讲求适当的“陌生化”效果,适当的陌生可以增加审美难度,唤起审美者好奇和体验的欲望,但是过分地注重新颖独特和与众不同,只会被归为异类,最终因为没有受众而被市场淘汰。商业的参与,不仅使艺术在与市场的竞争中退于边缘地位,使审美主体个性缺失或“泛个性化”,同时,作为艺术的创造者艺术家也被迫被纳入消费市场,艺术的物质性超过了精神性,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艺术,而是娱乐大众的艺术,为了去迎合观众,艺术家成为了卖笑者,成为了供大众娱乐消遣的对象。作为审美的创造主体也由原来的精英立场向大众立场转变。比之艺术看不见的精神价值,它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更具有刺激性、直接性和时效性,也更能激发创作者的创作欲望,这就使得艺术家不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生存而艺术、为利益而艺术。当下的文学艺术已绝少是真正的审美活动,而是文化商贾和政客借艺术的形式赚取高额经济利润的工具,它正在被商业化、形式化、流行化,美的文学艺术固然不是要被束之高阁,但也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一味的媚俗讨好只会失去它的本来意义,没有美感的艺术注定只会是昙花一现。消费时代的到来,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充斥眼前,加之金钱、名利、权位、等所带给人的福利和荣耀,面对诱惑很多人难以抵挡,在这个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中,人们渐渐迷失了自我,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对于审美将最终归于何处的问题再次受到了重视。但无论时代怎样发展,社会怎样变迁,只要人们秉承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和功利观,处理好精神、政治、以及物质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商业主义盛行的当下,人们就不会丧失真正的艺术,也只有这样,我们在追求审美的过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审美价值,从而不背离艺术的本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