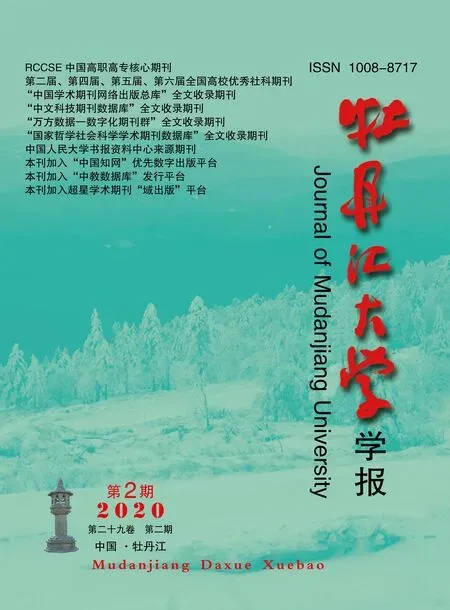粉墨春秋难入画
——元杂剧底层叙事特质探析
2020-02-27张建华
张建华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榆林学院文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元杂剧是一种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形式而形成的成熟的戏剧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散韵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与元代散曲并称为“元曲”,为有元一代之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它故事来自民间,曲词宾白源于民间口语,外形俚俗,内容充满火药气息,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正平和的审美要求,故而是一种反叛的文学。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反主流文化是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①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士人一向以文为重,诗为二,词次之,戏曲小说之流,则为不受重视的末流。然因为时代更替,社会环境及经济状态的变革,文士无法超越前朝之文学,且文学自身嬗变的历史亦复杂多变,故元杂剧不但产生而且大兴于天下,王国维先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②说明历朝士大夫对于市民文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因为在形式上挣脱了传统的束缚,而在内质上却又贴合了传统儒家道德理念,元杂剧有意无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个链条。
元曲是元代的精魂,构成元代精神精髓的两大纬度就是元杂剧与散曲,如果说散曲主要以精细的刻画和朦胧曼妙的意象取胜,可以以“雅”一言蔽之的话,杂剧就是以俗为尚,以热闹的场面和曲折的故事取胜,是一种典型的“俗”文学。简言之,是以反映底层人民生活为主体的写作行为,也是以下层社会民众为主要接受对象的一种书写行为,故暂以中国古代的“底层叙事”称呼之。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把文学——产生的过程总结为四个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纬度,即社会、作家、作品、读者。③本文即以此四个纬度为纲梳理元杂剧表现出的底层叙事特质。
一
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说:“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变革是导致文化转型的媒介,文化转型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主流文化(主体的生活方式)的位移。在元代,这种位移的完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独尊,另一是俗文化取代雅文化。而这是元王朝在思想文化上独立于此前历代中原王朝的主要特征,从深层意义上说,它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对内陆农耕文化及其思想观念强力冲撞之必然结果。”④
正如徐教授所言,作为元曲里面代表“俗文化”的杂剧,从先秦两汉古文及诗赋之中另辟蹊径脱颖而出,这种位移是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撮其要者有四:
(一)元杂剧是时代的产物:元朝一统中国,且西藏正式成为我国版图一部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非常频繁,这无疑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但是元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蒙古灭金初期,除劫掠财物、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使其为奴,并分封土地给蒙古贵族,封地内的人民不许随意迁移。而汉族豪强地主则乘机组建军队,投靠蒙古人,为虎作伥,欺压百姓。蒙古人将治内百姓分为四等,制定了强硬的法律、政治、经济条文以约束百姓,在蒙古人和汉族豪强的双重压榨下,民不聊生。人民急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疏解郁闷,元杂剧对于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和官府贪暴腐朽的描绘,正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放映。
元代统治者蒙古人长期游牧郊野,以武为尚,个性豪放,自然更喜天然真纯的杂剧,而不喜欢咬文嚼字的诗歌散文,掌握着话语权的统治阶层喜爱和推崇杂剧,自然成为杂剧兴盛的一大动因;我国戏曲艺术自原始社会农业歌舞萌芽至春秋战国巫觋俳优,从汉百戏到唐参军戏,从北宋杂剧到金院本,本身经历了从萌芽到逐步成熟的历程,至元代构成戏曲艺术的各项因素已充分发展融合,且宋词至此本已余响渐灭;且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也是一部充满家国悲欢的灾难史,百姓流离,生灵涂炭,其中自然有若干离奇故事可以演绎,为杂剧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艺术养分,而宋词的容量亦不足以叙述如此庞大的故事内容。故此,元杂剧可谓时代之必然。
(二)文人的分化及位移:中国文学体裁的发展素来先自民间而至文人创作。元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元初尤盛。科举被废,士人失去仕进腾达的途径,许多文人系由宋金入元者及其后代,蒙古统治者为达到分化各族人民团结的目的,将当时市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政治、经济上都规定了不同的待遇。文人本被家国之思所害,且又流离颠沛,加之受人欺辱,境地与下层百姓相差无几,因此,颇多文人流连市井,聊以抚慰心灵之忧,且因之与民间艺人呼朋引伴,既接受底层艺术的熏陶,也把自己的盖世才华用于杂剧创作,粉墨担当。下层失意文人的大量加入成为作为俗文学的杂剧花开朵朵的巨大推力。
(三)城市经济的发展:宋金元城市经济繁华一时,柳永、秦观、苏轼等人的都市词可以佐证。城市繁荣,为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及市民的文化需求,南北各大城市勾栏瓦肆星罗棋布,作为都城的杭州、大都、开封等地尤为繁盛,关汉卿描述当时的都市繁华曰:“满城中秀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时中定(今济南)、太原、平阳(今临汾)、京兆(今西安)、彰德、涿州、汴梁(今开封)、泉州、温州、苏州、广州等地,工商业兴旺,印刷业比较发达,为杂剧的兴盛和发展准备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同时,村野茅乡亦常有戏曲演出,现存晋南的壁画与舞台便可追踪溯源。节日、庙会皆可粉墨登场,一些著名演员也常常到各地作客演出,这就为杂剧的兴盛与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元朝疆域扩大,交通发达,国际国内各民族之间交流密切,特别是北方各民族乐曲的传播,对元杂剧的兴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已为杂剧这种市井文化的发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二
从作家这个纬度切入,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元杂剧作家,都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失意文人,明胡侍曰:“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⑤他们将百姓的疾苦和自身对于时代炎凉的体验融入杂剧创作,甚至亲敷朱粉,演绎悲欢,成就了伟大时代的伟大艺术。这一时期的作家,非但有名望者众,无名可考者亦不在少数;风格多变,主题各异。
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有八十余人,可分为前后两个创作期;有据可考的作品,有五百多种。从现存一百多种元杂剧⑥和钟嗣成《录鬼簿》、夏庭芝的《青楼集》等资料看来,元杂剧最兴盛的时期是在前期,也即元世祖到元成宗元贞、大德时期,这时期产生了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他为我国的杂剧留下了经久不衰的艺术珍品如《窦娥冤》《单刀会》《救风尘》《金线池》等,同时的王实甫、康进之、纪君祥、石君宝、马致远、白朴等人也为我们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从各个层面反映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歌颂他们的反叛精神与战斗意志。
这一时期杂剧主要活跃在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录鬼簿》所载“前辈名公才人”五十六人,皆为北方人。这是由于南宋以来在政治上长期南北对立的结果。
元代前期杂剧作家因为上文所述科举无门等原因,长期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熟悉他们的生活,并且这些作家本身状况堪忧,故此体验更加深刻。他们的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真实而鲜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见证者。
据《录鬼簿》与《辍耕录》记载,关汉卿与著名杂剧家杨显之、散曲作家王和卿是挚友,还和著名杂剧演员朱帘秀有交往。当时北方的杂剧作家高文秀有“小汉卿”之称,而南方戏剧作家沈和甫被称为“蛮子汉卿”,可以想见他在杂剧界的地位和影响。
同时代还有另一位杂剧作家王实甫,《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中原音韵》皆有收录。有关王实甫生平资料较少,从他的作品《破窑记》中流露的“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的思想和在《丽堂春》中抒发的宦海升沉的感叹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仕途失意的文人。明初贾仲名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显然他也是一个熟悉当时勾栏生活的剧作家。
这些底层文人的亲历亲为,无疑是元杂剧底层叙事特质产生的最佳资本。
后期的元杂剧由北方转到南方,由于南方偏安一隅,在历次战乱中受害较轻,蒙古人统治中原后南方人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故他们创作的杂剧在艺术价值及战斗精神诸方面皆有所削弱,有姓名可考者约有二十多人,有作品流传下来的也不过十几人,此后,元杂剧逐渐式微了。
三
再从作品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元杂剧反映现实主题之多、内容之丰富多彩、语言之灵活皆已臻顶峰。
从作品主题来看,元杂剧有历史剧、爱情风月剧、社会公案剧、神仙道化剧。
试看关汉卿今存杂剧作品,有历史剧《哭存孝》《单刀会》《西蜀梦》《陈母教子》《五侯宴》等, 有社会公案剧《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绯衣梦》等,有爱情风月剧《救风尘》《谢天香》《金线池》《玉镜台》《调风月》《拜月亭》《望江亭》等。他的旦本戏多为下层妇女申冤张目、叫好喝彩。《窦娥冤》描述了一个孝顺、懂事、隐忍、美丽善良且完全符合封建礼教教条的女子窦娥被封建礼教所杀,愤而反抗为己伸冤的故事,这个社会最底层挣扎的美好灵魂被黑暗无耻的社会吞噬,正因为其冤屈至深,其发下三桩誓愿才如此合情合理感天动地;《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的主人公是三个风尘女子,并围绕这几个光彩夺目的角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下层劳动人民形象,三个主角虽沦为娼妓,但是其重情重义、智勇双全,是受侮辱受压迫的劳动群体当中焕发耀眼光芒的经典角色——从中可以看出关汉卿的视野是倾注于何种方向的,这是典型的底层写照,典型的早期底层叙事作品。
从内容看,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歌颂人民反抗斗争、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残暴、反映当时尖锐阶级矛盾的作品。如《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等。
在这类作品中,凶狠、愚蠢的压迫者和善良、正直的被压迫者总是壁垒森严地对立着。作品不仅写了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而且还写出了他们之间思想意识上的明星对立,比如窦娥认为“人命关天地”,她的冤屈呼声可以惊天动地,而在昏官桃杌看来,“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他笔下的贪官污吏、流氓恶霸尽管开始时都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最后总逃不出正义的惩罚。
第二类作品是描写下层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突出她们在斗争中的勇敢和机智。那些貌似强大的恶棍,在他们聪明的对手面前,一个个被簸弄得像泄了气的皮球,因此作品也带有更多的喜剧意味。其中以《救风尘》最为典型,此外还有《金线池》《谢天香》《诈妮子》。《拜月亭》《望江亭》虽不是写下层妇女,却写了战乱流离、落魄书生,风格还是相近的。
第三类作品是歌颂历史英雄的字句。以《单刀会》的成绩最为突出。作者通过对历史英雄关羽维护汉家事业的歌颂,一定程度上流露了民族感情,同时也描写了他对敌斗争的勇敢和智慧,鼓舞了人们向压迫者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其他如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分别借离合之情述沧桑之感,借对历史事实的回溯改编来抨击鞭笞当时社会,亦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高文秀的《双献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尚忠贤的《柳毅传书》、李好古的《张生煮海》以及杨显之的《潇湘雨》和《酷寒亭》、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和《曲江池》以及《紫云亭》、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青衫泪》和《荐福碑》、郑廷玉的《看钱奴》、武汉臣的《生金阁》、李行道的《灰阑记》、孟汉廷的《魔合罗》、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昊天塔》《赚蒯通》亦是民间流传甚广的杂剧作品。
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有着底层社会劳动人民最美好的品质,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命运的漩涡挣扎哭号,关汉卿在塑造他们时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赋予他们绝不屈服的灵魂和战斗不止的精神,使他们始终如同寒夜里的光芒,照耀着后世的劳苦大众前进的路。
再从作品语言来看,元杂剧语言是以北方民间口语为基础写成的,并且吸收了民间文艺的营养,具有质朴自然、生动泼辣的特点。关汉卿非常注重用“本色”的语言来突出人物形象,真正做到了“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⑦的地步。试看其《金线池》第一折[混江龙]曲:
无钱的可要亲近,则除是驴生戟角瓮生根。佛留下四百八十门饭,俺占着七十二位凶神。才定脚谢馆迎接新子弟,转回头霸陵谁识旧将军。投奔我的都是那矜爷害娘、冻妻饿子、折屋卖田、提瓦罐爻槌运。那些个慈悲为本,多则是板障为门。
这段曲文,生动泼辣,毕肖妓女杜蕊娘的身份和口角。我们再来看看《窦娥冤》一段很普通的说白:
(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
这些语言出自窦娥这个封建小媳妇口中,贴切自然,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宛若生活本身现身剧中。
四
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消费指的是人们用文学作品来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过程,也即文学阅读或文学欣赏。”⑧这个“人们”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在古代,文学创作者大都有自己熟悉的固定的消费对象。民间艺人的消费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左邻右舍,而宫廷文人的作品则主要针对达官贵族。元杂剧亦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元杂剧的消费者,或者接受者。
元杂剧的消费群体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类:普通百姓,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在城市经济蒸腾如云的背景下,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欣赏这些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戏剧故事,从而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通过别人故事的紧张曲折来宣泄自己内心郁积的垃圾情绪,或以史为鉴,为自己的斗争寻求新的出路。王俊德先生说:“异族的统治给元代心灵造成了创伤,必然使他们在潜意识中得到修复、补偿,也必然使他们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统治者的敌对情绪。”⑨
第二类:失意文人,下层文士,杂剧创作者群体。“对社会的否定和敌对情绪,使元杂剧作家们远离了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而是在笔尖上刻意发掘着现实社会种种阴暗的主题,借以宣泄他们对那种冷酷生活环境的不满和愤懑。”⑩这一类消费者有更强烈的兴衰之感,有更敏锐的家国触角,他们往往鉴古烁今,从古代文献中汲取素材,从现实社会中找到灵感,演绎铺陈,另敷新篇。如《窦娥冤》原本《东海孝妇》,《赵氏孤儿》原本《史记·赵世家》等等。他们组成了著名的“玉京书会”,互相切磋交流技艺,互相欣赏新作,杨显之是关汉卿的挚友,关每有新作,辄乞为正,故有“杨补丁”之雅号,可见杨显之非常善于修改杂剧。这一类消费者的消费就带有形而上的意味了,既排郁解闷抒写心中块垒,又欣赏满足自娱娱人,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消费。
第三类:元朝贵族统治者。这些群体如前所述,早期统治者本身来自草原游牧民族,不惯汉族文化中典雅中正的诗词歌赋,天性喜欢不受约束的俗文学,因此元杂剧也成为他们的案头新宠和梨园至爱。而且有的消费者还从中寻找治理和愚化百姓的“良方”,从而推动社会,或者造成新的阶级矛盾和对立。这些接受者们虽然并非下层,但他们曾经是下层群体,且如今矛头所向,是水深火热中煎熬的百姓。
每一类接受群体在阅读和接受过程中也有复杂的动态心理过程,这也可以成为我们观照的对象,只有读者最后完成的作品才是一部完整、有生命力的作品。
人们在接受《窦娥冤》时,首先会由衷喜爱窦娥这个集美好善良与坚强于一身的女子,并对糊涂的蔡婆婆产生怨恨,同时刻骨厌恶张驴儿父子和贪官桃杌。而《单刀会》关羽出场后,大部分观众就会产生豪气干云、热血沸腾的感觉。再如《蝴蝶梦》中,包待制听了王母的诉说,就向张千耳语,要偷马贼赵顽驴为王三替死。这一带有关键性的情节,观众事先并不知道,因此总认为王三难免一死,最后突然把他放了,观众才恍然大悟,这种“悬念”设置与前面把偷马贼赵顽驴下在死牢这一情节遥相呼应,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且使观众在看到结局时不得不抚手称妙。这就在无形中冲击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完成了对于作品的再解读。
综上所述,元杂剧的产生和发展、作者群体的面貌和书写的内容及主题、作品的含义及社会功用、接受群体的底层特色,这些鲜明的特征构成了元杂剧的底层叙事特质。
注释:
①洪畅.元代艺术观念研究·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1.
②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M].上海:艺文印书馆,1972:1.
③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5.
④洪畅.元代艺术观念研究·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1.
⑤胡侍.真珠船[M].北京:中华书局,1985:35.
⑥注:臧晋叔《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共收剧种162种.
⑦臧懋循.元曲选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3.
⑧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271.
⑨王俊德,白俊卿.元杂剧本体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259.
⑩王俊德,白俊卿.元杂剧本体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