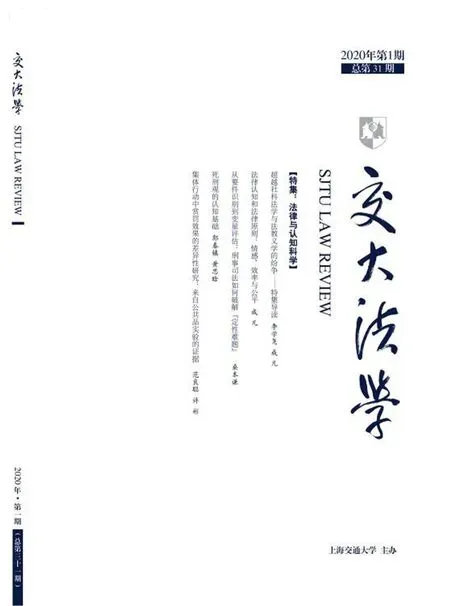死刑观的认知基础
2020-02-26郭春镇黄思晗
郭春镇 黄思晗
目次
引言
一、 死刑观背后的两种理性
(一)功利理性
(二)道义理性
二、 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威胁感知
(二)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
(三)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
(四)死刑的经济成本
三、 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公正世界信念
(二)归因方式
(三)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
四、 融贯性认知下的死刑观
(一)“义”与“利”的融贯
(二)传统与现实的融贯
五、 结语
引 言
死刑的存废问题在社会层面极具争议,在法学界也是聚讼纷纷。(1)参见赵秉志: 《再论我国死刑改革的争议问题》,载《法学》2014年第5期,第125—131页;赵秉志: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46—154页;陈兴良: 《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以首批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载《法学》2013年第2期,第43—57页;曲新久: 《推动废除死刑: 刑法学者的责任》,载《法学》2003年第4期,第43—44页;邱兴隆: 《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10—19页;邱兴隆: 《死刑的德性》,载《政治与法律》第2002年第2期,第50—53页。在本文中,死刑观也被称为“死刑态度”。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能够影响到法律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那么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甚至决定死刑的存废。研究公众的死刑观,不仅可以在现实层面探索和发现公众到底如何理解和看待死刑,还可以挖掘这一社会心态产生的认知基础。通过探究、理解、引导这一认知基础,可以在尊重公众态度的基础上,为相关的制度变迁提供心理支撑。
民众对死刑的态度主要源于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两种理性,而这两种理性建立在不同的认知路径基础上。本文通过导入认知科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和进路,对现有社会上不同死刑观背后的认知基础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本文还试图进一步探讨两种理性之间如何交织融合,以及传统与现代文化如何影响民众的死刑观。
一、 死刑观背后的两种理性
态度是制度的心理基础。如果我们认为公众对死刑的态度会影响到死刑是否应予存在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应该存在等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对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进行思考和探索。一般来说,一种制度要得到公众的认同、接受与信任,需要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获得其存在的正当性和道义上的权威性。公众评价制度的标准有两个,即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内在标准意味着这项制度具有某种内在属性,反映某种善的价值,由此可以被称为正义标准;外在标准意味着具有某种功效,即具有某种实用性或有效性,由此可以被称为功利性标准或功效性标准。(2)参见陈瑞华: 《论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23—29页。据此,也可以从功利理性和道义理性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一)功利理性
功利理性注重和强调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众所周知,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边沁认为,功利主义是立法的真正原则。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都有求乐避苦的本能,即“根据任何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3)[美] 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这种观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不以使犯罪人遭受痛苦为目的,而是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刑罚惩罚改过迁善,适应社会生活,不致将来再犯罪并同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4)参见逄锦温: 《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探析》,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第108—111页。在这个意义上,犯罪者已经损害的法益应被视为沉没成本,因为刑罚不是面向过去的,而是面向未来。
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来,刑罚的目的在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无疑,死刑具有特殊预防的作用,通过将犯罪者置于死地断绝其再犯的可能。但对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仍未有定论。有些人主张死刑具有威慑效应,我国古代就常有“以儆效尤”的说法。功利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体在决定是否实施犯罪的时候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刑罚的严厉程度乘以犯罪被抓获的概率就是犯罪最主要的成本,故而应该在考虑破案率的基础上使犯罪人所受刑罚之苦大于实施犯罪之利。又因为相对于其他刑罚,生命刑的威慑作用最强,所以死刑不应废除。也有人认为,死刑会产生负面激励,让那些犯下杀人罪行的人认为“反正都是死,杀一个是死,杀更多的人也是死”。陈胜、吴广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说明了当对一个轻罪适用重刑的时候,实施犯罪的人会采取极端手段逃避死刑,想办法销毁可能的证据和杀害能证明其犯罪的人,因此死刑会导致更多和更恶劣的犯罪。(5)见前注〔4〕,逄锦温文,第108—111页。
这两种论证的说服力都存在令人难以信服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威慑效应的认定上。判定死刑到底有没有威慑效果从理论和技术方面都是一个难题。显然“自然实验”并不可行,如果采取问卷调研的方式,样本选择也会存在偏差。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被调查者都不大可能是会犯罪的人,尤其是不会犯下故意杀人、伤害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行。因此,他们对于死刑有没有威慑、能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的想象,这种基于内省和心理投射所做出判断的说服力,令人怀疑。
判断死刑对于犯下可能判处死刑的罪行有没有正面激励效应,最合理的方式是面向那些将要犯下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调研。如果他们由于畏惧死刑的惩罚而没有犯下此类罪行,那么可以视为威慑作用生效;如果面对死刑惩罚仍然犯罪,则可视为威慑效用没有体现出来。但这里面对的一个难题是: 这类人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我们无法找到这类样本。即便找到了这样的样本,自陈式测验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他可能会自称由于畏惧死刑的惩罚而没有犯下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另外,人的态度和行为在一些情境下常常存在偏差,即使测量出犯罪分子真实的态度,我们也无法判定在真实的犯罪场景中,他会如何行事。
因此,死刑的威慑效用在逻辑上推理可能会产生有效或无效两种结果。从实践来看,这是一个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即便如此,虽然从逻辑上无法解决死刑到底有无威慑问题,但研究公众的死刑观仍然有意义。不管事实上死刑有没有威慑力,只要公众的判断是基于“认为有威慑”做出的,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们是基于功利理性做出的判断。
(二)道义理性
报应是论证刑罚的一种重要理论依据,死刑的正当性也在其论证范围之内。报应的核心意涵排除了功利主义的考虑,其逻辑更多地体现为“判处一个人死刑的理由,是因为他应该被判处死刑”。报应除了强调对等,更强调之所以让某人承担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是因为这个人的某个行为是错误的,基于道义应该受到惩罚。
一个应受惩罚的行为的错误体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主观方面体现为犯错者的主观意志,即他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了错误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为产生了危害的结果。法律科学的重要支点之一是自由意志,在法学的理论框架中,每个人都具有自由意志,具有认识自己行为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遭到法律的否定,但他仍然执意实施这样的行为,就表明了他的自由意志是在寻求这样的惩罚。对他进行惩罚正是把他视为理性的存在,因此报应本身就是正义。作为报应的死刑,其目的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威慑,也不是或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而是为了达到一个公平的结果。
受实证科学的影响,近代学派认为自由意志假设只是虚构的空想,是背离科学的杜撰。(6)Alfred Mele, Free Will: Action Theory Meets Neuroscience, in Intentionality, in Christoph Lumer & Sandro Nannini eds., Deliberation and Autonomy: The Action-Theoretic Basis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Routledge, 2007, p.257-272.近代学派认为犯罪是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犯罪行为由犯罪人本身的素质和社会环境所决定,而社会环境不是犯罪人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因此社会环境本身也应该对犯罪行为承担部分责任。让犯罪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由此剥夺其生命对他并不公平,因此死刑不符合道义论。在美国,在那些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团队中,有一个“减轻处罚专家”(mitigation specialist),这个专家可以是心理学家、医学家或者其他行业的专家,唯独不可以是法学专家,其工作职责就是从法律之外的各个方面寻找理由,以减轻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处罚。(7)参见[美] 迈克尔·E·泰戈、安杰拉·J·戴维斯等,《审判故事》,陈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15页。尽管有学者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基于决定论哲学论证了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决定了的,人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像”,(8)D. M. Wegner, 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 Will, MIT Press, 2002, p.74-78.但是主流的刑罚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将主体对自由意志的体验混同于自由意志本身,强调只能根据主体的行为来判断是否应该令其承担刑事责任,而行为本身不可能被还原为神经元的兴奋或抑制,“人”本身也不能被还原为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的集合。(9)参见郭春镇: 《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 法学研究的新动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第146—159页。归根结底,死刑是否正当取决于是否相信自由意志假定。
因此,“死刑的存废、去留,并不取决于其自身无法辩明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以及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威慑性。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受集体意识的公众认同以及政治领袖的政治意志左右的政策选择问题”。(10)梁根林: 《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5—27页。而公众对死刑是否认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死刑政策的走向。在了解到各类民意调查中反映出的公众对死刑的较高支持率、发现其背后蕴含着两种理性后,如何剖析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发掘死刑观形成的认知基础成为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
二、 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死刑观的形成是一个决策行为,人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拥有“完备信息”,因此在判断和决策时涉及很多不确定因素。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类有纯粹自利偏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众基于威慑作用支持死刑的态度符合“理性人”的目标。在马斯洛需求层级中,安全需求位于第二层级,人类满足了呼吸、食物、水、睡眠等生理需求后,就开始追求安全需求,即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的需求。(11)See 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50 Psychological Review 370-396 (1943).人的安全需求使其恐惧严重暴力犯罪,并对这种行为产生愤怒和攻击。在死刑观调查中,被调查者一般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大多数人不会触犯刑法或实施严重犯罪。在公众的朴素观念中,常常将自我投射到犯罪人身上,认为犯罪分子也是“理性人”,在从事犯罪行为时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犯罪的成本越高,其从事犯罪行为的概率越低,剥夺生命是最严厉的刑罚也是最高的成本,因此死刑相比其他刑罚威慑作用最好。相应地,社会的犯罪率越低,治安越稳定,则自己受害的可能性越小。基于这一逻辑,惩罚越严厉,自身越安全。因此,为了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人们往往希望对罪大恶极的人适用死刑,从而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威慑作用,以降低社会的犯罪率。
在刑罚博弈中,仅存在潜在受害人和潜在犯罪人两种角色。当保留死刑时,潜在犯罪人有被处以死刑的风险,潜在受害人认为这种刑罚的存在对潜在犯罪人具有威慑作用,因此自身更加安全,潜在被害者获利。当废除死刑时,潜在的犯罪人即使在实施了严重暴力犯罪后仍无须偿命,潜在的犯罪人获利。在各类民意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概率极低,因此往往处于潜在受害人一方。如果潜在受害人感受到更严重的威胁,那么就有更强的意愿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安全。越是认为死刑具有有效威慑作用的人,越是倾向于采取死刑这种控制措施。
但是,历史的一些教训也使公众认识到刑罚并非越严厉越好,对轻罪采取重刑,会导致无法对重罪施加合理的边际刑罚,从而失去威慑作用。一旦刑罚过于严厉,对轻罪施加死刑时,公众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乖乖就范后被处死;另一种则是采取极端的措施逃避刑罚,例如杀害证人或以更激烈的方式报复社会等。两种选择的最坏结果都是死,而采取极端措施逃避刑罚还有成功的可能,因此理性的犯罪人必然采取各种措施逃避刑罚,由此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危害性。此外,关押罪犯的成本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成本的权衡也是人们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基于此,威胁感知、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以及死刑的经济成本构成了死刑观中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
(一)威胁感知
威胁感知是一种对犯罪的感知和恐惧情绪。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暴露在各种致命风险中时,基于“刑罚越重,犯罪的概率越小”的这一未必正确的“常识”,会寄希望于通过严厉的刑罚来减少这种威胁。泽尔特和麦考密克分析了犯罪的恐惧感对死刑观的影响,研究者通过电话访谈采访了610名马里兰两个郡的民众,发现那些“非常害怕”成为受害者的人往往支持对谋杀犯适用更严厉的刑罚。那些认为“有一些害怕”的人支持死刑的概率较低。(12)See R. Seltzer & J. P. McCormick, The Impact of Crime Victimization and Fear of Crime o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Penalty Defendant, 2 Violence and Victims 99-114 (1987).地区谋杀率和种族偏见、种族结构、经济不平等等因素会通过影响公众的威胁感知,对死刑观产生影响。
地区谋杀率影响了公众对犯罪率的感知,从而影响了死刑支持率。兰金使用1972—1976年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研究地区犯罪率与死刑支持的影响,在控制了种族、宗教和时间的变量后,他发现死刑的支持率与滞后三期的犯罪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3)See J. H. Rankin,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 Punishment, 58 Social Forces 194 (1979).埃里克使用1974—1998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面板数据,也发现地区谋杀率显著地影响了死刑观。谋杀率高的地区,死刑支持率也越高。(14)See Eric P. Baumer, Steven F. Messner & R. Rosenfeld, Explaining Spatial Variation in Support for Capital Punishment: A Multilevel Analysis, 10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4-875 (2003).这种态度体现了公众的功利主义的思路,当他们认为社会环境不安全时,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或死刑使社会治安得到改善。此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经验也会影响民众对死刑的态度。在高犯罪率的地区,公众对暴力行为更习以为常,受环境的影响,也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对死刑这种暴力的惩罚措施接受度更高。(15)Ibid.
不仅是客观的地区犯罪率会影响民众的威胁感知,种族偏见、种族结构、经济不平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威胁的感知。很多研究表明,种族偏见与死刑支持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在美国,暴力犯罪人中非裔男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白人,媒体的报道也常常集中于黑人暴力犯罪分子和白人受害者的案件,这种渲染加剧了种族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民众会将非裔美国人与犯罪行为联系到一起。(16)See M. J. Borg, The Southern Subculture of Punitiveness? Regional Variation in Support for Capital Punishment. 34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5-45 (1997).奥利弗研究了与犯罪有关的影视作品,发现司法工作人员通常是白人,犯罪嫌疑人通常是少数族裔,这种做法导致了公众对少数族裔的憎恨。(17)See Mary Beth Oliver, Portrayals of Crime, Race, and Aggression in “Reality-Based” Police Shows: A Content Analysis, 38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179-192 (1994).巴坎和科恩考察了1990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数据,分析了两个反映种族偏见的指数种族厌恶(racial antipathy)和种族刻板印象(racial stereotyping)与死刑观的关系。在白人样本中,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种族厌恶、种族刻板印象都与死刑的支持度有关联。(18)See S. E. Barkan & S. F. Cohn, Racial Prejudice and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by Whites, 31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 Delinquency 202-209 (1994).威胁理论认为,富人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认为黑人和穷人具有威胁性,他们更可能进行暴力犯罪。当后者数量增加的时候,精英感受到更严重的威胁,进而希望采取强硬的犯罪惩罚措施。因此,人们对种族结构和贫富差距的感知对死刑支持率也会产生影响。利佐特和巴度发现白人对犯罪率的感知受他们与非裔美国人的物理距离影响,生活区域中的黑人越多,白人感受到的犯罪率越高。(19)See A. J. Lizotte & D. J. Bordua, Firearms Ownership for Sport and Protection: Two Divergent Models, 4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9-244 (1980).埃里克的研究发现,在拥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和更高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地区,死刑支持率也越高。(20)See Eric P. Baumer & Steven F. Messner, supra note 〔14〕, at 844-875.
此外,暴力犯罪发生的概率常常被人高估。范迪维尔和吉尔克帕斯研究了刑法专业和非刑法专业学生对美国年谋杀案件数量所做的估计,学生极大程度上高估了谋杀案的数量。非刑法专业学生中有近50%认为每年发生25万件谋杀案,约15%的学生认为每年有100万件谋杀案,刑法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的估计更精确,虽然相比实际的数据仍然是高估了。(21)See Margaret Vandiver & David Giacopassi, One Million and Counting: Students’ Estimates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Homicides in the U.S., 8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135-143 (1997).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外行人和司法从业人员对于盗窃犯罪的印象,外行人认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犯携带着武器,并有很大的再犯风险,因此外行人对犯罪的估计往往比真实情况更加严重。(22)See L. J. Stalans & A. J. Lurigio, Lay and Professionals’ Beliefs about Crime and Criminal Sentencing: A Need for Theory, Perhaps Schema Theory, 17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33-349 (1990).造成这些认知偏差的原因在于,一般大众对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是媒体,而媒体报道的往往是极具恶性的犯罪案件,导致公众对谋杀率和犯罪严重程度的错误感知。由于刑法学学生可以从课堂和司法实践中获取相关信息,他们的估计相对而言较为准确。(23)See Margaret Vandiver & David Giacopassi, supra note 〔21〕, at 135-143.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人们在面临风险决策时,对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与客观概率(objective probability)存在偏差,往往高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24)See D. Kahneman &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47 Econometrica 263-291 (1979).比如公众经常高估彩票中奖和保险出险的概率。公众对小概率事件的高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其一认为这是一种人类进化中的过度保护机制,原始人类生存中面临着很多威胁,虽然发生概率不大,但一旦发生将遭遇灭顶之灾,所以高估此类威胁发生的概率可以使人们具有防灾的意识,更有利于后代的繁衍与基因的延续;其二是鲜活性效应(vividness effect),即越是鲜活的信息越容易被提取。(25)See Punam Anand Keller & Lauren G. Block, Vividness Effects: A Resource-Matching Perspective, 24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95-304 (1997).人类在决策时并不会像计算机一样遍历所有的因素,并对所有因素进行客观的加权和评估,而是根据信息在大脑中的可得性进行提取。(26)See K. E. Stanovich, 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Scott Foresman, 1989, p.122-123.由于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是触目惊心,加上媒体报道的渲染,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行为主体在进行决策时更容易提取这种鲜活信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主体在进行决策时,犯罪发生的主观概率比客观概率高。
(二)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
公众有基本的安全需求,当感受到犯罪威胁的时候,希望用更严厉的刑罚措施来减少这种威胁。这其中蕴含着一个假定,即严厉的刑罚措施可以威慑犯罪。人们基于常识认为对一个行为的惩罚越重,则从事这一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这种常识符合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人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本能,对受刑罚之苦感到畏惧,故而犯罪成本越高,从事犯罪的概率就越低。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来,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性对死刑的支持有极大的影响。托马斯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提出了一个死刑观的功利主义模型,认为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与适用死刑来控制犯罪的意愿有关,而适用死刑来控制犯罪的意愿与对犯罪的恐惧和死刑的威慑作用相关。(27)See C. W. Thomas & S. C. Foster,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ublic Support for Capital Punishment, 45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41 (1975).在第一个调查中,他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样本为佛罗里达州的839户居民。结果表明,死刑的威慑作用的有效性与适用死刑控制犯罪的意愿显著相关,而使用死刑控制犯罪的意愿与对死刑的支持显著地相关。(28)Ibid.在第二个研究中,样本为3334名弗吉尼亚州居民。他同样考察了功利主义的信念与死刑支持的关系,发现犯罪率严重程度的感知、受害恐惧、对惩罚有效性的估计影响了被调查者选择适用的刑罚。(29)See C. W. Thomas & R. G. Howar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 Punish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6 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189-216 (1977).在两个研究中,最主要的影响死刑支持的因素是公众对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性的估计,两个州的样本都表明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显著地影响了死刑的支持率。(30)在佛罗里达州,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效性与死刑的支持相关系数r=0.772。在弗吉尼亚州的调查中,刑罚有效性和是否愿意适用重罪的Gamma=0.220,均表明具有很强的相关性。See C. W. Thomas & S. C. Foster, supra note 〔27〕, at 641.在笔者所做的X大学的调研中,大多数被访者相信死刑对犯罪具有威慑作用。有45.2%的被访者认为死刑可以预防和减少犯罪,38%的被访者认为应该可以,而16.8%的学生认为不可以。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与死刑的态度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越认同死刑的威慑作用,对死刑的支持态度越强硬。主张完全保留死刑的样本中有72.5%坚定地认为死刑能够减少和预防犯罪。而对于主张完全废除死刑的人中则有超过半数(55.6%)否定了死刑的威慑作用。
此外,在类似研究中,当被问及为什么支持死刑时,被调查者在自我陈述中表示威慑是一个重要的理由。维德马(N. Widmar)问及民众支持死刑的理由时,发现威慑作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占42%)。当要求被试在一般预防和报应中选择其一时,有63%的人选择了一般预防。(31)See N. Vidmar, Retributive and Utilitarian Motives and Other Correlates of Canadian Attitudes Toward the Death Penalty, 15 Canadian Psychologist 337-356 (1974).萨拉(A. Sarat)和维德马进行了一项实验,首先测量被试对死刑的态度,之后给181名被试提供关于死刑威慑作用的小册子,实验材料中的内容为死刑事实上并不能威慑犯罪,之后再次测量被试对死刑的态度。结果表明,前测中被试的死刑支持率为51%,当阅读完死刑不具有威慑作用的内容后,仅有38%的人还支持死刑。(32)See A. Sarat & N. Vidmar, Public Opinion,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 Eighth Amendment: Testing the Marshall Hypothesis, 17 Wisconsin Law Review 171-206 (1976). 这一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被试可以很容易地知道主试的实验意图,可能对被试的判断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对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
有关部门在制定或选择政策时,常常是根据政策运行的效果对政策本身进行调整,这一机制类似于反馈调节系统。系统本身的运行效果,反过来又作为信息来调节该系统的运行。在死刑观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的反馈调节机制。大多数人内心都相信“死刑能够威慑犯罪”的假定,基于此种假定,死刑数量的增加能对犯罪率起到抑制的作用。当犯罪率过高时,增加死刑执行数量,则犯罪率就会下降。但公众同样认识到刑事政策不应过于严厉,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都适用死刑。因此死刑执行数量在人们心理上存在一个阈值。
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主体首先会对主观威胁感知做一个评估,然后基于死刑具有威慑作用的假定,产生对死刑的初始倾向。如果犯罪率过高,则希望增加死刑数量以达到威慑效果。此时,还要进行一个判断,即死刑数量是否超过合理区间。当人们认为犯罪率过高,而死刑数量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时,他们就会支持死刑;当认为犯罪率正常而死刑数量过高时,则持限制和减少死刑的态度的概率较大;当认为犯罪率过高且死刑数量过高时,则可能在两种价值取向上产生一定的冲突,并进行权衡取舍。
对X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所感知到的判处死刑的数量与死刑的总体态度存在强相关(P=0.005)。此题为五点量表,(33)1代表“非常少”,5代表“非常多”。所感知的死刑数量越少的人对死刑的支持态度越强硬。主张完全废除死刑者得分3.63,主张保留死刑但限制死刑的适用者得分3.06,主张完全保留死刑者得分3.03。我国官方没有公布死刑的数据,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日常经验的感知进行估计。我们推测这一认知可能对死刑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民众可能认为我国判处死刑的数量太少,所以要增加死刑的执行数量,从而对潜在的犯罪产生威慑力。
法学教育影响了人们所感知到的死刑数量。笔者在对X大学的调研中发现,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不同年级所感知到的死刑数量并没有显著差异,均值为3.01。而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新生所认为的死刑数量比非法学学生多(3.16),经过一年及以上的法学教育之后,其感知到的死刑数量相比新生更多(3.33),差异显著。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法学专业学生接触到的死刑的案件较多——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等类似课程上,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我国的死刑的实践案例;另一种是死刑数量的多和少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进行评价的,法学专业学生了解到绝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现状,内心可以接受的死刑数量的阈值更低。相比其他专业学生,法学专业学生中更多的人认为死刑执行数量与文明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他们能接受的死刑执行数量可能更少,更可能希望限制和减少死刑。
(四)死刑的经济成本
很多人认为死刑是代价最小的一种刑罚,无非花费一颗子弹或注射一支针剂而已,而将罪犯关在监狱则要耗费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34)参见刘仁文: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死刑的成本》,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第40—42、56页。他们往往低估了死刑的经济成本。在博姆验证马歇尔假说的一个研究中,被试先要求对死刑相关表述的正误进行判断,其中包括“平均而言,死刑比无期徒刑花费更少”,实验组被试中最初有69.5%的人同意这一表述。但当完成了5周的死刑相关课程之后,有91.6%的人意识到这一表述是错误的。(35)See D. W. Grant, R. B. Meiris & M. G. Hollis, Knowledge and Death Penalty Opinion: A Test of the Marshall Hypotheses, 28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60-387 (1991).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死刑的成本明显比无期徒刑高。美国学者莱科尔曾从审批程序、上诉程序和矫正程序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死刑制度的成本,指出死刑案件审判实践更长、次数更多、需要陪审团审判,执行前的特别安全警戒须要耗费极高的成本。这些成本相加,远远超过了终身关押的成本。(36)见前注〔34〕,刘仁文文,第40—42、56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从审判到处死1个死囚平均花费2 400万美元,得克萨斯州的死囚年均花费高达230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在高度警卫下的3个普通犯人40年的花费。(37)赵广俊: 《“第1 000个死囚”引发激烈争议》,载《法制日报》2005年12月17日,第003版。
死刑的成本包括程序成本、执行成本和附随成本。相比一般的刑事案件,死刑案件需要更加复杂的程序设计并因此带来更高的成本。有学者曾将死刑制度的高昂成本作为废除死刑的论据之一。他认为,由于死刑审判要提供最好的法律援助、冗长的救济程序、耗费大量时间在审判和羁押过程中,在定罪方面的证据和法律标准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加严格,加上由于赦免而部分死刑最终没有被执行等因素,因此死刑的成本极其高昂。(38)[英] 罗吉尔·胡德: 《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我国目前死刑的执行方式包括枪决和注射。注射被认为是一种更为人道的执行方式,但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且每个案件都要独立申请,需要法官专程赴京取药。目前注射执行死刑的场所主要有固定刑场和执行车两种,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建一个固定刑场大约要200万元,死刑执行车成本略低,但买车要花40多万,而且每次执行注射价格高昂,导致很多地区无力承担。(39)见前注〔34〕,刘仁文文,第40—42、56页。此外,死刑还会带来较高的附随成本,包括死刑犯后事的处理、错案导致的国家赔偿、死刑引起的劳动力丧失等等。(40)同上注。因此,民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死刑的经济成本。
三、 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
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突破了理性人假设,发现人类除了纯粹的自利偏好之外,还存在着公平偏好(fairness preference),并通过不同种族和文化环境下的博弈实验加以证实。证明人类具有公平偏好的博弈实验包括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独裁博弈(dictator game)实验、礼物交换博弈(gift exchange game)实验、信任博弈(trust game)实验,以及公共品博弈(public product game)实验等。(41)魏光兴: 《公平偏好的博弈实验及理论模型研究综述》,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第152—161页。在这些博弈实验中,人们为了追求公平,不惜放弃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博弈双方分别扮演“分配者”(proposer)和“接受者”(responder)两种角色,对一笔奖金进行分配。其中分配者提出分配方案,接受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该分配方案。如果分配者提出的方案被接受,这笔奖金就按照分配者提出的方案进行分配;如果方案被拒绝,两人的所得金额均为零。按照纯粹自利偏好的假设,分配者应该会分尽可能少的金额给对方,而接受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的分配方案,因为任何数额的收入都可获益,聊胜于无。然而,大量实验结果背离了理性人的经济假设,一项包括了75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meta分析表明,分配者平均会分给对手40.4%的钱,而接受者通常拒绝低于20%的分配,并且拒绝率随不公平程度加深而增加。(42)See H. Oosterbeek, R. Sloof & G. van de Kuilen, Differences in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s: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7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71-188 (2004).被试在面对不公平的事件时,会产生厌恶和愤怒的情绪。核磁共振成像的结果显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当接受者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显著被激活。(43)See A. G. Sanfey, J. K. Rilling, J. A. Aronson 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300 Science 1755-1758 (2003).前脑岛负责的是情绪加工,与厌恶和愤怒的情绪相关,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负责认知系统对情绪的抑制控制。虽然对犯罪分子处以死刑无法使我们获益,但当出现不公时,我们会产生厌恶、愤怒等情绪,而这种“杀人偿命”的方式满足了朴素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道德情感。
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也表明,强互惠行为(strong reciprocity)在维持人类合作秩序上起着重要作用。所谓强互惠行为,就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范的人,即使这些成本并不能被预期得到补偿,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44)参见韦倩: 《强互惠理论研究评述》,载《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5期,第106—111页。有这种公平偏好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公平偏好个体比例高的种群可以更好地合作,通过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人们的公平偏好本质上是“自然为人类立法”。他们对不公正事件的接受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死刑的态度,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烈,越可能支持死刑。归因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死刑观,将犯罪原因归因于犯罪分子个人的人往往认为犯罪人应该受到惩罚,因而更多地支持死刑。此外,对刑事司法系统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也会对死刑态度产生影响——认为刑事司法系统中不公平的因素越多,支持死刑的可能性越低。
(一)公正世界信念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是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概念,是人对周围世界中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联系的一种假设。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应得的事物,所有高尚的行为都将得到嘉奖,所有罪恶的行为都将得到惩罚,(45)See M. J. Lerner & D. T. Miller,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85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0-1051 (1978).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认为生活是可以预期的,这在认知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可以减少他们对世界不确定性的风险感知。
公正世界信念对死刑观有一定的影响。陪审员的公正世界信念影响了其在死刑审判中的决策,研究者让陪审员被试完成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并提出对一个具体案件的裁判意见,结果表明,公正世界信念更强的陪审员有更大的概率决定对一个罪犯适用死刑。(46)See B. Butler & G. Moran, The Impact of Death Qualification, Belief in a Just World, Legal Authoritarianism,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Venirepersons’ Evaluations of Aggravating and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in Capital Trials, 25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57-68 (2007).当不公平的事件出现时,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威胁,从而往往采取一些方式重新构建这一信念——最常见的是减轻受害者的痛苦,使其获得补偿。当呈现给被试死刑替代措施的选项时,在替代措施为无期徒刑加上犯罪分子监狱中劳动补偿受害者家属时,替代措施的接受度明显提高,仍然坚持死刑的人明显减少。这一实验结果也说明补偿受害者的替代措施可以让他们的公正世界信念获得补偿,因而不再寻求极刑。
(二)归因方式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人在生活中时刻在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找原因,归因可以满足人对理解和控制环境的需要。个体在过去经验和当前期望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归因认知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特有的归因倾向,即为归因方式。(47)参见袁莉敏、张日昇: 《大学生归因方式、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年第2期,第111—115页。在犯罪问题上,归因方式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将犯罪归因于犯罪分子还是外在环境。内在归因(internal attribution)的人认为犯罪是由于犯罪分子本身的主观因素,如性格、品行等;而外在归因(external attribution)的人更多地认为是社会环境催生了犯罪行为。基于公平世界信念,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归因方式影响到民众对犯罪应受惩罚性的认识。在内在归因的情况下,被试认为个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刑罚后果颇为合理;在外在归因的情况下,被试会认为社会对犯罪承担着一定的责任,而用死刑终结犯罪人生命来达到社会控制目的,明显推卸了社会对于犯罪的责任。因此,主张内在归因方式的人更可能认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推论。卡罗尔和佩恩首先给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犯罪案件以及该犯罪的产生原因(内因或外因)的信息,被试需对犯罪的严重程度、犯罪分子应负的责任、应受的惩罚进行评价。研究者发现,被试认为基于环境原因的犯罪比基于内在原因的犯罪应受的刑罚要轻,对外在原因导致犯罪的罪犯,被试更可能做出释放决定。(48)See J. S. Carroll & J. W. Payne, Crime Seriousness, Recidivism Risk,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in Judgments of Prison Term by Students and Experts, 62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595-602 (1977).霍金斯给大学生呈现了很多犯罪情形,让被试选择这个犯罪产生原因和对应受惩罚的轻重程度打分(0~10),结果发现,归结于个人原因的犯罪比归结于社会原因的犯罪受到更严厉的惩罚。(49)See Darnell F. Hawkins, Causal Attribution and Punishment for Crime, 2 Deviant Behavior 207-230 (1980).人格与惩罚性的研究也表明,具有内在控制(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观念的人认为犯罪更具有惩罚性。(50)See R. H. Sosis,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and the Perception of Responsibility of Another for an Accident, 30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393-399 (1974).归因方式通过影响人们对犯罪可惩罚性的认识,影响了公众对死刑的态度。科尔伦的研究要求697名陪审员回答对青少年、精神障碍、智力迟钝的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的支持度,结果证明主张内在归因的人比主张外在归因的人更可能支持死刑。(51)See John K. Cochran, Denise P. Boots & Kathleen M. Heide, Attribution Styl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 Punishment for Juveniles, The Mentally Incompetent, and the Mentally Retarded, 20 Justice Quarterly 65-93 (2003).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人格的人也更可能支持死刑。(52)See M. Robbers, Tough-Mindedness and Fair Play: Personality Traits as Predictors of Attitudes Toward the Death Penalty — An Exploratory Gendered Study, 8 Punishment & Society 203-222 (2006).因为他们具有更强的自我控制信念,认为可以掌控自身行为的是主观意识而非环境。原教旨主义与死刑的相关关系通过归因方式产生作用。原教旨主义是指一种忠实于圣经教义的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更确信自由意志、人类内在有罪、上帝具有报复性和惩罚性的观念,其在评价犯罪行为时很少考虑到环境的影响,并认为人类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53)See R. L. Young, Religious Orientation, Race and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31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76-87 (1992).很多研究表明,原教旨主义者更多地支持死刑,归因方式被认为是原教旨主义与死刑支持的中介变量。(54)See H. G. Grasmick & A. L. Mcgill, Religion, Attribution Style, and Punitiveness Toward Juvenile Offenders, 32 Criminology 23-46 (1994).另一研究发现,刑事司法从业人员与普通大众对于犯罪的归因上也存在不同。比如,缓刑官员和外行人对盗窃罪的归因就大相径庭。外行人大都认为犯罪是出于个人意向的原因,如贪婪和懒惰;而缓刑官员则更多地归于社会原因。与此同时,相比刑事司法执业人员,外行人认为盗窃罪应该被施以的刑罚更严重。(55)See L. J. Stalans & A. J. Lurigio, supra note 〔22〕, at 333-349.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刑事司法执业人员与外行人的信息差异。人具有解释世界的需求,刑事司法从业人员对具体的犯罪行为接触更多,更了解产生犯罪的具体原因(如生计所迫、家庭和教育存在的问题),而外行人对犯罪的了解仅仅来自媒体的报道,对犯罪知之甚少,也并不了解导致犯罪的社会因素。此时,将犯罪行为归结于犯罪分子本人的品质恶劣是最容易接受的解释。
但人类的归因存在偏差,在解释他人行为时会产生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一种将他人的行为自发归因于行为主体的个人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的稳定倾向。(56)参见李陈、陈午晴: 《基本归因错误的文化局限性》,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6期,第938—943页。由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完全由个体特征决定,所以基本归因错误是一种有偏差的归因倾向,导致人们系统地低估了行为由外因引起的程度。(57)同上注。大众对犯罪接触极少,无法站在犯罪分子的视角看到引发其犯罪的社会原因,在不了解其犯罪原因情况下,相信犯罪分子生性恶劣是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犯罪原因。通过“坏人才会犯罪”的思维将“好人”与犯罪行为隔离,让自己相信周围的好人都遵纪守法、安分守己,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认知需求。
(三)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
马歇尔在福曼诉乔治亚案中提出了关于死刑的马歇尔假说(Marshall Hypotheses),其中假说一认为,公众对死刑信息知之甚少;假说二认为,当公众了解了死刑及其影响后,他们将反对死刑。(58)Furman v. Georgia, 408 U.S. 238 (1972).一般公民对犯罪及刑事司法系统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新闻报道或艺术作品。这些媒体所反映的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与真实世界的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死刑的知识更是极端匮乏。即使是刑法专业的学生,从课堂知识也无法对死刑司法实践产生系统的认知。一些研究验证了马歇尔假设,即当人们了解了死刑信息,尤其是死刑管理中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后,就会反对死刑。
博姆在1985—1988年间进行了实验,设置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实验刺激(experimental stimulus),让学生参与了长达四周、每周五天每天两小时的死刑课程,通过前测和后测问卷测量死刑课程对死刑观的影响。课程内容涉及死刑的历史、最高法院死刑判例、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证据、死刑的管理问题等。被试在课程初始和课程结束时填写同样一份问卷,问卷中包含了死刑观、死刑知识、报应观念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将被试前测和后测问卷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在进行了一个月的死刑课程后,学生对死刑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显著的提高,实验组被试中死刑知识回答正确率从课程前54%(前测)到完成课程后79%(后测),反对死刑的学生也从28.6%提高到41.7%。(59)See D. W. Grant, R. B. Meiris & M. G. Hollis, supra note 〔35〕, at 360-387.根据学生所陈述的其态度改变的理由,死刑适用存在的管理问题如任意(arbitrariness)和歧视(discrimination)、无辜者被判死刑的可能最容易引起态度的转变。(60)See R. M. Bohm, American Death Penalty Attitude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Recent Evidence, 14 Criminal Justice & Behavior 380-396 (1987).死刑的替代措施也能使死刑的支持率下降。但博姆对这些被试进行了跟踪,在课程结束后两三年和十年后分别向学生发送电子问卷并进行回收,结果表明,在实验刺激后,虽然短期内死刑支持率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随后死刑态度出现回弹,恢复到原来的水平。(61)See R. M. Bohm, B. L. Vogel et al., More Than Ten Years After: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Informed Death Penalty Opinions, 32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07-327 (2004).
当人们了解到死刑管理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的时候,其态度发生了转变。当不了解死刑信息的时候,他们认为死刑是满足公正和报应的功能,当经过死刑课程的学习,他们发现死刑管理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种族歧视、无辜者被处死的不公平的情况,死刑不再能满足他们的公平世界信念,转而反对死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死刑支持率出现了下降。但在下降之后为什么又发生反弹呢?态度回弹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认知失调削减(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很多研究证明死刑与个性(personal traits)和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有关。为了防止认知失调,死刑观必须与他们兼容。接受死刑知识可以带来暂时的、短期的改变,但新的立场应该与原来的个性和核心价值观相调和。如果这种调和失败了,那么立场就可能回弹到原来的态度。(62)See R. M. Bohm, B. L. Vogel et al., More Than Ten Years After: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Informed Death Penalty Opinions, 32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07-327 (2004).另一种态度回弹的原因是由于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heuristic)。人的判断是以记忆为基础的,即在判断时虽然手头上没有必要的信息作为依据,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过去习得并存储于长期记忆中的相关信息,而我们提取哪些信息作为决策依据取决于信息提取的流畅程度。(63)参见[美]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 《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有限理性人大都用这种简单地提取来应对判断任务,这种机制更符合生态理性的原则。在刚完成死刑课程后,对于死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信息很容易被提取,但两三年后,这些信息被渐渐遗忘,提取难度增强,人们在做出是否支持死刑的判断时,几乎不会考虑到死刑管理中存在不公平因素的信息,因此死刑态度出现回弹。
四、 融贯性认知下的死刑观
从调研得到的公众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整体上体现了义利融贯、传统与现实融贯的特点。如果一项公共政策重视公众的态度、试图让自己具有足够充分的民意基础,那么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也要立足于这种态度而进行,需要重视这两种融贯之后的社会心态。
(一)“义”与“利”的融贯
有学者认为,一个人不是密尔哲学的拥护者,就是康德哲学的拥护者。(64)Mitch Harden, Chimps Don’t Read Kan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ndiana (May 6, 2013), https: / /www.usi.edu /media /2416973 /mitchharden.pdf.也就是说,不是功利论者就是道义论者。义利之辨,在我国历史上也是长期存在的学术和实践问题。(65)孔子在《论语·里仁》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是非此即彼或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或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时候,利益本身就是道义的组成部分,对利益的不同分配方案,体现了不同道义观。人们的心态、观点和哲学立场并不是非此即彼且一以贯之的——在不同的场景、面临不同问题时,会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游移和摇摆。此时,两种立场和态度更多地呈现出对接乃至融贯的状态,对待死刑的态度也是如此。
调研数据证明了死刑观中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融贯。有学者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探究死刑观与各类认知基础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中国某大学通过系统抽样抽取52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要求首先回答死刑支持度并以此作为因变量。被调查者填写一系列李克特量表,被调查者量表中列举了死刑的威慑作用、报应作用、特殊预防作用、矫治作用以及错误执行的可能性。被调查者回答对这些表述的赞同程度来作为自变量。回归结果表明,通过观察被调查者对于死刑的各类认知能够一定程度上预测其对死刑的支持度。对威慑作用和报应作用的赞同程度与死刑支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对刑罚的矫治作用、错误执行的可能性的估计与死刑支持度呈显著的负相关。(66)相关数据分别是威慑作用(β=0.361)、报应作用(β=0.255)的赞同程度与死刑支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对刑罚的矫治作用(β=-0.131)、错误执行出现的可能性(β=-0.082)。R2为拟合优度判定系数,表示因变量的全部变异能通过回归关系被自变量解释的比例,R2=0.361就是说因变量的变异有36.1%是由自变量引起的变异。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用来比较变量间的重要性,自变量越重要,β绝对值越大。See S. Jiang & J. Wang, Correlates of Support for Capital Punishment in China, 18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4-38 (2008).这些数据表明,支持死刑态度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威慑作用,其次是报应作用,也就是说,此时公众对功利主义的偏好超出了道义论。(67)分别是β=0.361, β=0.255。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以下简称“马普所”)在中国也进行过类似研究,其结果表明,有78.1%赞同“杀人偿命”,66.5%赞同死刑能“给被害人及家属安慰”,63.6%的人赞同“死刑的废除将立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58.6%的人赞同“死刑比其他刑罚更能威慑犯罪”。(68)See D. Oberwittler & S. Qi, Public Opinion on the Death Penalty: Results from a General Population Survey Conducted in Three Provinces in 2007 /08, MPG. PuRe, https: //pure.mpg.de /rest /items /item_2500620_4 /component /file_3014342 /content.也就是说,马普所的研究同样证明了公众支持死刑的态度中威慑作用和报应作用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其报应作用的影响高于威慑作用。此时,道义论居于更有优势的位置。在马普所的研究中,曾经问及不反对死刑的人(“支持”和“不确定”),如果有证据证明死刑没有威慑力时的态度,只有17.5%的人会因为死刑没有威慑力转而反对死刑。(69)Ibid.在盖洛普1985、1986、1991年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平均70%左右的死刑支持者认为即使死刑没有威慑作用他们仍然会支持死刑。与此同时,即使死刑被证明有威慑作用,也有65%左右的死刑反对者仍然会反对死刑。(70)See P. C. Ellsworth & S. R. Gross, Hardening of the Attitudes: Americans’ Views on the Death Penalty, 50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52 (2010).这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死刑的态度,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摇摆,但没有一种死刑的认知基础可以完全取代另一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X大学进行的研究中,杀人偿命的认同程度比抚慰和威慑低。(71)此题使用5点式量表: 1~5表示“非常反对”“反对”“中立”“赞同”“非常赞同”,威慑作用的赞同程度为3.83,报应作用赞同程度为3.54。而在马普所的研究中,报应则获得了最为广泛的认同。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不同。教育程度对报应观念的影响可能两方面原因: 第一,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报应的认同程度更低;第二,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不愿意表达出自己的报应观念。在X大学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法学院学生的报应观念显著低于非法学院的学生,其原因可能是与法学教育有关。报应脱胎于复仇这种被认为情绪化、非理性的色彩原始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人们常常将报应与复仇相提并论,将报应与落后和野蛮联系到一起。(72)参见邱兴隆: 《从复仇到该当——报应刑的生命路程》,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83—91页。法学院的学生可能受此影响较深,认为现代社会的刑法应该更加宽和,也可能由于社会压力认为这一观念不体面(虽然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而不愿表达。
死刑观中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融贯于双系统思维模式。双系统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思维加工系统,即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前者以自动化、快速反应、无意识的方式进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可控制的方式进行,且加工的过程可以通过语言描述。基于直觉系统,主体可以迅速做出一个决策,但无法说明这一决策如何产生。社会直觉模型认为,主体在面对一个需要进行判断的情境下,先是基于直觉产生一个道德判断,再进行事后的推理,推理系统对直觉系统做出的判断进行监控和调整。两个系统得出的结论可能相同,也可能相悖。当两个系统得出相同结论的时候,道德推理为我们的道德直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当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就面临权衡取舍的问题,如果推理足够有力,就可能推翻直觉判断,从而改变决策。(73)See J. Haidt,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108 Psychological review 814 (2001).情绪对道德判断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直觉系统中产生直接的、无意识的影响,而在推理系统中认知对情绪进行抑制。因此,在死刑观的形成过程中,不公正厌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死刑的态度。
人在面对严重暴力犯罪时,常常会基于本能的情绪反应产生愤怒、厌恶等情绪,并快速形成支持死刑的决策。这一判断最初很可能是基于直觉做出的反应。而在产生判断之后,主体再进一步为死刑的初始态度寻找理由,这种道德推理于事后进行,很容易寻找到对受害者的抚慰作用以及死刑的威慑作用等使支持死刑态度正当化的理由。这种道德推理常常是“跟着直觉跑”: 一方面进一步检验自己的直觉决策;另一方面起到为直觉判断辩护的作用,也使自己的情绪化决策更加合理化、正当化。埃尔斯沃思和罗斯认为人们先形成态度,后产生理由,他们会认同所有与基本态度相一致的理由。支持死刑的人会认同所有支持死刑的理由,而反对死刑的人会认同所有反对死刑的理由。(74)See P. C. Ellsworth & L. Ross, Public Opin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Views Of Abolitionists and Retentionists, 29 Crime & Delinquency 116-169 (1983).在洛德和罗斯研究的死刑观问题上,人们认为与自己观点相一致证据的质量和可信度更高,更愿意吸收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忽视与自己观点相矛盾的证据。(75)See C. G. Lord, L. Ross & M. R. Lepper,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3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98-2109 (1979).这种现象称为确证偏误(confirmation bias)。这样,虽然很多人非常认同死刑的威慑作用,但面对死刑无威慑作用的证据时却仍然支持死刑就得到了解释。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功利性的考虑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事后推理时支持态度的理由,而不是形成态度的依据。当面对无辜者被错判这类信息时,这类违背民众道德直觉的信息会激发很多人本能的厌恶,直觉系统可能会产生反对死刑的判断。但当推理系统无法为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状况找到足够正当理由时,民众对于死刑的态度可能会产生翻转。对于这类人,这一信息的重要性就远远超过了死刑的抚慰、威慑、报应等因素。
(二)传统与现实的融贯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牛顿活在爱因斯坦之中,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立足于牛顿力学之上,相对论是牛顿定理的延续。与之类似,社会文化及其中蕴含的价值立场和偏好也具有延续性。一个时间节点,可以在政治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分段线,但在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上,仍然保持着连续性。这种延续满足人的认知需求,简化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流程,影响了我们思维和行为。一些新的行为规则可以通过国家或社会的强制力制定或执行,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未必会迅速产生相应的变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有些思维方式和观念甚至可以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比如,孔子的很多观点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甚至成为我们行为的指引与圭臬。
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活动,不同文化的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迥然不同,思维与决策的方式也各有特色。这是因为,文化以内隐方式影响人对行为信息的表征与编码,即以无意识的形式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76)转引自侯玉波、朱滢: 《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载《心理学报》2002年第1期,第106—111页。理解中国人的死刑观念,就需要了解文化背景对其认知的影响。我国在继受了大陆法系相关法律制度后,又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法制的深刻影响,法律制度经历了突变,但法律文化却是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和演进的,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也包括群众对死刑的态度。
从传统来看,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不同,我国更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群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77)See C. A. Kagitcibasi & J. W. Berry,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urrent Research and Trends, 40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93-531 (1989).这在政治和法律问题上表现为国家主义,与我国的中央集权政体和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有关。(78)参见吕世伦、贺小荣: 《国家主义的衰微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6—14页。西周推行的宗法制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权威和世袭特权的组织及其规范,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家族制度,(79)参见张中秋: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版,第42页。并最终生成了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社会格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被统治者采纳后,儒家思想长期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其伦理秩序成为维护政治制度的纽带。(80)参见吕世伦、张小平: 《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国家主义》,载《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第65—72页。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强调将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权力集中,纵向的行政命令在国家事务的管理和资源配置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强调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并移植了大量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这些现代法律是“从身份到契约”(81)[英] H. S.梅因: 《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发展而成的结果,其基本价值立场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作为市场主体为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我国在移植这些法律文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间接地接受了其规范中蕴含的价值,产生了“由形而神”的变化。(82)参见郭春镇: 《法律中“人”的形象变迁与“人权条款”之功能》,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第21—27页。这使得我们的法律文化和意识中存在着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杂糅和融贯,并进而影响到了群众对死刑的态度。
从现实来看,中国人的死刑观体现为更多地强调社会秩序。在一项死刑观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测量了中国和美国大学生对死刑的威慑、报应、矫正和特殊预防上的支持度,结果表明,对于四个关于死刑威慑作用的表述上,中国学生的支持度大约在46%~74%之间,美国有26%~31%的支持度;而对于死刑报应作用的表述上,中国支持度大约在29%~50%,美国约是36%~41%。由此可见,中国学生的报应观念比美国学生弱,而威慑观念比美国强。在美国报应观念是死刑观是最强的预测指标,而中国最强的预测指标是威慑。(83)See S. Jiang & J. Wang, supra note 〔66〕, at 24-38.产生这样的文化差异与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有关,这体现国人在对于犯罪产生原因上更多地进行外在归因,刑法的价值目标也更注重社会秩序。
从归因方式来看,中国人的死刑观更多地体现出强调集体和社会本位的心理。有学者认为,东方人更多地进行外在归因,而西方人更多地进行内在归因。(84)See C. A. Kagitcibasi & J. W. Berry, supra note 〔77〕, at 493-531.西方人常常系统性地低估行为受外因影响的程度,但这在东方文化中并不显著。(85)See A. Norenzayan & R. E. Nisbett, Culture and Causal Cognition, 9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2-135 (2000).莫里斯和彭凯平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他们对美国的两起杀人案件的媒体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中英文报纸在对案件的报道倾向不同——中文报纸强调环境因素对犯罪人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报纸强调犯罪人的个人特征。研究者要求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被试分别解释这两起事件,结果得到了相同的归因差别模式,即中国学生倾向于背景性的解释,而美国学生则倾向于特质性解释。(86)See M. W. Morris & K. Peng,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49-971 (1994).中国人的这种归因倾向会使其在对待犯罪的时候更多地去考虑导致犯罪的社会原因,并非将犯罪原因单纯归结于犯罪分子本人的特征。这种归因方式的差异与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北美文化将个体看作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东亚人则认为个人更多地受到社会集体制约且更少有能动性。因此,东亚人比美国人更多地关注集体的特质。(87)见前注〔56〕,李陈、陈午晴文,第938—943页。当然,将犯罪归因于社会并不必然意味着让社会分担一部分责任进而减轻对犯罪人的处罚。基于集体主义和社会本位的立场,为了消除犯罪人及其行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让其承担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乃至死刑,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更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
五、 结 语
基于上述讨论,支持死刑的主要论证来自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功利主义认为死刑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而道义论认为死刑满足了社会公正,但仔细推敲,其逻辑起点都基于不可证实的假设。人们支持死刑的动机来自安全需求和公正偏好,死刑通过预防犯罪和维护公正满足他们的这两种需求。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人对环境威胁的感知、死刑威慑作用的有无、当前的死刑执行数量以及对死刑的经济成本的认知都会影响大众对死刑的态度。从道义理性角度来看,公平世界信念、归因方式、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会对死刑观产生影响。人类的认知具有局限性,关于死刑的相关问题,信息来源的匮乏更是使公众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着较多的偏差,如公众对威慑作用的确信、恶性犯罪案件的鲜活性效应、死刑适用不存在不公平的假定、犯罪归因时的基本归因错误等等,因此死刑在人们的观念中既能满足功利主义的目标又能恢复公平世界的认知,由此可能导致更高的死刑支持率。
民众形成态度的过程中体现了功利理性与道义理性的杂糅和融贯。当问及公众支持死刑的理由时,抚慰、威慑、报应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死刑无威慑作用和死刑不符合道义都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态度的改变,无辜者被判死刑这种不符合道义论的信息对民众态度的转变影响更大。这是因为人们在整合各类信息形成态度过程中更容易受道德情感的影响,而功利主义常常只是作为为支持死刑态度辩护的正当化理由。死刑观也体现了传统与现实价值认知的融贯,个体对死刑的认知与传统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现代社会中对社会秩序的强调也使其更认同死刑具有的工具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