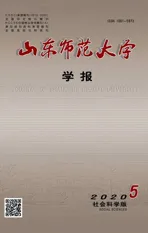卫道、救时与应时:晚清湖湘理学的学术特色与价值研究*
2020-02-26张晨怡
张晨怡
(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
清嘉道以后,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学术风气发生转变,汉学衰落,理学复兴。其中,湖湘地区是晚清时期理学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就时间而言,晚清湖湘理学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主要活动于嘉道年间;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主要活动于咸同年间。至光绪年间则已衰颓,不复成军。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而且积极促成了“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对于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湖湘理学,学界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如陈谷嘉和朱汉民的《湖湘学派源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立新的《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岳麓书社2003年)、朱汉民的《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上述著作为湖湘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均侧重于南宋时期,而鲜少涉及晚清时期湖湘理学的研究。作为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理学自然也被湘学研究者纳入研究范畴之中,如李肖聃的《湘学略》(湖南大学1946年)、朱汉民的《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黄圣旻的《湘学与晚清学术思潮之转变》(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陈书良的《湘学史略》(中华书局2015年)等。但由于湘学并非凝固的时间概念,南宋时期的湘学虽然可以等同于湖湘理学,然而随着湘学的发展,其内涵与外延均发生变化,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所以罗志田说近代湘学“杂而不纯”(1)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也正因为此,上述著作对晚清湖湘理学的关注程度与南宋时期的湖湘理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其研究成果也往往比较简略。此外,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张昭军的《清代理学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对晚清湖南地区的理学也有论及,但限于体例,着墨不多。专门研究晚清湖湘理学的著作仅有张晨怡的《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集中对咸同年间的湖湘理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限于研究时段,对嘉道年间的湖湘理学未予详细论述。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晚清湖湘理学虽有一定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又有一系列专题论文相继发表,但往往侧重于具体人物(2)相关论文主要研究晚清时期湖湘理学人物,如:乐爱国:《唐鉴与钱穆“朱子学案”的结构异同分析》,《求索》2013年第3期;罗检秋:《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张晨怡:《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范广欣:《刘蓉的“门户之见”与理学家的经世观念》,《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综论晚清湖湘理学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现状与晚清湖湘理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亟待学者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有所突破。本文将晚清湖湘理学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之下,对其学术渊源、学术特色、学术地位及价值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
一、晚清湖湘理学的学术渊源
就文化的传承而言,“生活于某一地域的人们对某一文化或文学具有浓郁的兴趣,由此培养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又反过来促成了某一文化或文学的赓续,使得这种传统继续找寻到传承人”(3)李宗刚:《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综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研究湖湘理学,也要首先追溯其地域文化渊源。湖湘理学发端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至湖湘学派出现而正式形成。周敦颐,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其代表作为《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基于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并吸收了道教《太极图》的思想,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论哲学。《通书》以“诚”为核心,“诚”既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又是“圣人之本”的道德人格本体,从而将宇宙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终极存在的本体依据。(4)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页。周敦颐的著作言辞简约,内蕴丰富,以论纲式的表述为后代理学家留下了十分广阔的引申和发挥的空间。此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重镇,号称“理学之邦”,数百年间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被尊为“道学宗主”,是湖湘地区后辈学人“自豪乡曲”“绍休前人”的主要对象。(5)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
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理学阵营中的一个学术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等。他们虽然不是湖南人,但是由于这个学派的形成、发展以及主要学术、教育活动皆在湖南一带,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湖湘学派。(6)陈谷嘉、朱汉民:《湖湘学派源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它是湖南地区形成最早、规模最大的理学学派,在湖湘理学的建构过程中居于十分重要、显著的地位。湖湘学派在研治学术的同时,还创办了多所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教育基地。胡安国、胡宏隐居衡山一带时,创建了碧泉书院、文定书院、道山书院;张栻在长沙传播理学时,主要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基地;张栻的弟子创建了湘乡的涟滨书院、湘潭的主一书院、衡山的南岳书院等。在当时,这一庞大的书院群作为湖南的理学学术——教育中心放射着巨大的能量,使湖南成为理学极盛之地。湖湘学派于南宋末年消亡以后,这些书院延续湖湘理学学统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著名的岳麓书院历宋、元、明、清四朝,一直兴学不辍,其他如城南书院、涟滨书院、碧泉书院、文定书院等也都得以延续,特别是在清朝办学更盛。湖湘学派推崇程朱理学、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通过书院积淀下来,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学风,对湖南的后代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明中后期心学兴盛,还是清乾嘉时汉学风行,湖湘地区的大部分学人都始终尊奉理学学统,并注意把理学与经世之学、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少有空疏之弊。
清嘉道以后,理学呈现出复兴态势,湖湘地区更是涌现了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多位理学之士。他们均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罗典,不仅自身尊崇理学,而且努力传播理学,为湖湘理学继南宋之后再度活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唐鉴,湖南善化人,为学笃守程朱,力辟陆王,著有《朱子年谱考异》《国朝学案小识》《省身日课》等。唐鉴官至太常寺卿,人亦高寿,弟子众多,曾国藩、倭仁、吴廷栋等均曾从其问学,影响巨大,堪称晚清复兴理学的宗主。陶澍,湖南安化人,尊崇理学,不废汉学。贺长龄,湖南善化人,“平生笃宗理学,以导养身心为主”(7)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70页。。陶澍官至两江总督,贺长龄官至云贵总督,二人位高权重,均不遗余力推广理学。贺熙龄,贺长龄之弟,执教城南书院多年,培育出左宗棠、罗泽南等众多理学之士。欧阳厚均,湖南安仁人,担任岳麓书院山长27年,以“忠孝廉节,敦品励行”立教,提倡“义理经济之学”,门下著录弟子三千,著名者有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等。胡达源,湖南益阳人,崇奉理学,执教城南书院期间,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著有《弟子箴言》一书,唐鉴、陶澍等曾联名向道光帝推荐该书,以传播理学价值观念。
咸同年间,湖湘地区又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继起,并借助湘军网络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理学群体。他们多就读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或涟滨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的濡染。以年岁论,则多为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人的后辈,无论是为学还是为政均深受前者影响。这一时期湖湘理学的核心人物为湘乡曾国藩,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创建湘军,利用师生、同学、宗族、姻亲、同乡等关系,将一大批有着共同学术旨趣和政治观点的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镇压太平天国,投身洋务运动,使湖湘理学爆发出巨大能量。他们撰写、刊刻理学书籍,兴办义学、书院,设立忠义局,修建祠堂,并借助政治军事力量将理学的价值理念推向全国。
二、修史辨学:晚清湖湘理学卫道的两种方式
按照理学的正统观念编修史书,驳斥各种被理学视为异端的学说,是晚清理学复兴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理学自形成以来即有修史辨学以维护圣道的传统,朱熹模仿春秋笔法,编《通鉴纲目》,“辨名分,正纲常”,以宣扬理学正统观念;张载、二程批佛,朱熹更是于佛老之学、陈亮的功利之学、陆九渊的心学等一切所谓异端邪说严加拒斥,无所不辨。延续至明、清两代,理学中修史辨学的传统一直绵延不绝。特别是晚清以来,社会政治发生严重危机,湖南理学家们更是热衷于秉承理学观念修史,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编修理学学术史,明宗续统,与各种被理学视为异端的学说作斗争,竭力树立理学的学术权威,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这一时期理学家编著的理学学术史中,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国朝学案小识》始作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全书收录清代前中期学者256人,共14卷,包括《传道学案》2卷、《翼道学案》3卷、《守道学案》4卷及《待访录》2卷、《经学学案》及《待访录》3卷,卷末另附《心宗学案》及《待访录》,列于正文之外,以示排拒。在体例上,《国朝学案小识》借鉴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和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是一部以学案提名的学术史著作。但它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该书以《提要》取代《凡例》,开篇即表明尊朱黜王、扬宋抑汉的著述宗旨,将传主按其对于道统传承的重要性分为五等,编制出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主干的清代学术发展史,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门户之见。
“《清学案小识》在道光中叶的问世,不是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面对汉学颓势的不可逆转,方东树、唐鉴皆欲以理学取而代之,试图营造一个宋学复兴的局面”。(8)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81、282页。因此,《国朝学案小识》成书之后,虽因门户之见深受一些学者的诟病,但还是得到了一大批致力于卫道的理学人士的称许和共鸣。湖南善化人黄倬称该书“正洙泗之坛坫”,“严洛闽之樊篱”,“为斯世扫榛莽,为后学正趋向,为希贤作圣者立一必至之正鹄”。(9)黄倬:《跋》,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末,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受唐鉴影响,云南理学名家何桂珍特著《续理学正宗》,并根据唐鉴的意见,续补清初窦克勤编《理学正宗》遗漏的道学传人,构建出更为完整的理学道统史。
除了编修理学史、分疏学术源流、表彰程朱理学,晚清湖湘理学士人还致力于辨学,从学理上驳斥异端学说。在这些崇尚辨学的理学家的心目中,辨学卫道与经邦治国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辨学卫道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更为深远。唐鉴、罗泽南、刘蓉等均“孜孜焉以崇正学、辟异端、正人心、明圣教为己任”(10)唐鉴:《罗罗山西铭讲义序》,《唐鉴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7页。。其中,罗泽南的《姚江学辨》最具代表性。
罗泽南,湖南湘乡人,除《姚江学辨》外,还著有《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等多部理学著作,是晚清时期理论体系最完整严密的理学家。秉承儒家的传统思维,罗泽南把政治的治乱、朝代的兴替归结为学术的正邪明晦所致,认为“世运之盛衰”系于“道之兴废”(11)罗泽南:《重修濂溪先生墓记》,《罗山遗集》卷五,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19-20页。,如果学术不正,世运必然随之而坏,“生民之祸遂有不可胜诘者矣”。因此要使天下百姓免于丧乱之苦,就必须昌明“正学”、“黜”“俗学”、“熄”“异学”(12)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第24页。。对于各种异端邪说,罗泽南按照它们对圣道、对人心危害的轻重缓急,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中对于王阳明心学的抨击是最为激烈的。
自朱熹与陆九渊之间围绕“道问学”与“尊德性”、“即物穷理”与“发明本心”等问题展开争论以后,“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别之间的论辩诘难始终持续不断,特别是在王阳明心学兴起以后,更是如此。明朝程瞳的《闲辟录》、陈建的《学蔀通辨》,清初张烈的《王学质疑》、童能灵的《朱子为学考》、陈法的《明辨录》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清中期以后,汉学兴盛,理学式微,程朱陆王之辨一度或息。然而,嘉道以后,沉寂多年的陆王心学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为了防止陆王心学借势复兴,罗泽南不得不重提程朱陆王之辨。(13)罗泽南:《与高旭堂书》,《罗山遗集》卷六,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3页。由于朱熹已经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进行了驳斥,所以罗泽南特著《姚江学辨》一书集中批判阳明心学。
《姚江学辨》著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分为上下两卷,约4万字,从学理上对朱王之辨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上卷主要依据程朱的“性”“理”至上论批判了王阳明以“心即理”说为核心的心性学说,下卷主要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否定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在体例上,该书基本上仿照朱熹的《杂学辨》,将王氏著作的原文按照不同问题摘引出来罗列于前,自著按文于后,引文辨文相间而行。
罗泽南对王学的批判得到众多宗程朱学者的高度赞扬。湖南理学家唐鉴、关中理学家贺瑞麟等都对《姚江学辨》一书津津乐道。笃守理学的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也说:“陆(九渊)、王(阳明)、陈(献章)三先生行谊、气节、功烈、政绩、忠节大端固皆可为后世师表,至其学之偏弊,则朱子、胡敬斋(居仁)、罗整庵(钦顺)各致争于生前,其后陈清澜(建)《学蔀通辨》、张武承(烈)《王学质疑》、顾亭林(炎武)《日知录》、陈定斋(法)《王学辨》、罗忠节公泽南《阳明学辨》(案:即《姚江学辨》)以及张杨园(履祥)、陆清献(陇其)、张清恪(伯行)、倭文端(仁)、吴竹如(廷栋)先生诸儒集中皆已辨之极其明矣。学者分别师法之可也。”(14)方宗诚:《志学录》卷八,清光绪三年(1877)刊本,第31页。括号之内字为作者所加。上述评论虽有一些溢美之词,但也可见《姚江学辨》在辨学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与唐鉴不同,罗泽南批王学并未停留在学术源流的分疏上,而是深入到王学的理论体系之中,进行学理上的辨析。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他对王阳明的心性学说、知行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驳斥,大有釜底抽薪的味道。可以说,罗泽南批王学,与唐鉴为理学家张目,互为补充,《国朝学案小识》长于历史源流的分疏,而《姚江学辨》长于学理的辨析,相辅相成,于扩大程朱理学的声势、推动其在晚清的复兴极为有益。但湖湘理学家修史辨学的目标不限于推动理学复兴,他们对“道统”建构的背后隐含着更重要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政教秩序。晚清理学对“道统”的建构与对“政统”的维护是联系在一起的,晚清理学复兴因此成为集思想与政治为一体的运动。
三、义理经世:晚清湖湘理学救时的主要途径
湖湘理学的经世色彩相当浓厚。早在两宋之际,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即强调以义理说《春秋》,著有《春秋传》,打下湖湘理学强调经世致用的基调。其子胡宏虽然终生不仕,但始终关心社稷安危,曾写下《上光尧皇帝书》,希望宋高宗能够“正三纲”“行仁政”,其代表作《知言》不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理论体系,而且突显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胡安国养子胡寅不仅是一位理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其立身行事皆以“尊王攘夷”为宗旨。胡宏弟子张栻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其治学、授徒、整军、为政无不强调“经济之学”,最终奠定湖湘学派的经世特色。
有赖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书院群的传承,明清时期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虽一度隐而不彰,但始终不绝如缕。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际,湖湘地区更诞生了一代大儒王夫之。王夫之曾就读于岳麓书院,青年时即关心时政,与同窗好友结成“行社”。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以读经著史表达经世之志,著有《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等约百种,进一步将湖湘理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晚清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
清嘉道年间,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社会危机进一步凸显,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15)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8页。,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他们皆曾就读于岳麓书院,为山长罗典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罗典,湖南湘潭人,担任岳麓书院山长27年,期间着意恢复和重建湖湘理学经世学统,为“湘系经世派”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湘系经世派”的核心人物陶澍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16)陶澍:《陶澍集》(下) , 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99页。,将一大批经世人才聚拢在身边,日“以文章经济相莫逆”(17)魏源:《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48页。,是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忠实的践行者和有力的推动者。邓显鹤编辑刊刻《船山遗书》、贺长龄、魏源主持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都离不开陶澍有力的支持。对此,清流党人张佩伦评论说:“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18)张佩伦:《涧于日记》已卯下,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188页。括号内字为作者所加。
在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直接影响下,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湖湘理学士人崛起于咸同年间,使湖湘理学的义理经世特色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出山之前,他们致力于以“礼”化“俗”,通过在家乡讲学施教,力图使地方上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道”的熏陶。在出办湘军之后,他们借助日益强盛的兵威,更将影响扩大到全国。利用宗族制度, 恢复社会秩序;改良吏治, 维护社会秩序;转变风尚,重塑理学价值观念。(19)张晨怡:《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正如民国哲学家贺麟所评:“在前清咸同年间,清朝中兴名臣如曾涤生、胡润芝、罗罗山三人,均能本程、朱之学,发为事功。”(20)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19页。
概而言之,晚清湖湘理学顺应了嘉道以来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的学术转向,进一步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并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特色。晚清复兴湖湘理学的宗主唐鉴在《国朝学案小识》中提出要“守道救时”,他说:“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21)唐鉴:《提要》,《清学案小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页。将“守道”与“救时”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内圣”与“外王”的合一。这也是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群体立场。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将“经济”从“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中的“义理”独立出来,进一步提出“孔门四科”,强调“义理经济”合一。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2)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42页。对于“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曾国藩也曾作如下剖析:“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23)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9页。将“内圣”与“外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同等重要。事实上,“内圣外王”虽出于《庄子·天下》,但自儒学诞生以来,就成为儒家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为了应对唐五代以来的精神危机和政治乱象,理学在宋代应运而生,本身就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实践。然而理学发展到后期,很多理学流派往往过于强调心性,将“内圣外王”割裂开来,日益脱离社会政治现实。在晚清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刺激下,湖湘理学士人重拾经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征形成了新的学术特色,扩大了经世之学的内涵。依照是否追求“经世”,史革新将晚清理学家划分为以倭仁为首的理学主敬派和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事实上,主敬派与经世派的分歧不是要不要“经世”,而是如何“经世”。理学经世派致力于求强求富,主敬派亦有图强言论,二者也均积极投身于实际政治,并在“同治中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区别在于,主敬派的施政纲领主要为道德论在政治上的延伸,而以湖湘理学士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世派则强化了理学资源中那些长期不被程朱后学重视的内容并有所发展,强调“外王”不能由“内圣”自然生发,而必须脚踏实地为秩序重建进行知识储备与政治实践。他们以义理经世为救时的主要途径,不仅纠正了理学末流“重内轻外”的弊端,推动了晚清士林讲求经世之学风气的形成,而且身体力行,在军事、政治、文教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晚清湖湘理学家的心目中,经世不仅是政治追求的过程,也是理想的境界,因此他们始终强调对“学统”“道统”“政统”三位一体格局的维护。可以说,经世致用虽非晚清湖湘理学所独有,但其义理经世特色却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既有主张,又有实践,从而与同时期趋向于经世的今文经学、汉学等儒学其他流派显著区分开来。
四、中体西用:晚清湖湘理学对西学的吸纳
理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中国步入近代才开始出现的新命题。关心时务的晚清湖湘士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符合时代需要的回答。与晚清时期一般理学家坚持“夷夏之辨”、完全抗拒西学的传入不同,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湖湘理学士人主张有限度地接受西学,赞同“中体西用”理念。
对于西学这一强势外来文化,倭仁、贺瑞麟、于荫霖等理学主敬派主张一概排斥。“持这种观点的人仍然用传统的‘夷夏之辨’观点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中外形势”,“拒不承认中国有落后于人的地方,不承认西方国家有先进发达之处,甚至连已经成为事实的西方经济科技的先进性也不承认”。(24)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4、165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同治六年(1867)倭仁反对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学事件。在奏折中,倭仁写道:“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5)《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页。在同文馆之争期间,倭仁所上奏折虽以倭仁个人的名义呈递,但实际上却是众多理学人士商讨的结果。在论辩期间,倭仁、徐桐、李鸿藻、翁同龢等经常聚在一起研究对策,“商略文字”。(26)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557页。可见,倭仁严守“夷夏大防”,代表了理学主敬派的群体立场。理学主敬派的主张,貌似纯正,实际上背离了儒学兼收并蓄的本来宗旨。儒学之所以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历久弥新,始终具有生命的活力,正在于对各家各派思想的不断会通融合。因此,理学主敬派于西学严加拒斥,无异于加速了理学乃至儒学在近代的衰落。
西学东渐虽然在近代才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但从理学发生过程中追根寻源,理学家应对异质文化,也是有一定经验可以借鉴的。中国历史上应对外来文化的传入主要有两次:一次应对的是佛教,一次应对的是西学。理学之产生,正是为了应对佛教传入并广泛流传以及道教盛行对儒学根基的动摇的挑战。经过一番“出入佛老”的努力,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老思想以弥补儒学思辨性不足的弱点,构建了一个十分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理学家虽无不以佛老为异端,但是理学的哲学体系中却渗透着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晚清湖湘理学之所以在咸同年间大放异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学的吸纳。相对于汉学家,湖湘理学家率先趋于经世,并以经世之学为接引西学的媒介,在知识转型的基础上进行思想转型。可以说,“清末理学派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正是理学的兼容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27)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0页。。
晚清湖湘理学对西学的吸收融合,最初主要在于对“西技”的学习。曾国藩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8)曾国藩:《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摺》,《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272页。左宗棠也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29)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27页。二人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赶超西方。正是基于此种理念,他们纷纷投身到洋务运动的洪流中去,“采西学,制洋器”。而随着与西方接触程度的加深,他们逐渐认识到西学中还有更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30)郭嵩焘:《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45页。,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取法西方现代政治制度。
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上述言论在当时遭致包括理学主敬派在内的保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和抨击。但是,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坚信,他们对西学的吸纳正植根于理学的内在精神。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中最重要的理论家罗泽南说:“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禹、汤、文、武即生今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尽行者。道无古今,用有古今也。必泥其迹而行之,非通儒之经济矣。”(31)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第11页。他强调“道无古今,用有古今”,道不可变,用则可因时而变,这正是洋务派“变器不变道”的理论基础。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学习“西学”,目的是发展“中学”。因此,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他们格外强调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即使是汲取西学程度最为深广的郭嵩焘,他的洋务思想也是建立在“理”“势”“情”“几”等理学基本观念基础之上的。在中西思想的激荡中,夷、夏、体、用、学、术、理、势等传统理学概念获得了新的阐释。西学对湖湘理学发生作用,并不一定指那些为湖湘理学所吸纳的部分,形成争论也证明影响已经产生,湖湘理学的思想转型就在此过程中进行。
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对“中体西用”的提倡和实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甲午战争后,“中体西用”还逐渐取代“崇儒重道”,并演化为清政府的文化政策。随着中国学习西方程度的加深,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西化”日渐等同于“国际化”,“中体西用”说由被顽固派斥之为离经叛道,到被革命派斥之为狭隘保守。对此,钱穆的观点还是比较公允的。他说:“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3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00页。钱穆对“中体西用”说基本文化内核的积极意义进行了正面的评价。
五、晚清湖湘理学的学术地位与价值
评价晚清湖湘理学,需要将其置于理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的框架之内。“清代理学上承宋、元、明,历经近三百年”,“前期兴盛,中期式微,晚期有所复兴又走向衰落”(33)龚书铎:《绪论》,《清代理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28页。。晚清湖湘理学初兴之嘉庆年间,理学虽然仍被清政府尊为官方哲学,但是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正如日中天的乾嘉汉学无法相比。道光朝以后,“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得到强化,汉学由盛转衰,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晚清理学复兴,主要发生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张栻等宋代理学家当年讲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其中,湖南地区宗奉理学的人数尤多,并形成了以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为代表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
在晚清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湖湘理学群体与其他地区的理学人士相比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道光二十年(1840),湖南理学家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以唐鉴为核心,当时在京为官,来自全国各地的理学家如曾国藩(湖南)、倭仁(河南)、吴廷栋(安徽)、吕贤基(安徽)、何桂珍(云南)等都从其问学,一改乾嘉年间京内理学沉寂的局面,京师理学群体正式形成。唐鉴对京师、湖南乃至全国的很多理学士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除了自己致力于编修《国朝学案小识》外,还积极推动其他理学士人进行理学著作的编撰。何桂珍著《续理学正宗》、罗泽南著《西铭讲义》,都与唐鉴有过密切的学术交流。一时间,在道光朝形成了一个修史辨学、传继道统的高潮,这也是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表征。由于对唐鉴“守道救时”说的领悟各不相同,从唐鉴问学的理学士人或强调“守道”,或强调“救时”,最终形成了两种理学治学路向。可以说,晚清理学主敬派、理学经世派均发端于此。主敬派的施政重点在于“正君心”,而以湖湘理学士人为核心成员的经世派的施政纲领基于更充分的知识储备更切中时弊,这也体现了晚清湖湘理学重“实政”对清初理学重“实学”的超越。
咸同时期,特别是同治年间,晚清理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以倭仁为核心的理学主敬派在京师多居于高位,以曾国藩为核心的理学经世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势力也急速扩张,呈现出理学盛极一时的局面。“尽管宗理学者不同于程朱理学本身”,但“宗理学者政治地位的高下一定程度上确又能转移学术风气,体现学术盛衰”(34)张昭军:《清代理学史》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理学这一兴盛局面的形成,与湘军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湘军集团不但是一个军政集团,还是一个文化集团,其核心首脑基本由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组成。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主体,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开掘出理学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并积极将自己的义理经世主张付诸实践。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和“同治中兴”关系密切,互相推动,而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在其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晚清湖湘理学的本质,不仅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在近代大变局中,晚清湖湘理学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对此,清末湖南士人曾廉评价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鑫、李续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不谓非正学之效也。”(35)曾廉:《应诏上封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93页。
史革新在研究晚清理学时曾指出:“近代社会的发展给传统理学提出一系列的新问题,也迫使这个古老的学派不得不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成功的一面,又有失败的一面”。(36)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页。理学虽然在晚清一度复兴,但终如昙花一现。光绪朝以后,在西学的冲击下,理学后继乏人,迅速衰落,湖湘理学也是如此。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核心人物曾国藩病逝于同治十二年(1873),重要成员郭嵩焘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至此,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已经凋零殆尽,影响渐失。此后,湖南地区虽有谭嗣同、杨度等继起光大湘学,但其学术已逸出理学范围,无法用理学涵盖,晚清湖湘理学中再未产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究其原因,湖湘理学虽注重因应时代,但由于在学理上鲜有创新,最终没有达到呼唤新生的目的。对于西学,湖湘理学基于经世理念,虽有所吸纳,但时变势易,与宋代理学初兴之时对佛教的包孕再生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反而动摇了理学的根本,加重了民众的思想文化危机。
中国历史上佛教东来并不伴随着武力入侵,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却与船坚炮利相伴而来,可见,晚清中国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 佛教于西汉末由印度传入中国,流传日广,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宋代以来佛教则被彻底中国化、儒学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应对佛教的过程中,儒学经过长时间的低迷,本身也如凤凰涅槃般,孕育出理学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晚清中国,国家衰败,社会停滞,西学强势,使得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困难重重。近代以来,儒学各派面对危机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学术更新,其中以晚清湖湘理学最具代表性,但最终都没有改变自身乃至儒学总体衰落的命运。事实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曲折而漫长,如不过分苛求前人,晚清湖湘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我们今天在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充分发挥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的过程中,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