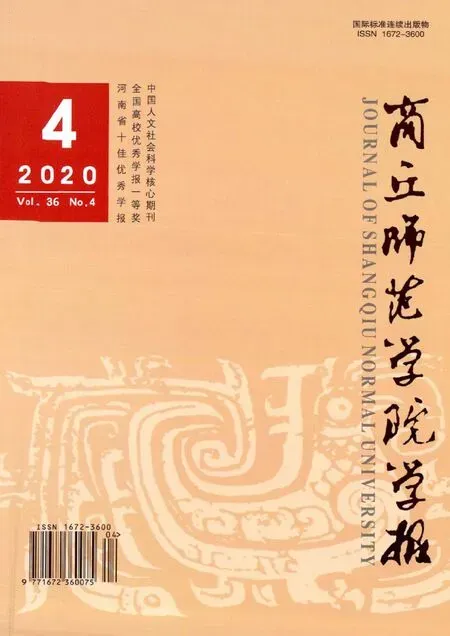德性与政制:列奥·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解读
2020-02-25景珊珊
景 珊 珊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施特劳斯学派代表人物,在美国80年代后期以来的保守主义革命中被誉为“共和党革命的教父”“当今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6。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被引介到中国以来,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自由教育亦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施特劳斯从古典政治哲学和当代西方现代性危机的高度对自由教育之真谛的揭示,赋予了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西方自由教育理念之丰足意蕴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对我们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思考自由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意义具有诸多裨益和启示。
一、古典政治哲学与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是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富有复杂性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一般的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中,概念的演变备受关注,厘清概念之历史演化对准确理解概念本身与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回溯自由教育的概念史,将有助于我们认知施特劳斯在何种历史意义上使用此概念,基于此,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脉络方得以展开。
(一)自由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化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译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或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概念通常作为同义语使用。国内常常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谈及“自由教育”时会用“通识教育”指代,论述“通识教育”时又会完全将其视为“自由教育”。实际上,Liberal Education与General Education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历史演化关系,二者的语义及其教育学意涵是有差异的。
在古希腊本源上,与英文liberal arts对应的是“Eleutherion epistemon”一词,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意为适合于自由人的科学或者文雅、高尚的科学。这种自由人的科学是指公民的科学(或技艺),与非公民阶层如奴隶(或工匠)等的技艺相对。亚里士多德认为,适合于自由人的活动不是谋生或生产必需品而是政治和哲学,并以参与政治、从事哲学生活为最终目的。同时,自由人科学也是自足的,非实现某些目的之手段,学习的是诸如音乐、绘画、文学等非用于谋生的、业余性质的科学。在拉丁文概念中,自由人技艺(artes liberales)与英文liberal arts相对应,该词在西塞罗著作中零星出现过,可译为适合于绅士或自由人的技艺。而在西塞罗《论雄辩家》等著作中出现的“Liberaliter educatione”,是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Liberal Education的概念。Liberaliter是liberales(liberalis)的副词形式,Liberaliter educatione一词从字面理解即是自由人的教育,考虑到西塞罗思想所指,西方学者一般将其译为“绅士教育”[2]。
16世纪末,英国人通过翻译创造出“Liberal Education”这个词语,但直到17世纪,该词并未被普遍运用,在教育学著作中更常出现和使用的概念是博雅科学(liberal sciences)和博雅技艺(liberal arts)[2]。 到18世纪时,Lib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方在英语词典中得到具体解释,意为“高尚(高雅)的教育”,在一些教育著作中也得到专门的使用,具体指一种广博的、绅士的教育。自此,绅士与非绅士阶层之间的划分取代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奴隶与自由人的划分,liberal的含义也从“适合于自由人的”演化为“适合于绅士的”之“博雅”教育。
到19世纪时,在Liberal Education的语义中,“博”和“通”的层面而不是“雅”的层面越来越被强调,成为与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相对的教育类型,这一界定被1828年的《耶鲁报告》与1852年的《大学的理念》同时采用[2]。同时,这一概念与18世纪末出现并逐步风行起来的Gen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成了同义词。19世纪初,作为与专业教育相对的通识教育这一概念逐渐多见,马修·阿诺德、威廉·休厄尔、约翰·密尔等均以同义词的形式在其著作中同时使用Liberal Education和General Education这两个概念[2]。可以说,Liberal Education这一概念从18世纪强调的“雅”与“俗”之别转向19世纪工业社会背景下的“通”与“专”之别。
自19世纪末起,liberal的语义再次发生转变,原有的“文雅、宽宏、绅士般”等语义消失,进而主要被理解为“自由的、解放的、通识性的”[2]。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背景下,Liberal Education被理解为所有自由公民的权利,并以促进其心智解放,习得普遍的、一般性的文化修养,有效行使和履行公民职责为目的,由此Liberal被赋予了“自由的、通识性的”等含义。在20世纪的美国,Liberal Education即已开始从针对绅士阶层的教育变成了对所有公民的通识性教育。
施特劳斯论及自由教育时,均使用Liberal Education一词。他指出,Liberal一词具有政治意义,但其原初的政治意义与当今的几乎是对立的,它是针对奴隶制度下自由人与奴隶而言。原初意义上的自由教育是相对于奴隶的自由人的教育,通过研习政治与哲学等科目来培养贤人(gentleman);贤人总是关注最重要的事情,关注灵魂和城邦的良好秩序;对于贤人的自由教育,首先在于性格和品位的塑造,经过自由人技艺的养成,贤人最后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基于此,施特劳斯总是考虑“教育的最好或最高目的,即过去对圣贤王者(perfect prince)的教育”[3]321。实质上,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自由教育的回归,是在自由教育的古希腊源头上重新审视自由教育对现代个人与社会的意义。这种审视与同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教育倡导者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不同。赫钦斯在不同的著作中分别使用Liberal Education 和General Education,他在保有Liberal Education的古典原意的基础上,更侧重于其现代含义即General Education的运用,其实质是将古典自由教育向现代的所有公民的自由教育,抑或说人人的自由教育转变。可以说,赫钦斯的自由教育正如前文所述,已经是一种现代意义的转化。相较于赫钦斯,施特劳斯并没有对自由教育进行现代性的转化,而是基于其古典政治哲学观念,对自由教育之意义进行了另一番引人入胜的思考。
(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与自由教育
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施特劳斯开篇即指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4]31。那么在什么样的文化中呢?施特劳斯进一步指明,文化在当今主要意味着“依心灵(mind)的本性培育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4]31。这种对心灵的培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with the proper care),阅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the great books)”,即“自由教育在于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对话”[4] 35。施特劳斯何以如此界定自由教育的内涵?其背后意指又何在?要理解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观,则离不开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认识。可以说,其政治哲学思想构成了其对自由教育的认知机理,其自由教育思想正是其政治哲学思想在教育上的延伸。
作为通过学术的沉思生活、审视时代弊症的思想者,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西方问题的根源孕于西方的现代性之中,而西方现代性的根源则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之果[5]1-2。因此,对抗现代性,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成为施特劳斯思想的中心议题。施特劳斯认为,原初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出现,是人们关于诸“善”(the good)的思考,是对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的追求,它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政治事务,“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6]3。这种古典政治哲学的宗旨即是要解决政治论争,并使得政治秩序成为最能与人的卓越品质相称的秩序[6]77。然而,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带来了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性一般被作为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对天堂生活的期待被依靠纯粹的人类手段于尘世之中建立天堂的信念取代,伴随着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使得古典政治哲学在当今已处于衰微甚至腐烂的状态,引发了西方现代性的危机。这一危机的重要表征即是西方已不再能确信自己的目标,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能确信什么是好与坏,什么是对与错[7]38。而施特劳斯也认识到人们通过“政治”什么也改变不了,要改变只能在教室里[8]345。由此,施特劳斯将政治哲学落脚于教育,通过在大学中进行自由教育来对未来公民与立法者施予影响[1]81。
施特劳斯指出,原初意义上的自由教育是由古典政治哲学支撑,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目标是哲学生活,因而人通过这种教育使自己成为贤人(gentleman),社会的最好形式是由贤人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进行统治。柏拉图也认为,最高的教育就是哲学。哲人是在最高程度上拥有了人类心灵能具备的一切优异,能够成为统治者。施特劳斯认为,我们虽然已不能成为这样的哲人,但可以进行哲学化思考,通过倾听最伟大心灵之对话,即自由教育来实现。可以说,自由教育是为了研习哲学所作的准备,通过自由教育,使得人接近最高目的哲学的生活方式,拥有节制与德性。
然而,西方现代性所造就的民主大众社会(democratic mass society),已不是少数贤人的统治,也背离了富于德性和智慧的真正的民主政制,而是被没有任何智识与道德努力的最低劣的能力极为廉价地占据的大众文化的统治,对真正的民主具有腐蚀性影响[4]33。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则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能够对抗大众文化中固有的只产生“没有精神或远见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的倾向[4]33。自由教育向人们呼唤人的卓越。它通过对完美的高贵气质(perfect gentlemanship)和对人的卓越(human excellence)的培育,能够唤醒一个人自身的卓越和伟大,最终使人从庸俗(vulgarity)中解放出来,给予人对美好事物的经历。因此,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是一架阶梯,是在民主大众社会里建立贵族政制(aristocracy)的必要努力,由此途径,可以从大众民主上升至原初意义上的民主[4]33,也即回归到古典政治哲学之所求的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概言之,自由教育蕴含着对德性生活与良善政制的追求。
二、自由教育与德性生活
施特劳斯指出,自由教育在于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对话,其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种有“文化”的人是具有哲学化思考方式、接近柏拉图最高教育的——哲人的人。通过与伟大心灵之间的对话,能够使人从庸俗中解放,赋予人完美的高贵气质和卓越的品质,引导人走向富有“哲人”德性的生活。
(一)伟大著作:与伟大心灵的对话
与伟大心灵之间的对话,是通过伟大著作的阅读达成的。施特劳斯认为,心灵的培育需要老师,那些“最伟大的心灵”即是老师。然而,鉴于这样的老师非常罕见,我们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得遇其一,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伟大的书来接近最伟大的心灵[4]31。
什么样的著作才是施特劳斯所讲的伟大的书呢?施特劳斯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出发,其理解亦区别于我们一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施特劳斯指出,哲学在于探求真理,哲学是“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对整全(the whole)知识的探求”,政治哲学“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事物的哲学的一个分支”[6]2-3。对于施特劳斯来讲,伟大的书中蕴含的即是对整全事物与真理的探讨[9]389-390,由此,“根据事物本身的状况,我们可以期望从正确理解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中比从自然科学(sciences)中获得更为直接的帮助,从知觉(perceptivity)和审慎(delicacy)中比从几何学的精神中获得更为直接的帮助。没有什么会比伟大著作是更好的开始了”[3]344。同时,施特劳斯也指出,我们应当阅读的最伟大的书绝非仅仅是西方的,受限于语言之贫乏,成为我们阅读非西方国家的最伟大的书之障碍[7]320。
施特劳斯主张“善优先于权利”,认为自由教育应该是一种“教养教育”,应该使人追求卓越的品性[10]。自由教育作为与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不断交流,即便不说是谦逊(humility),也是一种在最高形式的节制(modesty)中的锻炼[4]36。这种节制即是一种适度,而“适度是德性的特点,德性是选择适度的那种品质”[11]47-49。这种锻炼能够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和卓越,使人努力追求不朽之事物,过一种与我们自身最好之部分相适合的生活,一种符合德性的生活。施特劳斯指出,自由教育与人的灵魂有关,它对机器没什么作用,“如果自由教育成为机器和产业,除了在收入和公众效应,在表面的光彩(tinsel)和魅力方面,它将与娱乐业无二”,自由教育在于对远离喧嚣的心灵的内在的、自然的滋养,而非追逐舞台之光[3]345。因而,自由教育要求我们“冲破智识者(intellectuals)及其敌人的名利场(Vanity Fair),冲破这名利场的喧嚣、浮躁(rush)、无思考和肤浅低级(cheapness)”[4] 36,通过与最伟大的心灵的对话,使我们能够成为专注和温良的倾听者,能够将所接受之观点都仅仅当成意见(opinions),将普通意见视为与最陌生、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的、可能错误的极端意见,从而成为明智的裁决者[4]36。
亚里士多德有言,“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11]26,这正是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旨归。施特劳斯指出,古典政治哲学知道邪恶无法根除,因此人对政治的期望必须适度(moderate),宁静(serenity)或崇高的清醒(sobriety)正是激励着政治哲学的精神,由此古典政治哲学能够摆脱所有的狂热主义[6]20。而这也正是自由教育在最高形式的节制中之锤炼的成果。
(二)隐微主义阅读:与伟大心灵的最佳对话方式
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with the proper care)的方式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为何要以“特有的小心”呢?因为与伟大心灵的对话没有我们的帮助就不会发生,“最伟大的心灵们在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换为对话,使他们的肩并肩(side by side)变成一个整体(together)”[4]35。这种“特有的小心”,在施特劳斯一生的为学实践中则以字里行间的隐微主义阅读方式被淋漓尽致地体现。
隐微主义阅读源自哲学上的隐微写作。因为担心受到迫害,或因其他缘由,通过在字里行间采用隐微而不是直白的写作技巧,来传达非正统的思想,而表面上仍用传统的虔诚进行掩盖。由此,形成了显白的(exoteric)和隐微的(esoteric)两种教诲。对于一般人,只能看到字里行间的显白教诲,而对于能够领会其思想或懂得隐微阅读的人,则能看到字里行间的隐微教诲。亚瑟·梅尔泽在《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中指出,隐微主义写作自古有之,直至18世纪上半叶仍然被众人所知,被公开讨论,但到了19世纪,这种现象却逐渐被人淡忘,到了20世纪,则已湮没无闻,是施特劳斯又重新发现了它,施特劳斯“让我们回忆起自19世纪以来被我们想当然地遗忘的东西——人们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以往伟大作家所写的一切,也不应该相信他们在作品中所公开的一切就是他们内心想说的一切”[12]3。亚瑟·梅尔泽归纳了四种隐微主义写作方式,包括自卫性隐微主义、保护性隐微主义、政治性隐微主义、教学性隐微主义。自卫性隐微主义是出于防止社会给作者造成的危害;保护性隐微主义是为了防止作者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即向社会传播危险的真相;政治性隐微主义是为了不受阻碍的宣传社会的政治(文化、智识、宗教)改革思想,推动社会变革;教学性隐微主义,是少数富有才华之人的哲学教育,仅只教诲给能够听懂其思想的人。
显白教诲是每个人都能从文本中直接读出的字面之意,隐微教诲则是只有掌握隐微阅读技艺,通过隐微阅读方式才能领会的意义。施特劳斯认为,阅读伟大的书就在于读出伟大的书中的隐微教诲。“隐微主义与进步方法截然对立,它是一种迫使思考者自力更生的策略,是一种强迫他们自足自立,而不是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站在历史中的策略”[12]555。隐微主义的阅读方式要求能够悬置自己的问题而集中关注于作者的问题,依靠作者直接或间接的表达来理解其意,尽量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信息,基于作者的术语与前提进行“如实直书”式的理解,避免将现代术语和前提混淆其中使用[13]1048。因此,施特劳斯所主张的这种对伟大著作进行隐微主义阅读的方式与著名的以赫钦斯为代表的永恒主义的伟大著作阅读方式不同。永恒主义强调伟大著作与现代社会的契合,重视伟大著作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强调批判性阅读和阅读的大众化,在编排上运用现代性的观念范畴去整理,将现代人认为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和观念提取出来,形成阅读伟大的书的观念框架[14]。与此相反,施特劳斯认为,不应该利用现代的眼光去评判或解释伟大著作,对其的现代编撰也是“以今知古”的非恰当阅读方式。永恒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德勒(Mortimer J.Alder)也明确指出与施特劳斯之不同,认为永恒主义是辩证的(dialectical)教法,是让学生自己思考。施特劳斯是教义式(doctrinal)的教法,是让学生学习教导者的想法是什么[15]。由此可以看出,施特劳斯以隐微主义阅读伟大著作的方式与永恒主义的显著差异。此外,基于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中“古代与现代”的对立,使得他回到的主要是古代的伟大著作。而永恒主义把伟大著作视为所有时代的人类思想的精华,其著作选择面宽广,涵盖了近现代的科学等方面名著[14]。
此外,隐微主义阅读也是施特劳斯对抗历史主义,消解其不良影响,引导人去追求卓越与德性,探寻整全真理的重要方式。施特劳斯指出,历史主义用现代国家、现代政府、现代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和文明等问题,取代“政治事务之本性、国家、人的自然本性这类问题”。历史主义认为,对这些问题的任何回答和表述必然受到“历史性的制约”,要依赖于它在其中得到表达的具体情境。因而,关于这些普遍性的问题,“没有一种答案,没有一种论述或精确的表述,可称为普遍有效,对一切时代都有效”[6]49-50。历史主义消解了对人类诸事务之本性、对最好或最正当的问题的追寻。亚瑟·梅尔泽通过对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理论的研究,明确指出“施特劳斯的隐微主义理论通过多种方式构成了对历史主义高度原创、多层次、强有力的攻击”[12]511,由此实现将人从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歧路”中引导回来,通过与伟大心灵的真正对话,走向哲学的德性生活。
三、自由教育与民主政制
施特劳斯指出,“人无法抛开好社会的问题,人无法通过听从历史或任何其他不同于他自身的理性的力量来摆脱回答这一问题的责任”[6]19。好的生活之后,必然有对好的社会的渴慕,二者可说“唇齿相依”。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危机的思考,罕有不经过对教育问题的反思而进行的[16]35。施特劳斯通过将政治哲学落脚于自由教育,并由其后继弟子形成的施特劳斯学派传承延续,来影响未来公民和立法者,以古典政治哲学为路标,致力于对最佳政制的追寻,以使得现代民主政制由受到自由教育的智识者和富有道德努力的人所掌握。
(一)最佳政制与自由教育
在施特劳斯看来,政制(regime)是政治哲学的指导性主题。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是秩序、形式,能够为社会赋予特性,是“作为共同生活的生活的形式(form),是社会的生活和生活在社会中的方式”。政制意味着“整全”,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生活风格、道德品味、社会形式、国家形式、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精神”[6]25。政制涵盖了包含着个人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的所有重要的方面。不过,政制富含多样性,不同的政制会提出不同的主张,这些主张会超出任何特定社会的界限,因此会彼此冲突,这又迫使我们去思考在相互冲突的政制中,哪一种政制更好,哪一种又能成为最佳政制。施特劳斯认为,正是这一问题引导着古典政制哲学。
那么,古典政治哲学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何种最佳政制呢?首先,施特劳斯指出,古典哲人能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新(freshness)而直接的目光看待政治事务,能够从开明的(enlightened)公民或政治人的角度,看清楚他们没有看清或根本看不到的政治事务[6]19。其次,比之所有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哲学问题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能从古典政治哲学中找到,是因为所有古典政治哲人都从根本上、一致性地将德性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6]31。“什么是德性?什么是人一旦拥有便具有最高的统治正当性的德性——什么是人人心悦诚服,或因无可辩驳的理据而默认的德性”[6]78?这一问题成为古典政治哲人一直苦苦探求的所在。通过解答这一问题,古典政治哲学认识到“最有益于德性的秩序是贵族共和或混合政制”[6]31。古典政治哲学因而反对将自由作为原则的民主制,因为人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德性,自由既可是作恶的也可是行善的,这种自由作为目标是含混的。而德性通常只有通过教育才会出现,即“通过塑造性格,通过养成习惯”,这要求闲暇,而闲暇反过来要求一定的财富[6]27。基于这个原因,“民主制或多数人统治就是由未受教育者来治理”[6]28,未受教育很难严格遵循德性的生活,因而非最佳政制。
然而,这种古典的解决方案被所有现代政治哲学指责为不现实,古典政治哲学也认识到最佳政制的实现取决于各种事物的汇聚与巧合,其落实取决于机运[6] 25-31。那么在现代民主制下,如何达成政治生活的德性目的,或者转变民主制非由受教育者统治的境况呢?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一问题无疑要落实到教育—自由教育之上。施特劳斯指出,虽然民主制已经发现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今天所说的教育“往往并不意味着适当的教育,即性格的塑造,而是指导与培训”;此外,即使想塑造性格,也存在非常危险的倾向,“把好人等同于有风度的人、有协作精神的家伙和‘老好人’,也就是过分强调社会德性中的某一部分,相应地忽视那些在私下,更不用说在孤独中,成熟起来的德性”[6]28。现在,现代民主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危险,“它看到自己被迫思考通过返回古典派的教育概念——一种从未被想过是大众教育的教育,只是对天性适合的那些人的更高和最高的教育来评价自己的水准和可能性”[6]29。
这种教育就是施特劳斯所倡导的自由教育。自由教育在最高目的上是一种哲人的教育,是进行哲学化思考的教育。政治哲学的最高主题即是哲学生活。“哲学不是一种教诲或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提供了解决使政治生活变动不居的问题的方案”[6]78。因此,政治哲学“尝试将有资格的公民,或更准确地说,将他们有资格的后代从政治生活引入哲学生活”[6]81。这一目的通过自由教育得以实现。自由教育不仅是现代民主制下对抗大众文化的解毒剂,使得人从缺乏智识和道德努力的“贫瘠”和“庸俗”中解放出来,也使得受过自由教育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好公民,“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在最高的层面上履行好公民的责任”,“能够平息内争,通过劝说在公民中创造共识”,能够具备政治生活更高类型的政治理解力,成为立法者,“关心的是他为之立法的那一个共同体”,能够提出事关一切立法的最基本最普遍的问题,这将成为“最具建构性的且真正具有建构性的政治知识的主题”,成为“最优秀的仲裁者”[6]71。这样,由此受过自由教育者构建下的现代民主政制,才能远离人们对永恒的遗忘,远离人最深的欲望,进而远离种种首要的难题,才能使得现代人从“试图成为绝对主权者、变成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以及征服机运所付出的代价”中解放出来[6]46。
(二)施特劳斯学派的传承
施特劳斯学派是施特劳斯及其弟子所形成的一个以保守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流派。这一学派囊括了“带有施特劳斯著作之特色的一系列常见问题或疑问,古今之争、哲学与诗之争、理智与启示之间的张力”等[17]26。除施特劳斯外,主要代表人物有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威廉·盖尔斯顿(William Galston)、赛斯·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哈里·雅法(Harry Jaffa)、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等人。
自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培养出第一批学生起,施特劳斯学派形成了一套非常独特的诠释西方从古到今的重要思想文本的方式,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就。施特劳斯学派的弟子们继承了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理念,尤其重视本科的自由教育,带领学生研读传统的伟大著作则成为施特劳斯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1]23-29。施特劳斯学派的弟子们除了一些留在大学继续做学者外,多数人后来直接走向了美国的政治舞台。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界,施特劳斯学派延续了施特劳斯对自由教育与民主政制的看法,都通过所接受的自由教育传播和实践其所秉持的政治哲学理念。在美国政界,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政治与宪法研究领域俨然成为一大派,即便其中专攻古典的学生往往同时也研究美国政治。在施特劳斯学派看来,现代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问题,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美国的危机[1]26。
不同于其他直接参与政治哲学实践的弟子,施特劳斯学派中对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最直接和最有影响的传承人——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掌门人阿伦·布鲁姆主要作为一名大学学者,通过大学自由教育理念来为民主政制的问题寻找“药方”。布鲁姆在1987年出版了著名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该书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不仅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销售纪录,引发的各种评论更是几乎将整个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该书也被认为是对施特劳斯思想最通俗的发挥,是“要用‘哲学家暴君(philosopher despot)’来取代美国民主政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是用来引诱美国人民的“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1]37-38。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延续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第三波浪潮”的批判[18],从该书标题来看,走向“封闭”是与“开放”对应的。布鲁姆认为,开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现代民主方式所造就的所有人和所有生活方式都获得相同的地位的僵化、冷漠的开放;一种是不满足于迷惑人们,通过启迪探索知识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安于现状的开放。已成为我们文明社会的一种文化和习见的第一种开放,羁绊和阻碍着第二种真正的开放的实现,由此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封闭,使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进入“洞穴状态”[19]244。为了使现代社会摆脱这种洞穴困境,使我们的思想由封闭走向真正的开放,布鲁姆呼吁在大学中阅读古典的伟大著作,恢复自由教育的传统。这样一所好的大学“不是费力向学生提供可以从民主社会中得到的经验,而是提供民主社会中没有的经验”,它能够给出我们关于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能够告诉我们“有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应该被每一个人思考,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作为哲学生活存在的活的证明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家”[20]264-275。总之,在布鲁姆看来,大学具有很大作用,是一个可以用来追求哲学思考、抵制现代民主弊端的伟大机构[19]256。
四、结语
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其古典政治哲学所反对和追求的目标,而对现代民主政制的反思则构成了其现实起点。基于对人与人之间平等性的强调,现代民主理论试图拉平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差异,使人忘记了人类的卓越与德性等更高的教育目标;大众文化的盛行,使人类正在走向集体的平庸;专业化的趋势使人不再渴望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对整全真理的探求,使人与人之间无法就最重要的事情达成共识。这一切的解决之道,在施特劳斯看来,都寓于与伟大心灵进行对话的自由教育之中。然而,施特劳斯也意识到,“不能期望自由教育会成为普遍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它将总是一小部分人的义务和特权”[3]344。从这个意义上,自由教育不同于当代对自由教育的通俗化,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同时,我们也不能期望受过自由教育的人能够形成一种政治理论,因为我们不能期望“受惠于自由教育者都能以同样方式理解自己的公民责任或在政治上达成一致”[3]344。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教育也不失为一种保持清醒和节制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