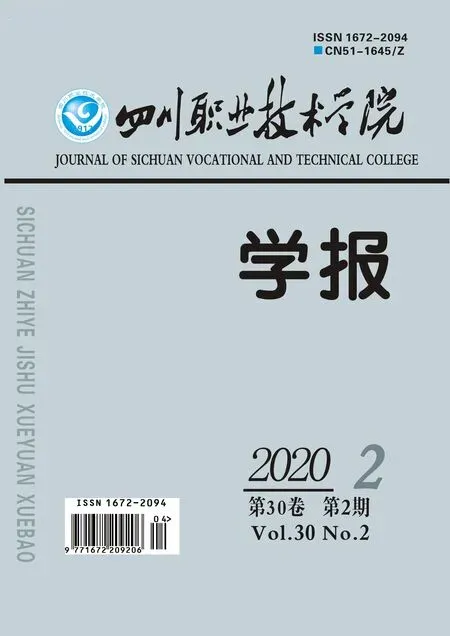投向深渊的凝视:布朗肖的文学阅读
2020-02-25梁梦琦
梁梦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207)
法国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学空间》(Espace littéraire)总共关涉了文学的三个主要元素:作者、读者和作品。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布朗肖的作者论及作品论,或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讨论布朗肖对作家主体性的解构,阐述布朗肖与巴特在“作者之死”问题上的异同[1];或是聚焦于作品,思考文学言语的自主性以及文学与死亡的关系,在“沉默”与“声音”的概念中考察布朗肖的语言观和文学观[2];或是向文学的外部进行探究,将布朗肖与列维纳斯、福柯进行对比,探讨其文学观与现象学、伦理学之间的联系。相较之下,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作者、读者、作品三方关系的阅读理论却少有研究者关注。
关于阅读经验的分析是布朗肖文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它与“作者已死”的作者论及“文学空间”的作品论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作者的不在场和文学言语的否定性决定了阅读的性质和形态,阅读的性质和作用又支撑了布朗肖关于作者和作品的论说。因此,对布朗肖的阅读观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和论述,有助于厘清《文学空间》中纵横交岔、错综复杂的思想网络。
一、生成:作者的隐退与作品的在场
从《文学空间》的整个理论架构来看,布朗肖阅读理论的起点和基础是他对语言性质的思考。在他看来,阅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阅读的对象——文学作品的特性,而作品的特性又与文学言语的性质密切相关。
黑格尔将人类语言的本质定位为否定性,即主体对对象的抽象化和概念化。“言说”利用文字的非实体性来否定事物的实在性以传递观念,在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过程中以理性把握世界。至此,“事物”在语言行为中缺席,而指向事物的观念却始终在场。马拉美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深化,布朗肖则在马拉美的基础上将这种否定性的语言观推向极致。他指出,“否定”是一般语言的一般属性,文学言语作为语言的特殊状态,还具有区别于一般言语的特性——将语言的否定性从“事物的实在性”扩散到“文字所指涉的概念”中。事物的实在与指向事物的观念都被否定之时,在场的便仅有文字;这文字如同倒影,虽有肉眼可见的形态,却无所谓实存。如此一来,文字只能与其他文字发生联系,意义在其中无限游离,无法构成一个明确的空间。言语折回自身,面向自身,又将自身否定,余下的唯有沉默——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所发出的沉默之声。
因此,由文学言语构成的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观念的传递,它还具有文学言语“回到自身”的纯粹性。这一特性将文学作品析为两个层次:可释读的文本与不可还原的文本。前者生成于文本的文化维度,是由稳定的意义编织出的材料,它与作品的物质载体——书本纸张和印刷的实在一道构成了布朗肖所定义的“书”;“不可还原的文本”则是布朗肖所说的“作品”,它仅仅向自身开放,狂暴而自由地抗拒着一切命名、定义和解释,因而永远无法被还原。
文学言语的二重性与文学作品的二重性引发了布朗肖对传统阅读的再思考和对阅读之本质的探究。在传统的文学阅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将作品还原为读者的内心生活”。读者将文本视为一种真实、一种对现实的摹仿,并将这种真实对应到自我经验到的日常现实中,进行自我疗愈或自我娱乐[3]27。但文学言语否定概念、指向自身的特性却在作品中开放了一个无法被探知的文学空间、令文本无法被单纯地还原为日常的现实,也使阅读成为一种不可穷尽的探知和进入,从而躲开了理论和定义的捕捉。可见,将文本还原为读者的传统路径不仅取消了作品生命的无限性,也封锁了阅读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此外,布朗肖对文学言语的独特理解也为作者的消失搭建了舞台。作品中的实在之物仅有言语本身——准确地说,是语言的“身体”,实存的作者本人并不存在于作品之中。因此作品一旦诞生、一旦进入被阅读的阶段,就意味着写作活动的终结和作者的死亡,“不再同某个完成作品的人有关”。“在创作所开辟的空间里,已不再有创作的位置了……任何一个已完成作品的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停留在作品旁边。作品就是决定本身,它把作家打发走,把他删除。”[4]5得益于作者的退场,作品得以向自身开放,阅读便于此刻诞生。
由此,布朗肖也批判了将文本视为作者生活之再现的阅读方式,在对作者权威的解构中召唤出读者的在场。向文本指明它的作者、将作品理解为作者的现实,实际上是在将文本放入一个人为预设的框架之中,封闭和固定文本的意义。此时读者也成为了一位“逆相的作者”,与其说他“在场于作品”,不如说他在场于那个由他所建构的作品生成的过程。但作品诞生的时刻,也正是作者被取消的时刻;作者“已死”,唯一在场之物仅有言语。因此读者“应当抛开一切偶像,同一切决裂,应当不把真实作视野,把前途视为逗留之地”[4]19。
简而言之,以“否定”为本质的文学言语在作品中开辟了一个不可阐释、不可还原的无限空间,这个深渊不具有包括作者在内的任何实存。将文本还原为读者的阅读取消了作品的无限性和可能性,从而将读者局限在日常的经验之中;而将文本还原为作者的阅读也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至此,布朗肖在黑格尔的否定语言观之上建立了他的文学本体论,又以文学本体论否定了以摹仿论为基底的还原式阅读,阅读的开放性也得以被重新发现和展示出来。
二、阅读:走向作品深处
在批判传统阅读路径的同时,布朗肖也对阅读重新进行了本体意义上的定位。他在《文学空间》中反复强调,阅读不是对现实的单纯还原,不是“那种保持含义又将它重新介绍出来的领会”[4]198,更不同于理解、阐释及其他以获取意义为目的的功利性行为。“还原”与“领会”这两种进入文本的方式都要求一定程度的“知”,阅读却不要求任何天赋,它是无功利的,有时甚至是无意义的,“阅读、看和听艺术作品更要求无知而不是知”[4]193。可以说,布朗肖的“阅读”更接近于一种感受式的体验和开放式的进入,阅读的过程就是走向作品深处的过程——“阅读是深深地返回到作品的内在深处,返回到似是作品永久的产生的那种东西中去。”[4]208这种进入如同一次无目的的、无终点的追溯,不是走向作品的有声之处,而是走向作品内部无声的沉默空间。
布朗肖将文学内部的这个空间称作“作为渊源的作品”,并将它作为文学阅读所要抵达的终点。究其根底,“文学空间”可以溯源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以及列维纳斯的“ilya”。列维纳斯在海德格尔之存在(being)的基础上提出了ilya 这一概念,来表示先于存在的“存在”。它意指一种“普在的不在场”,但“反过来却也意味着一种在场,一种绝对无法回避的在场”[5]。这就是《文学空间》中的“不在场之在场”。如果说“在场”是主体性的确认,“不在场的在场”就是对主体性的否定和取消。布朗肖在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文学维度上的这种特殊存在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无任何东西有意义”。同时它又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渊源,“所有具有意义的东西都回溯到那里,正如回溯到渊源一般。”[4]208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特殊的文学空间,布朗肖将死亡和夜类比于文学,在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彼此映照的镜像关系。其中,作为作品之渊源的空间与“另一种死亡”和“另一种夜”同构;相应地,作为文学体验的阅读同时也是对黑夜的体验和对死亡的体验。据此,布朗肖对“作为观念的死亡”与“本质的真实的死亡”进行了辨析,区分了“可进入的夜”与“不可见的夜”。传统的宗教、哲学和文学,常常将死亡观念化以寻求对有限之生的绝对掌控,从而忽视了另一面的死亡——他者的、本质的死亡。它位于知识之外、生命之前,是时间的不在场;在它之中,一切主体都被消解,存在的仅有彻底的、纯粹的被动性。构成“作品”第一层的可释文本,对应于作为观念的死亡,都是由稳定的意义编织出的材料;作为“作品”第二层的、不可还原的文本,则与本质的死亡同为他者性的存在。相应地,第一种夜、可进入的夜,是“白天的建树”,它接纳人们走进这夜中,在其中安息、睡眠或死亡。白天在第一种夜里建构自身,如同人们以理性将死亡建构为生的另一面;而另一种夜、他者之夜,则是一切都消失之后“一切都消失了”的显现。它并不接纳、并不开放,晦暗、中性而杂乱,唯有无根底和无深度之物在其中闪烁,如同拒绝了一切存在的他性的死亡。
至此,布朗肖将作品深处不可还原的、无源头亦无终点的场域与“另一种夜”及“本质的死亡”融为一体,共同指向先于存在的“普在的不在场”。而体验作品的经验过程——阅读,就是一种“投向无尽深渊的凝视”。
文学言语的否定性决定了文学的本体性,文学的本体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阅读的本质,同时也决定了阅读经验的两个特性:朦胧感和唯一性。文学作品中无法被理性范畴捕捉的沉默空间取消了作品被彻底理解的可能性,令作品如同置身于幽冥之地,忽明忽暗、不可捉摸,赋予体验者以朦胧之感。这种独特的体验不依赖于先天的知识范畴和后天的知识积累而存在,也不会因认知能力的提升而消失。正如布朗肖在《无尽的对话》中所说,“阅读是懵懂的……(严格说来)它并不理解,而是照顾”,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纯真”[3]29。
布朗肖在阅读相关的论述中也多次强调了阅读经验的唯一性。作为“事件”的阅读,是经验主体经验到外在经验物的一个经验过程。经验的主体——读者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水平时时刻刻都处于成长之中,它们的变化和运动决定了阅读经验的偶发性,令阅读具备了独一无二的现场感。从经验物——作品的角度看,作品深处的、渊源的空无永远无法被定义和捕捉,因此“在阅读中,作品总是首次出现。”[4]198“当它被阅读时,它不曾被人读过,它只有在由这种独一无二的阅读打开的空间里才能实现它的作品的影响。”可以说,每一次的阅读都是“第一次”,“每次都是唯一的一次”[4]206,阅读是“开始”而非“重复”。
三、建构:让作品成为作品
在既有的文学理论和我们的日常认知中,阅读常常被视作作品完成后可有可无的偶发事件。布朗肖则认为,阅读在作品的生成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作品,读者的阅读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学活动。这种建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阅读取消了作品之外的一切特权,将作品归还于它自身。在阅读中,读者无名的在场如同与作者相对的一道反作用力,它瓦解了作者的权威,让作品中“强烈的、非个人的表述”得以显露。如此一来,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决定作品,能够决定作品的唯有作品本身,以及作品深处永远沉默的文学空间。
其次,作品不是静止的统一体,而是矛盾的动态集合,作者——读者是其中最重要的对立组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作品内部作为矛盾双方的“作者”与“读者”并非具体的实存,而是一组内在于作品的结构。阅读激活了名为作者——读者的矛盾,令冲突的双方始终处于永不止息的交流和对话之中,作品才得以成为作品:“作品之所以是作品,只有在它成为某位写作品的份和某位读作品的人公开的亲密,成为由于说的权利和听的权利相互争执而猛烈展开的空间时。”[4]18
此外,阅读还自身的失败确认了作品深处的“不在场的在场”。作品在要求读者进入的同时也拒绝了读者,敞开与拒斥的力度同样强烈,双方势均力敌,令徘徊在外的读者只能无限逼近作品的深处,却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这片神秘的所在。但“失败”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失败”恰恰是无限与可能的确证。经由失败,读者以“是”的句式认证了空无,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无法被还原的幽灵空间。正如布朗肖所说,阅读是一种“无劳作的自由”——它不生产任何成果;是“顷刻间纯粹的喜悦的是”——它确认了作品内部黑暗而无声的深处。同时,这种空无也使作品自己向自己敞开,令作品“重新找到自身的不安,它的贫困的财富,它的空无的不安全”,“阅读同这种不安相结合又共同承担起这种贫困。”[4]206可以说,正是由于“拒斥”所带来的失败,文学才成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具有与创作等同的创造力,它使作品本身表现为作品,“让存在者存在”。
通过作品主体性的复原、内部矛盾的激活以及“失败”对文学空间的肯定,阅读迎接着作品的到来,迎接着语言文字对读者的照亮,同时也让作品得以自我完成。因此“阅读,不是重新写书,而是使书自己写成或被写成。”[4]194
在布朗肖之后,罗兰·巴特也强调了阅读在作品生成中的关键作用,但二者对阅读建构性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于巴特而言,阅读是意义生成的必要条件,阅读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文本只是一组现实存在的符号之链,唯有经过阅读以及阅读之后的批评,意义才有可能发生。布朗肖则表示,阅读能够“造成作品变成作品”,但这种造成“并不表明一种生产性的活动”。阅读不造成任何东西、不增添任何东西,它让存在的东西存在;它是自由,但不是产生存在或创造存在的自由,而是迎接、赞同,说“是”的自由[4]196。相应地,“阅读”的建构性亦不是意义的生成,而是要令作品成为主体、要激活作品的内在结构,向作品自身肯定“某种无作者的和无读者的东西”——一个唯有“不在场”在场的空无深渊。
可见,巴特所代表的结构主义式阅读致力于使特定的文本与更大的封闭性结构发生联系;而布朗肖的阅读并不造成某种外在之物同作品的交流,而是令作品“自己同自己交流”。阅读没有给出存在,亦没有把握存在,而是迎接存在,对存在说“是”。
从其根源上看,两位文论家的分歧来源于他们阐述的“阅读”所指向的不同对象。巴特建构阅读理论的依据是文本中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之构成的部分,这一维度上的阅读主要指向存在于文化结构中的“可释的文本”,意图走进“第一种夜”、可见的夜。布朗肖所定义的阅读则同时面向可进入的“书”与不可还原的“作品”,阅读路径的终点是“第二种夜”,即作品深处“时间不在场”的深渊。这种阅读也使作品“超越了产生它的人,超越其中所表达出来的体验,甚至所有一切传统使其成为可支配的艺术资源。”[4]195
总的来看,传统的阅读路径意图实现读者对作品的控制和超越;而在布朗肖看来,文学阅读应当是“作品”对“我”(作者或读者)的超越。作者与读者都是从属于作品的存在,“因为只有通过这部作品并以它为基点,他们才有实存。”[4]232二者既无法穷究作品,也无法掌控作品;面对作品,写下它的人和打开它的人都只能不断接受着文学之光的照射。而作者、作品、文本三方关系中主客等级的消解,也正是布朗肖对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反思在文学场域上的精确投影。它与文学空间、不可见的夜以及“另一种死亡”一道,构成了布朗肖文学思考中的现代性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