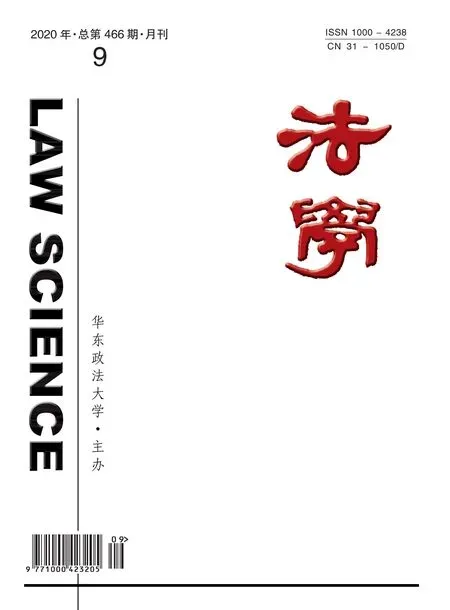我国民法典实质债法总则的确立与解释论展开
2020-02-25于飞
于 飞
在立法论上,我国《民法典》既没有设立债编,也没有设立债法总则。在解释论上,究竟是遵循立法形式,即按照无债编、无债法总则的方式发展解释论,还是不拘于立法形式,按照实质上仍有债编和债法总则的方式展开解释,这是中国民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其直接影响《民法典》的解释和适用。该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民法解释论的基本框架,故宜在《民法典》颁行之际予以阐明,并力争达成共识。
2002 年公布的《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未设债法总则。此后,学界针对我国民法典中是否应当设置债法总则进行了持续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意见。〔1〕赞成设立债法总则的意见居多数,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5 期;柳经纬:《我国民法典应设立债法总则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 年第4 期;孙宪忠:《我国民法立法的体系化与科学化问题》,载《清华法学》 2012 年第6 期;崔建远:《中国债法的现状与未来》,载《法律科学》2013 年第1 期;杨立新:《论民法典中债法总则之存废》,载《清华法学》2014 年第6 期;王利明:《论债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的关系》,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反对的意见居少数,参见王胜明:《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2003 年第1 期;覃有土、麻昌华:《我国民法典中债法总则的存废》,载《法学》2003 年第5 期;许中缘:《合同的概念与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兼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载《清华法学》2010 年第1 期;张素华:《有关债法总则存废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法学评论》2015 年第2 期。在法典编纂后期立法结构已总体确定时,有学者提出将债法总则“嵌套”入合同法总则,以体现实质意义上债法总则的正向体系功能和效益。〔2〕参见朱虎:《债法总则体系的基础反思与技术重整》,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3 期。笔者亦曾提出,若立法不设债法总则,则可基于“减编不减量,变表不变里”的现实主义路径,缓解不设立债法总则带来的问题。〔3〕参见于飞:《合同法总则替代债法总则立法思路的问题及弥补》,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 年第2 期。
《民法典》未设债法总则已属制定法上的现实。有学者提出以《民法典》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4〕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载《法学论坛》2020 年第4 期。有学者认为应当识别《民法典》合同编中的债法总则规定,以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5〕参见翟远见:《论〈民法典〉中债总规范的识别与适用》,载《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4 期。本文赞同以上发展方向,并将从解释论视角进一步展开深入探讨。首先,厘清《民法典》是否应设立债法总则,从而为后续讨论奠定正当性基础。其次,探究《民法典》是否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债法总则。再次,如果存在实质债法总则,则其制定法规则体系究竟为何,各种债又存在哪些“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债法总则的情况。最后,阐释我国实质债法总则的确立会产生哪些体系效益。
一、关于实质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该问题实际上可以变换为,如果《民法典》没有债法总则将会产生何种弊端。
(一)债法总则缺失之弊
否定债法总则,无论其为形式意义上的还是实质意义上的,这种立法思路确实存在过。2003 年,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曾指出:“不搞债法总则,合同编较为完整,侵权自身已有一般规定,未规定的适当参照合同编的规定,比较实用。”〔6〕王胜明:《制订民法典需要研究的部分问题》,载《法学家》2003 年第4 期,第10 页。这是以“参照适用”为关键技术,以合同编总则替代债法总则的立法思路。其具体表现就是2018 年《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同编》(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合同编征求意见稿》)第5 条:“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适用有关该债权债务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立法上专设债法总则,这是形式上的债法总则模式;立法上不设债法总则,但仍然制订债法总则规定并将其置于法典相关内容中,这是实质债法总则模式。此两者可统称为债法总则肯定模式。立法上不设债法总则,仅制订合同编,非合同之债参照适用合同规则,这是债法总则否定模式。上述《合同编征求意见稿》的立法思路即为债法总则否定模式之反映。
债法体系化的核心在于法律效果的相同性。〔7〕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5 页。各种债之关系固然在债的发生原因上不同,但原则上在债发生后的法律效果上应遵循相同的规则,此类规则即债法总则。若立法上设立债法总则,无论是形式意义上的还是实质意义上的,这意味着立法者就全体债之领域(包括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均要求一体适用相同的债之效果规则。若立法上仅制订了合同编,并规定非合同之债参照适用之,则意味着立法者仅就合同之债的法律效果作出了判断,而在非合同之债领域却整体地不作判断,并将判断是否参照适用的权力留给了个案中的法官。
此处涉及“参照适用”的方法论性质,参照适用即准用。〔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41 页;刘风景:《准用性法条设置的理据与方法》,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5 期。王泽鉴教授指出:“准用是法律明定之类推适用,而类推适用则是判例学说所创设之‘准用’。”〔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0 页。黄茂荣教授基于准用是立法明定的类推而将其纳入“授权式类推适用”的范畴。〔10〕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06 页。
适用与准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过程,会对法律适用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在设立债法总则的情况下,全体债之关系在法律效果上适用债法总则规定,法官在相同的“三段论”大前提下进行涵摄判断即可,法律适用的确定性高。而在仅设立合同编,并要求非合同之债在法律效果上类推适用合同规则时,法官对于任何一个非合同之债都要按照类推的思维过程,进行积极确定与消极确定两次判断。首先,判断在所有的重要评价点上,待判事实是否与法律已有规定者均相同。其次,判断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否不足以排斥此等法律评价。〔11〕同前注〔8〕,卡尔·拉伦茨书,第258 页。以上是“参照适用”的方法论性质带来的立法强制,除非无视立法用语,否则这种强制无法逃避。而这两次判断既会加重法官的论证负担,又可能导致法官在相似性判断上出现不一致。这种额外增加的判断环节将导致其法律适用面临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者的基本假设。在《民法典》设立债法总则的情况下,立法者的基本假设是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在法律效果上是相同的,故应适用同样的规则。而在《民法典》不设债法总则,并规定非合同之债参照适用合同规则的情况下,立法者的基本假设是非合同之债在法律效果上与合同之债是不同的。因此,法官在个案中处理非合同之债的法律效果问题时,要进行积极和消极的两次判断,通过论证以确定系争非合同之债能否适用合同规则。关键在于在产生特定人之间的给付关系这一核心点上,非合同之债与合同之债相同,债法总则否定模式却将此相同假设为不同,再强制要求法官于个案中论证其属于相同,以致付出不必要的论证代价,并会造成论证结果上的不一致。
(二)例外情形的存在不是否定债法总则的理由
当债法总则规定适用于各种债时,会出现许多例外情形。这构成否定债法总则的一个重要论据。例如,有学者认为:“尽管理论上和立法本意上债法总则对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具有可适用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债法总则在合同之外领域的适用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在侵权领域中,一方面,迟延履行、担保、抵销、混同等,这些制度尽管理论上存在适用的可能性,但由于各种或是法律上的限制,或是事实上的限制,其适用几乎不曾发生或是很少发生过。例如,关于债的抵销,各国法律一般规定,因故意侵权而生之债禁止抵销。”〔12〕同前注〔1〕,覃有土、麻昌华文。
笔者认为,法律规定中存在原则与例外是正常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真正重要的是,存在适用例外不仅不构成否定债法总则的理由,反而能够进一步论证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前引否定债法总则的观点提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外,即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得由债务人主动抵销,下文就以该规则为例进行说明。
在设立债法总则时,债的抵销属于债法总则规定。合同之债适用抵销,这在方法论上是“适用”。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同样适用抵销,这在方法论上也是“适用”。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能由债务人主动抵销,这是侵权之债可抵销的例外规定,该例外经由法定化,如《德国民法典》第393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39 条,在方法论上也是“适用”。以上三种情形均为直接“适用”,确定性都很强。
而在不设债法总则而仅设合同编时,抵销成了一个合同规则。合同之债可以抵销,在方法论上尚为“适用”,而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抵销就需“参照适用”合同规则,这在方法论上属于“类推”,此处就有可能出现法官在个案判断上的不一致。比如,可能有法官认为,侵权产生的不是债或不仅仅是债,还是一种责任,其与合同之债相较不具有足够的相似性,不能“参照适用”。于是,同样的案件就可能无法找到同样的“三段论”大前提,导致同样事项无法同样处理。在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能由债务人主动抵销这一规则层次,更可能发生规则遗漏。原因在于该规则是一个例外规定,而其原则性规定,即侵权之债可抵销,在无债法总则的体例下并非制定法规则,而是需通过类推才可产生。当原则性规定缺乏制定法基础时,例外规定就更无法明文作出,于是就可能发生规则遗漏。可资佐证的是,在《合同编征求意见稿》中即找不到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得由债务人主动抵销这一规则。
有观点认为,设置债法总则就应多设置一些限制性规范,不设置债法总则就应多设置一些准用性规范,很难判断哪一种方式更有助于找法和适法。〔13〕同前注〔2〕,朱虎文。以上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值得深入思考。要害在于设置债法总则时,多设置的那些限制性规范在方法论上仍是“适用”;而在不设债法总则时,多设置的那些准用性规范在方法论上却是“类推”。两种处理方法在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上是不同的。因此,多一些限制性规范与多一些准用性规范,恐不适宜相类比或等量齐观。
从方法论角度再多作一句解释,“参照适用”或准用在方法论上常被认为是填充法内漏洞的手段。〔14〕同前注〔10〕,黄茂荣书,第306 页;[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62 页。问题是我们明知规则是什么,规则即债法总则规定,也明明可以用立法方式(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债法总则)解决,为什么还要留下漏洞呢?只要是法律漏洞,漏洞补充就是法官的权限,就不可能在“三段论”的大前提上保持统一了。
二、我国民法典中的实质债法总则与债法体系
我国《民法典》上是否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债法总则及债法体系,这一问题值得深究。
(一)《民法典》第118 条第2 款为我国债法体系奠定了基础
《民法典》第118 条第2 款是我国债法的制定法基础,其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该款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该款与同条第1 款明确使用了“债权”概念,维系了民法财产权中“物债二分”的体系。以债统领各种给付关系,以债权统领各类请求给付的权利,为统一的债法奠定了概念基础。
其次,明示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为债的发生原因。其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明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王利明教授曾提出,侵权法应当从债法中分离出来,成为民法体系中的独立一支,〔15〕参见王利明:《论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载《现代法学》2003 年第4 期。我国《侵权责任法》立法即受此影响。《民法典》第118 条第2 款明确将侵权行为规定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二章的章名也从“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改为“损害赔偿”,明示了侵权法向损害赔偿之债的回归。王利明教授认可侵权行为不仅产生侵权责任,同时也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16〕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3 页。杨立新教授亦明确主张侵权责任法应回归债法并成为侵权损害赔偿法。〔17〕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回归债法的可能及路径》,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2 期。无论从立法还是学说上看,侵权法回归债法已成为主流趋势。
最后,债法统一于“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效果,也即统一于给付关系。在对给付关系的统一调整及共同规则的设置中就产生了债法总则。
(二)《民法典》第468 条确立了我国实质债法总则模式
《民法典》第468 条规定:“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有关该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与《合同编征求意见稿》第5 条相比,其核心变化是将“参照适用”改为“适用”,删除了“参照”二字。这一变化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中就已出现,一直延续到最终正式通过的《民法典》文本。这表明立法者改变了其基本假设,推定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在债的效果问题上本质是相同的,可以适用同等法律评价。在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中,立法者并不希望法官采用“类推”方法在个案中判断相似性,进而决定是否适用合同规则;而是希望法官原则上不要作相似性判断,直接适用合同编通则中的相关债法规范。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黄薇主任主编的民法典释义书(以下简称“立法机关民法典释义书”)指出:“本条(即第468 条——笔者注)规定的是‘适用’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不是‘参照适用’……不是再由裁判者斟酌具体情况‘参照适用’。”〔18〕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30 页。由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的民法典释义书(以下简称“最高院民法典释义书”)更是明确强调:“此处使用的表述是‘适用’而非‘参照适用’,裁判者在是否适用的问题上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19〕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50 页。
从“参照适用”到“适用”虽只删除了两个字,但却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变化。其意味着立法理念已从债法总则否定模式回到了债法总则肯定模式,也即废弃了以合同编通则替代债法总则的立法路径,而代之以将债法总则规定明确制订出来并置于合同编通则之中,然后对非合同之债直接“适用”债法总则规定的立法路径,这是实质债法总则模式。为配合这一立法路径的变化,立法者还对合同编通则作了债法总则化的调整,具体如下。
1.属于债法总则规定的,将原来合同式的表述修改为债法总则的表述。(1)将《合同法》第79 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修改为《民法典》第545 条“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将同条“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修改为“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2)将《合同法》第80 条“债权人转让权利”修改为《民法典》第546 条“债权人转让债权”;对《民法典》第547 条作同样修改。(3)将《合同法》第84 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修改为《民法典》第551 条“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对《民法典》第553 条、第554 条作同样修改。(4)将《合同法》第91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修改为《民法典》第557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债务终止”。(5)将《合同法》第92 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修改为《民法典》第558 条“债权债务终止时”。(6)将《合同法》第99 条“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规定,修改为《民法典》第568 条“根据债务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规定。(7)将《合同法》第105条债务免除后“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修改为《民法典》第575 条中的“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8)将《合同法》第106 条债发生混同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修改为《民法典》第576 条中的“债权债务终止”。
2.新增条文属于债法总则规定的,统一使用“债”“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等债法表述,不使用“合同”“合同权利”“合同义务”“合同权利人”“合同义务人”“合同当事人”等合同法表述。如《民法典》第514 条关于金钱之债、第515-516 条关于选择之债、第517-521 条关于多数人之债,第524 条关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第536 条关于债权到期前代位权的行使,第537 条关于代位权的法律效果,第542 条关于撤销权的法律效果,第550 条关于债权转让增加履行费用的负担,第552 条关于并存的债务承担,第559 条关于债的消灭对从权利的影响,第560-561 条关于债的清偿抵充,第571 条关于提存成立,第581 条关于第三人替代履行,第589 条关于债权人迟延受领等规定。原有条文中有新增债法性质之款项的,也按照债法方式表述,不再一一列举。
《民法典》第468 条从“参照适用”到“适用”的变化以及与之配套所作的债法总则式调整,使《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变成了合同法总则与债法总则的一个糅合体,并使其最终归于实质债法总则模式。这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但仍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
三、我国民法典中实质债法总则的规则体系
既然我国《民法典》存在实质债法总则,理应厘清其中具体包括了哪些制定法规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明了非合同之债对合同编通则的哪些规则能够直接“适用”,从而实现立法意图。这需要对合同编通则规定逐一进行识别。
(一)识别的若干标准
1.立法者使用的文本通常最能表达立法者的主观意思。〔20〕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315-316 页。立法机关民法典释义书明确指出:“将合同编通则中能够适用于非合同之债的具体规则,尽量通过措辞予以明确指示。对可适用于所有债的类型的共同规则,条文中尽量不使用‘合同’‘合同权利’‘合同义务’的表述,而是采用‘债’‘债权’‘债务’的表述,而就合同的订立、效力和解除等仅能适用于合同之债的规则仍然使用‘合同’的表述。”〔21〕同前注〔18〕,黄薇主编书,第3 页。因此,依立法者明示的意思,合同编通则中凡使用“债”之表述的,应先予推定为债法规定;凡使用“合同”表述的,应先予推定为合同规定。对以上推定持相反意见者,须负举证责任。这是识别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2.虽使用债的表述,但应认为是合同规定的情形。典型者如《民法典》第530 条提前履行规则:“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是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该条完全采用债之表述,亦有观点认为该条为债法总则规定。〔22〕同前注〔5〕,翟远见文。本文认为,提前履行以存在履行期限为前提,履行期限届至前的履行构成提前履行。法定之债中没有履行期限,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更是自成立时起债务人即陷于迟延,〔23〕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5 页;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81 页。故无从提前履行。因此,提前履行规则是合同法规定,不是债法总则规定。《民法典》第530 条完全沿袭了《合同法》第71 条,故这一表述上的偏离可能是立法惯性使然。
3.虽使用合同表述,但应认为是债法总则规定的情形。虽然立法有意识地“尽量通过措辞予以明确指示”债法总则规定,但可能仍有一些遗漏,须经解释进行补充。
(1)《民法典》第463 条规定,“本编调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显然,实际上该编还调整非合同之债,故第463 条的概括并不完全。这种概括不全导致《民法典》第463 条与第468 条“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形成矛盾。故应对《民法典》第463 条进行目的性扩张。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合同编对合同总则制度的完善体现在“通过规定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规则……完善债法的一般性规则(草案第四百六十八条)”。〔24〕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85页。由此可知以下两点。首先,立法者认为合同编可以调整“非合同之债”,即“合同编”的调整范围并不局限于合同。其次,立法者认为《民法典》第468 条的重要意义在于完善了债法的一般性规则,所谓“债法的一般性规则”实际上就是债法总则。
既然立法者已经认为合同编的调整范围包括非合同之债,并以“债法的一般性规则”(债法总则)统一调整之,则《民法典》第463 条仍将合同编的调整范围限于“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显然过于狭窄而与立法目的相悖,故应基于立法目的,将该条扩张为“调整因合同及其他原因产生的民事关系”。此处的“其他原因”,基于《民法典》第468 条“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之规定,应包括合同之外的其他债的发生原因,如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缔约过失、单方允诺等。《民法典》第463 条虽不发挥债法总则具体规定的规范机能,但作为适用范围条款,仍应与本编实质调整范围相协调,以避免矛盾。
(2)《民法典》第465 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第1 款文义虽仅指向“依法成立的合同”,但依法成立的债又何尝不受法律保护?该条第2 款更显属债的相对性之规定,不应仅限于合同。故该条应属于债法总则内容,应予目的性扩张为“依法成立的债,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债,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民法典》第509 条第1 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债的履行的根本要求之一即“全面履行”,这不仅是对合同履行的要求,而且是对全体债之关系履行的基本要求。〔25〕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408 页;同前注〔23〕,张广兴书,第171 页;陈华彬:《债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0 页。该款将“全面履行”的要求限于“按照约定”,使得非合同之债的履行欠缺根本标准,显然不当。对该款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债务人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债务”。
同条第2 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以上附随义务并不限于合同关系,而是贯穿于全体债之关系。〔26〕同上注,江平主编书,第409 页;同前注〔7〕,王泽鉴书,第82 页;同前注〔23〕,张广兴书,第168 页。故对该款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债务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债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同条第3 款“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之规定,可以被看作是《民法典》第9 条“绿色原则”在分则编中的一个映射,但其显然不应限于合同履行,而是债之履行的一般规定。故对其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债务人在履行债务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4)《民法典》第532 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姓名、名称以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都未引起主体资格的变化,特定主体之间的债之关系当然不会变动。以上原理不仅在合同之债中适用,在全体债之关系中也共同适用。最高院民法典释义书指出,合同未成立、无效产生缔约过失责任,责任人以该条所涉变化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由于责任主体未发生变更,故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7〕同前注〔19〕,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474 页。可见该条适用于法定之债。故对该条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债的关系成立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债务”。
(5)《民法典》第543 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能够变更的显然不止是合同,而是全体债之关系。〔28〕同前注〔23〕,张广兴书,第255 页。此为债的变更的一般规定。对该条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债的内容”。
(6)《民法典》第544 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同理,该条亦为债的变更的一般规定,对其也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当事人对债的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4.债法总则规定原则上须能够适用于债之关系全体领域。一个规则须一般化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债法总则规定?有学者认为:“构成债法总则的规范对各种债的关系的适用常常属于这种交错的情形:A 规则适用于甲债和乙债,B 规则适用于乙债和丙债,而C 规则可能适用于甲债和丙债。既然A、B 和C 规则都不只是适用于一种债的关系,那么它们就可以构成债法总则的规范。因此,所谓债法总则,仅指可供两种以上类型的债的关系共同适用的规则。”〔29〕柳经纬:《当代中国债权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1 页。本文同样认为,要求某一规则百分之百地适用于全部类型的债才能成为债法总则规定,显然过于绝对。但是,若只要可供两种以上类型的债的关系共同适用就是债法总则规定,似乎也过于宽松。比如,由于都是意定之债,许多合同法规则也可适用于单方允诺,如《民法典》第510 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该条是一个合同规则,无法适用于法定之债,但单方允诺中同样可能出现质量、报酬、履行地点等未能意定明确的情况,例如悬赏广告中广告人仅表示“必予重谢”,但没有明确报酬数额,又如设定幸运奖时以实物为奖品,但就质量、履行地点等当事人缺乏意思表示等。此时同样可以由当事人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可依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可以按照《民法典》第511 条以法定标准补充。那么,该第510-511 条是否因为可适用于两种类型的债而成为债法总则规定?本文认为恐怕不可。因为一旦肯定其为债法总则规定,依《民法典》第468 条就要适用于非合同之债,但其显然是不能适用的;接下来就不得不从“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入手予以论证排除,徒增司法论证负担。不如保留该第510-511 条的合同法规则性质,从而当然排除法定之债的适用。单方允诺基于其与合同都有“意定”这个根本上的相似点,在需要时类推适用相关合同规则即可。
因此本文认为,构成债法总则规定者,恐怕还是应当兼顾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两大领域,并且对于债之全体领域原则上得适用,仅在例外情况下不适用方为适当。也只有这样,《民法典》第468 条直截了当规定“适用”一词才是有道理的。
5. 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就同一问题都有规定的,不宜再将合同编规定上升为债法总则规定。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591 条的减损规则、第592 条的过失相抵规则是债法总则规定。〔30〕同前注〔4〕,王利明文。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577 条关于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作为“债务不履行的一般规则”是债法总则规定。〔31〕同前注〔5〕,翟远见文。以上规定有一共同特点,即侵权责任编中就同一问题都有相应规定。《民法典》第591 条的减损规则、第592 条的过失相抵规则在侵权责任编中由第1173 条过失相抵统一涵盖,并在用语上有差别。《民法典》第577 条是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系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编第1165-1166 条是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以过错责任为基础。本文认为,当合同与侵权两个领域已经就同一问题各设规定的,再将合同编规则上升为债法总则规定并不适宜。因为将合同规则上升一步后,也无法强行统一侵权领域相应规则的既有差异,其意义仅在于涵盖合同、侵权以外的债法领域。然而,合同、侵权以外的债法领域主要是法定之债,当这一领域需要一般规则的时候,该一般规则应来自合同领域还是来自侵权领域,或许还值得进一步研究。还不如保留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两大领域中的主干规则,对其他法定之债和意定之债视其性质类推适用相适宜的规则可能更为妥当。
(二)我国《民法典》债法总则规定的具体识别与体系建构
在前文所论基础上,笔者认为合同编通则中的以下条文是债法总则规定,并对这些规定进行梳理和体系化。在具体条文的识别上,有疑义之处详加讨论,无疑义之处一语带过。
1.一般规定
合同编通则第一章“一般规定”的多数规则不具有债法总则意义,但以下两条属于债法总则规定。(1)《民法典》第465 条关于债的约束力规定,经目的性扩张已成为债法总则规定。(2)《民法典》第468 条关于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规定,在全体非合同之债的法律效果领域建立了法律适用规则,是债法体系化的枢纽。
2.债的种类
本部分包括了合同编第四章“合同的履行”上关于金钱之债、选择之债、多数人之债的规则。这些规则不是合同或债的履行规则,将其置于“合同的履行”一章本是无奈之举。学说上在整理债法总则规定时,应将这部分债的种类之内容单列。
有观点将金钱之债、选择之债归于“债的标的”,将多数人之债归于“债的主体”。〔32〕同前注〔5〕,翟远见文。本文认为,债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这些内容已在民法典总则编中加以规定。多数人之债系以债的主体数量为标准而与单一之债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一个债的分类问题。由于“债的标的”的实质意义仍是基于给付内容之不同对债所作的分类,因此将金钱之债、选择之债、多数人之债规则统归于“债的种类”似更妥帖。(1)《民法典》第514 条关于金钱之债的特殊规则,实际上解决的是金钱之债应以何种货币履行的问题。(2)《民法典》第515-516 条关于选择之债的特殊规则。(3)《民法典》第517-521条关于多数人之债的特殊规则。有观点将《民法典》总则编第八章“民事责任”中的第177-178 条关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之规定也纳入多数人之债作为债法总则规定对待,本文认为不必如此。因为《民法典》第177-178 条的规则内涵已经完全被第517-521 条按份债务、连带债务规则所吸收,且后者比前者更为具体、细致,无需前者予以补充。而且如果我们秉持责任乃义务之违反的观念,则债务与责任尚非同一层面的问题。我国实质债法总则整理债的规则即可。
3.债的履行
本部分亦源于合同编第四章“合同的履行”,其是剔除了债的种类内容后,对其余有关债的履行的一般规则的集合。
(1)《民法典》第509 条的债的履行原则。该条经目的性扩张后确立了我国债的履行三大原则,即全面履行原则、诚信履行原则、绿色履行原则。
(2)《民法典》第522 条的向第三人履行规则、第523 条的由第三人履行规则。或有人认为,《民法典》第522-523 条源于《合同法》第64-65 条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之规定,属于合同规则。实际上,正如韩世远教授对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所作的阐释,该合同并非一种独立的合同类型,毋宁说它是一种变异,当事人多于订立普遍合同(基本行为)之时附加一项“第三人约款”,而不另行订立此种合同。〔33〕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361-362 页。而该基本行为也完全可以是一个非合同之债,即当事人就一个非合同之债的关系,约定向第三人履行或由第三人履行。正如前述《民法典》第543 条,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变更债的协议当然是合同,但这种变更却是对各种债进行处理的一种共通方式,故构成债法总则规定。同理,向第三人履行、由第三人履行也可以运用于各种债之关系的处理,故亦构成债法总则规定。
(3)《民法典》第524 条关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规定。第三人代为履行可以发生于所有的债的类型之中,也是典型的债法总则规定。《德国民法典》债编第一章第267 条、《瑞士债务法》第一分编通则第68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债编第一章通则第311 条均为成例。立法机关民法典释义书在解释《民法典》第524 条时指出:“我国民法典不设债法总则,为了使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作用,有必要补充债法的一般规则。本条参考境外立法例,就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而履行债务及其法律效果作了规定。”〔34〕同前注〔18〕,黄薇主编书,第213 页。此即明示该第524 条是债法总则规定。
(4)《民法典》第529 条关于债权人原因导致债务履行困难之规定。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此类债权人原因导致的履行困难可以发生于任何债的类型之中,因此其也属于债法总则规定。
(5)《民法典》第531 条关于部分履行之规定。债务人部分履行时债权人的拒绝权及例外,以及部分履行增加的费用负担问题,在各种债中都可能出现,故其为债法总则规定。
(6)《民法典》第532 条关于当事人变化对债务履行影响的规定。如前所述,此为债法总则规定。
《民法典》第511 条是否为债法总则规定值得讨论。该条规定了合同约定不明确时关于质量要求、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费用六项内容的法定补充规则。有观点认为,该第511 条中“履行地点、履行期限”等可适用于合同之外的其他债的关系。〔35〕同前注〔4〕,王利明文。有观点认为,该第511条中“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费用”的规定都属于债法总则规定。〔36〕同前注〔5〕,翟远见文。本文认为,不宜将《民法典》第511 条作为债法总则规定对待。《民法典》第510-511 条形成一个合同内容确定的链条,即“当事人约定——协议补充——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法定补充”,法定之债很难嵌入这一链条之中予以解释。将《民法典》第511 条作为债法总则规定的观点,似乎是将法定之债视为一种“不明确”的约定,直接依照最后一环即法定补充规则处理,但深入探讨会发现存在许多困难。例如关于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履行地点问题国内几乎没有讨论,参考德国学说,确定该履行地点的主要依据是在何处履行足以填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害。〔37〕Vgl. Münkomm-BGB/Krüger, 6. Aufl., München 2012, § 269, Rn. 43; Staudinger/Bittner, 2014, § 269, Rn. 35.就侵权行为产生的恢复原状义务而言,履行地点应该以受损物所在地为准,无需与侵权行为发生地保持一致。这主要是考虑到侵害行为发生后,债权人可能将受损物带往其他地方。〔38〕Vgl. Münkomm-BGB/Krüger, 6. Aufl., München 2012, § 269, Rn. 43.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给付地点,通常是在返还义务人的住所。但是在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中,如果同时也满足侵权之债的要件,则应适用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则。〔39〕Vgl. Münkomm-BGB/Krüger, 6. Aufl., München 2012, § 269, Rn. 44.以上规则与《民法典》第511 条中依标的的不同确定不同的履行地点显然不同。在履行期限上,侵权之债自成立时起债务人即陷于迟延,这亦与该第511 条关于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的规定显然不同。倒是在履行方式上,如因侵权行为确定产生了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债务后,有类推该第511 条第5 项“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规则,而产生并适用“按照有利于债的本旨的方式履行”之规则的余地。在履行费用上,非合同之债中亦由债务人承担费用,因债权人原因增加的履行费用由债权人承担,如《民法典》第511 条第6 项之表述,似乎并无疑义。但整体言之,本文认为《民法典》第511 条不宜作为债法总则规定,有个别需要时予以类推适用即可。
4.债的保全
其包括两部分。(1)《民法典》第535-537 条有关债权人代位权规则。(2)《民法典》第538-542条有关债权人撤销权规则。本部分皆为债法总则规定,立法表述也很明确,故不赘述。
5.债的变更和转让
其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典》第543-544 条关于债的变更之规定。如前所述,这两条是当事人合意变更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得适用于一切债之关系,故为债法总则规定。(2)《民法典》第545-550 条关于债权让与的规定。(3)《民法典》第551-554 条关于债务承担的规定。应注意本章第555-556 条有关合同承受规则仅适用于合同领域,并非债法总则规定。
6.债的消灭
(1) 《民法典》 第557 条第1 款关于债的消灭的法定情形之规定。该条将《合同法》第91 条上所谓“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七种情形区分为两款。第1 款规定的履行、抵销、提存、免除、混同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发生“债权债务终止”的后果,以上情形适用于全体债之关系。第2 款单独规定合同解除,发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后果,以示其仅适用于合同领域。于是,《民法典》第557条第1 款是债法总则规定,第2 款是合同法规定。
(2)《民法典》第558 条关于债消灭后当事人义务的规定。此类义务包括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该条源于《合同法》第92 条,并将“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修改为“债权债务终止后”,明示了立法者欲将该条修正为债法总则规定的意图。该条在合同法中虽常被称为“后合同义务”,但此类义务同样能够发生在其他债的关系消灭之后。最高院民法典释义书以《民法典》第572 条举例:“标的物提存后,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监护人、财产代管人。”任何债务均可因提存而消灭,但债务人在提存之后仍应向债权人或相关人通知。此即一种债消灭后的当事人通知义务。〔40〕同前注〔19〕,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608 页。另外,在知识产权侵权中,侵权人可能知晓了受害人的知识产权信息、在缔约磋商中一方可能了解了对方的商业秘密,在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缔约过失损害赔偿之债履行完毕之后,债务人仍有保密义务。
(3)《民法典》第559 条关于债的消灭对从权利影响的规定。例如,法定之债亦可设置担保。〔41〕同前注〔23〕,张广兴书,第215 页。法定之债经清偿而消灭后,担保权利亦消灭。
(4)《民法典》第560-561 条关于债的清偿抵充规则。此为典型的债法总则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66-367 条、《日本民法典》第488-491 条、《瑞士债务法》第85-87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21-323 条均在债法总则中规定了以上规则。
(5)《民法典》第568-569 条关于债的抵销规则。
(6)《民法典》第570-574 条关于债的提存规则。
(7)《民法典》第575 条关于债的免除规则。
(8)《民法典》第576 条关于债的混同规则。
7.债务不履行
本部分源于合同编通则第八章“违约责任”。若仅看文义,可能会认为该章仅系合同规则,但实际上该章也存在一些债法总则规定。
(1)《民法典》第579 条、第580 条第1 款关于金钱债务、非金钱债务的继续履行规则。金钱债务、非金钱债务均可能发生在各种债之关系当中,因此金钱债务可以请求继续履行以及非金钱债务存在的不能请求继续履行的例外情况,均系债法总则规定。由此,可知《民法典》第580 条第1 款中“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表述嫌窄,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债的内容”。
《民法典》第580 条第2 款是为了解决“合同僵局”问题产生的新规定,仅限于合同领域适用。
(2)《民法典》第581 条关于第三人替代履行的规定。对于不可强制履行的债务,债务人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债权人可以以第三人替代履行,并请求债务人负担费用。该规则不限于合同领域,如侵权人损坏他人物品应予维修而不维修的,受害人可以找第三人维修并请求侵权人负担费用。由此,可知该条中“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表述嫌窄,应予目的性扩张为“履行债务不符合债的内容”。
(3)《民法典》第589 条关于债权人迟延受领的规定。各种债均有可能发生迟延受领,故其为典型的债法总则规定。
在本章中,《民法典》第584 条是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第590 条是关于不可抗力免除违约责任的规则,至于是否有必要将第584 条提升为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将第590 条提升为债法上的不可抗力规则,值得讨论。有观点认为以上两条均构成债法总则规定,〔42〕同前注〔5〕,翟远见文。本文认为可以商榷。《民法典》第584 条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系以可预见性规则为核心;侵权责任编上没有以立法方式明确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工具,学说上通常认为是“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43〕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0-232 页;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222-223 页。。关于“可预见性”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这两项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规则有无必要统一、有无可能统一以及怎样统一并无定论。〔44〕既有相关讨论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633-634 页;同前注〔33〕,韩世远书,第790-797 页;潘玮璘:《构建损害赔偿法中统一的可预见性规则》,载《法学家》2017 年第4 期。故恐怕还是先将该第584 条保留在合同法领域,留待学说进一步发展为妥。
《民法典》第590 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则有无必要一般化?由于侵权责任编没有不可抗力规则,《侵权责任法》第29 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在民法典立法中被删除了,因此《民法典》第590 条有一般化的空间。但是立法机关民法典释义书指出,侵权责任编删除不可抗力条款的原因是“侵权责任法前三章的内容,有些已经放在民法典总则编中作出规定,例如不可抗力……”〔45〕同前注〔18〕,黄薇主编书,第2 页。就立法本意而言,侵权领域出现不可抗力情况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第180 条。而且《民法典》第590 条还规定了不可抗力发生后,债务人就不可抗力的发生以及对债务履行的影响负有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目的是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这是典型的合同规则。侵权领域中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产生类似的通知义务。总之,《民法典》第590 条没有在债法层面予以一般化的必要,也难以提升为一般化规定,把它保留在合同法领域作为一个合同法上的特别规定,也许是更妥当的。
以上这些《民法典》中实质债法总则的规定,就是第468 条所谓“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非合同之债可以直接适用。合同编通则的其他条文原则上只能适用于合同法领域,若要在非合同之债中适用,须以类推的方式进行法律论证。识别债法总则规定的意义就在于明确非合同之债在适用合同编通则时,何时需要额外进行论证,何时不需论证。
四、“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解释论探索
非合同之债原则上适用债法总则规定,但允许有例外,此即《民法典》第468 条但书“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之所指。最高院民法典释义书指出:“在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根据其性质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如何理解‘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就成了适用本条规定的关键所在。”〔46〕同前注〔19〕,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51 页。本文认可这一判断,同时认为这一关键问题需要学说与司法实践在长期互动中,逐个案件、逐个类型地渐进解决。本文对其试先作一些解释论上的探索。
(一)“根据其性质”并非指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的性质差异
当下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解须先予澄清。立法机关民法典释义书认为:“在判断合同编通则的某一法律规定是否适用于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时,要注意把握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在性质上的不同,结合该法律规定所规范的内容,根据该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作具体判断。例如,根据法定之债的性质,关于合同订立、合同解除的有关规则就不能适用于这些法定之债。再如,合同编通则关于违约金的规定,也不适用于法定之债。”〔47〕同前注〔18〕,黄薇主编书,第31 页。最高院民法典释义书认为:“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须注意如若一种非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会导致其违反其指导原则和基本功能,那么就应认定此债权债务关系依据性质不宜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48〕同前注〔19〕,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51 页。在《民法典》颁布之前,亦有学者指出:“将合同法规则适用于非合同之债时,应避免意定之债和法定之债不合事理的等量齐观,因此应规定‘根据其性质或者目的’不应当适用的除外规则。”〔49〕同前注〔2〕,朱虎文。以上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认为“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核心是法定之债(非合同之债)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意定之债(合同之债)的规则。所谓“注意把握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在性质上的不同”,“一种非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会导致其违反其指导原则和基本功能”,“应避免意定之债和法定之债不合事理的等量齐观”等,都是对这一核心点的不同表述。
在我国《民法典》实质债法总则的背景下,以上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依《民法典》第468 条,非合同之债并不适用合同之债的规定,而是应适用“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即债法总则规定。债法总则规定本来就能够同时适用于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对这一点在立法及学说识别的过程中已经作出判断了。因此,此处不会出现非合同之债依其性质不能适用合同之债规则的问题,因为单纯的合同规则根本就不会构成债法总则规定。正如前述立法机关民法典释义书所举的例子,合同订立、合同解除、违约金规则不适用于法定之债。然而法定之债不适用合同订立等纯粹的合同规则本是当然之理,这不是《民法典》第468 条但书要解决的问题,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问题。
(二)债的不同标的的性质差异是“根据其性质”的重要内容
债的标的有多种不同的形态,如金钱、实物、劳务、权利、不作为等。非合同之债中虽以金钱之债最为常见,但其标的的可能形态仍然是多样化的。债的标的的性质差异,构成“根据其性质”的重要内容。
例如,不当得利中会出现特定物之债,如特定物买卖合同无效、被撤销后,请求返还已交付的特定物;单方允诺也可能以特定物为标的,如球赛中以球星签名的球衣为标的,为到场观众设立幸运奖。特定物之债依其性质只能由拥有特定物的债务人履行,无法适用债务承担、第三人代为履行、由第三人履行规则;特定物基于其特定性,也无法适用多数人债务规则及法定抵销规则。再如,不当得利及单方允诺中,还可能出现以权利为标的的债,如股权、知识产权,这些权利与特定物类似,依其性质也难以适用债务承担、第三人代为履行、由第三人履行、多数人债务及法定抵销规则。质言之,以上提及的债法总则规定是以种类物尤其是金钱为假想标的设计的,特定物之债及权利之债打破了这一假设,导致不能适用。例如,侵权行为可以导致恢复原状的债务,如对毁损之物进行修复,这种以行为为标的的债务也不能适用以金钱债务为假想对象的诸多债法总则规定,如不适用多数人债务、强制履行、提存、抵销等规则。再如,大多数非合同之债是金钱之债,金钱之债不发生履行不能,故不适用不可抗力免责规则。这又是因为不可抗力规则是以实物之债为假想对象设计的,金钱之债依其性质不能适用。又如,侵权行为可能引发受害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使加害人负有不作为债务;由于债法是以作为债务为典型状态设计的,导致不作为债务实际上不适用债法总则的大部分规定,如不能适用多数人债务、债务承担、第三人代为履行、由第三人履行、部分履行、代位权、撤销权、强制履行、提存、抵销等规则。
一个规则是否为债法总则规定,检验方法是其对各种债,包括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缔约过失之债、单方允诺之债等是否都能够原则上适用。须特别注意,前述检验债法总则规定的各种债是以发生原因为标准划分的,而不是以债的标的为标准划分的,这就是问题根源所在。各种原因发生的债都能产生金钱之债,通常也能够产生一些其他标的之债;而债法总则规定主要的假想适用类型就是金钱之债,这就导致了各种原因发生的债似乎都能适用债法总则规定的印象。但如果我们依债的标的不同区分的各种债检验,立即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实物之债(特定物之债尤甚)、权利之债、劳务之债、不作为之债在适用债法总则规定时,都会遇到很多依其性质不能适用的例外,连金钱之债也会遇到不适用不可抗力规则这样的例外。依不同的检验标准会得到不同的结论。综上,“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重要考虑因素,是不同的债的标的之性质。
有学者指出,合同之债中债的标的的丰富性展现得更为典型,因此在合同之债当中同样有基于债的标的之性质不能适用债法总则规定的问题。〔50〕同前注〔29〕,柳经纬书,第147-151 页。但在我国民法典上,只允许在非合同之债中判断是否“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债法总则规定,在合同之债中却没有进行此种判断的立法依据。
(三)“根据其性质”应扩及“目的”
“根据其性质”的排除效果是否足够,殊值探讨。
例如,债的抵销是债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可以适用于整个债法领域,但是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能由债务人主动抵销,这是一个非合同之债不能适用债法总则规定的典型。〔51〕须注意,《民法典》第568 条抵销规则的但书“根据债务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与《民法典》第468 条但书“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功能相同,但第568 条将“根据其性质”具体化为“根据债务性质”,将“不能适用”具体化为“不能抵销”,故其构成第468 条但书之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得由债务人主动抵销的原因,一是该债务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这是对主观恶性强的违法行为的一种制裁,若债务人通过抵销行为轻松逃脱责任则会使制裁的目的落空。〔52〕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8 页。二是保障故意侵权中的受害人能够获得救济。三是避免诱发侵权行为。〔53〕同前注〔23〕,郑玉波书,第517 页;王利明:《债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766 页。可见,此处不适用抵销规则的原因似乎不是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性质”,而是故意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目的,即制裁故意侵权人、救济故意侵权中的受害人,以及避免发生非正义的后果。
又如,通说认为禁止扣押的债权不能由债务人主动抵销。〔54〕同前注〔23〕,张广兴书,第64、65、86 页;同前注〔33〕,韩世远书,第704-705 页;同前注〔52〕,王洪亮书,第177 页。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其旨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基本生活,即属于禁止扣押的债权。〔55〕同前注〔33〕,韩世远书,第704-705 页。此类债权可能基于合同产生,也可能基于非合同事由产生,如工资债权、抚恤金等,〔56〕同前注〔52〕,王洪亮书,第177 页。但在禁止扣押范围内,均不得由债务人主动抵销。这里不适用抵销规则的原因仍在于禁止扣押债权的目的,即保障被债权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该例再次说明两点。其一,无论是合同之债还是非合同之债,都存在不能适用债法总则的例外。其二,判断是否适用债法总则时,目的(债权目的)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有学者即建议第468 条应表述为“根据其性质或者目的”,〔57〕同前注〔2〕,朱虎文。此值赞同。
性质与目的并非一事。性质存在于事物自身,是对事物本质的描述;目的存在于事物之外,是事物追求的对象。以性质涵盖目的恐非可行。为实现《民法典》第468 条准确界定债法总则规定适用范围的立法目的,应将“根据其性质”目的性扩张为“根据其性质或者目的”。
五、实质债法总则的体系效益
由实质债法总则可以进一步确立与形成我国的债法体系,此举裨益甚多。
债法分则主要由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缔约过失、单方允诺等各种债的发生规则构成。其中,合同之债的特殊规则规定于合同编第一分编与第二分编,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特殊规则规定于侵权责任编,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的发生规则规定于合同编之准合同分编,缔约过失之债的发生规则规定于合同编通则第500 条、第501 条,悬赏广告之债的发生规则规定于合同编通则第499 条。以上各种债发生之后,在法律效果上统一适用处于合同编通则中的实质债法总则。以上就是我国民法典上的债法体系。可以说,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其实就是一个欠缺了侵权之债特殊规则的《民法典》债编。明确这一债法体系有以下益处。
第一,可以将准合同概念置于一边,给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留下更宽广的解释和发展空间。
在罗马法上,无因管理与非债清偿被归于准契约。法国民法沿袭罗马法。但《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排斥准契约概念,将无因管理以及设置了一般规定的不当得利都作为债的独立发生原因。〔58〕同前注〔23〕,张广兴书,第64、65、86 页。
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是事实行为,并非法律行为。以上行为中均不包含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法律效果也不是基于效果意思产生,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产生。之所以称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为准合同,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着眼于发生端,即其均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行为发生,故与合同类似。二是着眼于效果端,即其均发生与缔结合同类似的后果。但是从发生上说,合同的根本是双方意思表示合致,不具备这一点就会有根本上的差异,难言类似。而且在不当得利中的非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尤其是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中,债务人(侵权人)并非自愿承担债务,债权人也并非自愿受侵害而取得债权,这里无法用自愿行为加以解释。从效果上说,所谓发生与缔结合同类似的后果,其实就是给付关系,这就是债,不需要依附合同就能获得解释。质言之,准合同毋宁被看作是债法得到妥善建构之前,用以对实质债之领域进行体系化的过渡手段。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民法,一旦建立债法体系就会排斥准契约概念,并非偶然。正如王利明教授指出的,“在不设置债法总则的情形下,引入准合同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最佳的模式选择还是设置债法总则编”,“如果设置债法总则,就没有必要再引入准合同的概念”。〔59〕王利明:《准合同与债法总则的设立》,载《法学家》2018 年第1 期,第126-127 页。
尤应强调的是,以上并不只是一个概念使用的问题,而是涉及法律的发展。黄茂荣教授称这种为了维持原有规定之继续性的外观而进行的“表见拟制”为“一种说理上的幌子”,“其发生的原因在于为处理系争的问题,尚无成熟的法律原则被发展出来,以至于必须表见地将系争案型借用一个在当时被接受的法律原则,来加以处理——虽然这个借用的本身,正显示着被借用的法律原则并不是处理系争案型之该当原则。”〔60〕同前注〔10〕,黄茂荣书,第157、158 页。在债法被发展出来之前,对无因管理、非债清偿的处理须借用一个在当时被接受的法律制度,此即契约,于是它们被称为准契约;而这个借用本身正显示着契约制度并不是处理无因管理、非债清偿的该当制度。“其结果,这种借用一方面使或许本来被正确地发展出来并被接受的法律原则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使系争案型所预示的发展因而受到抑制。”〔61〕同前注〔10〕,黄茂荣书,第160 页。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固然可以借用合同获得一定的说明,但也会使它们因这种拟制而受到发展上的抑制。因为一旦使用“准合同”概念,又不肯把这个概念当成虚无,合同规则就会对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产生适用(准用)或解释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存在于债的发生领域,则等于在用意定机制解决法定机制的问题,其并不适当;如果影响存在于债的效果领域,则在已有债法总则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实属多余。质言之,在《民法典》立法中,我们并没有需要利用“准合同”概念解决的法技术问题,只是需要用它给出一个体系编排的理由,以回答为什么能够把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放入合同编。但如果理解了合同编其实就是缺少了侵权之债特殊规则的债编,那么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在其中取得一席之地根本就不需作特别说明。任何制度纳入债编都并非必须与合同发生勾连,只需要发生给付关系上的法效果即为已足。因此,在存在实质债法总则及债法体系的基础上,合同编第三分编其实不需要“准合同”这样的章名,正大光明地以“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为章名即可。今后也不必依托“准合同”概念发展解释论,避免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这些典型的法定之债被合同规则掣肘,削弱了保障其妥当发展的制度独立性。
第二,悬赏广告不必作合同化解释。
悬赏广告被规定在“合同的订立”一章。依体系解释,其似乎应被解释为合同订立的一种方式。但若依合同说解释悬赏广告,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完成指定行为时,会因欠缺缔约能力而无法取得报酬;不知悬赏广告存在的人完成指定行为时,会因不知要约的存在而无法进行承诺,亦无法取得报酬。与之相比,“单独行为说”更符合交易安全、行为人利益以及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62〕同前注〔23〕,张广兴书,第60 页。
若在实质债法总则统领下建立起我国的债法体系,则可认为合同编实为缺少了侵权之债特殊规则的债编,其他非合同之债的发生规则都已被安置在该编的相关位置。悬赏广告因系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发生之债,与合同订立近似而被纳入“合同的订立”一章,但它仍从属于我国债法体系中一种独立的债的发生原因,即“单方允诺”。此时,对悬赏广告作单方行为的解释就具有了解释论上的空间。〔63〕在民法典背景下,王利明教授仍然认为悬赏广告是单方行为,参见前注〔4〕,王利明文。我国《民法典》第三编的本质就是债编,不是合同编。对该编的内容不必非要作合同化的解释,否则将会影响相关制度理论构成的合理性,并限制其解释及发展空间。
第三,保持债的体系的开放性。
除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缔约过失、单方允诺这些典型之债以外,法律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的非典型之债。非典型之债在法律效果上同样具有适用债法一般规则的需要。〔64〕柳经纬教授对非典型之债进行了大量列举,如民法典债编以外的非典型之债(如物权编上拾得遗失物产生的债、添附中的求偿权、相邻关系中的补偿、共有关系中的优先购买权及费用分担、共有财产分割时的作价补偿关系和瑕疵担保责任、地上权期限届满后的补偿关系等;亲属、继承编中的扶养请求权、赡养请求权、夫妻离婚时的补偿和经济帮助请求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遗产酌给请求权、受遗赠人请求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给付受遗赠财物的权利等)、民事特别法上的非典型之债(如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及分红请求权、票据债务人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共同海损的分摊关系等)、公法上的非典型之债(如税收债务、规费之债和征收征用补偿关系等),同时明确指出了债法总则的设立对非典型之债的法律适用的意义。参见柳经纬:《非典型之债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4 期;柳经纬:《论添附中的求偿关系之法律性质——兼谈非典型之债与债法总则的设立问题》,载《法学》2006 年第12 期。而且非典型之债具有开放性,因此可以通过设立给付关系这一根本法律途径,解决社会及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新问题。如果不肯认债法体系的存在,只依法典形式认可合同编,则以后产生的新型非典型之债若要在合同编上寻得可适用规范,可能就需通过意思表示的拟制和推定合意的手段。但事实上非典型之债通常都是法定之债,合同化的解释方式会扭曲这些债的发生机制,实为一种不当的限制。相反,若确认了实质债法总则及债法体系,因各种非典型之债都是独立的债的发生原因,不必受合同规则的牵制,完全可以发展出一套适用于自己的发生规则,并在法律效果上直接适用实质债法总则规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