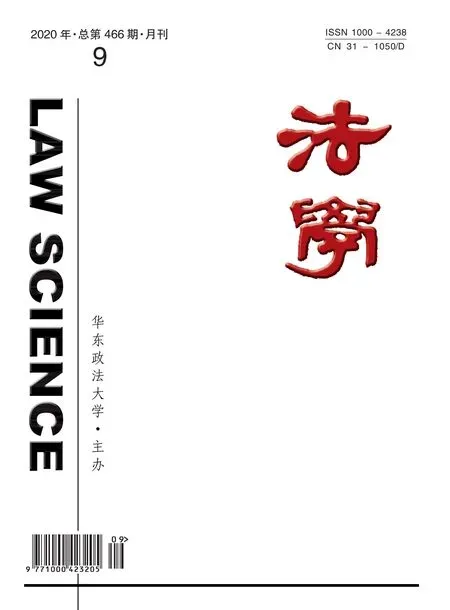《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的展开路径
2020-02-25叶金强
叶金强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款规定在承继《民法通则》第106 条第2 款、《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所确立的过错责任大一般条款模式的同时,也作了一些修正,即在《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前半句之后增加了“造成损害的”这一限定词。〔1〕一般条款中“造成损害的”表述,经历了从增加到删除再到增加之反复。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八编第7 条第1 款规定:“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其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中,草案条文中一直含有“造成损害的”表述,直至《侵权责任法(草案)》(四次审议稿)第6 条第1 款删除了“造成损害的”表述,形成了与正式通过的文本相同的规定,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现《民法典》重新加回。作为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该款规定具有非常强大的规范功能,称其为侵权责任编中最重要的条款亦不为过。1986 年公布的《民法通则》为何会选择这样大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不得而知,但自此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展开路径便已成为极具实务价值的理论问题,虽然该问题一度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对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讨论热情在新世纪后持续升温,〔2〕参见张新宝:《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载《法学研究》2001 年第4 期;刘生亮:《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功能论》,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 年第4 期;周友军:《论我国过错侵权的一般条款》,载《法学》2007 年第1 期;王利明:《论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的关系》,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3 期;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载《中外法学》2009 年第5 期。伴随对其保护范围、“权利利益区分论”等问题的讨论,〔3〕参见王利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载《法学家》2009 年第3 期;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3 期;于飞:《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4 期;方新军:《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的解释论前提》,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1 期。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而在司法实践中,该一般条款也被大量地援引作为裁判的规范基础。〔4〕笔者于2020 年6 月8 日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获得的裁判文书总量有156 万多件。目前的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该如何运用《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判断侵权是否构成。
《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具有完整的规范结构,采用经典的“要件—效果”模式。在各项要件均已满足的情况下,将发生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而在要件层面上,对于其中的过错要件、因果关系要件、损害要件没有争议。至于在过错之外是否还有违法性要件,学界则有不同观点。针对《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的解释则形成了“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之争。〔5〕《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与《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学说发展脉络是完全可以贯通的。“三要件说”论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依文义解释得出的结论是其未采违法性要件,且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也排斥了违法性要件。〔6〕参见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1 期,第5 页。而“四要件说”论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将“过错”和“侵害”行为分别加以规定,表明立法基本上采用了“四要件说”;〔7〕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10 期,第29 页。该款通过规定“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这一要件“征引”了违法性,一个行为如果造成了他人民事权益遭受侵害的后果,原则上就具有违法性。〔8〕参见李承亮:《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及其类型化——以过错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兴起与演变为背景》,载《清华法学》2010 年第5 期,第90 页。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四要件说”坚定的支持者。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七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该司法解释明确支持“四要件说”。各级法院在个案中也多采“四要件说”。例如,在“郑晓东与王玉臣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款规定,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有四:一、须有违法性之行为;二、行为人存在过错;三、受害人有损害事实;四、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郑晓东主张王孙艳应对其承担侵权责任,其应举证证明王孙艳的行为已满足上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9〕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 民终5498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 年作出的一份裁判文书中也明确表示:“根据民法原理,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以及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10〕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申3200 号民事裁定书。综上所述,虽然“三要件说”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考虑到不作为侵权和间接侵权不断扩张的现实状况,但我国学说和裁判的主流是采“四要件说”,即承认违法性要件的独立地位。
在要件、效果明确的前提下,法律适用似乎不再成为问题。但其实面对这样大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法官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立法者就是否应采法国法的大一般条款模式也曾有过长时间的立场摇摆,后认为法国法模式只是将既存难题掩盖起来并推卸给法官,立法应有更多的担当,从而创设出三个小一般条款模式。〔11〕Vgl. Hein Kötz, Gerhard Wagner, Deliktsrecht, München: Luchterland, 10. Aufl., 2006, S. 40.德国法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其降低了法官的法律适用负担,但也存在显著的缺陷。如今,在我国法上过错责任的大一般条款之下,如何让法官获得充分的指引,法教义学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盖法教义学原本即具有减少法律适用负担、促成法律规范体系化、存储法律解释可能、使法律理性化的功能。〔12〕参见卜元石:《法教义学的显性化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载《南大法学》2020 年第1 期,第51 页。
我国《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的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为应如何确定侵权法所保护范围及保护强度之难题。在因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情形下,被侵害利益是否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通常被认为是关键之所在。“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中“民事权益”的范围如何划定,纯粹经济上利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获得保护,条文所立“要件—效果”模式如何与个案相结合,这些均直接关涉过错责任如何实现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在现有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建构契合现行法律体系的法教义学框架,为司法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引。
二、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展开模式之争
(一)德国法模式魔力之破解
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展开模式是学界争议较大的重大问题。秉承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民法,很难抗拒欧陆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影响力。对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有学者提出遁入德国法模式的解释论观点,认为对其应作“目的性限缩”解释,进而具体化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绝对权并造成损害、因过错违反保护他人法律并造成损害、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方式加害于他人。〔13〕同前注〔3〕,葛云松文,第44 页。这三种类型完整落入德国法模式之中,分别与《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第823条第2 款、第826 条相对应。由于一般条款非常具有弹性,法官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类型化一方面可以为法官裁判提供指引,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度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14〕不过,此处一般条款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具有完整的规范结构。所以,具体化的问题在类型化之外,处于有力竞争地位的就是以要件为基础的弹性评价框架。对此,下文将详细论述。就我国法上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展开路径而言,德国侵权法上的三个小一般条款模式确实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在解释论上直接将其限缩解释为德国法模式,多少有些雕琢痕迹。
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展开过程中,很自然地会形成一些类型,这些类型与德国法具有相似性也很正常。民法在现行法秩序下构建了民事权利体系,确立了各项权利所覆盖利益的应受保护属性,侵权法当然应对其提供救济,正所谓“有权利即有救济”。由此,自然形成了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展开中的第一个类型,即权利侵害型。权利之外、未被权利所覆盖的利益保护问题,则更为复杂一些。而在存在保护性法规的情况下,自然会形成另外一个类型,即违反保护性法规型。保护性法规确立了相关利益的应受保护属性,行为人侵害此类利益即具有违法性,应构成侵权。此外,私法领域公序良俗原则构成行为自由的重要约束,基于伦理性的考量,违背公序良俗侵害他人利益的,侵权法上必然给予高度的负面评价。此时,即使被侵害利益的价值位阶不高,可归责性的高强度也可弥补利益保护力度之不足,使其同样可构成侵权。这样,类似于德国法模式的三个类型确实可以推导出来。
在司法实践中,除权利侵害型,后两个类型也不乏案例支持。例如,在“王培堂与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被告连续数年的年报对其受到环保处罚的情况均未予披露,法院认定其构成虚假陈述,根据《证券法》(2014 年)第63、69 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15〕参见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 民初909 号民事判决书。《证券法》的规定为保护性法规,使得投资人性质上为纯粹经济上利益的投资利益获得了保护。在“李某、王某诉寿某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当事人之间只发生一笔借贷关系,被告利用担保协议续签形成的第二份担保合同,恶意提起诉讼迫使原告应诉。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恶意诉讼侵权,也未设立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制度,但因恶意诉讼引起的侵权赔偿案件,并非无法可依,其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畴;《侵权责任法》第6 条是对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恶意诉讼侵权属于行为人利用诉讼程序进行的一种侵权行为,自然受该条的规制。”由此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16〕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4 民终810 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属于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他人纯粹经济上利益的案型。在“黄家祥与唐春秋、唐春燕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用锄头将原告父亲的坟墓挖出一个土坑,二审法院认为,黄家祥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并侵害了被上诉人的人格利益,故维持了一审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 条作出的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17〕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 民终170 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属于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他人人身利益的案型。
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展开形成上述三个类型,虽可能受到德国法模式的潜在影响,但其具有自身价值体系的内在合理性,也系逻辑推演的自然结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大的一般条款,其展开不应止步于这三个类型,而应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具备为无法被涵摄于此三个类型的利益直接提供保护的可能性。在上述三个可自然形成的类型之外进行扩展的可能性,除个案正义之外,同时是基于法律发展、法律与社会同步之考虑,没有必要人为阻断大一般条款所具有的法律发展功能。透过法官自由裁量权寻得个案妥当判断,既可以实现个案正义,又可以为法律发展积累经验。前述学者主张限缩解释需排除的三种情形,〔18〕同前注〔3〕,葛云松文,第44 页。并不能排除综合权衡之后得出构成侵权之结论的可能。在未涉及权利侵害且未违反保护性法规又不与公序良俗相冲突的情形下,侵害他人利益导致损害的,一律否认构成侵权的可能是不妥当的。虽然公序良俗极具弹性,背俗侵权类型辐射范围的扩张可以增加刚性三类型模式的弹性,但公序良俗仍然有其辐射边界,有其力有不逮之处,保有大一般条款的开放性仍然有其意义。
除了上述理由之外,德国法模式本身的缺陷也值得关注。德国民法主动放弃法国法的过错责任大一般条款模式,所选择采行的三个小一般条款之结构在其民法典实施之后很快就被突破了。《德国民法典》生效后的实践发展表明,该侵权构成体系已经基本上被打破。〔19〕Vgl. Ernst von Caemmerer, Wandlungen des Deliktsrechts, Verlag C. F. Müller Karsruhe, 1960, S. 69.通过塑造所谓交往安全义务、构建对营业企业的侵权保护、承认一般人格权,德国司法实践迅疾地进行了漏洞填补;通过此三个小一般条款,使得德国法与采一般侵权构成体系(systemen des allgemeinen deliktstatbestandes)之立法在结果上高度接近。〔20〕同上注,第71 页。由此,德国法所赋予的这一法律保护,得以与采一般侵权构成体系之立法同样广泛。〔21〕同前注〔19〕,Ernst von Caemmerer 书,第71 页。德国法系通过发展出另外三个小一般条款,即交往安全义务、营业权、一般人格权条款,弥补了原有三个小一般条款的不足,逐步达到与大一般条款相当的保护程度。〔22〕德国法此处的“转型”源于实质正义的牵引,但其过程却迂回曲折。有学者指出:德国法官为了达到其预想的结果,必须采取违反方法论上各项原则的方式,完全不顾法律中明确、固定的表述,将立法者的明确意图置之不顾。参见[奥]海尔姆特·库齐奥: 《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朱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6 页。那么,如果将我国法上的过错责任大一般条款限缩解释为德国侵权法上的三个小一般条款模式,我国法是否还需要重走德国法的发展道路,通过法官造法弥补其不足即成问题。比较法上可以观察到的倒是相反方向的努力。在采德国法模式的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 条第1 项前段规定的保护客体范围大幅扩张,其规范功能亦随之扩大,更加确立其属“一般概括条款”的规范地位。〔23〕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 卷第3 期,第233 页。即将对应于《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 条第1 项前段“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扩张构建为类似于法国侵权法的大一般条款。
此外,德国法为克服其侵权法结构上的不足,还大量地将侵权案件置入合同领域予以救济。有学者指出,德国学说采用合同义务思想保护生命、身体和财产(保护义务),这实际上是在合同法领域创造了一个设立侵权法注意义务的镜像。〔24〕参见[德]格哈德·瓦格纳:《比较侵权法》,耿林译,载[德]马蒂亚斯·赖曼、莱因哈德·齐默尔曼编:《牛津比较法手册》,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06 页。诸如缔约过失责任、积极侵害债权、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等,均是因侵权法保护范围过于狭窄而被挤压生成的。因为合同法上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身体完整性与有形财产,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允许纯粹经济损失赔偿。〔25〕同上注,格哈德·瓦格纳文,第1007 页。这样,如果将我国法上的过错责任大一般条款限缩解释为德国法模式,则是否还需要创设诸如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制度?可见,无论是从保有大一般条款的弹性,还是从德国法模式的本身缺陷考虑,均不宜将我国法上的过错责任大一般条款限缩解释于德国法上的三个小一般条款模式。
(二)“权利利益区分论”之检讨
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展开与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密切相关,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侵害具体利益是否构成侵权。就此而言,“权利利益区分论”也系指向一般条款的具体化路径,现有讨论多将其与德国侵权法上的三个小一般条款模式联系起来。“权利利益区分论”者主张,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程度不同,对权利采原则上保护的态度,对利益则采例外保护的态度;法国法模式不区分权利与利益,以过错责任概括保护两者,德国法模式则采区分保护的态度。〔26〕同前注〔3〕,于飞文,第104 页。区分保护也称差别保护,与之对应的可以是平等保护。〔27〕平等保护同样存在问题,不同利益的价值位阶不同,保护力度则不得不有所差别,实不宜平等。而区分保护、差别保护的问题是,权利、利益各自内部等值化处理,以及任一权利均高于任一利益之安排,均与价值体系相冲突。至于区分论之中的结构性安排,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差别保护说”以法益是否具有社会公开性或排他支配性、法益是否具有确定性或预见可能性等作为区分权利与利益的基础,进而以之作为侵权责任类型化基础,使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理。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利益者,不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 条第1 项前段规定,被害人不得请求损害赔偿,只有在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方法或违反保护他人法律而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形,被害人才能依该第184 条第1 项后段或第2 项规定请求损害赔偿。〔28〕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155 页。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通说认为,应区分权利与利益采“差别保护说”;〔29〕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96 页。若对其“民法”第184 条第1 项前段不作区别权利与利益予以差别性保护的解释,则第184 条整体法条文义及规范结构将失去意义。〔30〕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98 页。这是采德国法模式在解释论上的正常推论。但已有学者指出,德国法模式并非将权利和利益区别保护,而是将绝对权与其他利益区别保护,后者包括绝对权以外的权利(比如债权、形成权)以及权利之外的其他利益。〔31〕同前注〔3〕,葛云松文,第45 页。
我国许多学者十分认同德国法模式,主张我国法应采“区分保护论”。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的解释必须以权利和利益的区分保护作为理论前提;〔32〕同前注〔3〕,方新军文,第156 页。另有学者主张,《侵权责任法》第6 条第1 款、第2 条虽没有规范途径的规定,但没有限制对权利和利益采不同的规范途径,学说与司法解释可以在该第6 条第1 款、第2 条的基础上,发展出权利和利益的区分保护模式。〔33〕参见王成:《侵权之“权”的认定与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路径——兼论〈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载《清华法学》2011 年第2 期,第68 页。不过,参与立法的全国人大法工委人员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于权利和利益在保护程度和侵权构成要件上不作区分,两者完全等同。〔34〕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 页。笔者认为,权利与利益不存在区别保护还是平等保护的问题。《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规定的是“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并没有在规范结构上区分权利与利益而给予不同安排,解释论上也解释不出所谓的“区分保护论”,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利益区分论”实际上是对德国法模式的一种解释,但其实德国法如果存在区分,区分的也不是权利和利益。一方面,《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不包括相对权,即使存在区分,也是将绝对权区别于相对权及其他法益。另一方面,德国学者已指出,《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列举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种生活利益(lebensgüter),并不是权利,但在受到侵害时却完全等同于权利,给予同等保护;而同样非属权利的名誉因没有被第823 条第1 款明确提及,最初只是由第823 条第2 款结合刑法的规定而间接得到保护,现被认为是由一般人格权导出的具体人格权。〔35〕Vgl.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Verlag C. H. Beck, 7. Aufl., 1989, S. 127.这样,在四分五裂之下,并无“权利利益区分论”的立足之地。
其次,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通常同时意味着权利内部和利益内部的平等保护。但是权利存在价值位阶的不同,利益同样如此,故而在法伦理上,不同位阶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力度应有不同,何来各自内部的平等保护?若主张权利和利益内部仍然是区分保护,则一方面其规范构造何在,另一方面,将应区分保护者分成两个系列的意义何在?况且这两个系列就不存在交叉的可能吗?权利的内核为利益,其与未被权利覆盖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重要性程度位差。未被权利覆盖的利益之价值,在位阶上同样可能高于权利覆盖之利益。例如,未权利化的人格利益可能高于物权覆盖下物的使用利益(使用功能妨碍)。这样,如果存在区分保护的系列,其构成也应当是不同权利与利益的交叉站位,根本不可能形成机械的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即存在当时并未权利化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四项法益立于与绝对权同样重要的位置,超越了债权这样的相对权的现象。在日本法上,有学者指出,在权利侵害以及与其相当的较强利益受到侵害的场合,除非有正当防卫等特别的正当化事由,应该不问侵害行为的样态而判断存在违法性;与此相对,被侵害的是除此之外的不那么强有力的利益的场合,因为对这种利益的侵害未必可以被直接评价为值得法的责难,所以就有必要根据侵害行为的样态相应地判断违法性的有无。〔36〕参见[日]吉村良一:《日本侵权行为法》,张挺、文元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8 页。“较强利益”的存在已经足以瓦解“权利利益区分论”的阵型。
有学者为“区分保护论”提出了三点辩护理由:德国法模式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区分保护,使得司法实务具有相对明确的可操作性;德国法模式在公法和私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德国法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37〕同前注〔3〕,方新军文,第146-147 页。对此,德国法模式所获得的可操作性是以保护范围过于狭窄为代价的,而且,可操作性完全通过其他模式获得。所谓架起公法与私法之间桥梁的功能,是通过保护性法规实现的;保护性法规并非德国法模式所独有,我国法和法国法上也存在保护性法规,同样可以发挥连接公法与私法的功能。而架起法律与道德之间桥梁的媒介是公序良俗原则,该原则当然也不是德国法模式所独有,即使德国法模式土崩瓦解,公序良俗原则仍然继续发挥沟通法律与道德的功能。
另有学者从权利与利益的关系角度对“区分保护论”予以批驳,认为“权利”与“利益”两者本质上并无不同,不足以作为差别保护的正当性基础;〔38〕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125 页。权利与利益的相同本质,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流动关系,难以严格区分,两者差异往往只是一线之隔、一念之间、不同观察角度而已;人格权或人格利益、身份权或身份利益、物权或支配利益、债权或给付利益,甚至财产权或财产利益等均是明显例证;此种微妙、模糊的关系不足以作为差别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亦不足以作为拒绝保护利益的法律理由。〔39〕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225-226 页。这些理由有一定说服力。
整体而言,“权利”与“利益”之间不存在区分保护还是同等保护的问题,在实质正义牵引下,只能是跨越权利与利益的彻底的区分保护。〔40〕有学者指出,实质性的法益区分思想在各国侵权法中都存在,对不同类型法益进行不同程度的侵权法保护是各国侵权法的制度共识。参见朱虎:《侵权法中的法益区分保护:思想与技术》,载《比较法研究》2015 年第5 期,第47 页。权利覆盖的利益和未被权利覆盖的利益,在价值体系中均有其独有的重要性程度,相应的保护力度也会不同。重要性程度差异恒在,但差异并非横亘于权利和利益之间。区分权利与利益而构建两立的规范结构予以区分保护,在价值上不妥当,在技术上也问题重重。正因为如此,德国法在立法之初便将部分利益上提、将部分权利下拉,勉强确立两分的规范结构,并自此走向消解该规范模式之途,通过判例创设框架权、扩张契约法版图等方式进行矫正。日本于2004 年民法现代语化的修改中,在《日本民法典》第709 条的权利侵害要件中加上了“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形成可导向违法性多元化的立场,〔41〕同前注〔36〕,吉村良一书,第28-29 页。同样是与权利与利益二分结构呈南辕北辙之势。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 条也被批评为对利益保护不足并形成规范漏洞,认为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破除或超越权利与利益的严格区别,将第184 条第1 项前段规定的保护客体范围扩大,使其及于“利益”。〔42〕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178 页。凡此种种,足见“区分保护论”之弊端。
(三)努力之方向
由前文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德国法模式本身即存在重大缺陷,在立法论上并不是妥当之选择;在我国法采行大一般条款的背景下,试图通过解释论导入德国法模式更不可取。“权利利益区分论”者真正指向的仍然是对德国法模式的肯认;但区分权利与利益而设置不同规范结构的二分方案,会导向对部分利益的过度保护和对部分利益的保护不足,形成大面积评价矛盾。这些解释论主张在一般条款具体化问题上均非妥当之选。同时,像法国法这样的大一般条款模式也有明显的不足,诸如纯粹经济上利益是在保护范围之内,但从立法中根本无法识别出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方予保护。〔43〕Vgl. Helmut Koziol, Das bewegliche System: Die goldene Mitte für Gesetzgebung und Dogmatik, Austrian Law Journal 3/2017, S. 163.接下来的问题是,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到底应如何和个案情境相结合。
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展开,核心便是具体侵权构成的判断,故可能还是需要回归至责任基础与责任的一般构成。从责任成立的正当化基础角度探寻一般条款的具体化路径,也许可以寻得妥适的方案。已有学者将目光转向此一领域,主张应让侵权法回归其“保护合同以外利益”的一般法和普通法的功能,让“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过错”等原本开放、可塑的传统侵权责任要件扮演其控制角色;对一般财产利益的保护,应回归传统侵权责任四要件控制体系,确定注意义务存在与否及其范围;〔44〕参见贺栩栩:《侵权救济四要件理论的力量——权益层级保护方法论之检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5 期,第121 页。“损害”“行为不法”“过失”“因果关系”等过失责任原则下既有的侵权责任成立要件,其概念本身所负载的规范功能已经足以使其妥适承担筛选过滤各种社会生活利益的任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可以向法律解释适用者提供足够的方法或手段,使其考量权利与利益特性上的不同,在责任是否成立上作出适当的判断,以达到适度合理限制加害人责任的目的。〔45〕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156 页。
上述观点侧重于各要件分别独立发挥过滤的功能,对此有学者还详细阐述了各项要件是如何实现对“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的。〔46〕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157 页以下。但是要件之间不应该是相互割裂的关系,要件具有满足度之纬度,以要件背后的要素及其满足度为基础的动态体系可能更有利于价值的实现。〔47〕参见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1 期,第164 页以下。针对法益区分保护的问题,已有学者指出,为了解决德国法规范技术所带来的问题,更为妥当的方式是以动态系统作为方法基础构建动态、弹性的法益区分保护规范技术。〔48〕同前注〔40〕,朱虎文,第59 页。不过,在其所主张的动态体系中,所列举的因素都仅仅是考量因素而非要件,司法者要在个案中对这些考量因素进行权衡。〔49〕同前注〔40〕,朱虎文,第58 页。笔者认为,应当以要件为中心,通过要件的要素化形成动态体系并由此体现立法的约束。
三、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基础性评价框架
(一)动态体系论与要件的动态化
动态体系论是由奥地利学者维尔伯格教授所首创,〔50〕Vgl. Walter Wilburg, Die Elemente des Schadensrechts, N. G. Elwert’sche Verlag, G. Braun,1941; Walter Wilburg, Entwicklung eines Beweglichen Systems im Bürgerlichen Recht, Verlag Jos. A. kienreich, Granz, 1950.主张动态的法律构成,由多种要素构建综合评价框架,在个案中根据实际出现的要素数量及其强度,经权衡得出结论。学界对动态体系论在我国的影响已有详尽的梳理。〔51〕参见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第41 页。许多研究已较为精准地展现了动态体系论的特质。例如,有学者利用信息重要性、披露可能性、期待合理性与信赖紧密度四个要素构建评价框架,以判断说明义务之有无及程度。〔52〕参见尚连杰:《缔约过程中说明义务的动态体系论》,载《法学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103 页。动态体系论中各要素的背后是一个个价值判断,要素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而选定。已有学者指出,维尔伯格将各法域的基础性评价称为要素,目前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原理。〔53〕同前注〔43〕,Helmut Koziol 文,第165 页。私法的价值基础是由复数的原理构成的,原理之间的角力、竞争与合作〔54〕参见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51 页。推演出全部私法秩序与私法的具体构造。故私法原理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与动态体系论中各要素强度的综合考量之间具有内在的亲缘关系。正如学者所言,原理之间的“协作”与维尔伯格“可变的体系”模型观念的想法相近。〔55〕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351 页。如此一来,倒是可以获得对动态体系论更好的理解。
当然,要件的设定也是以原理为支撑,规则的核心是“要件+效果”之构成,原理与具体类型对接便会生发出要件与效果的安排,形成规则,而规则的解释仍需回到原理。要件并非评价的对象,其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特征表现在其也是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而存在,〔56〕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六版),建诚印刷有限公司2011 年版,第291 页。此种评价系取向于其背后原理价值的实现。同为原理之外化的要件和要素,有着质的相似性;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的刚性与弹性之差异应是外加上去的东西,系概念法学的遗迹。如果为实现实质正义的需要,为什么不可以将要件弹性化?“要件—效果”模式完全可以优化。
传统的“要件—效果”模式以要件之满足导向效果之发生,其核心特质包括要件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发生影响;单个要件评价结论两极化,忽视要件满足度之纬度;效果上的“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 Alles-oder-Nichts)安排。这些特质重在法律安定性的维护,但忽略了个案实质正义的要求。要件之间的隔绝模式是刚性架构的特征之一,但是,要件的设定本来就是一种法技术措施,个案的结论应是一个整体评价的结果,不同的要件反映的往往是冲突主体不同的正当利益诉求,将各要件割裂开来,放弃比较、权衡的努力,有违私法衡平的目标。〔57〕参见叶金强:《私法效果的弹性化机制——以不合意、错误与合同解释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1 期,第105 页。而要件存在满足度的差异是不争的事实,将要件满足度置于考虑范围之外,与要件设立之初的考量相冲突,存在评价上的矛盾。例如,《民法典》第151 条规定的显失公平之构成需要具备意思瑕疵之要件,而意思瑕疵存在程度的不同。胁迫情形下的意思瑕疵程度极高,可无限接近于意思强制,故胁迫的构成根本不考虑给付是否失衡,欺诈情形下的意思瑕疵程度次之,但因同样存在一方较高强度的可归责性,故也不考虑给付是否失衡。在显失公平情形下,意思瑕疵程度弱于胁迫,〔58〕显失公平情形下的意思瑕疵程度未必弱于欺诈情形,但可归责性程度较弱,在欺诈情形下是故意误导对方使其陷入判断错误并加以利用,在显失公平情形下只是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行为人的可归责性程度弱于胁迫和欺诈,故法律行为效力之否定需要考虑给付是否失衡。这样,意思瑕疵、给付失衡及可归责性成为三个独立的要件,且均有满足度的问题,显失公平之构成需要在综合考量这三个要件满足度的基础上作出判断。〔59〕有学者构建了显失公平的动态体系,抽取出自治原理和给付均衡原理,并将意思瑕疵和可归责性置于自治原理之下,其所谓“双重要件”与此处的三要件构成具有实质的一致性。参见王磊:《论显失公平规则的内在体系——以〈民法总则〉第151 条的解释论为中心》,载《法律科学》2018 年第2 期,第91 页。不考虑要件满足度会陷入价值上的自相矛盾,即同时主张意思瑕疵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
“要件—效果”模式之“全有或全无”的效果安排同样存在问题。要件综合满足度不同,效果就应该有差异,否则也会出现评价矛盾。已有学者建议以阶梯化的效果(Abgestufte Rechtsfolgten)代替“全有或全无”规则。〔60〕同前注〔43〕,Helmut Koziol 文,第176 页。放弃“全有或全无”规则而使效果与要件综合满足度相调适的途径,在损害赔偿领域可以包括个别损害项目的排除、比例责任的采用、金钱量化方法之选择等。在契约法上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个方向的努力,即在效果十分刚性的情况下,通过要件的调整达成规则的合理化。《民法典》第487 条规定的承诺传递迟延规则,没有留下权衡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的空间,效果已被设定于一定的强度之上,即肯定合同成立并提供履行利益保障,故在解释论上会将要件严格化,限缩规则适用范围,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要求提高到一定程度,同时要求受要约人没有任何可归责事由。〔61〕参见叶金强:《合同法上承诺传递迟延的制度安排》,载《法学》2012 年第1 期,第93 页。
“要件—效果”模式虽存有诸多缺陷,但在法律体系中仍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为此,优化与改良应是努力的方向。阶梯化效果模式涉及“要件—效果”模式效果层面的改进,不在本文主题范围之内。本文主要讨论透过要件动态化所达成的构成上的弹性化。如前所述,要件与要素均是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而选定;实定法上的固定构成要件只不过是多个评价要素各种强度的排列组合中的一个示例。〔62〕同前注〔51〕,解亘、班天可文,第55 页。那么,为何“要件—效果”模式就不可具有与“要素—效果”模式一样的弹性?立法上两种模式的表达形式虽可能有一些差别,但是,“要件—效果”模式之立法表达通常并未明确排斥对个案情景的综合考量。基于价值法学之取向以及实质正义目标达成之需要,完全可以打破要件之间的相互隔绝模式,充分关注要件满足度之纬度,在个案要件综合满足度之基础上,作出应否发生相应效果的判断。要件之间的相互隔绝破坏了其背后原理之间相互妥协、合作的关系,割裂了价值之间沟通与调和的渠道;对要件满足度纬度的无视,引发前文所述的评价矛盾;而对要件满足度的综合考量,正是在多重价值背景下寻得个案情景下妥当结论的必由之路。
(二)《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下的基础性评价框架
《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虽为一般条款,但其却具有一般性的规范结构,从中可以分梳出要件与效果之构成。由此,该款规定实质上成为固定规则和诸如公序良俗这样极度空灵的一般条款之间的中间形态,而动态体系通常被理解为介于固定的构成要件和模糊的一般条款之间的中间道路。〔63〕同前注〔43〕,Helmut Koziol 文,第169 页。如此一来,该款规定恰好与动态体系处于同一位置。本文在批判的基础上正是要导向一个动态的基础性评价框架,为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构建一个可操作的具体化方案。
如前所述,通说在一般侵权构成上采“四要件说”,在四要件具备的前提下,侵权法律效果即行发生。《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中“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之表达,分别列举了过错、违法性(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因果关系(造成)、损害这四个要件。这四个要件背后的原理构成了责任的基础。原理间的竞争与合作,需要打破要件之间的藩篱。为此,打通要件之间的通道,将有些要件分解成数个要素以达成精细评价,充分考虑各要件的满足度,并在要件综合满足度的基础上得出责任是否构成之结论,这些成为基础性评价框架的结构性特征。而基础性评价框架的灵魂,是由各要件支撑起来的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之中,各要件可以以单一要素的面目出场,也可能分解为数个要素。
损害要件的具备,不仅要有事实上的不利益发生,还需通过违法性、过错、因果关系三要件的评价过滤。对此需考察是否有法律保护的利益受损、所受损害是否可以预见和避免、损害是否与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其中有任何一个得出否定结论,或者在综合考量后得出否定结论,就会认为损害要件并不具备。在损害赔偿范围的动态体系构造中,损害要件没有被植入评价体系之中,〔64〕同前注〔47〕,叶金强文,第167 页。除考虑其上述特殊性之外,也与相应作业指向的就是损害相关。现予讨论的是构成上的动态体系,损害要件之中哪些要素可以参与进来,值得讨论。有学者在讨论损害要件的过滤功能时提及损害的正当性和严重性两个纬度,正当性系指得请求赔偿之属性。〔65〕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157 页以下。其实,正当性纬度与违法性判断完全重合,盖不法利益不予保护,故从违法性要件切断可能更为合理。作为事实性前提的事实上损害之存在,乃逻辑上的当然要求,本身并不含有评价因素。而损害“严重性”之表达未能反映问题的实质。轻微损害可不予考虑,倒是一个通行的观念;在其他要素满足度均不强的情况下,损害的轻微性甚至可以成为否定责任构成的关键理由。这样,损害的轻微程度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力较弱的要素纳入评价框架之中。
在诸要件之中,违法性要件最为复杂,其承担了核心的评价功能,是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展开中的主角。有学者指出,违法性要件的主要功能是限制侵权责任,系区分合法行为造成损失与不法行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工具。〔66〕参见[瑞]海因茨·雷伊:《瑞士侵权责任法》,贺栩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85 页。另有学者认为,不是损害也不是过失,而是义务违反(Pflichtwidrigkeit),构成了损害赔偿义务的基础。〔67〕Vgl. Gert Brüggemeier, Gesellschaftliche Schadensverteilung und Deliksrecht, AcP 182(1982), S. 450.此处的义务违反恰好与违法性相对应。德国法在扩张侵权法保护范围,通过判例创设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这样的框架权时,其侵权构成的核心问题便是违法性判断问题;侵害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违法性不是通过侵害行为直接导出,而是在个案中通过利益权衡确定的。〔68〕同前注〔11〕,Hein Kötz 书,第158、169 页。违法性要件相比于过错要件和因果关系要件,在责任成立的判断中担负了更大的功能。就像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定适宜通过因果关系要件来实现,违法性程度和过错程度也是透过因果关系要件来影响损害赔偿范围那样,〔69〕参见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08 年第1 期,第51 页。责任成立与否的判断适宜通过违法性要件来实现,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满足度常被汇入违法性要件影响责任的成立。在过错或因果关系满足度没有低到可以直接否定责任构成的程度时,过错和因果关系满足度对责任构成的影响会透过违法性要件加以表达。关于日本侵权法上违法性之“相关关系说”,有学者批判其已包含了将违法性与故意过失一元化理解的方向;〔70〕同前注〔36〕,吉村良一书,第24 页。即含有将过错程度纳入违法性判断框架以影响侵权构成的意味。在背俗侵权类型中,违法性要件的具备需要行为人违背公序良俗,由过错的高强度弥补利益保护力度的不足。另有学者指出,保护范围取决于所有要素的总分量。〔71〕See Helmut Koziol, Wrongfulness under Austrian Law, in Helmut Kozio(led.), Unification of Tort Law: Wrongfulnes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p. 16.该论点所强调的正是诸因素之合力确定保护范围,透过违法性要件影响责任的成立。
任何侵权法秩序的基本问题均在于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72〕Vgl. Larenz, 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 Besonder Teil, 2. Halbband, 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 S. 350.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形成一种对抗,前者趋向于证成违法性,后者趋向于否定违法性。法益保护依据利益重要性程度呈现为不同的保护强度;行为自由则可作更宽泛的理解,将作为行为基础的权利行使、自由竞争价值等所有可以支持行为人有所行为的因素均包括进去。这样,违法性内在之考量可区分为两个要素,一是利益保护强度,一是行为正当化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关关系说”,也许可以获得更好的理解。“相关关系说”主张,违法性的有无应该按照被侵害利益的种类与侵权行为的样态相互关联地进行判断;侵权行为的样态有作为权利的行使而被认可的样态,有作为自由活动的范围而被放任的样态,还有作为法规的违反而被禁止的情形等。〔73〕同前注〔36〕,吉村良一书,第23 页。这在违法性的内部可以理解为利益保护力度和行为正当化程度的相关化处理,从而将违法性建立在利益保护力度和行为正当化程度综合考量的基础之上。
利益保护力度表现为由零向上的一个递升系列。参照《欧洲侵权法原则》的理解,处于保护力度顶端的是生命、身体和精神的完整性,以及人的尊严和自由,其次是包括无形财产在内的财产权,再次是纯粹经济上利益和契约关系。〔74〕See Art. 2:102 of PETL.从只要有侵害就能直接判定为违法的予以强有力保护的利益,到需要附加侵害行为的恶性才可能判断违法的利益,侵权行为法所保护的利益存在许多种类。〔75〕同前注〔36〕,吉村良一书,第41 页。不过,利益本身虽有相对确定的保护力度,但是具体案型中侵权行为触及的是利益的核心地带还是边缘地带,违法性程度还会有所不同;故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侵害高位阶利益边缘地带之违法性程度,可能低于侵害低位阶利益核心地带所形成的违法性程度。利益保护力度为零的情形相对罕见,通常都是保护力度上存有差异,绝对不保护的不法利益很少。窃贼行窃获得的利益为不法利益,对窃贼被他人致伤住院未能行窃而遭受之损失,行为人显然不需要赔偿,行窃获得的利益在法律上的保护力度为零。类似地,诸如违法经营色情场所或赌场的营业利益、人贩子可获得的售卖人口之利益、买凶者支付的报酬利益等,均为非法利益,不具有合法性。不过,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被害人单纯从事不法、不当或不道德的行为、活动、职业,或是处于类似状态下所取得的利益,不能当然即可认为该利益不正当,必须进一步审查该利益的取得本身,是否为民事责任法规范秩序所禁止取得的利益,或从民事责任法规范目的观察,如允许赔偿此一不利益,是否足以导致不法、不当或不道德的结果。〔76〕同前注〔23〕,陈忠五文,第158 页。此外,不法利益与合法利益之间也存在灰色地带,呈现边缘模糊状态。例如,在有些案型中,相关费用到底是绝对不保护的非法“保护费”,还是应予保护的“安保费用”,可能存在争议。
行为的正当化程度,类似于违法性的消极要件。足够强大的行为正当性可阻却违法,否定责任的构成;较弱的行为正当性可降低行为违法性程度,进而在综合权衡中影响责任的构成与范围。可为行为提供正当化支持的情形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受害人同意、权利行使等,行为的社会有用性、经济活动自由等也可以为行为正当化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撑。在行为系权利之行使的场合,实质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涉及权利边界问题。损害越是发生在权利内核处,被侵害权利的力量越大;行为越是处于自身权利核心地带,该权利的正当化功能也越强。〔77〕同前注〔47〕,叶金强文,第169 页。在个案中,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具体的合理性程度直接影响其正当化程度,在正当化程度不够充足时,会发生承担部分责任的效果。〔78〕参见《民法典》第181 条、第182 条之规定。这可以认为是在未能彻底阻却违法的基础上,违法性程度对赔偿范围发生了影响。作为行为正当性基础的诸多因素,共同为行为正当化程度做点滴贡献,最终形成一个合力,再和利益保护力度相折衷,以确定行为违法性程度。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过失又可以分为重大过失和轻过失。故意含有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是“知”和“欲”的结合。过失则是表现为应当预见损害发生之可能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未能避免可避免之损害发生。过错有程度的不同,从轻过失到重大过失再到故意和恶意,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法伦理上对过错的负面评价,与过错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负面评价的程度应当对责任的构成与范围产生影响,不能做门槛式地切断于某处、门槛上下效果截然两分的安排。在基础性评价框架之中,当然应有过错的一席之地,过错要件将以过错程度这样的单一要素参与进来。
因果关系要件是效果动态化的重要实现工具,但在责任构成方面,更多地是以事实面的一些因素发挥影响。法律上因果关系中的价值面上的因素,多是从其他要件中借来,此时自然会回归其本位。因果关系要件可分解为两个要素,即因果关系贡献度和因果关系确定性程度。这两个要素虽均以事实为基础,但其背后有相应价值支撑,该价值判断为行为人应当对其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79〕在过失标准客观化、无过错责任扩张的大背景下,价值理念上致害人担责理念已取得了更大的优势。而因果关系贡献度反映的是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由行为人导致,因果关系确定性程度反映的是损害在多大可能上由行为人导致,这两者正是实现上述价值所需要考量的因素。
综上所述,基础性评价框架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利益保护强度、行为正当化程度、过错程度、因果关系贡献度、因果关系确定性程度以及损害轻微程度。这些要素在个案中会以不同的强度出场,司法者通过综合考量各要素强度作出裁决。如学者所言,一个公正的判决仅在权衡个案所有情景后才能够获得。〔80〕Vgl. Walter Wilburg, Entwicklung eines Beweglichen Systems im bürgerlichen Recht, Verlag Jos. A. Kienreich, Graz, 1950, S.16.源于原理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要素之间也表现为或协作或制约的关系。同质功能的要素在协动作用中通常形成合力,其可以相互补强从而更趋近于实现其共同的目标;异质功能的要素则在协动作用中往往是背离的,从而形成相互的制约关系。〔81〕同前注〔59〕,王磊文,第94 页。行为正当化程度和影响力很弱的损害轻微程度系指向责任的否定,其他要素指向责任的肯定。有学者指出,要素的权重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塑造出基础性评价(Basiswertung),型构出标准案型(Normalfall),确立通常足以成立责任的影响因子的总权重;只有存在用于比较的标准时,才能确定个案中的权重是更多还是更少;当影响因子总权重达到标准量时,无论单个要素的权重如何,责任均可成立。〔82〕同前注〔43〕,Helmut Koziol 文,第167 页。总权重标准量的确定应是基于一种法感觉,即在权衡各项要素的量度、进行必要的叠加或折抵之后达到的一种应可构成侵权的判断。总权重标准量不可能十分精确,只需要适度、妥当。
维尔伯格在损害赔偿动态体系中强调,在某一要素以特别的强度登场时,该要素独自就足以正当化损害赔偿责任。〔83〕同前注〔80〕,Walter Wilburg 书,第13 页。在此次讨论的基础性评价框架之中,通常不会出现单一高强度要素直接证成责任的情形,单一要素的高强度只是使得判断更容易得出,但对责任的证成通常需要其他要素的适度支持,因为单一要素存在独自否定责任成立的可能。例如,在行为正当化程度非常高时,可直接阻断侵权的构成;在事实上因果关系确定不存在,即因果关系贡献度为零、因果关系确定性程度为零时,即不构成侵权;在不法利益遭受损失时,即使是故意导致也不负责任;在行为人根本无法预见也不可能避免的损害发生时,其会作为意外事件而不发生责任问题。不过,损害的轻微程度再弱,也不能单独确定责任不成立,在故意致害的情形下损害程度再轻微也不能免责。整体而言,单一要素决定的情形较为少见,通常情形下均是在综合考量各要素强度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基础性评价框架是在立法控制下构建的弹性体系,立法通过设定要件限定要素。正如学者所言,动态体系是立法者给予法官受控制的裁量可能,故立法对应予考量的有限数量的要素和因子之命名和描述就非常关键,至少其可以从法条中推导出来。〔84〕同前注〔43〕,Helmut Koziol 文,第168 页。过错责任一般条款已设定了基本的要件构成,为弹性评价体系提供了价值基础。通过明确规定法官裁判时应当考量的各种重要因素,立法者能够决定性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并且也使得法官裁量具有可预见性,同时又有所控制地兼顾了生活事实的多样性。〔85〕参见[奥]海尔穆特·库奇奥:《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朱岩译,载《法学家》2009 年第3 期,第6 页。基础性评价框架的运行,经由法官受限的自由裁量,兼顾个案正义和法的安定性。
四、具体案型中基础性评价框架之运用
(一)权利侵害型
将基础性评价框架运用于个案,可以得出个案中被侵害利益是否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具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结论。基础性评价框架的运用成为《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具体化的基本方案。极度空灵的一般条款的具体化,通常只能借助于类型化。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因具有完整的规范结构,得以构建基础性评价框架,但其并不排斥类型化,类型化仍然有其意义,但仅是辅助性的意义。以现行法为基础,可以区分出“权利侵害型”和“利益侵害型”两大类型。一方面,法条即以“民事权益”(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概括保护客体,另一方面,权利的识别采形式化标准,以现行法有明确规定者为限;这样,这两个类型已隐含在现有法律体系之中。
在传统“要件—效果”模式下,依“结果不法说”之通说,权利侵害征引违法性,〔86〕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8 页。在其他要件同时具备时即可构成侵权,除非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这使得权利侵害型案件给人以争议不大的感觉,但其实只有非常典型的权利侵害案件才会有这样的可能。所谓“非常典型”是指侵害行为触及的是权利之核心,其他要件满足度又适中,相对容易得出确定性结论。此时,运用基础性评价框架,也会相对无争议地导出同样的结论。但是当行为触及的并非权利非常核心区域,而是处于权利射程之边远地带,其他要件满足度错落参差,行为又有一些正当性支撑时,就难于径直得出结论。在权利辐射的边缘地带,可能也需要背俗侵害才能构成侵权。这样的案件可能被定位为疑难案件,对于疑难案件应如何裁判,“权利利益区分论”等均没有提供答案。此时,唯有引入基础性评价框架,通过谨慎的权衡导出契合个案情景的妥适结论。而上述典型案型实质上也是运用基础性评价框架完成评价,只是其过程被简化并可能是无意识地在运用。
也许有人会认为在权利侵害型中不需要运用基础性评价框架。日本法上“法益二阶构造说”认为,应该对法益进行二元划分,对于强的法益类型,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认可损害赔偿请求;对于弱的法益类型,则要综合考虑行为的样态等因素再行决断。〔87〕参见龙俊:《权益侵害之要件化》,载《法学研究》2010 年第4 期,第36 页。对此种二元构造的问题,在前文对“权利利益区分论”的批判中已有充分讨论。区分法益差别化处理,是与现行法相冲突的。一般条款已设定了统一的构成要件,要件均具有满足度问题,实宜通过动态权衡框架导引妥适的裁判结果。基础性评价框架是在要件约束下、解释论空间内的展开,具有坚实的规范基础。无论权利侵害还是利益侵害,均需要在弹性的要件构成框架下完成评价工作,不存在例外。将权利侵害案型均描述为简单、清晰、无疑义,与实践完全不符。其实,对绝对权的保护范围是高度不清晰的,事实上也根本不是绝对的,并非可对抗任何妨害。〔88〕同前注〔43〕,Helmut Koziol 文,第172 页。在权利侵害案型中,同样是权衡无处不在。权利给予权利人的利益,是通过限制他人的自由而得以实现的;有时某一权利的实现会给他人带来严重的损害。〔89〕参见[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700 页。当然,法律安排之内的他人不利益本来就是其应承受的,以体现分配正义,关键是边缘模糊性无处不在,并且他人行为还可能是以权利行使的名义作出的。
在权利侵害型中,需要精细权衡、充分利用基础性评价框架的复杂案件,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行为触及的是权利边缘地带的案型,在受侵害利益是否已超出权利范围、保护力度强弱上会存在争议,此时,公序良俗原则都可能被引入。行为人过错程度等其他要素的强度也会存在差异。需要在综合考量各要素满足度的基础上,得出侵权构成与否的结论。二是行为正当性获得良好支持的案型,尤其是表现为权利行使的场合,行为正当化程度与利益保护力度之间需要进行较量。例如,在言论侵害名誉权的案型中,需要充分考虑名誉权的保护范围与力度、言论自由的范围与强度,在结合具体案情让两者背后的原理充分角力之后得出结论。此外,个案中要件满足度、要素之强度,存在各种复杂多样的组合可能。此时,均得在基础性评价框架中劳心耗力地完成细致的评价工作。
(二)利益侵害型
利益侵害型与权利侵害型共享同一架构,均是以基础性评价框架为其法律构造之核心。如果存在利益保护力度之差异,不同保护力度之影响也是在评价框架内实现。问题不是在抽象层面哪些利益应受保护,而是个案中具体的利益是否应予保护;无论是权利侵害型还是利益侵害型,均是以此作为基本问题,这决定了两者对评价框架的共同需求。两者可能的不同在于,权利核心区域的利益保护相对清晰、肯定,而权利外利益之保护多相对模糊;而且,利益保护模式也存在差别,一为权利化模式,一为行为规制模式。有德国学者归纳出权利的分配属性(Zuweisungsgehalt)、排除功能(Ausschlußfunktion)、社会典型公开性(sozialtypische O☆enkundigkeit)等特征。〔90〕同前注〔72〕,Larenz、Canaris 书,第374 页。通过将一定利益划归权利人享有并赋予排除他人干涉的效能,权利化模式为特定利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保护可能。而行为规制模式系通过对他人行为的控制构建利益的生存空间,故行为控制形成的利益空间之判断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些差别在基础性评价框架的运用中会带来不同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利益的行为规制模式是建立在相应立法规定之上的,并非所有利益均有行为规制规则的支持,对这些利益的侵权构成判断,就需要回归法秩序的深处作更为自由的价值权衡,进而从基础性评价框架中得到妥当的结论。与此不同,权利化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下的判断,是有立法选择在其中发挥支撑与限制功能。
利益侵害型中的利益,主要包括纯粹经济上利益和一般人格利益。对于一般人格利益保护,现行法已设有规定。《民法典》第109 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该规定性质上为人格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为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人格利益提供了一般性保护。在个案中对相应人格利益侵害是否提供救济,还是要通过基础性评价框架导出结论。对于纯粹经济上利益,有学者指出:纯粹经济损失问题在美国侵权法中仍旧是“一潭死水”;其原因也许是,大部分重要的案例制定法对此已有考虑,制定法已经将其作为各种制定法责任。〔91〕同前注〔24〕,格哈德·瓦格纳文,第1006 页。而纯粹经济损失对法国法学家来说是个难题,其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甚至连这种表达方式都不知道。〔92〕同前注〔24〕,格哈德·瓦格纳文,第1001 页。法国法上的此种状况可能与其侵权法采过错责任的大一般条款模式有关。大一般条款模式本身已为纯粹经济上利益之保护留下了空间。在我国现行法上,纯粹经济上利益可依据《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之规定,利用基础性评价框架导出是否予以保护的结论。在有保护性法规的情况下,〔93〕保护性法规未必仅为权利外利益提供保护,在指向权利的场合,其功能定位更值得探究。其解决的是违法性、因果关系的问题,还是仅为作为义务发生基础,值得专题研究。规则同时提供了支持和约束,相关权衡已由立法者完成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立法作出的价值选择在为司法提供指引的同时也构成对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法官可在对相应规定解释的基础上,透过基础性评价框架导出结论。有学者指出:在奥地利法中,违反保护性法律与违反善良风俗行为的意义远远小于在德国法中的意义,因为德国法尝试通过保护性法律与善良风俗原则克服《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的狭窄性和僵硬性。〔94〕同前注〔22〕,海尔姆特·库齐奥书,第179 页。言下之意,即奥地利法中即使没有保护性法规、不惊动公序良俗原则,也能从一般条款中得出是否保护的结论,而德国法不行。就此而言,我国法上背俗侵权、保护性法规之意义也会相对较弱。
在背俗侵权之中,有学者认为,善良风俗与侵害故意乃不同的要件,前者为客观归责,后者为主观归责,仍须加以区别,因此应认为侵害行为违背善良风俗本身即足以成立其违法性。〔95〕同前注〔86〕,王泽鉴书,第274 页。在现行法下,违背善良风俗导致他人损害,虽没有明确的规范基础,但是从基础性评价框架之中相对容易得出相应结论,即背俗侵权者在侵害的利益保护强度较弱时,也应承担侵权责任。由比较法实践形成的此种类型印记,也可以减轻法官在相应案型中的评价负担。保护性法规本身具有规范效力,可以明确部分权利外利益的保护条件。不过,即使按照保护性法规得不出利益应受保护的结论,也不排除经基础性评价框架而得出构成侵权结论的可能。由此,进一步反映了基础性评价框架的重要性,以及保护性法规和背俗侵权类型之意义的减弱。
五、结论
我国《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作为过错责任的大一般条款,在解释论上应维护其开放性功能,而将其限缩解释为德国法上三个小一般条款的方案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德国民法典》相关模式已在实践中被修正得支离破碎。“权利利益区分论”是以德国法模式为背景的解释论,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权利覆盖之利益的保护力度,并不均高于未为权利覆盖之利益;在缺乏立法支撑的前提下,力主“权利利益区分论”,近似沉醉于德国法模式的“痴人说梦”。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具体化,需要回归立法设定的要件,以要件的动态化为基础构建基础性评价框架,为一般条款与个案的结合提供技术性方案。
作为一般条款具体化的基础性评价框架,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利益保护强度、行为正当化程度、过错程度、因果关系贡献度、因果关系确定性程度以及损害轻微程度。这些要素在个案中会以不同的强度出场,司法者应通过综合考量各要素强度作出裁决。权利侵害型和利益侵害型案件均需透过此基础性评价框架导出结论。保护性法规、背俗侵权的结构性意义已大幅度降低。过错责任的大一般条款结合基础性评价框架所形成的具体化路径,为我国侵权法实践提供充足的弹性空间,在开放性的态势之下个案正义的实现可获得有力的技术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