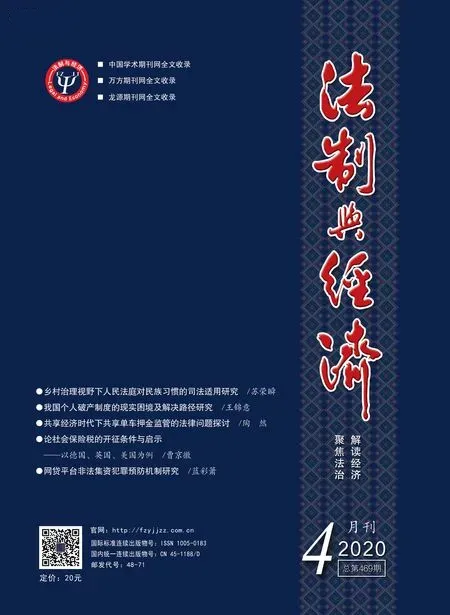关于封闭领域支配性成立作为义务来源的探讨
2020-02-25张琪舒
张琪舒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266000)
一、不作为的原因力
(一)不作为的概念
不作为本身不具备直接的物理表现,一直处于静止状态,若没有发生相应后果,不作为将难以被捕捉,如李斯特所言:“不作为是指对结果的意志上的不阻止。”[1]不作为是否是行为,在理论界曾有过争论。但不作为犯罪责任的追究本就是在行为人没有实施动态行为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不作为的行为性与否对司法实践意义不大,研究重点应移至对不作为的原因力的探索。[2]
(二)有关不作为的学说
不作为以“无”的状态存在,但应承认其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因果关系的证成也存在不同的学说:1.他行为说。行为人对于结果无所作为,但实施的其他行为中包含结果发生的原因力。2.先行行为说。其主张不作为与不作为之前的行为即先行行为,共同对结果的发生产生了原因力。3.干涉说。该学说认为不作为人决意控制身体静止,积极地打破起果条件与防果条件均衡,实现危害结果。4.义务违反说。该学说则认为仅在行为人没有承担法律所期待的作为义务时,其不作为和结果之间才具有原因力。(5)防果可能性说。该说认为,在不作为犯罪中,行为人掌控结果回避的可能却不采取阻止措施,从而对社会具有显而易见的危险性。反之,即使行为人负有防果义务但无力改变,其不作为便对社会没有危险。[3]
以上学说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但它们对不作为原因力的阐述都依托于对作为的考察,这也是淡化不作为犯偏理罪刑法定原则的有效途径。刑法中明确规定了作为犯罪的形态,作为犯罪的实质是对刑法义务的积极否定,因此,对不作为犯的判断逻辑可以从不作为人的应负义务出发。
二、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
社会因每个人都积极履行义务而井然有序,但违反义务并不全然是积极作为,如遗弃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上述犯罪以不作为的形式构成,理论上称之为纯正不作为犯。相应地,不纯正不作为犯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触犯法定的作为之罪,属于适用刑法定罪的非常态问题。
(一)形式义务论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以形式判断为开端,发展出义务论的三分法、四分法甚至五分法。形式的作为义务论最早由费尔巴哈提出,他企图从刑法规范以外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中找寻类型化、体系化的判断规则。[4]然而违背刑法的独立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义务来源形式主义提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均非刑法规范。另外,就我国而言,后续确立的职务、业务要求这一类义务来源同刑法相距更远;法律行为虽有设权性,但多为民法等私法范畴,同刑事责任的关联之薄弱固不待言。由此观之,单纯的形式标准无法达到限定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范围的目的。如陈兴良教授所言:“最初的形式,仅限于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民法的规定,后来扩大到合约,最后又进一步扩大到条理。因为条理属于不成文的道德义务,因而将条理作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加以确定,既有混淆道德与法律之嫌,又有暧昧不明之弊,引起较大争论。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教授所言,包含了条理的作为义务已经突破了形式的界限。”[5]
(二)实质义务论
自德国学者斯鸠贝尔提出将“先行行为”纳入义务的范围后,形式义务论的立场就不再纯粹,带有明显的实质论色彩。从形式作为义务论到实质作为义务论的演进,是后人站在前人的筑基之上对研究方法的变通,而非排斥和舍弃。从存在论到价值论的视角迁移,学者们更加关注风险发生与应负义务者之间的关联度,出现了“功能说”“支配说”和“承担说”。
阿明·考夫曼立足被害人的风险提出“功能说”,强调作为义务的出发点是使无辜的法益免受危险源的侵害,从而认为对危险源有控制力的人具有作为义务。这一观点未考虑实害发生的复杂条件,不能在实质上限缩义务人的范围。许乃曼从因果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支配说”,解释确定义务人的依据是“其对造成结果的原因有支配”。[6]与“功能说”不同,此说着眼于义务人的实际控制力,对“介入型不作为”有指导意义,但类似于“围观群众和父亲均不救助落水孩子”的情形,根据朴素法感情的指引,难以认为围观群众的不作为构成不作为的犯罪。日本学者在研究实质的作为义务来源时,认为应将公序良俗纳入考量范围,后受德国行为理论影响,形成了以堀内捷三为代表的“承担说”,他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是身份犯,具特定身份的义务人有使法益免受行为侵害的保障责任。[7]“身份犯”的定位虽然受到质疑,但义务人特征的考察角度是对形式义务论的深化,类似于德国学者纳格勒首倡的“保证人说”,①将实质论发展的方向引至关注义务人本身。
对比形式说和实质说,前者倾向于借助整个法律体系的规范,以及抽象“等值”判断给出作为义务的模糊框架,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的根据。后者在无形的不作为与被侵害的法益之间建立“支配力”这一有形抓手,基于支配的事实,当然产生保护责任,但在保护义务团体“亲密关系”的认定上可能混入道德义务。
三、认定封闭空间支配力的双重标准
在私法领域,安全保障义务的形成与一定的土地范围相关联。[8]类似于英美法上土地占有利益人的安保义务和德国法的交往安全义务,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了某些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保义务。按照义务来源形式论的标准,这类主体的不作为造成法益侵害可能需要承担刑法责任。民法关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而刑法看重行为,土地占有人尽管对土地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却不一定能实际主导危害结果的演化。与开放性的建筑场所不同,封闭领域的密闭空间性质将支配者作为义务的有无判断集中于对其保证人身份和控制整体因果流向的认定上。
(一)封闭空间内保证人身份的认定
保证人地位的成立可基于法律规定和事实创设。在父亲家暴孩子致其重伤,母亲冷眼旁观的案例中,因法律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明确规定,可期待母亲对孩子的保护,这种信赖关系的产生先于法律规范,后在法律规范的强制下增强,并赋予母亲相对于孩子的保证人地位。当主体之间不存在法定关系时,实施了某行为且该行为产生的结果足以超出合理范围而增加行为之外的危险的人,可被信赖对其这一事实创设行为的后果加以预防,从而以作为的方式确立该主体的保证义务。以上两类情况并不要求保证人对封闭空间的必须持有,但信赖关系的形成为封闭空间持有类保证人的讨论提供了思路。
有学者认为,空间的持有之所以可以形成保证人地位,是因为对私人生活领域的自治权范围,国家无法或者难以介入,因此个人有维护私有空间秩序的义务。[9]甲相对于闯入家中突发心脏病的乙是否具有保证人地位?依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如果法益危险的发生处在不作为者支配的领域中,不作为者就承担实质的法义务。乙在甲支配的封闭空间内,脆弱的法益依赖于甲的救助,所以甲的不作为将会承担法律后果,但这一结论违背刑法的归责原则,有道德绑架之嫌。甲乙之间并不存在法定或先前行为的铺垫,信赖关系的形成不能取决于弱势法益的单方主张,还要对甲的风险接管态度和外在表现予以考察。
(二)整体因果发展的排他性认定
要判断封闭领域的支配者是否具有作为义务,还要考虑其基于保证人身份对法益实害形成的整体因果流程的支配作用。义务人需要满足对法益自始至终的控制,试对比以下两个“出租车案”,以对此观点作出说明。案例1:甲将乙捅伤后,将其抱上丙的出租车,共同前往医院对乙进行救治。行至途中,甲骗丙停车,弃乙离去,丙遂将乙抛弃在超市门口,乙因失血过多身亡。案例2:出租车司机A在男乘客B强奸女乘客C的过程中未采取任何措施,最终B对C强奸得逞。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形成封闭空间,司机是这一空间的支配者,基于和乘客之间的契约享有保证地位。案例1中司机丙对被害人乙的脆弱法益有短暂的排他性监管,但丙无起果力,从乙受伤到死亡均未产生阻碍法益保护的排他性控制。案例2中B的行为使C的法益陷入不安定状态,司机A保持了支配的空间封闭状态,既保障了施害人对结果的积极推动,又排除了被害人防果的可能性。同样具有保证人地位的出租车司机,在所支配封闭空间助长危害实现的情况下,对排他状态的积极持续维护时,可认为其介入因果流并接管了阻止风险实害化的责任,反之则承担不作为的后果。
四、结语
封闭领域支配者并不总是负担作为义务,其对空间的支配性产生作为义务要进行形式和实质的综合分析。形式上要谨防依据信赖关系确立保证人地位时对道德义务的混淆,如近来学者们对“见危不救罪”的激烈探讨,引发道德义务刑法化的质疑。此外,要对封闭领域形成的排他性特征理性看待,从实质上判断对这一条件的持续性利用是否成为控制因果发展的关键因素。
注释
①证人指在发生某种犯罪结果的危险状态中,负有应该防止其发生的特别义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