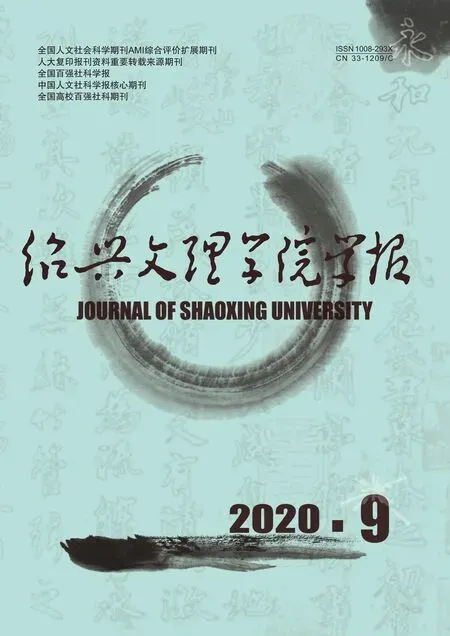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鲁、郭、茅负面评价的理论反思
2020-02-24鲁雪莉
鲁雪莉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来,一批重要现代作家被重估、重评,解构经典形象及经典作品的负面评价成为主潮。最显著者,莫过于对鲁迅、郭沫若、茅盾(以下简称鲁、郭、茅)的重评。以往对三位作家的评说,大抵将其定位为超一流作家,研究者的关注度之高、研究领域之拓展、研究成果之丰硕,非其他作家所可比拟。重评中,对三大家的评价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对鲁迅的评述曾多次泛起否定性的非鲁思潮,茅盾跌出20世纪十大小说家排名,郭沫若被列为中国新诗人第30名之后,已远非原先作家的定位。笔者以为,对鲁、郭、茅的评价,不只是对单个作家的价值评定,实则已关涉多种理论话题,而对中国现代文学领军人物作出苛评或轻率否定,也不利于文学史经验的总结,实有认真辨析的必要。
一、鲁、郭、茅负面评价的理论误区
综观新时期以来重评视阈中的鲁、郭、茅研究,已造成了对作家作品的种种误读,涉及多方面的理论话题。笔者以为,下述三种颇具代表性。
(一)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片面否定
重评中,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焦点话题,在于三位作家与现实主义不同程度的关联:鲁迅和茅盾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郭沫若虽游走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但后期确信强调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质疑,以对茅盾的评价尤甚。王一川认为,茅盾“高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偏见:似乎‘现实主义’‘史诗式’作品就高于其他”。蓝棣之则强调,《子夜》“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导致了主体性大大削弱”,因而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宣传品”,“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徐循华也在《重读〈子夜〉》中认为,茅盾坚持文艺为人生,念念不忘“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因而使作品有“传声筒”嫌疑。鲁迅的现实主义重在启蒙,他主张文学创作“为人生”,“改良人生”,旨在犀利指出人们的精神痼疾。但此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在重评中被斥为“愿意听将令,写将令文学”。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的价值大于审美的价值”。对于郭沫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大量抒写了汇入现实主义诗潮的政治抒情诗,许多研究者认为,郭沫若后期诗歌艺术不如前期,正在于他“片面否定浪漫主义,片面强调现实主义”,并认为这也同样体现在其戏剧创作中,“铺张扬厉到声色俱厉,可却掩不住骨子里的单薄虚弱。这就是主题先行之弊了,不存在任何独创性,文学的丰富性完全被抹杀”,也归咎于其剧作与现实政治的呼应。
(二)对文学思想和审美的偏至认知
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排斥,从深层透视出重评论者对文学“思想性/审美性”“政治性/艺术性”两难困境的偏至认知,这在重评中成为一个重要症候。葛红兵评价鲁迅,认为鲁迅“开始了中国新文学一个不好的历史就是偏重于思想、偏重于直接的社会功利”,“而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具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压抑了自己的审美感受在写作品,他的作品比较干巴,干涩,比较阴暗”,后来的作家服膺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可能跟他们潜意识中有鲁迅这个大师有关”。张闳认为鲁迅因拘泥于“国民性批判”观念,致使其小说的艺术空间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也过于单调呆板。李振声评价郭沫若,认为因趋附政治而“主体性主动摒弃”,“限制、妨碍、遮蔽了郭沫若‘自我’感受的真实性”。唐晓渡认为《女神》“渲泻式的大叫大嚷”,埋藏着新生后来遭受毁灭性命运的种子,郭沫若应对50—70年代流于标语化、口号化的恶劣风尚负责。由此,中国新诗逐步被意识形态与权力美学所支配,贫弱的“自性”沦为“他者”。黎焕颐批评郭沫若的“双重政治人格”,认为其“一旦置身庙堂和政治强力合而一,就必然会失去思想的个性独立和人格的道德力量”,在“政治需要”与“艺术审美”之间,郭沫若选择前者,摒弃后者,失却了一位诗人必备的思想和审美情愫,历史与自我、理性与情感无法平衡。王晓明在《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中认为存在着政治家和文学家“彼此对立”的两个茅盾,因其“没有建立起皈依文学的诚心,轻漫了文学”而“遭到艺术女神的拒绝”。徐循华阐释“子夜”模式,认为《子夜》“主题是正确无误的,但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政治性目标,‘为人生’就自然而然地变异成为‘为政治了’”,“为政治”而非“为人生”文艺观这种“重大的缺陷”使得《子夜》成为一部失败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
(三)以断裂的历史意识估定价值
对鲁、郭、茅的批评,通常也蕴含着代际之间的断裂,其中体现的历史意识,不啻是普遍性、知识性的理论话语的演绎,而并非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应对具体的历史问题。如新生代作家朱文批评鲁迅的“断裂答卷”。当代青年作家韩东、述平等认为,“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毫无教育意义”,“没有任何一位思想权威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指导意义,包括鲁迅”。诗人于坚甚至认为,鲁迅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1985年《杂文报》和《青海湖》引发的论争中,一些观点认为鲁迅的作品瑕瑜互见,“有泛泛之作与充数之篇”,《狂人日记》只停留在“模仿”程度,“而不是创新”;《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把‘典型化’变成了‘脸谱化’”。散文诗集《野草》是“二流作品”。《故事新编》“艺术价值不高”。朱光灿评价郭沫若的两篇文章中,对“《女神》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奠定了我国新诗的基础,开一代诗风”等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拔高了《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开一代诗风”有违史实,还可能导致“人们对我国新诗开创期现象认识的模糊”,引发对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地位与贡献的论争。此外,对早期和晚期郭沫若进行割裂式对比,也有把作家从历史语境中剥离之嫌。茅盾研究中,出现如王一川重排现代文学大师座次,将茅盾剔除前十排位等文学现象。这些否定性评价都是以断裂的方式将历史价值判断简单化。
二、负面评价的逻辑偏差
探究负面评价的逻辑偏差,可以作出多种理论概括。笔者以为,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由,在于“去政治化”与“去历史化”两种偏向形成的理论误导,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一)二元结构中的“去政治化”倾向
在“政治/艺术”“思想/审美”二元坐标系中,“政治”常被简单地转喻为“功利”,而“审美”也被简单地转喻为“非功利”。当评说一个作家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实则意指其艺术蕴含不足。反之亦然:当一个作家淡薄政治,专注“纯文学”“纯艺术”的追求,也似乎表征了其艺术价值较高。这种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简单理解,当然并非对文艺问题的正确阐释,其理论根源,正是在于“去政治化”偏至。通过“审美”构建的“主体”“试图更为干净地撇清其与国家/社会等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17]98,而此种惯性思维,在鲁、郭、茅的重评中却有突出表征。
对现实主义认知的迷误,甚至常常把它看成是文学“政治化”的一种手段,就有对茅盾创作的误读。如所周知,茅盾的创作推崇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主张张扬文学的社会功能与现实要求,甚至直言其创作总是“从一个社会科学命题开始的”,而其“社会科学命题”又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这在许多人看来太过“政治化”,理所当然成为批评对象。其实,茅盾所坚持的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主张,并无特别“出格”之处;特别是在“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浓厚变革风气的社会背景下,作家们用被压迫者的语言来抗议和拒绝社会,反映强烈的政治制度变革要求,是他们切入现实关怀的途径。文学的“社会化”思潮异常浓厚,文学与社会变革的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在此背景下,茅盾创作对社会现实的书写,显然契合了这一时代主潮。许多评论者批评茅盾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子夜》等作品,甚至将其升格为“茅盾创作模式”的批评,就难以避免评价的失误。如果对茅盾的“创作模式”作全面评价,还应当涉及其艺术思维的严谨性、将创造形象置于“第一位”等艺术要素的揭示,但可惜在“政治化”的命题下,这些都无足轻重,他们认为一个注重“社会化”的作家就不可能有对“艺术性”的重视,而茅盾的创作恰恰是经得起“艺术分析”的,于是这位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就被轻而易举否定了。在茅盾身上,“二元性”对立的操作与弊害,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鲁迅的评价,也存在此种“二元性”现象。在王朔看来,鲁迅“当杂文写的小说”《阿Q正传》用的都是“现成的概念”,而“概念形成的人物当作认识的武器,针对社会陋习自有他便于发扬火力指哪儿打哪儿的好处,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他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就极为有限了”[18]。张闳认为“被视为鲁迅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之作的《阿Q正传》,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未必是最好的作品”,理由之一就是“过于明显、直露的观念化的痕迹,在风格上也极不协调”[7]。如何看待这些评价?毋庸置疑,这篇小说在思想上的深刻之处,正是鲁迅洞察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深受专制暴政的压榨和蹂躏,从而在小说中剖析了在等级特权统治下禁锢而成的浸透着奴性主义的国民性,他愤懑而激烈地呼号冲破专制统治的牢笼,实现人性的解放。而深邃的思想,是否阻碍了小说的艺术性,却并不尽然。小说中的阿Q形象塑造极为成功,阿Q既是一个具有极大普遍性、进行了高度理性抽象的精神典型,又是融合了感情具象的个性鲜明的“这一个”,正如鲁迅所说的,没沾染游手之徒的狡猾就不是阿Q,但流氓气多了也不是阿Q;戴瓜皮帽而不是戴毡帽就不是阿Q,上刑场时乘摩托而不是坐大车的也不是阿Q。鲁迅赋予了“国民性”概念以独特的文学演绎,因而,《阿Q正传》同样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
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文学与政治结缘,作家倾向不同程度的政治化,或承担多种社会角色,正是特定历史语境中中国作家的独特所在。鲁、郭、茅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审视,有其对政治的独特参与方式,介入政治必能获得对现实的独到体认,“去政治化”恰是取消其特色与优势所在,显然并不可取。政治文化因其交织着现实、历史、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复杂性,往往使人们呈现出对复杂状况的认知差异。鲁、郭、茅创作的政治文化蕴含也会有不同表征,重要的是将其置于特定语境中,分析其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阐释政治的方式,从而对其文学创作与思想的政治文化蕴含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
(二)价值重估中的“去历史化”偏颇
以“断裂”的话语方式和实践方式参与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其深层的历史观念,即新历史主义所主张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是新生代作家批评鲁迅的“断裂答卷”,葛红兵对鲁迅作品语言问题的苛责,还是蓝棣之讨论茅盾《子夜》,其共同点均在忽视历史事件所独具的主体和语境,而单纯以想象中的当代性立场对之进行颠覆式批判,其本质即“去历史化”。
“去历史化”尤见于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除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立场、态度的对立之外,还来自研究者的时空错位。郭沫若的《女神》鲜明地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了新诗初创期的最高成就。但较多的评论者往往偏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并不顾及历史链条,从中寻找价值所在,确定其历史地位。《女神》的主要价值,是以暴躁凌厉的诗歌风格引领时代精神的凌厉之“气”,它为五四时代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开启了痛快的情绪宣泄通道,激发了青年们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温儒敏曾说,“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迅的小说),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如冰心的诗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19]。从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而言,郭沫若的《女神》堪称一流。大变动的五四时期,反精美、反中庸、反优雅,追求新异、叛逆的审美趣味,故《女神》中《天狗》《晨安》这类稍嫌粗放的诗作更能获取读者的青睐。对《女神》这类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经典评价不高,正是割裂了郭沫若与特定社会历史的关联,恰显示出作家评价中一种粗暴地进入历史的方式。
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提醒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形态分析”的基础上,因此,对于经典作品这一“形式”(理论)的分析,也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形态(思潮或者事件)之中,这样才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的“现场”,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20]36,对鲁、郭、茅的断裂式批评,以当代性取代历史性,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狭隘理解,显然靠不住。“去历史化”的本质必将遮蔽文学现象的历史本相,带给文学的不是历史的多元与丰富,而是单一和遗忘。
三、反思与启示
对鲁、郭、茅经典的重评,与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审美原则的确立和叙事体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次学统重建。以往的评价被概括为“仅仅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的而非广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学现象,并以此来代替或排斥艺术审美评价”[21];而提倡所谓新的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不再是特定的政治理论,而更是文学史家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它的分析方法也自然不再是那种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要深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审美的分析方法”[22]。这里的“艺术感性”和“审美的分析方法”,既指“对作品的情感体验”及具有“强烈个人性”[23]的主观描述,又指“情绪性的心理的层次,表现为各种模糊的‘政治无意识’,存在于人的各种情绪和下意识冲动,包括人的审美情绪当中”[24]264。在“重写”“重评”的许多表述中,“艺术感性”和“审美的分析方法”常常以“纯文学”概念一言蔽之。“纯文学”是鲁、郭、茅负面评价的逻辑出发点。
以“纯文学”为立足点梳理重评,从中可以发现“重写文学史”知识范型的一个本质特点,正是基于一种二元对立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理念。在重评论者看来,文学的“审美性/政治性”“艺术性/思想性”“形式语言/思想内容”“客观/主观”“集体/个人”“理性/情感”是相互排斥,不可共存的。而与“审美”相对的“政治”概念既然指的是与“革命”“功利”相关的写作模式,那么它就并不能被视为一种对等的文艺观念,而被视为压抑和控制“文学(审美)”的渊薮。因此,重评要“去政治化”,也包括要剥离与“政治”相关的“现实主义”方法论。在“去历史化”前提下,他们所提倡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潮中各种新兴、热门的新批评方法: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宗教哲学等。一些重评文章单纯以某种西方理论去印证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对事实真相的巨大盲视。
对鲁、郭、茅的负面评价中,确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或可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启示一:摒弃二元论思维,寻求解构中的建构。重评中,对“纯艺术”的强调固然有其合理性,对“审美”的强调是“回到文学自身”所需要的,但三大家创作的经典并非经不起审美分析,这只要不持偏见不难认知。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强调美学标准而虚化意识形态,甚至主张“去政治化”,则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思想立场与艺术审美并非决然对立的两个概念。对立笼统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地鼓励文学的非政治化,就有使文学创作与批评走向非公共化,丧失参与社会文化、回应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能力。在“政治”与“审美”的二元框架中否认鲁、郭、茅的艺术成就,进而否认作家现实主义选择的积极意义,无疑极端。三位作家之所以被标举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性人物,正是在于他们选择了作家的历史担当与社会责任。他们的现实主义选择既是基于“现实”需求,又是严肃审慎的理论自觉。重新评价鲁、郭、茅,必须摒弃“政治/审美”的二元论思维,寻求建构文学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内核。
启示二:把握动态系统中的恒定因素。作家评价的历时性差异,受制于人们审视文学问题采取不同的评判标准,随着时代、环境、文学观念的变迁而变迁。对鲁、郭、茅等现代作家作科学的历史评价,应将之置于中国20世纪历史文化的复杂场域中。在文学评价的动态系统中,坚持历史主义,回到历史现场,研究的分析方法与价值取向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具体地形成,考量作家在“历史的具体性”中是如何把握历史的前进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审察作家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至关重要。对复杂理论问题的解答,尤需坚持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唯如此,方能准确估量作家实现价值的可能性和未及性,对作家的评价才更具历史合理性。同时,在动态评价系统中,还应具有相对恒定的评价因素,这个评价因素,或可落实于“人的文学”标准。对鲁、郭、茅的价值评定,最终也应落实于他们对“人的文学”的贡献上。
启示三:在反思中探求一种沟通中西方不同价值的批评空间。运用西方新批评方法,从学理角度对以往被确定的鲁、郭、茅经典形象提出另一种视角的分析,完全可以。然而,唯西方方法论,简单搬用新潮批评方法,力求寻找作家“传记事实”的“外部证据”与文本“内部证据”之间的差异和裂缝,欠缺作家“内部证据”的搜寻以探究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甚至以“外部证据”颠覆“内部证据”,必出现评价的迷津。且不论西方新批评话语存在与公共经验疏离、以自律隔绝的眼光关注文艺自身以及“形式崇拜”“反教化论”“自我中心”等流弊,更应该看到中国作家的创作既受中西文化综合影响,又立足本民族的现实土壤,批评需以中国自身的文艺实践与文艺经验为基础,寻求沟通中西方不同价值的批评空间,重返“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论或是可取途径。理论与方法的中外融合和自觉自省尤为重要,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多远,有多丰富,“知人论世”或许仍是有效阐释文本、评判作家价值的方法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