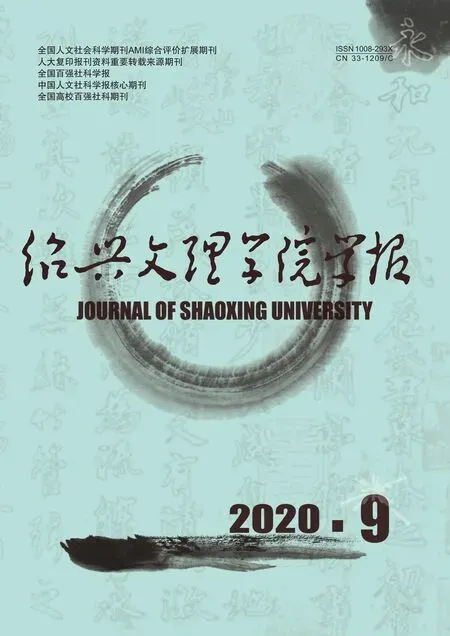叶朗“美在意象”理论反映出的当代美学主要问题
2020-02-24田义勇
田义勇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不能说没有巨大的成绩,相对于前人而言,无论从学术现代转型讲,还是从成果数量看,都有可观之处。而且,不少的美学家颇有理论雄心,在代表性的观点创新方面亦有不俗表现。单就意象研究而言,知名学者叶朗先生就有“美在意象”的较有体系性的努力尝试。这就不单纯局限于传统某一范畴之考究,而是表现出一以贯之、自成体系的理论态势。且不论成败如何,单是这种理论建构的勇气魄力就是难能可贵的。
但与此同时,笔者也由叶朗先生的著述中,加之近年来所见所思的学术诸现象,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界研究,有一种理论忧虑。所以,笔者想通过分析叶朗先生的美学研究,兼及相关的研究现状,来集中思考中国当代美学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术话语个体性意识缺失与集体群言性叙事遮蔽
当代学术界经常强调理论创新,但理论创新是以鲜明的理论个性为标志的。这就需要有强烈的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在历史上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往往是有明确的理论个体的,比如西方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中国的老子、孔子、韩非子,其理论是可以用其人命名的。就是政治人物,其思想立场也主要是以其个人名义来指称的,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再比如人们经常讲的“文责自负”,其中就有责任到具体的理论主体的要求。落实到理论话语而言,这种“文责自负”的主体意识与个人意识就具体化为理论观点的表述。而在中国学术界,习惯成自然,包括笔者在内,却经常不是单个人的立场表述形式,比如最简单的“我认为”“笔者以为”,等等,而是采取一种有意无意的“大而化之”的众人言说、集体群言的表述形式。其最为常见的表述形式,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觉得”,等等。当然,这里面也有增加理论亲近感的意图,所以也不能过于苛求。但是,倘若是进一步模糊化、以宏大叙事的口吻,就很有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文论认为”“中国传统美学以为”。这种推扩到全体的话语方式,笔者以为是现代学术话语应避免的大忌。
在叶朗先生的学术表述中,这一形式也是很典型的,比如在提出“美在意象”的命题时,他不是以“我以为”的话语形式,而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回答是:‘美’在意象”[1]。后面紧接着又是:“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这种主语设置并不是偶然的,它涉及利奥塔所谓的“科学合法化”与“语言的招数”[2]问题。在这种“中国传统美学”为主语的话语背后,是个体性主体意识的遮蔽或缺失。为什么会这样?是“法不责众”的潜意识,还是借群体、整体以自壮声势?但恰恰在这种整体化的话语主导下,理论的说服力遇到了最简单有力的挑战。“中国传统美学”,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括,倘若具体细分,就至少有儒道释之别,更不要说还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这样的朝代差异。而究其实,不是“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而显然是“叶朗先生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清楚的基本事实。但为什么会采取“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这样的模糊化、整体化的表述形式呢?在这种形式之下,有没有掩盖理论依据的不足呢?
细看可知,“美在意象”命题的提出,实质性的文献依据是两条,一是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二是马祖道一的“心不自心,因色故有”。这本来是两个独立的古人基于各自的特殊场域而各有所指的特殊言说。但是,在叶朗先生的精心组织下,两个富于个性化的言说被吸纳为一个共同的话语场的两个组件了,即是说,都各着一偏,分别否定了“美”的客观外在性与主观内在性。造成的印象是,好像这两个古人早就在等着叶朗先生来总结,统一为“美在意象”命题。这个思维论证的框架隐然是马克思批判过的那种“绝对方法”,“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正题、反题、合题”[3]。柳宗元代表的是“正题”,强调的是人的参与性;马祖道一代表的是“反题”,强调的是物的介入性;叶朗先生则代表了“合题”。这个逻辑框架可谓是“主客观统一”的翻新版本。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深入到马祖道一的言说语境中去。马祖道一说:“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随时。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4]马祖道一是禅宗大师,他的言说基于“三界唯心”的宗旨,表面上他既反对执着于心,又反对执着于物,但宗旨仍是以“心”为主,只是讲不要执着而要“随时”罢了。叶朗先生片面摘取了“心不自心,因色故有”这个片段,而不顾“凡所见色,皆是见心”这个部分。质言之,马祖道一的思想实情远比叶朗先生理解得要复杂、甚至还很全面。对照叶朗先生讲的“马祖道一的话消解了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则可知判断不确。
由上可知,由于叶朗先生缺乏明确的个体性言说意识,导致了他引述材料时也就不尊重文献本身的个体性言说。实际上,历史中的每一个言说者都是特定的话语主体,其思想观点都有特殊性乃至异质性,是不允许做简单的“同质化”处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些特殊性的言说抽象化为一种理论体系、逻辑框架的部件。这就好比一个机器零件,它不可能轻易地就被拿来严丝合缝地安装到自己的机器上,即使是一颗螺丝钉,也要考虑到尺寸配套的问题。
敉平言说者的个体性特征,统而言之,或者大而化之,只顾自家言说的逻辑自洽或自成一体而不顾所摘取文献的原有语境,就会非常麻烦。这个问题还表现在不顾中西之别,把胡塞尔等人的主张或概念拉来比附于中国传统思想,再加以个人的主观性发挥,统统融汇入自己罗织的理论体系。比如王夫之的这段话:“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5]叶朗先生说“如所存而显之”“很有现象学的味道”。这是很笼统的说法。现象学作为一个流派,不仅有胡塞尔,还有舍勒、海德格尔、英伽登、杜夫海纳,每一个都有其独立的言说,甚至单就胡塞尔而言,他前后的言说也有变化。倘若不顾及言说的个体性特征,叶朗先生的那种笼统讲法当然也说得通,但只要思考深入就能发现问题所在。比如王夫之这段话的“两间”,其作为前提已经界划出“心目之所及”(感官的相关项)与“文情赴之”(主观的相关项)的区别,所以作为王夫之而言,“间”是预先存在的基础。再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中国这方面的专家倪梁康曾有专门注释,但它的言说基础是“先验还原”,是将“生活世界”“转变为一个无兴趣的旁观者的相关项”[6]。对比之下,两者的差异非常之大。王夫之讲的“文情”恰是胡塞尔“先验还原”所要剥离的东西,王夫之讲的诗歌世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妨看一下他所评论的谢庄原诗《北宅秘园》:“夕天霁晚气,轻霞澄暮阴。微风清幽幌,余日照青林。收光渐牖歇,穷园自荒深。绿池翻素景,秋槐响寒音。伊人傥同爱,弦酒共栖寻。”[7]这首诗的情感是在末两句集中体现出来的,而此前的景色描述也暗中传递了消息,比如“幽”“荒”“寒”字眼就富有情感意味。显然,这是一个“文情赴之”的世界。再看看胡塞尔的话:“生活世界是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人们确认它的存在,并不因为某种意图、某个主题,也并不因为某种普遍的目标。”[8]要获得这样的世界,任何兴趣都是不允许的[9]。对此,瑞士现象学家也只是不确定地说:“也许胡塞尔在这里所要求的那种观点已经接近于美学上的无目的性和无兴趣性。”[10]但显然,既然艺术存在着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11],那么这种“无目的性和无兴趣性”就与艺术世界并不吻合。而若从海德格尔的立场讲,他讲得更多的是“周围世界”,即“日常此在最切近的世界”[12],这样的“日常在世”不仅谈不上“充满诗意”,相反,它是“沉沦”的世界[12]246。
由上可知,叶朗先生对于原有文献材料的理解是不遵从作者本义的,甚至仅凭个人的理解而想当然。因此,必须呼吁“个体性话语意识”的到场,否则,那种“群言性”的言说方式将会扭曲众多的言说者的话语,敉平古今理论家的独有立场而变成貌似逻辑一贯的话语部件。陈寅恪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3]其流弊所及,就可能导致一种“语言腐败”,因为它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理论需要,“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14]。提倡“个体性话语意识”,也有治疗“语病”的意图。我们的理论界,尤其美学界,许多混乱是由于话语的混杂、概念的任性造成的,这种语言的“病症”是亟须引起治疗的注意的。李泽厚说:“像澄清语言这样的工作,到今天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文章经常概念不清楚,在论述中自相矛盾,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追问。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澄清语言,缺乏语言的洗礼所致。”[15]
二、西方理论运用的批判性缺失与中国本有特色遮蔽
如何对待西方理论的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了当今学界的重视。一方面,随着“中国话语意识”的自觉自信,有的人开始排斥否定西方理论,体现了文化自闭的倾向。这诚然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很多学者步趋于西方理论的新潮,对于其中的弊端缺乏必要的辨识与批判。这也是需要指正的。叶朗先生的“美在意象”的理论探索,就既有积极借鉴西方理论的可取之处,亦有批判不足而遮蔽了中国自家特色的地方。
拿西方现象学来说,它对于中国美学界俨然是一门显学。叶朗先生对此也是大量引述的。但现象学毕竟是西方的理论,它的很多论述与主张未必就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现象学从根本上是注重于“显”的,由此产生的弊端就是“光的暴力”[16]。其实,西方哲学一直有看重“光”的传统,从柏拉图著名的“洞喻”,一直到海德格尔,都有关于“光”的论述。现象学实质上就是“显现学”,是侧重于讲“显现”“敞开”的。海德格尔在阐释赫拉克利特思想时,就强调他是“光明者”:“因为他试图把光亮召唤入思想语言之中,由此来道说光亮……我们把它的照亮称为澄明(Lichtung)。这种澄明的内涵,它的发生方式和发生之所,还是有待思索的。‘Licht’一词意味着:闪耀、闪烁、发亮。光亮允诺闪现,把闪现开放出来,使之进入一种显现。”[17]
但是,倘若考察中国传统,就会发现古人在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8]的同时,更有注重于“密”“微”“隐”的传统。比如《周易》早就有“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的思想。就儒家来说,他们更强调“微”,比如“未发之中”[19]的那种“隐微之地”[20]。就道家来说,“隐”更是其鲜明的立场,所谓“道隐无名”(《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就是认为“不可见”更重要。所以,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有意地寻求“微”“隐”而不是“显现”是异于西方文化的非常突出的特点。
回过头来,再看叶朗先生的论述,就能看出其受西方理论的引导(一定程度上是误导)而产生的理论问题。叶朗先生多次强调“照亮”[1]73,77-78就是受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等人的影响。海德格尔强调:“自由的本质简言之,就是明亮的目光:让自己先行上升到某种光中,并将自己约束在光中……”[21]杜夫海纳强调:“审美对象不是别的,只是灿烂的感性。”[22]这都是从西方文化主流讲的,实质上都是“在场形而上学”的产物,本质上都是强调“人”的在场,强调“意识”的在场,换言之,都是把对象置于“目光”的暴力之下。而中国传统一向对于“我”的在场保持警惕,特别是老庄哲学,总是强调“无我”而主张“隐”。
倘若我们从“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对立关系来看问题,那么,西方文化更注重于“可见性”的探求。这方面黑格尔也不例外,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应当把最好的东西隐藏在内心里,而是应当促使它突破封锁,走向光明。”[23]可见,诉诸“光明”的朗照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与“光明”对照的是“幽暗”,中国文化特别是老子哲学具有突出的注重“幽暗”的趋向。《道德经》第一章就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的本质就是“幽暗”。苏辙《老子解》说:“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24]由此可知,“玄”就是“黑暗”,正与“光明”对立。老子更强调的是人的缺席与意识的黜落:“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道德经》第十四章)“不可致诘”就是光芒照不到的地方,就是人到不了场的情况,就是拒绝人的意识穿越的存在。所以,相比于通常的强调“象”,老子却强调“无物之象”“大象无形”,原因就是超越于这种“显现”“敞开”“光明”,而偏要去呵护着“隐藏”“遮蔽”“幽暗”。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为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相比而言,西方人性格开放外露,中国人多内敛含蓄。从《论语》的时代,中国人的理想性格就是“刚毅木讷”类型的,是不张扬而可以低调的。这种“内向型”的民族性格被梁漱溟概括为“向里用力”而区别于西方人的“向外用力”[25]。由此而带来迥异于西方艺术的艺术精神。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形式追求,一言以蔽之,就是“隐”。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曲”的强调正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重含蓄蕴藉的自觉意识。与之相对比,《文心雕龙·定势》则说:“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中国艺术的这种特点在中国画方面表现得很突出。首先,与西方绘画相比,中国传统人物画几乎没有裸体的,这是重“显”与重“隐”的最直观的反映。其次,作为最诉诸视觉的艺术,中国画偏偏不大在乎“形”的刻画,所以写意画是主流。中国画的基底不能“有形”而是“无形”,其艺术本体是“不可见”“无定形”[26]。中国诗作为中国文化性格的艺术结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远比西方诗歌含蓄蕴藉。中国传统诗歌,“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中国传统显得调门很高的,很热烈浪漫的,若与西方诗歌比较,就显得低调平和。而照中国传统艺术评价标准,“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27]。
由上可知,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在哲学上,西方是“光”的追求为主导的,中国则是“玄”“隐”为主导的。在艺术上,中国诗与画都迥异于西方艺术,表现为重“暗示”“含蓄”的特点。中国艺术喜欢追求“远”,强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而相比之下,西方艺术常常置于眉睫之前,是追求“近”的逼真的。因此,叶朗先生大量引述西方现象学家的艺术主张,却还要结合中国传统来谈问题,就显得龃龉不合。这就表明,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时,一定要有所辨识,更要有所批判。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西间的巨大差异。叶朗先生曾引述海德格尔论凡·高油画《农妇的鞋》的文字来阐释自己的主张[1]60-61。海德格尔的文字是围绕着“劳作”“辛苦”展开的。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讲,从艺术主流讲,中国更侧重于“闲”的意趣,更注重于对于“劳苦”的淡化。中国学者面对着这样的油画会怎样想的呢?请看郑湧先生的质疑:“在这里,海德格尔展示的是农妇在田间的劳作和生活。然而,凡·高这幅油画中的‘鞋’,明明是解开了鞋带的,静静地摆放在那里的,没有穿着的。这恰恰是说明:此时农妇没有在田间干活……为什么不从‘不工作’、休闲的状态、角度去解读这双鞋呢?”[28]郑先生的质疑是可贵的,且不说其是否在理,至少体现了中国人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三、感性的片面强调与盲目排斥“主客二分”模式的误区
叶朗先生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突出了“感性”“显现”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并不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有陷入于非理性主义的危险。
讲“意象”,一定不能单纯地偏于“象”而片面地强调感性。在汉语语境中,“意象”作为合成词,“意”这一端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乃至于说,就“意象”一词而言,“意”具有对于“象”的统摄作用。如果说,“象”侧重于感性的一面,那么,“意”就侧重于对于感性的理性照管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叶朗先生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过多地强调了感性、直觉性,就有滑入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尽管他也提及理性成分,但毕竟只是“包含有理性的成分”[1]148罢了。
中国古典艺术向来不是纯任感性的,相反,它表现出强烈的“尚意”“传神”倾向。就拿老子的思想来说,“象”从来不是最高的存在,而以“无物之象”超越这种纯任感性冲动的势力。所以,受此影响,中国传统诗论更强调的是“象外之象”,是对于“象”的超越。因为,倘若过度地追求“象”,就陷入“形”“迹”的拘泥,就不够空灵而导致粘皮带骨。在这方面,明代王廷相的主张就是典型代表,其《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说:“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也……嗟乎,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29]所谓“意象透莹”,就如同陆时雍强调“实际内欲其意象玲珑,虚涵中欲其神色毕著”[30],不要过于直接,而要超越意表,而强调“邈焉深矣”,强调“虚涵”,都是这种超越于直观感性的艺术追求。基于此,传统绘画艺术实践有意地避免过于“实”,而向着“虚”发展,追求“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对照画家潘天寿的示例,可知中国画不仅难言如西方画那样的“灿烂感性”,反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抽象性,可谓“虚涵中欲其神色毕著”的具体实践[31]。
比较一下中西诗歌,就会发现中国传统诗歌很少西方诗歌那样的感性逼真的描写,突出表现为中国古诗很少限定词,形容词、修饰词都极为节省。中国古代艺术强调的是“气韵生动”而不是逼真形似,所以陶渊明被推崇备至。陶渊明的诗是纯以神韵取胜,他的诗歌与西方诗歌相比,甚至常常很抽象,因为他很少那种直接物象的刻画与雕琢。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底是什么样的“菊”?什么样的“南山”?其中有“灿烂的感性”吗?有西方油画般的感性呈现吗?但是,中国人就觉得它“妙”!古人不是不注意感性,但是却认为它不是最高境界。陆时雍说:“庾肩吾张正见,其诗觉声色臭味俱备。诗之佳者,在声色臭味之俱备,庾张是也。诗之妙者,在声色臭味之俱无,陶渊明是也。”[30]10653显然,这里的高下抑扬的态度是鲜明的,陶渊明诗歌的“妙”就在于“声色臭味之俱无”,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并不是以感性显现为主的。因此,所谓“灿烂的感性”并不是中国传统艺术创造的至高境界。
西方现象学,尤其是萨特、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都带有非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尽管在救治理性主义的弊端方面有一定贡献,但其弊端乃至于更大。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思潮有其历史土壤,反映了包括现代艺术在内的现代人“精神上的贫困”[32]。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所以现代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才诉诸感性的刺激。从艺术的整体而言,强调感性、直观,等等,也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一旦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则这种矛盾就暴露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强调精神的充实自足而有意地避免感性的刺激的。恰恰是叶朗先生以及其他美学研究者又寄希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获得与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契合或理论共性,这事实上是南辕北辙的。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了解不深的,包括海德格尔本人,他对于老子《道德经》的理解也是粗暴的,采取西方哲学的思路而多误解的,这方面已经引起有关学者的重视[33]。
就中国当代的理论实际需要而言,西方非理性主义或所谓感性的强调既是值得吸取的营养,但也要警惕其中的破坏性作用,这方面本来已经有卢卡奇做过尖锐的批判[34],尽管其论述不乏争议性。我总以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是理论体系的营构而不是理论体系的解构。我们必须先要造好了一幢幢现代化的理论大厦,然后才有破坏、颠覆、解构的奢侈。从这样的思考出发,我们当前最需要的反而是理性主义的东西。事实证明,理性主义才是更富建设性的精神取向。这里也有必要提到黑格尔。黑格尔是理性主义的代表,近年来可能是理论的“死狗”,乃至于是备受批判的“主客二分”模式的代表。但是,我认为,黑格尔仍是中国当代理论体系建构实践过程的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许多中国学者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的思想,比如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人,但是,杨大春教授指出:“对于当代法国哲学而言,黑格尔始终如影随形,是无法轻易摆脱的。”[35]像上述这些思想家,无一能够绕过黑格尔。
甚至于说,“主客二分”模式也不是叶朗先生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简单而仍有大量的可值得发扬的东西。在这方面,张世英先生是有反省与修正的。他说:“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传统,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是‘主客二分’,强调人的‘个体性’、‘主体性’。中西对比来看,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首要的是重‘合一’,重‘一体’,这里所蕴含的和谐高远的精神境界,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但它也带来了一些缺点,就是过分强调‘合一’,不重区分,于是忽视了每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性,忽视了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性。人的个体性被湮没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群体之中,缺乏自我的独立性;人的主体性被湮没于与自然合一的‘一体’之中,自然科学不发达。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而欠缺了科学与民主两个重要环节……我一再强调要中西结合,就是说在中国‘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主体性、个体性思想,把西方追求自我的自由思想吸纳进来,建构成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或者新的‘万物一体’的更高级的文化形态,我称之为‘万有相通’。”[36]遗憾的是,叶朗先生的《美学原理》仍局限于引述张世英先生的较早时期的思想观点,片面地高举“天人合一”模式,而排斥“主客二分”模式,过于突出了两者的对立关系,而不能像近年张世英先生的思想发展的那样,开始强调两者的兼容性。
倘若我们暂时不谈理论,而只需凭常识回顾一下西方的审美创造历史,就可知正是在“主客二分”模式的主导下,西方创造了辉煌的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单就文学艺术而言,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文学就杰作迭出,异彩纷呈,涌现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席勒、海涅、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系列光辉灿烂的世界级大师。就拿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些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来说,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拜“主客二分”模式所赐。既然在“主客二分”模式下,西方文明取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而且其成就远远超越同时期其他文明模式,这不反而证明了这种模式的优越之处吗?再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可知令当时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恰恰就是“主客二分”模式下的主体觉醒与精神反抗的特质。鲁迅《文化偏至论》赞之为:“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37]鲁迅《摩罗诗力说》更是专选富于反抗精神、主体性张扬之士:“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37]68由鲁迅的“争天拒俗”之语,即可知其心目中所激赏的恰恰是“主客二分”模式下的主体抗争精神,再结合鲁迅对于“平和”的拒斥,则可知其所批判的正是传统“天人合一”模式下的消解主体性而泯灭抗争性的安于现状的态度。而对于盲目鼓吹“天人合一”为民族特色的观点,何兆武先生质疑说:“天人合一曾被有些学者认同为中国哲学的特征。但古今中外又有哪一家哲学不是以指向天人合一为自己的归宿的呢?甚至于不妨说,凡是不归本于天人合一的,就不是哲学。所以天人合一并不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哲学家的特征。它是一切哲学家的本质和鹄的,问题只在于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论证。”[38]
质言之,“天人合一”模式重人与现实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心性是平静的、和顺的、温润的,其艺术至境如尼采《悲剧的诞生》所谓日神阿波罗;而反之,“主客二分”模式重人与现实的对抗、人与自然的分裂,其心性是激烈的、抗争的、刚毅的,其艺术至境如尼采所谓酒神狄奥尼索斯。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短,本是互补的关系,而不应该搞是此非彼的矛盾对立。再回顾一下鲁迅与朱光潜之间的围绕着“静穆”展开的论争[39],亦可从中西之间的不同民族性格、美学性格的差异来理解。所谓“静穆”,正是鲁迅批判过的“平和”,这与鲁迅所推崇的“摩罗诗力”是相互冲突而又可以彼此兼容的人格范式与美学范式。因此,对待“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之间的思维模式差异,以及由之产生的人格范式、美学范式差异,应采取笔者的“异在论”立场,在“求异”基础上“承认不同的他者之间的共在共聚”[40],而不是以此代彼。
就中国当代实际而言,我们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许多现代性的优长仍是需要积极学习吸收并整合发展的。连哈贝马斯都还在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41]。因此,不应该亦步亦趋于西方后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潮流,对于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列维纳斯、德里达、巴塔耶等思想家的立场观点也应该有所甄别乃至于严肃批判。像张世英先生就能反省自己过去强调“天人合一”的偏颇而重讲“主客二分”模式的优点[42],这种敢于自我批判的大家风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值得那些还在片面地把“天人合一”模式与“主客二分”模式相对立的学人反思的。倘若吸收“主客二分”模式的长处,就要吸收西方理性主义的长处,就要克服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弊端。而这方面,又是与片面地鼓吹感性相矛盾的。所以,我们既然讲弘扬传统文化,就应该同时弘扬传统文化中对于感性刺激的警惕与超越的思想。具体到“意象”这个概念,就应该重视“意”这个语素与中国传统重神韵、重写意的内在联系,就应该重视对于“象”的超越,就应该强调“超以象外”的方面。
总之,本文以叶朗先生的“美在意象”的理论探索为例,一方面肯定叶朗先生的理论努力及其价值,但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要指出问题,进而从当代美学研究的整体着眼,来揭示其中值得注意的弊端。这些弊端,是值得当代美学研究者引起高度重视并尽力规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