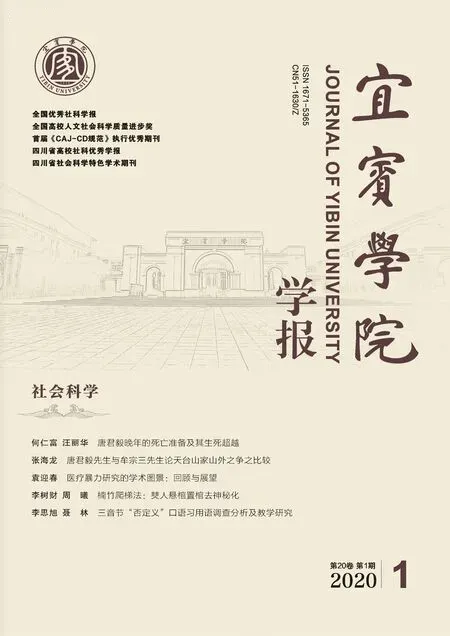论双重效果原则解释道德直觉的可能性
2020-02-23康腾岳
康腾岳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00)
20世纪60年代,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论已经在西方激烈展开,这项议题不仅是哲学上的论辩,还牵涉到宗教、政治领域堕胎与反堕胎团体的战争,与性解放与女权运动交织在一起,1973年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①的判决进一步激起了一些政治团体特别是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让关于堕胎的论辩进入白热化阶段。在传统堕胎争论中,人们主要诉诸“权利”问题来为堕胎或反堕胎辩护(即使罗纳德·德沃金后来认为这不是传统主义者的核心立场所在,从深层次来看,生命的神圣性与尊严才是双方的基本出发点,这里姑且不论②),在这一框架下,除了对胎儿是否是一个人以及是否具有“生命权”的争议之外,最值得研究的是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对堕胎行为的区别对待,例如:如果胎儿的存在危及母亲的性命,那么为拯救母亲生命的堕胎毫无疑问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堕胎仅仅是出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如出国旅行或者保持身材),那么堕胎无异于谋杀。而教条双重影响(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也称为双重效果影响,以下简称DDE)对解释这一问题有着强烈的直觉上的吸引力,它通过区分故意为之(intend)的伤害和预见(foresee)却不希望发生的伤害之间的区别,认为在为了拯救母亲的性命而堕胎的情况中,我们当然预见到了胎儿的死亡,但是这一结果属于一种令人遗憾的副作用(side effect),而不是有意以胎儿的死亡作为最终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两种不同情况的行为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也是我们对其持不同立场的原因。
这仅仅是教条双重影响的其中一个运用,这一原则的直觉吸引力还体现在著名的电车难题、临终关怀等问题中,这些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在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道德评判的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直觉是耐人寻味的,一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社会学家都对如何解释我们的道德直觉之由来贡献了不同的智慧。
一、故意与预见——双重效果原则的核心标准
教条双重影响的提出最初与自卫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探讨自卫的可允许性时认为,如果某人不是有意要杀害攻击者,而是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那么这种杀害就是正当的。阿奎那反对奥古斯丁的杀害他人是不允许的观点,认为一种行为一定会产生两种效果,其中只有一种是行为主体有意为之的,而另一种则是与行为者意图无关的副作用。从自卫问题来看,阿奎那认为自卫行为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另一种是杀害了攻击者。自我防卫的正当性之所以能够得到辩护,是因为其目的不是有意杀害他人,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所以因自卫而杀害的行为是允许的。[1]226-227阿奎那的讨论已经基本明确了应用DDE判断行为许可性的核心原则——区分故意与预见却不希望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区别,并且明确提出禁止以杀害他人为目的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新天主教百科全书为DDE的应用提供了更加全面且明确的条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就可以运用DDE来解释行为意图:
1.行为本身必须是道德上善的或者至少是道德上中立的。
2.行为主体可能不会主动追求坏的效果发生,但是也会默认允许它产生。如果能毫无坏的副作用而获得好的结果,那么这种方案是更可取的。坏的影响有时被认为是间接自愿的。
3.善的效果必须像坏的效果一样立即从行动中产生(按照因果关系的顺序,但不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亦即好的效果必须直接由行动产生,而不能从坏的效果中得出。否则,行为主体将利用不好的手段来达到善的目的,这是该原则所不允许的。
4.善的效果必须足够补偿所产生的负面效果。[2]1020-1022
基于以上四个条件,Joseph Mangan在《双重效果原则的历史性分析》(AnHistoricalAnalysisofthePrincipleofDoubleEffect)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今天更通用的(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基本框架:
1.行为本身及其作用对象必须是善的,或者至少是中立的。
2.善的效果是行为主体的意图,而不是坏的效果。
3.善的效果不是通过以恶的效果为手段而产生。
4.存在一个相应的重大理由而允许恶的效果产生。
5.行为人努力将可预见的损害降到最低。[3]43
在两种解释中,第四个条件被称为是比例条件,这一条件是决定行为可容许性的关键,它使得遗憾造成伤害的行为主体会倾向于避免造成伤害或尽量减少造成伤害的程度。
从根本上来说,故意造成的伤害与仅仅预见到同时作为副作用而产生的伤害之间的区别是应用双重效果的核心。一直以来,天主教将这一原则作为反对堕胎的有力武器,而在哲学、法律、战争以及医疗等问题中该原则同样应用广泛。那么,这一原则是否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我们道德直觉的困惑呢?或者说这一原则是否足够强有力地独自面对不同情境下判断行为可允许性所带来的困难?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即《堕胎问题与教条双重影响》(TheProblemofAbortionandtheDoctrineoftheDoubleEffect),在这篇极富洞察力的文章中,福特不仅直面了堕胎问题在道德哲学层面的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是真正意义上推动了电车学的问世[4]。虽然福特并不支持运用DDE原则来解释堕胎问题,但是她依然承认DDE可以作为解释我们道德直觉的可能性原则,而且通过设计电车问题的思想实验来充分证明其可行性。[5]35-36直至今天对于电车难题的讨论依然在继续,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讨中,电车难题也不断升级,不仅环节更加曲折,而且场景也更加复杂化,学者不断从道德哲学、实验哲学乃至神经科学领域对置身于其中的行为主体的道德直觉及其对于行为可允许性的道德判断之根源进行探讨。让我们回到福特所提出的电车难题中,试举几例。
二、电车难题——环轨场景的悖论
在《堕胎问题与教条双重影响》中,福特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某人驾驶着一辆失控的电车,当前轨道上有五个人在工作,他只能从这条狭窄的轨道上转向另一条,而另一条轨道上有一个人正在工作;无论他怎样转向,都有人注定要被撞死。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说,驾驶员应该把电车转向只有一个人的轨道上。而在另外一种情景中,我们要将某种紧缺药物给几个需要它来挽救生命的病人,其中一个病人需要一剂大剂量的药物,而另外五个病人每人只需要这一剂量的五分之一就可以活命。我们会很遗憾地说,我们不能把药物只供应给那一个病人。如果我们只有唯一选择,应该选择让一个人付出生命而不是许多人。但是在另外一个例子中,设想有五个身患重病的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经检查有一个健康的人血型完全匹配,外科大夫是否有权力将其杀死,用他的器官拯救那五个人的生命呢?无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为了拯救五个病人而放弃给予那一个病人药物,却不能为了拯救五个濒死之人杀死一个健康的人呢?福特认为DDE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根据这一原则的观点,在岔道电车的场景中,我们不是有意(intend)要杀死另一个条轨道的那个人,也不是将蓄意谋害一个人作为拯救其他五个人的手段,只是预见(foresee)到了他的死亡,但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我们也不会将他撞死,甚至如果轨道上的那个人能够临时想起别的方法逃脱,我们会为之感到庆幸;在第二个例子中也是如此,那一个病人的死不是我们所乐见的结果,也不是我们有意为之,而是为了拯救其他五个病人所带来的坏的副作用;但是恰恰相反,在最后一个例子中,我们却蓄意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将其作为目的甚至作为带到拯救另外五个人生命的手段,这是不被允许的。
可见,只要满足DDE的几个基本条件:1.为了达到一个善的目的;2.坏的效果是作为预见到的副作用而遗憾发生的,不是行为主体所追求的目的;3.努力尽可能避免或降低坏的效果的危害。虽然福特没有利用DDE来解释这些场景,但是她似乎确实承认DDE能够为我们的道德直觉提供这样一种解释。然而福特没有预见到电车问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一问题更戏剧化的场景中,DDE似乎也无能为力。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姆逊的两篇关于电车问题的文章(Killing,LettingDieandtheTrolleyProblem和TheTrolleyProblem)[6][7]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电车难题的影响范围,更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入新的层次。汤姆逊设想了如下场景:某人站在铁轨上方的天桥上,一辆失控的电车驶来,前面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如果电车不受控制就会撞向这五个无辜的人;此时天桥上站着一个胖子,体重足以阻止电车前进,只要这个人伸手将胖子推下天桥,就可以使被绑的五个人免遭横祸,天桥上的人可以选择这样做吗?毫无疑问是不允许的,DDE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们将胖子推下去的时候,是有意将其作为达到目的(即逼停列车)的手段,因此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但有趣的并不是场景的转换,而是汤姆逊的理由,她并没有用DDE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是诉诸其一贯的“权利”概念,认为将胖子推下去侵犯了胖子的个人权利。究其原因,还需要探讨她基于此设计的另一个“环轨场景”: 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电车向五个人驶来,这五个人体型都非常瘦并且被绑在铁轨上,如果电车撞上这五个人,他们一定会死,但是也会让电车停下来。你站在轨道外,可以扳动把手将电车引上另一条环形轨道,而一个胖子被绑在这条轨道上,他的阻力足以逼停电车。最重要的是如果环轨上的胖子逃跑了,列车也不会停止,还是会撞死那五个人。汤姆逊认为,如果在岔道情景中我们接受撞向那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的选择,那么在环轨情景中同样如此,我们同样应该同意将电车引上环轨。教条双重影响在愈加复杂的情境下似乎失去了效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杀死胖子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以达到逼停电车拯救另外五个人的目的,甚至并不希望他逃脱这场灾难。
对DDE的探讨当然远不止于此,本文以堕胎问题与电车难题为切入,但是其后的探讨会更进一步,目的是试图通过阐释DDE的具体内容,探究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们的道德直觉,该原则强大的直觉吸引力来自怎样的原则基础。
三、教条双重影响的局限性
随着思想实验和现实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DDE对于道德直觉的解释无疑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即使在很多常见例子中,也存在对该原则有效性的广泛质疑。可见DDE原则不能统一适用于解释所有非故意伤害案例中的道德直觉。因此需要反思故意与预见作为核心原则的可靠性,以及双重效果原则对于道德直觉解释的局限性。
(一)故意与预见的区别何在
如前所述,支持双重效果原则的人强调的是行为主体的意图与动机在决定行为可允许性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区分有意为之与仅仅预见到的结果之间的区别就成为双重效果原则的核心。但是这一点不仅被结果主义者反对,甚至也受到了非结果主义的诘难。首先,结果主义对道德行为的评判取决于行为后果总体的道德价值,所以行为者故意或预见的意图区别根本不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但是本文认为,非结果主义者对双重效果原则所提出的质疑才是该原则需要反思的核心所在。许多批判质疑两种结果——有意作为行为者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一部分与仅预见到作为行为者手段的副作用(side effect)——是否真的能够被区分清楚,尤其是在这两种结果都不是行为者所乐见的情况下,判断有意和预见或者手段和副作用之间的区别就更为困难,但是双重效果原则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区分方法和界限。这就导致对双重效果原则的运用出现与我们道德直觉不相符合的情况。例如,该原则认为对怀孕妇女实行子宫切除术是允许的,而为了拯救母亲的生命进行堕胎则是不允许的,因为杀死胎儿成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的一部分。同样战场上为了掩护战友而自我牺牲的行为对该原则来说也是不可行的,这一点经常为反对者所诟病。有学者提出需要尽可能严格地解释行为主体的意图,许多双重效果原则的支持者也为此做出过努力。例如,Warren Quinn就对该原则做出过修改,提议用直接行为替代有意作为手段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用间接行为替代预见到而遗憾产生的副作用的行为。他认为直接行为是指行为者有意将受害者牵涉进行为过程中,作为进一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间接行为指的是伤害性行为并不是有意为受害者设计的,或者行为者的意图并不是造成这种伤害。Quinn认为直接行为与间接行为并不一定和故意与预见完全吻合,这无疑拓宽了造成有意伤害的结果的种类,因此战士通过自我牺牲而掩护战友的行为就是完全允许的。[8][9]
但是本文认为这种努力并不足以弥补双重效果原则的缺陷,无论是直接行为与间接行为,还是故意与预见的结果之间的区别,首先二者都不能从逻辑上说明为什么将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作为手段以达到目的就是不允许的;其次面对以死亡作为达到善的目的的手段的情况,双重效果原则无法给出清晰的说明。Quinn的努力尽管扩大了有意的结果的范围,但某种程度上却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由于双重效果原则界限的模糊导致其应用范围的有限,即使在如此有限的范围内(例如上述提到的堕胎和自我牺牲的行为),该原则对于道德直觉的解释也是含混不清而且备受争议的。
(二)DDE作为独立原则何以可能
双重效果原则经常被应用来对行为者的行为意图做出判断, 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对某一行为的意图做出可容许性判断的过程中,是否只有双重效果原则在独立发挥作用?事实并非如此,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行为意图的判断会受到独立的道德考虑的影响,这里我们需要援引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这一过程,即诺布效应,也称为副作用效应(Knobe effect或side-effect effect)。这一效应由实验哲学家约书亚·诺布(Joshua Kobe)提出, 他设计了如下实验,并将实验中的两个被试场景分别称为伤害条件和有利条件:
伤害条件:公司副主席向董事会主席提议说:“我们正试图开展一项新计划。该计划有助于公司提升效益,但是也会破坏环境。”董事会主席说:“我一点也不在乎是否会损害环境,只想提升效益,就开展这项计划吧。”公司按照计划开展了新项目,果不其然,环境也受到了破坏。
有利条件:公司副主席向董事会主席提议说:“我们正试图开展一项新计划。该计划有助于提升公司效益,而且它也会改善环境。”董事会主席说:“我一点也不在乎是否会改善环境,只想提升效益,就开展这项计划吧。”公司按照计划开展了新项目,果不其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在实验中,公司提升效益是主要目的,而对环境造成影响属于副作用。实验要求被试判断董事会主席是否有意导致副作用产生,即是否有意破坏或改善环境。实验结果表明伤害条件下有82%的被试认为董事会主席有意破坏环境,但在有利条件下77%的被试认为董事会主席不是有意要改善环境。这个实验似乎说明对副作用的道德判断会影响我们对行为者意图的判断。当副作用被认为是道德上善的时候,人们倾向于认为行为者并不是有意导致其发生;当副作用是道德上不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认为行为者有意导致其发生。诺布效应有多种理论解释,例如道德效价论、心理偏见论以及权衡假设等等,也存在对这一实验结果的多重争议。[10]218-240但是本文认为,诺布效应确实指示了在道德判断和行为意图判断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这种关联会影响我们的道德直觉对行为意图可容许性的判断。道德直觉的生成机制同样是复杂多变的,因此简单的DDE原则并不能完全独立解释这种道德直觉的生成原因,其作为基础的故意与预见之间的区别也会受到其他主观的、独立的道德考虑的制约。对于双重效果原则所强调的区别是否适合作为评价道德判断的中立性基础,同样也是值得反思的核心问题。
(三)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与权宜之计的隐忧
电影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军事情报官员鲍威尔奉命远程指导捣毁肯尼亚内罗毕境内一个恐怖分子的窝点,据无人机探测显示这个恐怖组织将进行一项自杀性的恐怖袭击,但是在执行射杀任务时,一名9岁的小女孩以外闯入了射程范围,鲍威尔、律师以及政府官员对是否继续执行任务有着强烈的分歧:如果继续执行任务,小女孩一定会无辜丧命;如果为了这一条生命而停止射击,那么恐怖袭击将会使更多人丧命。这部电影将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以及在哲学上探讨的两难困境生动展现在了大荧幕上。历史上的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将两枚原子弹投放到日本的广岛、长崎,杜鲁门本人解释是为了促使日本投降从而早日结束战争,事实上一周之内日本也宣布了投降,但是战后对于使用原子弹的争议一直存在,这两枚原子弹当时造成了150 000~245 000人死亡;可是如果不使用原子弹,以日军的疯狂战争将会持续多长时间、造成多少伤亡也是未知的。之所以探讨这两个事例,是因为事实上DDE原则通常被应用在恐怖袭击与战略性打击的对比的例子中。按照该原则的看法,人们普遍承认恐怖袭击的行为是不允许的,而军事战略打击虽然会伤害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决策者所乐见的,而且行为直接的意图是要打击敌人,伤害平民只是不幸产生的副作用。在电影《天空之眼》中,指挥官所有的努力宣告失败后,毅然下令继续发射,电影的最后人们对小女孩的死都表示遗憾与惋惜。DDE似乎可以完美解释这一行为的可允许性,但是让我们回到行为本身,思考两个实质性问题。
首先,在做出军事决策的过程中,军事战略专家有多少义务避免对平民造成伤害?这是基于战争当下的境况以及限制军事决策的各项公约(如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共同决定的,这些考虑远超双重效果原则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仅仅依靠双重效果原则并不能为轰炸的可允许性提供足够的条件。
其次,双重效果原则对于道德直觉的解释,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规范性准则决定我们具体判断的内容。双重效果原则的解释有强大的直觉吸引力,但是反过来看,有人认为双重效果原则的这种直觉吸引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错觉。就从对于电车难题的直觉反应来看,有些人并不认同双重效果原则的解释,而是从道德直觉本身出发,认为如果人们普遍不愿意将某人推到轨道上以阻止电车来拯救五个人,这种想法本就不理性,而有人会认为旁观者转换电车方向仅是因为反思不充分或情感参与不足的原因(贾维斯就这样认为)。双重效果原则基于对行为者意图的判断而做出决定,但是却忽略了道德直觉及受其影响的行为意图本身或许是有缺陷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双重效果原则也存在一种隐忧,即它看似合理的解释可能被当作行恶事的效果,而这还是因为,即使某种行为满足了:追求善的目的,带来令人遗憾的坏的副作用,副作用不是达到善的目的的手段,同时已经努力把坏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它仍然没能说明为什么这种行为就是允许的。如果在逻辑上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无论双重效果原则改进得多么完美,都不能确定我们所做决定的具体内容,也不能为这些决定的可允许性做出道德判断。
结语
总而言之,教条双重影响或双重效果原则作为对道德直觉的一种解释是有其合理性的,它强大的直觉吸引力来自其对行为者意图的关注,它看到人们道德直觉中自主性和非自主性的一面。但是本文认为,这种解释仍然是片面和绝对的,它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该原则并没有明确故意与预见二者之间的界限,就将这一区别作为理论的核心,它虽然极力简化判断依据,力求简单明了地准确解释道德直觉,但事与愿违,反而产生了诸多更为复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我们针对行为者意图的评判并不完全基于双重效果原则,还掺杂着许多有关道德判断的独立考虑,这无疑限制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最后,在更复杂的现实境况中,很多考虑远超双重效果原则的范围,如果忽略对道德直觉形成机制的客观分析,不解决行为意图区分与可容许行判断之间的逻辑困难,而将该原则一概运用于这些实例中,也极有可能导致它成为一种作恶的借口。因此本文认为,双重效果原则在诸多讨论中可能提供了一种道德直觉的解释框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行为者意图与决定的某种道德约束,但是并不能作为我们所做决定之确切内容的规范性准则或判断依据。
注 释:
①1969年,一位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德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战。该法令规定,除非因为维护孕妇的生命,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手术。罗伊主张: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剥夺了她在妊娠中的选择权,因为她既无钱到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又不能终止妊娠,所以,分娩之后不得不将孩子交给了不知身份的人收养。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使得她无法自主地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为何种理由而终止妊娠。被告德州政府在诉讼中辩称:生命始于受孕而存续于整个妊娠期间,所以,怀孕妇女在整个妊娠过程中,都存在着保护胎儿生命这一国家利益。宪法中所称的“人”包括胎儿在内,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禁止的行为之列。该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见裁定,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孕妇在妊娠过程中的选择权,侵犯了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构成违宪。
②参阅美国罗纳德·M·德沃金著,郭贞伶、陈汝安译《生命的自主权——堕胎、安乐死和个人自由的论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