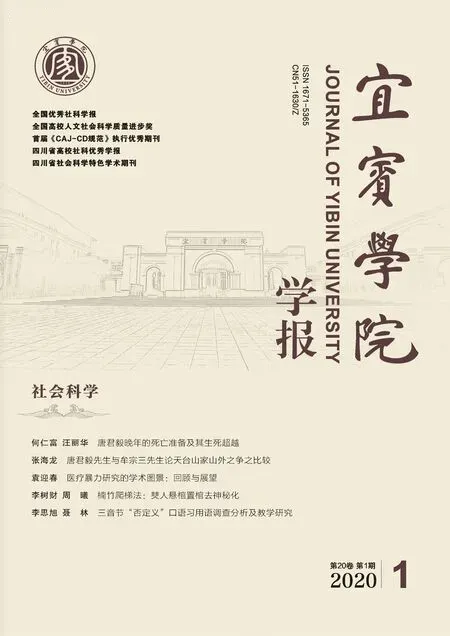唐君毅晚年的死亡准备及其生死超越
——唐君毅的生命体验及其哲学建构(之三)
2020-02-23何仁富汪丽华
何仁富,汪丽华
(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18)
吾之为哲学,亦初唯依吾之生命所真实感到之问题。而此中之问题,亦正多非出于个人一己之私者。
——唐君毅[1]352
吾初感哲学问题,亦初非由读书而得。
——唐君毅[1]353
公元1978年2月2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廿五日,凌晨五时半,现代大儒唐君毅先生因肺癌病逝于香港的家中。依公历计算,唐先生已度过七十寿辰(1月17日),若依农历计算,则唐先生还差一日(12月26日)才满七十岁。
唐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生死体验和终极情怀的思想家,同时,对生死哲学又有自觉而系统的理论建构。这样一位思想家是如何面对和准备自己的死亡呢?或者说,死亡作为一个生命事件,对唐先生晚年的生活与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唐先生作为一位自觉的儒者,他对死亡的准备具有怎样的生命意义?本文以唐先生晚年的日记为基本材料,结合唐先生的生死哲学建构,从生死学维度梳理唐先生作为一位儒者的死亡准备及其生命意义。
一、接受天命:先行到死的生命自觉
说到关于直面绝症与死亡的理论,人们最常提到的便是库伯勒·罗斯的“哀伤五阶段”理论,这一理论甚至成为现代临终关怀的理论标准。按照库布勒·罗斯1969年出版的《死亡与临终》一书中提出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即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对照唐先生从得知罹患癌症到最后去世的经历和日记记载的情绪表达来看,罗斯的这一“哀伤五阶段”理论就显得非常缺乏说服力。因为,唐先生似乎并未经历明显的“否认期”“愤怒期”,也许有内心的挣扎并且如罗斯所描述的“协议期”与“绝望期”的某些情绪反应,但我们从唐先生的生命行为中更为直观地看到的是,他似乎是很快就直接进入了“接受期”:以相对平静的心情去办完要办的事,然后听从命运的安排。
1976年8月,刚经历了香港中文大学改制风波的身心煎熬后,唐先生的身体和心理都感受到了极度的疲惫,咳嗽不止。8月12日,经几位医生诊断,唐先生罹患肺癌。当唐先生意识到自己罹患癌症后,所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立即给台湾学生书局张洪瑜打电话,请其速排《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以便到台湾治病时校对。[2]308-30914日,去慈航净苑拜祖先父母。[3]48417日,到律师楼立遗嘱。22日,唐先生与夫人到台湾治病。此次在台湾的治疗一直到12月5日回香港,前后计106天。但在唐先生的行状中我们看到,他似乎不是来治病,而是来完成书稿校对的。每天除了医生吩咐应做的事外,唐先生即“付出所有时间,亦可以说付出他的生命校对他的书稿。”甚至在频频咳嗽并口吐鲜血的情况下,唐先生依然继续校对书稿,他左手拿着一叠草纸,接着一口一口的鲜血,右手拿着笔杆一心一意校对书稿,还向夫人说,“不要怕,我不觉有什么痛苦,我如不校对书稿,恐以后就无时校对了。”到9月8日,手术前一天,《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已大体校完,完成了唐先生直面死亡威胁时最想完成的伟大工作。唐先生自谓,心愿已了,可以安心治病了。
1977年2月1日,唐先生按照第一阶段治疗的要求到台北荣民医院复查,被医生告知,病情恶化,治愈希望甚微,只有不足三月的生存期,而且痛苦很大。作为一位内心真诚的儒者,唐先生就如他在《病里乾坤》中所强调的一样,在面对“天命”时放下自己的傲慢心,绝不“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自认为“天从吾愿”,也不“怨天尤人”而将自己所得疾病归之于“命运不公”;而是真真切切地接受“天命”,直面现实,“直视骄阳”。唐先生的决定是,一方面要在台湾买一块墓地,另一方面接受学生和朋友的建议在台湾寻求中医保守治疗。唐先生在服用中药后病情趋于稳定,身体状况也得到恢复,便决定回香港。此次赴台治疗时间共84天,至4月25日返回香港。
1978年1月23日,唐先生自罹患癌症后第四次入院治疗,癌细胞已侵入淋巴腺,血液沉淀度数很高,医生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试用抗癌素针,但后果不能预断。唐先生很了解自己的病况,唯有接受医生的办法,听天由命,次日即注射抗癌素针。医生告知唐先生夫人,唐先生病愈的希望甚微,希望夫人应当有所准备。1月26日,感觉到自己身体快被癌症导致的咳嗽、气喘折磨地难以承受,唐先生提出回家休养。
唐先生何以可以这样“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死亡呢?这与他作为一位自觉的生死哲学家对生死、疾病有“先行”的理性思考密切相关,也与他作为一位大儒所坚守的核心信念密切相关。一方面,唐先生是一位非常早慧的思想家,十几岁就开始思考死亡问题,并且将生死问题视为自己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不同阶段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我们在早起的《人生之体验》、中期的《人生之体验续编》、晚期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唐先生的相关思考和理论探讨,甚至对于疾病也有在罹患目疾后的《病里乾坤》中的深入思考与讨论。按照唐先生在《病里乾坤》中的分析,人的生命在时间流逝中,每经历一件事情,就会留下在以后类似情境下再做此事的趋向,这就是“习气”。如果某事被多次重复,则习气就会增加而呈“习惯”,此“习惯”会进一步影响人心当下的判断;这些习气产生的诸多妄念种类不同、方向不同,时有冲突,会导致生命力的分裂,如此生命不能和谐贯通,这就会导致生理的疾病。既然疾病是自我生命的分裂所导致的,那么如何面对疾病或者“养病”呢?唐先生认为,养病当先从事于静功,而此静功当始于求妄念之停息,以拔出习气。唐先生通过自己的体证,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何对治人的慢心处下手。这种不易去除的“轻慢心”的一个主要表现即为,以为事物的变化可以不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而发生自然的按照我的个人意愿的演变,“凡人之自谓我生有命在天,天必不违吾愿,其根源皆在此种慢心”。唐先生强调:“实则人之自谓有命在天,必有天佑,正为人之傲慢心之一种表现。此乃人所未必知,而亦吾之昔所不知。”[4]11强调“天从吾愿”,实际上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卑视天意、天命之广大,是对天或客观世界之一大傲慢。有了这样的“理论准备”,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理解,当唐先生在得知自己病情恶化被宣布“只有三个月”的情境下,将如何面对自己的疾病和可以“看见”的死亡。
对于这样一位已经不断“先行到死中去”的思想家来说,死亡是随时都在与自己“照面”,因此,当真实的死亡到来之时,他不至于因为“不了解”而恐慌、否认、拒绝。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信奉儒家思想与生活的大儒,相信天命,相信鬼神,相信祖宗与自己的生命的内在连接,相信“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大道,因此,他的主要用心是在当下生活中做最该做的事情,时刻为死亡做好准备;同时,因为死亡并非“空无”,而是可以幽冥感通,所以死亡本身并不是生命的消失,而只是生命的暂终,所以并不可怕。
二、为所当为:道德自觉的生命超越
由于唐先生有“先行到死中去”的生命自觉,因此,他将自己的生命全幅用在当下该做的事情上,而不是用在思考和恐惧死亡和疾病本身上,并以此实现了以道德自觉为基础的生命超越,让自己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不留遗憾,任何时候都可以“死而无憾”。
做一个如儒家圣贤一样的真正的人,是唐先生很早就有的志向。他曾自言:“吾年十四五时,即已有为学以希贤希圣之志。”[5]3这样一种“希贤希圣之志”所确立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呢?二十多岁的唐先生在其《柏溪随笔》中这样写到:“一个伟大的人格,任何小事都可以撼动他的全生命。好比一无涯的大海中,一小石落下也可以撼动全海的波涛。一个伟大的人格,任何巨大的刺激,他都可使它平静。好比在一无涯的大海里,纵然是火山的爆裂,也可随著来往的波涛而平静!”[6]111很显然,在唐先生看来,圣贤的人格是真性情的、伟岸高卓的。伟岸高卓的人格是可以大中见小、小中见大、大小圆融、天人合一的。
当然,在“希贤希圣”的人生旅途中,唐先生也有过诸多艰难、困顿。但是,这些艰难困顿没有成为他放弃希贤希圣的理由,恰恰成为他历练自己生命、提升自己人格的动力。为了安顿自己的生命,他将文学、哲学、宗教等各种中西方人文思想作为自己学习、思考、反省的对象,并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试图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人生的理解,由此成就其早年的《人生之路》十部曲,特别是《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两书。在这两本书中,唐先生建构起自己终身坚守的生命意识、生命信仰:一念翻转做当下该做的,过道德的生活。在唐先生看来,只要我们“当下自我一念自觉”,我们便可以由“自然的生活”进入“道德的生活”。因为我们之所以不能进入“道德的生活”,根本原因只在于我们陷溺于“现实的自我”,被我们自己过去所流传下来的盲目势力如本能、冲动、欲望等支配。所以,我们要完成自己的“道德自我”进入“道德的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摆脱本能、冲动、欲望的支配。我们“一念”至此,便当对自己下命令并遵循自己“道德自我”的命令去摆脱它们。这种“道德的生活”无它,就是将人生实践回归到我们自己“心”本身的当下“自觉”上,“自觉”的做我们当下的“心”觉得“该做的”。唐先生强调:“人生之目的,唯在做你所认为该做者,这是指导你生活之最高原理。”[7]27-28
这一“做当下该做的过道德的生活”的最高人生原理,也是指导唐先生“死亡准备”的最根本原理。正因为有这一原理的坚信,所以唐先生可以坦然面对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而唯一可能会让自己不安的,便只是是否做了当下最该做的。因此,当他认为,当下最该做的是保证自己在死亡到来前完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校对,他就不顾疾病带来的剧烈痛苦,一手拿着纸巾擦口吐的鲜血,一手却在校对书稿;当他认为,当下最该做的是完成自己应该给学生的上课,他就可以不顾气喘和咳嗽而照例给学生大声讲课;当他认为,当下最该做的是回家休养静待天命,他就离开医院回家休息、看书和工作。
从被诊断罹患癌症到去世,唐先生总共经历了545天的“死亡准备”时间,期间,先后四次住院计205天。由此,这一阶段唐先生的生命经历被住院和居家分为若干个小阶段:在香港被诊断罹患癌症(1976年8月7日-8月21日,15天)、首次赴台湾检查治疗(1976年6月22日-12月5日,106天)、在香港家中养病(1976年12月6日-1977年1月31日,56天)、再次赴台湾检查治疗(1976年2月1日-4月25日,84天)、在香港的休养与工作(1977年4月26日-12月23日,242天)、癌症复发入香港圣德肋萨医院检查治疗(1977年12月24日-1978年1月1日,7天)、在家治疗与休养(1978年1月1日-19日,19天)、病危入香港浸信会医院检查治疗(1978年1月20日-26日,7天)、临终在家(1978年1月27日-2月2日,7天)。每一个阶段,唐先生都有生活理性化的反思,都竭力做了他自己觉得最该做的事。当他做了所有当下之心告诉他该做的一切事情后,死亡的来临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当下”的生命事件,他完全可以从容接受,并进入下一个生命历程。对唐先生来说,疾病和死亡只是提醒他当下应该做什么事的一个生命事件,而不是超控他生命行为的“重大事件”,他已经完全超越了当下疾病和死亡对他的生命“掌控”。
三、终极关怀:宗教变道的生命安顿
唐先生最后一年不管是在重病住院治疗期间还是在家休养和工作期间,阅读始终还是他“习以为常”的日常生命行为,甚至如他自己所说的“习气”。只不过,这一阶段的阅读呈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阅读不再是为了研究和写作,而只是安顿当下心灵的纯粹阅读;二是阅读内容上偏重佛教和佛学。在台湾住院治疗期间,唐先生夫人即言,唐先生近年喜读佛教书籍,所以特别在床头给摆上两本佛经供唐先生阅读。在回香港家中休养、工作的九个多月时间里,尽管也偶尔读“杂书”,也读西方学者送他的哲学著作,但主要阅读的是佛学和佛教著作,尤其是禅宗的语录和经典,包括:欧阳竟无先生《释教》,宋代赜藏《古尊宿语录》凡四十八卷,沈介山所译《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吴经熊《禅学的黄金时代》《宗密答斐休问禅门师资承袭图》,南怀瑾《禅海蠡测》,张钟元所译《传灯录》,永明《万善同归集》,Barnett编的Suzuki选集,Suzuki的ZenBuddhism(禅学论集)第一、二、三集,李世杰所译suzuki《禅佛入门》,隋代慧远《大乘义章》凡十四卷,窥基《法苑义林》及慧诏《法苑义林章补阙》,Suzuki的OutlineofMahayanaBuddlism,牟宗三先生《佛性与般若》,宋代了然著《大乘止观法门宗圆记》五卷。在生命最后一段相对“健康”的日子里,即癌症复发后两次入香港医院检查治疗之间的间歇时间段,从1978年1月1日回家到1月19日再次入院,唐先生除了2日阅《禅学论文集》外,其余时间几乎每日都在阅《圆觉经》和宗密的《圆觉经疏抄》,这也是唐先生生前最后的阅读内容。
作为一位大儒,唐先生为什么在最后直面死亡的岁月里以读佛教和佛学书籍为主呢?这与唐先生对宗教的态度以及生命的常道、变道的理解密切相关。
生死问题历来似乎都是宗教的核心问题,大多数哲学家也不将生死问题作为自己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好像这个问题“本来”就应该属于宗教。唐先生是哲学家、思想家,而不是宗教家,更不是宗教信徒,但是,其生死哲学的建构,却具有强烈的宗教“味道”。在唐先生看来,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抑或其他宗教,都不如儒家圆融、高明、广大、悠久。因此,一方面,他将各种主要宗教文化的超越性信仰涵摄于其思想体系中,将基督教、佛教作为“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列入“超主客观”的生命境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宗教的超越性信仰只能够居于“阴位”,只能够在“消极意义”上发挥作用,只能是人之现实生活处于“变道”之时的应变之策,而不能将其居于“阳位”,在“积极意义”上作为生活之“常道”应用。
当一个人遭遇生活的“变道”,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量渺小而无可奈何时,基督教通过设定和召唤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无所不知的上帝,个人凭借观想、思慕、崇拜“上帝”的全能大德以扫除一己生命力量的渺小感;佛教则教人明白,一切皆由人自己的贪瞋痴慢等妄执引起,只要知世间万法皆为虚妄,本性即空,就可以有智慧破除生命力量的渺小感。唐先生认为,尽管基督教与佛教都提出了助人破除生命力量渺小感的方法,也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他更加强调,依中国传统圣哲之教,人有心而能反躬自察,只要反躬自察即可发现自己的“好善恶恶之情”,此“好善恶恶之情”是人之“性”,将此“性”充内形外,即成德业事业;因此,对于自感生命力量渺小者,不必先教他相信有一全知全能的上帝会助他成就理想,由此破除自我渺小感;也不必先教他遍观世上一切不合理事都出于人之妄执,教他生智慧而破渺小感;而是可以直接将中国传统的相关思想扩大,依其核心之义融会二教。唐先生是要以儒家的尽性立命涵摄基督教和佛教的“超越信仰”,将宗教的超越信仰置于生命存在的“阴”的一面,而将儒家性情之教置于生命存在的“阳”的一面。不过,当一个人的生命遭遇巨大的现实困境,当下无力直接以直通性情的“阳”的方式应对时,在短时间或者过渡时间,以“超越信仰”的“阴”的方式借助“外力”增加个体生命面对当下困境的力量,在唐先生的理论系统中是被允许和成立的。面对死亡的威胁和疾病带来的巨大身体痛苦,当然不是生命存在的“常道”和阳面,而是生命存在的“变道”和阴面;当此之时,通过阅读佛教强化自己的精神力,甚至如唐先生临终前给夫人所言,通过观佛像来凝聚自己的生命力,是最切己的“变通之道”,因为佛像俯视,静穆慈祥,不使人起念;孔子像远视前方,使人有栖栖皇皇,时不我予之感;耶稣像在苦难中,更使人不安。
四、尊严死亡:居家临终的生命善终
“善终”在学术意义上被界定为“尊严死亡”,日常话语中也叫作“好死”或“优死”,是中国古人所企求的五种幸福之一,被视为完美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尚书·洪范》谓“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考终命”即是“善终”。在现代医学技术非常发达的情境下,死亡往往不掌握在个体生命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医院、医疗和医生,因此,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善终”即“尊严死亡”的追求,对由生到死的“死亡过程”的研究和讨论,已经成为一门大学问,不仅在纯粹学术意义上有“死亡学”“生死学”等,在医学、护理学层面也有了“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等专门学问。将西方“死亡学”和中国传统的生死哲学智慧相融合而创立华人社会“生死学”概念的台湾著名生死学者傅伟勋先生,曾经从理想条件和起码条件两个方面来理解死亡的尊严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善终”,“就理想条件而言,我们都希望能够避免恐惧、悲叹、绝望等负面精神状态,能够死得自然,没有痛苦……就起码条件而言……至少能够依照本人(或本人所信任的亲属友朋)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无苦无乐,心平气和”。[8]23这样的死亡不但能让终末期病人可以平静地安排自己人生宝贵的最后时光,而且也可以因此减轻生者的悲痛,不至于为死者的死亡而痛不欲生。
但是,在“现代医学情境”下,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学本身的异化,终末期病人往往遭遇着失去“死亡尊严”的尴尬处境,人们似乎越来越得不到“善终”。王云岭教授在《现代医学与尊严死亡》中指出,伴随各种“生命维持疗法”如人工呼吸装置、起搏器、鼻饲或静脉营养装置、透析仪、心血管药物等的应用,现代社会中的终末期病人常常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身上插满管子,身体极度衰弱,床头的心电、脑电监视仪器时刻向医护人员报告着他的生理指标,鼻饲管供应着他赖以为生的营养,呼吸机给他提供着氧气;他不能活动,哪怕一个微小的翻身动作也不可能;周围没有亲人陪伴,除非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医院的特许。这就是所谓的“ICU病人形象”[9]80。很多人这样孤独地死去,而这正是多数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的死亡群像。针对现代医学情境下个人死亡的无尊严现状,王云岭认为,在现代医学情境下,“优死”或者说“善终”“好死”,最为主要的内涵有两个:一是死亡时刻没有痛苦;二是死亡之前未曾受病痛折磨,特别是长期的病痛折磨。如果可以更进一步界定死亡过程中的尊严问题,则可以说:“一种死亡被视为优死,首先,意味着这种死亡是没有痛苦的,包括没有身体的疼痛以及精神的恐惧和压力。其次,意味着在这种死亡中,主体经历了精神的内在成长,这包括面对死亡的态度与选择死亡方式的意志。这种精神的内在成长是个体生命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意味着在这种死亡中主体获得了死亡的尊严,即或者因这种死亡赢得了他人的尊敬,或者在这种死亡中未曾遭受来自现代医学的侮辱,或者两者兼有。”[9]181-182
唐先生对死亡的过程有非常自觉的准备,这些准备不仅是在灵性精神的自觉方面,甚至包括死亡场地的选择、死亡方式的选择、死亡时刻的选择。唐先生手术后发现癌症复发后没有再进行极端的治疗而是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以减少痛苦;唐先生在病魔还没有导致其身体上如医生所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迫生”状态前,选择回家“等待”“自然死亡”;唐先生选择了生命最后阶段的居家临终,在亲人陪伴中而不是在孤独的ICU病房中安然离开这个世界;唐先生临终的最后时刻,是自己走到椅子上坐下来,在夫人打两个求助电话的短暂时间平静死亡。这其中,有几次关乎唐先生死亡品质的自觉选择。1977年3月4日,在得知自己病情恶化只有不到三个月的生命时间时,唐先生特地对夫人正式谈了他对自己疾病的想法:他相信他还可以拖一段时间,他希望在台湾能有一小屋,希望在台湾买一块墓地;同时,接受学生看中医的建议,并最终让病情得以缓解,而且比医生预估的多活了将近一年。1978年1月25日,唐先生最后一次住院期间,医生告知唐先生夫人,唐先生病愈的希望甚微,希望夫人应当有所准备。1月26日,感觉到自己身体快被癌症导致的咳嗽、气喘折磨的难以承受,唐先生提出回家休养,当日即从医院回家。1月31日,唐先生请夫人为自己理发,并自行洗头、洗澡。2月2日凌晨三时半,唐先生咳嗽气喘,不能安睡。用氧气筒后,虽然好些,但毫无睡意,乃与夫人讨论静坐之法。夫人谓,有时静不下来,便观想圣哲之像。唐先生谓,此时观佛像最好,因佛像俯视,静穆慈祥,不使人起念;孔子像远视前方,使人有栖栖皇皇,时不我予之感;耶稣像在苦难中,更使人不安。稍后,夫人在昏沉中入梦。凌晨五时半,唐先生突然气喘大作,自言不行了,夫人给氧气筒,亦不肯使用,直奔客厅坐在椅上。唐夫人让金妈陪着唐先生,急电医生求救,并电话李国钧夫妇过来帮忙。就在两个电话之间,唐先生一时接不上气,已瞑目不动,对夫人无数声的呼唤,均无反应。医生谓,唐先生这样安静地过去是幸福,否则来日的痛苦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3]514
在唐先生的死亡准备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基于自己的生死智慧和生命自觉,他没有强烈的“精神恐惧和压力”;而且,他还在这一准备死亡的过程中经历了“精神的内在成长”;并且,因为唐先生在临终前选择了类似于当代的“居家安宁疗护”的方式回家休养和保守治疗,因而“未曾遭受来自现代医学的侮辱”,也没有经历剧烈的“身体疼痛”而导致自己失去尊严。因此,不管是从现代医学情境下的“尊严死亡”角度看,还是从中国传统社会所期待的“善终”来说,唐先生的“死亡”这个生命事件,都可以称得上是“善终”。
五、生死互渗:完善不朽的生命永恒
对生死问题的体验和意识关切,是贯穿唐先生一生的生命与学问中的。他在生命成长的早期,经历并深刻体验了好几次生死离别等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以及所带给他的生命体验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唐先生在写就他一生最宏伟的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还特别在“后序”中对它们一一记述;在他躺卧在病床上深刻反省自己的生命经验之时,也将它们梳理出来作为自己生命经历的重大事件;而在他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退休演讲中,这种生死经验的回忆仍然是重要主题。而其终身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带着这一问题意识的,并围绕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为了解决他自己和现代人的生死困顿,唐先生立足于儒家生死观的基本立场,整合佛教及西方哲学的生死理论,提出了以实现“不朽要求”为目标、以“心灵生命”为基石,以“立三极”(人极、太极、皇极)、“开三界”(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人文世界)、“存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为归旨,以“生死呼应”“生死感通”为根本的一套性情化的生死哲学理论。
这样一套影响他终身并指导他的“死亡准备”的生死哲学理论,用唐先生在二十六岁时发表的《论不朽》一文的话语来说,即是一种确证生命永恒的“完善不朽论”。从青少年时期的生死体验与感悟,到三十岁左右撰写的《人生之路》十部曲(包括《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三书),再到五十岁左右撰写《人生之体验续编》《病里乾坤》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等著述,及至晚年的结晶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唐先生在理论上建构起了这样一套“完善不朽论”的生死哲学。这套生死哲学以“心”为生命存在的依据,此“心”作为本体,既源于超越的“天”,又内在于每一个人的“性情”,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之内,又连接于生命和世界的本源之“天”的超越性。此“仁心本体”的超越性表明,它不会随着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成为“非存在”,所以是不死的;“仁心本体”的超越性会不断向自我发出超越性的自我命令,即提出理想志愿,而这种命令本质上也就是“天命”;人的身体和心灵以“呼应”关系,共同不断实现这些心灵志愿,创造新的“属人的”人文精神生命。由此,人的肉体与心灵一起,因为此人文生命的永存而永存。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尽管有身体的死,其生命却是“死而不亡”的。不过,这样一种“死而不亡”的生命,必须建立在生者自己不断自觉地自我超越,以“义所当为”来要求自己“自觉地做自己该做的”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生命存在必须充分发挥其“用”,此“用”也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理性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心”行“义所当为”之事,必然包括对其他个体生命的体认,亦即对人与人之间“精神空间”的确认,此精神空间也包括对“死者”之“余情”的体认。由此,生者与死者之间,通过“情志感通”建立起了通达的道路,“死者”以事实上的情意存在,生活于生者的生活世界,“洋洋乎其上”,“洋洋乎在左右”,生死世界成为一个整体通达的世界,这个世界涵摄在我们的“理想”亦即“性情”之中。
1976年8月12日被诊断罹患癌症的当晚,唐先生与夫人一夜未成眠。面对突然而至的死亡威胁,以死观生,唐先生反思了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念及自己学问工夫,谓,“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今日下午与廷光谈我所见之理,自谓不悟。但智及不能仁守,此处最难,望相与共勉,应视当前困境作吾人德业之考验。”[2]309见夫人精神恍惚,情绪反常,唐先生乃与之细说生死之道。唐先生告诉夫人,儒家的伟大处,是从道德责任感出发来讲生死,生则尽其在我,死则视死如归,故居恒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若生与仁义不可兼时,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同时,儒家承认鬼神之存在,人死幽冥相隔而精神相通;儒者的下手功夫亦略有次序,首先要超语默,其次要超去就,最后是超生死;如果一个人可以从超生死的视域来谈生死,那么,不管是生还是死,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重要的只是我当下的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和尽当下的人生使命亦即个人的天命。[3]484唐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以“超生死”的方式来言说生死、面对生死。1978年2月1日,再过两天便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唐先生七十寿辰。当天下午,唐先生向夫人忆述三位前辈的事迹:对中国文化充满无私悲悯的美国人William Hockeng,有儒者风度的日本前辈宇野哲人,对自己极尽关怀爱护的梁漱溟。说到动情处,唐先生情不自禁就哭了起来。[3]513-514这样一种生死幽冥的情志感通,恰恰就是唐先生自己生死哲学的当下实践。
当唐先生意识到自己罹患癌症后,所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立即给台湾学生书局张洪瑜打电话,请其速排《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以便到台湾治病时校对。[2]308-309面对死亡威胁时,作为一位儒者,唐先生关心的不是疾病和死亡本身,不是肉体生命的痛苦,而是关注生命本身的完成和人生的无遗憾。而此刻,唐先生一生心血最重要的著作还在出版社的排版中,他不希望留下“未完成遗著”这样的人生遗憾。诚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死亡的意义不是由死亡本身来界定的,而是由完成生命的人生来决定的。而人生的根本目标对于儒者来说就是“闻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对于一位思想家来说,“闻道”还必须通过自己的文字将它呈现出来,这就是自己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的出版,关乎唐先生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关乎唐先生对“道”的领悟、阐释与践行,此比之他的肉体生命的病痛更为重要。该书最终在唐先生第一次赴台治疗期间,于9月8日在做癌症手术的前一天完成全部校对,于1977年底在唐先生逝世前正式出版,成为唐先生贡献给这个世界的最重要著作,也让唐先生可以走得没有遗憾①。
唐先生生死哲学的核心意味,是要人领会到,一个人的“心”,是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只要你跟着自己的基于“性情”的“心”走,使自己的生活不断“理性化”,你的生命即“一有永有”而进入“完善的不朽”。而面对自己的死亡,唐先生同样禀受天命,自觉地做自己该做的,使自己面对死亡的生活仍然是“理性化的”亦即“道德的”生活,从而实现由生到死的真正的“尽性立命”“天德流行”。可以说,唐先生以其全副生命实践着他自己生死哲学所倡导的“生活理性化”目标(尽性立命的道德生活),并以真切的行状给人们呈现了一副真正的“生活理性化”的生命样态。唐先生实际上是在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和生命实践,双重地建构自己让生命永恒的“完善不朽论”生死哲学。
注 释:
① 唐先生自言,“三十余年前,即欲写此书”。在《人生之体验》一书中的“自我生长之途程”、《心物与人生》一书中的“人生之智慧”、《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书中的“孔子与人格世界”、《人生之体验续编》一书中的“人生之艰难”等篇,唐先生尝以带文学性的语言和宛若天外飞来的独唱、独语方式,涉及到此书的根本义旨在人生方面的表现,并言,“此乃吾一生之思想学问之本原所在,志业所存”。1964年,唐先生在母亲逝世后,曾经决定废止一切写作,也包括此书在内。1966年,又罹患目疾,更有失明之忧。在日本住院治病期间,时念义理自在天壤,而此书亦不必写,以此自宁其心。又尝念,如果自己果真失明,亦可将拟陈述于此书的义理,以韵语或短文写出。幸而目疾未至失明,唐先生方可以继续完成此书及其他著述。1968年,由春至夏到八月初,四月时间,唐先生撰成此书初稿五十余万字。此时,目疾加剧,旋至菲律宾就医看病。在医院中,唐先生更念及初稿应改进之处甚多。1970年初,又以五月之期,将全书重写,并自谓“此重写者较为完备,俟以后再改正。”在之后的七八年中,唐先生于写《中国哲学原论》四卷六册之余,又陆续对自认为的疏漏之处不时加以增补,似已较为完善整齐。因此,此书的写作,从1968年正式动笔到1977年完稿交付出版,历时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