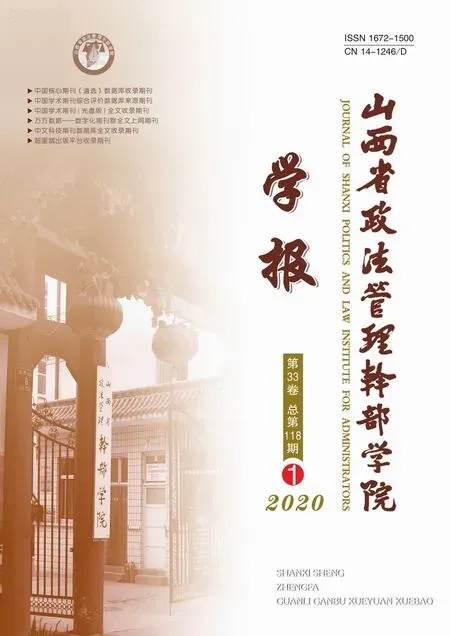社会公共利益与强制性规定在无效合同认定中的适用关系
2020-02-22朱霄霄
朱霄霄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一、案例梳理
(一)案件事实
君康人寿于2010年1月28日召开股东会,就“五环氨纶已将所持公司2亿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比例20%)转让给天策公司”事项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和股权结构。2011年9月16日,保监会批复同意:泰孚公司将所持君康人寿2亿股股份转让给伟杰公司,伟杰公司持股比例为20%。2011年11月3日,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签订《信托持股协议》,协议约定:鉴于委托人天策公司拥有君康人寿2亿股的股份(占20%)的实益权利,现通过信托的方式委托受托人伟杰公司持股。受托人伟杰公司同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2014年10月30日,天策公司向伟杰公司发出《关于终止信托的通知》,要求伟杰公司依据《信托持股协议》终止信托,将信托股份过户到天策公司名下。
(二)争议焦点及裁判情况
本案焦点主要集中于《信托持股协议》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针对《信托持股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该协议也没有提出异议。从《信托持股协议》约定的内容上看,受托人伟杰公司接受委托人天策公司的委托,代持君康人寿股份,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信托持股协议》为有效合同。
二审法院认为,依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信托持股协议》违反了此项规定,尽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本案认定《信托持股协议》无效。
二、强制性规定概述
(一)强制性规定的界定
强制性规定没有明确的国际界定标准,德国、日本学者还有以史尚宽先生为代表的台湾地区民法学者都认为强制性规定是关于保护公共秩序的规定,并且与任意性规定是相对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法律行为往往也对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我国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将强制性规定定义为:一切与国家利益、社会秩序以及第三人利益有关的事项。[2]所以,强制性规定有两个特点:行为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变更或者排除适用;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针对第一个特点,根据文义解释,这是强制性规定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与任意性规定相区分的最本质的内核。如何理解第二个特点,王泽鉴先生认为,任何法律都是有立法目的的,当我们研究强制性规定条款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有必要制定强制性法规,立法目的是什么?我国订立《合同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旨意是保证当事人契约自由并侧重政府管理。例如,本案中《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虽然《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对强制性规定范围进行了限缩,这种限缩是建立在《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五项的适用之上的,但并不能否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中关于禁止保险公司股权代持规定的强制性规定的实质,该办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契约自由是近代民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3]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无限制的,不是绝对的,绝对自由有时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国家加强了宏观管理,相应程度的限制自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自然可以成为限制合同自由的正当理由。
(二)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困境
自《合同法》确立合同无效制度以来,强制性规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的争议就从未中断。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将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且违反前者合同才会无效。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司法实践更加混乱。
1.强制性规定位阶的局限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合同法司法解释进一步强调,合同无效不能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法律依据。并且在《民法总则》中也重申:强制性规定必须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是,学者对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范围有不同的看法。根据《德国民法典》,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范围没有被限制,法典中的“法律”是指一切法律规范,除法律、行政法规之外,还包括地方性法规。在日本,末弘严太郎也主张不对强制性规定进行具体区分,这是日本的通说。台湾地区民法同样主张强制规定包括了法律、行政规则以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命令。[4]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不能将所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现实情况都涵盖进去,因此,当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相关行为损害公共利益时,法官很容易根据法律规定确定合同的有效性,必然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失衡。例如,在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完全根据法律规定,认为《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属于行政规章,效力低于法律、行政法规,该办法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因此判定《信托持股协议》有效。但是这种做法就会影响保险公司的经营稳定,进而会损害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合同法》保护公共利益的宗旨。
2.强制性规定分类面对的难题。对于强制性规定的分类,大多数学者提倡进行二分类,即将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法解释二》也呼应了这个观点,并且明确指出,如果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则无效。但是如何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没有明确的标准,理论上的争议仍在持续,立法不足,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有学者主张,从司法裁判出发,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行类型化研究,这也许会为法官裁判合同是否有效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这种方法又带来新的问题,类型化的标准如何把握?并且这种分类也过于僵硬,非此即彼的做法对法官的裁判指引功效不足。因此,目前的司法难题变成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适用及发展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
从论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一审、二审法院对股权代持合同的效力做出截然相反的认定,二审法院以代持保险公司股权损害保险业的公共利益为由判定合同无效。究竟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各国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这样就容易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误解以及司法实践对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的滥用。从文字概念角度来看,国际上通用的“公序良俗”与“公共利益”有着相同的内涵,国内大多数学者也认同这种说法。[5]
笔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与范围不应该过于精确,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同的案例中有着不同的内涵。比如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基于保障保险公司的稳定来看的,如果经济市场允许他人隐名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保险公司投资人就会逃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如此一来势必威胁保险公司的经营安全。并且保险业涉及不特定多数被保险人的实际利益,某些潜在的经营风险将会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从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与北京德法利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协议纠纷案中,再审法院判定合同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是否影响到福利彩票销售资金中其他两类资金的比例,是否违反公平原则为依据。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理论界没有明确社会公共利益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反映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序良俗的行为无效,这也是各国立法所普遍确认的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遵循四个要点:主体的广泛性;空间和主体人数的不确定性;公众收益性;合理合法性。[6]
(二)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第三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出现了多种利益的概念,但如何区分这几种利益,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对于他们的关系,各个学者认识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利益不等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7]还有学者认为集体利益不同于公共利益,不能混淆两者的概念。还有学者认为集体利益就是公共利益。[8]笔者认为,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第三人利益是指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是最大范围的社会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利益是某个地域、某个空间的公共利益。[9]他们之间可以交替使用,内涵是等价的,只是范围上有些许区别。
四、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适用关系
案例中涉及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二审法院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没有适用《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而是径直依据《合同法》第四项的规定直接判断,认为协议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学者对这种做法并不能认同,认为这会造成法律适用关系上的逻辑不清晰。因此,有学者认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等都属于合同无效制度中的强制性规范,法院在审查合同效力时,应该平等适用以上规定。这种观点并非不合理,但是必须以我国的社会形势为基础,依据我国的立法体系,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大、省级政府等均有制定法规或规章的权限,如果把这些规范都纳入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这可能会导致大量合同无效,影响交易秩序的稳定。[10]提高强制性规定等级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或者部门为了自身利益通过规范性文件获得优益地位,从而促进交易自由与安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强制性规定的位阶进行限缩。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司法实践将面临上述两种困境,所以我们可以巧妙利用《合同法》五十二条第四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第四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都具有强行法的特征,两者立法意图是一致的,强制性规定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社会公共利益不仅存在于法律、行政法规中,低位阶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同样体现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在两者的适用关系上,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崔教授的观点,即第五项具有指引具体的强制性规定及引入公法强制性规定的功能,第四项对强制性规定的法律适用具有漏洞填补功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只是该条第四项的特别法。[11]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针对强制性规定适用的第一种困境,即强制性规定位阶的局限性,当法律、行政法规层面的强制性规定缺失时,且不得不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可以运用《合同法》五十二条第四项,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这种做法就是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作为兜底标准。结合本案——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来看,双方签订了《信托持股协议》,约定由伟杰公司通过信托的方式,代委托人天策公司持有股份。但是《信托持股协议》违反了《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此规章也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即保持市场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因此,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以维护金融行业稳定为由判定合同无效。在这种处理背景下,就可以进行两个步骤,首先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适用不在此位阶的强制性规范,但需要判定合同无效时,就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否定合同效力。
其次,针对强制性规定分类带来的困境,在实务操作中,法官对于强制性规定的判定并不清晰,最高院颁布司法解释,明确将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只有在违反效力型时才无效。但是如何区分效力型成为新的困惑。有学者提出了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区分标准的观点。[12]这个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前文已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利益都是指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是导致所有合同无效的最本质的原因。从这个关系上来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界定标准仍然需要回归到社会公共利益中去,基于这个观点,有学者提出,应当将第四项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删除。但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这容易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倡导成为空话,并且不利于法官运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裁判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