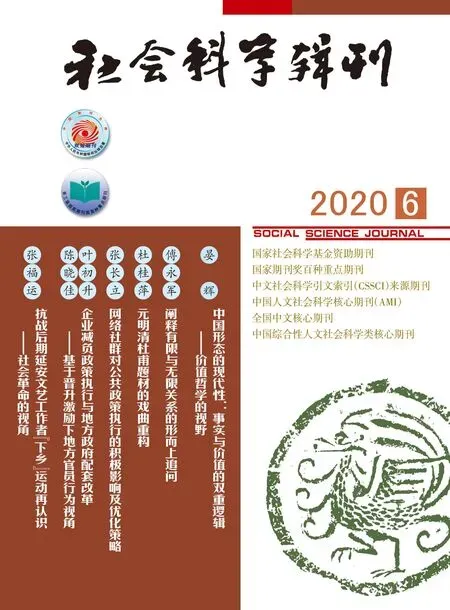是否、应否、能否:信任的道德形上追问与经验省察
2020-02-21李建森
李建森
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似乎“人心惟危”了。从所谓“道德冷漠”到“道德焦虑”,从“道德绑架”到“道德恐怖”,人们不时面对各种非道德问题。就连罗尔斯都说:“在对长久的传统价值产生怀疑和丧失信念的时代,在诚实的德性上,即在诚恳和真挚,坦白和承诺,或如一些人所说,在真实性上存在着一种倒退的倾向。”〔1〕也许这是一种遍布中西并反映资本文化矛盾的时代风格。〔2〕2018年10月,重庆市一辆公交巴士因为其司机与乘客的殴斗而冲下大桥坠江,车上乘员全部罹难。假如这辆巴士上哪怕有一位乘客能够义无反顾挺身止恶,这“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就不大可能发生。①这些现象可以看作是加勒特·哈丁所谓“公地悲剧”的否定式表现,或者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地悲剧”,参见Hardin 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vol.162,no.3859(1968),p.1243。但不是“反公地悲剧”,参见M.Heller,“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Harvard Law Review,vol.3,no.111(1998),p.621。而如果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那么,那些只得到最少照顾的共享事物,却注定要惩罚最大多数人。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8页。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公共性道德问题与雾霾一样,似乎都表征了一种非常普遍的道德“现报”世相。这与其说是“我们的道德”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我们”出了问题。那些使“我们”成为可能的最基本要素,无非就是同构的身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现在,肉体之同一性依旧,可是道德精神之统一性却千金难求了。我们道德“文明的可靠性疲惫不堪”〔3〕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追求精神之统一性,而那个使我们的道德精神统一性得以确立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建基于“人同此心”集体性思维的社会信任。避开流行的经验社会学非批判性研究样态的观点,本文将以“是否”“应否”与“能否”为切入点,在逻辑和历史论域,不仅发掘社会信任之“形而上的存在论意义”,更要开显其中的“意志自由自律的纯粹意义”以及“具体实践的功夫意义”〔4〕,以便对重拾我们之道德精神统一性信心有所裨益。
一、作为道德事实和前提的信任:一种生存前提和基于对此前提的尊重所给予的道德生活必要资源
信任(trust)究竟“是什么”?这属于道德形而上的存在论问题。如果选择一种大多数人都比较乐意接受的客观主义的道德表现方式,就可以说,信任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事实。信任属于“非物质性”(non-material)社会事实范畴。〔5〕它既体现着自己的道德形而上的基础地位,又体现着自己在逻辑和历史两方面的古老经验存在。在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这里,社会事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物质性的社会事实,即真实存在的物质实体,包括社会、社会结构性组成、社会的形态成分;另一种是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包括道德、集体意识、集体表象、社会潮流。〔6〕信任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范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信任与“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是在相互限定、相互塑造中同时形成的。虽然在事实上,“信任”“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在生活的经验世界是不可分析的,但是,在对于思想的分析世界里,它们是可以分别陈述的。信任既促成了“我们”,又保持了“我们”,还使得“社会的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得以不断地生成和发展。信任就是社会事实、社会世界、生活世界的最根本基础,具有伦理发生学逻辑上的“第一性”意义。
社会经验的系统事实显示,信任行为、信任关系和信任现象等社会道德事实要比信任道德哲学意识出现得早。德国哲学家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就曾说过:“道德要比道德哲学古老,没有道德作为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道德哲学。道德哲学产生于对支配着生活和判断的现存道德进行思考的时候,而且这种既定道德是不会因为道德哲学的出现就被废除或变得多余。”〔7〕照此来看,人在移情规律的支配下,将同类个体类同于“我”的同化本能行为〔8〕,虽然还不是如后来那样典型的信任伦理关系,但是,它肯定就是信任伦理关系的生长点或胎胞。在前道德意识时期,人本能地将自己和自己的同伴看作是相同的、一致的或近似的。随着人类进化的完成,这种同化本能,慢慢升华为类思维。〔9〕这种类思维,不仅把同伴看作是与自己同质的,进而赋予同伴与自己一样的地位,相信同伴会和自己一样以同质的方式存在,而且,还会把同伴与自己看作是相同社会结构内部的合作者,相信同伴和自己一样受益于彼此的支撑帮扶。这样,信任完成了从感性事实向自觉观念、从偶发实然向规范应然的跃升,并产生了自己的积极成果,这就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倾向”的信任道德思维和意识。〔10〕而在这种道德思维和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自觉的、体现着道德主观和道德客观相统一的知行统一体,就是具有“元道德”“元法则”(principle of principle)地位的、作为最基本社会道德事实的信任。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信任常常因为种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即那些常常能够被理性人所宽容的原因,并不总是靠得住的。可尽管如此,在既定的生活世界中,虽然信任常常被“背叛”,可是,除了继续给予更多的信任之外,人们并没有更好的对于信任的替代方案。而且,人们不断创造出一些新的社会道德事实,如原始宗教、图腾力量、风尚习俗、契约和法所凝结的道德诉求,以此来进一步强化信任理念和信任事实。于是,信任这种社会道德事实在道德文明或道德文化的自我淬炼和塑造中越来越被强化了。信任所包含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契约力量或契约精神,成为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最基本力量,成为保证人们历史活动确定性的最重要假设,成为包括道德生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和资源,即成为每个理性人都需要的“社会最基本的善”(social primary goods)。〔11〕
不管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和进化主义的分野如何巨大,在契约精神起源及其所蕴含的最基本“元法则”的先验性地位上,即在信任重要性的问题上,它们的预设应对与道德语言表现都是高度一致的。“事实的客观性”“规律的必然性”“自然的意图”“适应的鬼斧”“理性的狡计”甚至“神的旨意”等结构性道德语言的语义核心或论证方式,无不指向那个使人、共同体和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可预见的、稳定的、确定的社会基本的善,这就是社会信任。可以说,没有隐藏着信任假设条件——诸如“自然状态”“无知之幕”之类——的一切思想实验,都无法得出理性结果。理性的结果只能从理性的原因(根据)中生发。理性的结论只能潜在于道德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之中。①任何道德说词、道德判断或道德叙事都可以被建构成或还原为一个三段论推理,其中大前提即普遍性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小前提为所申诉的特殊道德事实,结论为新产出的道德认识。参见〔美〕史蒂文·卢坡尔:《伦理学导论》,陈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从某种社会语用学(social pragmatics)的角度看,这个三段论大前提中所隐藏或暗示的可能性答案,就是社会信任的前身原型。正是在这种社会信任的结构中,包含着更具体的可被社会语用“外在动力”激活的道德信任意识和行为家族。无论是无动于衷的“漠然”,还是从善如流的“幻想”,都是对特定场域(field)下,基于语言交换所期待的利益实现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抑或其他因素的“市场”交换关系的肯定、相信或信任。〔12〕
尽管人们日后会逐渐意识到,上述信任所期待的并不一定会如期而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心中的“绝对命令”还是要赏识地说:“除了信任,只有信任。”〔13〕而对于普遍的世俗灵魂而言,失信的试错行为,还有他者背信弃义招致的严厉惩罚,以及世俗教育、政治权力和宗教信仰的鼓动,都使他们不得不对社会信任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并成为其拥趸:信任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事实或社会力量,是所有社会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最可贵的原生资源。
二、作为道德原则和智慧的信任:一种基本安排和源于对此安排的放心而推崇的底线道德规范
人们彼此之间“为何应该信任”?作为“应该”(ought)的信任对人们意味着什么?信任意味着人的意志自由自律。人无信不立,人们彼此之间应该信任。从生存论角度看,信任与确定性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信任既表现为对确定性的结构性把握,又表现为对确定性的文化性追求,并因此在个人层面获得安心,在社会层面成为人和人的全部“规范丛”的最根本基础和生长点。可以说,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是文化生活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类的一种与安全相关联的本然性需求。人类对于变化的好奇兴趣和深层探究,说到底都是为了追寻某种真善美的不变、宁静或永恒,寻找带有终极性意义的生活根据和精神家园。柏拉图《对话录》中关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划分,以及对现实世界变动不居的虚妄症状的否定,就是对永恒而完满的“旅程的终点”——理念世界的热切期冀。〔14〕儒家群经之首《易经》与其叫作“易经”,还不如叫作“不易经”。所谓“易”,乃“不易”也,乃“有常”也。至于释家所谓“即动而求静”,也许不仅仅反映了人类对于尘世无常所引发的烦恼焦虑的厌倦,而且也印证了人类对于岁月变故招致的困顿迷茫的不安。古往今来,社会确定性供给匮乏正是社会信任需求旺盛的最根本动因。
如何才能够保证生活的确定性?就自由人类与自在物界的区别来看,应该就是“思想的生命意志”所独有的知性技术和理性智慧。〔15〕正因为知性技术和理性智慧对于确定性的生成、把握和运演,才使得信任成为可能;正因为信任对于生活世界内容和结构的确立、确认和确证,才使得一切可预见的思想行为成为可能。这个进程绝不是“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不断增加的经验和行为的可能性”〔16〕的悲观论解释,而是信任的“内在积累与交替上升”〔17〕。所以,几乎所有文化形态都将信任安排或设定为最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和底线规范。知性技术通过认识因果间的决定性关系而确立和把握确定性〔18〕,实践智慧则通过主体的程序性建构而生成和运演确定性。
最能够体现知性技术的就是知识。知识的巨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预见性。正是在知识预见性的基础上,我们确立起关于自然对象可预见的信心。我们确信明天“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是基于我们对太阳系的“真理性”知识。但是,基于对自然对象的“真理性”知识的信任与基于对社会对象的“真理性”知识的信任在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以致于很多人宁愿将它们看作完全不同的社会事实。基于对自然对象的“真理性”知识而衍生的信任似乎总是可靠的,因而在此反而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任问题。〔19〕相反,基于对社会对象的“真理性”知识所带来的信任,总是难以令人完全放心的。因此,要保证生活的确定性、稳定性或者可预见性,就必须使基于对社会对象的“真理性”知识所带来的信任能够得到最大范围的遵循。信任现在变成一种使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进行的普遍道德原则。同时,信任之所以必须被当作普遍的道德原则,还是因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活动总是被禁锢在重重的因果链条之中的,总是被架构在变化着的整体性之中的。他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变化的,他所承载的因果联系是多样的。而这些角色的义务和因果联系的趋向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有时候甚至是相互抵牾的。他既可能是主体—自我,又可能是客体—对象,既可能是窥视者,又可能是被窥视者。〔20〕而这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在“置对方于死地”。自我与他者只有在相互“注视”的彼此确认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在场存在。也许,彼时之自我只有在与此时之自我的相互“注视”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在场存在。因此,那些看起来在同一因果链条上的“蚂蚱”,即同质性存在,常常很自然地要面对同伴的意外“出轨”。可是,如果因此而不再坚守对于稳定性的期待,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一个人根本无法正常生存。所以,信任还是必须被当作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只有当人们确信他人一定会如他所期待地行动的时候,他才可能是放心的。或者说,只有当人们确信他自己的期待是“可期待”的时候,他才可能是放心的。现在,信任不仅仅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德性。〔21〕信任不仅仅是对于知识所凝结的必然的确定性的自觉遵循,同时也是对于理性所内蕴的种种或然的确定性的自由选择。
而最能体现理性智慧的就是实践精神。实践精神凝结的自由意志所体现的智慧,即实践智慧(phronesis)①对于实践智慧(phronesis)范畴,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界定是不同的。伽达默尔与亚里士多德相似,将实践智慧看作是具体情境中的总体善断。康德对实践智慧持批判态度,因为实践智慧肯定并强化了对于非普遍性的考量。所以,在康德那里,实践智慧几乎是被看作机巧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实践智慧是为实践服务、指导实践行为的一种非独立性真理,是使行为自身透明的真理,它对于行为的正确实行而言是共构的(mit-konsititutivi)。,能够通过主体的程序性建构而生成和运演确定性。实践面对着普遍的偶然性(contingency)存在。欲求、机遇以及所有与变幻无常高度相关所造成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得生活世界深陷不可预知性。“审慎的理论家总是强调审慎的分析就开始于结构性断言的终结之处。”〔22〕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指涉并处置的是那些不能被普遍必然性所决定的非典型性的历史行为。〔23〕历史的实践面对多元性存在。对于行为抉择而言,常常置身于复杂的实践情境中,与形而上学理想的或者先验的主体不同,现实的实践主体每每具有相互冲突的异质性价值需求,不同的主体之间、不同时空境遇的同一主体之间、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都要求一种恰当的具体性、境遇性的平衡、结合或安排。因此,实践智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被看作是潜在不可通约的,是各种复杂交错的视角的交融。也就是说,能够关照并最后超越历史性、情境性的不确定性的存在的实践智慧,就是一种对各个内在的相互竞争的决定性变量的调适。而且,它还不能被“概括”为内蕴着普遍性迷失危险可能性的理智或德性规范。〔24〕实践智慧既要体现恰当的自由意志,又要反映不那么绝对的决定性。在社会群体中,实践智慧既能够容忍因为自由意志而可能造成的审美意外(无论是惊喜,还是颓丧),又要抵消因为不那么绝对的决定性而可能导致的意义沦陷(命定论、虚无感)。实践智慧凭借自身的中庸平衡结构思维及其主导的程序性社会建构而生成并保证了生活世界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从而也给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须臾不可背离的充沛的信任资源。其重要性正如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25〕由此看来,信任是最基本的底线道德规范或社会道德生活规范的底线。
三、作为道德理想和追求的信任:一种悖论性追求和由于对此追求的反思而鼓励的道德超越期待
我们“能够信任什么”?这是关于社会信任活动限度、阈值的“实践功夫”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可以将社会信任寄望于何等高度的问题。它包括信任的对象范围和信任的程度大小等内容。在道德哲学发生深度社会学转向的今天,在主体性哲学被普遍诟病的当代,在“器惟新,人亦惟新”的当代现实生活里,我们似乎不得不去认真思索社会信任实践的可能理想高度和严峻的现实际遇,冷静于社会信任的现实性矛盾并发奋于对“惟信为宝”“惟善为宝”“讲信修睦”之治郅的追求。比如在生态伦理领域,如果沿袭传统信念而将基于自然对象因果律知识的信任排除在伦理规范之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同时在德性向善立场上也是不可取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合理根据与正当理由去否认那些高等动物尤其是与人具有亲密关系的动物(如导盲犬)具有信任伦理问题?但是,这可能产生一个让我们无法回避的时代性难题,即动物比人更可信任之“彼得·辛格难题”。①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存在着从平等主义出发最后得出不平等结论的逻辑困难。“生命的质”(quality of life)这一新的伦理标准,虽然维护了动物的道德权利,但是却使得婴儿和智障残疾人等失去了“人”的尊严。这是一个善心和逻辑的张力难题。一个恰当的伦理思维的选择可能是,我们一方面不要完全否定那些内在自足的“深层”的广义信任伦理,另一方面,要将关注的重心放在那些外在的“浅层”的信任伦理上。而且,当代社会发展也似乎更加迫切需要我们重建外在“浅层”的狭义的社会信任的德性基石,提升社会信任的“实践功夫”。
严格意义上,关于信任的合理伦理表现只发生在非信任即疑虑可能发生的伦理情境中。在那些超高概率事件及其缺乏意志自由余地的甄别选择上,可能谈不上典型的信任伦理问题。社会信任就是文化系统把在群体或共同体生活中的决定性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对抗关系,朝着整体进步的方向不断展开的方式。这里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假设。其中的绝大多数就其内容而言是有限的、消极的。第一,个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除非他品尝到得不偿失的后果,或者其得到其他形式的更大替代的满足,否则,这个利益最大化过程不会真正停止。第二,在特定的时空和条件下,群体或共同体内部能够用以分配的福利和机会是一定的、有限的。在特殊条件下,未来福利和机会可以被提前分配。第三,参与分配的群体或共同体成员具有必要的经验或理性强度,这种强度恰好足以压制因为分配纠纷而产生的可能导致共同体破裂的激烈冲突。这些前提假设分别表达了在具体社会条件下人性的有限性、利益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进而言之,它们更表达了人性、利益和理性置身其中的有限性现实和无限性理想的矛盾漩涡。正如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所说:“普通人介于对立物之间,并懂得他永远不能取消它们。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恶就没有善。其中的一个制约另一个,但它不会变成另一个或取消另一个。”〔26〕也许藉此可以说,我们介于希望和失望之间,我们介于信任和疑虑之间,并应该懂得我们永远不能取消它们。没有失望就没有希望,没有疑虑就没有信任。其中的一方制约着另一方,但是永远不会取代另一方。
如果因此而得出有关社会信任的悲观主义结论的话,那是不恰当的。也许普遍失信会成为时代特色,并因而成为有限个人生活的全部历史背景,可是,从更长远的状况看,理性最终会成为赢家。只有个人才具有道德悲剧,历史自身无所谓道德悲剧。那种只接受其他鸟给自己头上抓虫子却从不给其他鸟头上抓虫子的鸟(鸟甲),只是在最初的道德试验中生活得最好,此时被淘汰的是那个只给其他鸟头上抓虫子而从未得到相同回报的鸟(鸟乙)。但是,随着实验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逆转。最终胜出的是那只既给其他鸟头上抓虫子又得到相同回报的“赞成合作”之鸟(鸟丙)。〔27〕当然,这个博弈模型只是自由主义的解释方式。它本身不能说明鸟丙和鸟乙之间伴随着一些信任的期待是美梦成真的原因。那只看不见的调节之手,就是社会群体或共同体在历史中展开的制度实践理性。
如果因此而得出社会最终会自发走出社会信任危机的盲目乐观主义结论的话,那也是不恰当的。信任本身不可能是产生信任危机的原因,同样,信任本身也不可能是解决信任危机的可行策略或出路。信任危机是一个伪命题。至少,这个术语存在着理解的困难或歧义。信任不会出现危机,危机只是共同体的危机,是“我们”的危机。所谓的信任危机实际上只是共同体危机在信任领域无可抵御的“印染效应”,即是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危机“祸水”对于道德信任这种“白纸”的印染浸渗。所以,不能期待信任能够解决信任问题,信任问题只能通过非信任的力量和因素来解决。这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至少它没有循环论证的弊端。可是,扪心自问,非信任力量凭什么能够解决信任问题?外在论证方式的合理性根据又是什么?在其三段论的简单道德推理中,它们结论中的合理性是存在于什么样的作为大前提存在的道德原则之中?
关于信任的一切道德乌托邦主义和道德主义都是不现实的。社会信任伦理注定只存在于层层叠叠的形而上矛盾之中。消极悲观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都是不可取的。《镜花缘》里讲信修睦的“君子国”之类的绝对精英主义从未超越文学审美意境。诚如康德之“至善”“圆善”(highest good)虽然远在有限理性无法企及的不朽彼岸,可是,我们不可能不在心中常怀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如此,辩证否定的实践智慧选择信任现在进而信任未来,一个没有背信弃义的守信重诺的社会就在有限的信任“实践功夫”之中,而不是在其之后,就在现实世界,而不是在彼岸世界。
综上,社会信任是标志实然性的最基本的道德事实,是彰显应然性的最普遍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承担生活理想之最重要的道德追求。可见,天下之治,无非心安其分,人任其责,民享和乐而国祚悠长。的确,想要完全达到“人人可信,事事堪任”的理想社会状态,并不现实。对此,就连那些倡导绝对文化价值的思想形态也并不完全拒斥这一看法。撇开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神秘主义错误,它也包含着对守信、忠诚、承诺、诚恳、真挚、背叛、怀疑、违约、虚伪、猜忌和失信等道德善恶“合理性”的深刻辩证。它认为,神的智慧超出人们的理解,在人看来诸如失信违约之类的恶,其实根本不是“恶”。在《约伯记》中,约伯的忠诚和可信任被不厌其烦地考验着,尽管约伯历经磨难而不失忠诚,但神还是没有终止对他可否信任的残酷考验。于是,约伯质疑道:为何如此“待我残忍”?神以雷霆作答:“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圣经》)据此,诺斯替神正论认为,此乃提醒约伯,有限人类不能认识无限心智。〔28〕经验世界里的背信弃义,不仅仅是客观的伦理事实,而且也是自由意志的起点、对象和归宿。因此,社会信任是相对的、历史的、结构性的,也是持久的。就客观伦理史而言,社会信任危机从来没有也永远都不会成为历史逻辑的飞地。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包括社会伦理进步在内,“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29〕。社会信任的进与退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进步对于被资本逻辑统御的有限生命是这般无情,恶的“代价”似乎不明不白地僭越为生活本身。面对由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指数性增长所造成的后现代信任问题及其所导致的新道德问题,现代人也许该放弃偏执,安心于全部现实性,以此让心灵得到安抚和升华:人不可能不是“人”——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人”逻辑上优先于人,相应地,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长远而言,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根基的“总信任”从未真正远去,也不可能真正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