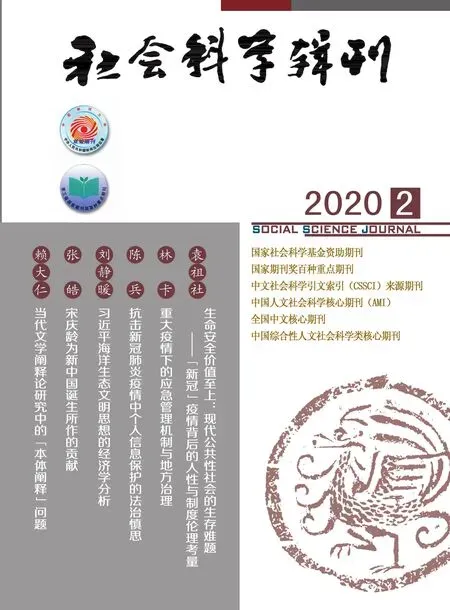明清灾害文学书写与御灾信仰的精神史意义
2020-02-21王立
王 立
灾害,是人类社会演进中不可避免的自然异常现象;应灾、御灾是人类社会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承领的巨大挑战和考验。 对灾害本身的自然科学、历史学研究,成果甚丰,与此不相称的是灾害文学书写及民间信仰的综合研究,对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史意义揭示不足,这里就较晚近的明清应灾、御灾问题试予梳理阐释。
一、视角交替:灾害叙事、文学书写及民俗信仰多维考量
20 多年来,灾害学已成为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的“显学”。 而对于更能生动形象地反映应灾、御灾行为的灾害文学以及其中蕴含的民俗记忆、民俗信仰的研究,尚处于探索中。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研究者即曾感慨我们祖先一直就有观察自然、记录自然的光荣传统:“许多史书、地方志中都有 《五行志》 《祥异》 等篇章,对许多重要的自然现象不管他们懂与不懂都记录下来传给后人。 而近代科技工作者确有数典忘祖的现象,不仅对祖先留下的大量记载轻易地斥之为迷信、非科学,而且对正在发生的一些罕见的、现代科学力量尚不能充分解释的现象也麻木不仁、不闻不问,使许多有价值的自然现象仅留下一些不伦不类的传闻。 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亟待改变!” 〔1〕其后虽有所改观,但总体看,数据汇编更偏重于灾害记录,“在灾害来临之际人类采取的救荒减灾措施方面,资料薄弱,对此的研究亦缺乏”〔2〕。 对明清灾害的民俗叙事、应灾心态、御灾抗灾意识的发掘和提炼,对灾害与灾荒作文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综合研究,更有现实针对性,有助于加强灾害学的人文化、人文精神的探讨。 〔3〕除此更应关注的是,多样态的载录模式及其蕴含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社会效应。
首先,多种文本的灾害叙事载录,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多重多维再现,更是民间信仰的集大成。对于我国的民间信仰,台湾人类学者认为:“其实我国民间宗教信仰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间固以佛道的教义为主要成分,但却包括许多佛道以外的成分,例如民间信仰中的祖宗崇拜及其仪式,就是最古老的信仰成分,比道教教义的形成早很多;其他又如许多农业祭仪,也都与佛道无关,所以说我国民间宗教是融合了佛道以及更古老的许多传统信仰成分而成,因此我们无法像西方人称某一民族的宗教为某某教一样来说明,只能称之为 ‘民间信仰’。” 〔4〕“精神史”又可称为“心智史”“文明史”,在此意在表明偏重明清下层民众内心世界为主的探讨。 灾害习俗与御灾信仰不是简单的仪式问题,而且牵涉宗教、民俗、道德伦理等一系列精神领域,其间界限往往很难分清,御灾信仰、文学叙述与民俗仪式等,都属于在现实物质存在构成基础上的精神表现。 这类语词,也往往适用于其他相关领域,如在民俗神话研究中的界定:“中国神话研究史是中华民族心智史、文明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之应当予以全面的研究。” 〔5〕在御灾、救难故事中,存在不少袁珂先生所说的“广义神话”。 因而,作为重要民俗事象的灾害及灾害叙事,也包括应灾、避灾、御灾等民族记忆的文学性描述;它们是历史实存,但伴随时间的淘洗,更多的内容不断转化为观念、习俗的对象化遗存。 因此对灾害、御灾的民俗记忆就更加值得关注。
其次,图画与新闻、文字结合,渲染了灾害的多维影响力,多种载体与御灾实践合题共鸣。图画,作为古老的纪事形式,简洁明了,形象直观,老少咸宜,具有强大的社会传播效果。 明清两朝赈灾实践、荒政及其御灾书写众多,是我国灾害学、灾害文学及御灾信仰的集大成时期;而晚清社会的灾害文学则在外来文化冲击和时代挑战面前打破旧有的文化壁垒,发生异变。 仅从我国新闻史、近代文学领域多有探讨的清末新闻画报看,其生成、导向和主题直接建构在光绪初年北方九省“丁戊奇灾” (1875—1879)民俗背景上,告灾、赈济成为其不约而同关注的主题之一,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以图像说时事,传播新知,渲染 ‘果报’ 与 ‘奇闻’,逐渐成为晚清的一大时尚。” 〔6〕据陈平原的研究,1879 年 《申报》 所刊 《寰瀛画报》 上的广告,已刊载 《中国山西饥荒出卖小儿图》。 此后20 多年间,它持续报道现实灾情,广泛介绍国内外多方面御灾、赈灾、济困经验,所载图画还大量采借此前笔记小说等文献,体现出赈灾书写与传播的跨学科性。 如光绪十八年 (1892)《申报》 副刊 《点石斋画报》 中著名的“郝连大娘” 图画,表现出兽灾降临时,民俗信仰对于舍己为人、救苦救难的善良妇女的褒扬。 图载,北方某山村妇女带周岁孩子从娘家归,值农忙惟邻家少年同行,遇群狼来扑邻子,大娘急呼:“此子不可食,是邻家倩来者。 请以我子易之!” 即投己孩于地,夺少年踉跄归家;其夫携枪赶来时,见群狼环伺,其子坐中挖土为戏。 不久,邻子采野菜时为狼所食,村人更加尊大娘为神,死后建庙祭祀,传言遇虎狼时只要大呼“郝连大娘”,必有旋风来护,其祀至今香烟犹盛。 〔7〕
画家吴友如此一新闻图画的构图场景及配图文字,当出自吴炽昌 《客窗闲话》,事实上,这一点尚未见有人指出。 按吴炽昌 《客窗闲话》 刻本序等的提示,这是图画文本生成50—70 多年前发生、传扬的故事。 而图文说明省略了开头的史传表述:“北平民郝连大之妻于氏,天性贤慧,其为人也,抑已尊人,让利趋义,故姑姊妯娌间,莫不亲爱而师事之,群尊之曰 ‘大娘’,以示不敢尔汝之意也。 ” 《客窗闲话》 原文 365 字,而此图画说明加以简化、通俗化与生动化,浓缩为190 字,言简意赅,约有原文的一半篇幅。“抑已尊人”的郝连大娘面对群狼,舍亲子而救邻子,是一种侠义的、超越伦常的行为。 但只是暂时推迟了邻子死于狼口的“宿命”,终不能从根本上“转运”,说明兽灾中人力的有限——这在虎故事中很多见;然而这种在危难面前舍却“亲子之爱” 的义举,在兽灾多发的北方民间,表达了应对凶险时的舆情褒扬,无疑有着御灾济困的现实意义。 御灾民间信仰基于“万物有灵”“兽有仁心”,饱含在地性的幸运经历,造就了郝连大娘成为旱荒背景下兽灾猖獗中的“方神”。 作为民俗传闻载体的小说、野史笔记及图画等作为媒介,藏蕴了多种灾害民俗事象、民间信仰,增强了小说史价值,并传承、延伸中出新的御灾文化价值认同。 因此,灾害民俗叙事属于灾害民俗事象的延续,也属于灾害主体及旁观者参与的动态化民俗实践。 对此,还有民俗学者如安德明据甘肃天水旱灾求雨的考察 〔8〕,万建中对东海孝妇与旱灾祈雨民俗联系的探讨〔9〕,都甚为精当。
显然,多种艺术形态的灾害、御灾呈现,图文并茂的文学书写模式,在文学、图画、新闻、民俗多个面向上各有侧重,又合力凸显了灾害的诸多震撼意义,助力了御灾过程中民间信仰观念的持续性、扩大化影响。
二、灾害张力:灾害种类及多灾叠加的审视
“灾害” (災害)是一个组合词,有灾发生,造成危害,才称之为“灾害”。 灾本作“災”,在古代多指火灾,后引申为水旱等各种灾害。 对灾害作多元性认知,有利于感受与把握灾害与被灾主体、灾害与次生灾以及多灾叠加的多重张力间性,也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于灾害存在的容忍度。
首先,种类繁多的灾害,既造就了应灾、御灾的民族经验,也展示出经久不衰的民族信仰。灾害种类繁多,层次上可分天灾、地灾、人灾;性质上有水、旱、风、雨、霜、雾、冰、雹、沙、雷电、疾病等,不同灾害间还会生成多重联系,问题更复杂且动态衔接,至今未有充分的研究。杨庆存教授就指出:“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中大量涉及自然灾害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更欠缺深入扎实的细致研究。 近些年来,虽然不乏微观层面的单篇研究成果,却很少有学者从文学角度专门进行中观、宏观的系统研究,以致专著阙如。” 〔10〕而不同时代的灾害叙事文本及文学书写,审视视角、呈现张力及社会效果各有特征,比如元代前的文本多为体制短小的诗文,元代后的文本多付之以小说戏曲及野史笔记,内容驳杂丰富,更需要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今天看来的许多粗疏、稚嫩甚至迷信、荒诞之说,从民俗记忆角度,则揭示了冰山下较为隐晦却深有精神意义的文化蕴涵。 如祭蝗神、河神、求雨等禳灾仪式,贯彻了农耕民族的民俗心理与民间信仰。 而祭祀水神以祈免水灾、驱旱魃以求雨、祭蝗神祈免害等仪式,实际上都属“农业仪式”,但又与具体化、实用化的“神灵崇拜” 结合。
其次,“次生灾” 及多灾叠加,在加重灾难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应灾机制与变通能力。 如兽灾即生态环境恶变,或旱灾、水灾、虫灾等衍发的次生灾害之一。 兽灾在民间信仰中带有“次生灾害” 的警示意义以及生物链支配下的生态保护意蕴。 荒旱往往导致野生动物不得不跑出林莽,侵入农田村落。 以往我们较为关注古人如何对猛兽勇敢抗争,甚至针对某一物种的书写可成系列,如怪牛形象体现对外来动物的不适应感,在大量驯养后仍对家畜牛的野性仍心存余悸。 尽管大多文本显示出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来看待人兽关系的,但后世没必要苛责书写者的视角与价值关怀。 伴随御兽能力增强,人兽冲突未必就要以猎取、消灭猛兽为目的和快事。 于是明清时人也想象出一些具有人性人情的“情虎”、报恩知义的“义狼”“义猴” 等形象,人兽关系有时被设想为可和谐相处,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可能变为文学书写和野史传闻驰神畅想下的可能。
以今天生态美学、动物伦理角度看,亲和动物就可能会进行“换位之思” ——人与动物平等,人们滥砍滥伐、开荒造田,侵犯了原本属于动物的领地,动物生存受到威胁,才带来了人兽矛盾的激化;而人消灭了食肉猛兽,也势必打破了生态环境中的生物链,使得牛、羊、野猪、野鹿等草食动物大量繁殖,增加植被破毁的风险,造成大规模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水旱灾害由此更加频繁,灾情因森林植被的缺少而变得更重、更难恢复。 那么,人类还要将猎兽成癖、杀虎狼为能事的描写看作是光荣和胜利吗? 生态美学先驱利奥波德,震撼于老狼垂死的眼光,认识到生态平衡对环境维持的重要:“我亲眼看见一个州接着一个州地消灭了它们所有的狼……我看见所有可吃的灌木和树苗都被吃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大海去。 ”〔11〕对人与动物、环境关系进行一种整体性思考,离不开人类作为“灾害主体” 世代反复遭受灾荒、苦难的感受、刺激、记忆与思考。 虽不能说所有自然灾害都与人类活动有关,至少,相当多的灾害是因人类过度、失控甚至有害的破坏生态行为而起。 各类灾害,如雹灾、蝗灾、兽灾、风灾、水灾、旱灾、地震 (含火山爆发)、火灾、冰雪严寒、瘟疫等,各有其种类特征,也往往有相应的民俗书写的某种程式为主导,如瘟神疫鬼、雪神滕六、雹神李左车等故事,均纽结、派生出许多应灾、御灾故事。〔12〕依据现有文献总结其中的告灾描述特征、民间信仰的具体对象、禳灾仪式场景等,更便于展示其主要特征。 当然,一些不同灾害之间(如水旱、旱蝗)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可进一步探讨多种灾害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从整体的角度讨论灾害的叠加、引发、催生、延续、扩展等一系列互动纠结的情况,以及灾害与自然界动植物的内在联系。
其三,灾害文学母题相互生发,增强受灾者间接经验以及社会“与灾共存” 的容忍度。 灾害文学母题昭示出,社会应灾、御灾的神秘信仰、仪式与想象等,如何促动朝野互动的赈济机制形成,需要总结施救一方 (地方官)与被救助一方(受灾者)的各自正反表现,也就更能全面了解冒赈、匿灾、助赈等一系列应灾态度行为的细节表现〔13〕,并推究其多重社会与文化成因。 对民众不当应灾态度的纠正与批判,先前也属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方面。 灾害带来的生存挑战与人类社会的应战,往往呈现出递进式的:各种灾害及其民间信仰的展示分析→多种灾害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应灾、赈灾经验的丰富及其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 晚清热门的赈灾新闻图画“铁泪图” 、《点石斋画报》 等告灾宣传,借用民间传闻与既有野史笔记题材,选材精当,扼要浓缩,图文并茂,言约意丰,在唤起全社会共情关注、中外人士赈灾募赈等方面,起到了多文化领域“合力” 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诸类灾害及其应灾、御灾、赈灾问题虽非灾害书写的全部,却是包含主要灾害并具有内在联系和互动整合功能的系统;许多灾害、应灾现象都不是个别孤立地发生,常常合成、转化并派生出“次生灾害” 或有效减灾。 如旱灾就易于引发蝗灾,风灾每多伴随冰雹,旱灾可能很快转成洪水,诸多自然灾害可能引发瘟疫,等等。 在民间信仰中,诸般灾害也有自身的神灵,如旱魃、蛟怪、瘟神、疫鬼等,抵御克制的一方有龙神、许真君、金龙四大王、黄大王、刘猛将、关帝等等,相关的祈神、祭祷仪式则异中有同,又同中有异。
其四,灾害虽为自然力量的具体显现,但在人与灾害的交互作用中,灾害张力特别是多灾叠加的灾害合力,其影响不仅在灾害发生的当下,更在于灾害民族记忆的遥远延伸与不尽的影响。灾害阻断正常社会生产,给人类社会造成破坏,引起禳灾和应灾、避灾等社会应激活动,许多社会正常时期一直隐伏的矛盾、问题,都在灾害降临时集中、尖锐地凸显。 如匿灾、冒赈、侵赈等一系列赈灾弊端,不仅是贪欲、权力对救灾资源的攘夺、挥霍,深层上还有“天降灾惩罪”“宿命” 等民间信仰下的心理逃避,有小农经济地方保护主义式的以邻为壑,也有好逸恶劳的伸手坐等受赈现象,以及趁火打劫的盗匪扰乱等,如《林公案》 写“荒虫” 土棍为了骗赈,逼着种田的农民结队逃荒,然后串通漕书猾吏先期赶回领赈;如 《老残游记》 中写灾民坐等馒头、拒绝转移等等惰习。 因此,进行禳灾救助民俗事项的综合汇通、多层次多角度的揭示,有助于了解古代社会中多灾合力的破坏度及其消解方式,并通过调整表达要素、选取题材以及传播效应等,强化应灾、御灾中的人文关怀。
三、多维汇通:文本书写的民俗记忆与人文关怀
灾害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如何应对灾害则不仅体现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更展示出体现出特定时代的人文精神。 就中国灾荒史而言,李文海先生在 《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害史研究》 中指出清代应是研究重点:“清代灾害极其严重,而人民群众的抗灾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的救荒机制及实际运作,也集古代荒政之大成,更加完备和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最后,迄今留下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也以清代为最多……清人所写的荒政著作,占了全部资料的百分之九十。” 清代荒政许多制度内容因袭明朝而来,这或许还与历史演进以及民族间文化交流整合有关,其中自然也涉及到主流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问题。 但就野史笔记以及各类小说戏曲等文本而言,明清展示出的文化与文学特点,是文人情怀与世俗伦理的空前融合,儒道佛多种思潮观念在此空前会通,因此,关于灾害抵御的文学与文献,构成了与多种文化、多重社会阶层相关联的特殊民俗记忆。 今天所见,绝大部分属当时人们用世情小说、神怪想象、公案实录、野史传闻等各种方式留存下来的民俗记忆材料,带有彼时更为看重的伦理情怀。 例如,明清人对某种灾害的伦理推因,就属值得关注的灾害叙事的时代特色。 有载嘉庆己卯年 (1819)杭州大火,一王姓家宅屋独存,时论称,盖因其家有“五世不以麦粉洗衣服” 的善行,载录者以农耕文化心理推度,珍惜粮食资源就可得福辟祸:
《寒夜丛谈》 云:“麦为百谷之始,所以养人之生者甚广,而世人多以之浆洗衣服,甚至裙裈足缠亦用之,云如是则耐著,且易去垢也。 今试以一家计之,每日约费麦三合,通十七省四五千万家计之,每岁共需麦四五千万石。 嗟乎! 登之则历四时,食之则遍天下,徒以区区污私浣衣之故,悉举而弃诸沟渎中,暴殄天物,无逾于此! 安得家喻户晓,而为世惜此无穷之福耶?” 此论最为明切,无如举世习惯,莫知警戒也! 〔14〕
如果说,灾害的发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受灾与否、受灾轻重,是人员伤亡还是财物损失,却部分地是可以人为控制的,那就是平日的积德行善,惜物撙节。 这与今天的提倡低碳消费实无本质的不同,都在倡扬节约资源,只不过一个是以神秘主义思维被动规制的,一个以科学理性为自觉追求。
对应灾、御灾书写的审视,会有效提高国人对灾异现象的认识。 特别是当今,需要既理性地看待明清灾害祭禳活动的迷信及其超现实想象,又应予以历史而客观地理解和评价地方官吏利用神灵崇拜御灾驱害、维护统治、安定人心的苦衷,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 有论者即指出:“在瘟疫爆发后,明朝政府重视对疫区民众的精神慰藉。 当时人们相信疫灾是神灵所降,故最高统治者在自省和整肃百官的同时,又举行各类祭祀活动,祈求神灵的宽宥。 正如明臣霍贵等人所言:‘自古帝王遇灾戒惧,未尝不以祈祷为事。 ’(《明宪宗实录》 卷86)每有大的疫情发生,明朝皇帝便派中央官员到疫区祭祀神灵。 ……以今视之,明代的祈禳无疑是自欺欺人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医疗水平落后和人们普遍相信天人感应的时代,祭祀使惊恐万状的瘟疫患者能够安然地面对死亡的威胁和失去亲人的痛楚,对安慰人心具有一定的效果。” 〔15〕
大规模瘟疫爆发之际,在有限的医疗救助条件下,能以祈禳仪式暂时性地取得疏导、安慰人心之效,其可以增加人们应对灾害的心理承受力,适当缓冲灾害造成的心理创伤,一定时段内给人以信心、恢复精神状态的勇气,无疑也属于必要而且难得。 比较而言,彼时记录者书写者的精神境界更为重要,面对反复肆虐的灾害,能抓住应灾御灾核心问题,则是观察者审时度势的能力体现。
明清小说家多数是民间观念的直接体现者,他们的贴近平民社会的白话、文言笔记小说具有鲜活、生动的人文情怀。 如明万历时野史笔记即认识到荒岁民艰,莫不以赈济、遏籴为急务:“惟无田产无职业及老幼残疾者,乃为真贫,所宜赈济。 其或户有田粮,而为他人所诡寄,或同户各房有田粮,而本身无有,又无伎艺营生者,亦为贫民,亦宜赈济。 此等事若非为政者先之劳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则有无端卖弄作弊,不惟无益,而反有害矣。” 〔16〕正是赈灾中最易发生的鉴别受赈对象时“领导力” 与“执行力” 错位的问题。 而提出的荒旱之际不许外来贩粜,“乃世俗私小之见,非公平正大之道……一言之失,弊端随起”,亦有见地,但荒政文献并未收列。
应灾中地方官员承上启下,往往是主流话语的直接传达者与践行者。 官员们言行常以日记、奏章、地方志以及募捐赈灾图画等方式留下历史印痕,这些也是富含角色特征的民俗记忆,展示灾害下的恐惧感和应灾、御灾中的种种社会伦理。光绪三十二年 (1906)成书的刘大鹏 《晋祠志》载,同治十三年甲戌 (1874)夏四月二十三夜大雨,明仙、马房两峪爆发洪水,晋祠南门外庐舍田园淹没大半,淹死人畜很多,时年18 岁的载录者亲睹惨状:“其人有母抱幼稚子女同衾而毙者,有父子昆弟同床而殁者,有夫妇姐妹同室而殂者,有覆压于倾屋败垣者,有漂流于稻畦麦陇者。 哀哭之声,惨不忍闻……一夕遂成荒墟,令人为之怅怅。” 〔17〕载录者以第一人称书写的“民俗记忆”,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伤亡数字;对灾情的形容刻画,点面结合,声容并举,行文感慨抒情,恳挚真诚。 还推测了具体成因,书写了昔盛今衰的对比给人的感受,灾难带来的震撼构成了这位清末名臣的“童年情结”。 要了解灾害体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途径,需要在资料上另辟蹊径:“寻找那些间接地、无意间揭示人们如何应对灾害的文献。 获得这类文献并非易事。 中国丰富的宗教文献可能提供相关的内容,而叙事文学和民间传说是可能利用的另外一类文献。” 〔18〕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小说,往往能切实诉诸审美效应以达到应有的警示、认知功能。
清代画家擅长以白描艺术直观地呈示其人文情怀。 新闻画图、说明文字可有效补充原生态性质材料的系统性、多维性的不足。 万建中教授指出某些“田野作业” 的偏颇:“文化人类学家一直热衷于 ‘田野作业’,正兴高采烈地高呼 ‘理解他人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无视民间文化的系统性及衍生规律,肆意攫取自己所需的材料,为重新阐释和建构理论模式服务。 民众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他们理论天平上可以任意添加的砝码。” 〔19〕这在19 世纪中叶后特别具有针砭时弊的价值,有些材料即“田野作业” 所得。 比后来才“采集” 的那些传说晚出,如 《点石斋画报》 亥集描绘光绪十七年 (1891),北通州浮桥马范庄一带灾民聚居,某隐居君子常在此观察默记极贫、次贫者。 二月二十三日他牵骡挟资来,酌情施粥给经过的饥民,见一妇衣衫褴褛,便给她一包银子,妇人以为他有歹意,将银袋掷地上掉头就走。 隐居君子慨叹:“如此贫穷还能洁身自好,实在令人钦佩! 又令人怜悯。” 女灾民的自尊,不仅“清介可风”,更反映出灾害中极其无助才抛头露面领粥的生存状态,赈灾者眼中的“极贫” 妇女,担心接受赈银带来风险,竟不顾自家已无隔夜粮断然拒绝救助,也折映出灾荒中不仅社会治安、生存状态恶化,“礼教” 杀人的舆情尤甚。 而新闻报道却只是着眼于表彰她的人格。 相传某儿科医生杨天池精于痘疹,人称“痘神”,却拒绝治一患痘小儿,小儿后来被杨弟子江昆池勉力治好,其父母酬谢时也请了杨天池,杨到场,但演剧时小儿闻锣声而死。 杨此时才“笑谓” 江曰:“此痘闻锣则死,尔未知也。”载录者认为此传言可疑:“何不戒其家禁锣而治之,必待以锣死而后言? 将曰故待其死以自喜,是为不仁;妒其徒是为不义。 以天池之拥重名,恐必不出此,此无学者傅会之耳。” 〔20〕传闻载录者都对本事抱有怀疑,藉此提出了在面对天花疫情,医术高下之名与患者生命孰轻孰重的问题。 医术高者更在于以生命为上的医德,谅不会如此无仁无义,否则何以有“痘神” 之名;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杨天池这是一种苦笑、无奈,说明了当时医治儿童天花的局限性和行医者的苦衷;至于为何不事前告诉其徒“闻锣” 有风险,是否折射了天花疫情的严重和市井舆情的复杂带来的行业内部人文生态非正常化情形,以及医者堪忧的生存状态。
文化他者的介入,可打破原有灾害思维模式与思维惯性,给应灾、御灾的生存竞争注入了尊重生命与人文关怀的精神意义,使得被灾者不再是拘泥于生命体的苟活,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有序与良性循环。 多维、细致地分析彼时灾荒济困传闻,以“他者” 眼光关注被灾者形象,发现另一面向上的的灾害心态和想象的时代真相。 据载,同治元年 (1862)夏,18 岁的日本青年纳富介次郎曾随船抵沪,亲见20 多岁穷书生带来旧时木砚台漆套出售,人们只评论价格,都不肯买。 书生对纳富介次郎哭述因灾携老母来此漂泊:“无家无业,无法糊口,到了屡屡断炊、山穷水尽的地步,求您买下这漆套吧,我好拿钱换米……” 青年提高价格买下,书生拜谢,次日又拿来一块水晶印材相赠,说归后觉得“物轻价贵,实在有负于心”,今天再加上这个抵偿;青年推辞,书生执意不肯,便收下。 介次郎感慨系之:“我佩服他的正直。” 〔21〕漂泊异乡的书生拿出家传贵重物品卖,本属无奈,却能持守内心的伦理底线,这类感人故事,成为维持人们济困救难心理动力的恒久助推能量。 故事来自东邻异邦,礼失求诸野的别样意趣更带有本真的魅力。
灾害,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恒久的存在,对灾害的感受、载录和书写却带有文明阶段、人文情怀的印记。 明清的灾害、御灾书写不论其实写、虚饰的比重如何,形诸文字后许多都带有极为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与审美意蕴,不仅体现出多维度、多层面的人文情怀,也展示出应灾、御灾的精神史意义。 古代灾害、御灾书写的文学价值,离不开其百科全书式的多学科内蕴,文体方面小说及其多种“副文本”、互文性关系,特别是对人性、审美价值的阐发,都具有丰富民族精神史建构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