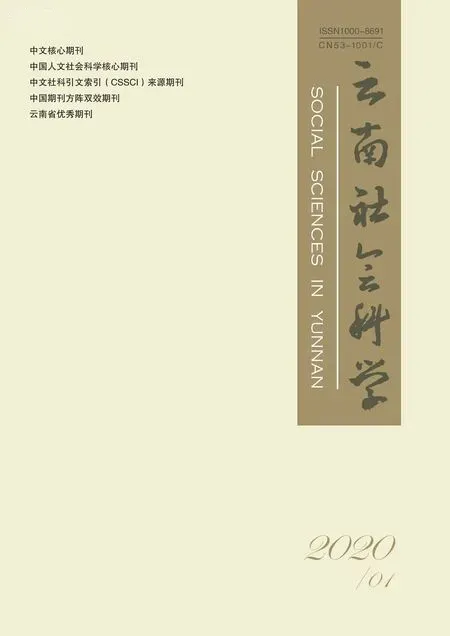再谈草场承包
——对德姆塞茨土地产权理论的修正
2020-02-20阿妮尔
阿妮尔
草场承包是中国牧区研究的焦点之一,然而,已有研究还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牧民们会接受和维持前所未有的草场承包,草场承包总是被视为既定的结果。换句话说,部分学者认为,草场承包只是一项自上而下推行的、由外部强加的政策,牧民们不得不接受草场承包,甚至承担了由草场承包带来的高昂成本。①Caroline Humphrey, David Sneath, 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达林太、郑易生:《牧区与市场:牧区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张雯:《剧变的草原与牧民的栖居——一项来自内蒙古的环境人类学研究》,《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此类观点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得通。一些田野资料表明,草场承包更多的是政府与牧民利益耦合的过程。在很多地区,一方面政府为了推进市场化、缓解草场退化将草场承包到牧业小组;另一方面,牧民们为了获得更多收益主动要求将草场承包到单户。这个现象挑战了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德姆塞茨的产权理论。虽然德姆塞茨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设立私有产权才是对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他同时指出,对于畜牧业来说,土地的共有反而是有效的。不过,中国牧民提出将草场承包到户的诉求证实了草场的共用并不总是有效的。本文通过呈现两个关于草场承包的案例,试图回答为什么牧民们会接受,甚至拥护草场承包的问题,以此修正德姆塞茨产权理论的不是之处。
一、草场承包的新故事
198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第三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全区旗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畜草双承包”责任制改革,在“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同时,实行“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的政策。②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主编:《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与牲畜作价归户不同,在很多地区,草场并不是一开始就承包到户的,草场承包主要有三种形式:承包到单户、承包到联户、承包到浩特或独贵龙(分别为蒙古语hot、dogoilang,意为牧业小组)。本文主要关注将草场承包到浩特或独贵龙的情形。
任何一项政策的落实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互动的影响,草场承包也不例外。草场承包是政府与牧民在互动过程中共同选择的结果,包括政府根据牧民们的反应调试政策、牧民们根据政策安排调整与其他牧民的关系、以及向政府提出诉求,等等。下面以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吉日嘎朗苏木(为保护报道人隐私,该苏木名称为化名)和青海共和县黑马河乡为例,展现草场承包的具体过程。
(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吉日嘎朗苏木
吉日嘎朗苏木的前身是公私合营的吉日嘎朗牧场,1970年转由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并成为国营牧场。197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吉日嘎朗牧场移交给锡林郭勒盟农牧场管理局管理。
1983年底,“畜草双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全区推行开来。由于草场承包只在苏木体制内推行,国营牧场不在政策覆盖范围内,因此在实行承包制改革的前两年,吉日嘎朗牧场只分了牲畜,没有分草场。这引起了该牧场牧民们的不满。他们看到周围苏木乡镇的牧民都分了草场,觉得分到草场就多了一样“资产”。于是,该牧场向锡林郭勒盟农牧场管理局提出申请,将吉日嘎朗牧场改为苏木,实行草场承包政策。不过,锡林郭勒盟农牧场管理局起初没有批准该申请,随后该牧场的领导和牧民多次到自治区政府反映情况。在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该牧场的申请才予以批准。1985年,西乌旗党委印发将吉日嘎朗国营牧场改建为苏木的请示报告,将吉日嘎朗牧场改为苏木体制,下设5个嘎查,启动草场承包制改革。
起初,西乌旗政府决定,将吉日嘎朗苏木的草场承包到独贵龙。独贵龙相当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一般由5至7个成员户组成,同属一个独贵龙的成员户有的一起游牧,有的分开游牧。然而,成员户之间却开始出现矛盾。只要他人的牲畜跑到附近草场上来,牧民就会把这些牲畜赶走,甚至与这些牲畜的主人产生争吵。经过两三年,成员户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于是,牧民们要求将草场承包到单户,明确各户间草场的边界,以期减少纠纷,这个诉求与政府将草场逐步承包到户的政策目标相一致。1990年,西乌旗实行第二轮草场承包,在吉日嘎朗苏木取消了将草场承包到独贵龙的形式,直接将草场承包到了单户。
在吉日嘎朗苏木的案例中,牧民们两次提出草场承包的诉求。第一次是为了获得草场这份“资产”,要求实行草场承包。可见,即使草场承包是自上而下推行的,这些牧民却很欢迎草场承包政策,更准确地说,他们很向往草场使用权的私有化,甚至为此多次到自治区政府反映情况,申请解散国营牧场,因为牧民们对草场承包的诉求不仅具有合法性,也符合他们的利益。第二次是牧民们为了在独贵龙的范围内尽量为自己多占些草场并减少由此产生的纠纷,要求将已经承包到独贵龙的草场进一步细分到单户。将草场承包到独贵龙后,游牧直径从相当于两个嘎查的分场范围缩小到牧业小组范围,即从60-70千米缩小到10-15千米。同时,牲畜的作价归户和市场化的推进驱使牧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牲畜头数增速迅猛。1990年,内蒙古自治区牲畜头数达到5307.43万头,与1985年相比,5年间增长了千万头。①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主编:《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于是,草场变得拥挤,甚至成为稀缺资源,多占草场就意味着可以多放牧牲畜,赚到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牧户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博弈,而非合作,出现了驱赶他人牲畜的情况,纠纷频发。可见,牧民们没有像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寻求集体行动②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而是要求将草场细分到单户,明确各户草场边界,各自经营草场,避免纠纷的发生。
(二)青海共和县黑马河乡
王晓毅研究员在《公共管理模式有利于草原生态平衡》③王晓毅:《公共管理模式有利于草原生态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10日,A08版。一文中讲过一则非常有趣的案例。青海共和县黑马河乡在刚开始实行草场承包政策时,由于牧民们不愿将草场承包到单户,便把全村牧户分为11个牧业小组,将草场承包到牧业小组。在一些牧业小组中,成员户间是独立经营的。然而,由于经营状况不同,成员户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出现了多畜户、少畜户,甚至无畜户。多畜户占用的草场自然要比少畜户、无畜户多,造成草原利用的不平衡,这引起了少畜户和无畜户的不满。为此,小组内部制定了一套补差制度:每年特定时间由小组领导清点每个成员户的牲畜头数,商定补偿数额,由多畜户给予少畜户和无畜户相应的补偿,组内补偿通常低于草场租金。
对于组内补偿为何会低于草场租金的问题,王晓毅研究员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小组成员户之间都是熟人,很多还是亲戚,碍于情面要价较低;第二,如果将草场承包到单户,特别是出租草场,就需要建造网围栏将彼此的草场分隔开,这对于当时的牧民们来说价格十分高昂,因此他们通过压低组内补偿的方式维持现行制度;第三,如果将草场承包到单户,牧户虽然可以通过出租草场获得更高收入,却很难做到有效监督,草场就会遭到滥用,但若继续维持牧业小组,使用补差制度,成员户之间就可以相互监督和制约,防止过度放牧的情况出现。
在当地一些牧业小组中,这项补差制度至今还在良好运行,然而,另一些牧业小组的成员户却并不喜欢,之后进一步把草场细分到了单户。究其原因,一方面,有些多畜户的畜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超过了牧业小组草场的承载力,需要租赁更多的草场;另一方面,由于组内补偿较低,有些无畜户希望把草场细分到单户后,通过出租草场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在黑马河乡的案例中,很多牧民逐渐从不支持将草场承包到单户变为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当然,牧业社会一直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乌珠穆沁旗草原为例,据当地老人回忆,吉日嘎朗苏木所在地区是一片富庶之地,在1949前,不少富户的畜群多到要以洼地为单位计数,还有些人家的牛、马数以万计。在富户周围,一般会集结十个左右的附属贫户,这些贫户带着自己少量的牲畜为富户放牧、挤奶,以此获得富户些许牲畜的皮毛奶肉。那么,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何让黑马河乡的一些牧民转而寻求草场使用权的私有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将草场承包到独贵龙后,可供畜群游走的草场范围缩小了,多畜户和少畜户、无畜户之间草场利用不平衡的问题被放大了。随着牲畜数量的不断增多,这个问题变得异常棘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这些牧民市场化程度变得越来越深。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即出租或租赁草场的形式,解决草场资源配置的问题,这会让他们获得更多收益,而不是继续依赖组内补偿等非市场化的手段。换句话说,在草场变得稀缺的情况下,只有追求草场的市场价值才会使牧民的收益最大化。
二、德姆塞茨土地产权理论概述
在当今牧区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基于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理论模型探讨草场承包政策的合理性。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学派对“公地悲剧”现象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就在哈丁发表《公地悲剧》一文的前一年,产权学派的先驱人物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以《通向产权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①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No﹒ 2 (May 1967),PP﹒ 347-359﹒一文,对“公地悲剧”问题进行了精彩的经济学分析。德姆塞茨认为,如果实行土地的共有产权,个体使用土地的成本并不完全由使用者承担,而是摊派到所有共同体成员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体就会滥用土地,导致环境恶化。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共同体成员间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规范共同体成员使用土地的行为,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确保协议的效力。然而,这在谈判和监察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该成本往往非常高昂,以至于协议无法达成,就算达成了协议,也很难执行到位。因此,土地的共有产权总是会导致共同体成员过度使用土地,不利于土地的持续利用。在德姆塞茨看来,只有私有产权才会有效保护土地。在实行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使用土地的成本就会集中在使用者身上,原来分散的外部成本就被内化了。这在激励私有者实现现期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私有者考虑长期成本收益,合理使用土地,自觉地保护环境。总之,在德姆塞茨看来,土地的私有产权优于土地的共有产权。
不过,德姆塞茨指出,这个结论存在一个例外。他认为,虽然土地的共有产权往往会造成对土地的滥用,但对于畜牧业来说,草场的共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经济。他通过对比西北部印第安人和西南部印第安人的土地产权问题来说明这一点。他在人类学家的田野材料中发现,在西北部以狩猎为生的印第安人当中产生了土地私有制,但在西南部从事畜牧业的印第安人当中却没有。他提到,17世纪中期以前,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一直通过在森林中狩猎获取肉食和皮毛,维持生计。然而,皮毛贸易的兴起使皮毛价值猛涨,打猎规模也随之扩张。没有人再去考虑增加或保持动物存量,大家只顾着自己如何最大限度地猎取动物皮毛,导致打猎行为的外部成本迅速攀升。为了遏制过度狩猎的现象,西北部的印第安人逐步发展出了以家户为单位划分狩猎区域的土地私有制,由此内化了打猎行为的外部成本。如果哪个家户过度狩猎了,皮毛动物被捕杀殆尽的后果只能由他们自己负担,而不会影响其他家户。每个家户在狩猎区域中又分出了几个次级区域,每年在不同的次级区域轮流狩猎,并且留出禁猎区域,保持动物存量,以防过度狩猎。即使划地需要一定的成本,但皮毛贸易有着巨大的利润,使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完全担负得起这笔费用。
相比之下,在从事畜牧业的西南部印第安人当中却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德姆塞茨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牲畜有着游动的习性,不受人为限制,总是闯入他人的草场。这就要求生产者额外投入对牲畜的监察成本,用于维护私人草场,而且监察成本并不低,因此牲畜游动的外部成本无法通过私有产权内化。再者,牲畜的商品价值相比皮毛动物要低很多。高成本低收益使草场私有产权的建立成了无利可图的事。西北部印第安人之所以发展出了土地私有制,是因为皮毛动物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将打猎范围限定在较小的地块就不需要太多成本,加之皮毛价值高昂,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由此,德姆塞茨表示,土地的私有产权并不总是最优的,对于畜牧业来说,草场的共有产权才是合理的安排。换句话说,在德姆塞茨看来,土地的产权安排主要是由产业决定的,畜牧业与农业、狩猎业等产业不同,土地的私有产权对其不适用。
三、对德姆塞茨土地产权理论的修正
德姆塞茨的土地产权理论相较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模型更为新颖和丰富。
第一,德姆塞茨只提到,畜牧业实行土地的共有产权会降低个体对牲畜的监察成本,却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共有产权会不会使共同体内部谈判和监察成本攀升的问题。在对农业和狩猎业土地产权安排的分析中,德姆塞茨强调了谈判和监察成本过高是农业和狩猎业无法继续维持土地共有产权的重要原因;但这在对畜牧业土地产权安排的分析中却被忽略掉了。或许德姆塞茨认为,由于草原宽广辽阔,共同体中的不同个体在放牧时不会相互影响,因此不需要谈判和监察成本,或谈判和监察成本很低。
然而,上述吉日嘎朗苏木和黑马河乡的两个案例表明,对于畜牧业来说,谈判成本有时会非常高昂。在将草场承包到牧业小组后,吉日嘎朗苏木的牧民之间因草场使用的问题不断产生纠纷,使谈判成本大大增加。黑马河乡的牧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使他们为此发明了补差制度,试图弥合由贫富差距的拉大所引发的矛盾,但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当地牧民更倾向于选择收益更高的市场化的手段,要让他们继续使用非市场化的手段需要极高的谈判成本。在谈判成本急剧攀升的情况下,解散牧业小组、将草场使用权私有化变得有利可图,吉日嘎朗苏木的牧民可以免于纠纷困扰,黑马河乡的牧民便会通过草场的流转,扩大畜群规模或收取较高的租金。因此,将草场承包到单户成为两个案例地牧民一致的诉求。
可见,畜牧业并不完全像德姆塞茨想象的那样,总是拥有充足的草场。近几十年来,大多数国家都在推行或已经实现了游牧民的定居化,并不断缩小放牧范围。以内蒙古为例,自治区政府于1951年开始在牧区实行定居游牧政策。政府一方面引导牧民搭建简易棚圈,用来在冬春两季御寒抗灾,实现了季节性的定居。同时,初步划定冬春两季的草场,防止牧民过早地转场,使“自由放牧”逐步转变为有计划地利用草场。另一方面,在夏秋两季,牧民们仍旧以盟旗为界从事游牧生产生活方式。①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主编:《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1953年,政府又进一步推行定居移场放牧,草场以及打草场被逐步划分到合作社以及国营牧场、公私合营牧场等单位。②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主编:《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第106页。人民公社化后,政府将草场收归集体所有,并且由生产大队向生产队划拨草场,确立生产队的草场边界,放牧和饮畜都必须在生产队范围内进行。启动草场承包政策后,草场又被承包到几户组成的独贵龙,甚至承包到单户。就吉日嘎朗苏木的情况来看,即便在人民公社解散后承包草场前的一段时期,吉日嘎朗苏木的牧民在夏冬季节还会到邻旗游牧,其游牧直径在夏季和冬季分别达到了60千米和70千米左右。然而,草场承包到户后,每户畜群的游走直径缩短到2-5千米上下了。因此,这些牧民提出将草场承包到单户的诉求不仅是出于对草场使用权私有化的向往,政府对游牧的限制造成草场稀缺也是其重要原因。
第二,土地的私有产权同样可以在畜牧业中得到有效实行。在牲畜的商品价值依然低于皮毛动物的情况下,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畜牧业大国的牧场不仅拥有广阔的私有土地,还大规模地建设了网围栏,将各自的草场分隔开,把草场划分为不同区域。这说明,将广阔的草场私有化的成本并不总是高昂的,而是相对的,取决于网围栏建设后的成本收益率。
上述两个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在这两个案例地每户草场面积远远没有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牧场大,但牧民们依旧建设了网围栏。张雯等学者认为,网围栏的建设和维修费用过高,为牧民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③张雯:《剧变的草原与牧民的栖居——一项来自内蒙古的环境人类学研究》,《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然而,网围栏其实可以为牧民减少劳动力投入,具有一定投资回报率,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首先,网围栏的建设可以减少为避免纠纷而产生的劳动力成本。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如前所述,草场被承包到牧业小组后,成员户间渐渐因草场使用问题产生了纠纷。由于谈判成本过高,牧民们提出草场承包到单户的诉求。草场被承包到单户后,很多牧民并没有立即建设网围栏,而是按照政府划分的草场边界,紧跟着畜群放牧,以防畜群超越边界与邻户产生纠纷,这让牧民付出了比平时更多的劳力。一位20世纪90年代在吉日嘎朗苏木当羊倌的报道人讲,因为当时网围栏还没有普及,她就要一直跟着畜群在外放牧一整个白天,不能离开畜群太久,午饭时只能匆匆忙忙赶过来,跟早餐差不多,只能喝上几口奶茶,好一点也就是把煮过的牛羊肉或血肠割下来放到奶茶里热着吃,这样可以快些吃完赶紧出门放牧,直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到家吃到正餐。在建设网围栏后,牧户间的草场边界变得更加清晰,网围栏可以较大程度地阻止牲畜跑到他人草场上去,这样牧民就不必紧跟着畜群、担心引发邻里纠纷了,节省了一部分劳动力成本。
其次,牧民们通过建设网围栏,转变原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游牧是非常辛苦的,牧民不仅要花费很多时间放牧畜群,还要不断迁徙,寻找水草丰美的牧场。网围栏的建设使牧民转向暖季散养和冷季喂养相结合的生产模式。牧民将打草场单独围封起来后,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可将畜群置于剩余草场上吃草,白天出去看两次羊群,让羊群早晚饮两次水就可以了,晚上羊群不用赶回来,就地休息。冬季就将羊群关在棚里,提前刈割打草场里的草,每天早上喂一次干草就好了。马和牛向来不需要人紧跟着,放牧方式倒是没什么变化,白天任其游走,傍晚将马群和牛群赶到一起,聚集在家附近即可。到了夏季,傍晚把牛犊赶回来关在棚里,和母牛隔开,以便第二天挤奶。也有些牧民将自家草场用网围栏分割成四季草场,不同季节将牲畜赶到不同草场上,不仅更方便看守,还有利于草场保护。
当然,网围栏的建设费用和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取舍是需要衡量的。以吉日嘎朗苏木的牧民为例,他们是在2007年左右大规模建起网围栏的,谁先建谁出钱,不会与邻户分摊费用,一般来讲每户会建造一至两排的网围栏。当时,网围栏的价格在1元/米左右,铁杆10元/根,每隔三四米立一根铁杆,而且还需要专人修建,每百米收取60元劳务费。如此一来,每个牧户至少要修建上千米的网围栏。当地牧民莫日根④为了保护报道人隐私,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作了化名处理。告诉我,他为其3000亩的草场建网围栏花费了2万左右,而他当年毛收入为6万左右。虽然网围栏的建设费用大约占据了当年收入的1/3,然而,如上所述,由此可以减少今后多年的劳动力成本,让牧民享受更多的闲暇。对于雇主来说,则可以通过建造网围栏,向羊倌支付更低的工资。因此,从长期来看,牧民建设网围栏是会获得较高收益的。
第三,德姆塞茨没有在关于畜牧业的土地产权理论中引入对环境成本的考量。依据德姆塞茨的土地产权理论,在农业、狩猎业等产业中,产权安排决定了土地是否会遭到滥用,然而,德姆塞茨却没有回答畜牧业会不会产生“公地悲剧”的问题。对草场的不当利用会使环境成本变得十分高昂,进而导致收益缩减,而这与土地产权安排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从当今牧区的案例来看,对草场使用权的私有化加剧了草场的退化。草场承包造成了草场的细碎化,使牲畜难以游动,草场遭到过度使用,使环境成本攀升,收益受到严重影响。
很多学者据此认为畜牧业存在“私地悲剧”,即土地的私有产权会使草原生态遭到破坏,从而否认畜牧业实行土地私有产权的有效性。①敖仁其:《对合作放牧制度的实证与理论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6期;张雯:《自然的脱嵌——建国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环境成本是可以通过草场产权交易得到解决的。以内蒙古为例,自治区政府在1990年代发放《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后,开始建立草场流转市场。2006年,自治区政府重新修订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文件,规范草场流转市场,草场流转的规模逐渐扩大。尽管政府推进草场流转的目的是为了使草场达到满载,提高牲畜出栏量,然而,一些牧民基于此做了相应的创新,即通过草场的流转在多片草场间实现轮牧,缩短每个草场的使用期,使草场得到休养和恢复,以此保护草场。这些牧民的游牧实践表明,环境成本是对畜牧业生产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将环境成本纳入其中后,畜牧业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依然是有效的。
四、结 论
基于当今牧区的草场承包政策实践,本文得出了两点相互关联的结论。第一,即使草场承包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牧民不欢迎草场承包。吉日嘎朗苏木的草场承包就是当地牧民通过多次申请后得到的;草场被承包到牧业小组后,吉日嘎朗苏木和黑马河乡的牧民都提出了将草场进一步承包到单户的诉求。牧民们的诉求与政府推进草场承包的政策进程相一致,草场很快被承包到了单户。如果说政府实行草场承包的目的在于推进市场化、避免“公地悲剧”,那么牧民提出将草场承包到单户的诉求则是对草场使用权私有化的向往和草场稀缺二者合力的结果。因此,草场承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由外部强加的政策,而是政府与牧民利益耦合的过程。
第二,上述两个案例表明,德姆塞茨的土地产权理论不仅在有关畜牧业的讨论中忽略了谈判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且没有认识到畜牧业实行土地私有产权也是有效的。德姆塞茨很难得地对畜牧业的土地产权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过他的观点还不足以概括所有畜牧业的生产形态。在德姆塞茨看来,畜牧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无法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然而,不管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牧场,还是中国内蒙古、青海等地的牧区,都是对其反驳的例证。首先,虽然与农业、狩猎业相比,畜牧业需要更为广阔的土地,但对畜牧业来说土地也不总是充足的,这很容易导致谈判成本攀升,使土地的共有产权变得无效。其次,尽管畜牧业一旦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会产生诸如建造网围栏等较高的维护成本,不过从长期来看,作为生产性投入,它也会带来一定收益,甚至高于其成本,由此产生利润。再次,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后,草场产权交易还会降低由土地细分造成的环境成本,提高畜牧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率。因此,不管从经济生产还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讲,畜牧业实行土地的私有产权都是有效的。这两点结论正是被当今很多牧区问题研究者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