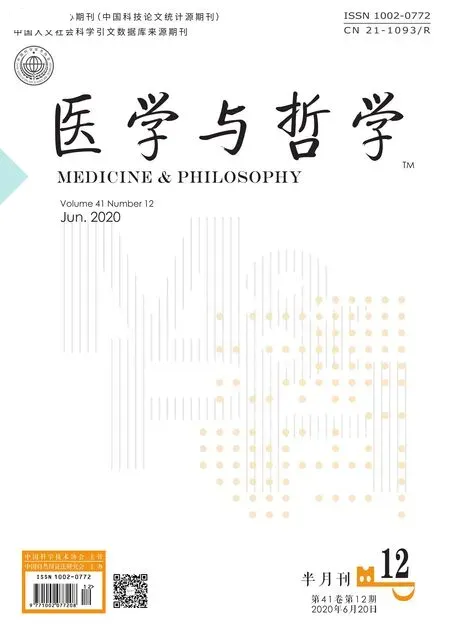安宁镇静在存在性痛苦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2020-02-16王继超翟晓梅
王继超 翟晓梅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老龄化的加剧,生命末期生存质量与死亡质量受到了来自医生与患者,乃至社会公众更强烈的关心。由临终关怀(hospice care)发展而来的缓和医疗[1](palliative care,旧称姑息医疗,或称安宁疗护,以下简称“PC”)在这样的背景下蓬勃发展并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2]。PC倡导由“以专科医生为中心的多学科背景团队进行全人照护”的理念[3],世界卫生组织肯定PC是整合性的、以人为中心的健康服务的关键部分,而且“没有什么是比救助人们的痛苦(不论是躯体的、心理的、社会性的还是灵性的痛苦)更以人为中心的了”[4]。PC的目的可以被总结为根据患者的意愿尽可能地减轻痛苦和提高生命质量[5]。在PC的情景中,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借助先进的护理辅助工具和依靠药物的合理使用,PC在缓解患者的躯体性痛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如何恰当且有效地处理晚期和渐进性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存在性痛苦(existential suffering,ES)成为了新的严峻挑战。
1 ES的概念
在我国积累生命末期照护经验的过程中,如何为患者提供更有人文关怀的照护越来越受到关注,PC团队在临床经验中发现终末期患者会因为对一些问题的关心和担忧,感到痛苦,并产生焦虑、抑郁、烦躁不安等痛苦症状,有时这些症状会过于严重,影响到患者整体的生存质量[6-7]。这些问题可归入自由、孤独、无意义、死亡四个主题[8],它们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被认为是人的存在的核心本质问题[9]。因此,这些问题被称为存在性问题,由这些问题引发的痛苦被称为ES。从概念上去认识和理解ES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痛苦本身是一种主观体验,人们只能基于自己的经验,结合痛苦者的表现和对痛苦的描述去试图理解别人的痛苦。痛苦的这个特点,使它很难被当作一个客观对象去认识;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性概念的抽象性,“存在性”并不像“存在物”一样可以被直观认识,理解ES的“存在性”需要了解一定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不是物质世界的生理(躯体)疼痛(physical/somatic pain),也不是精神世界的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disorder)或精神病(mental disease)。虽然ES的“存在性”也有“真实存在”这层含义,但它不是仅指真实性,它还指人的存在(being)的内在属性,即创造性[10]、规定性和局限性[11]。
一项综述研究显示,ES和灵性痛苦在多篇文献中是作为可相互替换的词语使用的,而且意义混在一起[12]。这一方面表明在一段时期内,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两个词就是同义词或在所指含义上有相当大的重叠,另一方面也表明二者之间虽然关系密切,却又有所不同。后续的研究澄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6]。灵性痛苦可被定义为由于灵性或宗教关切而造成的痛苦,可被归为ES的一种类型。ES所关心的主题及其引起的感觉,是普遍化的,并非追求某种信仰的人所独有的[13]。
ES和灵性痛苦在临床上可以区分,而且有必要区分,因为一些有ES的患者可能不认为自己有灵性需求,如果临床医生建议患者咨询神职人员,患者可能会感到不安;灵性对于不同的个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但相同的是,有灵性需求的个体都会产生加入团体或组织的需要;灵性是每个存在性领域的一部分,然而,它并不包含每个存在领域的所有方面。因此,所有的灵性痛苦都是ES,但并不是所有的ES都是灵性痛苦。区分ES和灵性痛苦的目的是为了识别患者的需求,选择相应的处理方法,对症状的难治性做出准确判断。
2 处理ES
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能会经历ES,但通常不会严重到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性,因此,不需要医学干预,可以通过自身的思想、行为调节来处理。在特殊情况下,由于意识和物质、身心的相互作用,ES可能会严重到引起身体上的健康问题,出现症状表现。同样,身体的健康问题也可能会引起ES,特别是在疾病晚期,严重的ES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这时患者就需要医学的帮助来处理ES了。
心理学可以为ES提供许多有效的干预方法,如以意义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法、认知行为干预、催眠促进疗法和心理教育咨询等。但在ES显示出难治性时,安宁镇静(palliative sedation,PS)将是最后一种可以有效解除患者痛苦的方法[14-15]。它通过对患者实施镇静,降低患者的意识清醒程度,来使患者不再感受到痛苦[16]。PS不是指在PC中使用的镇静(sedation in palliative care),而只是在PC中使用镇静的诸多情况中的一种。它也不同于为使临终患者在安静平和的状态下离世而实施的末期镇静(terminal sedation)。如果镇静不是有意实施的,而是为症状的处理合理地应用具有镇静特性的药物,产生非故意的镇静后果,那么只是发生了继发性的镇静作用[17],不是实施了作为治疗方法的PS[18]。例如,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激越性谵妄,会有继发性镇静作用,此时,镇静是非故意的后果,应与使用镇静药物有意诱导致嗜睡乃至昏迷相区别。
尽管ES在我国的生命末期照护相关文献中是相对陌生的概念,但在我国也有使用PS处理生理疼痛合并ES的病例报告[6-7],也有医生在关注终末期患者的PS治疗时关注到了处理ES的伦理问题[19]。将PS用于处理ES(PS-ES),虽然在科学上是有效的,但在伦理上却存在争议,给临床决策带来困难。了解这些伦理争议,可以为PC团队与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有益于实质伦理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
不论痛苦的来源和类型,痛苦症状都会在临床中得到关注和响应,但对某一疾病或症状应当采取何种医疗干预措施,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在痛苦症状的常规干预和标准治疗药物失败时,采用PS可以达到控制症状和缓解痛苦的目的,但仅凭有效性难以为这一方案提供充分的支持。不同于对某种症状使用有镇静作用的常规治疗药物,镇静是可预见但无意导致的副反应的情况,PS有意地通过降低患者意识程度的方式来使患者对痛苦不敏感,这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引起了许多伦理争议,这些争议一部分围绕PS作为治疗手段本身的合理性,即PS是否违反义务,带来坏的后果;另一部分围绕PS-ES作为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即PS是不是处理ES的合理手段,PS-ES不能得到伦理学的辩护的理由是什么和能得到伦理学辩护的条件是什么。
3 PS提出的伦理问题
PS作为治疗手段本身的合理性是PS-ES作为治疗方案的合理性的逻辑前提,因此,在研究PS-ES提出的伦理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PS提出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痛苦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是否有义务承受痛苦?对痛苦的理解影响着人们对PS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人需要经历痛苦才能成长和完成自我,人应该依靠内在的成长去化解ES,而不是通过逃避来解决它,因为解决存在性问题比逃避痛苦更重要[20]。对立观点认为,痛苦不具有意义,痛苦单纯地只是人们应该避免,且有权利要求避免的体验。另一种观点认为,痛苦作为一种个人体验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都赋予痛苦重要的意义,但如果将哲学上对痛苦意义的肯定作为指导医疗实践的准则是荒谬的。人在对痛苦的反应中塑造自身,借助医学干预来克服痛苦正是人对痛苦的极具人性关怀的反应。不是痛苦的价值要求人们放任痛苦、忍受痛苦,而是人们对痛苦的反抗使痛苦具有价值。关于痛苦价值的观点间的冲突可通过尊重原则化解,不同立场的人们可以互不干涉,尊重对方各自的选择。没有理由将第一种立场中的价值观强加给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即使痛苦确实具有观点一所声称的作用和意义,尊重自主性的价值也有后果论的理由被认为比痛苦的价值更重要。
第二,PS是对痛苦的治疗还是对患者大脑意识功能的伤害?是否违反了医生对患者的义务?一种观点认为,PS虽然能使患者免于感受痛苦,但并不是对痛苦的治疗,因为造成痛苦的原因没有被纠正,反而是人正常的意识能力被破坏了,这违反了医生对患者的不伤害义务[21]。另一种观点认为,当痛苦严重到令人难以忍受,且没有其他干预手段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痛苦的时候,意识则不再使人受益,此时医生符合患者自主意愿地为患者实施PS是履行了医生维护患者最佳利益的义务。
第三,如果PS需要持续性深度镇静直至死亡才能使患者免于感受痛苦,这样做是否等于把患者变成了“活死人”,或对患者实施了“慢性”安乐死?有学者认为,在终末期患者身上使用PS来企图消灭所有痛苦导致了人脱离其自身和其所在的环境,使人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活死人”,本质上使他在社会属性意义上已经死亡[22]。反驳的意见认为,活死人的概念是荒谬的,人总是不能时刻发挥他全部的潜能,深度睡眠中的人和婴儿的意识水平也是低的,在低意识水平下活着也是活着,PS中的患者并没有丧失全部的社会联结,与家人和照护团队的人际联系使患者在社会属性意义上也是活着的,应得到尊重和善待。有观点认为安乐死的概念内在地反对“慢性”,因为死亡过程如果被拖延就不符合“安乐”的含义。PS和安乐死在定义和操作上都有着界限分明的差异。不同的观点认为,PS和安乐死在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为患者解除难以忍受的痛苦,在策略上也相近,都是消除不了痛苦就消除感受痛苦的能力,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方法,一个用了镇静,另一个用了死亡。PS曾被认为会加速患者的死亡,也是导致认为PS就是“慢性”安乐死的原因,但后来的研究证明PS不会加速患者的死亡。
第四,PS的适应证是难治性痛苦症状,但难治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难治性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指尝试了多种干预方法仍然久治无效。但是否要穷尽所有已被证明有效的干预方法,还是仅经过那些对患者可及、可获得、可负担的干预方法就能确定难治性是有争议的。患者的意愿是否应影响对难治性的判断,如果患者拒绝其他所有的干预方法,就判断症状具有难治性——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治疗了,这样做似乎是在做不负责任的逻辑游戏,但在选择治疗方法时又应当尊重患者的意愿,这里似乎有一个伦理困境需要解决。
第五,如何保障PS不是由于比其他治疗手段的陪护成本和经济成本低而被强加于患者,以维护患者的自主性和最佳利益?在处理ES时,使用PS与使用生理治疗、心理治疗和精神护理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相比更便宜[23]。这可能导致人们在面对复杂情况时会更愿意接受PS[24],也容易导致死亡过程极端医学化[25]。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可能会被诱惑去控制患者生活的每一个方面[15]。一些营利性的临终关怀机构可能试图通过提供不太全面的护理服务、节省人力资源和根据患者的缴费潜力选择患者来创造收入[16]。因此,PS对他们来说可能相当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因此,如何维护患者的自主性和最佳利益就成了PS应用中需要特别仔细考虑的问题。
4 PS-ES提出的伦理问题
关于PS-ES的伦理讨论主要围绕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首先,既然PS的适应证是难治性痛苦症状,那么合理地应用PS是否有必要区分引起难治性症状的痛苦的类型?对哲学上身心关系问题的不同看法会导致对PS-ES持不同的意见,有两种互相冲突的立场。身心二元论者认为PS用于处理与精神或非生理顽固性症状有关的痛苦,心理上的痛苦、生存和精神上的痛苦等,是一种不适当的和无效的干预措施,心理治疗和精神护理才是对非生理性痛苦的更恰当的干预措施。身心一元论的立场挑战心灵-身体的双重性,并主张人的整体观念。这一视角导致拒绝承认多种不同类型的痛苦,认为任何一种痛苦对人的影响都是全面的、整体性的,身心二元论会导致身体还原论,将症状和痛苦区分开会使痛苦的涵义被消解,但并不能改变痛苦的存在。是否区分痛苦的类型对考虑ES的难治性会产生影响,因为这决定了断定症状的难治性前应该尝试的治疗手段的范围。
其次,虽然解除痛苦是医学的目的之一,但解除ES是否超出了医学的边界?有一种观点认为,PS-ES是对镇静药物的滥用,因为医学的目的是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而非解决一切痛苦。质疑医学是否应该干预ES的理由是,人会遭受各种各样的负担、失望、失去带来的痛苦,这些痛苦不是医学应该治疗的对象,医学应该仅为那些由于健康损害而引起的痛苦提供干预。也有人主张PS-ES是合理的,医学应该尽可能地为患者提供帮助,PS能帮助患者缓解ES,而且可以帮助受ES折磨的终末期患者追求安详的死亡,因此PS-ES符合医学的目的。虽然ES不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会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医学出于缓解痛苦和促进、维护健康的目的,有必要对ES进行干预,设法缓解或消除ES。即使仅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理解健康,当ES表现出严重的症状,威胁到人的正常活动(如睡眠,进食等)时,控制这些痛苦症状也会成为医学维护健康的必要内容。
医学不能回答存在性问题,但医学可以向有ES的人提供一种缓解痛苦的帮助,当这种帮助给患者带来的受益大于风险时,才是伦理上可允许的。对医学目的的理解解释了为什么PS-ES在一定条件下是可允许的,甚或是应当的,也解释了为什么PS-ES只有在PS是ES的患者能够寻求的唯一帮助时才能够在伦理上被接受。
再次,由于意识对人的意义,如果在ES没有严重到它本身已经损害了患者正常的意识功能时就实施PS,是否因对患者造成的伤害大于给患者带来的受益而不能得到伦理辩护?如果ES已经严重到损害了患者的意识功能,也就损害了患者的自主性和知情同意能力时,患者是否就失去了决策权?患者预先表达意愿或授权代理决策能否合理地解决这个困境?根据经典效用论,PS-ES会带来的好结果是痛苦症状得到控制,坏结果是意识受到抑制,使人不再获得意识清醒带来的受益。因此,有学者认为,只有意识被症状完全侵蚀,患者的意识除了体会痛苦不能发挥其他任何意识所具有的作用时,抑制意识才是允许的[26]。但是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受到严肃的挑战,即PS-ES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痛苦症状得到控制,意识受到抑制是获得这个结果的手段而非另一个结果。
最后,考虑PS-ES的临床决策过程中,应该依据哪些条件和标准做出符合伦理的选择?调查研究显示,医生对PS-ES的看法尚未达成共识,临床实践多样[27-28]。家属和照护者对PS-ES也有伦理方面的担忧[29-30]。多个关于PS的临床指南,都认为PS可以用于处理ES,但因其伦理争议和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PS-ES需要非常谨慎,应当经过临床伦理委员会的咨询[31]。但是,这些指南没有给出要对PS-ES做出一个合适的临床决策,在伦理方面应该考虑的要素。大多数医生认为应用PS的必要条件是症状的难治性、进入临终阶段和患者的主动请求[32]。临床伦理学的论证[33]为考虑一个合适的临床决策提供了帮助,建议从适应证、患者意愿、生存质量和社会因素四个方面来考虑决策。能够得到伦理支持的PS-ES应该与其他医疗干预一样遵循医疗实践的规范性原则[30],从相称性、恢复性、整体性、适度性和审慎性五个方面来规范PS-ES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