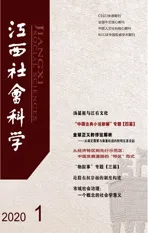清末民初小说观念转型与《红楼梦》阐释的公共化
2020-02-11
1897—1916年间,清末民初文坛上围绕着小说界革命问题而对《红楼梦》进行大量讨论,其中,侠人、王国维、管达如、成之、蔡元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这些阐释文章看起来观点不一、视角多元,但其共同点是论者都凭着自身有限的跨文化对比视域,引进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观点,关注《红楼梦》的社会性指向与反传统内容。重点是,在清末民初初步形成的“公共领域”中,《红楼梦》第一次从“社会公义”的角度被阐释,《红楼梦》的政治意义、道德意义、美学意义、伦理意义都在“公共性”的平台上被展开讨论。这是《红楼梦》阐释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文化事件,同时在现代文学发生史上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关于清末民初阶段的《红楼梦》阐释,目前学界所关注的基本是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1916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其实,在清末民初的新小说界,作为古代小说经典之一的《红楼梦》,与《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西厢记》等文本一起,经常被新小说的创作者和评论者所讨论,而《红楼梦》在其中出现的频率之高、被阐释之深与广、它的意义以及它在当时语境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都足以令它成为《红楼梦》阐释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文化事件,彰显着它在现代文学发生史上的意义和特点。
一、新小说语境与《红楼梦》阐释“公共性”视角的建立
清末民初的《红楼梦》阐释,最值得探讨的是在文本解释上一种“公共性”视角的建立。在历史上,文学要求“公共性”是欧洲启蒙运动的观念,它和当时启蒙思想者运用文学创作反抗封建王权息息相关。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在思想资源上援引的就是启蒙运动,他的“新民说”就是建立在对启蒙思想吸收转化基础上的。当然,相对于现代文学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人民性”文学思想,小说界革命时的文学思想是幼稚的,但考虑到它的时代背景,就仍然要肯定其中的历史先进性。当时受西方启蒙运动历史经验的影响,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学,要么是王权政治的附庸,要么是退守书斋的个人吟咏,两者都不具备“公共性”。文学不具备“公共性”,则无法在社会事务中担当一些公共性的文化使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谈起,所谓公共性,是在“公共领域”里才有的,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1](P2)“公共性”“公共领域”的特征必须:“最大程度的公开性”“公共同时必须有足够的分量”“参与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2](P32)公共领域的出现有几个必备条件,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比如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快速传播的媒介平台、社会平等协商意识的确立等。
反观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前的二十多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曾把文学视为无用之物,梁启超曾指出:“‘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斥责制造‘古玩文艺’的作者是‘社会之蝨’。”[3](P111)谭嗣同更是宣称在这“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当抛弃全部旧学之诗,他认为:“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施于今,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4](P81)之所以这样偏激否定旧文学,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清王朝本身没有公共领域,旧文学要么服务王权,要么吟咏个人性情,没有公共性,没有公共效用。
中国文学在观念上开始“公共性”追求,是清末时期在西方现代文化模式的启发下建立的。一方面,1897年之后,在洋人聚居的租界和通商口岸等地,人们移植西方文明模式初步建立起了以报馆、出版社、学堂等为中心的文化公共领域。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也借助国外条件的便利形成华人的文化公共领域。国内和国外的文化公共领域互相连接,成为酝酿新思想、新文学的策源地,在这些圈子或平台上,各种思考中国社会变革的声音可以众声喧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平台,即“从一言堂的君权神授到公共合理讨论的飞跃,独断型话语让位给了平等对话。”[5](P108)
如果说清末社会的这个文化公共领域给新小说的公共性提供了平台和载体的话,那么,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自著的或从西方翻译引进的各种启蒙哲学著作、社会学著作、政治学著作则给新小说的公共性注入了具体的精神内容。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性”意识的缺乏,梁启超在《论公德》中说:“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缺乏”[6](P213),“私德者何?对于身家上之德义是也。公德者何?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6](P213)他对比了中国的旧伦理与西方的新伦理,得出:“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6](P213)梁启超多次进行中国“私德”与西方“公德”间的优劣对比,反复说明公德就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群体观念基础上的“公共性”伦理,“新民论”就是要帮助个人建立社会公共意识。
同样,严复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On Liberty》(《论自由》)先是翻译成《自繇释义》,后又改成《群己权界论》,其所担心的就是没有“公共性”观念的国人一听说可以追求自由就把自己的权利扩展到危害他人的地步上,因此做了这个特别中国特色的改动,提醒国人首先要建立团体、群体、民族、国家等共同体观念,个体与群体应该处在独立而又互助的关系中。
随着西方思想著作的大量译介引进,人们渐渐了解了社会契约、民权、自由、民主、平等、个体与群体、国家、民族主义、市场经济、男女平权……等概念,这些“基本上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念”[7](P236),在“小说界革命”中指导着新小说的内容变革,尽管新小说论者对这些观念的接受理解存有囫囵吞枣的现象,但在价值系统转换的起步阶段这种激进冒失是不可避免的。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看出,以上说明的两个条件仅为新小说变革的非文学条件;从文学条件来说,清末文学革命的重心落实到小说这种文体形式上,也完全是借鉴国外的文学经验。如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郑重宣告:“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8](P27)此文被梁启超称之为“雄文”,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进一步重申这个观点:“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时,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8](P37-38)言必称欧美、东瀛等国,几乎是新小说论者的惯用语,但这些惯用语的重点在于指出国外小说具有形成公共舆论、引导社会公众形成价值判断的公共作用,而其作者“魁儒硕学”的知识身份、“仁人志士”的道德身份确保了其写作内容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新小说就是要以此为目标,服务于社会,完成“新民”和“改良群治”的重大使命。
新小说在这种公共性视角下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这不是私人对私人的服务;而是在文化公共领域中,用文学来完成私人对“群体”、对“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服务。这个思路落实到《红楼梦》阐释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维新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看待《红楼梦》往往从其反对专制社会、反对清朝统治、痛社会之污浊等角度出发,蔡元培通过索隐来确证《红楼梦》是一本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小说,而王国维则用叔本华观点来论证这是一部悲剧中之悲剧,管达如、成之从文艺心理学角度认为该书是社会痛苦心理之反映,林纾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到了《红楼梦》与狄更斯小说之间反映社会层面的不同,梁启超、松岑、海天独啸子等则认为《红楼梦》沉溺儿女缠绵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是新小说要批评的对象……这种众声喧哗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实在性要取决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或评判标准的。”[2](P35)也就是说,“公共性”仅是一个多元敞开的平台,它并不要求其中发言的人遵循一个设计好的标准或观点。而且,在实际上,正因为观点的多元和争议的存在才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到了事情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对我们今天来说,能把当时发表的所有评论言论都公布出来一起讨论,这是更可以发现《红楼梦》阐释在现代文学发生史上的特别意义的。
二、《红楼梦》阐释中对公共性社会正义的追求
社会正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模式,是指由公平合理的制度而形成的和谐社会状态;其精神实质是要求确认、维持、捍卫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公平性和正当性。资产阶级的社会正义观被经典性地表述为“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这些在欧洲启蒙时代被确立的社会价值观念,在清末维新启蒙运动中被大量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在一些较为发达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庚子之乱之后,国内居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至有四千年史一扫而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9](P306)这段话被记载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可信度高,从中可见西方社会制度与社会观念在当时国人心中的重要位置,竟至已经完全主导了他们对“新”中国之社会正义的想象。
有论者认为在中国,“正义从一开始就是被局限在个人品德的范围内来理解和使用的……中国历史上的‘伸张正义’也大多是从超功利的伦理诉求和道德标准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少有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法律层面的言说。直到西学东渐以后,社会正义的概念才被我国学术界广为采用。”[10](P58)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义论之所以给人一种局限在个人品德范围内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儒家理论是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很多社会政治问题是用伦理话语方式来表述和阐发的,表述上常常以个人境遇比拟政治境遇,不像西方现代思想那样学科分殊明显,观念和思路非常明晰化;但儒家伦理“怎样表述”这样的学术性问题,并不是清末那些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所在意的,他们在意的是,作为祖宗成法的传统社会制度在观念上已经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欧洲、美国、日本这些西式的现代社会价值观。
在对《红楼梦》的阐释中,这些关于西方社会秩序、社会理想的想象,指导着评论者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揭示传统中国社会种种不公平、非正义的小说。如侠人在梁启超组织讨论的《小说丛话》中谈到《红楼梦》的种种反叛性,归结为四种:
一是政治上对专制王权的反叛。“……于其叙元妃归省也,则曰‘当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8](P89)
二是对家族制度及伦理要求的反叛。他引用宝玉所言“于父亲伯叔都不过为圣贤教训,不得已而敬之”,加上“书中两陈纲常大义……言外皆有老大不然在”等例子,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家族之制,与宗教密切相附,而一种不完全之伦理,乃为鬼为蜮于青天白日之间,日受其酷毒而莫敢道。……而著者独毅然而道之……”[8](P89-90)
三是对社会罪恶的批判。他认为“凡一社会,不进则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昭然,故一社会中种种恶业,无不毕具”,因此,在《红楼梦》这本书中“贾宝玉视世间一切男子,皆恶浊之物,以为天下灵气,悉终于女子。”是“因为男子者,日与社会相接触,同化其恶风自易;女子则幸以数千年来权利之衰落,闭置不出,无由与男子之恶业相熏染。”[8](P90)
四是《红楼梦》“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之尤伟者也。”[8](P91)
通过以上四点,侠人指出中国数千年的道德是违背人性的牢笼,严重阻滞中国社会的进化,却无一人敢言修改,只有曹雪芹通过贾宝玉等人物写出要保有人性就要反叛与世界相违背的旧道德,他认为该作者真正具有远见卓识。
侠人的这些结论,完全是以一套西式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清朝社会,在这种对比中,欧、美、日本的社会制度是进化的、民主的、理想的,而清朝社会是退化的、专制的、罪恶的,而且他的批判所针对的,不是单纯一个清朝时期,而是整个的传统专制社会的数千年历史,他说这罪恶累积到清朝,更加让社会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侠人把维新派人士的政治见解运用到《红楼梦》当中,找到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书中对传统社会的批判之全面、独到、深入、有预见性。总体来说,侠人的这个阐释基本上是合理的,他引证的例子也基本能够说明他的观点,虽然他在阐释中带入较多阐释者的语境,但并没有过渡到脱离文本的地步。
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以社会责任和社会正义追求来评论《红楼梦》的是蔡元培。蔡元培在论《〈石头记〉索隐》一文中,首先总结了以前人对《红楼梦》的错误读法,错误的产生是由于《石头记》的写作在“本事”上加以数层障幕,“本事”隐蔽得很深,读者云里雾里。为答读者惑,先前的评论者拆解《红楼梦》为这样几层,具体为:“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8](P546)蔡元培认为以上四种视角,是把小说看作闲书,注重的是《红楼梦》对闲情家风等的叙事——缺乏大义。而在清末民初的新小说语境中,尽管这样的看法还偶有出现,但也都是置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域中,被“小说改良社会”的思想所引导,其价值导向也是被一种“公共性”和“社会大义”所提升的。
松岑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这样的思路。其实,他的基本观点是非常守旧的,但他把这种“旧观点”结合到新小说的社会正义追求中去对《红楼梦》进行批判。他在《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中写道:“故吾所崇拜夫文明之小说者,正乐取夫《西厢》、《红楼》、《淞隐漫录》旖旎妖艳之文章,摧陷廓清,以新吾国民之脑界,而岂复可变本而加之厉也?夫新旧社会之蜕化,犹青虫之化蝶也,蝶则美矣,而青虫之邘则甚丑。今吾国民当蜕化之际,其无以彼青虫之丑,而为社会之标本乎!”[8](P172)松岑这个态度和梁启超的较为接近,他们喜爱那些表达社会观点更直接的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对这种言情小说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其对个人情事的引导远远大于其对社会观念的启蒙。这种“公共性”不足的小说类别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
这里要指出的是,总体而言,反对者的声音在新小说语境中是属于三五个少数派,多数人对《红楼梦》的社会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认为小说的主题分为“英雄”和“男女”,这是人类的公性情,“此公性情者,原出于天,流为种智。儒、墨……凭此而出兴;君主、民主、君民并主之政,由此而建立。”[8](P18)因此,可以推导出儿女私情并不“私”,是社会种种思想和政体赖以建立的人性之一。与这种观点相继承者,管达如在“小说之分类”中谈到:“写情的,亦可名为儿女的,若《红楼梦》其代表也。夫世界本由爱情而成。男女之爱情,实为爱情之最真挚者。由此描绘,诏人以家庭压制之流毒,告人以社会制裁之非正义,且导人以贞信纯洁之死不相背弃之美风,亦未始于风俗无益。”[8](P400)同时,他又警示说:“彼《水浒》、《红楼》等之所以有名于社会者,非徒以其宗旨之正大,理想之高尚,亦以其文学之优美也。”[8](P411-412)在注意小说“社会性”的同时也注意强调其“艺术性”。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提出的,其创意源自严复,本身是为宣扬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但“其基本主张适逢其时,很快打破了政治上党派的局限,得到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8](P3)这些有识之士都认同小说的社会性,相信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但在具体主张方面又会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规划和想象而呈现出不同。在《红楼梦》的分析和评判上,维新派人士把曹雪芹所批判的社会认定为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一个缩影,尽管它以康乾时期为背景,但社会全方位的罪恶是从数千年的专制传统中延续累积下来的,并不专指清王朝;而革命派人士则紧扣住“清王朝”这一个历史时期,用民族主义来看待《红楼梦》的批判性,如蔡元培所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者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8](P546)文中,蔡元培通过大量的历史史料来阐发“本事”,其实,在《〈石头记〉索隐》中的所有发现,都源自评论者更为执著的民族主义观念。
三、《红楼梦》阐释中公共性的审美正义维度
在清末民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成之在《小说丛话》中论《红楼梦》的思路属于审美正义维度的追求。在理论上说,审美正义是在审美自律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的追求,正如徐岱在《艺术自律与审美正义》中指出:“如果没有艺术自律的前提,审美正义的讨论也就无从谈起。”[11](P181)因此,本文要讨论王国维和成之的审美正义追求,就要先论述他们的艺术自律观点。
艺术自律是审美现代性理论的一个观点,“通常认为,最先在哲学上对‘艺术自律性’进行系统论证的,是有‘现代美学第一人’之称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1](P182)而王国维正是在1903到1908年间,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思想学说,并以他们的美学理论为基础阐发了自己对文学自主性问题的理解,提出“游戏说”“纯文学”“专门的文学家”“真正的文学”“文学自己的价值”“为文学而生活”等说法。在德国自律论美学思想的启发下,王国维不仅对中国旧文学“文以载道”的说法提出批评,而且对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新文学工具论也进行批评。
1903年,他在自己主编的《教育世界》第56号上发表《论教育之宗旨》,提出“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12](P58)这是美学上的无功利论和自律论,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提倡的“觉世之文”“小说新民论”则是文学工具论,在王国维看来是急功近利、违背了美的自律性,他批评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术之价值,安可得也?”[13](P391)可见,王国维并不反对政治教化,他只是反对用哲学与文学这种需要独立精神、自律精神的门类去进行政治教化,因为政治教化的功利目的损害了美、损害了精神,最终使得哲学和文学没有价值了。在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结合老子和叔本华的“无功利”美学观点,再次强调:“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8](P98)在1905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他又重申:“哲学、美学乃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14](P35);“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14](P35-36)我们看以上王国维的话和他的立场,对于维护文艺的自律性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在对应时代要求方面,梁启超的功利论美学显然要比王国维自律论非功利美学更与那个时代亟需整合一切力量来推动民族国家转型的社会心理合拍;梁启超的观点之所以比王国维的更有影响力、更有号召力,其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正如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5](P118)对比王国维和梁启超的文学主张,其“思”都有相当之价值,然工具论合时自律论并不合时。
在当时的情况下,梁启超“新小说”理念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与王国维言论合拍的只有成之。在《小说丛话》中,成之继承了王国维的说法,提出了代表纯文学的“理想小说”或“理想主义小说”概念。成之把小说分为写实小说和理想小说,并认为写实小说的文学性不如理想小说,因为它“或欲借此以开启人之道德,或欲借此以输入智识,除美的方面外,又有特殊之目的者也。”[8](P424)因为理想小说以“美”为目的,乃“人类之美的性质之表现于实际者也”,“特其宗旨,不在描写当时之社会现状,而在发表自己所创造之境界。”[8](P421)所以,“自文学上论之,终以理想小说为正格。”[8](P445)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是提倡写实小说的,这里,成之通过对写实小说之启蒙内涵的反思,实际上是对新小说的工具性思路提出异议以及对王国维文学自律观念的一次声援。
成之不但在文学观念立场上与王国维接近,在《红楼梦》的评判和定位上也是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一个发挥。他首先是肯定《红楼梦》的纯文学性质。对于王国维来说,《红楼梦》是一部符合老庄、叔本华之纯粹精神的、“使人忘物我之关系”的绝大著作;对于成之来说,《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尚优美之感情”的理想小说;都属于他们各自定义中的纯文学,而且他们对《红楼梦》小说艺术技巧的欣赏,都道出了如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自律的王国是由审美形式建立的”[16](P219)这一原则。不过,成之并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把《红楼梦》认定是中国文学的巅峰,而是在一类优秀作品中肯定它,当然成之在论说时其哲学深度和逻辑论证能力也远远不如王国维。其次,对于王国维和成之来说,接受德国古典美学思想而强调审美自律的文学观念,不是要去“躲进小楼成一统”,或者归隐式的逃避;而是类似于比厄斯利所说的“艺术必须通过其感染力,为更高的社会目的服务。”[17](P328)这是一种“公共性”视角下的审美正义维度。为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强调“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8](P116)以及“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8](P128)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不过是作者根据人性某种本质概念而虚构出来的代表符号,他反对索隐派对所谓人物正事的考据。在他看来,书中固有些实事,但作者本意并不在此,小说所承载的宗旨和意义才是艺术形式的灵魂,可以给人带来深刻的思想启悟。王国维说“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唯《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故美学上之最终目的,与伦理学上之最终目的合。”[8](P123)当然,这个伦理学不是社会上一般实践层面的伦理学,而是超越层面的伦理学。
同样,成之在《小说丛话》中也否定了考据家之所为,他说:“即如《红楼梦》,今之考据之者亦多矣……”,然则“小说所假设之事实,所描写之人物,可谓之代表主义而已,其本意固不徒在此也。”[8](P458)这个主义便是作者对人生种种境况的不同理解。在《红楼梦》中集中体现为对人生之苦及解脱之道的终极探索,这个观点和王国维是一致的,但王国维以贾宝玉为主人公,成之则以“十二金钗”为主人公,他说:“《红楼梦》中之人物,为十二金钗。所谓十二金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8](P458)这种苦的总根源在于人性知苦乐,不管身处什么境况总是难以摆脱,“足见苦乐非实境,所谓苦乐者,实人心所自造也。”[8](P458)可见,在成之看来,《红楼梦》中的“苦乐”不指向现实,而指向心境;是要用心灵去消化苦乐,而不是直接改造社会改造“苦乐”。
总起来说,成之和王国维所崇尚的“自律论文学”,当然也有“社会性”;但这个“社会性”并不是现实实践的层面,而是哲学意义的“社会与人”层面。因此,王国维和成之所论《红楼梦》悲剧观,都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他们要求的审美正义维度不但指向人类的总体性,同时也指向时间的永恒性。很显然,这种境界高远的东西只适合那些本身素质就较高的群体,他们久而久之可以潜移默化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理想化,但完全不适合当时处于危机之中亟待迅速变革普通大众思想观念的时代要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小说界革命之“新小说”,在价值理念上获得的最明显现代特征就是在“公共性”视角下,开始追求文学的社会正义或审美正义,他们的理论资源或者是来自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思想,或者是来自西方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他们带着这样的思想来重新审定传统小说,其中成果最突出的是对《红楼梦》的评论。从启蒙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当时的人们要求小说能够参与到社会大变革当中,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因此,在《红楼梦》的评论上就看到了《红楼梦》一书所蕴含的反专制的历史内容,同时人物也被区分为守旧和维新的不同类别,以说明作者所具备的政治前瞻性和高超识见。而从审美现代性出发,他们强调《红楼梦》文本在美学观念上的自律论立场和颠覆性内容,他们证明《红楼梦》和尚利务实的国民性是格格不入的,《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小说界的精神瑰宝,是美学上的极其成功。审美现代性立场对启蒙现代性立场是持批判态度的;启蒙现代性立场虽没有直接回怼审美现代性立场,但对自己的观点是坚信无疑的。
当然,跳出门派之争,今天来看这些多元的观点,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用“公共性”视角看待《红楼梦》,无论是强调《红楼梦》的政治价值、道德价值,还是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都是在“社会公义”的前提下展开的。按照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既不单纯掌握在创作者那里,也不单纯掌握在阅读者那里,而是跟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地生成。从这个角度来说,了解清末民初这一段《红楼梦》阐释史,既是对《红楼梦》的一个理解,也是对中国文学现代发生史的一个侧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