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探缘
2020-02-05李育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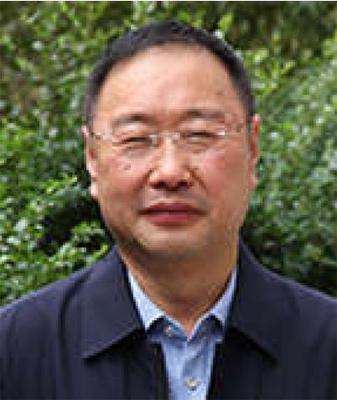
李育善
缘起
秦岭是一道龙脉,商洛是秦岭一个点。秦岭山中的万千沟壑,孕育出一条条流淌着的河,丹江就是这万千条河流中较大的一条。
真正对丹江的关注,还是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成功前的事。2013年底我去北京,拜访《光明日报》的韩小蕙老师,说到调水的事,她说那是湖北的水,跟你们有啥关系。我仔细给她说明了情况,她这才恍然大悟,说:“北京人一点不知道这些,你赶紧写篇文章发来,让人们都知道丹江源头在商洛,商洛人为保护水源是出了力流了汗的。”回来后,我利用周末,从丹江源头走到一脚踏三省的白浪,采访了上百名丹江边的群众,如实书写了为了“一江清水送北京”,政府和老百姓所做的事情。在《光明日报》一个整版刊发,不少北京的朋友看到后,电话告诉我,他们代表北京人民感谢默默为保护丹江做贡献的商洛人民。
外地朋友越关注丹江,我心越虚。我是商洛人,对丹江知道的却很少很少,丹江的命运是咋样起起伏伏,又充满着咋样的传奇色彩?就像一个儿女对自己朝夕相处的父母一样,知之甚少。日复一日,我忙我的,丹江依然日夜川流不息,吻着商洛大地的泥土,穿过青山,跳过峡谷,激越滔滔。这条江是古老久远的。
我出生在丹江源头一条叫苗沟河的小支流边,南面迎风坡面发源的小河,水质甘甜,从红黄色的细沙中流过,河旁有个小村。村子依傍着大山。我是喝着丹江的水成长的,是丹江哺育了我。于是,在2017年的某一天,萌生了走丹江的冲动,决定考察丹江,探究这条江的过去和现在,人与江,江与人的特殊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对立与斗争,相互消解与滋养,以及时光赋予它的新的使命和荣光。
丹江,是秦岭腹地一条最长的河流,也是长江水系支流汉江最大的支流。因产丹鱼,吃了长寿,尧时名丹水,又传,禹之外孙丹朱治水有功,为纪念之,叫丹水、丹江。史载,天下名水有二十种,丹江排名第十五。在陕西境内的商洛辖区也叫州河、寨河。丹江发源于商洛的秦岭山,流到丹江口市入汉江,干流长390多公里,在商洛就有249.6公里,流域面积7510.8平方公里,占全流域的百分之四十。
丹江历经沧桑。春秋时期就有了航运,明清时代是航运的黄金时代。《徐霞客游记》盛赞当时的龙驹寨是“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关中灾荒,襄阳20万石仓米靠丹江水运经龙驹寨,转运西安,以解饥荒。
陇海铁路通车,货运转移,加之丹江峡谷、川塬交替成藕节状,水位下切,泥沙涌阻,丹江航运日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彻底停运。
从此,丹江沉寂了,尘封在历史岁月中,要不是遇到旱灾和水灾,人们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一遇灾,多是骂声。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作为丹江口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的丹江,从沉睡中唤醒,成了一条不大不小的动脉,川流不息,日夜兼程,保证着一江清水送北京。历史钩沉,现实寻觅,把丹江——这条母亲河丰厚的一面挖掘出来,让我们重新认识新时代下的丹江,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期盼。
我家就在秦岭东南部的棣花苗沟村。村子不大,上百口人,沿苗沟河散居。全村除了招上门女婿几户,多是李姓。几年前,我从一位堂叔父那里找到了“李氏长门宗谱”,这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甘肃陇西人,是从那里迁徙而来。至于是官方组织的搬迁,还是生计所迫,不得而知,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
苗沟也是两山挤出的一块小地方,两边山呈“V”字型,村子就在底部。苗沟河水只是丹江一个毛细血管,夏季发洪水时会露出肆虐的凶相,也曾冲走过房屋家具和树木,毁坏过农田。邻居家牛哥的一头猪被冲走,他气得连哭带跑赶了上百里到月日滩,连根猪毛也没找到,病了半个月没起床。冬季小河结冰,是孩子们的溜冰场。

去棣花镇街,沿河边小毛路顺流而行,走个把小时就到了。现在有苗沟水库,也有了通村水泥路。苗沟河流到贾塬村,就入丹江。贾塬人把流到他们身边的苗沟河叫小河,自然是相对丹江而言。见一农夫荷锄,问话,说是到小河地里去了。他说的就是这里的苗沟河边上的地。
小时候,夏天到苗沟河里游泳,奶奶常常站在涧塄边,放着嗓子喊:“小心发大水把你一伙鬼娃子冲到州河里,冲到月日滩,冲到老河口去了,赶紧给我回来。”奶奶说的州河就是丹江。第一次见丹江约莫在我五六岁时,跟奶奶熬娘家去。奶奶是棣花街贾塬人,她是咋样嫁到苗沟山里,又怎样把她的亲侄女许配给三叔父,谁也说不清,好像记得奶奶说过,“还不是为填饱肚子!山里坡地多,有啥吃哩么。”这也许是缘由,也许是缘分。
那时,舅爷给贾塬队上喂牛,牛圈里有几十头牛。牛圈就在涧底下,牛圈下面是一大片稻地,地中间有条路,通到州河里。我跑到牛圈外场子玩,有不少男女从田间路上背着青草向牛圈走。他们都是刚刚趟过河,裤子都直流水。到牛圈场上给草过秤,记工分。我曾好奇地问:“舅爷,这河咋恁大呢?比我家的大多了。”舅爷笑着,用他那六只指的手,轻轻一戳我的小脑袋,说:“好瓜娃哩,这是州河,就是人说的丹江。一流就流到老河口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偷偷跑到丹江边,见不少比我大的男娃娃,从那石鳖子上跳水,那姿势美得叫我蛮咂舌头,我要能跳恁美多好呀,说不定一下子还能游到老河口哩,那地方一定大的很吧。“寻你多半天,你这狗东西跑这儿来了。”奶奶边骂边扯着我的耳朵,我想到老河口的念头也被吓得不知蹤影了。
丹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神秘的种子,听贾塬的孩子说,他们还在河里逮到五颜六色的金花瓣鱼。奶奶也说过,她们小时候拿竹笼捞鱼,全是金花瓣鱼,听得我眼前仿佛是一片金花瓣鱼的世界,更加神往丹江了。
上中学要到棣花街,得租房住,还得自己做饭,父亲就带我去他工作的地方上学。父亲在那里邮电所工作,我去一切都很方便。那地方也在丹江畔,我几乎天天放学都要找借口到丹江河边上,有时还主动要求给邮电所担水,半天才担两半桶水回来,时间都在江边玩耍掉了。一段时间,丹江两岸,也就是河南河北的孩子闹矛盾,就约好一个下午放学后,在一个地方用石头相互砸仗。我力气小,甩出的石子总是掉到河中央。有的伙伴一使劲就能甩到河对面的人堆里,我佩服得不得了。有几次还在河里摸到金花瓣鱼,同学教着用芦苇叶子包住,再拿青泥糊住,放到柴火上烧。少时工夫,一股淡淡的清香让人馋得流口水。夏日里一放学,甩下书包,就扑到河里,脱个精光跳进水里。有一次,一个漩涡把我卷进去,我喝了好几口水也没挣扎出来,喊叫“救命”的声都变调了,还是大个子魏同学一把把我拽出水来。
后来国家恢复了高考,学习也紧张,也少到丹江边去了。有时手捧书卷在河边吟读,心里全想的是学习的事,无暇顾及丹江了。考上师范,也是在丹江边学校就读,在丹江边玩耍,打水漂,洗衣服,尽情放飞青春的小鸟。
毕业后又回到上中学那儿教书。那时年轻气盛,学校几个青年教师被电影《少林寺》看得热血沸腾,每天天不亮就到丹江边舞枪弄棒。晚上送走最后一拨上自习的学生,照常到江边习武,有几位学生也加入我们的队伍。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根本没感觉啥叫疼,一心想成为武林好汉。
有时一个人沿丹江漫步,稻田的蛙声、江里的水声和自己心里的激情,一同呐喊成命运交响曲。我暗暗下决心:像丹江一样永远向前,向前,向着目标——大海奔流。
工作后又考大学,依然在丹江边上。以至于后来改行从政,一刻也没有离开丹江。工作、成家、生子……这一切忙得不亦乐乎,去丹江边上浪漫的事再也没有过。丹江还是那样默默流淌着。有几个夏天,它也疯狂过,冲走过财产、田地乃至于生命。像“八一四”水灾,是1988年8月14日午夜一次洪水,把商州三岔河一条沟冲成一趟平,房屋没了,耕地没了,啥都没有了,人都说水火无情一点不假。那种损失不仅仅是对财物、对生命,更是对灵魂的一次重创,无形中改变了人们对丹江的敬重。近二三十来年,随着山上树木渐渐长大,植被好了,泥石流洪灾也少了,丹江依然母亲般滋润着两岸的老百姓。
每当我静夜沉思,总觉着自己对丹江——这养育我们的母亲河知道得太少,做的事情也太少太少。作为生在丹江支流之一的苗沟河边、长在丹江边的汉子,对丹江这位伟大的“母亲”也应该做点事情,至少了解她的历史,她的前世今生,了解她身边如儿孙般无数个支流的故事。
这样,我便下定决心,利用每个周六“走丹江”。从2017年6月初开始,寻找源头,探视支流,翻阅资料,采访群众。我们一行四人,小陈开车,小贾记录,他是记者,这方面是强项,老喻提问,他是我大学同学,小说写得有出息,也能问到点子上,我在边上听,用手机录音,像是个旁观者。回家再整理,还有小贾记录的东西,一手资料可以说是满满的。一路下来,我越走越认识到自己的浅薄,越感觉对丹江太陌生了,都有点不敢轻易为丹江写东西了。
小贾、老喻给我鼓劲加油,他们相信我能做好的。老喻还自己把一些小标题列出来,用手机短信发给我。我只好说:“那只好把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几位朋友的辛勤付出,我要是再不动笔,真的对不起人了。
怎么写?一直在困扰着我。原想从丹江的历史、丹江水运、丹江与人、人与丹江之间发生的事情写下去。当我们走到丹凤竹林关时,我的思绪发生了大的变化。从现在写起,以时间为序,把走过的点上的故事一一串接起来,把历史融入被采访者的叙述中。就这样,自己的思绪也同丹江一样从过去流向未来。
在丹江边生活了几十年,说不了解她,外人会耻笑的,说对她很熟悉,有人要问到丹江从哪里来的?源头在哪儿?我只能认真地说:“志书上说在商州牧护关镇的凤凰山南麓。”凤凰山就在秦岭山脚下中坪村的沟垴。其实,我也没去过,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探源
一
2017年6月3日一早,天阴沉着,偶尔还飘点雨花。我和老喻、小陈驱车,沿312国道,溯丹江河而西行,过麻街,穿黑龙口街,到铁炉子,进七里峡。传说当年太上老君炼丹炸开了峡口,才有了这条路,史料无从考实。
七里峡进去分西峡、东峡。最早的长坪公路,也就是后来改成的312国道都是从西峡过的。我们自然先走西峡。
秦岭半山腰的一个点,海拔1693米,在商州境内。
这是目前确认的丹江源头。
我十二岁上跟父亲外出求学,从那时起,就喝着这地方流下去的水长大的。今天我站在源头水边,倍感亲切,思绪万千。水是从山中间流出来的,一股白花花的,从石层中涌出来,初生牛犊般有力,跌砸在乱石上,白菊花瓣一样向四周弹射,淙淙有声。水边草木茂盛,在这大约三四公里长的坡谷里,挨水边主要是水芹菜和夏枯草。水芹菜密密麻麻,家鄉人用它窝酸菜,吃着香香脆脆;夏枯草顶上绽放出紫色毛茸茸的花蕊;还有像荷花样的植物,一枝细杆上撑着一片荷叶般大小的叶子,在风里摇曳,涩涩的叶面没有荷叶那么光滑。更有不少胳膊粗的柳树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树,把河遮得严严实实,只闻其声,不见水影。
这条沟叫张沟。
昨夜下了一场小雨,土路松软。沟口住着三四户人家,我们是随了人家的指点,从沟口用了两个多小时,走走停停,到源头。
车子上到西峡半山腰,我们下车问路边一位中年男子,他有点不耐烦地说:“你没看那儿立个牌子么。”猛一抬头,见路边核桃树后面有一个大大的牌子,绿底白字写着:丹江源头,2013年立。看来我们也来对了。又问洋芋地里拔草的中年妇女,她直起腰,用手一指说:“在张沟,远的太太。”我们沿她指的方向,朝下面沟口走,正好一家门口一位二十来岁的胖女子在水池子边刷牙,问她,她没理,院子还有一位老大娘,一只手缩在胸前,含含糊糊地说:“张——沟——远。”
沿河道边的土路进沟。路下是小河,这就是没长大的丹江。河边是一台一台梯田,地里长着开紫花白花的洋芋,套种苞谷,也有一拃高了。走了上百米,见一水泥池子加盖,能听到流水声,想必是下面人家的自来水。沟里很安静,偶尔听到远处车子的轰鸣声,再就是流水声和鸟鸣声。我们走着说着,缓缓而行。前面有土坯房子,破破烂烂,外面有一堆牛粪,屋里有两三头牛。再走,有一片缓坡,草过脚面,有点草原的气息。坐下来歇息,花丛中蜜蜂飞舞着不惹人,蝴蝶上下翻飞着,也不怕人。草地上留有一串串牛脚印。
小河其实就是小溪,溪流不大,水声很响。山上铺盖着悠悠的翠绿,郁郁葱葱,还有一堆一堆开白花的树,像雪花一样洁净舒心。
转过一个山垭继续爬山,这时能听到“汩汩”的水声,却看不见小溪。从岩上爬过去,连水声也没有了,地上是湿湿的土。这里距离山顶也不远,一定是源头了。水成了潜流了。前面说到涌流的场景只是想象。站在湿地回望,对面山上公路翻秦岭处就在脚下。
下山走到海拔1000米左右,远远听见羊叫声,却不见羊,我们学着羊“咩咩”叫了几声,一只白山羊从一棵小松树下露出頭张望,另一只两眼和耳朵土灰色、额头到嘴都是白的山羊也挤出头看我们。下行走了一会,有一群羊从身前跑过,两个大的还在用犄角顶仗,小羊羔在地上撒欢子。
返回到公路上,见那家门上樱桃树上有个中年男人在摘樱桃,问咋卖哩,那男的笑着说:“不要钱,谁摘归谁,快来摘来。”听口气是关中人,地上有个小伙正朝袋子装。刚才问话没理我们的那位胖姑娘走过来,笑笑地说:“不卖,要吃了自己摘去吧。”我们从城里带有大颗樱桃,在水池子洗过,让这家孩子吃。房子是青瓦白墙灰墙裙。门上的对联还鲜红着,上联是:猴年一帆风顺,下联是:鸡年万事如意,横批是:富贵平安。对联宽大,下面印着中国邮政字样。门口坐着那位大娘,就是刚给我们说路不太清楚的那位。老人给我们找凳子坐,跟我们拉话,说话确实有点困难,土红色的脸上露出熬煎,说,得了脑梗、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住院花了3万多。糖尿病是六十六岁上,国家给免费体检才发现的。她家姓赵,儿子在西安打工,女儿嫁到镇上了,她也七十多,到这里快六十年了。“叫野猪害糟(糟蹋)的地也种不成了,你们去的张沟过去都是牛犁的地,现在都荒了,公路不走了,也冷清了。住这儿空气好,就是没法发展。”老人还说,原来是西峡村,都合成铁炉子村,做啥都不方便。话语不太清,意思能明白。
下雨了,老人要留我们吃饭,我说还忙着哩,就走了。之后,又走了几户,到第三户,一个老汉站在门口柴堆前,两手捏着一根树枝顶端,并顶着下巴,光头,上身红线衣,蓝裤子,给我们笑,看着脸上还有些红润,问话,他直摇手,耳朵笨。老太太怀里抱着柴,走过来,她也有七十七八,说沿河边的地是1958年大会战修的,这才一人分上四分地。一年种一料,苞谷洋芋豆角,种麦收成不好,都是春小麦。儿子到山外住家去了,也不常回来,孙子都二十六七了。还说她老汉的大(父亲)去给老蒋当兵时,老汉才会爬步。家里三间土房也有四十多年了。屋里黑洞洞的,电视里正播着打仗的电视剧。老人说他们姓王,自然说的是男人的姓,邻居一家姓党。他们的老祖先,是从河南底下啥地方挑着担子来的。老汉说他快九十了,又重复说了他姓王。
沿旧312国道(现在已改道)步行而下,见涧底下一大片耕地,我们从公路拐到地边,遇见一位老大娘在栽黄瓜。她家院子晾着不少豆腐干。她说话瓮声瓮气,说儿子在商县(也就是现在的商州区)拉砖,儿媳在县上经管娃上学,在城里租房住。老喻指着地里有半人高的植物问:“老人家,这是洋萝卜,也叫洋姜吧,自己吃哩么,还是卖啦?”老人说:“就是的,人家说今年收哩,吃也吃不完。”老喻又问:“是不是卖到森弗公司去了?那里收哩。”老人说她也不知道。我问门上的豆腐干卖不?老人说:“卖哩,两块钱,卖个个子哩。”又问卖的咋样,老人说:“遇相哩,有时来人多,有时没一个人来。”老人说她这家姓祝,邻居还住了三四家。这时,山上“唔儿,唔儿”一阵鸟叫。走出地里,朝前走,老远看见一位老汉正在拿锯锯手腕粗、丈把长的树。我们走过去和他拉话。
二
我们从另一家到他门口时,他正在锯木头,问老人,他笑着说:“用这出个锨把。”也就是做个锨把。问他高寿,他直起腰,放下手里的活,一笑,瘦瘦的脸上涌出一堆皱褶,幽默地说:“不大,才七十二三。”我笑着说:“看着跟我们差不多,像五十多。”老人说:“老粗咋能跟你轻汉人(出力少的人)比。”他干活麻利灵感的样子,真不像七十多的人。他家瓦房是1968年盖的,老房在上面早都拆了。过去他们西峡村有130多户,500多口人,从他记事起,没发过大水。老路原来在河对面,1958年修公路时才改到这边。上面那一弯地是1970年代修的。那时河在地中间流着,修地时才改到坡边。说话间,他放下活,从屋里拿出凳子,还给我们发纸烟。他坐下说,没修河边地前,沟沟岔岔坡地也多,就是不咋长庄稼,只种个洋麦(荞麦)。那时地少,生活也不好,人干劲还大,现在人嫌种地来钱慢,好多平地都荒了,不如外出打工好。“咯咯咯”一声野鸡叫打断了他的话,他又去锯木头了。
老徐的记性很好,过去哪年哪月哪日发生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他有五个娃,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女儿都出嫁了,儿子在西安打工,孙女上高二,在大荆中学,他们黑龙口镇中学撤了。说到祖辈,他说祖上是从湖北孝感龙岸洲迁来的,是乾隆年间来。他也有家谱,他排兴字辈,徐姓是个大户,和洛南古城姓徐的也是同宗。
老徐住的属于原西峡村四组,也叫上河组,老名字叫大杨树,过去这里有一棵大杨树,几个人都搂不严,一到夜晚,树上有上百只鸟;也叫骡马店。路是民国27年修的,有了骡马车,家家户户都歇的有,这才也叫骡店,还走过汽车。关中道人都知道秦岭山里有个大杨树、骡店,就是这儿。
说到上面姓王的那一家,他说儿子女子都是抱养的,儿子到泾阳住家,女儿嫁到镇上。算命先生也算过,这一家是“铜盆子铁刷子,凑凑合合一家子”,果真是凑合成了一家子。
记得是1951年夏季,抗美援朝部队路过,人一溜带串,骡子拖的大炮也是一溜溜,群众把竹叶烧成开水放到路边叫部队人喝,把馍烙好让部队人吃,吃了喝了不要錢。到1954年以后,骡马车慢慢多了。1956年车也多起来,都是些卡车,没有大轿子车。1958年长坪公路通了,路才走这边,那边老路还走了三四年。修路时,家家户户住的人都是满满,人挤人。干活用钎子锤,黑火药放炮,也死伤了些人。1956年商县成立了运输合作社,把各村的马车集中起来,城里搬运站就是运输公司的前身。当时也有护路队,后来改成养路段,那些人吃上了公家饭。修路时,想挖开秦岭垭子,阴阳先生说那里是龙头、龙脉,一挖就会出水,这才修成拐来拐去的盘山路。如今都从长江底下打洞子哩,修高速路不见人,全是机械化么。
我们夸他记性好,他却笑着说:“好啥哩,日梆子谝闲传行,正事儿没门。”
老徐的手机报时中午十二点了,他说给做饭,我们告别了。这里农村是两顿饭,早饭九十点左右,午饭下午三四点,也不是饭口儿。车子下行二三百米,有家丹江源头饭店,一位中年妇女和她的女儿在忙乎着。女儿在城里上中学,周末在家帮忙。她们开饭店的房间是原来村上的办公室,合村后没用了,租过来的。女的笑着说:“一个人25块,三凉三热,不够了加,不加钱。”
女的胖胖的,干净麻利,不大功夫,菜就端上桌。吃饭间,男人开车回来了,人瘦瘦的,中等身材,一进门就给我们发烟。交谈中,得知他原来是西峡村的支书兼主任,现在成铁炉子村副支书。说到丹江源头的话题,他笑着说:“当初东峡村、中坪村、还有梁坪村都在争这源头,后来上面来在我们西峡一栽牌子,再也不争啦。再说现在东峡、中坪和我们西峡都合到铁炉子村,源头也在一个村了。”他抽了一口烟,弹了弹烟灰,又说:“村子合大了,压缩了干部,群众办事不方便,干部坐班嫌麻烦,就说我吧,一天工资43块,开车烧油,两个娃上学,老人又是脑梗,自己是心脏病,一月1300块不够花。”
问这里的鱼一定无污染吧。他笑着说:“有啥鱼哩,连鱼鳞都没一片。”他说听老人讲当年王莽追刘秀到这里,刘秀把鞋倒着穿,雪地里脚印是反反子(反方向),让王莽跑岔了。刘秀在西峡河边歇脚时,让刺扎了,他以为是河里的鱼咬了,破口大骂:“把你这绝死鬼哟!”这一骂再也没鱼了,真给绝了。说到保护水源,他说铁炉子的硫酸厂停了,铅锌矿关了,河水清了,经济却不好了。
吃完饭,和他又说了一会儿话,我们一行到东峡去。东峡河也算丹江源头的一个孪生兄弟,到底咋样?总得眼见为实,看个究竟。
三
红豆杉多生长在南方,古诗有“红豆生南国”。东峡口却长着千年的红豆杉,真是一大稀奇。
出西峡,沿312国道左手有一条通村水泥路,溯流而上就是东峡村了。这里的河水比西峡还大。车行百十米,见河对面绿栅栏围着一棵大树,枝叶繁盛,那就是红豆杉,树根在一块大青石上盘旋着,树身向前扑着,罩着河里的水潭,水潭有半个篮球场大,潭边有一个椅子样半圆形岩石窝窝,像是人坐出来的样子。
路边竖有一块席大的绿牌子,上面写着白字,是林业部门和村上合立的。那上面说,这棵红豆杉是东北红豆杉,很稀有,是国家一级珍稀树种。东北的树能在西北秦岭山里生长上千年,该不是上天也给树进行“移民大搬迁”。
这几年,人生活富裕了,也在追求享受了。城乡人都在玩串珠了,崖柏、红豆杉树枝成了抢手货,有人以此发家。有人就盯上这棵红豆杉,偷偷砍下枝股,拿去旋出珠子好卖钱。要不是主管部门及时保护,说不定有人连树根都给刨掉了。
山里的古树奇石之类的,大都被人们赋予神秘的传说,可见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这棵树相传是太上老君栽下的。当年他来到秦岭山里寻找灵丹妙药,见山大沟深,人们无路可走,便在峡口架起炉子,在风箱洞支起风箱,炉火炼丹炸开了七里峡,后人也叫老君峡。天长日久,火炉烤得他难受,便到东峡口水潭洗澡。为纳凉才栽下红豆杉的。后人还在树边建了庙宇,塑有太上老君、龙王爷、药王爷的像,逢年过节烧香祭拜,听说很灵验。
那潭边的石椅子,刚才也听老杨说当年刘秀躲王莽时也在这里坐过,想必一定第一个是太上老君先坐。
千百年来,这棵东北红豆杉在秦岭这一旮旯见证了这里人们的悲欢离合,聆听了河水的涨涨落落。要是有耐心坐在树下听听红豆杉说说话,一部人与水的故事长篇也道不尽。
“走吧,天要下雨了。”同行的老喻催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阵微风拂过,树上那千手佛般的叶子,像无数小孩的手在跟你挥手作别。那挥手之间,让我感悟到大自然给人类的无限恩赐,亲人般那么亲切,那么温暖。
车子已经拐过弯,看不见红豆杉,我还在依依不舍回头望,心里那棵红豆杉还劲道地摇曳着。
我们沿河边路朝沟里走。路与河并行,只是路在侧上,河在斜下。人家也多居住在河的两边,甚或住在山根。潺潺流水声很响,偶尔有两声不知名的鸟鸣。路边地里种有苦荞麦,黄杆杆,绿叶叶,开满碎白花。

车子一直开到岔磨沟顶上。我掏出手机测:海拔1330米。住了三两户人家,都是门上锁。只见一老年人担尿浇豆苗,问他这里为啥叫这名字和河的情况,他摇摇头也不知道。路边还有一小块辣椒苗没栽。想起老家一句农谚:茄子栽夹,辣子栽花,就是说茄子苗一出来就要栽,辣子苗到开花了栽照样能活,能结果。
走了一会儿,又见一位七十来岁的老汉在地里栽玉米苗子。老人看见我们就笑笑地问话。老人说这沟叫菖蒲沟,山上有不少菖蒲,夏天了能熏蚊子。菖蒲是一种中药材,提香料,治头痛牙痛。这也印证了“秦岭山中无闲草”一说。看来山里旮旮旯旯的名字背后都有一大堆“古经”。面前几台平地是1958年修的,当时砍了十几棵核桃树,那树要长到现在准有一搂粗。这个岭翻过去就是蓝田县的霸源,祖先是从蓝田搬过来的。过去村上有几百人,现在都没几家。有的搬到黑龙口赵湾移民点,只是回来看坡种地远些。
返回到庙沟交叉口,雨下大了,到一家农户门口避雨。院子里两位老人忙着给蜜蜂箱上盖石棉瓦。老汉一扬手,说:“下雨哩,屋里坐。”收拾完,忙着给发烟。老汉仄脸大耳,胡子麻擦,蹴在门墩上,抱着双手跟我们拉话。看着院子樱桃在树上一片红,问咋不卖呢?老大娘说:“没人要么,也没人拿到街上去,要吃了上树摘去。”老汉是解放前两年生的。他觉得村子这几年变化最大,拉上水了(自来水),各家各户房也刷新了。
说到养蜜蜂,他还很内行。他养的土蜂,是中蜂,也叫中华小蜂,还有洋蜂,叫意蜂,是意大利蜂。家里养了十来箱土蜂,一年能产百十斤,一斤卖二三十块。蜂辫割出来了,在锅里一蒸,一篦就行了。一蒸把有些啥好东西就糟蹋了,说是用啥桶子搅着好。原先收了别人五六笼(箱),分了这么多。咋样时才分窝哩?他憨憨一笑,说:“那得看王台么,蜂辫下面有指头蛋大的嘴嘴子,看那盖盖子泛红了,就要分了。蜂王没定,自己分。”
说话中间,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在门口走出走进,一句话不说,也不搭理我们。老人说是他儿子,有精神病,在渭南上门,病严重了,自己跑回来了。孙子还在那边上学。四个女儿,一个嫁到韩峪川,其他都在外地。他家现在是包扶对象。
雨还在不停下着。要走了,老人送我们到路边车上,笑笑地说:“没事了,可来转嗷。”看着老人诚挚的笑脸,我感受到了那笑里藏着多少磨难,多少坚强,多少包容。
四
铁炉子村是现在丹江源头第一村,由中坪村、西峡村、东峡村、铁炉子村合并而成。
原来的中坪村就在凤凰山脚下,是志书上载的丹江源头第一村。这里条件差,地少,吃粮都困难。村上干部先从修地入手,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57人组成的长年基建队,用双手改变生存环境,在12条沟,垒起2800多台石坎梯田,修地300多亩。人们高兴地编成顺口溜称赞“石坎坎,金碗碗,银边边,钱串串”。有了平地,地里种庄稼,地边栽种经济植物,一举两得。
中坪村是当年全市的明星村,2006年被国家命名为小康村。过去治坡造田、开矿办厂,村上有个铅锌矿,年年人人都要分上万元。沟道治理,能修地的地方都修成了梯田。基建队队长王贤印因长期劳动,手都变形成了耙耙子了。
1995年12月22日江泽民同志来到中坪村,和群众一道修地,还给王贤印一双黑皮手套。直到临死前,他还要再戴一次呢。如今这里的老人说起那时的景况,也还很感动,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眼睛湿湿的,说:“我还有和主席的合影哩。”老百姓对中央领导那份情意是真诚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还依然珍藏在内心深处。
那天,我们是冒雨来到中坪村的,当年修的地现在也荒芜了。路边见一位老大娘,老人说,娃们都走完了,村里就剩些老汉老婆。昔日的辉煌只能从那一幢幢新楼房上感受得到。村子撤了,原村委会的办公楼也冷落一边。
在铁炉子村委会办公室见到现任支部书记张强。他五十开外,长得五大三粗,有保镖样的身板,说话声音洪亮。我俩是老熟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是中坪村的支书兼主任,他正在忙着和镇上干部在填贫困户人口的各类表册。
现在这个村子有800多户,2300多人,人口和面积相当过去一个乡。村部所在的地叫道岔村。是先前合并到中坪村的。
这个道岔村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因王莽追刘秀而得名。
村子合并大了,干部责任也大了,村干部得天天坐班。张强说,他几乎没回过家,他给我递上一根烟,我摇摇手,他叼上自己抽,感慨地说:“当年在中坪村当支书那才叫风光呀,大小的会,不是讲经验,就是领奖牌。上到中央领导下到镇上干部,哪一级领导没见过呀。走路都整天是背着手,高昂着头。现在村子大了可是个贫困村,这个头头不好当呀,自己总觉着都很没面子。明年要是摘不了贫困帽,我请组织摘我的帽子。”
他如数家珍般介绍着脱贫的项目。哪些项目投多少钱,收入咋样,他说得头头是道,看他满脸的喜悦劲,我也高兴得蛮点头。
说到水土流失治理,他也是信心十足。污染的企业该关的关了。小流域治理也是一条沟一条沟搞着。就说北京人来要开矿,环评是第一关,不达标,再有钱也不让干。新修的地由村上统一流转,栽核桃,种樱桃,再带上蔬菜自采自摘,加上农家乐,让游人来吃好玩好,再带上无污染的有机蔬菜,哪个不喜欢呢?
他告诉我,他现在都是副科待遇,月收入也上四千,他笑着说:“知足了,现在一门心思想着解决脱贫的难题哩。当然了,扶人先扶心,不然,今天脱贫了,明天还会返贫的。”
雨还在下着,张强一定要留我吃饭,我说等任务完成了,好好喝两盅。他到院子站在雨里送行。
五
黑龙口是个镇街,算是丹江源头第一街了。这里是西安到商州的必经之地。平凹先生写的《黑龙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景,两边来的客人都要在这儿歇息,吃饭喝水。商州去西安要翻座麻街岭,早早出发到黑龙口也饭时了;西安过来的,到这儿也是饿得前心挨着后背。于是,这个不大的小镇,卖吃食生意还红火,捎带也卖山货,基本上都卖给外地人了。如今,312国道改线,高速路开通,原来的老国道也冷落了。黑龙口一下子萧条了,国道边饭馆大多关门,曾经车水马龙的汽车站也废弃了,变成一家农业合作社;人们排队抢着买猪肉的收购组,也是人去楼空,一些房子都坍塌了,俨然一位交际花人老珠黄。只是逢集时,街上人才多一些,多数是老人妇女,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
黑龙口街是闵家河、七盘河入丹江处,水势大。那天我们冒雨寻找七盘河的源头。在街西4里处七盘河畔,就是秦岭铺村。这里曾是商於古道最早的驿站之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秦汉时在此形成集市,唐宋元明兴盛,光绪25年(1899年)衰败。1951年曾设秦岭铺乡,下辖秦川、秦峰、大岔等村。1954年撤销。到秦峰村,进银厂沟,有一家门口站着两女一男三个老人,在呆呆地看雨。一位老人说过去这里开过矿,才叫银厂沟。这沟河水没名字,商洛山里丹江无数支流,几乎都没名字,像过去农家人的孩子。这水是半山上岩缝里冒出来的,一年到头不歇气地流,老人说没记得河啥时候干过。门口那一片地是二十世纪六几年修的,河改道山边,路把河给扛住了。老人神秘地告诉我们,这里的水,神仙洗过脚,是神水,喝了能活百岁。山背后就是湘子洞,韩湘子曾在这里吹过笛。镇上人吃的自来水就是从这儿压下去的。
6月10日,雨后初晴,蓝天白云绿树,一切都像洗过一样清新。第二次来黑龙口街。街上卖豆腐、豆腐干的摆了一长溜,这里的豆腐在西安卖出名了。路和街岔口一位卖麻花的老大娘,面前摞着一米多高的麻花,笑着说:“这一盘200多个,一块一个,吃呀来!”我们每人买了一个,咬一口,香又脆。
这里的街分前街后街,从公路上下到前街,站到一人粗的柳树下,丹江河水在脚下哗哗流淌。小贾说,这座跨丹江大桥也是丹江第一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的,那时每天上劳在百人以上,这才连通了丹江两岸,是通往牧护关的唯一通道。河道干净,绿草丛生,成了一片片给水过滤的湿地。街房临街全是木门做墙,遇集时拆下来摆成摊子。门上面还有窗子,木楼上能住人,当年下面开店卖饭,楼上住宿睡觉。那房都有上百年历史,还有一家的山墙全是石头砌的。前街和后街由丹江分开。后街口上一家,邻居说人都住到城里去了。门口一个石板上有一个凹型的坑,是长年打糍粑砸出来的。
这里人打的是洋芋糍粑。每年收上洋芋,农闲时,把洋芋蒸熟,去皮,放到青石板凹里,用木锤子砸,直到砸成黏糊成胶状,便能吃了。吃时,可热可凉,炒好酸菜,或者蒜苗、葱等调好汁子,浇着吃,很香。过去,这里人给客人才吃洋芋糍粑,现在只要想吃,随时都可以打糍粑。
看那临河的一排排房子,多少有点沈从文笔下凤凰城的影子,只是这里的丹江水急无船。街上一位耳笨的老汉说,过去街上人马可多了,还有四处水磨坊。一个小伙子跑过来说:“问水磨呀,我陪去,学校边上的老磨坊,我舅爷住着。”
来到水磨房前,一位老大娘正招呼孙子玩耍。问她水磨的情况,她木木地说:“我是从宜君搬回来的,啥都说不清。”不一会儿,从桥上走来一个老男人,个子不高,小头圆脸,两腿像罗圈一样,一瘸一跛走来。问起话,他很警觉,不肯说。小贾亮了记者证,他的话匣子才打开。老人叫程存生,63岁。他说这些水磨大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街上一户财东修的。解放后地分了,水磨也成集体的,一直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改成水轮泵。方圆几十里外的人家也来上磨子,磨些杂面、苞谷,常常都是排队等半天。这儿地少,缺吃的。1968年全家迁到宜君。那年他才十来岁,过去那里的水不太好。一早擔回来的水上面老是漂一层子油,他这腿就是水吃成栁拐腿的。后来他在那里喂牛,四门不出。去的时候六口人,他大伯他父亲都过世了。回来也是六口人,老两口,儿子儿媳,两个孙子。1998年312国道改线时,他一家子搬回来,买了大队的水磨破房,盖了三间。他笑嘻嘻说:“全家人回来都说咱这儿好,水好能养人。回来都二十年了,我一家子身体都没出啥毛病,我的老毛病也好多了,你看,腿也跛的不厉害了。日子也过得安安闲闲。”说着他在老水渠边走来走去叫我们看。他又拧身指着地里说:“这里原来是水磨的上水渠,现在都种成地了。那时,水渠里的水满满的,还有不少鱼和鳖哩。”
程存生老人送我们走过丹江桥,他走路依然跛着,可走得很有劲,说:“常来游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