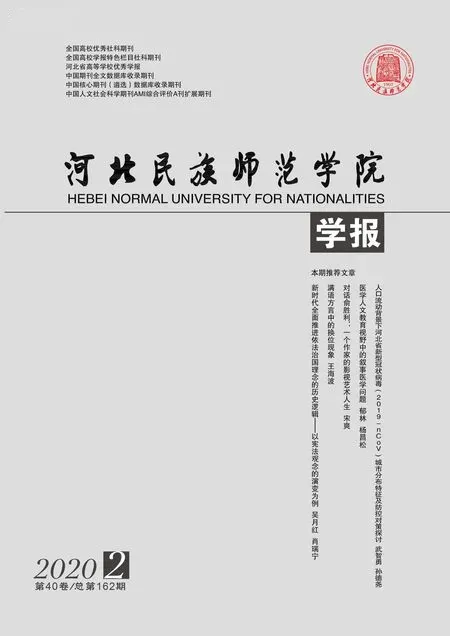论冯国佩的花鼓灯舞蹈美学特征
2020-01-17陆娟
陆 娟
(安徽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冯国佩(1914-2012)——一个出生于安徽怀远县冯嘴子村贫苦农民家庭的农民,却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一个民间舞蹈流派——“冯派花鼓灯”,并形成了其独特的舞蹈美学特征,进而推动了安徽民间舞蹈花鼓灯的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坛掀起了一股“花鼓灯”热潮,成为花鼓灯界“教父”式的人物。鉴于他对于花鼓灯艺术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对“冯国佩的舞蹈美学特征”进行深入探究。
一、花鼓灯与冯国佩
俗话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这一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不仅孕育了历史悠久的淮河流域文化,还诞生了著名的汉族民间舞蹈安徽花鼓灯。花鼓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夏代,传说当人们为了庆祝大禹治水的胜利,跳起来舞蹈,随后就逐步产生了花鼓灯,但也有的说花鼓灯起源于唐代、宋代……实际上,“花鼓灯”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乾隆年间刊印的《缀白裘》十一集,“梆子腔·看灯”一戏中:“合:抬头俱把灯来看,那边来了花鼓灯。”[1]但真正形成“千班锣鼓万班灯,村村都有花鼓灯”的繁荣景象,则要等到清代末年。清代文学家姚燮《今乐考证》记载当时有一个场面:“舞者十二人,每人手持二花灯,按节奏盘旋起舞。走出各种花样,有所谓‘三十六变’,如:双龙随会,倒连环,孔雀东南飞,鸳鸯阵等。”花鼓灯的繁荣景象,在当时可见一斑。
冯国佩,1914年生于安徽怀远县冯嘴子村一个贫农家庭,家中世代为农,同时也是安徽民间歌舞花鼓灯的传承世家。鉴于花鼓灯的悠久历史,到冯国佩这一代,家中已经连续四代有玩灯的历史。自冯国佩的曾祖父起,到冯国佩的二叔、三叔,都是玩花鼓灯的好手,每年到了年节、庙会或农闲时节,村里村外,四乡八镇的乡亲们都会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玩起花鼓灯。
长期受到花鼓灯熏陶的冯国佩,自小就对花鼓灯痴迷留恋,幼年还曾经因为迷恋花鼓灯而受到学堂老师的责骂批评,使得他索性更加专心的投入到花鼓灯的学习中了。1931年,冯国佩17岁的时候,拜在了当时有“花鼓灯状元”美誉的陈华美老师门下,由此技艺飞速进步,很快就学成出师,并开始了搭班卖艺的生涯。由于扮相俊美,体型匀称,个头较小,舞姿灵活秀美,因此冯国佩擅长反串花鼓灯中的女性角色,也就是花鼓灯中的“兰花”①花鼓灯中的女性角色统称为兰花,男性角色统称为鼓架子。,还由于衬子(跷)②以木头为主做的鞋子,鞋身比较短,用于模仿旧社会女性三寸金莲的小脚,穿上这种鞋子跳舞只能用前脚掌着地,难度非常大。踩得好,获得了“小金莲”的美名。
冯国佩在长期的表演生涯中,不仅熟练运用花鼓灯的各种舞蹈语汇和造型,还自发编创了许多的动作,比如通过观察老鹰在天空中飞翔的姿态,发明了“老鹰展翅”,看到野鸡受到惊吓时扑腾翅膀的样子创作了“野鸡溜”,他还从武术、杂技、劳动中寻找灵感,创作了“单拐弯、三回头”等动作,不仅丰富了花鼓灯语汇,也逐步形成了带有冯国佩个人特点的“冯派”花鼓灯艺术。
二、冯国佩的舞蹈美学特征
有关舞蹈美学方面的探讨,借鉴欧建平先生在《舞蹈美学》中对欧美舞蹈美学总结与阐述,大致上可以分为“模仿论、表现论和形式论”[2]这三大主要学说,并且根据欧先生在后来多年的潜心研究中,更加得出了这三者之间实际上是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的结论,是舞蹈美学从低到高的三个不同层次。那么下文将根据这三条不同的脉络,来分析冯国佩的舞蹈美学特征。
(一)形神兼备的表演
在冯国佩长达八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一直不忘记学艺时老艺人的谆谆教诲,他自小就被老艺人教育要懂得“挖相”,就是通过观察,模仿生活中的人和事,而冯国佩也是个有心人,他不仅这么做了,还做的特别仔细,由于他扮演的是“兰花”,也就是花鼓灯中的女性角色,他特别注意观察农村女性的一举一动,甚至跟在她们身后模仿她们的步态,神态。他通过踩衬子,将农村小脚女性的体态模仿的惟妙惟肖(解放后,他又大胆的放弃了“衬子”这一象征落后女子的形象,使舞蹈动作更为流畅自然)。他还模仿小姑娘端针线扁子绣花描朵的样子、模仿农民们端簸箕筛粮食、扯轱辘纺线的样子等,并由此改进、创造了花鼓灯语汇风摆柳、簸箕步、单扯线、花鼓灯扇花等;他还模仿小鸡受惊时转圈的样子,并编成舞蹈动作“野鸡溜子”,成为花鼓灯舞蹈语言。此外,“斜塔”“拐弯”也是他在细心观察女性的行为特征之后总结创造出来的舞蹈语言,并形成了他“溜得起,刹得住”的“冯派”舞蹈美学特征。
冯国佩在对于外部事物的模仿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形似”的层面,而是迈向了“神似”的更高层面。“模仿”对于冯国佩花鼓灯艺术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欧洲有关舞蹈美学中“模仿论”的说法实际上对于东西方世界来说也是成立的。
(二)舞以尽意的表达
冯国佩在琢磨花鼓灯的表现方法时,充分发挥了模仿的作用,他不仅从外形上模仿,更通过研究女性的心理活动,在表演时从内心深处去打动观众,比如,在席家沟演出传统花鼓灯后场小戏“王小楼卖线”时,他通过平时仔细观察生活中曾受过婆婆和老公虐待的农村妇女,在扮演王妻哭诉时,真的打动了在场的老奶奶和小媳妇,有些观众甚至当场嚎啕大哭,还有的一边抹眼泪,一边夸他演的好。由此可见,冯国佩在表演过程中对把握艺术的“技艺结合”和“艺术的真实”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诣,深得其要领和精髓,并通过表演表现了旧社会农村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从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为了表现解放后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冯国佩在进行“兰花”角色的创作时,也表现出了与解放前截然不同的方式,比如,在动作方面变得更大、更美,情感的表达也更为热烈,从旧社会妇女的笑不露齿、眼不敢看、头不敢抬、腼腆扭捏的动作变成昂首挺胸、自信大胆、泼辣阳光的姿态等等。
由此可见,在冯国佩的花鼓灯表演中,舞蹈美学有关“表现论”的说法也是有充分体现的。
(三)继承中加以创新的独特形式
花鼓灯舞蹈的特点,体现在其各种风格化舞蹈形式和舞蹈动作当中,经过历代的传承,如今已经形成花鼓灯许多固定的舞姿、队形以及表达方式。比如:花鼓灯中男性角色叫鼓架子,女性角色统称兰花。舞蹈表演有大花场、小花场、站肩、滚伞、绕门转子、编篱笆子、九连环、二马分鬃、上盘鼓、中盘鼓、地盘鼓等。
冯国佩在精通传统花鼓灯舞蹈表演的基础上,编创出很多新的舞蹈动作,让他的表演形成了“脚下溜、韵律强、身姿美、情感真、神态媚”的特点,在形式方面充分体现了“冯派”花鼓灯的舞蹈美学特征。
同时,冯国佩认为高超的技巧在表演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一次“抵灯”(花鼓灯班子互相较劲,比赛)过程中,冯国佩运用了一系列的高难技术,赢得了观众们的赞誉,“等我把观众的情绪抓住了,再来一个‘燕子出水’‘砍腿片马’,接着又是一个‘喜鹊登枝’,我们两个玩的真叫得心应手,配合默契,相映生辉,我们冯嘴子的灯真是‘一花独放’出尽了风头。”[3]同时,他认为习舞者的先天条件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勤学苦练才是更为重要的,比如他在评论“野狼”冯国亮时说:他虽然长的粗大结实,看上去又憨头憨脑显得笨拙,但是经过若干年的苦练,也练就了一身的硬功夫,“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个人的天赋条件,固然对自己有很大的限制,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只要肯下功夫,刻苦磨练,天然的素质同样也是可以改变的,正如老一辈花鼓灯艺人经常说的:‘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3]36“要想成为一名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花鼓灯舞蹈演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若没有个三冬四夏的功夫和刻苦锻炼的韧劲,即使能在花鼓灯班子里混混,最多也不过是个“半瓶醋”而已。[3]23
由此可见,模仿论、表现论和形式论这三种舞蹈美学流派,在冯国佩的舞蹈美学特征中,不仅有充分的体现,还体现出了一种逐步递进上升的内在逻辑关系。
三、解放前后冯国佩舞蹈美学特征的变化
在对于花鼓灯舞蹈美的理解上,在解放前后,冯国佩的认识是不同的,有关这一点,在他的作品《新游春》中有所体现。在解放前,《游春》原本是一个三人舞蹈,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社会的影响,《游春》中的少女动作幅度小,纤弱,含蓄内向,很少有夸张、泼辣的动作出现,而且,由于旧社会舞台上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由男子反串完成的,但在《新游春》中,冯国佩通过一系列创新的舞蹈动作,如“单拐弯”“双拐弯”“野鸡溜子”“凤凰三点头”“小二姐踢球”“雁落平沙”等,将新时期少女的矫健、俊美、泼辣、妩媚、天真、活泼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一改旧社会的传统,用了真正的女性来表演这个节目,体现了新时代少女们朝气蓬勃的美,在改造创新的同时,又极大程度的保留和凝练了花鼓灯的元素,提升了花鼓灯的艺术品位和价值。
根据陈琳琳在其硕士研究生论文《安徽花鼓灯“冯派”舞蹈艺术考察研究》所记录,通过对时任安徽蚌埠文化局局长谢克林局长、冯国佩的第一代亲传弟子娄楼及冯国佩本人的采访,也准确传达了冯国佩在解放前后对于花鼓灯审美的变化。
据冯国佩自述,解放前他的动作比较小,比较丑,还要踩衬子,解放后就把衬子放弃了,还把动作放大变美了,花鼓灯表演变的“开朗、奔放、动作美,艺术超群,”而谢克林给的评价是:解放后,冯国佩在外出北京、上海等地的教学过程中,也见识了外面的世界,从而吸收了很多东西融进了花鼓灯,把原先花鼓灯中的扭捏、小气去掉了,冯国佩的舞蹈动作更加开放、在速度和力度方面都有改进,舞姿也变的昂扬了;娄楼也认为冯国佩在解放后,他的舞蹈美学特征、舞蹈感觉有很大变化,但在吸收外来舞蹈动作的同时,冯国佩并没有失了花鼓灯的本色,而是秉承他少年学艺时老艺人的教导——“挖到篮子里都是菜”,在符合花鼓灯特点的前提下,[4]吸收其他的民间舞蹈技巧,为我所用。比如他吸收河北“拉花”中的丢扇、朝鲜族舞快速旋转式移动脚的技巧、芭蕾的挺拔舒展、古典舞的圆润韵味到花鼓灯中,使花鼓灯变得更美、更有特点。
他还率先改变了男扮女装的表演习惯,让真正的女性参与到表演中来;第一个甩掉表现小脚女人的“衬子”,让新时代的兰花女舞步更加稳健;他改变了扇子的握法,使得扇子在舞动起来时更为自由、灵活、优美;他从中国古典舞、芭蕾舞以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民间舞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融入花鼓灯中,在保持花鼓灯特点不变的情况下,改良、充实了花鼓灯的表演,所有的这些改进,都使得花鼓灯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有了一定的国际范,当然更加凸显了“冯派”花鼓灯的舞蹈美学特点。这些都是冯国佩在解放后的所感所悟后再投射到花鼓灯艺术中的体现,也是他舞蹈新思想的具体体现。
解放后,在剧目方面,除了“新游春“之外,冯国佩还新编了一系列反映新社会的作品,比如“送郎参军”“卖余粮”“接模范”等,从创作思路上体现了他在新时代对于美的理解的变化。
由此可见,冯国佩的舞蹈美学特征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他自身见识的拓展而不断变化的,在对美的理解和创作上,他是与时俱进的,甚至是走在前列的。不断吸收创新,以及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
结语
冯国佩这个生于旧中国的农民舞蹈家,在中国民间舞蹈的滋养下成长,在新中国的阳光中沐浴成熟,在接受新的舞蹈理念之后,他大胆地对花鼓灯中封建落后的东西加以革新,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冯派”花鼓灯舞蹈艺术。虽然冯国佩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他通过民间艺人的口传身授以及自己的感悟,形成了“冯派”花鼓灯独特的舞蹈美学特征,从而影响了整个花鼓灯艺术的发展和变革,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