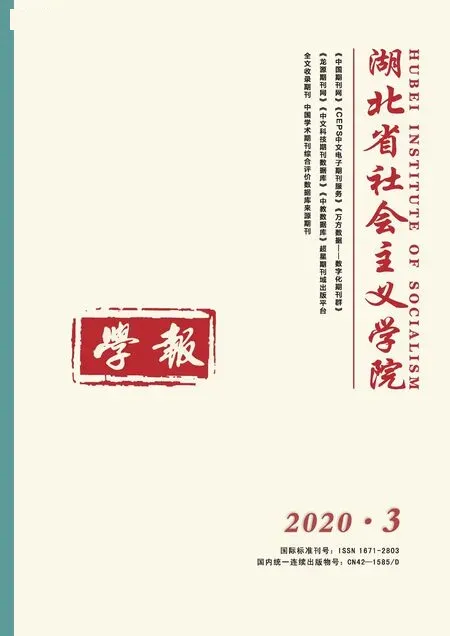浅析“大一统”观念与国家建构
2020-01-16王凯
王 凯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论述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历史性、文化性特征,为推进制度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正如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学者沟口雄三在其“中国基体论”中所述:“中国由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而展开,这体现于漫长的不同时代种种现象的缓慢而连续性变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应该在现代、近代、前近代的关联中来把握。”[1](P111)在塑造现代中国国家制度的传统政治思想资源中,“大一统”观念是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本文拟从历史实践、近代转换与未来超越三个方面简要剖析“大一统”观念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关系。
一、“大一统”观念与古代中国的历史实践
(一)“天下”观念与“大一统”观念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下”的思维观念。《尚书》有“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诗经》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大陆文明早期的一种地理观念,“天下”观念不断向心理层面延伸,《老子》提出“以天下观天下”。“大一统”观念是“天下”观念的延续,发端于先秦诸子百家,成熟于秦汉之际,并最终成为塑造中国文明基体并关联中国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政治思想。
《公羊传·隐公元年》首次提出“大一统”命题,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评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是动词,有张大、重视之意。“统”即开端之意。“大一统”观念强调“正五始”,即“天、岁、人道、政教、国家五端”的归正合一,指周王受天命而改制,应天命而建立国家政统、法统的根本。[2](P3)孟子提出“定于一”,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天下“定于一”,认为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管仲也指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可见,“大一统”观念的内核是“政治秩序的实现”。这是先秦诸子认为天下可以实现大治的关键。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则是政体层面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与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3](P31)“大一统”是政道思维的关键,核心是“秩序”。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古代中国为何始终走不出治乱循环之怪圈”[4](P227)之问大致反证了古人视角之准确。无论是孔子的“礼”、韩非子的“法”,还是老子的“和”,都以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为理想。
(二)地缘政治与“大一统”观念
地缘政治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超大的地域决定了中国地缘政治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安全是政治秩序的根本。古代中国饱受外敌入侵的现实是形成“大一统”的客观原因。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早期地理——政治思想,“大一统”观念既蕴含着“战略缓冲区”“防御纵深”“领土控制”等现代军事思想,也与以陆权学说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颇有相通之处。现代地缘政治学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在1919年提出“陆权说”,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5](P14)之后,被誉为“地缘政治之父”的德国学者拉策尔从“领土控制”和“生存空间”角度发展了地缘政治,认为“国家需要有‘大空间’和有效利用大空间的能力……国家及其制度的发展完全取决于领土、边界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6](P27-30)。
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就立足长江黄河平原,以农耕区文明与畜牧区文明为分野,提出中国版的“陆权”概念——“大一统”观念。“大一统”观念的内涵除了公认的中央集权制度外,还包括涉及国家安全与外交的制度体系。一是打造防御屏障并形成一种“人法地”的朴素地缘学思想。“人法地”思想认为,若遵守地缘的规律,“善用地势”,则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二是建立“中心——边缘——半边缘”格局,营建军事缓冲区、扩大安全地带,如设立都护府、藩属国、朝贡国、土司衙门等。三是“软实力”输出。中原王朝通过对外开放,利用文化和制度的优势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实施扩大国际交往,接收外国移民和留学生,限制武力征伐,优先使用和亲、册封、羁縻等外交政策。由此,形成了类似同心圆“差序格局”的天下体系。当然,以防止内部分裂、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共享、促进人才培养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其中发挥基础作用。
(三)经济基础与“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观念是农耕文明集中资源的现实需要。作为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既依赖水又被水患所侵扰。以黄河为例,她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一条大河,“一碗水,半碗泥”就是对黄河水文特征的描述,每年平均每立方米河水含沙量达34至155千克,最高达391千克,暴雨时局部甚至超过600千克。当黄河干流进入下游,随着河道宽阔,水流缓慢,中游的泥沙便淤积在河床中,每年约有4亿吨。黄河经常性地淤塞河床,易引发堤防溃决。
为治理黄河,客观上需要在黄河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政权,能够整合和使用集体资源,组织动员人民,筑坝挖渠减少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从“炎黄结盟”到“秦并六国”的政治军事因素背后,隐藏着社会希冀权力统一以有效“治水抗灾”的需求。如黄仁宇认为“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7](P26)。同时,在农耕时代,土地产出是国家的绝对财政收入来源。“消除水患,开发水利,王朝才能有更多的收入,才可能展开、维系和拓展其治理,防止可能的社会动荡。……黄河治理因此一直是促使王朝不断强化其政治统治和治理能力的最大动力。”[8](P20-31)反过来,“大一统”观念带来农耕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二、“大一统”观念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研究院考察时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隔断历史。”中国不但没有在历史中解体或湮没,反而总能在一次次危急中自我修复、自我革新,“大一统”观念就是不竭生命力的源头。在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一统”观念通过三层重要的文化对接成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础。
(一)第一层文化对接:“天下为公”与“三民主义”
近代现代化与工业文明的冲击使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官僚制度为支柱的封建王朝陷入分裂与亡国的危机。重建中国是当时社会的共识,但作为现代政治核心价值的“民主”和“共和”观念如何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对接,使其兼容于一个新的现代中国却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课题。
中国是否和西方一样采用三权分立的内部制衡制度或从根本上改造哲学——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消解中央集权的传统呢?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要以“大共同体”为政治基础,即“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结成一块坚固的石头一样”“这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能自由”[9](P818-842)。孙中山的“大团体”是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不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也不主张中国的民权是割裂于民族问题与民生发展问题的纯粹的自由主义民权。
孙中山依据“天下为公”理念,提出了“权能分开”理论,解决了政权与治权的现代性转换问题。一方面,“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融合“民主”,强调“人民集人民权力与意志而形成政权”。另一方面,国家管理者须以儒家提倡的公共责任为己任,“负责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掌握治权,治权交给有能力的职业管理者,其运行受到人民监督”[10](P7)。“权能分开”既避免了西方式人民与国家的尖锐对立,又兼顾了民主与效率,背后是“天下为公”观念对“民权”与“民主”的价值匡正。“三民主义”之民权指向“大政府模式”,认为“真正的民主和民治是真正‘共有’和‘共享’国有公有经济利益的前提”[11](P79-84)。张文蔚指出:“孙氏学说是有目的的对儒教文化、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这三个传统的结合。孙氏相信一个独特和自豪的中国,只要以儒教文明为基础,就会在文化上复兴。”[12](P359)
(二)第二层文化对接:“民本观念”与“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在寻求救国理论的初期,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观念曾广泛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作用。之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建立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从文化角度看,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社会等主张与以“民本”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个体层面,儒家学说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体利益的社会建构性,认为“共同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集合”思维先进于“独立”思维。《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家天下”作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终极平台,这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P1-32)等主张是高度一致的。社会层面,马克思主张“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这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一致。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平等精神及其影响下的抑制土地兼并、干预商品经济、政府救灾等制度使中国具有朴素而深厚的社会主义因子。”[14](P45-138)政党层面,中国共产党主张“人民万岁”,要“夺取全国胜利”和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继承着中国传统的“士人”情怀,而且具有恢复“大一统”的革命主张,从道义上获得了革命和建国所需的合法性资源。战略层面,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大多数”的法宝,统一战线是“大一统”在革命时期的实践创造,寓文化、政治、军事于一体,有效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治理。毛泽东曾将统一战线誉为“天下国家道理”[15](P115)。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为“大一统”政治服务,这也是其今天依然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根本原因。
(三)第三层文化对接:“和而不同”与“协商民主”
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再到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印发,直至党的十八大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协商民主的渊源是中华传统文化。“协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其核心价值是“和而不同”,即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和”文化。《尚书》云:“汝则会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意思是说,如果首领遇到重大疑难问题,除了自我思考外,要分别与卿士、老百姓、负责占卜的官员商量,权衡多方意见后决策。可见,“在上古时期就形成了一套以王为中心的具有开放性的多方参与的决策体系”[16]。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礼法介入政治,儒家知识分子通过察举制、科举制参与政治,一种介于皇权、贵族、平民的协商文化被逐步构建起来。一方面,协商实践较为丰富。“秦朝凡是重大事件如议帝号、封建、封禅等都与大臣商议。汉代协商的议题则扩展至立嗣、立法、人事任免、教育、盐铁专卖、边事、出战、迁都等问题,也设置了针对某项重大政策如盐铁、文教的专题协商会。”[16]隋唐三省六部制以“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施行”的分权设计,强化了以宰相为代表的中枢辅政集团“协商”议事并作为皇帝最终裁决基础的制度。另一方面,儒家知识分子因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特点成为上下沟通的中枢。从历史看,皇权、儒家政治精英与老百姓三者沟通则天下大治,沟通阻断则天下大乱。畅通的协商,一要依赖于皇权机体的健康,二要依赖人才选拔与官僚制度的有效,三要依赖协商机制如集议、清议、谏议等正常运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继承“大一统”“天下为公”理念,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以“求同存异”为行为逻辑。它开辟了与西方竞争性选举民主不同的治理方式,主张“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既继承了“大一统”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又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克服了西方因竞争民主对社会的撕裂及囿于集团私利的民主弊端。林尚立认为:“对中国政治来说,政治协商不仅仅是一种机制与平台,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精神与原则……这种政治精神与原则不仅能够从中央贯穿到地方,而且能够跃出政治领域,同时成为非政治领域建筑秩序创造和谐促进发展的精神与原则。”[10](P53)
三、“大一统”观念与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大一统”观念蕴含着对国家观念的超越性的治理逻辑,体现《老子》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进阶性思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这表明,随着国家实力日益上升、制度体系不断定型和文化更加自信,“以天下观天下”必将超越“以邦观邦”成为引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观念,从而为“大一统”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任何文化都是优劣共存,西方文化注重科学与思辨,但受限于其线性思维与宗教根性。线性思维使西方政治陷于个体、社会、国家的权利分野不能自拔,“民主”从共同体治理工具沦为个体防范共同体的武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始终难以找到理想的平衡点。与中华文化“和谐万邦”“求同存异”的思维不同,西方文明因其宗教根性带有排他性观念。当代西方一系列政治理论如“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都隐含着与宗教相关的“上帝选民”“异教徒”和“审判”思维,其借“民主化”的对外战略使世界长期处于冲突动荡之中。未来,中国“协和万邦”的理念不仅能够保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将为国际政治注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