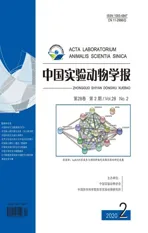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啮齿类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2020-01-15孙浩然徐艳玲李长江连波王艳郁孙琳
孙浩然,徐艳玲,李长江,连波,王艳郁,孙琳*
(1. 潍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山东 潍坊 261053; 2. 潍坊医学院心理学系,山东 潍坊 261053; 3. 青岛大学心理学系,山东 青岛 266071; 4. 潍坊医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 潍坊 261053)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人们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严重精神障碍,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人群中总体发病率为8%。PTSD患者通常呈现出回避、入侵、高警觉、情绪和认知改变等症状。目前,PTSD的治疗主要采用药物(例如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及心理干预(如认知行为疗法)等方法,但治疗效果不理想且个体差异较大。同时,PTSD的生物学机制尚未明确,对临床药物的研发造成了极大困难。近年来,以大、小鼠为代表的啮齿类动物PTSD模型的建立为研究人员探究PTSD相关表现及生物学机制提供了便利。本综述将对大、小鼠PTSD动物模型的建立方法进行总结,为PTSD动物模型的选择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PTSD动物模型建立的一般条件
Willner于1984年提出了动物模型的3个标准,即模型应该与模拟条件具有现象学相似性(表面效度),表现出与人类疾病相同的潜在机制(结构效度),并做出关于治疗效果的正确预测(预测效度)[1-2]。就PTSD而言,其临床表现的多样性与发病机制的复杂性是构建动物模型困难的主要原因。一个良好的PTSD动物模型应当包括能引发与PTSD相似的应激源,使模型产生长期行为症状,且症状可通过确定的精神药理学治疗得以改善,以达到预测效度的标准。由于PTSD产生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尚未明确,因此很难确定结构效度的确切条件。
Yehuda等[3]提出了一个有效比较应激源的标准。其中,至少有5条可用于评估一个模型与创伤后应激的相关性:(1)即使是非常短暂的压力暴露也会诱发动物模型的PTSD行为学或生物学症状;(2)应激源所产生的症状应该是强度依赖性的;(3)产生的生物学改变应能够持续或随时间的推移更加显著;(4)造成的改变应有生物学和行为学的双向表达;(5)个体差异应由经验或基因造成。该标准最初是为评估PTSD研究中使用的应激模型而提出,对当下的研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2 常用啮齿类动物PTSD模型
2.1 单程长时刺激模型(single prolonged stress, SPS)
SPS模型是第一个能够模拟人类PTSD患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gland, HPA)轴改变的模型[4]。1997年, Liberzon[4]初次描述了SPS模型的三个步骤:首先将动物束缚2 h,随后动物在24℃左右的水中进行20 min的强迫游泳,休息15 min后,用乙醚蒸汽麻醉直至其失去意识,最后将动物放置在安静的环境下7 ~ 14 d。SPS模型主要是以啮齿类动物为造模对象,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其中大鼠模型更为常见。研究证实,大鼠经历SPS后,焦虑水平、唤醒程度以及恐惧记忆水平均提高,并出现睡眠异常,且空间记忆和再认记忆、社会交互及恐惧消退均受到损伤[5-6]。多数改变在建模7 d后出现,而非1 d之后,提示SPS诱导的行为学及生理学变化具有时间依赖性。已有研究发现,仅采用SPS的部分步骤建立模型并不会损伤恐惧记忆的消退[7],而具体哪些步骤诱导了PTSD样核心症状尚未明确。尽管多数研究者对于SPS的步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例如,在7 d安静饲养时采用群居或者独居),但是研究结果相对一致。
2.2 束缚应激模型(restraint stress, RS)
束缚应激虽然经常被作为SPS中的一部分,但是,仅通过束缚应激就可以产生PTSD样焦虑症状。根据束缚时间不同,大致分为急性应激模型和慢性应激模型。单次应激时间为15 min ~ 6 h不等。研究发现,急性束缚应激显著提高了大鼠脑垂体的肾上腺髓质素(adrenomedullin,AMD)水平,出现肾上腺功能紊乱,焦虑水平提高,血浆皮质酮水平上升,持续的急性束缚应激能够破坏小鼠部分系统的生理节奏,诱导更高频率的排尿行为[8-9]。慢性束缚应激大鼠还会出现痛觉过敏现象[10]。研究显示,当大鼠第二次接受束缚应激时,HPA轴出现了慢性脱敏现象,且改变了部分脑区的C-fos mRNA的表达,使应激个体对同型应激源的生理反应降低[11]。研究表明,连续21 d(6 h/d)的束缚应激,导致大鼠空间记忆受损,体重减轻,海马CA3区神经元尖端树突萎缩,且存在性别差异[12]。而连续13 d(6 h/d)的束缚应激却能够诱导机体的适应性功能,短期内对大鼠的认知和记忆功能产生积极影响[13]。
2.3 足底电击模型(foot-shock, FS)
FS是一种能影响身体和情绪的复杂应激源。该模型诱导的行为能够满足PTSD动物模型的表面效度,例如持续的恐惧反应,情绪淡漠、社交回避、高觉醒、持续的睡眠障碍、认知障碍和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症状。Siegmund等[14]研究发现,强度为1.5 mA,持续时间为2 s的FS能够使小鼠产生PTSD的核心症状条件性恐惧记忆,并能对雄性B6N小鼠的社交行为产生持久(28 d)的影响。Philbert等[15]发现同样的FS范式能够持久地改变小鼠的睡眠模式,使觉醒时间增多,快速眼动睡眠时间减少,小鼠普遍出现回避行为,长期损伤了认知能力。
FS应激同样适用于大鼠。Louvart等[16-17]给予大鼠单次电击并在随后的3周内,每隔1周将其重复暴露于创伤情景中,以诱导PTSD样症状,结果发现大鼠社交能力下降,皮质酮分泌节律钝化,且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另有研究者对大鼠分别使用高强度电击(3 mA)和低强度电击(0.8 mA),通过社交回避测试以及心理社交相互作用测试发现两组大鼠皆出现社交障碍,高强度电击组有持久的行为改变,低强度电击组的行为改变有时间依赖性,在第28天时达到高峰。并且FS经常和其他应激源,例如SPS,共同诱导PTSD症状,可持续增强大鼠的条件性恐惧行为。
2.4 水下创伤模型(underwater trauma, UWT)
水下创伤是由Richter-Levin[18]在1996年提出的一种建立PTSD动物模型的方式。建模方法为,将大鼠放入撤去平台的水迷宫中游泳1 min,随后,用金属网将大鼠从水中捞起使之不能随意游动。水下创伤不同于强迫游泳,该模型模拟了生活中“溺水”这一应激源的创伤性事件。有研究者从PTSD的闯入性再体验症状的角度出发,用该动物模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19]。研究发现,经历过水下创伤的大鼠,焦虑水平显著上升并且可持续一个月。20 min后将其再次暴露于创伤环境中,可出现空间记忆能力受损,并且该行为可持续存在3周。但将水下创伤的大鼠放入非创伤环境中,空间记忆能力与对照组并无差异。Wang等[20]认为,大鼠在水迷宫中的成绩不佳是由于创伤事件影响了与记忆相关的过程,例如注意力。因此,水下创伤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应激、认知和学习之间的关系。在诸多脑区中,海马、杏仁核以及齿状回与水下创伤模型大鼠的研究联系紧密,其中腹侧海马回被认为是创伤记忆形成的核心脑区。水下创伤能够引起海马CA1区促炎性环氧合酶2的长期过度表达,损伤齿状回的长时程增强以及腹侧海马回和基底外侧杏仁核的ERK-2活动[21]。
2.5 时间依赖性敏感化模型(time-dependent sensitization, TDS)
自然环境下,敏感化是对威胁的基本反应,它可以增强逃生反应,保护受试者免受未来的危险。1988年,Antelman[22]描述了TDS范式,该范式包括一系列短暂而强烈的刺激,随着时间的流逝,建模鼠可对不同的应激源产生长期、逐渐放大的应激反应。常见应用于该模型的应激源有心理性应激源(如暴露于黑匣子或者固定束缚)和药理性应激源(例如注射可卡因)[23]。尽管应激源类型多样,但该动物模型表现出的共同特点是时间依赖性的敏感化,即时隔很久之后施加与之前相同或不同的二次刺激,第二次受到刺激与之前未受过刺激的动物相比,对压力的生理和行为反应显著改变。TDS范式的作用可以在多个水平上观察到,包括行为的长期改变,神经递质浓度,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反应,以及对药物的敏感性改变[24]。
2.6 生命早期应激模型(early life stress, ELS)
研究证明,经历过生命早期应激的儿童更易患PTSD[25]。而母婴分离作为一种生命早期不良事件在人类PTSD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动物研究中模拟母婴分离的具体操作为仔鼠在出生后一段时间内(通常为前21天),每天与母亲分离一段时间。母婴分离会使大鼠的惊反射增强,焦虑样行为增多,在成年期应对轻度应激时皮质酮分泌过多。研究发现母婴分离后的症状表现存在性别差异,但成年后雄性和雌性鼠均可都表现出焦虑水平的提高[26]。
2.7 社交失败模型(social defeat stress, SDS)
SDS广泛用于研究经历反复多次应激的个体行为反应及生理机制。SDS模型的建立通常使用同种雄性鼠,一方为具有侵略性的“定居者”,另一方为“侵入者”,以“侵入者”和“定居者”同处于“侵入者”所占领的区域,双方交战打斗,通常“侵入者”处于劣势并投降[27]。小鼠和大鼠均可建立SDS模型,但由于该模型无法体现女性面对的社会压力,因此雌鼠不能使用此方法建立PTSD模型[2]。SDS的一致结果是社交回避水平的提高,具体表现为更少地与同种动物接触。其他表现为高警觉和快感缺乏(蔗糖偏好的下降,颅内自我刺激奖赏阈值增加)以及奖赏、激励行为和奖赏回路的损害。SDS模型也混合了其他与PTSD相关的表现[28],例如对热刺激痛觉减退,对机械刺激痛觉过敏;但对于恐惧学习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在生物学方面,SDS通过减少前额皮层控制的中介效应使杏仁核活动增多,强力诱导持久性的中枢和外周神经的炎症[29]。同时,SDS可损害睡眠,使快速眼动睡眠减少,非快速眼动慢波睡眠增多[30-31]。
2.8 社会隔离模型(social isolation,SI)
SI也称社交孤立,将拟建模鼠单独饲养3 ~ 4周,失去与同龄鼠社交接触的机会,造成行为、生理上的功能失调以及分子机制的改变[32],如血浆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ACTH)以及皮质酮水平的下降,对急性应激性刺激的反应增强,增加了垂体对外源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CRH)的敏感性,并且通过地塞米松抑制试验测试发现HPA轴负反馈受损。同时有研究发现,SI模型可以很好的模拟PTSD患者对应激事件的回避行为(表现为恐惧反应增强)和恐惧记忆消退的障碍[33]。
2.9 天敌应激模型(predator-stress, PS)
天敌应激的范式包括单一应激暴露,如无保护地暴露于天敌,或有护栏地暴露于天敌,又或暴露于天敌的气味之下[34]。经过这些处理,建模鼠会在3个月内表现行为上或是生理上的变化,包括回避、夸张的恐惧反应、高警觉和痛觉过敏。在直接天敌暴露范式中,如将建模鼠再次置于创伤相关线索中,可测得较明显的回避行为。长时间服用SSRIs(主要是舍曲林和阿米替林)对改善线索回避有较好的效果。
天敌应激造成了HPA轴负反馈增强,暴露后的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皮质酮水平与回避行为之间的呈现负相关关系,提示减少HPA轴对应激的负反馈应答可预测该模型长时程的焦虑样行为[35]。天敌应激模型可诱导持续的脑部炎症,且对抗炎治疗敏感[36]。Cohen等[34]发现,应激后7 ~ 90 d,大鼠的探索行为极端减少以及警觉性提高。这一发现提供了一个区分天敌应激后“易感”和“非易感”亚群的行为学标准,且有相应的标准解决个体反应中的变异。
2.10 不可预计性应激模型(unpredictable variable stress/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UVS)
UVS模型最初用于构建抑郁模型,但由于其能够产生PTSD相关行为表现并且对SSRIs类药物[37]和氯胺酮[38-39]保持长期敏感性,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和预测效度,因此也作为PTSD的动物模型来进行研究。该范式通过使用数种不同的应激源,从而引起拟建模鼠行为及生理异常。应激源主要有:垫料潮湿、无垫料、笼子倾斜、居住拥挤、悬尾、束缚应激、食物或者水的剥夺、天敌气味应激、热刺激、不可逃避电击、剧烈的声刺激或光刺激、社交应激、强迫游泳和昼夜颠倒等。每天随机地接受其中几种应激源的刺激,持续1 ~ 8周时间。UVS模型可以诱导动物产生除特定线索性回避外的大多数PTSD相关行为。有研究表明该模型可使恐惧环路异常(杏仁核及其亚群的c-Fos水平较高),且易感和非易感的大鼠在海马和皮质功能活性方面也存在差异[40]。该模型也能够诱导HPA轴相应后续应激或地塞米松的负反馈调节。
3 PTSD动物模型的研究展望
一直以来,动物模型在PTSD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用于PTSD研究的实验动物有啮齿类动物、兔子、斑马鱼、猪等,而以大小鼠为代表的啮齿类动物在PTSD研究中被使用的最多。由于PTSD在病因和症状上和抑郁症的重合性,许多PTSD的关键症状都已经在啮齿类动物身上实现了重现,而旷场、高架十字迷宫、强迫游泳等实验的开发也为啮齿类动物焦虑、抑郁、社交回避等PTSD症状的检测提供了可能。与猪等大型哺乳动物相比,啮齿类动物易于处理、繁殖速度快、寿命短等特点提高了实验的效率。而对于斑马鱼等低等动物来说,啮齿类动物有更发达的中枢神经系统,与人类有更高的遗传相似性;且被认为与PTSD的发生密切相关的恐惧和焦虑的神经回路在整个进化过程中高度保守,有利于人类通过研究啮齿类动物进行PTSD分子生物学研究[2]。
结合模型分析,所有的范式均可以使啮齿类动物模型在产生焦虑、抑郁样行为的同时诱导其杏仁核功能增强。SPS模型是第一个可以模拟PTSD患者海马和内侧前额皮层中HPA轴的激活以及神经化学物质活性降低的动物模型,其在多个实验室取得结果的一致性为我们研究PTSD提供了一种标准的程序,但其局限性在于缺乏创伤相关线索和性别差异的数据[41]。而FS模型虽然仅有一种类型刺激,但由于使动物产生了条件性恐惧,所以非常适合于进行认知方面的研究。PS模型与军人PTSD的发生尤其相关,因为它与实际或威胁的死亡或严重伤害密切联系,因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由于不同个体对社交和孤独的敏感性不同,因此SDS、SI模型在鉴别PTSD易感性上面较好,但SDS模型不能应用于雌鼠[42]。
正是由于动物模型的提出,使许多潜在的生物学机制得以被进一步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探究PTSD的发病机制,进而研究有效药物或治疗方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动物模型作为间接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因此,在本综述的基础上,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可考虑一下几个方面:
(1)目前没有一个动物模型能够完全地模拟PTSD,每个模型都只能模拟其中一种或几种症状,这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通过不同的模型以及不同的症状表现特点来研究PTSD的发病机制和治疗干预措施。研究还显示,与大鼠的模型相比,小鼠模型需要相对更强的压力源才能可靠地唤起类似焦虑或类似抑郁的行为,因此也需要注意同一物种甚至不同个体在应对压力时的差异[43]。
(2)研究证实,PTSD的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相关研究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PTSD发病机制及治疗干预的关键,FKBP5基因敲除小鼠在内的遗传动物模型已经为应激反应的神经生物学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新见解。HPA轴调节,FKBP5信号传导和SSRI效应的相互作用已经在慢性应激动物的研究中初步得到证实,并且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索[44]。
(3)未来实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可能是探究创伤事件以及更广泛的不利压力条件如何影响整个身体。在这方面,关于血管疾病(例如中风,心肌梗塞)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问题似乎特别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