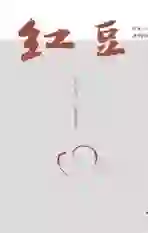贴近生活与历史现场的写作
2020-01-13张艳梅
张艳梅,女,1971年生,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作家研究所所长,淄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作协签约文学评论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已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期刊发表论文近20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2项,出版《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生态批评》《文化伦理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等著作。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2019年转眼成为过去,又到了各种排行榜和年度综述刷屏的时候。梳理分析一本刊物的某个栏目,其实并不容易。首先需要了解刊物的整体定位、发稿原则,以及刊发作品的社会反响,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视野和比较客观的评价尺度。从办刊宗旨到刊物特色,《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钟山》《花城》或《青年文学》《雨花》《西湖》等等,这些文学刊物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定位和风格追求。
就《红豆》而言,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但并不局限于此。2019年小说栏目除第4期长篇小说专号和第10/11期为广西本土作家专号外,其他的都是中短篇小说和微篇小说。作者则来自全国各地,一般文学刊物,多半都有相对集中的作者群和与刊物风格相近的比较稳定的作者队伍。这一年《红豆》刊发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年轻写作者的面孔,他们带给我们的作品,或是针对社会问题,或是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现实主义白描还是先锋叙事探索,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时代生活的现场
重提现实主义,在文学与世界的关联愈发复杂的当下,衍生出太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红豆》2019年小说栏目的作品,大多是朴素的现实书写,其中有人性的温暖,也有人性的挣扎。日常生活叙事之中包含着怎样富有多重意味的现实?我们对日常生活耳熟能详,并不需要小说家提醒我们把目光投放在哪里。小说家应该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看到的,甚至努力观察到的,可能并不是生活的真实,有时候,对于生活的理解,要借助文学想象或是文学虚构,才可能真正有效抵达。
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愁。我们生活在迅捷的时间和凝滞的空间里,日常生活在现实逻辑里自主运行,个体往往是被裹挟的,即使主体经验有多少偏差,都很难在对世界接受的诸多障碍中,自动获得认知的提升。换句话说,身份危机是在文明危机和存在危机的包裹之中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被迫离乡离土,城市给了许多人安身之所,但是也有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在城市中安心生活。
次仁罗布《那片白云处是你的故乡》,虽然小说题目诗情画意,但其实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底色。日常生活里总有一些超越性的东西,只不过大多时候我们被日常性裹挟习焉不察罢了。而这些超越性的东西,无论是痛苦,还是喜悦,都更接近生命的内在本质。多尔衮是社区里的环卫工人,一家人来自草原,渴望在城市里扎根,慢慢习惯了拉萨的生活。“我”和妻子对环卫工人有着朴素的情感,多尔衮善良勤快,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喜欢讲故事,和热爱诗歌的表弟看起来很像。表弟为了追逐自己的浪漫梦想,死在冰天雪地的藏北草原,多尔衮的梦想是让孩子好好读书成为城里人。年轻人对草原早已经没有诗意的想象,那里贫穷落后,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小说最令人感怀的是多尔衮母亲的乡愁。这个始终渴望回到草原的老人,故乡对她来说,没有风花雪月的诗意想象,也没有城市生活的温暖舒适,而她一心想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中去,城市对她来说,永远都是异乡。作为一个客居他乡的老人,最难的不是文化无法认同,而是情感无法复制。小说没有怀旧情绪,也没有刻意的底层关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之中,流动着淡淡的感伤,算是时代情绪的一种记录吧。
于同友《幸福五幕》写的是新农村建设题材。王文兵与妻子韩小兰离婚后,春节带着儿子王子涣回老家。王子涣奶奶之前一直养鸭放鸭,生活中总有一片广阔的水域。住上楼房之后,不能再养鸭,耳朵里却总是能听到鸭子叫,只好深夜偷偷喝棉籽油治疗尿床。幸福花园里这一户人家,有着各自的烦恼,爱始终是主题,子涣有着童话世界的目光,奶奶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乡愁,离婚的王文兵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抱怨。小说里漫漶着的温情很感人。虽然这五幕生活场景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稍显笨拙的生活体验里,反而有着某种让人心安的笃定。
乡村现实反思。福柯在《另一空间中》谈到:“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们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叙事,在很多时候,是在破坏性和整合性之间获取微妙的平衡,巧妙的、智慧的、有趣的叙事方式里,包含着美学的创造性。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先锋小说家不断拒绝现实主义,我们仍旧不会轻易绕过文学的现实感,文学始终都是在场的,作家有着介入生活的思想本能和心理需要,并且始终力图给出现实问题的答案。
王方晨《大国民走失事件》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作为报社记者,去鸣沙庄调查老客意外失踪事件。老客为什么失踪,如何失踪,是否还会回来,并没有交代清楚,小说语焉不详地讲述了在一段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人经历的不同生活和感触。大国民的经历,也是现代中国转型的表征。關于这篇小说的艺术性,王春林在同期评论文章《深度谛视个人与历史记忆的生命般若》中有比较全面深入的剖析。我们总是渴望有些文字可以替代性地说出我们引而不发的那些心曲,走失者太多,不被定义为事件,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迷失和失踪的路上。
邱振刚《天上的桃树》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孤儿,被五伯抚养长大。两个人相依为命,依靠种一片桃树勉强维持生活。后来上游建了造纸厂,污染水土,桃树、庄稼、蔬菜陆续绝收。村民去城里告状,被有着黑社会背景的造纸厂老板派人关押毒打。多年后,男主人公在城里开出租车,看到当年殴打自己的人,整天跪在夜总会门口,被保安打得全身多处骨折,他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冷眼旁观,而是选择送多年的仇人去医院救治。小说还写到了底层的相互温暖。开小超市的女人,同样面临各种骚扰和威胁,两个善良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亮。我们从这些小说中,不断发现生活的复杂性,也不断认识人性的复杂性。
小人物的悲欢。袁有江《下落不明的家》中的“我”是个小偷,跟着干爹老鬼行竊为生。与辉皇酒店的韦经理相爱,二人年龄差距很大,老鬼想拆散二人,最终差点要了“我”的命。小说中写到“我”经历的残酷折磨打击,和心理纠结煎熬,就像那个人到中年、见惯娱乐场和江湖上各种恩怨、依然有着本能良善的韦经理。这些背负着各种不幸的人,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小说对人世的体恤饱含着不欲明言的温情。
邓洪卫《我想跟你谈谈》写三个勤杂工,汤队长,玉芳,玉茹,一起工作生活的互助与矛盾。几个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平凡琐碎的日子,自以为是的正式工,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每个人都有对感情的需要,汤队长脸上五颜六色的茶汤,大桥下舞厅里昏暗的暧昧,玉芳对司机的拒绝和牵挂,都写得平易真实。
那些歇斯底里或无聊的女人。马顿《歇斯底里夫人》是一篇家庭伦理小说。谢思礼的妻子离家出走,谢思礼卖掉北京的房子,回到老家生活,继续在淘宝网上卖衣服。小说有两条线,一是回溯谢思礼和妻子赵清丽吵架歇斯底里拳脚相加的过往。一是与张娟相恋同居,被丈母娘打砸,被迫分手的经过。普通夫妇每天如何面对柴米油盐,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小说对夫妻之间,对刚刚为人母的女性的内心焦虑、困扰,揭示得淋漓尽致。
夏群《双面人偶》中两个女生家境很好,夏智和刘子涵自小优秀,父母严厉的教育,过高的期望,让她们深感压抑,缺少自由,选择去夜店释放发泄,在想象中不断自杀,试图以死亡完成对父母的报复和自我救赎。经历险象环生的高考,形同鸡肋的婚姻,失业求职,为什么不能够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和爱情?两个女孩子都处在自我分裂中。这种分裂究竟意味着什么?单纯是对家庭教育的反思,并没有太多意义。个人处境里包含着的绝望和反抗,作者在自我对话中给出了反思的多重精神维度。
文珍的《淑媛梅捷在国庆假期第二日》,诚如她在创作谈里写到的,这就是一篇流水账。梅捷在国庆假期,没有出去旅游,待在家里无聊,突发奇想去公司加班。在漫长的一天里,她并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事。逛街,吃东西,去公司偷窥同事的工位,各种猜测和臆想,连缀平日里的生活。
近年来,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底层文学,渐渐淡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挣扎于无声的泥泞之中,被抛掷在可能的意义之外,小说无非是把撕裂感触目惊心地张贴于我们伪装得无懈可击的生活高墙之上。作家如何面对这一堵墙,批判现实主义集中火力正面强攻,魔幻现实主义如崂山道士穿墙而过,心理现实主义凿壁偷光,超现实主义满墙涂鸦,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写作者能够直面这堵高墙,并且愿意严肃表达自己的立场。贝克特在1983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这样一个想法中寻求慰藉,也许有一天,也即现在,真正的文字终于从心灵的废墟中显露出来,我仍紧抱着这个幻想不放。”或许,这应该是所有写作者的心愿吧。
记忆的展览馆
记忆与心理,在历史和生命的黑洞里,埋葬着无数的碎片。有多少接近自然和情感的镜头,赋予过往的生活以诗意光彩,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记忆倾向于自我修复和心理补偿。电影也好,篮球赛也好,都具有表演性质,观众也是参与者,尤其是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哪个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呢?今天对历史,或者童年做出的种种回望,很难不带有文化想象力的影响,那些富有仪式感的画面,存在于真实可感的时间长河之中。我们常说,70后可能是最后一代有着强烈的乡愁和怀旧意识的人。在朱山坡和李云雷的小说中,既有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怀,也有对生命存在的清醒思考。
电影院与篮球场。朱山坡《先前的诺言》是“蛋镇电影院”系列中的一篇。朱山坡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不同的故事,细水长流的社会变迁,于无声处的人心回响。风俗人情,生老病死,家长里短,都在小镇年复一年上演。县城的电影院,是神秘主义之源。电影如何塑造世界,与作家如何塑造世界,可能有着很大差别,而在那个时代,提供的是一种艺术品,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超越日常性的生活状态,覆盖吃喝拉撒日常生活之上,通过视觉艺术,尝试着重新理解生活,或者是看待自我,是一种成长,也是一个起点。就像荀滑可以从荧幕里出走,尽管小说这个结尾是超现实主义的,其实又是最符合艺术内在逻辑的。《先前的诺言》是一个典型的悲剧。笔墨依然是轻松的。父亲诺言的悬置,是一个打开的过程,也是一个阐释的过程。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时代闭口不言,时代同样还我们以沉默。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更好的时代,就应该把时代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艺术从来不是孤立的,朱山坡写电影院,目的不在电影本身。电影院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显影器,主观立场更接近所要获得的价值取向。所以那些看起来浪漫色彩的怀旧,深藏着历史理性和意义空间。孩子,棺材铺的老李,对于父亲一生的追溯,未曾实现的诺言,让人泪落。虽然小说写的是往事,我们还是看得出怀旧的表象里有着苦难的反光。孩子被周围人围观,观众在电影院里观看他人的生活,而我们,以怎样的目光去看待那一段历史,无声的观看之中,轰然作响的是敲击那口薄皮棺材的咚咚声。这种声响与永恒沉寂的死亡构成了彼此对视。没有上帝之眼,没有第四个视角,小说从不同位置观察围绕电影院奔走的孩子,这个空间是敞开的,连接生死承诺,又是封闭的,把活着的诸多心愿禁锢在死亡的沉默黑暗之中。孩子的眼睛是移动的,却无法从那个时代边缘移除,仿佛这个世界所有的重量都附加在那两张一元的纸币之上,是最大的荒谬,也是最大的真实。山坡在这个空间之外,还建构了一个心理空间,用于安放那些得不到抚慰的伤痛,安放那些来不及实现的诺言。面对这一深度空间,我们经历的所有对于时代风轻云淡的赞美,都会产生一种犯罪感。这是个现代性话题,也是启蒙理想坚守的价值理性。
李云雷《杏花与篮球》写的依旧是少年往事。如何书写乡村?乡村记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意味着什么?与我们的人生走向和价值判断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李云雷小说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观照。研究李云雷的文学创作、学术立场和艺术追求,对于我们了解70后一代作家的思想轨迹和文学理想,有着重要意义。之前的一篇短文中,我曾经写到过:“云雷写了好多乡村事物,很细小,也很朴素。一树梨花白,一地明月光,乡间小路,河边蛙鸣,云朵,野花,土地,石头,门口的狗,村头的牛,还有最重要的,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亲人。他怀着缱绻深情,默默记录,安静书写,都是日常性的,没有夸张的苦难,也没有随意的美化,不会刻意放大,也不追求所谓的缩影,平静的叙述中有着温润淳厚的情感。”这篇小说围绕杏花与篮球,写六哥的故事,六哥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英俊洒脱,心地善良,篮球打得特别好,给乡村孩子带来了许多成长的欢乐。后来放弃去省篮球队,选择和喜欢的人安安静静生活在乡下。杏花飘落,他依然英俊帅气,转身上篮,就像是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小说中,六哥和代莲的相爱,乡村的劳动打闹,孩子们的追逐奔跑,花开花落,炊烟袅袅,娓娓道来,依旧是散文诗一样的文字,李云雷把记忆中如诗如画的美好乡村和童年生活还给了我们。
战场上的爱与牺牲。书写历史记忆比起复现童年生活要沉重得多。我们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之后,依然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对历史重塑或者试图以新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努力,这种过程往往携带着更多的现代性基因,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传统历史主义的思想路径,作家以怎样的视角切入,如何讲述战争,是对牺牲的怀念,还是对战争的反思,是创伤记忆的疗救,还是沉湎于伟大胜利的光荣,其实关乎不同的史观。
赵焰的《彼岸》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1990年代,“我”与洪春花重逢,就此敞开记忆大门。幼年时的伙伴小玉短暂的一生起伏跌宕充满了戏剧性,追溯的过程同样曲折跳跃,仿佛记忆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物质,散落在时空之中,小玉手稿、对话与搜索记忆相互补充印证,发黄的稿纸,模糊的笔迹,记录的是黄山游击队的故事,似水年华已逝,记忆却历久弥新。多数人热衷于此岸的事物,对彼岸世界没有探求的兴趣,而生命存在本身包含着此岸和彼岸双重维度,合在一起才是全部的完整。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生命和死亡都是考验,现在、过去与未来,就是此岸与彼岸,小说贴着生命历程走进历史深处,一代又一代人的生生死死,饱含着内在的热爱,小说写得如诗如画,又不乏理性思辨,世界包容于此在,而又超越具体时空的困扰,都在此岸世界交融为一体。回溯性叙事里,不断叠加手稿和讲述,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双重复调性。
李俊虎的《太原劫》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太原的一段旧事。徐家与木村家族之间的别离与重逢。由此展开广阔的历史空间。张子影《月色皎洁》既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也写出了枪林弹雨中的爱。新兵袁庆生与护士米如月的历险、共同战斗和模糊的情愫,战友之间的同生共死,自我牺牲,都感人至深。小说沿着一个人的成长,拉开历史帷幕,袁庆生从胆小懦弱,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到最后为了保全战友选择自我牺牲,袁庆生最终完成了他的成长。小说还写到了司机老王、董大中、高兴等人的牺牲。这些牺牲看起来是战争中的必然,对于今天的我们追忆起来,却有着更复杂的思考。那些沉默在历史深处的灵魂,意味着我们对历史认知和重新书写历史的可能。
在先锋的话语场
很高兴看到这一年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提供了新的审美要素。小说是理性的产物,不经过思考的小说只会停留在生活的表象。思考抵达的深度,就是小说表现生活的深度。当下小说写作,充斥着各种后现代物化和欲望的碎片,这些显性的物质漂浮在文字河流表层,既不能呈现河流自身的样貌,也遮蔽了水面之下更深邃广阔的世界。这里面涉及到表达的本质和自由。文学阅读,其实就是在众声喧哗的驳杂表达里,辨析作家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写作者书写的价值所在。
房伟的《阳明山》是对话,是自语,是对历史讲述的重构。讲述的过程比历史本身具备了更重要的表意性。或者说对话本身被赋予的能指和所指,超出了历史真相。房伟在创作谈中写到,这是他的幽灵战争系列的收官之作。他对当下的历史小说写作不满,无论是过于局限于史实,要么是胡乱戏说。在这篇小说中,他引入符号学话语,用写学术论文的方式讲述历史和战争。读完小说,我们忍不住追问,历史真的可以符号化吗?那些血肉模糊的死亡和伤痛,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过滤,真的可以抽象為无聊和虚无吗?房伟的思考和追问,既是为历史设喻的过程,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从更隐秘的角度祛魅的努力,人类心理上的成长,还远远没有走出贪婪和暴力的循环。这种先锋叙事,为抽离出来看历史提供了另外一重视界。
黑丰的《弥漫》是对死亡的凝视,同样是先锋的。死亡被符号化,一个女孩子一生被死亡和噩梦纠缠。梦境与现实,自我与他人,窥视与围观,出走与梦魇,蛇,原梦,灵魂,爱,臆想与理性。被抽象化了的死亡,更像一个具有多重意义指向的符号。死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当内心深处的孤独,战胜了世界的召唤,死亡唤醒了自由的可能形态,生活并没有确定不移的意义,而虚无往往能够迅速俘获一颗备受摧残的心。当单个人面对庞大的世界深感无力、无趣和无意义时,自救永远都是最终极的拯救,如果不能唤醒内心的力量,他人的爱与慰藉,无非是面对世界的隔离带。
综观这一年的小说,有些作品在生活表现和艺术探索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还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停留在对生活表象的呈现上,艺术品质还有待打磨和提升。如何书写今天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面对严重的同质化写作现状,写作者要有勇气直面问题,既依附于时代,又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今天的文学写作者究竟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如果我们还愿意接受文学创作应有所承担的话,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写作者来说就必然是一个永恒之问。写作需要正视时代生活的勇气,无论是同步,还是错位,无论是敞开,还是幽闭;克服问题意识的匮乏,理解小说美学的多样性;在充满不确定的生活之中,建立起来一种稳定性的写作立场。
责任编辑 丘晓兰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