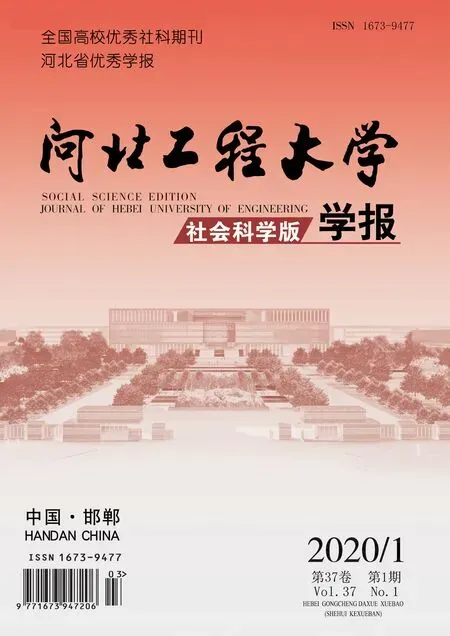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保护机制探析
2020-01-09王力康
王力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保护机制探析
王力康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市 20004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社会恐慌、焦虑会使公众对于知情权的渴求进一步增大。如何在保障特殊时期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维护好患者隐私权从而稳定社会情绪,守护法治社会之基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有依法应“急”,依法防控,在维护社会公益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每一位患者人格隐私之利益,才能驭法治之利器克时局之多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患者隐私权;隐私权;知情权
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席卷全球。截至3月末,全国已有8万余确诊患者,对国家对人民对日常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害。在疫情面前,在疫情防控面前,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依法治疫,合规行事。加缪在《鼠疫》中曾言:“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1]。而诚实、信任则是法治国家公民应有的道德精神与人本情怀。人与人之间只有秉承互信,通力协作才能打赢这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歼灭战。在疫情初始,由于过度压抑敏感,导致一些入院患者的个人隐私曝光于网络之上。鉴于此,如何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维护、保障患者隐私权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患者的个人隐私权、个人信息权,更涉及社会公众情绪的稳定,如何在疫情面前维护患者隐私权的同时做到及时合理适当的公开患者信息是稳定社会情绪,抑制恐慌,遏制谣言的必要之举。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之界定
从隐私权到患者隐私权再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患者隐私权,三者不是独立的概念范畴,而是递进关系、属种关系。概念的内涵外延皆在隐私权的基本范畴中。只有对三者涵盖内容及适用对象范围的厘清才能正确处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关于隐私权概念在实体法中的规定,可以管窥于《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典(草案)》第四编人格权中第六章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保护的规定①《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民法典(草案)》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现行立法对于隐私权的概念缺乏清晰的定义。学界对于隐私权概念的定义也不近相同,杨立新教授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对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2]。王利明教授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3]。张弛教授认为:自然人可依法支配私人秘密信息且不受干扰或侵害的精神性人格权[4]。详鉴于学界对于隐私权的各种表达可以看出,人格性、个体性、私密性是隐私权所涵盖的三个基本特征。三个特征中犹以私密性更能概括隐私权的自身独有内涵。与私密相对的乃为公开,每一个社会行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公益不涉之生活状态可评价为其私益生活领域。私益,表明其隐私权益之表达与否依行为人主观状态意愿之表达,不以公共利益为取舍、左右。简而言之便为无涉公益之区域即为私益之属地。而且从学界关于隐私的定义也可看出,隐私权的关键便是私生活的信息是否公之于众取决于行为人本身意志自主决定以及私生活领域不受外力外人私自干扰。私密性可以说是隐私权区别于其他人格权的根本标志。1960年,普洛塞(Prosser)教授在对相关案例梳理的基础上,将隐私权的保护总结为四种类型:其一,公开他人隐私。其二,侵扰他人生活安宁及私生活。其三,公开扭曲原告形象。其四,窃用他人姓名以及肖像。[5]从对隐私权的保护以及概念界定可以看出隐私权的内容主要包括隐私维护权、隐私支配权、隐私利用权、隐私隐瞒权。
关于患者隐私权的定义可见于《侵权责任法》第62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掌握隐私权及患者隐私权的基本定义后,可以看出患者隐私权并非属于新型权利类型,与隐私权实乃属种关系。且62条对于患者隐私权的界定与一般隐私权在概念及保护客体上并无实质差异。首先患者隐私权的主体与一般隐私权主体相同,同为自然人个体,而其客体为自然人(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不涉他人利益及公益的个人诊疗隐私,其中包括患者生理习性、诊断疗程、用药方法等,其核心依然是对患者在医疗机构诊断康复活动中对其人格利益的保障,与普通隐私权一致,但凡不涉公益则凭行为人(患者)之主观意愿决定其隐私公开与否。所以与一般隐私权的基本要素相同,即个体性、人格性、私密性。其次,从62条规定的表意来看,其意在强调,医疗机构场合下的医务人员应当注重对于患者病历、病情及其个人信息资料的保密,不可擅自泄露。所以患者隐私权依然属于隐私权概念之范畴当中。而患者隐私权的内容具体包括如下方面:第一,涉及患者生理特征、健康形象的私密。第二,患者的疾病史、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生活史、婚姻史。第三,患者家族的疾病史、家族基因及生活习性。第四,患者的个人信息资料,包括人际社交范围、财产状况经济能力、个人姓名住址等基本情况。而在此次冠状病毒患者的个人信息泄露中,第四类患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尤为显著。
通过对隐私权及患者隐私权概念的界定厘清可以进一步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的概念进行明晰。首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概念源于2003年为应对非典疫情国务院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条例》第2条规定: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疫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从规定可以看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三大特征:其一,突发性,即是不可预测,突如其来的事件。其二,公共性,即在公共卫生领域发生。其三,危害性,即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或可能造成极其严重之损害。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界定,可以看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由于客观公共属性的特质则与普通患者隐私权有所不同。因之公共性所涵盖面之广,突发性之快,危害性之大,所以在隐私权的保护方面较普通患者隐私权保护更加突出公益,则患者在合理范围内必须做出合理披露义务以维护社会公众之公共利益。而对于在突发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保护的方向上则更加偏重于患者个人信息尤其是姓名、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的保护。对于患者病情及病因由于涉及社会公众之必要安全则私密必须让位于公益,赋予医疗机构及相关部门合理披露之权限。所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可以界定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中,患者为社会公众利益健康之需要,适度披露自身病情病因及相关行为行事之余,对于自身不涉社会公共利益之个人秘密信息及私有领域之维护。而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平衡公众知情权以及患者隐私权,拿捏好“度”,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曾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讲过:“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能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6]事实上关于隐私权的法理基础与分析也是一样,从不同的角度(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去探析不同的侧重点会有不同的法理、立法倾向。但在根本上来讲,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概念,在权利属种上属于“人格权”大类。既然人格权是与个人的人格价值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的权利,那么隐私权在人格权内涵的涵盖下其核心保护的法益乃是人性之尊严,故而隐私利益的保障是肯定及必要的。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平衡
在经济高速运营发展的今天,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所以对于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尤为重要,尤其是突发事件来临时。由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会超乎事件本身,对社会运营体系、社会经济生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作为个体的社会公民又无法对整个危机事件的全局做出精准的判断与理性的分析,所以大多数人将危机发生时信息的披露以及预防措施的布控寄希望于公共管理部门,以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透明的信息反馈,从而掌握一手的信息资料做出判断应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果缺乏客观、真实的信息沟通,无法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则必然会引起极度的民众心里恐慌、焦虑等负面心里情绪。在青萍之末,危机之初,由于普通民众面临着信息获取的延迟性、不对等性、不完全性,如若无法及时从国家正式媒介中获取真实信息,则各种信息就会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失实传播,这种传播往往具有快速性、失真性、放大性,从而形成极具情绪性和感染力的谣言干扰社会稳定造成民众恐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涉及的风险信息不同于国家的政治信息及安全信息,但却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所以对于公众知情权的保障是必要的。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众的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它是社会公众对于和自己有关事务以及有兴趣的事务和公共事务接触和了解的权利。完善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求保障公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知情权,是提高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必要之举,更有助于社会情绪的稳定及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
但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适度”的披露患者个人信息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平稳社会恐慌情绪需要进一步思考。尤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重大传染疫情肆虐全球,例如时下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还有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在这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一般不希望医院向媒体公布其诊疗过程,且在官方公布患者的活动区域,接触对象,家庭成员社交方面,患者也希望在合理的限度内保护其个人隐私,仅在涉及公众健康安全方面合理公布其个人信息。在面对流行病学以及传染病学的药用临床分析,以及医疗资料的分享研究上对于患者个人隐私的要求在客观上有很大增进,从而对患者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公共利益与患者隐私权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
不论是否存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患者隐私权都应该给予保护,我国实体法关于患者隐私权保护的条款详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因违法实施行政管理或者预防、控制措施,侵犯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一般而言,当患者隐私内容侵害到他人利益时,立法和司法上常常会要求患者披露隐私,但在现实中如若依此要求则时常欠缺操作性,并且在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从法益维护及价值取舍角度来看,患者病历之隐私如若涉及公众之利益则需屡行披露义务以满足公众之知情权益。在立法及实务操作中虽然会有明显的倾斜、导向,但具体操作时仍需价值判断、司法衡量。例如在此次对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隐私权的处理中,一方面《传染病法》、《条例》规定各级机关一经发现疑似、及确诊病患应立即上报。在此情形中医务人员不得以患者要求保护其隐私而拒绝上报患者病历情况。另一方面立法又要求各级机关要严格保护患者隐私,严格监管,禁止泄露患者有关个人隐私。这表明知晓患者隐私内容的仅为相关部门而非社会公众,满足社会知情权也非将患者隐私全部公之于众。那么在重大疫情防控面前,为了稳定社会情绪,又不得不突破仅职能机关了解患者相关隐私的这个限度。有必要向社会公布患者的活动轨迹以及社交范围以达到抑制恐慌的作用。所以如何把握好患者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度”的掌控是问题的关键。
在实务操作中,法院及各级职能机关要通过价值位阶判断以及具体突发事件的客观情形进行利益衡量。一般来讲,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存在病毒扩散,可能导致难以及时有效抑制的客观性,患者应在维护必要公益的限度内克制自身隐私利益的行使。但同时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应当限缩(即在保障公共基本生命健康权、知情权的限度之内)否则患者隐私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将徒有其名。在涉及公众利益及他人基本利益或者为满足职能部门控制疫情之必要或医务人员抢救病患之必须,患者则应适度克减其隐私利益。但职能部门或医院获取其隐私皆必以客观之必要为前提。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保护机制探析
此次的新冠病毒的侵袭更像是一张奇特的魔镜,映射出了社会管理中的诸多不足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新冠病毒不仅是一场自然病,也是一场社会病。“人类是摆脱不掉自然的,他只能为自己创造出另一个可以支配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社会”[7]。法律便是通过对“社会病”的治疗而间接医治“自然病”,问题永远难以避免,关键的是把一切的行为、操守、意识纳入法治轨道,保障公民权利,依法而治,依法而为。在突发事件中,由于事件急迫、形势危急导致公众心理失衡、恐慌,存在倒逼政府过度公开患者隐私的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是在现代化法治国家建设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以及各方权益的维护都是以基本法治原则为准衡,只有依法而治才能稳定社会情绪破除恐慌,保障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转,切不可因一时之动荡而因噎废食。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于患者隐私权保护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患者隐私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主客体的限定性。主体范围涵盖了各级防控职能机关、医疗机构和患者,而侵权者为防控机关以及医疗机构,被侵权者为患者。所以保护范围限制于机关间的信息管理、上报以及医疗机构内的诊疗活动。第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应严格依照我国《侵权责任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对患者隐私权保护的明文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患者隐私权并没有突破基本隐私权概念的涵涉范围。从立法层面分析,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保护和尊重患者隐私权不仅是我国有关立法一向以来坚持的原则,更是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举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信息接触的频繁性和涉及面的广泛性增加了、提高了患者隐私侵害的可能。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客观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患者隐私保护的重要性,基于此,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的保护机制上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增加依法行政,依法防控意识
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侵权责任法》对于患者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明晰各级职能部门、医疗机构在处理患者隐私权问题上的职能以及权限,实行问责机制,严格保护患者个人隐私。对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状态中,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以《传染病防治法》、《侵权责任法》中对患者隐私权保护的条款为准。
第二,严格明确患者个人信息的公布限度以及权限
对于患者个人信息的公布需交由专门机关统一行使。对于患者信息公布的限度,以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保护人民健康权益为第一操守。合理适度公布,不可越规行事。从此次防疫治理看,合理公布内容应仅限于:患者行动轨迹(路线、乘坐车辆、聚会用餐购物场所)、患者病情(诊疗手段、用药标准、康复说明)。严禁过度披露以损害患者其他人格权以及隐私权。
第三,对于已经造成患者隐私泄露的损害赔偿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以及《侵权责任法》规定依法承担相关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责任方式包括财产责任以及非财产责任。前者包括物质和精神损害赔偿。后者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其中各种责任方式可以并用也可单独使用。
第四,患者如果主观同意披露其个人信息及隐私内容,则医疗机构及各职能部门的主观状态、目的及行为方式则不涉侵权行为。
第五,各级单位组织机构,须严格依照《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支撑个人数据隐私保护。规范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收集程序以及保护措施。对保存公民个人数据以及负责信息监管的相关部门和个人进行引导监督。对于保存的信息、数据,未经法定许可任何部门不得用于商业需求及与第三方共享。疫情结束后数据的保留与销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除了上述建议外,在涉及公民个人与组织机构能为与应为的限度上,除了立法规制,更多的需要社会及个人由内而外的一种法治观念、法律信仰的逐步养成,在客观法律强制性之外而树立一种群己权界的自我束缚、自我克制。在大数据信息海量,互联网广泛应用的今天,数据信息的泄露小到影响个人之私益,大到使国家利益受损。所以在立法规制以及网络科技对个人、国家信息保护技术提升的基础上,在根本上仍需个体树立群己权利义务理念。只有如此,谣言才会止于智者,社会于风浪中不摇摆于流言四起。
总之,要积极控制、引导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情绪的负面心里,逐步完善、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在保护患者隐私权之余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通过对疫情发布准确、合法的信息以引导舆论走向、引导社会,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里承受能力,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1](法)阿尔贝.加缪.鼠疫[M].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何颂跃.医疗纠纷与损害赔偿新释解[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王利明.人格权法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4]张弛.患者隐私权的定位与保护论[J].法学,2011 (3):43-44.
[5]文森特.R约翰逊.美国侵权法[M].赵秀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patients' privacy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ANG Li-kang
( Law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
Social panic and anxiety caused by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public's desire for the right to know. How to maintain the patients' privacy and stabilize the social emotions under the premise of protect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in the special period is worth exploring.Only through emergency respon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fully respecting the interests of each patient's personal privacy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social public welfare, can we control the sharp weapon of the rule of law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patients' privacy; privacy right; right to know
2020-02-18
王力康(1993-),男,河北衡水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
10.3969/j.issn.1673-9477.2020.01.022
D92
A
1673-9477(2020)01-108-05
[责任编辑 王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