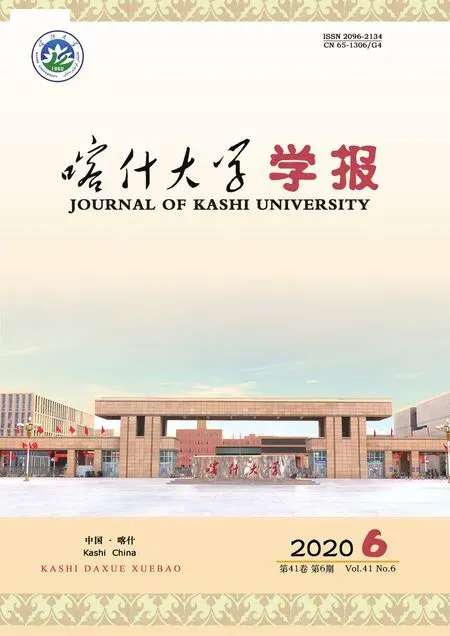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危机及干预和救援对策研究综述
2020-01-08王志锋薛海红田珍珍
王志锋,薛海红,田珍珍,姚 崇
(1.西安工程大学a.体育部;b.学工部,陕西西安 710048;2.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019 年年末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疫情,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流行范围最广、感染人数最多、危害程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止2020 年9 月9 日,全球已累计确诊2748.69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高达89.49 万[1],死亡率达到7.07%,其严重程度已远超H1N1 流感和SARS[2].COVID-19 疫情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精神和心理健康问题,如紧张、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PTSD)、恐惧不安、恐慌、抑郁、强迫症、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倾向等,并被认为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公共心理健康危机[2,3].本文对COVID-19 疫情期间普通大众、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各种心理危机问题进行了综述,并探讨了认知行为疗法和运动疗法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
1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中的心理危机问题
1.1 COVID-19 疫情对普通大众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COVID-19 疫情初期,由于对病毒性质、传播途径、潜伏期的不甚了解以及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等,加上严格的社交隔离和“封城”“封国”等措施等都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4,5].有报道显示,截至3 月25 日,全世界已有150 个国家关闭了学校和教育机构,直接影响了世界上80%以上的学生[6].大规模的社交封锁极易使人们产生无聊、易怒和失望等负性情绪[7,8],以及孤立、无助和被遗弃的感觉.来自美国高校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有71%的学生表示COVID-19 疫情增加了个人的压力和焦虑情绪,导致压力增加的原因包括对自己和亲人健康的恐惧和担忧、难于集中注意力、睡眠障碍、社交受限以及对学业成绩的担心等.此外,由于COVID-19 疫情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不良影响,以及疫情期间社会上传播的虚假或不良信息,都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愤怒情绪[10].还有研究认为[11],COVID-19 疫情对公众而言是一种高强度的紧张性生活事件,是引发个体生理、心理紊乱的重要应激源.在这种应激状态下,人们内在的身心平衡状态被打破,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身心反应,包括紧张、害怕、担心、焦虑、失眠或多种躯体不适.一项由2091 名普通大众参与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2],COVID-19 爆发后一个月,中国大陆居民中PTSD 的患病率为4.6%,在高风险地区(武汉)这一比例高达18.4%.另一项以584 名中国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也显示[13],在疫情爆发后两周,有近40.4%的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另有14.4%的抽样青年有PTSD 症状.国外研究结果也显示[14],COVID-19 疫情爆发后,PTSD 在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从4%增加到了41%左右,抑郁症患病率在疫情爆发后增加了7%,女性性别、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人际冲突、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以及较低的自我恢复能力和社会支持都是导致以上不良心理的风险因素.一项有2458 名美国普通群众参与的在线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示,COVID-19 疫情爆发后美国公众心理健康水平与疫情前相比普遍较低[15].相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16],他们认为COVID-19 疫情可引起广泛的公共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痛苦反应(失眠、愤怒、对疾病的极度恐惧)、健康危险行为(过度饮酒、社交隔离)、心理健康障碍(PTSD、焦虑症、抑郁).对于疫情以前就患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在COVID-19 疫情期间,原有的疾病被恶化.例如,在一项针对32 名饮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患者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COVID-19 疫情期间有38%的患者饮食障碍症状被进一步恶化,另有56.2%的患者认为自己增加了额外的焦虑心理[17].另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在COVID-19 疫情期间有20.9%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症状被恶化[18].即使一些普通流感的患者,由于病情相似进而产生压力和恐惧等心理问题,并且这些精神困扰还会使原有的精神症状进一步恶化[19].另外,污名化和仇外心理也加重了公众的心理负担.被污名化的群体和个人往往会遭到排斥、回避、孤立,甚至会在就业、居住、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20].例如,在COVID-19 疫情中,亚裔群体在国际上经常会受到谩骂或歧视,湖北籍或武汉籍群众在中国内地受歧视现象也屡见报道,因此,来自疫区的群众往往会遭受疫情本身和社会污名化的双重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更加令人堪忧[14].
1.2 对患者和疑似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
有研究结果显示[21],尽管COVID-19 的确诊病例与疑似病例的比率相对较低,大多数病例是无症状或轻微感染,而且该疾病的死亡率也相对较低,但是COVID-19 疫情对患者精神上的影响却十分严重.无论是COVID-19 确诊患者,还是疑似患者,他们除了经受病痛的折磨和隔离的煎熬之外,还会对感染病毒的后果产生极度的恐惧心理,由此所导致的心理问题十分严重[20],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孤独、焦虑、失眠、绝望、恐惧、愤怒和抑郁等[22].一些疑似患者被隔离之后,处于对自身健康的担心或可能对是否感染病毒的怀疑,以及是否会死亡或是否已将病毒传染给家人和朋友的不确定性等,都可使其产生烦躁不安、恐慌和焦虑的情绪[23],甚至还可能产生强迫性神经失调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例如,他们会一遍又一遍的洗手、反复的消毒、频繁的测体温或坚持遵守一些几乎苛刻的预防措施.Jie Zhang 等对57 名COVID-19 患者和50 名隔离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COVID-19 患者中具有抑郁心理的比例达到29.2%,隔离者中抑郁心理比例为9.8%,前者显著高于后者[24].Hai-Xin Bo 等[25]对714 名住院治疗、且病情稳定的COVID-19 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有96.2%的患者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 ss symptoms,PTSS).Nina Vindegaard 等[26]在综述论文中也提出,COVID-19 患者中具有PTSS 和抑郁症状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大众.还有研究认为,COVID-19 疫情可以对患者和医护人员造成进一步的心理创伤,甚至引起妄想症和自杀的行为心理[27].因此,对COVID-19 患者和疑似病例,除了要给予其必要的医学治疗之外,还要积极的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对他们的心理创伤进行及时的干预性治疗.
1.3 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
COVID-19 疫情是对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重大考验,尤其是在疫情初期,由于感染和疑似病例的急剧增加以及医疗资源的相对不足,医护人员常常要在被感染的环境下承担高负荷的工作量,他们身着防护服、工作环境相对封闭,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很容易使他们产生恐惧、疲劳、失眠和情绪障碍[28].Wen-Rui Zhang 等[29]采用修订后的症状检查表(SCL-90-R) 和患者健康问卷-4(PHQ-4)对927 名医护工作者的社会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与非医护人员相比,COVID-19 疫情爆发后医护人员患失眠、焦虑、抑郁、躯体化和强迫症的比例都显著升高,而且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女性、接触COVID-19 患者是失眠、焦虑、强迫症和抑郁症的最常见危险因素.Yun Chen 等[30]和Ling Mao 等[31]的研究也显 示,COVID-19 疫情爆发后医护人员患抑郁或抑郁症的比例增加.J Z Huang 等[32]对中国一家三甲医院的230名医护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COVID-19 爆发后医院医护人员焦虑和压力障碍发生率很高,分别达到23.04%和27.39%,而且护士的发生率要高于医生.来自希腊的研究结果也显示[33],由于医疗资源有限,以及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愿合作或不遵守安全指示等原因,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疾病发病率很高.来自巴西的一项综述研究显示,在参与抗击COVID-19 疫情的护士和医生中,压力、焦虑和PTSD 的发生率很高,女性和护士的焦虑水平分别高于男性和医生,而且医生的社会支持水平与睡眠的有效性和质量显著相关,与焦虑和压力负相关[34].另外,Andrea M Stelnicki等[35]和Benjamin Y Q Tan 等[36]针对加拿大和新加坡的相关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进行的调查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医护人员的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纾解,不仅会影响他们的注意力、理解和决策能力,还可能降低他们的生存质量,并最终降低他们战胜COVID-19 疫情的能力,因此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
2 心理危机的干预方法
2.1 认知行为干预疗法对心理危机的干预作用
面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人们的应激心理反应会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创伤性事件后,受害者是否会发展为PTSD 或成为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个体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恐惧、焦虑和抑郁情绪可以严重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甚至造成认知功能障碍,从而使人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甚至自责、自恨和自杀.因此,提高个体对应激反应的知识水平,纠正其不合理的思维或对灾害性事件的错误认知将对提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大有裨益.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是一系列干预方式的总和,对焦虑、抑郁等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及精神疾病均有良好的干预作用.大量研究已经报道,CBT 可以有效提高肝硬化[37]、冠心病[38]、自闭症[39]、强迫症[40]、乳腺癌[41]以及失眠[42]等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或)生活质量.除了对疾病患者之外,CBT 对正常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仍有促进作用,Qiuyuan Xie 等[43]对65 名就读于中国香港的大陆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 进行了为期3 个月、8 次/周、3h/次的认知行为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组心理健康水平和整体QOL 显著且持续提高,而且不良态度(dysfunctional attitudes)的改变在CBT 和心理健康及QOL 之间起中介作用.另有研究发现[44],CBT 干预还可以提高脑卒中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主要表现为降低抑郁和焦虑情绪等.对于经历过战争或重大灾难性事件的人群来讲,其心理上的创伤也可以通过CBT 干预的方式加以纾解.有研究发现,PTSD 是导致经历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产生自杀意念的主要因素,对于这些具有PTSD 症状的退伍军人实施CBT 干预,可以促使他们主动寻求治疗,并能长期主动保持治疗,防止自杀行为[45].还有研究发现[46],CBT 干预还可以改善低收入群体和武装冲突环境中幸存者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以及创伤后的精神压力.李建明等[47]采用CBT 对SARS患者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后发现,患者的躯体化、强迫症、焦虑抑郁、人际敏感性得到显著降低.综上可知,CBT 干预可以作为重大疾患、安全事件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心理危机干预的有效方法,但是,针对CBT 在COVID-19 疫情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的研究报道还较少.
2.2 体育运动对心理危机的干预作用
体力活动对维持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改善精神障碍和个体心理健康问题都有积极的作用[48].Daphne J Korczak 等[49]的研究发现,抑郁症与体力活动缺乏有关.体育锻炼对于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均具有良好改善作用[50].Esra Tajik 等[51]通过实验研究后发现,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以降低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心理和精神压力.对社区老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52,53],体力活动不足与老年人抑郁和焦虑水平有关,同时低水平的体力活动还可以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体育活动对孕、产妇的产后抑郁症也有良好的干预作用[54],甚至被作为PTSD 的有效干预方法.Lauren M Oppizzi 等[55]曾经报道,体育活动能改善PTSD 患者可能伴随的健康状况(例如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步行、有氧运动或瑜伽等运动项目都可以作为PTSD 患者的有效干预方式.近年来,体育运动在重大灾害性事件后居民心理重建和心理康复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56,57].有实验研究发现,为期2个月、每周3 次、每次30min 的中等强度运动(靶心率为110~130 次/min)可以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层面提高地震后学生的总体心理健康指标,减轻焦虑、抑郁、恐怖和强迫症状,改善人际关系、降低PTSD 评分[58].由此可以见,体育运动可以作为突发灾害性事件中大众心理康复的有效干预措施.但是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众心理健康问题,该采取何种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在何时介入?目前还都需要实验证实.
3 心理危机的救援对策
3.1 建立重大传染病疫情心理危机长效救援体系
与2003 年爆发于广东省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和2012 年爆发于沙特阿拉伯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疫情一样,COVID-19 疫情同样是一起严重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在患者、医务人员和普通群众中均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问题.这些心理危机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纾解,还会导致生理功能的损害,甚至还会引起自杀、抑郁等恶性事件.面对当前COVID-19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现状,以及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新的由某种未知病毒引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积极建立重大传染疫病心理危机长效救援体系已刻不容缓,具体措施应该包括:(1) 在处理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应将从事公共心理卫生方面的专家纳入政策决策层,积极采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2) 建立完备的公共心理卫生干预或救援体系,这方面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措施,例如美国的灾难心理卫生服务网络在“9.11”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9];(3) 培养和储备公共心理卫生工作队伍.专业心理卫生工队伍相对不足是各国都存在的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在平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鼓励更多的专业人员从事公共心理卫生工作,建立高效精干的心理卫生工作队伍.
3.2 遏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是避免公共心理危机的最佳方式
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的基因序列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 的同源性高达96.2%[60],结果提示,2019-nCoV 可能来源于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尽管2019-nCoV的自然宿主和中间宿主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19-nCoV 从野生动物到人类之间的跨物种传播,最终造成COVID-19 疫情的全面爆发已是不争的事实[61].这与早期艾滋病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历程十分相似.因此,要想避免公共心理危机的发生,从根本上阻断野生动物病毒与人类间的跨物种传播,并最终遏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将会是最佳途径.长久以来,自然界和人类之间存在着某种模糊的平衡关系,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在增加,环境污染、自然森林被大面积破坏或被人类侵占,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尤其是一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减少,致使一些野生动物被迫进入人类的生活空间中,进而增大了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风险.此外,一定地区的人们还保持有捕食野生动物的习惯[62],一些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蛇、蝙蝠、果子狸、大猩猩等)很可能是某种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食用这些野生动物必将使人类面临被直接感染的风险.因此,要保护好自然环境、戒除食用野生动物的恶习,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是人们免受疫情侵袭,并最终避免心理危机的根本途径.
4 结语
COVID-19 疫情可以使患者、广大医护人员和普通大众都可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根据SARS 疫情期间大众心理的研究结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众心理健康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对躯体健康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更加持久、更加深远[63].一些心理危机事件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纾解,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抑郁、自杀等恶性事件,甚至还可以引发声援性集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64],对此国家已高度重视.早在2020 年1 月26 日和3 月18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就分别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和《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两份重要文件,旨在全面加强和科学指导各地开展COVID-19 疫情相关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工作.但是,在实践中仍存在个别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心理卫生工作队伍力量较薄弱、心理干预方法滞后、缺乏系统性等现实问题.认知行为干预疗法和体育运动疗法在心理危机干预中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是这些心理干预方法在COVID-19疫情中的实际应用还十分有限,尤其是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的心理症状该如何有效的介入?目前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从长远来看,积极建立重大传染病疫情心理危机长效救援体系,戒除滥捕、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阻断病毒在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跨物种传播途径,遏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将是人类免受心理危机困扰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