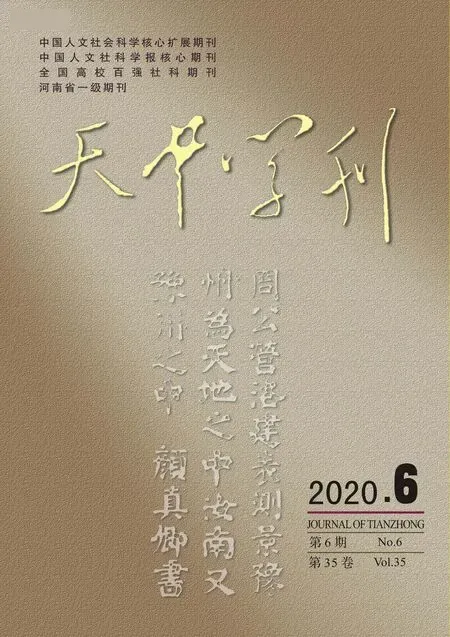西方卫生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传播
2020-01-08王少阳
王少阳
西方卫生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传播
王少阳
(重庆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2160)
随着西方近代卫生观念的引进与传播,中国传统卫生观念开始发生改变,逐渐被赋予了科学、文明和现代性意义,其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艰难。
卫生;近代;文明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既有卫生观念开始逐步发生转变。一方面,它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生”和“保卫生命”的基本意涵;另一方面,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西方近代卫生观念的冲击,它也开始被中国本土的精英人士赋予了诸如“文明”“科学”和“现代性”的意涵,“卫生救国”也一度成为一个响亮的时代口号。
一、近代西方卫生观念的传入
“卫生”二字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庄子》中就有记载:“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趎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1]这里“卫生”主要指“保卫生命”和“养生”。近代以来,在殖民入侵与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卫生观念开始逐步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精英人士不断对传统“卫生”概念加以重新解读与运用,最终促使“卫生”演变成一个与“Hygiene”相对应的具有丰富的社会与文化意涵的现代词汇[2]。而作为与现代西方文明相伴而生的近代卫生观念,则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与文化意涵:“自19世纪以来,东西各国于卫生一道莫不极端讲求,不遗余力,久为世人所推许,其种族之强,国家之盛,良由是也。”[3]因此,“卫生”不仅被视作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近代国人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复杂性[4]。
一般认为,东亚地区近代意义上的“卫生”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1873年,长与专斋结合中国《庄子》中有关“卫生”的记载以及西方Hygiene的现代意涵,将“内务省”更名为“卫生局”。此后,“卫生”在日本逐渐成为一个通用词汇,日本的近代卫生事业也随之取得了长足发展[5]。中国直至光绪年间,随着西方现代卫生知识不断输入,传统汉语语境中的“卫生”概念才开始悄然发生改变。为方便读者理解,中国早期的汉英字典和译著中较多地使用了“保身”“养身”“养生”“慎疾”等中国传统词汇来指代现代意义上的“卫生”。
1881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学者傅兰雅翻译的《化学卫生论》一书,是国内目前已知最早冠以“卫生”之名且与近代“卫生”密切相关的译著[6]。它丰富了传统“卫生”概念的内涵,为此后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卫生学著作翻译提供了很大便利①。而1883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翻译的《卫生要旨》一书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卫生学著作,该书除介绍一些日常卫生知识外,还特别强调了国家与社会在卫生事务中担负的重要责任,从而将以往仅作为个人私事的卫生问题推衍为国家与社会需要重点考虑和推行的要务[7]。此后,近代意义的“卫生”不仅频繁出现在书名中,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正文中,其中很多用法也与今日大致相同[8–10]。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作为日本明治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卫生行政日益受到中国社会的瞩目。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促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人士开始积极主动吸纳西方现代卫生知识与观念,并尝试创建现代化的国家卫生行政体系。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先进经验来改善中国落后的卫生状况,以期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11]。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日本的近代卫生文化与制度,由于日语中的“衛生”直接用汉字来表达,这大大增加了中国人使用该词的机会和频率。随着中国人对待西方和日本近代卫生文化与制度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主动,大量与此相关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近代“卫生”的内涵,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近代“卫生”增强了认识[12–13]。
直到1905年,在借鉴西方和日本近代卫生行政经验的基础上,清政府设立了卫生科[14],标志着国家对近代“卫生”的认可。此后,近代“卫生”的使用越来越大众化,并最终成为一个表示维护健康、预防疾病等含义的社会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使得近代“卫生”观念基本得以确立。与此同时,近代“卫生”仍具有一定的传统因子,传统“卫生”的使用现象依然存在[15]。
二、近代卫生观念的传播及影响
随着近代卫生观念的输入与传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公共卫生建设不仅关乎个人身体健康,还与强国强种和民族复兴有密切关系,并会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形象造成影响。对此,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不能仅将公共卫生看成一般性的清洁打扫,而忽略其丰富的内涵,故对公共卫生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时人认为,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建设担负主要责任,不仅需要建立相关专业机构,还需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同时,公共卫生建设也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广泛配合与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预期的计划和目标[16]。
为改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局面,有人开始提出“卫生救国”的口号,卫生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此项工作“成功著而费用省,足以祛世人之惑,济行政之穷,为卫生界及教育界所特别注意也”[17]。以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桥头堡的上海为例,当地的卫生教育和宣传最早是由在沪的外国人开展的。比如,1871年,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贾米森医生主编的《海关医报》出版,对传播近代卫生知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8]。此后,以伍连德为代表的中国本地西医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在传播西方现代卫生知识和卫生理念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比如,在1915年上海博医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伍连德举办了一场有关东北鼠疫的专题卫生展览,他利用图画、模型等直观的卫生宣传品向前来参观的民众传播有关防治鼠疫等传染病的卫生知识与方法,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赞誉[20]。
近代的卫生教育和宣传活动主要采取卫生运动、卫生展览、卫生演讲、放映卫生电影、印发卫生宣传品等形式进行。比如,1915年2月,中国博医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会议期间,特邀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组织了一次大型公共卫生展览。他借鉴美国医学会举办公共卫生展览的经验,和同事们一起制作和购买了大量海报、图片、小册子、幻灯片和模型等卫生展览品,在2000多平方英尺的展区内,充分利用它们向中国观众展示结核病和天花给人类造成的种种危害,并传播有关如何防治此类疾病的卫生知识[21]。在1922年5月由上海青年会举办的一场大型公共卫生展览上,胡宣明、胡厚斋等人都陆续发表了有关卫生的演讲,并组织观众观看形象生动的卫生电影,画面清晰,观众赞美不绝。展览场地更是挂满旗帜、彩灯、中国卫生会所制作的图画和古今卫生箴言,并有专门人员做详细讲解。童子部陈列的中华职业学校制作的梅毒及疫症细菌模型标本,则让民众触目惊心。中美大药房、中国化学工业社、华强卫生用品厂展示的各种预防消毒药品,应有尽有,不胜枚举。展览客厅临时搭建了两间诊室,有眼科医生刘尊值、牙科医生叶经甫等现场免费施诊。此外,俞家毅和翟志复等人还在现场进行了滑稽表演,令人赞叹。据统计,此次卫生展览期间,每日约有万余人前来参观[22]。
举办卫生运动大会是近代卫生教育宣传的另一种重要途径,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1928年4月,经上海市市长张定璠提倡,上海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卫生运动大会,仅开幕式当天就有万余人前来参加。会上,张定璠积极阐释了卫生对于市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公共卫生,是要各个市民都能够完成自己的卫生工作,以免妨碍他人的卫生利益,务使全市人民都得到身体上的健康,精神上的愉快。进一步说,市民有此愉快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便能免却夭折,日登仁寿,便能努力完成他一生的事业和生活上的需要。我敢说卫生是人类于其生活上的基本工作。”[23]而针对当时我国民众人均寿命低、死亡率高的情况,他也给予市民以希望:“现在,我们为经济和时间所限制,只能就社会上现行的衣食住行各种制度之下,求十二分的清洁和整齐,并将市内不适用的卫生设备加以改革,以减少病菌,减少疫疠,并避免人生不可预测的各种灾害。等到北伐完成,党内的政治完全注重到建设事业的时候,我们还要把衣食住行逐渐改善,务使市民在生活上得到一个总解决,以完成总理的民生主义。”[23]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他还特别呼吁市民积极与政府合作:“今天卫生运动大会,市民来参加的非常踊跃,很有一种除旧布新的气象,并且可以表现出市民革命的精神,可以表现出市民与政府合作的观念,我担负着市政的责任,对此是如何的欢喜。但是卫生不过是市政的一部分事业,其他市政之应该除旧布新,及应该用革命手段于破坏后来建设的还是很多的,自今天以后,我希望市民对于其他一切市政,都要同参加今天卫生运动一样的热烈,与政府合作起来。”[23]此次卫生运动大会的节目有图画文字宣传、卫生通俗演讲、卫生专门演讲、各影戏院加映卫生标语、各游散场加演提倡卫生的歌曲或表演、卫生商品陈列展览会、公开检查身体、游行等[24]。
出版发行卫生书报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卫生教育和宣传活动的开展。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时期出版的卫生书籍就有近4000种之多[25]12。中国近代早期的生理卫生书籍于19世纪70年代后由来华传教士编译并出版,《孩童卫生论》《初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等书的主要内容均来自西方实验医学和卫生知识,主要关注人体健康问题。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精英人士开始积极参与卫生书籍的编译和出版,极力宣扬卫生对于个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近代卫生书籍的编写和出版与社会风气、政治形势以及大众阅读心态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内容涉及人体健康、家庭、学校和军队卫生管理等多个方面。上海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益智书会和上海医学社等机构因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丰富的书籍出版经验以及数量众多的新学人才,组织出版了大量卫生书籍,为近代中国的卫生教育和宣传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26]。随着我国西医医院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卫生报刊也相继兴起。据不完全统计,仅1921至1937年间就有西医报刊237种,中医报刊190多种[25]14。由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华卫生教育会合办的《卫生月刊》于1928年创刊,刊载内容有图书论著、译述、卫生局工作报告、各种卫生法治规则、世界各国卫生新闻等信息和相关介绍,由国内多名中外卫生学专家常年担任义务编辑,选取材料以学术研究和事实报告为主,在刊登医药广告方面有严格规定,坚决不为药物成分不明的丸丹制剂等有害药品刊登广告,并搜集市场上出售的各种药品加以分析,将其中有毒药品的名称刊登出来,“害人药品不致畅销,而市民之受其骗,受其害者日少”,为维护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27]。
在近代家庭卫生教育方面,由于长久以来,中国家庭卫生意识淡薄,“平日起居饮食既已不慎,临病时看护不得其法,药石又复误投,其不死于非命者几希,及一旦酿成疫疠,又无防遏传染之策,以补救于后,故年来各省每至夏秋之际偶起时疫,则十室而九染,朝生而暮死,深堪浩叹”。对此,越来越多的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家庭卫生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应改善中国家庭的卫生状况,以增进民众身体健康与国家振兴,“此事关系至重,小则保全家庭之安宁,而改良其生活,大则增进国民之健康,而谋邦家之幸福”。对于怎么做才可以普及家庭卫生教育,当时有人提出了以下四项措施。首先,在国人最容易忽略的人生日用方面,最应该讲究卫生,如居住室宜通空气,勤洒扫,必须清洁,室无灰尘,以防微生物传染疾病;衣服裁制必须适宜,尤当勤洗,以清净为主;饮食烹调须合法,以清洁为主,尤忌食腐坏之品;疏菜等类不宜置诸地上,又不宜置近其他食物。其次,在日常活动方面也要讲究卫生,如起卧须有一定时限,成人者须卧六时,小儿须卧八时,过多过少,均有碍于卫生;唾涕不宜随意,恐其传染疾病;作事须有休息时候,过劳或伤福经,或伤体力。再次,在养育方面亦需注意卫生,“养育之法,中国古人颇有注意者,然近来每易误用,为害滋大,不可不研究也”。如要避免这些危害,在妇人妊娠时,可以借鉴日本有关种种保卫之法的研究专书。而父母养育小儿不可以放任溺爱,“不知爱儿者,则因放任而种种之病生,溺爱其儿者,则因姑息而种种病生,不可不慎”。最后,在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须注意医师命令、病人饮食、病气传染、病室扫除、交换空气、病褥清洁、衣服洗濯等。总之,家庭卫生教育无论于家还是于国都很重要,其方法也十分多样。“所望研究卫生之学者发宏愿,立大志,或仿日本设立卫生学校,或设卫生演说社,分赴各处演说,尽力提倡,以冀一班社会皆知家庭卫生之必要,则其有益于国家非浅鲜矣。”[28]
综上,近代意义上的卫生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国家命运,需要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其中。“所谓大众卫生是没有阶级的,就是要人人都知道卫生的真意。社会上各色人等,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分贵贱,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应该具备这种卫生常识,躬行实践,以谋自己和人类的幸福。”[29]“盖国家兴衰,以人民之强弱为衡,而人民能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一个国家的文明与野蛮,就是清洁和污秽的区别……卫生是养成健全民族的基础。”[30]诸如此类论述在各种近代媒介上十分常见。近代卫生逐渐成为中国精英借以改造国家、社会和国民的工具,他们把卫生对国家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关注集中在国民身体上,利用卫生来改造一个城市并为自己建立起“现代人”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卫生已包含了一些象征“生命权利”的东西,国家借助卫生这一新工具对国民个体进行管理和统治[31]。首先,卫生的近代化变迁,是中国人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和华洋文化冲突的重要体现,成了双方用以争夺话语权的工具;其次,近代中国的卫生事业引发了不同国族之间的文化互动,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卫生的近代化是都市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都市的文明化进程[30]。
因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卫生始终是人类共同关心和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卫生建设始终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事业。“如今,世易时移,当一份从容和优裕已相对不再是奢望时,抚今忆昔,我们自然不必去苛责先人的努力和局限,但无疑有必要去尽力还原历史的复杂,让今人有机会在复杂的历史图景中,去发现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以及反思现代性的灵感和资源。”[32]
① 此后,傅兰雅以“卫生”之名翻译了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近代卫生学著作,如《居宅卫生论》《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初学卫生编》等。参见罗芙芸著《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34页、王扬宗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4页和第132页。
[1] 庄子今注[M].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599.
[2] 余新忠.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J].東洋史研究,2005(3):560–596.
[3] 天津卫生展览演讲大会布告[N].益世报,1916-05-26(1).
[4] 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1(3):133.
[5] 松本順自伝·長与専斎自伝[M].小船鼎三,酒井シヅ,校注.東京:平凡社,1980:133–139.
[6] 卫生化学论[M].傅兰雅,译.光绪七年格致汇编馆刊本.
[7] 卫生要旨[M].嘉约翰,口译.海琴氏,校正.光绪九年刊本.
[8] 中山市人民政府.郑观应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342–343.
[9] 刘小斌,郑洪.岭南医学史:中[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46–49.
[10] 高日阳.岭南医籍考[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1:518–519.
[11] YU Xinzhong.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cepts of Public Health[M]//Angela Ki Che Leung, Charlotte Furth.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51–72.
[12] 邹振环.疏通知译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88–291.
[13] 陈可冀,周文泉.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210–211.
[14] 郑天挺.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册[M].音序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2786.
[15] 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M]//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273–290.
[16]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39–341.
[17] 高维.卫生教育浅说[J].中华医学杂志,1934(3):409.
[18] 戴文峰.海关医报与清末台湾开港地区的疾病[J].思与言,1995(2):159–160.
[19]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20] Hutcheson A C.An Appreciation of the Conference Exhibits[J].Chinese Medical Journal,1915(2):133–134.
[21] BU Liping.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Picturing Health: W. W. Peter and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in China, 1912-1926[M]//David S.Imagining Illness: Public Health and Visual Cul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27.
[22] 青年会卫生展览会续纪[N].申报,1922-05-12(14).
[23] 卫生运动大会昨日开幕[N].申报,1928-04-29(13).
[24] 卫生运动大会今日开幕[N].申报,1928-04-28(13).
[25] 王东胜,黄明豪.民国时期健康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6]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99–125.
[27] 胡鸿基.卫生月刊之希望[J].卫生月刊,1928(1):1.
[28] 论家庭卫生宜注意[N].申报,1906-06-20(2).
[29]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125–126.
[30] 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99.
[31] 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M].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18–319.
[32] 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J].清史研究,2011(3):54–74.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Health Concepts in Modern China
WANG Shaoya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modern western health concep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concept began to change. Modern health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ty, its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fully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health; modern; civilization
K25
A
1006–5261(2020)06–0142–06
2020-03-08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S13);重庆文理学院引进人才项目(2017RMK48);重庆文理学院人文社科振兴项目(P2019MK19)
王少阳(1986―),男,河南濮阳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