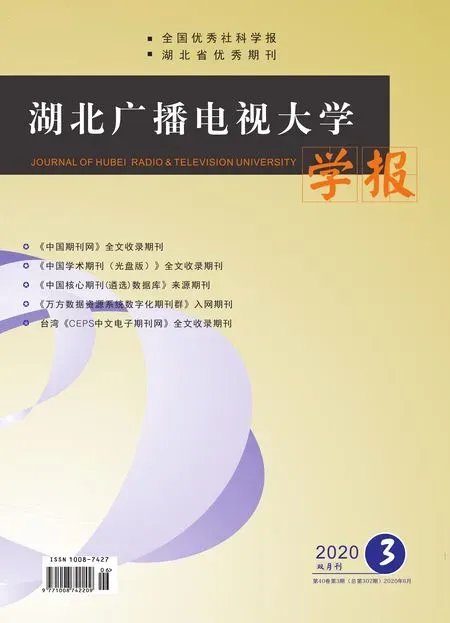论《千与千寻》对日本物哀美学的继承与突破
2020-01-08何刚刚
何刚刚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千与千寻》在内容上吸收了日本美学的诸多元素,而“物哀”作为日本美学的独特理念,对《千与千寻》的形成影响重大。《千与千寻》在故事情节与环境塑造上都吸收了物哀美学。目前很多研究都已触及了这方面,如《日本动画中的物哀美学》一文认为日本动画在影像呈现、视听语言和叙事方法等方面深受物哀美学的影响。然而此文只是从宏观层面分析了物哀美学对日本动画的影响。《宫崎骏影像中的日本美》一文,通过选取了宫崎骏导演的一系列动画电影作分析,认为物哀美学的情感关切包含着对生命美的赞颂,与宫崎骏的人文主义关怀有相似之处。
本文对《千与千寻》中的物哀美学进行分析,旨在说明《千与千寻》实现了对传统物哀美学的突破,从而将传统的价值转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普世价值。
一、《千与千寻》中的物哀美学
(一)“物哀”概念的提出及其流变
“物哀”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他将日本平安时代的美学理论概括为“物哀”,并且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动最深的”[1]。物哀这个概念简单地说是“真情流露”。而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其文学理论就是以物哀为中枢的。可以说“物哀”是紫式部文学思想的主体[2]。物哀可以理解为客观事物引发的主观情感的变化,但是这种主观情感大多数往往表现为哀伤。这种“哀”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表达,利用情感上的“哀”对于客观的外物进行渗透,使得物与我之间发生某种感通与共鸣,形成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一方面,物哀将自我推向于外物,看到万物的兴衰而联想到人世间的生灭;另外一方面,物哀又将外物消解于自我的情感之中,于是外界的自然变化都成了自我的一部分。《源氏物语》一书中出现的“哀”多达1044次,其中有大量的情节体现了物哀美学。
在《源氏物语》中作者将主人公一生的命运与四季的自然变化联系在一起,情景交融,展露出深刻的物哀美学。而平安时期的另外一部著作《枕草子》,也表露出明显的物哀美学。《枕草子》文字表面清新明朗,看起来与《源氏物语》极为不同,但实际上在这种清新背后亦存在一个物哀的基调。川端康成将这种物哀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如在《伊豆的舞女》中他将爱情与环境的描写交融在一起,结局隐含着无限的哀伤。而在小说《雪国》中,他将这种物哀美学运用到对环境的描写之中。开篇写到“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 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面停了下来”[3]。展露出一片孤寂与凄美。总之,物哀美学对日本的文学与艺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千与千寻》对物哀美学的继承
《千与千寻》不论是从环境的描写、故事情节。还是人物的设定等方面都受到物哀美学明显的影响。
首先,在对环境的描写方面,当影片开始,车子穿过幽暗的隧道后,出现的是一个90年代经济泡沫时期所建立的主题公园,蓝天之下葱郁的草地与清新的风交融一体。这种看似唯美的环境与现实的荒凉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而横于水面的铁轨,行驶在水面的列车,稀疏的乘客,这些环境描写完全符合物哀美学一贯的风格。
其次,《千与千寻》在情节上吸收了许多日本物哀文学的故事,其中最明显的是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宫崎骏多次提到《银河铁道之夜》对于《千与千寻》有很重要的影响和启发。《银河铁道之夜》中的主人公乔邦尼和千寻在人物性格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乔邦尼孤独而敏感,他渴望友情与爱,却又不得不逃避在梦境中去实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千寻的故事也是如此。
而且,在一些基本环境的设定上《银河铁道之夜》更是对于《千与千寻》有着直接的影响。尤其水上行驶的列车,夜晚星空之下列车缓缓行进中斑斓的景色,这些对于《千与千寻》画面的使用都有影响。
最后,《千与千寻》在人物的设定上也符合物哀美学的传统。日本的物哀美学可以说在一开始就建立在女性意识的基础之上。物哀所要表达的敏感、多情、柔弱,这些特点正好是女性独有的。而日本电影尤其热衷于去挖掘这种意象。在宫崎骏的动漫中很多都是有关少女成长的故事,这些作品往往用少女的内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少女的成长过程往往充满了忧伤与惆怅。千寻这一角色与成长轨迹完全符合日本物哀美学中一贯的人物形象。
二、《千与千寻》对于传统物哀观念的突破
如上所述,《千与千寻》不论是影片中的环境描写,还是故事情节的发展逻辑,以及人物的设定方面,都受到了日本物哀美学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对传统的物哀美学做出了突破与创新。《千与千寻》立足现代性,挖掘出了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新的物哀意象,这种物哀表现为科层制管理存在的问题,个体的异化与沉沦,以及现代人内心中的孤独感等三方面。
(一)从对自然的物哀到对理性的物哀
在早期的文艺作品中物哀建立在对宇宙荒凉意识的体认之上,它是在人和自然的对比之下,产生出的失意与落寞的感受,这在日本文学中多有表现。如《枕草子》中所说的“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紫色的云横在那里,秋天则是夕阳环照,山顶的乌鸦归巢。大雁排列着归去,日落以后,风声响动”[4]。到了近代,许多文学作品中表现物哀的时候大多依旧利用的是这一手法,尤其以川端康成的作品为代表,更是将这种物哀美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千与千寻》却在继承传统物哀美学基础上实现了突破。
《千与千寻》中的物哀,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的感受性的物哀,而是从对自然的物哀转变为对理性的物哀。《千与千寻》中挖掘出了现代性之下一种新的物哀意象。产生这种物哀的核心原因是现代性的理性管理制度。韦伯认为现代性往往与科层制的管理联系在一起。科层制是历史上技术发展最为完善的一种组织形态, 其专业化与客观化的外表使整个系统的“可计算性”达到最高程度。但却正是在这种管理之下,个人的自由将受到压制。[5]
宫崎骏在《千与千寻》中同样表达了对现代科层制管理的批判。作品中的汤婆婆作为汤屋的主管,她经常化身为黑翅膀的大鸟出门巡视。在汤屋的所有人都要工作。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难以逃脱被剥削的命运。为了便于管理,汤婆婆将千寻的名字改为了“小千”,而与千寻一起工作的人则叫“小玲”,负责烧水的人叫“锅炉爷爷”。在这种管理之下,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中运转的一个零件,逐渐地被吞噬掉原有的生命力,逐渐地服从于这种程序化的管理,而这种科层制的管理正是现代性的产物。
因此,《千与千寻》中的物哀已经不再局限于自然性的物哀了,而是关注对整个现代性管理方式的反思。古典性的物哀主要是在自然与个人的对比中产生的一种私人化的情感。《千与千寻》中流露出的物哀不再是仅仅出于个人的感受,而更多的是在现代性之下个体的异化所造成的悲剧。汤屋里的人被欲望所支配,最终丧失了人之为人最根本的东西。千寻的父母为了美食而变成了猪;白龙为了学习魔法被汤婆婆所操纵,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名字;而汤婆婆本身也受到金钱的驱使,当无脸男拿着许多金子进入汤屋后,汤屋里的人可以违反规则,甚至不顾生命为其服务。因此,汤屋成了对个体的束缚,只有千寻面对着金子依然能够保持平静,对魔法和其他的东西也毫无兴趣。汤屋里的其他人都将他人与自我看成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欲望与制度的冲突之中的悲剧凸显了一种现代性的物哀美学。
(二)从孤寂到孤独的情感体验
古典性的物哀美学所传达的是一种孤寂的情感。而《千与千寻》中则更加强调孤独。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然而孤独却要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才能体会到。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他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6]。孤寂是因为离群索居,造成了一种寂寞感。而孤独则是虽然主体依旧处在人群之中,但是在内心之中却很难与他者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孤寂往往意味着状态上形单影只的寂寞与空旷,而孤独则是在情感上无法与他者产生交流。
在古典性的物哀中更加强调孤寂,而非孤独。如《银河铁道之夜》中的主人公乔邦尼因为被别人所嘲笑,所以很少有朋友,于是“他吹着落寞的口哨,他独自走过两旁都是柏树的黑暗林荫道”[7]。接着书中写到的“斜坡下的银白色的亮光,乔邦尼想象的流星与银河”,都是对于这种孤寂情感的渲染。因此,《银河铁道之夜》中主人公实际上依旧是一种孤寂感。
而《千与千寻》中这种传统物哀美学中的孤寂情感转变成了孤独。虽然汤屋里热闹至极,白龙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但是内心深处对于其他人并没有多少信任感。而无脸男和巨婴的表现则更为明显。无脸男站在桥上看着汤屋里的热闹繁华与人来人往,但是却无法融入其中,直到千寻看见了他,主动和他说话,关心他是否被雨淋湿。在这一次无脸男开始感觉到被尊重,由此对于千寻产生了爱慕的情感。而汤婆婆的婴儿,虽然整日备受呵护,房间里充斥着各种玩具,但是他内心也是孤独的,所以当千寻出现,他用尽各种方法不让千寻离开自己。最后,处在权力顶端的汤婆婆也是孤独的。虽然她管理着汤屋里的所有人,但却难以与汤屋里的其他人发生共鸣,甚至难以与自己的孩子有真正的交流。因此汤屋虽然表面热闹喧哗,但是来往的人彼此充满着猜忌和诡诈,每个人内心中都充满着孤独感。
三、“现代物哀”下救赎观的转变
传统的物哀美学之下,个体最终沉溺在物哀之中,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因此早期的物哀往往与幽玄,甚至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都以死亡作为结尾。传统的物哀美学往往与悲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物哀之下,个体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与彻底救赎的可能性,只能利用梦与幻想营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来逃避。
而千寻并没有像传统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利用幻想和梦境来逃避现实。她之所以能够获得救赎,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对自我同一性的坚守,二是对于自由与责任的平衡,最后是对于爱的追求。
(一)自我同一性的坚守
千寻能够实现救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她对于自我同一性的坚守。自我同一性概念最先由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它是指:个人未来生活目标的感觉, 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内信。因此同一性强调“人必须体验到自身内部一致性, 才能保证行动和决定不是任意的,其二, 内部一致感是跨时间连续的, 即过去的行动和对将来的希望被体验为与现在的自我相关”[8]。而千寻之所以最终实现自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她对于自我同一性的坚守。
在作品中其他人与千寻的单纯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汤婆婆代表的权力机关,为了统一管理热衷于剥夺别人的名字。千寻在白龙的提醒下最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这实际上代表着人对于自我同一性的坚守。在现代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纷繁复杂的角色,尤其是职业的角色对于人的影响最大。这种角色有时会淹没我们的本性,让我们忘记自己。千寻是唯一没有忘记自己的人,她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始终不被欲望所蒙蔽。千寻最开始被汤婆婆命名为小千之后,一度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名字是联系她虚幻身份和真实世界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钥匙,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也就失去了人类社会的身份认同和自我生存依据。而汤屋中的其他人,诸如锅炉爷爷、小玲、白龙,这些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甚至于连汤婆婆本人也是没有名字的。虽然她站在了权力的制高点上,是汤屋的主人,但是她也丧失了自我的同一性。
而千寻的自我同一性除了坚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寻找失去的记忆,获得了同一性的连续性。因为只有如此,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线性,这种同一性才是完整的。钱婆婆告诉千寻“过去的事只有可能想不起来,不可能忘记”。在这种提醒下,千寻不仅仅找到了过去的自己,而且也帮助白龙找到了失去的名字。
(二)对于自身责任的承担
千寻获得救赎还出于她对于责任的承担。在影片开始之初的千寻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小姑娘,因为搬家、换了新学校而一直坐在汽车后座上生气,言谈举止间充满着不成熟。直到千寻的父母被变成猪之后,千寻虽然充满恐惧,但是依旧承担起了拯救父母的责任。即使在白龙的劝说和汤婆婆的威胁之下,千寻依旧选择留在汤屋里工作,她承担起了对于父母的责任。白龙受伤之后,千寻不顾危险去向钱婆婆寻求帮助,千寻发现无脸男痛苦之时,将河神给予她的丸子给了无脸男服用,并在之后带着无脸男和巨婴去求助于钱婆婆,这一切都是出于责任感的驱使。
千寻正是在这种对于责任的承担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救赎。这种救赎不仅仅意味着挣脱原有的束缚,而且意味着获得新的本质。在作品最后,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重塑了自己新的本质。以汤婆婆的巨婴为例,开始他在汤婆婆的溺爱下变得蛮横无理,直到在钱婆婆的魔法之下,变成了一只小老鼠,巨婴在这种落差中实现了自己的蜕变。在去往钱婆婆家的路上,巨婴拒绝落在千寻肩上,而独立行走。当最后汤婆婆为难千寻的时候,巨婴已经站在正义的一边为千寻说话了。千寻自己也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三)“爱”是救赎的动力来源
千寻之所以能够实现救赎固然有自己对于自我同一性的坚守和对于责任的承担,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爱。这种爱既包括对于父母的爱,也包括对于爱情,乃至对于他人的同情。千寻最早只是想救出自己的父母,这是儒家所强调的孝悌之爱。而后来白龙几次帮助千寻之后,千寻逐渐对于白龙产生了感情。因此,在白龙受重伤垂死之际,锅炉爷爷告诉千寻可以去找钱婆婆求助,虽然他也告诉了千寻此行的危险性,但是千寻仍然毅然前往。所以,当千寻出发后,锅炉爷爷感慨爱情的伟大。千寻对于白龙则是纯粹的爱情。
此外千寻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无脸男也有足够的关爱与尊重。如千寻看见无脸男淋在雨中,就将门留了个缝,后来当无脸男痛苦时,她又给无脸男服用了河神给她的丸子。这一切都是源于对于他人的关爱与同情。正是在这种对于爱的追求与升华过程中,千寻不仅拯救了自己,而且让每一个人都实现了拯救。父母最终变回了人,白龙摆脱了汤婆婆的束缚,无脸男有了归宿,巨婴也获得了成长,就连原来冷酷无情的汤婆婆也开始萌生了怜悯与爱意。因此爱才是实现救赎最终极的动力来源。
四、结语
《千与千寻》作为宫崎骏的代表作,其在环境的描写、故事情节,以及角色的设定上都受到了物哀美学的明显影响。然而《千与千寻》中的物哀已经不再是古典式的物哀,而是聚焦于现代管理制度对于个体自由的剥夺、个体的异化与孤独感等方面。在这些新的物哀意象之下,《千与千寻》中人物的救赎则立足现代性的价值观。其救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我同一性的坚守,以及对自身责任的承担,而救赎的动力源于对爱的追求。因此,可以说《千与千寻》受到了传统物哀美学的巨大影响,但其所传达的价值观完全是具有现代性的。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价值的融合之中,《千与千寻》才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