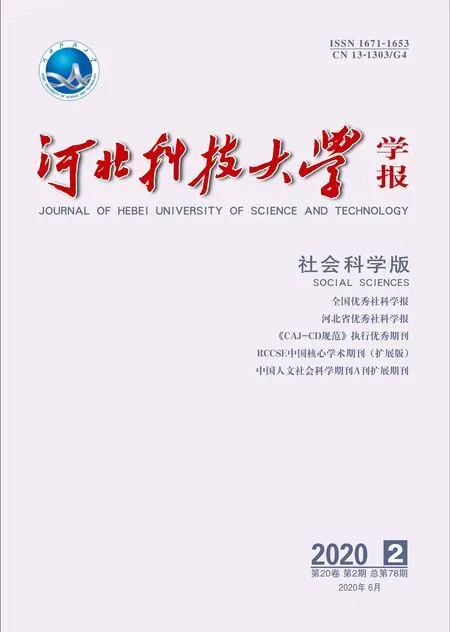豪华落尽见真淳
——黄永玉诗歌精神探析
2020-01-08胡王骏雄
胡王骏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耄耋之年的黄永玉仍然活跃于文艺界,绘画、木刻之余,在文学中也辛勤耕种,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文学在我的世界里是排第一位的”[1](P300)。黄永玉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而他最先接触的便是诗歌:“我写诗,时间不短了……那是1943年左右在江西信丰县,诗人雷石榆和野曼的报纸副刊登过我的一首短诗……题目已经模糊了。”[1](P194)目前能搜集到黄永玉最早的作品是在上海《诗创作》丛刊上发表的长诗《风车和我的瞌睡》。至“文革”结束前,黄永玉的文学创作都是以诗歌为主,但1953年离开香港回京后,笔触短暂停滞,进入潜在写作期。改革开放后,黄永玉的文学创作成果不断,涉猎诗歌、杂文、游记、小说、剧本等多种文体,更是凭借《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于1982年同其他九位专业诗人一道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这意味着黄永玉完成了在大众视野中的身份转变,更标志着其文学创作开启了自觉的时代。此后,黄永玉又相继出版了《我的心,只有我的心》《花衣吹笛人》《老婆呀,不要哭》《一路唱回故乡》四本诗集。201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黄永玉全集·文学编》,其中诗歌卷收录了其诗作共计一百二十余首。黄永玉的文学生涯迄今已逾七十余载,如陈实先生所言,“我觉得(可能是错误的印象)知道文学家黄永玉的人没有知道画家黄永玉的人那么多”,但近年来,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及六卷本《黄永玉全集·文学编》的出版,备受读者钟爱,其中必然也是因为“读他的文章,能感觉作者的心跳呼吸,分享或分担他的喜怒哀乐”[2](P62)。黄永玉一生传奇,倘若说他的绘画与木刻承载的是无尽的理想与抽象,那么他的文字则记载着所有的现实与具体。他是特例,是无以复制,正如他的诗歌,铅华洗尽,只现真淳。
一、真实:“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文艺是社会实践,因此,它并非发自于思想或者其自身,而是源自生活。文艺的生命在于真实,即便作为最自由且富于浪漫理想的诗歌亦是如此。“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3](P55)艺术的特性正是将“客观存在(事物)所显现的作为真实的东西来了解和表现”[4](P200)。真正的艺术作品应该通过合乎规律的方式呈现社会的真实境况、人生的真正面目以及艺术家的真实情感,以其真实、自然、深刻感染读者。黄永玉自始至终都是率性真实的,因而,他是极其善于书写这类别林斯基所推崇的时代需要的现实性的生活的——真实的、真正的诗歌,但没有修习过任何文学理论的他同样明白,艺术的真、诗的真实不同于科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通过诗的真实,读者可以从更多样的维度更直接地去认知客观世界,可以更真切地回归诗人涌动着血脉温度的生命旅途。
1964年,黄永玉赴邢台参加“四清运动”,此后便是暗流汹涌的检举与揭发、批斗与高压。“黄永玉是一位艺术家,他更愿意随性情而行,视感觉而动。现实中许多人与事、是与非,触动他、刺激他,一旦找到合适的方式,便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表达。”[2](P36)于是黄永玉以“动物短句”书写人情冷暖,针砭社会百态,也因此在“文革”前期就遭到了严厉批判。随后,黄永玉几乎是在无数的批斗与劳动改造中熬过那段岁月的。1974年其又因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画作而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成为“黑画事件”的最主要受害者,遭受了公开的讨伐。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生活没有放弃黄永玉,而黄永玉也不曾放弃文艺,经历了“潜在写作”,“文革”结束后,他创作了大量的诗作,真实再现了曾经的苦难时光,激愤地批判“四人帮”的罪恶行径。据黄永玉回忆,“‘文革’末期,天安门的‘四五运动’,忽然诗情大发,一首又一首地写个没完。写了又怕,怕了又写;今天藏这里,明天藏那里。直到‘四人帮’倒台,简直是放手奔腾,李白加杜甫的激情也包括不住。”[1](P195)这些作品均收录进了黄永玉获奖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写作于1979年的《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是黄永玉对数十载社会动荡与生活苦难的真实书写。
人们偷偷地诅咒
又暗暗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
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害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
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哈,谢天谢地,
幸好那种时候,
它永远不会再来临!
在那样的年代里,不少人生活在惶恐中,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原本开往光明与未来的联系远方与故土的火车,却也使得一些家庭处于不安。然而历尽劫难,所有一切最终迎来了光亮,更振奋人心的是,曾经暗无天日的时光再也不会来临了,迎接人们的是改革开放的温暖春天。全诗字字真切,不讲求任何技法,也不刻意追求诗意诗美,但读过后,却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正因其真实而动人。
死亡是令人生畏的事情,然而在那种时候却是司空见惯的。“什么都难,/就是死容易。算一算,/在那个倒霉的年代,/有几个人/能幸福地死在自己床上?能死得合乎逻辑?死得让同志们/来得及哀悼和流泪?……”(《死,怎么那么容易?》)当诗人用一行诗去推敲世界时,才真正获得了死去的资格。死亡无所谓你是否存在,它天然地、必须地伴随着每一个生命而同在,捉摸不透、飘忽不定。死亡也是精神通往彼岸的风帆,超越了时空限制。蒂利希说,人们可以肯定生,但要肯定死则需要一种勇气,而那些能够肯定死亡的人都能在生与死之间自由抉择。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也提出,人们应该时刻追问自己:“我能够死亡吗?我有权死亡吗?”[5](P83)得到了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会明白,能够死亡就不再毫无意义,而人的目标本应是寻求死亡的可能性。黄永玉是不惧怕死亡的,但如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每个人,“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惟愿,/死在自己睡惯了的床上。”(《死在自己的床上》)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黄永玉写下了组诗《天安门即事》,如实地描绘了一张张人民追思周总理的动人画面:“一群褴褛的人,抬着/一个褴褛的花圈,/说是从丰台来的,/说是从丰台走着来的,/还说是一路号哭着走来的……献上他们哭碎的心。”“‘警卫员同志,/让我们进去/和总理告别罢!’/警卫员用沉默/回答少女的要求,/却肃立着跟少女们一起哭泣。/警卫员们像一堵哭泣的墙,/哭泣的少女趴满墙上。”白描勾画,对话入诗,简单自然却情真意切。
“文革”后的中国文学怀着极大的热情批判“文革”,揭露“伤痕”,呼唤“人”的回归,这时期黄永玉的诗歌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创作的,回首往昔,难免会有部分作品受制于情绪的喷薄而略显稚嫩,欠缺诗性。但黄永玉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境遇,更是一代人的痛感,诚如T.S.艾略特所说,拥有了个性的诗人,才能在一定意义上“放弃”个性,获得个性叙述与个人抒写以外的,更为普遍的意义,以完成对个人抒写的超越。“他在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说话的同时,开始为人类说话了。”[6](P167)这正是黄永玉多年以来不变的艺术精神追求。
二、真情:“我深爱这个世界”
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诗即情感的抒发,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最适合表情达意、感物抒怀的文学形式,尤其是源自于《诗经》与《楚辞》的文学传统而传承发展至今的中国诗歌,更讲求诗人情感的抒发。陆机早在《文赋》中就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即便是在探讨重叙事的西方诗歌时,黑格尔也认为,“继绘画和音乐之后,诗更确切地形成了浪漫型艺术的第三方面。”[7](P5)足见诗歌的抒情性一直是古今中外的诗人与批评家更为关注的层面。黄永玉是至情至性之人,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多年的艺术浸染,让他能够更敏锐地捕捉生活的点滴,更自然地抒发真实的情感。
长诗《老婆呀,不要哭——寄自农场的情诗》是黄永玉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时,夜晚弓在被子里,打着电筒,耗费数日写作的。他在诗歌引言中回忆:“那时候家人心情懊丧,日子太长了!展望前途如雾里观河,空得澎湃。启用几十年前尘封的爱情回忆来作点鼓舞和慰藉,虽明知排场、心胸太小,却祈望它真是能济事的。”[2](P90)全诗十三节,共计两百余行。其中前四节,黄永玉用舒缓的笔调回顾了其早年在家乡凤凰的温情时光。童年的黄永玉,通过家的窗口,看“棘园”、草木、城墙、河流、山川,从这明丽的窗口感知世界。“我看云,/我听城墙上传来的苗人吹出的笛音,/我听黎明时分满城的鸡鸣,/还有古庙角楼上的风铃……”然而,十二岁的一个轻率的早晨,黄永玉背负行囊远走他方,从此故乡也就成了梦乡。第五节至第九节,则是对诗人与妻子张梅溪从相识、相知到相爱这一过程的温暖回忆。十八岁时,黄永玉到江西一个小艺术馆工作,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美丽大方的广东姑娘张梅溪。姑娘的天真纯朴以及聪明伶俐深深地吸引了他。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经历,他们终于迎来了希望,在一个小旅馆中举行了极其简单却又令两人终身难忘的婚礼。而张梅溪也就此开始了跟随黄永玉长达数年的漂泊生活,直至黄永玉1953赴京任教于中央美院,他们才算过上安定的日子。“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从一开始,他们就共同面对着无尽的黑暗与哀愁,但握紧彼此的双手,战胜了多少无谓的忧伤。张梅溪的相伴,让黄永玉走出对故乡的漫漫思念,也成为他艰难岁月中温暖的依赖。“我常在夜晚完成的收获,/我每次都把你从梦中唤醒,/当我的收获摊在床前,/你带着惺忪的喜悦,/像个阿拉伯少女/拥着被子只露出两眼,/和我一起分享收获的恩赐。”妻子不仅是黄永玉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艺术知音。最后四节,黄永玉描绘了两人的境况,传达出对妻子深情的思念与感念,同时安慰妻子,坚信一切美好都会很快到来。人至中年,“我们有过悲伤,/但我们蔑视悲伤”,“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生活一样顽强,/生活充实了爱情,/爱情考验了生活的坚贞。”黄永玉被批斗,接受劳动改造期间,张梅溪一直坚强而无悔地支撑着家庭,面对着一切的风雨。即便生活如此困苦,黄永玉也要告诉妻子,在他们的人生航船上,如今还有两个年轻无畏的水手,儿女们终将接过舵和桨,一家人也终会迎来团圆和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全诗感情真挚,语言朴实,节奏多变,温暖人心。正如李辉先生所说,创作这首诗时,黄永玉“超越外界纷扰,回到内心的浪漫,营造诗意的纯净”[2](P46)。全诗读下来略显感伤,但毫无悲观之感,在文革时期那种沉闷高压的气氛中,通过对爱情的真挚吟唱,传达出面对苦难的坚毅与豁达,同时也是对压抑人情、人性的文化氛围的一种反抗。婚后半个多世纪,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因此,在《献给妻子们》一诗中,黄永玉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对张梅溪的情感:“人家说,/我总是那么高兴,/我说,/是我的妻子惯的!/人家问我,/受伤时干嘛不哭?/我说是因为/妻子在我旁边!”年轻时的热烈终换来相守一世的情长。
让黄永玉一生真情相思的还有他的故乡—凤凰。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黄永玉,自小就受到了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化的熏陶,有一个专情文字的表叔,加之凤凰的奇山丽水与风土民俗,注定了黄永玉一生都将与故乡、与文学形成最深的牵绊。在总结黄永玉的文学创作时,李辉将“乡愁”放在首位,因为这是贯穿黄永玉文学创作始终的充满真情与诗意的永恒主题。凤凰,在黄永玉的笔下无数次地呈现,总有不同,却总是最温暖的地方。他曾说,“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要真忘记故乡的一切,是该有多狠心?“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1](P3)他认为故乡是一个人感情的摇篮,它的影响将贯穿人的整个一生。黄永玉更用饱蘸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溪桥夜月、东岭迎晖、奇峰挺秀、梵阁回涛、兰径樵歌、山寺晨钟、南华叠翠、龙潭渔火这凤凰八景,用质朴醇美的诗句赞颂忠诚、辛劳、勇敢、灵巧又强悍的凤凰人民。黄永玉出走一生,却从未走出故乡温情脉脉的目光。“文学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在意大利家里三楼写文章,写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我女儿就问我笑什么,我说写到得意的一段,是关于家乡的事情。”[8](P188)对于家乡的描写,黄永玉将更多笔墨放在散文与小说中,他为文昌阁小学所写歌词中“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想望”可谓是在外漂泊几十载的诗人对故乡所有情感的精准表达。有一首短诗《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更诉尽了黄永玉对故乡的衷肠。
我画画,
让人民高兴,
用诗射击和讴歌,
用肩膀承受苦难,
用双脚走遍江湖,
用双手拥抱朋友,
用两眼嘲笑和表示爱情,
用两耳谛听世界的声音。
我的血是O型,
谁要拿去,他对谁都合适。
我的心,只有我的心,
亲爱的故乡,
它是你的。
黄永玉曾说过,有生命就必然有感情,他深爱这个世界,爱他的亲友,爱河流山川,爱故里旧岁,也爱未知前路。所有情感都见诸于笔端,无论悲苦,无论光亮。
三、真心:“文学让我得到自由”
金圣叹说诗无非就是诗人心中沉积必须说出的一两句话罢了,完成于笔端的诗句,必然生发自诗人的真心。李贽提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若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9](P118)风雨九十余年,黄永玉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对艺术,追求真理与纯粹,对生活,始终享受且乐观。在黄永玉看来,人活着就要有意思一点,而在《全集》文学编自序中,他直言一生的读和写都没有特殊的意义,仅仅出于兴趣。正是这份随性与豁达,让他的诗作返璞归真,清幽恬淡。
黄永玉爱好文学,也说过文学于他是第一位的,但他也多次说,“我写诗,自命不是诗人”[1](P200),“我到底不是诗人。诗人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的。”[1](P195)他甚至还写过一首《“豌豆”诗人自叙诗》自嘲:世人都称赞诗的美好,但于黄永玉而言却并非如此,“只觉得,写诗辛苦”。生活的磨难,让他写下的句子,无关风月,渗透鲜血。“我呼吸苦难得以为是/最后几口气,/诗在脑门上冒着火星。”到如今,艰辛历尽后,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今天写诗,有一张专门写诗的桌子摆在窗口,渴了有绿茶,饿了有饼干,凉了可以套上背心。原本只需要一个宁静的环境就能写出最美的诗篇。但不知楼上住着谁,一整天都弄出声响,完全不知道在三楼住着一个正要写诗的诗人?完全不知道任何声响都是写诗的敌人?直至第二天清晨,“我”实在无法忍受,愤然起身上楼,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位活像“我”母亲的白发的孤独老太太,屋内挂着一个老兵的遗像,摆放着缝纫机和几百双布鞋面,因为老太太想自食其力度过残年。她问“我”是否有需要缝补的东西,“我”只能掩饰羞愧,谎称来寻走丢的猫咪。回到书房,“我”恨不得狠狠扇自己,生活越来越好,人却越发娇气,所谓诗与灵感,都是被优越生活惯坏了的借口。
足见,黄永玉是清醒的,没有忘记一个写诗的人真正来自何处,要如何写诗。这自然是诗人的谦辞,他的文艺创作是献给曾经饱受苦难的人民和他们布满鞭痕的受伤的灵魂的,是为渺茫的希望、绝望的离别、牵肠的思念、污染的友谊和无数永不归来的战斗者,是为这世间所有的美好与丑恶、光明与阴晦、痛苦与幸福而作,更是为了讴歌爬出深渊的勇气、伤口愈合的欣喜、人性的觉醒、爱与团圆的温情和建设新时期的坚定信念。他从未脱离于人民,称自己“和所有的同志一样,/只是苦难和欢乐的/历史的儿子,/故乡和土地的儿子”。(《为了……》),从《哑不了,也瞎不了》,我们可以看到,黄永玉从未改变自己对艺术的初衷。
……
如果,挖了我的眼睛,
再也不能画画,
我,就写许许多多的书。
如果,打断我的双手和双脚,
我还有嘴巴能说话。
……
如果,
把我切成碎块,
我就在每一个碎块里微笑,
因为我明白还有朋友活着,
恐怕所有的人都那么想过,
所以——
今天又出现
动人的诗,
美丽的画
和年轻而洪亮的嗓门。
读黄永玉的诗,感受到的并非是向永恒的春天去逃避,而是居于山巅与废墟之上,翱翔于黑暗与风暴之中,闪烁着星芒。对黄永玉而言,写诗与自由是同一回事,“文学让我获得了很多自由”。[1](P301)因为诗人的触及,个人、历史、未来、传统、故土、他乡、文化乃至人性深渊的所有黑暗都层层绽开,以达到诗歌的澄明境界,实现灵魂与世界的泅渡。
面对生活,经历坎坷与劫数后的黄永玉更加懂得珍惜。曾经的经历时常在脑海回放,灰暗岁月中的小小美好却是比深入骨髓的痛苦更让诗人回味。那是一朵开在白雪肃杀的冬天里的金色小花,全世界对“我”投来冷漠甚至是迫害时,只有它给“我”以微笑。那是残酷汹涌的年代里人性的微光。如今时代改变了,迎来了朝气的春天,繁花锦簇,而“我”怀念的,是那凌冽严寒中的点滴温暖。他是一个烟火气极重的“老顽童”,热爱一切新奇的事物,但也“孤独得莫名其妙,/充实得非常空虚”。(《一张想哭的笑脸》)他是个账房先生,小心地作一些忧伤的记录,也释怀了过往的所有:“我用微笑来表达憎恨。/我屈着无恙的十根手指/细数几十年的风波。”(《老糊涂》)他是旷达的,面对流逝的时光,人生的暮年,他坦然喊出:“老就老吧!/人老,心是活的,/能看,能听,/能呼吸,能爱,/能吸收一切。/那些水和山,/树、空气、阳光,那一切/仍然都是你的。”(《老就老吧!》)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曾写诗想象自己活到百岁的情景:同辈人都已去世,同志们都已不在,唯独留下孤零零活着的“我”,“我是干瘪的橘子,/我是熬过了冬天的苦瓜”,“我”双手皱纹,步履蹒跚,打翻饭碗,烫坏衣裳,“我”还忘记了爱和恨,存在于“我”已与别人无关。死亡或许终究会来,就如同一场旅行,而“我”会收拾行囊,带上旧梦与希望,不惊扰旁人,悄悄离开。“我尝够了长寿的妙处,/我是一个不惹是非的老头,/我曾经历过最大的震动/和呼唤……/我与我自己混得太久,/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好。”(《假如我活到一百岁》)现今,九十五岁的黄永玉依然过得风采卓绝,洒脱超然。
黄永玉说他有很多前辈和朋友是诗人,他们的生与死都不苟且。而他的这一生荣辱历尽,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对生活的至诚热情,可又何曾苟且过!
四、结语
文学创作几乎伴随了黄永玉的一生,然而,他最为被大众熟知的身份,毋庸置疑是画家。而黄永玉的文学创作是独立的,不附属于其美术创作,但二者又并非割裂的,在黄永玉尝试文学创作初期就“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将文学与美术融为一体的创作意识”[2](P208),美术创作的思维方式与经验技巧在其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为自己很多诗作或短句配画插图,呈现出文中有画、相映成趣的审美效果,而文学创作中,黄永玉也自然地融入了绘画的手法技巧,使其文学作品极具画面感,让读者如临其境。
黄永玉的诗歌,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却也是走过了一个由稚嫩到成熟的过程,诗成为他认知世界、思考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承载着他的精神追求。其中最为动人的,莫过于摹写生活的真实、记事怀人的真情以及初衷不改的真心。“他的文学让人重新记起被遗忘的存在,让人怀着乡愁寻找失去的精神家园。”[10](P77)豪华落尽见真淳,黄永玉说他喜欢古今中外的好诗人和好诗。或许他自己还不知道的是,诗人黄永玉已然成为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好诗人,而他笔下的那些好诗也将被更广泛地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