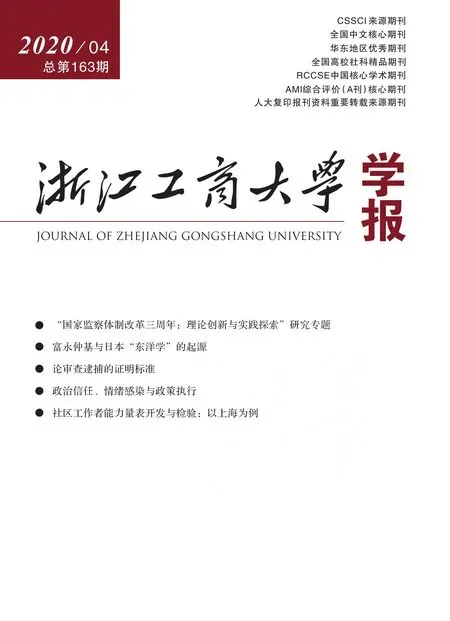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
——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2020-01-07黄继刚
黄继刚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一、 空间经验的缘起及其逻辑演进
空间经验自人类产生伊始就普遍存在了,空间感知被预设为浩瀚无边的虚空,或承载万物的巨大容器,由原子粒子构成的事物在其中按照物理定律运动,它表达出人类对生存世界的基本判断,体现为一种对方位的确认意识,诸如上下左右、远近高低、前后内外等等。但是在这种具体的经验性体认之外,人类意识到还存有总结性概念,它对所有空间经验做出合理而又一致的解释,但这种概念又不是唯一的抽象。(1)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当中,原初的空间经验主要有三种:处所经验、广延经验和虚空经验,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空间观念,即关系空间观、属性空间观及实体空间观。”第一种空间经验是事物的实体存在方式,关乎地方、处所和位置,是物物的相互关系;第二种是“虚空”的状态,是独立于物之外的存在,诸如空房子、空空荡荡的教室;第三种是物体的长宽高等形状差异,是物体自身和物体之间不可分割的空间属性,也就是广延经验。作为对空间的理解和言说方式,明显这时期虚空、广延和处所经验还没有能够综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经验。详见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如果说空间经验是人类共有的普遍性存在,那么空间概念就是对相关经验的总结,其因为地域文化、种族历史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表述空间方位意识主要有以下四个重要概念:处所(topos)、空隙(chora)、嘘气(pneuma)和虚空(kenon)。以“处所”为例,其最早出现在巴门尼德的残篇当中,芝诺对其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稍后的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专门讨论了这个空间范畴,并已然发觉了这种实体空间论的悖谬之处:“处所”具有先验属性,万物都在“处所”当中,事物都依赖于它而存在,但是任何“处所”都不过是空间的局部性区域。这一特性随后也被柏拉图所察觉,“所有存在的东西必然存在于某地,占有一个位置,既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的东西只是空无”[1]。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还是未能够有效地阐明处所和实体的辩证关系问题。
而近代空间概念的超越之处就在于其走出“处所”陷入的自我循环论证,而视空间为物体运动的参照坐标,其帮助物体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并做到了确定处所和虚空的统一,由此空间具有两种属性特质:背景属性及几何化属性。笛卡尔的空间坐标、牛顿的绝对空间和莱布尼茨的“相对空间”是近代空间概念当中的代表性思想。其主要受到自然数学化的影响,使得近代空间成为几何化的产物,并兼具可度量性和三维延展性的特点,这也是和古希腊空间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整体来看,无论阿奎那、牛顿、还是笛卡尔与莱布尼茨都试图将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同科学真理的发现过程相融合,以此来证明客观世界的本质是可以通过科学活动来认识的,并将哲学研究的任务界定为:实现理性对人的主观研究活动及对客观世界的本质性认知活动的真理性和恰当性。由此,空间观念获得不言而喻的自洽性。但我们亦不难看出这种空间概念的悖谬之处:其在经典几何的框架中建构了一个无限、同质的空间,并将之设定为一个整体性体系,诸如牛顿的“实体空间”将空间视为不变的容器,空间成为对象本身的属性;莱布尼茨的“相对空间”将空间视为诸物关系及承接秩序,这两种认知皆是将空间当为孤立于认知主体之外的实体,空间成为万事万物的承载体,其并非物质性的实际存在,最终二人都将空间的生产溯源为上帝的赋予。换言之,空间的绝对性被预设成为自然科学建立的前提条件;但同时人类经验对这种绝对性的存在既不能证明也无法证伪。所以,这种空间观念受到怀疑论者的质疑和诘难,也是应有之义。
康德受惠于莱布尼茨学派的智者氛围,绝对空间在逻辑上先于物之经验的先在性也影响到他的认知,嗣后他对绝对空间的继承性批判成为建构新的空间思想的必然路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识到“我们的物体经验中把那些可以归诸感觉经验的东西移去,物体将会消失,但它所占据的空间仍旧留下,从根本上讲,它会在思想中消失”[2]31。由此康德通过空间观念的重构来提供了一种理论解决方案,并用人类学的“绝对纯粹”来替代宗教神学的“神秘经验”,这是一个崭新的、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具体而言,康德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借用哥白尼的大胆预设和反转模式来论证形而上学科学化的历史依据和合理性,这种预设的激进性首先体现在空间设想方式的转变,从围绕认知对象转变为围绕认知主体去假定空间的存在,亦是从对象决定直观转换为主观的直观来决定对象,正如哥白尼打破围绕地球的传统,来以太阳为核心研究诸行星的运动。康德在《可感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原则》中阐明空间是“从精神本性当中生产出来的图式”[2]47,并从认知主体角度出发来兼顾“先天”和“综合”,这也标志着他坚定地从空间实在论转换为形而上观念论。而后完成于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的“先验感性论”正是沿袭了这一空间观念并有所拓展。康德认为空间是主体的纯粹直观形式,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一连用了四条释义来对空间属性做了“形而上的阐明”,用必然性和先天性来阐明空间认知只能是与主体相关的属性,而非是对象事物自身属性;随后用唯一性和无限性来佐证空间表象并非一个推理式的知性概念而是纯粹直观,这就把空间议题归入到认识论范畴,将空间建构为内心朝向事物的先天观看方式,这一逻辑演绎可谓釜底抽薪般地斩断了神秘主义诸如上帝与空间经验的关联,取而代之以主体的内心;同时他也解构了牛顿等自然科学家视为理论自明的绝对空间,空间成为主体感知事物存在的先验方式之一,这种先天形式指涉的并非属于对象自身的属性。这算作“将空间从自然哲学中解放出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将空间判断为纯粹知识,也是构建我们语言、思想和实践的潜在背景。换言之,康德打破了空间与上帝神圣存在的传统联系,用精神空间替换了神学意义上的绝对空间,标志着现代空间意识的萌蘖,其先验直观形式的精神空间也代表着近代以来思考空间的基本路径”[3]。毫不夸张地说,康德正是凭借空间观念来厘清了科学和信仰、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分界点,巩固了近代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绝对确定性。
二、 先验空间和“时间空间化”
近代哲学的关键议题是认识论,经验主义认为认识缘起于感觉经验,并以经验为其检验标准,所谓“凡是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中”[4],而理性只依靠自身来建构知识,最终只能沦为没有根据的玄想,这种唯物主义的预设很快就受到质疑。贝克莱认为物质是感觉的复合,存在即为感知,抽象之物都是不可感知的,因而也都是不存在的。这一推演逻辑使得经验主义陷入“独断论”“唯我论”的泥潭,并走向了对经验认识论的自我否定。也正是上述经验主义所引发的知识界恐慌使得康德从“独断的美梦中”(2)康德在1798年写给格拉夫(Garve)的书信中,曾经对自己的“思想觉醒”做出过解释:“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包括对上帝的信仰与否,自由意志或者不朽的难题,将我从独断的美梦中唤醒,并且驱使我走向理性的批判”。详见邓晓芒:《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被震醒,他通过卢梭的《人性论》意识到人的尊严和平等,随后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并重新建构了认识论原则来拯救自然科学的理性根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康德表达了重建形而上学的雄心和使命,并对纯粹思维做了严格的哲学规定。康德将人类知识构成要素三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知识既离不开先天的东西,也离不开后天的经验,智障者有经验,但无理性,并不能形成知识;而盲人有理性,但无经验,也不能形成知识。康德就此认为“一切知识都开始于经验,但并非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2]1。他举的就是挖房屋地基的例子,其知识不必真的等到房屋倒塌后才能验证这一后果,而是从房屋建筑的普遍规则中就可以引出这一经验。换言之,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其一旦开始,作为思辨的主体就要反过头来对已经接受的知识进行理性反思,这其中普遍必然性和感性直观的关系正如邓晓芒的总结“思维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5],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调客观的外在经验内容和主观的先天认知形式的统一,其构成了知识理性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二者不可偏废,侧重于先天感性形式的部分(包括时间和空间),被称为“先验审美观”或“先天感性论”,但是这里的“审美观”概念并非意指“美学”,而是指涉“感觉论”,在这个先验感觉过程中,主体将凭籍空间这个先天外感形式来有效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最初认知。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主要阐明的是纯粹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知识的发生过程,但是就表象产生的立场而言,康德在与伊波哈德(Eberhard)的商榷中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关于时空表象“先天获得”的可能性,并探讨了空间应该怎样被呈现的问题。“关于空间的形式直观,作为一种先天获得的表象,其先于事物的特定概念,而之所以这种获得被称为先天,是因为它并非从经验中获取,而是源自于人类感性的本性中”[2]32。这也印证了康德关于空间先验性的属性判断,即空间的显现必须倚重于知觉材料,正偌我们无法感受到空的空间一样。“空间并非自在的存在,而是外部表象呈现的形式,没有外部表现显像的可能性条件,空间终归是无”[2]28。康德用先验感性论来讨论空间和时间两种先天直观形式,这种阐明方式分为两个层面,形而上学的阐明是就空间与时间的概念来加以说明,讲清楚“是什么”;先验的阐明是从认识论角度讲清楚对象的知识何以可能,说的是“做什么”。康德所谓的先验阐明,就是将概念解释为原则并以此来证明其它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如果说“形而上学阐明”不过是把概念意义解释清楚;那么“先验阐明”就是要解决认识论上的问题。就此,康德将空间区分为“直观形式”和“形式直观”,前者是先验,后者是主观。“直观形式”虽然属于是主体的认知形式,但却不是对客体的具体规定,其具有普遍有效性;作为“形式直观”则是针对个人有效,其被知性所规定,故而具有对象性;而从先验范畴进入到对象化层面,这是概念客观化的必然过程。在这其中“康德把空间作为直观形式保留在现象界,存在于主体的认识形式和认知能力之中,并形成了他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有力证明”[6]。康德在《未来的形而上学》当中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存有我们以经验方法和手段亦不能阐明的认知条件,诸如数学就包含着不能通过感觉获取的先验知识。他在先验感性论当中阐明了我们感性认识当中的先验成分,先验关注的是逻辑学上的先于经验,而不是心理学上的先天遗传,其体现为主体的一种先天能力。也就是说感性认识不仅仅是后天获得,其之所以能够“给予我们”,在于我们具有相应的接受能力,感觉所接受的感性表象当中已然包蕴着先天的成分,而空间和时间就是这种先验成分的体现。先验和先天尽管意义相近,但是有所区别,先天是不涉及对象的,诸如逻辑形式;先验是指经验之先,就是考察经验知识如何可能,以及凭何种条件建立可能性的,但是它并不脱离于经验,其具有认识论意义,指涉是对象的知识。康德认为如果没有对空间概念的运用,就不能描述任何外在于他的失去,也不能描述任何相互并列或外在事物的表象,在纯粹描述中,并不需要寻求和事实的吻合,而应该坚守的是从纯粹意识立场来进行的反思。但是事物背后的自在之物,对其的认知超越了主体的经验范畴。我们对其的关注将放弃认识论视角,改为实践论视角,在这个系列中,主体将按照自己的自由意识来形成他的客观规定性并完成主客体的统一。换言之,康德在对范畴的先验性演绎中,从知识的来源性上否认了概念和直观之间的关联,因为概念的自发性以及直观的否思性使得二者将这种差异性充分表现在纯粹知性范畴和经验直观当中。
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空间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如果以现象来审视空间,空间具有经验性并具有客观实在的有效性;而以本体审视空间,空间具有先验性,其内在于人类心灵的认知,构成了先天纯粹直观,并且先天直观要先于经验实在,这其中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他努力在“先验”与“经验”之间寻找一个有效平衡。同时通过细读他的哲学文本,我们发现他最终确立的立场是“既支持空间的经验性的实在性,同时又主张空间的先验的观念性”[2]32。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也表达了对时间和空间自相矛盾的阐明,他在谈及先验感性时认为,时间并不是外部现象的规定,他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六节中言道“时间是所有现象的先天形式条件,所有的表象,其自身都牵涉到内心的规定性”[2]37。具体而言,时间和空间作为外部和内部现象的先天形式条件,二者存有不对等的地方,康德论证了空间和时间都是对外部事物的纯粹先天直观形式,但是空间只是一切外部现象的先天直观形式;在言及二者的作用时,康德设定时间为“先验图形”,而空间却付诸阙如[7],因为时间被作为内感官的普遍原则比空间更富有主体性,这就很大程度上预设了“时间优位”。有基于此,康德将时间和此在、主体与人类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时间必然以空间表象为发生条件,倘若没有了外部直观,那么内部直观将是无法呈现的空洞表象。康德这段关于空间和时间纠结缠绕的关系论述,被视为“争论较大的教义”[8],甚至连康浦·斯密这样的专业阐释者也陷入困惑。而邓晓芒教授则归咎于康德没有清晰地界定“直觉”(intuition)和“直观”(ansehauung),也就是说,“时间不能‘直观’而只能‘直觉’,因为其自身不能相对独立地形成表象”[9]。但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将之视为康德在阐明传统的时间空间化视域的同时,实际上拓展出空间时间化的可能性维度,尤其是主体凭藉时间空间化的表象,可以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而将时间空间化就是“把主观内感官中的‘我’视为空间中客观经验对象来认知”[9]。最终对其的演绎,我们则可以寻根溯源到康德对先验感性的表述中去,尤其是他对时间空间两种直观形式的阐释过程正好为后来审美对象预设了话题。甚至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康德对“现象”的阐明尝试可以和《判断力批判》当中的“审美对象”进行有效关联,并在论述当中看到他逻辑演进的思路。不仅如此,按照目前学界的普遍性理解,空间相较于时间而言可以更加有效地表现出“经验实在性”,这被邓晓芒先生称之为康德设定好的“更深伏笔”,“我们必须使自己把作为内感官的形式的时间形象地通过一条线来领会,把内部变化通过延伸这条线来领会”[2]214,这条“伏笔”的线索就是以空间为媒介和手段,将认知的条件归结为先验主体性,而康德阐明的“时间空间化”则是西方哲学中的一股强大的思想暗流,这也正契合了后来柏格森的概括总结:“流俗时间概念指涉的时间就是空间”[10]。嗣后这一重要的理论视域为海德格尔所继承,他的存在论框架中就将空间统辖到时间范畴并作为“此在”的存在根基,而“世间之存在”(In-der-Welt-Sein)则被他视为解析空间性本质的有效途径。
三、 经验性和空间的“具身化”
在自然哲学抑或思辨哲学中,形而上学无疑是空间关注的议题,但进入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人文学科以及心理学的发展,空间被置入到实证性论争当中。诸如人类学证明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具有迥异的空间认知;心理学亦通过空间知觉的个案研究,认为空间存在及形式皆是环境与主体交互的后果。而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思想家则沿袭经验主义的学理脉络,以主体为视角来重新审视空间这一概念,从先验之空间转向生存之境遇,他们在空间现象学的建构中引入主体的认知和动觉,从而使得冰冷的物理空间过渡到带有鲜活经验和主体温度的“此在”空间,空间研究也从形而上学走向具身化。换言之,空间研究不再仅仅是关涉抽象的纯粹形式,而是内在地关联着场域化、情景化的实际内容,这其中胡塞尔的《事物与空间》、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可谓是思想代表。但是笔者在细读康德哲学文本的基础上,认为这前后思想的转向还并不能称之为“断裂”而应是“过渡”,包括康德对经验性、具身化的论述并不是付诸阙如的存在,他对身体的研判也并不是部分学者所归纳的那样,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11]。换句话来说,笔者认为康德空间观已然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就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独立于它向某个主体显现。当然,这其中的逻辑演进首先要从他的“经验”开始。康德认为“经验”(Erfahrung)是物自体呈现出来的感性直观和各种表象,这些凭借知性能力与想象力形诸成经验对象之表象,划定了经验对象的范畴是自然界,或称为包含内外自然的现象界。按照预设,经验对象“兼有先验之观念性和经验之客观性”[12],物自体则是“超验”对象,其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关涉的是彼岸世界;纯粹理性是对经验的现象世界进行理解的能力,而实践理性是对超越于经验之外的,绝对的、无限的物自体的认识。康德认为既然不能从理论上来证明物自体,那么就应该在实践上去信仰它,其不在于知道什么,而是在于应该做什么,这是道德的职责,或者无上的命令,这并不是由外力来监督执行,而是完全处于内心的自由意志。康德认为空间的先验属性对应着宇宙世界的非对象性,诸如我们谈论“世界”这一概念,其指涉大多是对象的认知视域,而并非实指的具体认识对象。康德严格界定了人的认知能力,其只能在经验对象所感知的范围内有效,而在经验世界之外的存在是“自在之物”,我们不用白费力气地去证明其是否存在。借此,康德意识到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并将超过自然科学的现象,划入到信仰的范围。譬如自由,就不属于我们的认知对象,尽管人的理性不断试图去认知何为自由,但最终也枉然一场。
除此之外,康德认为经验是一切“经验表象”的总和,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然阐明经验是可以建构出对象认知的,因为它既是想象力联结知性和感性形诸的结果,又是理性判断和感性直观二者结合的产物,所以经验也具有知性范畴的综合统一性。不仅如此,康德言及的经验实指为“经验性知识”,其并不仅仅是感官知觉层面的累积,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即“经验判断”(Erfahrungsurteil)。这种判断超越了心物对立,其开始于经验的认知并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经验客观性。由此,康德将知识和对象二者的关系调整为概念和经验的相关议题。具体而言,空间并不是主体感觉的内容自身,亦非外在的客观实体,但是我们对空间的考察却又不能脱离主体意识和经验感受。空间和时间作为先天直观的纯形式,其使得主体的认知成为可能,其逻辑生成并不是先见的现成秩序令我们看到空间,而是我们面向世界和事物的观看行为为其安排了秩序,也即其并不是各种外在事物安排在物理空间之中,等待我们来观审并获得空间的观念,而是我们的先验直观使得我们熟练地用物理空间在理解外在事物的既定秩序。空间作为形式不再仅仅拘囿于人类心灵的纯粹直观当中,认知主体通过身体将意义完全敞开,这是“在世存在”这一结构的本真呈现方式,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时间链条上的有限存在,所以也只能凭借“物”向我们敞开的形式来认知其属性,由是,我们对物的全然判断和意义界定也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对物自身的认知并不等于关于对象的认知。上述康德的空间经验认知和后来空间现象学所强调的理论重点已然不谋而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海德格尔与胡塞尔都将康德看作为现象学的肇始人。
1768年,康德在《空间中的方位区分的最终根据的考察》一文中条分缕析地阐明了“空间性是感性的主观形式”[13]4。该文也成为目前我们重审康德空间性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康德是从质疑莱布尼茨的“位置研究”开始,认为莱氏并没有阐明空间本身的方位性,在文中康德用左手和右手在三维空间当中无法叠合而只能镜像对称的事例来否认了莱布尼茨的空间位置分析,并进而驳斥了莱布尼茨的空间关系论。嗣后,康德以身体的感知和体认来说明空间方位性究竟为何,他认为空间判断应该来自主体的感知,包括指南针或者罗盘对空间方位的定位、地理学方位上的区分实则都是以身体对空间的判断为基点,而身体对左边、右边的截然不同感受是产生这种判断的天赋能力,“自然于这一感觉与身体组织之间建立了一种比较牢靠的关系”[13]369。由此不难理解,康德已经将“具身化”视为空间性的预设条件。而之后他在《就职论文》中具体论证了空间作为直观形式的想法,这实则和《纯粹理性批判》当中的“先验感性”是一脉相承的。康德在文中认为心灵具有相对集中的“空间效应”(Spatial Effects),心灵具有一定视域的而非实体的空间呈现,正是有基于此,“追问心灵究竟归依于身体的何处是不正确的提问”[14],因为心灵不是身体的外部对象,也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明心灵究竟应该定位在身体的那个部位,但二者是处于交互关系当中,也就是说,在身体存有和外界事物刺激的关系认定中,身体充当的是表象和对象二者的中介,“身体是生命存在的绝对条件,倘若心灵没有感觉,那它只是没有材质符合思维而已,而设若心灵与身体相隔绝,则意味着生命终止”[15]279。由此康德认为“心灵并不依靠自己的纯然意识来呈现自我的准确位置,而是恰恰相反,是身体安顿心灵”[15]273。假若将空间性设定为心灵的属性,那就将心灵视为感官物质对象,但实则是无法准确呈现的,我们对其把握只能是借助它对身体产生的影响来确定。换言之,主体只有依靠身体才能认识自我,但自我并不占有身体的某个空间,亦不能按照空间形式来被把握。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在康德这里传统的身心二分论已经被克服,康德既肯定了主体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又确定人类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目的性,身体所在亦是心灵所在,这也反证出传统灵魂不朽的荒谬之处。身体作为精神性器官亦为主体意义之所在,凭借身体,主体被纳入情境空间当中,其在空间中的一切遭逢都是和身体的经验相关,而空间面向主体将意义敞开。康德从人类知识出发,嗣后来追问这些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为何,正是在此条件下,如若“注意到了所在和空间的关系,将获得线索帮助我们思考人和空间的关系”[16]。而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关于身体空间性的哲学论辩,则是更加表现出这种思想论辩的张力,主体对周围环境的空间经验构成了身体存在的基本要素,如果说“心”受困于时间,“身”则是空间时间化、内在化,那么“物性之身”局限于当下和瞬间,是完全空间化的(亦是受困于空间的物性),这些空间运动的意义节点构成了自我存在之本质。
四、 结 语
时间性和空间性分别成为阐释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的两个切入点,尤其是空间性成为解读当下存在之关键,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用“为自然立法”的方式以阐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成立,又明确了先验理性决定主体认知能力的基本图式,这实际上是从现象学的视域,将空间纳入此在的存在结构中。后来的海德格尔在《面向思的事情》当中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观点,海氏认为空间方位的判断首先要保证主体在世存在这一基本前提条件。他在总结时也批判性反思地说道“我试图把此在空间性归结为时间性,但这种企图是站不住脚的”[17]33。此举实则要廓清时间性对空间议题的遮蔽,并要求就空间问题本身来重审空间,这也是海氏认为在解答“时间为何”之后又一个重要命题。空间到底是认知对象,还是认知对象向我们敞开并呈现的背景视域?究竟是存在之实体,抑或认知之视域?这一系列疑问及议题是20世纪以来的“后康德哲学”,包括现象哲学研判解读的重要对象。现象哲学要求“重返事物本身”并“回归体验世界”,并且以“现象还原”的方式来探索本真的空间,其途径就是以“此在”的空间性开始,因为这里的空间具有和处境相关的境遇性。
整体而言,目前国际学界也逐渐倾向于从康德的“具身性”视角来重读复释他的哲学思想,并认为这是当时康德质疑“唯心论”时的基本立场。譬如莫艾尼克就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当中的身心交互的形而上学议题值得学者对此书进行重新审视[18];卢佐则认为自我经验的建立需要身体对世界经验的把握和引领[19];而施瓦沃在《康德的身体实践》当中更是笃信肇始于康德的空间现象学通过经验性、具身化和境域化的方式来揭橥出一个斑驳的世界图景[20]。以上种种学术路径既是康德思想在当下的重要回音,也是我们目前阐释康德哲学美学的全新起点,值得学界同仁们来进一步关注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