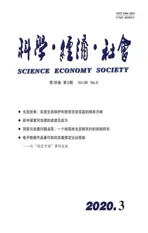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的“相遇点”
2020-01-07白洋本
白洋本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r)在2011年凭借凝练、深刻的意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对自己的诗歌如此总结:“我的诗歌就是相遇点(meeting places)。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被常用语言和外表所割裂开的现实诸层面之间建立起突然的连接。风景的大概轮廓和细小枝节的相遇,被分割的文化和人在艺术品中流汇在一起……诗歌就是一种积极的思索,他们想让我们醒来,而不是让我们陷入沉睡”[1]。
有研究者发现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的“相遇点”问题,但仅仅以“让大自然或生活周遭的细节相互撞击出奇异的火花”[2]来总结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艺术特点,忽略了对特朗斯特罗姆所面对的“被割裂开”的现实的分析,更未触及诗人如何通过“突然的连接”实现了“相遇”这一问题。本文围绕特朗斯特罗姆对自己诗歌的总结,首先分析“被割裂开的现实”的具体指向,然后探究特朗斯特罗姆如何在诗歌中建立起“突然的连接”,继而指出这种“突然的连接”对于“让我们醒来”的形成方式和现实意义。
一、“被割裂开的现实”
特朗斯特罗姆说诗歌的“目的就是在被常用语言和外表所割裂开的现实诸层面之间建立起突然的连接”。为了理解他的诗歌如何实现“连接”,首先应该研究他试图缝补的是何种“被割裂开的现实”。
现实是“被割裂开的”,并不是说特朗斯特罗姆会用科学或者哲学的方法对现实的诸多层面进行解剖和分解,而是说他通过诗歌表现人的存在所处的分裂和隔离状态,这种“被割裂的现实”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体现为存在迷失而物真实的现实迷惑感。《带解释的肖像》是一首回忆朋友的诗,但与传统的回忆诗不同的是其出发点不是人,而是肖像:“这里是我认识的一个男人的肖像”[3]163,这个特殊的开头已经预示着较传统回忆诗更为深刻的主题,诗人紧接着说“他父亲挣钱多似晨露”,这句诗歌交代了典型的现代人背景:物质富裕,然而即使在这种处境下,人对自我仍然不相信,个人主体不稳定且易受攻击:“但全家仍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怕陌生的思想/在夜间闯入他们的别墅”。他为什么脆弱?诗人说是因为“他身上的自我在休息/自我存在,他不去感受”,他不去感受他的存在,他被其他事物吸引而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方式,抑或他的存在停留在纷繁复杂的物上:“肮脏的大蝴蝶——报纸/椅子,桌子,脸在休息”,自我的迷失让诗人问了又问:“自我是什么,自我是什么”[3]103-104。
人的存在是什么?什么才是人的真实?在这个商业主导人潜意识欲望的时代,人的存在,人的真实都成为了一个值得怀疑和思索的事情,因为人似乎越来越不真实,而物却越来越真实了,正如特朗斯特罗姆在《波罗的海》(三)中所说:“但照片上其他东西却真实得惊人”[3]180。由此可见诗人对现代人的存在状态特别关注,而人的存在被他者或者物所占有的事实就是诗人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让物更真实,而人却没有了存在的真实?特朗斯特罗姆认为是利用人的欲望缺陷而得逞的商业文化。
其次,体现在被商业戴上“面具”的双“面”分裂感。诗人在诗歌《在劳动的边缘》写道“休闲的月光围绕着工作星球/带着他的阴影和重量——这就是他们所想要的”[3]122。诗人认为工作带着他的阴影和重量占据了人的休闲,人变成机械。而人不仅仅变得机械化了,更被剥夺了存在的真实面孔,以一种非真实存在。在《画廊》中诗人写道“我们僵硬地穿越过事业,一步一步/就像日本的能戏/戴着面具,高高地被扔出的歌声:我,这就是我/一条卷起的毯子/代表了被击垮的人”[3]207。我们被剥夺了真实存在,以一种“其他”的面具而存在。有评论者认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描述的被伪造的自我是被市场规律掌控的个人的重要产品[4],确然,在现代社会,物所扩散出的包括欲望、财富等意义符号构成了一个比真实更具诱惑力的超真实世界,从而使人脱离此在,进入非本真的存在,所以现实只剩下躯体,而城市就变成了陈尸馆。正如在诗歌《舒伯特》中诗人对纽约的描述:“纽约夜色中郊外的一个地方,一个一眼能望尽八百万人家的景点……半睡的躯体蜷缩在地铁车厢,一座奔驰的僵尸陈列馆”[3]201。在另外一首描述纽约的诗歌《悲歌》中,诗人说现代人生活在白天,却饮用着黑暗,也感受着一种不安的震动,而世界留给人的经验却只是美丽的残留物:“经验美丽的熔渣”[3]171。诗人在给英国诗人布莱的信中说虽然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但也是一个让人避之不及的社会。这种避之不及就是超真实世界剥夺了人的存在之后,个体存在被商业戴上面具从而导致的双“面”分裂感。
最后,体现在语言失效的艺术无能感。诗歌不仅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还面对着诗歌自身艰难的处境:诗歌的工具——语言受到经济符号的攻击并陷入现代性感受描述与语言抵达能力之间的矛盾。面对商业符号对语言符号的侵袭,诗人为了能够有效抵达思想情感,就需要寻觅新的语言,正如特朗斯特罗姆在《夜值》中说:“语言和刽子手并肩在走。/我们必须使用新的语言”[3]147。特朗斯特罗姆也表达过词语与主体体验之间的抒写困惑:“某个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某个东西无法表达”[3]184。或者即使词语靠近过主体感受性体验,但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却发现词语并没有产生意义,“但造成:同样的词空洞无物”就“像一个无法描述的真理被打捞出沉寂,变成一团僵死的黏块”[3]184。
面对这样的现实,诗歌的目的就是联接日常生活的细腻体验,重新将人混乱的存在构建出来,正如特氏在《波罗的海》(一)中所写:“‘我们就在这里’的感觉/被稳稳揣着,像某人滴水不溅地揣着一只盛满的陶罐”(《特》:176),诗人通过将生活中的具体物质(揣着盛满水的陶罐)来比喻人对存在的感悟(人揣着自己存在的感觉)来恢复主体对自我存在的感知。
二、建立“突然的连接”
面对物真实而存在迷失、双层“面”具造成的分裂感以及语言失效的无能感,面对这种被割裂的现实,特朗斯特罗姆试图通过诗歌所做的就是缝补起被割裂的部分。他说诗歌所作的是“建立起突然的连接”,将现实中的大概轮廓和细小枝节、将被分割的文化以及被分割的人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连接,通过这种连接黏合被割裂的存在和现实。
“突然的连接”不仅体现在“……好像……”结构中,还体现在情景与情景通过连接而构建相似性中。在这种连接中,被连接的两个部分的共通点被凸显出来。诗人力图强迫人认识其中的相似性,借此挖掘隐藏在人生活中未觉的“意识”问题。
首先,“突然的连接”体现在“……好像……”结构中,这种“……好像……”结构并不是指传统的比喻手法,而是指两种情景现实的相似。特朗斯特罗姆在诗歌《七二年十二月晚》中写道:“紧闭的白色教堂——一个木制圣人/站在里面,无奈地微笑,好像人们摘掉了他的眼镜。”[3]167诗中,诗人将圣人看不清现代生活与近视眼被强行拿走眼镜构建了相似性。诗人在给布莱的信中指出,这首诗是他观察教堂里的一个人而写的,这个人是近视者,但却丢掉了眼镜,显得非常尴尬。诗中,特朗斯特罗姆把受人崇敬的圣人比作被摘掉了眼镜的近视者,而且他的眼镜是被一些人故意摘掉的。特朗斯特罗姆说:“我不认为眼镜是被偷掉的,而更像是从他那里拿掉的。我选择用复数‘他们’而不是单数‘某人’,表示拿走他眼镜的是一个不友好的大多数”,这些“大多数”主要指向发动战争或者非法使用核武器的政治领导人[5]。诗人非常厌恶他们的行为,在给布莱的信中曾多次提起该事。诗人将教堂中的木质圣人和一个被拿掉眼镜的近视者联系在一起,由“好像”突出了两者的相似性,即便是圣人,也无法看清现在的世界,这种悖论不仅显现了圣人的微笑、圣人的地位在现代世界中的尴尬,更加标识出了现代社会中多层次勾结的复杂性及危险性。诗人正是通过“圣人看不清——近视眼看不清”的连接——相似性建构,表现了人类现状及社会复杂性。
其次,“突然的连接”还体现在情景与情景的突然连接中,与“……好像……”结构不同,这种情景的连接没有明显的连接词,而是突然地在两种不同的情景之中通过连接建立相似性,使得被掩盖的相似得以凸显出来,通过创造新奇感而揭示现实。在组诗《波罗的海》第五首中,诗人叙述了一位有才气的音乐家,遭到黑暗政府的迫害,患上脑出血而身体半瘫,只能进行简单的言语表达。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情景连接:“他给自己看不懂的歌词谱曲——/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在错说的合唱队里/表达着个人的经历。”[3]185。诗人将一位遭到政治迫害的音乐家与幸福时代的“我们”连接在一起。音乐家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及自身特殊的经历下,依然用音乐寻求心灵的自由,而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仍不能自由地表达个人经历和生命情绪,只能在合唱队借一些悲伤抑或愉悦的音乐来舒缓自我。诗人用构建音乐家和我们连接的方式,突出了共同性:本我的被压抑,而音乐家、我们所处两个时代的差异性,愈加深化了现代人虽处发达社会却依然生活错位的精神状态。同样的例子还可见《波罗的海》(三)中,诗人将万人坑中的牙齿与教堂洗礼盆下的名字连接在一起,《七二年十二月晚》中将人对自己的强迫睡眠与战争连接在一起,等等。
借由“……好像……”的结构和不同情景之间的“突然连接”,特朗斯特罗姆通过构建相似性在被割裂开的部分之间建立联系,从诗歌的角度对人类精神现状及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三、诗歌“让我们醒来”
特朗斯特罗姆面对“被割裂开的现实”,通过在诗歌中建立“突然的连接”,让人们从沉睡而迷失的现实之中醒来,正如他说:诗歌“让我们醒来,而不是让我们陷入沉睡”。为了能让人们醒来,在建立连接的方法中,他以直觉联接形象,以重新命名更新阅读体验,以相似性照亮隐藏事物,从而恢复了人对存在的感受力,努力照亮并叫醒存在。
首先,“突然的连接”通过相似点的照亮突出被隐藏的共同点,并在相似点的两个不同时间的张力中,反思历史,认清本质。特朗斯特罗姆在《七二年十二月晚》中写道“他是孤独的。其他都是现在,现在,现在。重量定律/白天压迫着我们工作,夜里压着我们睡觉。战争”[3]167。重量定律是指人受到大小与人的重量成正比方向指向地心的吸引力。特朗斯特罗姆固然知道压迫人睡觉的是除地心引力以外其他的东西。那是什么?是人在商业与欲望的怪圈中的自我迷失以及自我惩罚。现代人为了维持生计,需要工作,而在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的过程中人深陷复杂的商业物欲中,以至于潜意识地将工作、金钱和物质满足树立为生活的最终目标。这种情况下,睡眠不再是人辛苦工作之后娱乐享受,而成为机械化推进生活的动力和必要条件。面对这样的人类精神现实,诗人所做的就是力图恢复人生活原初的“纯洁”,正如特朗斯特罗姆在这首诗歌的开头所说:“也许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为了活到现在”[3]167,在给布莱的信件中,当谈到这首诗歌时,他说:“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我有一种责任去反对某种隐藏的‘意识’。”[5]特朗斯特罗姆就是通过将压迫人不断工作的潜意识和战争之间构建“突然的连接”的方法,企图告诫人们:战争残酷地吞噬人的生命,而现代社会中,也有某种利用人的欲望缺陷而吞噬人生活的隐藏意识,以战争般的巨大危害悄然侵袭每个人的生活。
“突然的连接”将两个类比事件的时间背景叠映在一起,但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距离并没有被取消,反而,在共同性因素的照亮中,两个时间点的差异性被突出显现,在遥远过去的时间点和诗人所处的现实时间点之间长长的时代发展中,关于人类是否进步(战争是否被制止)、人的生存(物质、精神)处境是否被改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被强力地质询。如在《七二年十二月晚》这首诗歌中,虽然一战、二战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但依然有“战争性因素”蔓延。简单的情景诗句下,诗人关于历史、时间、人性等伟大主题的深切关怀也逐渐显露出来。特朗斯特罗姆对历史非常关注,也极具反思精神,诗人在《历史》一诗中说历史中的叛国者(法国叛国者德雷福斯)、关于“激进”“反动”的历史故事,都像三月开裂冰块下的低语一样,让人聆听,让人思索:“这一切就像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下沉,我们聆听”[3]117。诗人对历史的聆听和反思,就潜在于“突然的连接”的两个时间点中,正是通过“突然的连接”,通过两个时间点的互相对照,诗人用自己的语言摸索着真理的方向。
其次,特朗斯特罗姆重新命名词语,从而更新阅读体验。海德格尔认为:“诗人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在其所是中的事物。这种命名并不是在于仅仅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而是由于诗人说出本质性的词语,存在者才通过这种命名而被指说为它所是的东西。”[6]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有另外一种“突然的连接”,即对词语的重新定义。通过重新定义,诗人把读者带到了生活感受的深处并向本质逼近。这种定义往往以“:”为标志,如“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3]158。《序曲》中诗人写道“未来:一队空防部队/在飞雪中摸索着前进”[3]151,这种定义以清晰的形象诠释了定义词与词语的相似性。未来的不可知因素如突然到来的一队航空部队,未来会遇到的困难就像人在飞雪中困难前行。诗人对未来的定义,意味着读者必须放弃自己的阅读经验史而向自己内在体验倾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诗人帮助读者丢开过往和其他,而向存在感受回溯并让自己的存在批判性地建立起来。
最后,特朗斯特罗姆以直觉来“突然地连接”意象,完成对生活感受的细腻追踪,从而恢复对存在的感受。《波罗的海》(三)中诗人以万人坑中闪着光亮的牙齿比喻教堂洗礼盆上被刻下的名字,认为现代人:“没有避风港,到处是危险。/只有洗礼盒中才有安宁,在无人看见的水中”[3]179。在他看来,现代人虽笃信宗教,似乎获得了一种稳定可靠的信仰支撑,但实际上,人只是以宗教掩饰了内心不安、狠辣的阴暗面以及以历史为证的事实。这里特朗斯特罗姆用了奇妙的联接:“人,野兽,花纹/没有风景,花纹”[3]180,诗人通过直觉将三个意象联接在一起,让野兽的整体形象和兽野蛮的本质特点越界进入人的范畴,让“人”“兽”“花纹”之间互相渲染,以一种抽离的态度审视现实,将野蛮、虚伪、干枯的现代性感受呈现出来。
现代人的潜意识、存在方式都受到他物隐秘而深刻的影响,诗人通过“突然的连接”的方法,不仅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意象,还通过相似性建立了一种向内部更深意义层面的挖掘。这时,语言也脱离了话语经济的惯用模式,词与词,句与句之间互相影响并制造出新的意义,正是如此“想象力和感受性重新复活在一个个词语的关系之中”[7]。此外,特朗斯特罗姆受到艾吕雅、荣格的影响,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衔接靠直觉性的跳跃,关于这一点,于坚曾指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常“把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语词联系起来。并抛弃他们之间世俗的‘雄辩’,以直觉来把握它们的组合”[8],但这种跳跃都被特朗斯特罗姆约束在理性的总体思维之下,诗人用这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直觉性梦境与现实相遇的方法达到了对现实的迷醉化抽离(68)关于“迷醉”见详见(德)卡尔·曼海姆.文学社会学论集[G].艾炎,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222-250.,进而对现实有了理性的反思,也许就在这一点而言,特朗斯特罗姆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超现实主义者(69)Jaan Kaplinski认为特朗斯特罗姆学虽然学习了超现实主义的语言,但并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哲学。。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中,意象的移动与人的主体感受密切相关,而诗人正是通过对主体感受性的细腻追踪,完成了对现代性感受的表达以及对存在感知力的恢复。
四、结语
现代社会中,由商业主导的行为律令逐渐内在化,变成了个体的潜意识自主要求,外物不仅诱惑、进入了人,更剥夺了人的存在。人不断被自己舍弃,物成为了更明亮的存在,而自我却成为巨大的黑洞,人类从而进入了一种波德里亚所称的“拟真实存在”(70)现代社会中,人不仅看重物的使用价值,而且看重物所代表的价值,即物所代表的地位、财富等意义,而价值是一种符号,波德里亚将这样的由符号所构成的世界称为“拟真”世界,在现代社会中,拟真世界所构成的“超真实”却比真实更具有诱惑力,似乎更加真实。关于这点,详见(法)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2006.境遇之中。诗歌不仅面对着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商业社会、自我被诱导的虚拟超真实现实,还面对着语言被经济符号瓜分、必须寻找新的语言的书写现实。
在这种处境之下,特朗斯特罗姆回归自我生活体验,以“突然的连接”将两个“被割裂的”事物连接在一起,开放了词语和想象力,让词语脱离了惯常的意义系统而自动生发,让想象力在主体感受和现实之间不断跳跃、闪烁、联接,从而构建了一种新的面对现实的语言,正是依靠这种手段,诗人把诗歌拉回到繁琐的生活中,达到了对人的存在状态及人类历史现实的反思与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