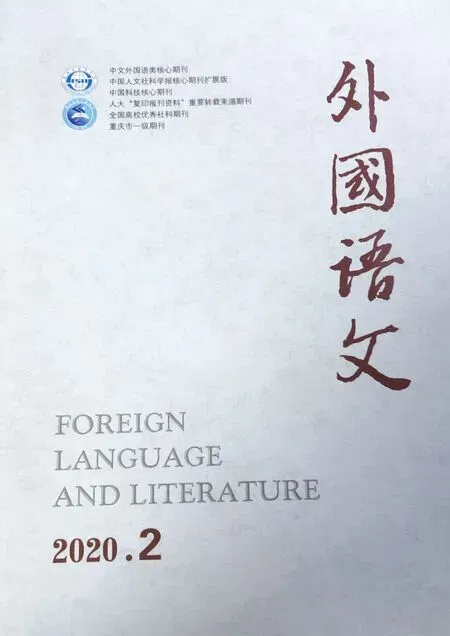马修·阿诺德的Hebraism及其在中文语境的延伸解读
2020-01-03傅晓微王毅
傅晓微 王毅
(1.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2.四川外国语大学 旅游与审美文化研究所,重庆 400031)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讨论西方文化源头时往往将希腊文明(文化)与希伯来文明(文化)并提,称之为“两希”“二希”或“2H”,并将这种“两希说”追溯到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一书中那篇著名的文章《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如有学者说:“阿诺德以降,人们普遍视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宋立宏,2000:50)也许正是因为阿诺德“两希精神说”的巨大影响,中国近30年讨论西方文化的论著大多把“希伯来精神”(Hebraism)与“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明”画上等号,有时等同于“基督教文明”。这种误读对正确理解西方文化中的希伯来(古代犹太)文化因素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为此,本文梳理“两希精神说”在中文语境的误读,力图还原马修·阿诺德“两希精神”二分法的由来及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含义。
1 “2H ”(两希)在中文语境的引进与误读轨迹
3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两希”文明说大致包含以下三种解读:(1)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文明的产物;(2)两希文明指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3)希伯来文明即基督教文明。
持第一种观点的大多为对西方历史比较熟悉的哲学、宗教以及历史学方面的学者(杨洪,1995;潘玥斐,2016)。第二种解读似乎想通过连字符突出希腊与罗马文明,基督教与希伯来文明的传承关系。但这一说法也可能强化另一种似是而非的认知,抹杀二者的差异,如费尔德曼在评价美国20世纪中叶以来流行的术语“Judeo-Christian Tradition”(犹太-基督教传统)时所说:“这一术语暗示,其一,犹太教需要改革和被取代;其二,现代犹太教不过是作为‘古代信仰的遗迹’存在的。最重要的是,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一说法隐隐地模糊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真正的重大差异。”(Feldman, 1997:27)
第三类解读将“希伯来文明”直接等同于基督教文明。比如有论文通过分析加缪小说《不忠的女人》与《约翰福音》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设定上的密切关联来说明“西方文学文化的源头可追溯至‘两希’文明,《圣经》作为希伯来文明的宗教圣典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至深”(安亚菲,2014)。论者将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属于《新约》)与希伯来《圣经》等同,所谓的希伯来文明也就成了基督教文明的同义词。有的论文称“欧洲文明的起源就是两希文化,其中希伯来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刘雪晴,2016)。学术界的这种认知,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的言论,在经过网络、电视媒体等方式传播后进一步扩散,加深了希伯来文明即基督教文明的错误认识。如百度百科、360百科、道客巴巴等网页上有关“两希文明”“两希文化”的定义,几乎直接复制一位知名学者的原话——“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典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将源头最小化为两个希,就是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Greek civilization and Hebrew civilization)……希伯来文明系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郭小凌,2006)这一错误认知通过上述渠道向普通网民及学生传播,影响不小。
笔者通过检索还发现,尽管一些学者将“两希文明”英译为“Greek Civilization and Hebraic/Hebrew civilization”或者“Greek-Roman Civilization and Hebraic-Christian Civilization”,而“两希文明/文化是西方文明/文化的源头”这一说法似乎只在中文语境通行。另一方面,论者在使用“两希精神”“两希文明”或“两希文化”等表述时,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将其归到马修·阿诺德身上。如《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译者对 “Hellenism”和“Hebraism”的解释:“这两个词后来一直被用来指称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一是古典的,一是基督教的,包括各种倾向不同的思想体系、价值取向、文化风气等……”(阿诺德,2012:20)。这里Hebraism(希伯来精神)与“基督教的”划上了等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中译本出现在2002年,但中国学术界对马修·阿诺德“Hellenism and Hebraism”二分法的介绍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茅盾在1933年出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中指出 “文学批评家解释文学思潮的变迁,有‘两个H四个R ’之说。所谓‘两个H’便指的是Hebraism(希伯来主义)和Hellenism(希腊主义)。……尤其是‘二希’,很被重视为欧洲文艺史的两大动脉……”(杨克敏,2014:38)可见,民国时期所谓的“二希”“两希”“2H”均指“Hellenism and Hebraism”中文的缩写,而“Hebraism”被译为“希伯来精神”“希伯来思想”“希伯来主义”,且被用作Christianity 的同义词。民国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包括朱自清、赵景深、曾虚白等,“大多认为西方文学思潮的起伏消涨,不外是性质相反的‘两希’相互斗争的结果,这几乎成了他们论述西方文学发展不证自明的现代标尺”(杨克敏,2014:55)。
民国时期,马修·阿诺德的“两希精神”二分法是随着厨川白村等日本学者的著作进入中国的。厨川的《文艺思潮论》“将欧洲文艺思潮的历史变化概括为基督教思潮(希伯来精神)与异教思潮(希腊精神)的对立与交战”(刘君君,2019:39)。这一二元对立的观点显然来自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只不过厨川白村将Hebraism等同于“基督教思潮”,Hellenism等同于“异教思潮”。这一误读直接影响了他的中国读者,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中的“人性论”研究模式明显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而“田汉关于‘两希’思潮的定义几乎是复述厨川白村的观点”(刘君君,2019:39)。受此影响,以“两希”或“2H”代表的“灵肉二分”法讨论西方文学史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风气,对希伯来文化与基督教关系的混乱解读也十分普遍。如曾虚白在《欧洲各国文学的观念》(1930年)一文中称,罗马衰退后,欧洲文艺进入黑暗时代,因为一种“弥浸全欧的新势力,垄断了思想界的权威,抑制了人类智识的自由:这就是从基督教中茁生出来的希伯来精神”(杨克敏,2014:259)。这显然颠倒了基督教与希伯来文化的关系。遗憾的是,一些当代学者沿袭了民国时期学者们模糊不清的说法,即“两希”既指两希精神、思潮、主义,也指文化、文明。而且将希伯来精神等同于基督教,在研究者看来似乎并无不妥,如称“曾虚白对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所体现的‘两希精神’的分析,以现在的学术眼光来看,也是极为正确的”(杨克敏,2014:261)。可以说,在这场“两希精神”从英国经由日本进入中文的文化译介之旅中,对马修·阿诺德的误读也随着译者、学者的传播进入了中国学术语境,且一直影响至今。
例如,1988年的一篇论文在时隔几十年后再次提到“两希精神”,但没有出处,也未说明两希精神具体指什么,由谁提出来的。论者显然延续了民国时期对“两希”的解读。90年代以后,学术界有关“两希”的论述大大增加,使用更加混乱。Hebraism被随意翻译成“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化”“希伯来精神”“希伯来主义”并以之与Hellenism(译成“希腊精神”“希腊文明”“希腊文化”)对应。
亚瑟·赫兹伯格曾告诫犹太学者应警惕英语中包含的“大量的基督教历史成份……任何用英语进行写作的严肃的犹太作家也不得不克服这一语言中的基督教元素”(Hertzberg,1989:155)。在中国,读者长期以来只能通过英语等诞生于基督教文化的西方语言了解犹太文化,在引进的过程中,深受英语中“包含的大量基督教历史成分”的影响,形成上述误读似乎难以避免。相当一部分论文的英文摘要把“两希文明”直接译为“the Hellenic and the Hebraic”或者“Hellenism and Hebraism”。译(作)者们似乎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两希文化或两希文明就等于“两希精神”,基督教就是希伯来文明。如一篇论文摘要中说莎士比亚悲剧的思想根源“分别来自希腊-罗马文明的人本主义和基督教的神本主义……体现了希腊罗马文明与希伯来文明这两种异质文明对自杀以及人生态度的不同看法,也体现了莎士比亚在其悲剧创作中对两希文明的深刻理解与完美融合”(潘汝,2013)。
那么,这种混乱现象是否与词典等权威资源有关呢?笔者发现《现代汉语大词典》《汉英词典》等中文词典都没有“两希精神”“两希文明”“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这类词条。只有一些英汉词典,如柯林斯公司与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新世纪英汉大词典》收入了Hellenism 和Hebraism。 而Hebraism词条下只有 “希伯来用语”“犹太人习俗”“犹太人文化”三个中文短语 。但在英语词典中,Hebraism的释义则要复杂得多,大致包含以下义项:指希伯来语的用法,特征或特色;或描述属于希伯来人的一种品质、性格、本性或思维方式,或宗教体系。其语义延伸,有时指犹太人的信仰、民族意识或文化。据此,Hebraism大致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翻译成“希伯来语特征”“希伯来精神”“希伯来文化”,或引申为“犹太文明(Judaism)”。但“Hebraism”并不包含与基督教或基督教文明画等号的意思。
中文的“精神”“文化”“文明”等概念的内涵差异很大。“精神”有时与英文后缀“-ism”构成的词相当。“-ism”可指某种特定的思想、教义、理论、宗教,也可指对某种学说体系、原则的坚持,或是特定人物特有的行为方式、作风或信仰体系,相当于中文的“主义”“精神”“教义”等。阿诺德的“Hellenism and Hebraism”大致在这个层面理解,即“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有时也可译成“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狭义的文化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Hebraism很难与“文明”这样宽泛的概念联系。将阿诺德的“2H”精神引申为“两希文明”显然是误读。把“希伯来文明”等同于“基督教文明”,更是大谬。
对犹太历史或西方宗教关系史不甚了解的部分中国学者很难想象这种误读后果的严重性。笔者曾在一次会议中提到当代学术界翻译犹太文学作品时混淆犹太教与基督教术语的现象,不少同行都认为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理由是借用已有的宗教术语翻译外来宗教经典本来就是一种传统,比如翻译佛教经典时借用道家的术语,景教经文译成中文时也借用了佛教、道教、儒教术语。就连《基督教圣经》译成中文时也借鉴了不少中文原有的宗教术语,比如将《约翰福音》中的“Word”译成“道”。但如果我们因此将中文的“道”等同于英文圣经里的“Word”或希腊文《圣经新约》里的逻各斯“logos”,因而“道”就等同于基督教的“神”或等同于“耶稣基督”,显然也是误读(1)1998年的一篇论文摘要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欧洲文明,成形于欧洲中世纪的中晚期……罗马人根据他们社会生活的需要,将‘道’制度化为法律,保护了私有权和商业;希伯来人出于民族复兴的要求,将‘道’人格化为基督。”该文涉及三个方面的错误认知:欧洲文明的形成时间;中文的“道”与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无法对应;希伯来文化也并不认同基督。。事实上,西方历史上因为宗教术语翻译导致的激烈冲突层出不穷。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一些犹太学者针对上述翻译和误读现象马上联想到“基督教的文化霸权对犹太文化的贬低和压制”,甚至提高到 “基督教取代犹太教这一西方古老的反犹主义思想”的地步。有时我们不得不从中国独特宗教观、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多个角度解释那些我们认为“不必大惊小怪”的问题,说明中国学界对两教术语的混淆与西方文化中的“文化霸权”“反犹传统”等毫无关系(2)笔者曾应美国一份学术期刊主编的邀请,专门就此撰写了一篇论文“Confusing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etters” (2006)。另见拙著《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2006)。。
从人是自身文化传统的产物这一角度看,在从英语等西方语言中获得资料或者进行翻译的时候,我们难免在不经意间从自身文化角度解读外来文化。而且翻译中遇上文化空缺的语汇,借用母文化现成词语翻译也无可厚非,甚至文化误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创造性解读。但有些误读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犹太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客观理解,那就应该引起重视了。最近笔者组织翻译的《犹太性与犹太创新思维》丛书中,有译者原本按照中国惯例将the Lord 一词译为“耶和华”(这是中国基督教指称上帝的表述之一,该词的英文Jehovah,在英语基督教圣经中已经被弃用,代之以the Lord),但遭到原书作者——一位犹太裔教授的反对。该作者用三封长信,详述犹太教对上帝之名的处理及上帝之名的翻译在西方历史上引起的多起冲突。由此可见,术语的翻译,尤其是一些涉及文化差异和民族感情的术语翻译,还真不是小问题。
2 Hebraism在西方语境中的复杂含义
“Hebraism and Hellenism”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在西方学术界的解读也充满分歧。《今日诗学》(PoeticsToday)1998年曾出了两期特刊,专门梳理这两个术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与发展演变,探讨了这两个概念在古代与现代语境中的不同含义,以及现代西方思想家将这一对概念两级化、本质化、去历史化的过程。鉴于中西方学术界大多把“两希精神”对立的概念追溯到《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下面以该书为例,对Hebraism的含义和阿诺德的本意做一番考察。
在西方学者眼里,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融合的产物。在现代,尤其是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希腊与希伯来的对立成为理解有关理智、启蒙以及伦理与政治的主体性等相互对立的概念的关键。《今日诗学》特刊主编大卫·斯泰恩指出:“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的二元对立的确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在讨论文化影响、文化差异与交流等问题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建构……这两个术语已经被捆绑在一起来表征西方文化与知识传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对立的东西,比如‘正确的思考’与‘正确的行为’、哲学与启示、空间思维与时间思维、静止的存在与动态的存在等等。”但他认为这两个术语代表了本质上的对立,这一观点“本身就是西方传统的一个虚拟的神话”(Stern,1998:1)。
许多西方学者将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对立追溯到两种文化首次相遇之时。最形象的表达莫过于公元2世纪的基督教神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一句话:“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在他的眼中,“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代名词,它已经取代了犹太教。而犹太学者则大多将“雅典与耶路撒冷”解读为“希腊与希伯来的”“希腊人与犹太人”的对立,如哈佛大学斯泰恩等人在介绍黑格尔的 “希腊与希伯来” 的二元对立以及马修·阿诺德等19世纪学者将二者的不同进行抽象化和隐喻化时,使用的就是“希腊人/犹太人的对立”( the Greek/Jew distinction)。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教授苏珊·韩德尔曼在《杀死摩西的人: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拉比阐释影响》开篇就说马修·阿诺德把“希伯来与希腊”之间的紧张关系看作西方文化最本质的创造辩证法。但她也说:“雅典与耶路撒冷的这种对抗呈现出很多面孔:它是哲学与教会、希腊智慧与犹太律法、理性与信仰,以及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冲突;或者用另一种变通的说法,是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对立。” (Handelman,1998:3)韩德尔曼提到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隐喻在西方学术界的多种表达:“哲学与教会”意即“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对立,“希腊智慧与犹太律法”突出的是“知与行”的对立,或者是“理性与信仰”“世俗与神圣”的对立。但她最后笔锋一转,把“雅典与耶路撒冷”转换成了“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对立”,从而突出了作为古代希伯来文明直接继承者的犹太教与作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之产物的基督教的对立。
如前所述,中国学者对西方宗教文化的理解大多通过基督教《圣经》和具有强烈的基督教特色的西方语言,因此,这种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隐喻直接等同于“希腊与基督教”对立的认识一般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许多中国学者眼里,无论是马修·阿诺德的“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还是德尔图良的“耶路撒冷与雅典”或者犹太裔哲学家舍斯托夫、利奥·斯特劳斯等笔下的“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对比,似乎都是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立。但这是一种与文化霸权主义、基督教取代论无关的中国式误读。
近年的研究表明“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代表完全对立的两级,二者从一开始就相互交融。而且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教也吸收了不少希腊文化因素(Bickerman,1988; Hengel,1989)。比如公元2世纪的马加比起义被视为犹太人为捍卫希伯来文化的纯洁对罗马统治者实行希腊化的抵抗,但西梅尔法布指出最早出现“Hellenism”一词的《马加比二书》这部作品本身已经受到了希腊主义的影响(Himmelfarb,1998:19-40)。因此,Hellenism 和 Hebraism代表的不是两个“纯粹的具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价值观的范畴,相反,它们本身就代表了西方传统复杂、混合的特性” (Stern, 1998:3)。英国大学学院伦纳德(Miriam Leonard)认为黑格尔有关世界历史进步的描述清晰地将“希伯来的”与“希腊的”世界相对立。黑格尔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运用,影响了马修·阿诺德等19世纪学者将二者的不同走向抽象化和隐喻化(Leonard,2012)。有学者指出在那些谈论“Hellenism and Hebraism”的西方思想家们那里,这对概念代表着与犹太人无关的希伯来精神和与希腊人无关的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实际上成为纯粹的抽象物,与具体的或历史的希伯来或希腊没有任何联系。”(Stern,1998:11)但他们可能从未想到中国的阐释者会将这些抽象化的表达如“希伯来精神”“希伯来文明”等同于基督教或基督教文明。
在抽象意义上使用这对概念的代表人物海涅指出,“16世纪出现了双重的文化复兴——一种希腊文化(a Hellenic renascence)与一种希伯来文化的复兴(a Hebrew renascence)”。海涅甚至用“犹太人和基督徒”来与“希腊人”对立。他说:“‘犹太人’和‘基督徒’对我来说意思相近,二者的对立面是‘希腊人’——当然‘希腊人’的说法在此也并非指涉某一固定民族,而是表示一种既是天生、又是后天培养的思想倾向和看问题的方式。”(阿诺德,2008:97)也就是说,无论是希腊的与希伯来的对立,还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与“希腊人”的对立,都是在“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联系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海涅声称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具有希腊的和希伯来的倾向。作为一个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他迫切需要寻求两种宗教的共同点。尽管阿诺德从未明确承认,但学界普遍认为,阿诺德将“希腊人与犹太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两极对立的抽象使用深受海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文化理论基础 (Fisch,1993:498)。
3 阿诺德的Hebraism(希伯来精神)
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语境来看,将这两个术语译成“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是比较恰当的,因为阿诺德比较的不是这两种文明或者文化的异同,而是说西方文化中始终有代表了人的“智性冲动”(希腊的)和“道德冲动”(希伯来的)的两种精神力量的影响。它们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此消彼长。阿诺德说:“在整个过程中,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互相更迭……两种力量各有属于自己的辉煌,各有一统天下的时光。如果说伟大的基督教运动(即基督教初期)是希伯来精神和道德冲动的胜利,那么被称作‘文艺复兴’的那场伟大运动就是智性冲动和希腊精神的再度崛起和复兴。”(阿诺德,2008:108)他接着指出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常被称作希伯来复兴(a Hebraising revival)”,同时强调“要想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仔细分出希伯来和希腊的因素是十分困难的”(阿诺德,2008:109)。由此可见,阿诺德这里所说的“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分别指的是古代希腊文化和古代希伯来文化中蕴含的截然相反的两种传统,以及这两种文化精神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二元对立通常被定义为“古典的与基督教的”或 “古典的与浪漫的”(阿诺德等人语)或“智力与情感”或“形式与感情”之间的论争。但西方学界普遍认为,阿诺德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选用Hebraism来描述西方文化二元对立当中的一极。但西方学术界似乎并不关心阿诺德这个19世纪的英国“基督教徒”为什么选择用Hebraism将“清教的英格兰与其希伯来遗产之间如此特别地联系在一起”。大多数西方批评家在指出Hebraism一词与基督教中的希伯来遗产的关系之后,就转而讨论阿诺德的“2H”所指涉的“知与行”的二元对立的意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论者不会担心西方读者会因为阿诺德使用了Hebraic(希伯来的), Hebrew(希伯来人)便把Hebraism and Hellenism直接转换为“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更不会将Hebraism视为等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希伯来精神或希伯来文明”。
研究表明Hebraism一词在古代并无确切的对应词。在希腊语中与该词最接近的是Ioudaism,即犹太教Judaism这一带有强烈的种族或民族含义的术语,指的是犹太人应该遵守的文化和宗教规范。尽管阿诺德是在抽象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但他在《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一文中引入这两个关键概念时也明确指出,“最显著最辉煌地展示了这两种力的两个民族可以用来为之命名,我们分别称之为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 (阿诺德,2008:97)。这里的“两个民族”当然是古代希腊民族和古代希伯来民族(闪米特人)。在后文中阿诺德说:“种族差异成分使印欧语系的民族和闪米特民族在创造力和人文历史等方面都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差别。希腊精神长于印欧民族中,希伯来精神是闪米特民族的产物。英国是个印欧语系的民族,似乎自然属于希腊精神运动。”(阿诺德,2008:111)这里,阿诺德将这两种精神的源头追溯到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古老民族。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似乎很喜欢提及种族。特里林曾说阿诺德使用Hebraism 还因为这个术语与19世纪人们对种族理论以及对闪米特民族的着迷有关,但与阿诺德本人接触的同时代的英国犹太人并无多少关系 (Trilling,1958:235)。不过,在19世纪种族主义盛行的欧洲,“闪米特民族”往往与卑贱的犹太人连在一起。阿诺德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就毫不掩饰自己对犹太人的厌憎态度,声称犹太人无权获得政治权利,因为他们是住在英格兰的外人,也不同意给犹太大学生授予学位。相比之下,马修·阿诺德对待犹太人、犹太教的态度要友好得多。托马斯·阿诺德把犹太教比作“有毒的植物”,将其论辩对手斥为“犹太人” (Alexander,2012:18) ,而他的儿子却盛赞英国新教教徒继承了“希伯来人”的特性,尽管他所谓的希伯来人,更多是指圣经时代的犹太人。马修·阿诺德明明白白指出了基督教对希伯来精神遗产的传承,“基督教丝毫没有改变希伯来精神将行置于知之上的基本倾向”(阿诺德,2008:100)。他说作为印欧民族的英国人不仅具有“卓越的印欧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分享了作为“闪米特民族”的“希伯来人”卓越特性(Arnold,1993:163)。阿诺德明确指出“希伯来精神是闪米特民族的产物”,这本身体现了他对同时代人狭隘的反犹主义情结的超越。
当然,也有犹太学者从阿诺德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中看到了种族主义倾向。比如他提到西方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时,称“希腊精神重返世界,又一次同希伯来精神,一种经过更新和清洗的希伯来精神(a Hebraism renewed and purged)照面”(阿诺德,2008:110,译文参照英文版有改动)。这里的“Hebraism”是前面加上了不定冠词的“一种经过更新和清洗的希伯来精神”。原华盛顿大学犹太中心主任爱德华·亚历山大在与笔者讨论阿诺德的“Hebraism”的所指时说,阿诺德所谓的“Hebraism”最多可以视为“他那个时代的世俗新教主义”,即“具有希伯来传统的新教主义”或者“基督教希伯来精神”。或者如费尔德曼所说,阿诺德“将希伯来精神等同于苦行的基督教(ascetic Christianity)”( L.Feldman,1994:5)。弥尔顿·西梅尔法布就曾不客气地说,“最令许多犹太人失望的是阿诺德并没有,事实上他也不在乎,谈及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品格和存在方式。……阿诺德是在定义他所理解的19世纪英国偏狭的新教精神。他所谓的希伯来精神指向的是狭隘的新教圣经崇拜。”(Himmelfarb,1973:299)事实上,在将“希伯来的”视为西方文化基本要素的同时,阿诺德也试图保持某种清晰的距离:将闪米特人与印欧民族,犹太人与基督徒区分开来,或者如他在《圣保罗与新教》一书中所说,将古代希伯来人与“我们现代的西方的人民”区别开来(Alexander,2012:26)。
在《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一文里的确可以读出阿诺德随处可见的对犹太教的优越感。在讨论希伯来精神在人性论方面对希腊精神的超越时,他说“那结果了并统治着原先走了歪路,已经一无可取的世界的希伯来精神,正是,而且只可能是后来发展阶段的、更加属灵的、也更加吸引人的希伯来精神,这就是基督教”(阿诺德,2008:105)。这里,阿诺德明确指出基督教才是古代希伯来精神的真正继承者,犹太教是“走了歪路,已经一无可取的世界”。这也许是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希伯来文明即基督教文明”的出处吧。但事实上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流行的观念,即上帝已经抛弃了犹太教徒,基督教已经取代犹太教,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在该文的另一处,阿诺德再次强调:“犹太人承担着宣告神的诫命的职责,强有力地阐明了‘良知’‘自制’等词语所指向的境界,因此,‘神的圣言要交托他们’这句话所言十分精当。基督教紧随犹太教,对神谕作出更为深刻有力的阐述,产生的影响也广泛得多。”(阿诺德,2008:107)我们不可能要求处在种族主义盛行的19世纪的阿诺德具有21世纪的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思想,如亚历山大所说,作为一个基督教徒,马修·阿诺德“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基督教战胜‘旧’的律法——犹太教的思想(Christian triumphalism)”(Alexander,2012:26)。
综上所述,在阿诺德的论著中,Hebraism 一词语义宽泛,有时指古代犹太教,有时指人类生活中道德-伦理的一面,也有时指的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不过,无论怎样,马修·阿诺德所谓的“希伯来精神”不等于基督教精神,希伯来文化或文明也不等于基督教文化或文明。中文语境里,部分研究者将这一理解和延伸归结到阿诺德的“两希精神”显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