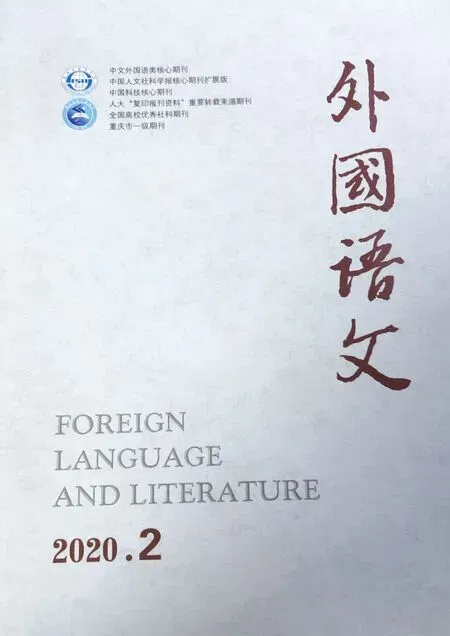黄瀛与宫泽贤治:以心象素描为介质的回声
2020-01-03杨伟
杨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重庆 400031)
作为诗刊《铜锣》(1925—1928)的主要同人,黄瀛(1906—2005)与宫泽贤治(1896—1933)都是个性鲜明、不可复制的独特个体,但在致力于突破语言界限、地域界限乃至民族界限这一点上,两者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纵观黄瀛的诗歌创作更是会发现,其中充满了与宫泽贤治之间以“心象素描”为介质的回声,印证了他对“心象素描”这一宫泽贤治特有的诗歌手法的共鸣和仿效。正如日本学者冈村民夫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当说到贤治对同时代诗人的影响时,大都停留在讨论草野心平与中原中也上。显然,对黄瀛与宫泽贤治进行比较考察,在思考宫泽贤治的接受史上,无疑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冈村民夫,2018:22)。
我们知道,黄瀛与宫泽贤治的交往乃是围绕着《铜锣》进行的,大致始于草野心平与他联名写信邀请宫泽贤治加入《铜锣》同人的1925年7月。当时,在中国岭南大学留学的草野心平因“五卅运动”的影响而被迫回国,在黄瀛位于九段附近的公寓里寄宿了近两个月。此间,草野心平在黄瀛的协助下不仅装订发行了《铜锣》第3号,还给宫泽贤治写信,力邀他成为《铜锣》同人。尽管宫泽贤治的诗歌在当时遭到了文坛的漠视,但仍然引起了为数不多者的瞩目。无疑,草野心平就是其中之一。草野心平因曾在中国广州岭南大学留学,与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的成员多有交往,并深受美国诗人桑德堡等的影响,所以能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上去认识和评价当时不被狭隘的日本文坛所接受的心象素描集《春与阿修罗》。可以想象,黄瀛很可能正是通过草野心平而知道宫泽贤治的。随着宫泽贤治从杂志第4号起成为同人,宫泽贤治与黄瀛在《铜锣》上同时发表诗作,已成为该同人杂志上一道日常的风景。通览《铜锣》整个16期杂志会发现,宫泽贤治和黄瀛在《铜锣》上同台献技,主要集中在1925年9月至1927年2月的大约1年半时间。特别是在第4号、5号、6号、10号上,黄瀛和宫泽贤治的诗作更是一前一后刊登在紧邻的位置上,这不能不促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关注彼此的诗歌。
黄瀛在《自南京》中自述道:“说到与他(指宫泽贤治——引者注)之间作为诗人的交往,虽然是在《铜锣》上开始与他为伍的,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话,其实在佐藤惣之助于《日本诗人》上评论《春与阿修罗》之前,我就知道他了。”(黄瀛,1981:209)我们知道,所谓佐藤惣之助对《春与阿修罗》的评论,是指发表在《日本诗人》1924年12月号上的《十三年度的诗集》,该文认为宫泽贤治的《春与阿修罗》是大正“十三年度的最大收获”(佐藤惣之助,1924:96)。无疑,这是日本诗坛对宫泽贤治进行的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评论,黄瀛特意在《自南京》中强调,在这之前他便已经知道宫泽贤治的存在,显然是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他不是借助他人,而是自己独具慧眼地注意到了专注于“心象素描”的宫泽贤治。不用说,在这种自豪的口吻中蕴含着他作为诗人对宫泽贤治的高度景仰和强烈共鸣。黄瀛曾这样谈到他第一次阅读《春与阿修罗》时的印象,“我被它的韵律感深为震撼。接下来,我又惊讶于他作品的多样性,即涉猎领域的广泛性。他的诗兴就如同涌泉一般迸发,令人惊叹”(黄瀛,1986:39)。黄瀛不仅对宫泽贤治的诗歌,也对宫泽贤治其人抱有浓厚的兴趣,不仅“从草野心平、栗木幸次郎那里听到过关于他的传闻”(黄瀛,1981:209),还从其他人那里打听过宫泽贤治的为人和趣闻。关于这一点,有同是《铜锣》同人的森庄已池的文字可以佐证(森荘已池,1988:167)。作为贤治在盛冈中学的后辈,森庄已池从盛冈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曾寄宿在九段中坂与黄瀛寓所相距仅两三分钟的地方。据说他时常去拜访附近的黄瀛,而两个人的主要话题就是围绕着宫泽贤治展开的。此外,森庄已池还证实,他曾听黄瀛这样说起过他与贤治之间的书信往来:“能把收件人姓名‘黄瀛’这两个字一笔一画写对的人只有两三个人,宫泽贤治就写得又大又正确,几乎占满了整个信封。”(森荘已池,1988:167)尽管现在尚未发现相关的物证,但在这两个诗人之间的确曾借助信件进行过文学或精神上的交流。
显然,正是由于黄瀛对宫泽贤治其人其诗的强烈关注,才在1929年春天催生了两人之间的唯一一次见面。1929年春天,黄瀛借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旅行到花卷温泉之机,特向上级军官请假,去拜访了宫泽贤治家。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宫泽贤治,也使他不仅成了“与生前的贤治有过谋面之交的唯一中国文人,也是最早评价贤治的外国人”(王敏,2010a:176)。
根据黄瀛《自南京》中的回忆,“1929年的春天,当学校宣布毕业旅行时,我可是兴奋不已。那既不是即将毕业的兴奋,也不是即将看到山海之自然美,获得新知识的兴奋。从北海道到东北一带,吸引我的就只有宫泽贤治的存在了”(黄瀛,1981:208)。黄瀛独自一人搭乘电车来到花卷,又在夜色中坐了约1小时的人力车去拜访宫泽贤治家。不料,当时的宫泽贤治因积劳成疾已卧病在床。“我本想立刻回去,好像是他弟弟还是什么人出来,说本人一定要见我一面,于是我进了宫泽君的病室。我们俩大概是先从各自对对方的想象开始聊起的。”之前说好“只聊5分钟”的约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宫泽君一再挽留,“结果聊了半小时之久”(黄瀛,1981:208)。从这些表述中可以推想,宫泽贤治对黄瀛其人其诗也颇有好感,评价很高,才会不顾身体抱恙而一再挽留对方。时隔67年之后,黄瀛又在《日益繁荣的宫泽贤治》的演讲中重温并补充了那段回忆的部分细节:“那时的宫泽由于生病,身体很孱弱。他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有点丑。”但“如果作为一个诗人来看,宫泽贤治分明透着诗人的威严和美感,不像是一个普通之人”(黄瀛,1997:66)。
据黄瀛自述,这次会面并没有怎么谈论诗歌的话题,虽然他嘴上没说,但却是抱着“你的诗很好,我的诗也不赖” (黄瀛,1997:66)的心态去见宫泽贤治的。在此,切不可忘记一个事实:当时的黄瀛早在东京的中央诗坛上年少成名,大肆活跃在《诗与诗论》《诗神》等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线杂志上,而宫泽贤治则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诗人,所以黄瀛那种“我的诗也不赖”的自矜亦非空穴来风,毋宁说反倒说明,他能抛开诗坛的偏见而对贤治诗歌的价值洞悉于心,所以才会对一个游离于中央诗坛之外的无名诗人抱着如此强烈的较劲意识吧。尽管“比起诗歌,聊得更多的是有关宗教的话题”(黄瀛,1981:208),但与仰慕已久的诗歌伙伴面对面地交谈,这件事本身就有着巨大的意义,以至于在回去的途中,“我感受到一种如同幼儿看见了纸罩蜡灯似的幸福,一边在心里祈祷着他的病早日康复”(黄瀛,1981:208)。
不用说,与宫泽贤治的唯一一次见面给黄瀛留下了日久弥深的印象,以至于他后来多次著文不断填充着这次见面的诸多细节。1986年黄瀛在《宫泽贤治随想》中回忆道:“他似乎对我太过年轻和健康感到颇为诧异。而他虽然卧病在床,但却表现出浩渺博大的精神,这确实让我惊讶不已。”但黄瀛也同时承认,“因年龄的差距、环境的殊异等种种原因,导致谈话不无龃龉”(黄瀛,1986:40)。所谓谈话中的“龃龉”或许指的就是,黄瀛原本期待的是诗人与诗人之间关于诗歌的倾心交谈,不料宫泽贤治却聊的是宗教的话题,以至于“我在昏暗的病室里,一边仔细端详着宫泽君,一边听着不明就里的‘大宗教’话题。他说话时那种讷讷的口吻让我有点害怕”(黄瀛,1981:208)。
67年后的黄瀛是这样来描述当时的自己的,“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小青年。说是小青年,其实还只不过是个孩子,不是很明白,只是觉得宗教什么的很无聊。但是听宫泽讲得津津有味,我意识到他确实对宗教抱有极大的期待。后来他提到田中智学,而我正好对田中智学也略知一二,我在浅草附近寄宿的时候,知道他很受平民百姓的尊重,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就比较起劲儿了。” (黄瀛,1997:67)显然,黄瀛67年后的这次演讲,对《自南京》中那句“让我有点害怕”的简短表述进行了某种背景上的补充,并具体举出了田中智学这个人名。不难看出,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黄瀛对宫泽贤治的“宗教”话题有了更深的领悟,从《自南京》中的只是“让我有点害怕”变为尽可能去试图理解宫泽贤治的宗教观。
回到东京后不久,黄瀛就在当时最前卫的现代主义诗歌杂志《诗与诗论》1929年6月号上发表了一组题为《心象素描》的诗歌。可以说,这组诗歌是在向当时已经暂停文学活动,但却在诗坛上依旧默默无闻的宫泽贤治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或许黄瀛是有意提醒世人:不要忘了宫泽贤治这位无名的地方诗人,不要漠视他那崭新而独特的创作手法。同年11月,黄瀛又在《诗神》上发表了《初春的风》一诗。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身为军人的黄瀛吹拂着初春的风,策马行进在泥泞道路上的情景。随着马儿的前行,诗人的思绪也随处流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病中的诗友宫泽贤治,不由得祈望他抱恙的身体早日痊愈。诗人最后写道:“我们映照在大地上的影子多么凄寂!/马儿啊,你得睁大眼睛!我在日本的生活也已所剩无几!”(黄瀛,1929:84)显然,对自己回国后前途未卜的担忧,与对宫泽贤治身体状况的牵挂交织在一起,化作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其描写初春风物的诗行中。不久,黄瀛又发表了题为《诗人交游录》(《诗神》1930年9月号)的随笔,栩栩如生地记录了他与各位诗友交往的始末,其中也不忘提到居住在花卷的宫泽贤治,说他“是我不能忘怀的友人” (黄瀛,1930:82)。
那以后不久,黄瀛“在日本所剩无几的”生活宣告结束,于1930年底回到中国南京,任职于国民党参谋本部。在这期间,黄瀛还不时向东京的各种杂志投寄诗稿或应约撰写诗论。黄瀛在《诗人时代》1933年6月号上发表了总题为“涂鸦”的组诗。笔者注意到,在《涂鸦》的总题下,黄瀛特意加上了这样的说明文字:“谨以此‘涂鸦’来代替向冈崎清一郎和宫泽贤治君汇报近况。”(黄瀛,1933a:23)从中可以看出,黄瀛是把宫泽贤治作为潜在的对话者和阅读者来撰写这些诗歌的。
不久,他又在《日本东京》(《诗人时代》1933年12月号)一文中,抒发了他在离开东京后,身在南京远眺日本诗坛所萌发的种种感想。其中既有对日本诗坛现状的冷静观察,也有对日本诗友绵长的思念。而宫泽贤治也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在令人怀念的诗友名单上。而且黄瀛意识到,自己和宫泽贤治等诗友的疏远不单单源自于地理上的距离,更源于两国间急剧恶化的政治局势。而就在黄瀛写完该文时,竟传来了宫泽贤治去世的消息:
追启:当写完这篇文章时,接到了宫泽贤治病逝的噩耗。原来他的病真的没能好转。事到如今,更是对人一生的脆弱涌起无限的感慨。不久前,我才刚刚从杂志《面包》上读到某人写的宫泽贤治论,不禁备感亲切,不料……(黄瀛,1933b:23)
从这些文字中,能读取到黄瀛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恸。尽管黄瀛与宫泽贤治只见过一面,但宫泽贤治却早就作为其灵魂上的朋友和诗歌上的共鸣者,成了他谈到诗友时必然提及的对象,更是他创作诗歌时浮现在脑海里的对话者。《日本东京》一文完成时恰逢接到贤治病逝的噩耗,这种巧合或许颇具象征性地暗示了黄瀛与贤治之间不可思议的缘分和羁绊。
而事实上,黄瀛和宫泽贤治的缘分和羁绊并非仅仅见证于这些回忆性的文字里,而毋宁说更多地体现于两者对诗歌创作的强烈共鸣中,以及黄瀛对贤治诗歌有意识的仿效上,特别是对宫泽贤治的心象素描这一创作方法的仿效上。
据笔者对现有资料的查证,发现黄瀛最早使用“心象素描”一词,始于《某个心象素描》(《碧桃》1927年2月号)。显而易见,此处的“心象素描”乃是对宫泽贤治这一特有术语的借用。不过就体裁而言,该作品不是诗歌,而是黄瀛早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之一,描写的是作者利用寒假回中国探亲,某个清晨与妹妹和表姐三人在天津法租界家中的生活片段。坦率而言,它与其说是诗人流动心象的记录,不如说更像是对某个清新温润的生活场景的细致临摹,以及对身处这种场景中的“我”的“感觉”的随手记录。而笔者注意到,这种对“场景”和“感觉”的准确描摹其实也是贯穿黄瀛此前大部分诗歌的一大特点。比如,日本学者栗原敦就认为,黄瀛的诗歌通常描摹的是“被认为是在‘感情·情’之前,更接近意识产生之初始阶段所感受到的东西,试图表现当从知觉中形成认识之际,知觉的主体与对象作为在分化成对对象的认识之前的未分化状态下而发挥着作用的‘感觉’”(栗原敦,2010:328)。
换言之,黄瀛的诗歌总是聚焦于在与感受对象达成一体化的过程中所萌动的原初感觉,而并不试图将其加以分化或整理成某种已经概念化的情感。毋宁说,正是依靠固守这种未被分化的混沌而鲜活的感觉,他得以保持住了备受其他诗人赞誉的清澄的感受性,形成了即物性的、朴素而健康的明朗诗风。而我们知道,“心象素描”作为贯穿宫泽贤治整个创作的一种独特方法,强调的是对“心象”——心灵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这一意义上的“内心的风物”——的“记录”,即“严格按照事实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宮沢賢治,1995:215)。我们发现,在强调保持鲜活、写实、精准的原始性上,黄瀛与宫泽贤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尽管黄瀛捕捉的是与感受物一体化中产生的“感觉”,而贤治描摹的是作为意识内一切现象的“心象”,具有不同的射程,但在强调“感觉”或者“心象”处于“未分化状态下”的原始性和鲜活性这一点上,两者无疑是毗邻而居的存在。而恰恰是在这里,潜藏着他们产生共鸣的原点。因此,黄瀛对宫泽贤治“心象素描”的关注和仿效,无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有趣的是,黄瀛将“心象素描”这一术语首次引入自己的作品,却不是在诗歌,而是在小说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为了降低实验的风险,黄瀛选择了从诗歌以外的小说门类实现突破。或许黄瀛是深谙这种风险的,所以特意给作品名“某个心象素描”附加了一个副标题:“往坏里说,就是笔记本上的涂鸦。”(黄瀛,1927:1)而笔者注意到,这与其说是通常意义上的副标题,不如说更像是带有自嘲性质的说明文字,但却可以让我们管窥到诗人在写作的具体操作上与宫泽贤治的趋同性。我们知道,宫泽贤治外出行走时,经常都随身携带着笔和笔记本,一旦在外界的触发下感觉到心象的流动,便会当场记录下来,并据此来创作童话和诗歌。比如,从《小岩井农场》一诗中就能管窥到他一边步行一边记录的情景。在散文《山地之稜》中更是记录了其用来素描的笔记本被人偷看一事。而黄瀛所谓的“笔记本上的涂鸦”,显然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即指在笔记本上的随手记录。尽管小说《某个心象素描》作为对某个清晨生活场景的细致临摹,与宫泽贤治意义上的“心象素描”相去甚远,不能说是成功的尝试,但却是对“笔记本上的涂鸦”这种方法的一次演练,也预告了接下来“心象素描”在黄瀛诗歌中的正式登陆。
果不其然,两个月后,黄瀛在《文艺》1927年4月号上发表了《心象素描》一诗,紧接着又发表了《在夕景的窗边——心象素描》(《诗神》1927年9月号)、《心象日记》(《诗神》1928年5月号),以及组诗《心象素描》(《诗与诗论》1929年6月号)等一系列诗作。而及至黄瀛发表在《作品》1930年7月号上的《到了这里时》,则以更加明确和具象的方式向我们宣告了他对贤治式“心象素描”的模仿和运用。
这首诗一开始就表达了一种创作的焦虑,即为何记录了58页的心象素描戛然而止?可自己却对其中的缘由一无所知。诗人用“干涸的我”和“断线的电力”来比喻自己才思的枯竭,如同身陷于“台灯熄灭后的世界”,看不到创作的灵光。但诗人却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它有着反抗的弹力”。于是,借助花香(嗅觉)、虫鸣和风声(听觉)等多种知觉,诗人又开始挣脱焦虑和绝望,重新“凝视着这个笔记本” (黄瀛,1934:27-28)。显然,这是一首带有“元诗歌”特点的诗,“换言之,这首诗构成了具有反论性质的、对自己不能画出心象素描这一过程所进行的心象素描”(冈村民夫,2018:22)。值得关注的是,黄瀛在该诗中明确写道,自己在笔记本上记录了长达58页的心象风景,而这一点正好与小说《某个心象素描》中所谓在“笔记本上涂鸦”的方法一脉相承,并在更多的细节上印证了黄瀛对宫泽贤治“心象素描”这一创作方法的仿效。笔者注意到,与这首诗发表在同一期《作品》上的,还有题为《花虽香》《素描》《明信片——绘在眼里的画本》等三首诗。除了“素描”“画本”等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心象素描”的用语,《花虽香》的诗末还特意附上了“心象素描”几个字。而据目前可以查证的资料来看,这也是黄瀛诗中有“心象素描”这一明确标记的最后一组诗歌。可以说,从《某个心象素描》(1927年2月)至《到了这里时》(1929年7月)为止的近两年半里,“心象”“心象素描”等词语频繁出现在黄瀛的诗歌中,而这恰好与黄瀛在文化学院和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并毕业,面临即将回国,迎来人生重大转折的时期相重叠。可以想象,这也正是黄瀛从潜心于诗歌创作,转而不得不面对众多现实困惑的时期,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中日关系走向的忧虑、对个人未来命运的担忧、对爱情最终结局的悲观等等。而这些复杂的情感与镜中的风景、窗边的夕景等交织在一起,幻化为各种流动的心象,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黄瀛与宫泽贤治一样,一边追寻眼前的风景和时间,一边记录下了跟随风景而曳动的意识。黄瀛是一个注重动员视觉和听觉等多种知觉来捕捉外界的风景,并依靠把观察原封不动转化为感受,固守未被分化的鲜活感觉,从而得以保持住了清澄感受性的诗人。当他把“心象素描”引入自己的诗歌时,意味着他并不满足于只是表现这种原初的“感觉”,而试图表现比“感觉”更复杂也更内面的“心象”。为此,他除了动员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身体性知觉,还不惜动用“幻听”这种超越了身体性而与内心意识有着更直接关系的知觉形态。比如《幻听与我》(《文艺都市》1929年6月号)就是这样的诗歌。
这首《幻听与我》描写的是,“我”来到初夏的野州某个高地,耳朵里传来了各种声音。在接受了陆军军人训练后登高眺远,顿觉人生的渺小,从而获得了稚童般的兴趣,甚至忘记了地图上的敌人。尽管“我”否定自己陷入了幻听,但“被从某处迫近而来的家伙深深地吸引”(黄瀛,1934:64-65)这一点却似乎反倒印证了“幻听”的存在,因为“那个从某处迫近而来的家伙”肯定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毋宁说是我借助“幻听”或者“幻觉”而感知到的假想现实。这首诗故意借否定幻听来渲染幻听的存在,更是凸显出诗人在初夏的风物和大气中那种内心的善感和莫名的期待,而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宫泽贤治题为《痘疮(幻听)》一诗的影响。在《痘疮(幻听)》一诗中,宫泽贤治把在脸上长出红色痘疮的传染病和进入春季后变得旺盛的性欲隐晦地联系在一起。而该诗就发表在其友人森庄已池主办的岩手县本土杂志《貌》第3号(1925年9月)上。如前所述,森庄已池也是《铜锣》的同人,并一度与黄瀛在九段多有交往,不难设想,黄瀛很可能通过森庄已池而读到过这本杂志。当然,除了这首《痘疮(幻听)》,宫泽贤治还用这种手法创作过不少的作品,让我们有理由认为,黄瀛是从贤治那里获得灵感而引入“幻听”这一创作手法的,以便让自己对“感觉”的记录能够上升为对“心象”的素描。
笔者注意到,《幻听与我》发表在《文艺都市》上,正是黄瀛前往花卷探望宫泽贤治之后的1929年6月。同一时期,黄瀛还在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诗歌杂志《诗与诗论》1929年6月号上发表了总题为“心象素描”的组诗,其中第一首就是《士官学校之夜》。在这首诗中,诗人描写了自己在寒冷的夜晚起床撒尿的情景。“有如手术刀般”的冰凉感觉(触觉)、厕所里把人刺激得一阵亢奋的“阿摩尼亚气味”(嗅觉)、耳边神奇地传来的“‘嘀嗒’的钟声”(听觉),成了汇聚在“我”这个年轻士兵身上的各种知觉。而那“十一点三十分的报时声”则准确地告知了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成了对某个事件和某个时间的心象进行记录的原始证明。诗人接着写道:“缅甸的皮影戏正可怕地摇晃着窗户的玻璃/掉头一看,周围整齐地排列着战友的一个个脑袋/死者的形象直让人毛发竖立!/我欲翻身做梦,却只闻寒风的攻击在远处狂吠。”(黄瀛,1934:116)在这里,“缅甸的皮影戏正可怕地摇晃着窗户的玻璃”,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客观现实,即外面什么东西随风晃动着映照在窗户上的影子,也不妨视为在黑暗与寒冷中出现在“我”眼前的幻影,以至于神思恍惚中战友的一个个脑袋也成了让人毛发竖立的死者头颅,从而暗示着诗人逐渐加深的幻觉和意识的渐次模糊,动态地折射出诗人半夜时分的心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貌似用“只闻寒风在远处狂吠”来暗示“我欲翻身做梦”的失败,但事实上也存在着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即所谓“寒风的攻击在远处狂吠”乃是诗人的意识渐渐模糊,由近向远浮游而去所产生的幻听,而这两种貌似矛盾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同时成立,恰好与诗人半梦半醒、似睡非睡的恍惚状态达成了高度的契合。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宫泽贤治的某些作品,比如描写因火山性气体而导致意识模糊这一过程的《真空溶媒》,还有记述修行僧入眠时产生幻觉体验的《河原坊(山脚的黎明)》等。这是因为,在宫泽贤治那里,“不管是描写幻视或者幻听,都从不当作神经病的征候,而是作为意识现象之一来加以处理”(鈴木貞美,2010:241),从而得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心风景。显然,黄瀛在仿效“心象素描”这一创作手法时,除了动用各种身体性知觉之外,还不断扩大表现的手段,试图借助幻听、幻觉等多种介于身体性与心理性之间的感觉来摹写内心的风景,以达成最忠实的心象记录。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尽管黄瀛与宫泽贤治的“心象素描”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但两者的差异性也同样相当明显。如果说“宫泽贤治的心象是把精神的、质的变动与变化的风景及身体的移动结合在一起,连续而多层次地描写出来”,那么,“黄瀛的心象素描更加具有瞬间性、静谧性以及极强的画面感,其重心放在作为抒情诗乃至叙景诗的结构上”(冈村民夫,2010:294)。此外,与宫泽贤治笔下的自然所孕育出的宗教性和宇宙论相比,黄瀛诗歌所呈现的自然更具人本主义的色彩,更富于即物性和抒情性。如果说宫泽贤治的心象素描渗透着宗教的激情和晦涩,那么,黄瀛的心象素描则浸润着世俗的情念和人伦的明朗。换言之,我们无法从黄瀛的心象素描中读取到宫泽贤治所定义的“心象”那样的宗教意义和浩渺的宇宙意识。毋宁说倒是从他的诗歌中感受到一种近似于肯定自我、以简明的语言去临摹日常生活的淳朴感性。
原本我们可以期待他们之间的文学交往结出更多更美的花朵,但宫泽贤治的早逝使得他们之间的交往画上了句号,不,这只是在现实的层面上。毋宁说宫泽贤治化作了黄瀛灵魂上的朋友,成了他心目中最尊崇的诗人形象。也正因为如此,黄瀛成了宫泽贤治在中国被广泛阅读和研究的重要推手。黄瀛曾在《日益繁荣的宫泽贤治》的演讲中谈到自己向鲁迅先生推荐宫泽贤治的往事。1932至1934年的两年间,身在南京的黄瀛曾不时出入于上海的内山书店,并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与鲁迅有过多次促膝交谈。鲁迅曾建议黄瀛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翻译成日语,介绍到日本去。“因为说到它(指《聊斋志异》——引者注)是一部动物的小说,所以,我就稍微谈到了宫泽贤治。于是,鲁迅就连声追问道,这个人如何,这个人如何。那时候,我只知道他的诗歌,对他的童话只是读过,但研究并不深入,所以只是尽我所知告诉了鲁迅。”黄瀛不无自豪地说,“把朋友的优秀东西介绍给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这是我的明智,而且鲁迅先生听后也一个劲儿地问道,还有呢?还有呢?”(黄瀛,1997:69)黄瀛无非是想告诉我们,回到中国后,他总是一有时机就向中国文学界宣传着宫泽贤治文学的魅力。黄瀛1980年调入四川外语学院(现四川外国语大学)任教,向研究生们教授日本文学之后,宫泽贤治的诗就成了他首选的讲授文本,而《不惧风雨》作为其讲解宫泽贤治的入门作品,更是引起了在座学生的极大兴趣。日后成为宫泽贤治研究专家的王敏就曾说起,自己与宫泽贤治的邂逅乃是在黄瀛先生的课堂上。在问及对贤治的印象时,她就听黄瀛说道:“虽然贤治绝不能算是美男子,但他的诗却非常美。出自他笔下的诗,一读便知。”(王敏,2010b:268)而正是这些话使得王敏最终选择宫泽贤治为自己毕生的研究对象,其由黄瀛担任指导教师的《宫泽贤治的童话——关于“猫鼠篇”》(1980年)乃是中国第一篇以宫泽贤治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契机,王敏成了在“文革”后的中国最早翻译宫泽贤治童话的人,并推动了宫泽贤治在中国的译介,也成了在日本以《宫泽贤治与中国》为题获得文学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以至于黄瀛不无自豪地说道:“关于宫泽贤治的童话,我指导的研究生王敏(现为四川外语学院教师)比我有着更为详细的研究。(中略)总之,我认为,她在中国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将宫泽贤治当作了自己的研究目标,这一点还是值得给予些许重视的。”而且黄瀛还意识到,“在日本,关于宫泽贤治的评论和研究似乎方兴未艾,开展得相当深入,而在其邻国中国却还远远没有展开”(黄瀛,1986:40 ),所以,他才更迫切地想向人们传达宫泽贤治的魅力。毋庸置疑,在他心中燃烧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让宫泽贤治成为世界的贤治。而笔者认为,这或许是1929年那次见面的延续,是黄瀛以自己的方式向身在另一个世界的宫泽贤治持续发出的超越时空的回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