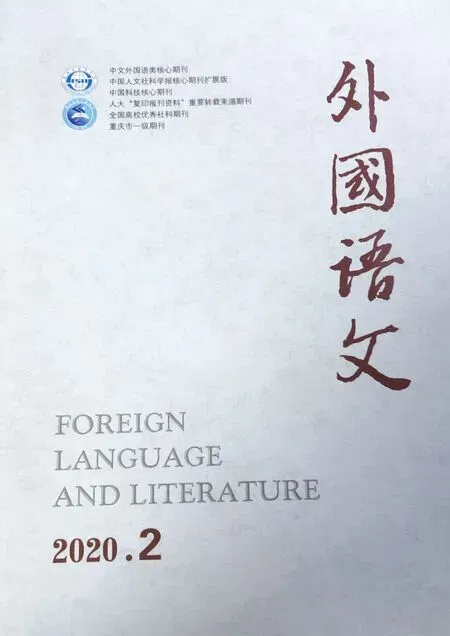实至名归
——格里美尔斯豪森《痴儿西木传》
2020-01-03李昌珂景菁
李昌珂 景菁
(1.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2.慕尼黑大学 德国 慕尼黑)
李昌珂,1977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法德系德语专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浙江科技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德语副主任委员。主要学术代表作有:《德国文学中国题材小说》,获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一等奖;《德国文学史》(第5卷),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中国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我们这个时代”的德国——托马斯曼长篇小说论析》,获北京大学第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 德语经典之作
16世纪中叶,西班牙费利佩王朝末期,西班牙社会“经济开始衰败,大批抛弃土地、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沦为无业游民,此外还有众多的从战场上伤残而归的贫穷的士兵,这些人很难靠劳动糊口和安分守己地生活。他们养就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毛病。而且当时社会上冒险的风气盛行”(沈石岩,2006:58)。这个背景下,一部世界名著应运而生,问世后即在读者群中风靡,在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引发了模仿潮,对西班牙文学和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作品就是《小癞子》(LaVidadeLazarillodeTormes)(1)这部小说原名为《托尔梅斯河的小拉撒路》。,作者佚名,是一部描写一个泼皮流浪汉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流浪汉小说。
德国人自创的流浪汉小说也陆续面世,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夫·冯·格里美尔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约1621—1676)的《痴儿西木传》(DerabenteuerlicheSimplicissimusTeutsch, 1669)。该作最初以笔名发表,问世后很长时间内人们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该小说曾风行一时,后遭时间冷落,湮没了一百多年后被浪漫派作家重新发掘,传世至今,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名著。歌德推许它比18世纪的著名小说还要更胜一筹。托马斯·曼读后有感:“这是一座极为罕见的文学与人生的丰碑。它历经近三百年的沧桑,依然充满生机,并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更长久地巍然屹立;这是一座具有不可抗拒魅力的叙事作品,它丰富多彩,粗野狂放,诙谐有趣,令人爱不释手,生活气息浓厚而又震撼人心,犹如我们亲临厄运,亲临死亡。它的结局是对一个流血的、掠夺的、在荒淫中沉沦的世界彻底的悔恨与厌倦。它在充满罪孽的、痛苦悲惨的广阔画卷中是不朽的。”(格里美尔斯豪森,2004:译本序2)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杰拉德·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推崇它为一部“把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广博的教育小说、流浪汉小说、塞万提斯式的幽默、法国讽刺模式以及象征性旅行等各种叙事形式铸为一炉”(杰拉德·吉列斯比,1987:129) 之作。我国学者赞许它“显示了日耳曼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潜能”(蹇昌槐,1995:102)。
2 战争罪恶叙事
《痴儿西木传》全书结构分为五卷,以一成不变的、有时还直接向读者打招呼的第一人称“我”叙事。主人公“我”是个孤儿,从小被偏僻农村农户收养,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少不更事,懵懵懂懂。小说开篇段落,格里美尔斯豪森巧妙利用“我”对世界的一无所知,写“我”把自家茅屋赞美得胜过皇宫,“我敢说,任何一位皇帝,即使他比亚历山大大帝更有权力,也不可能亲手盖成这样一座宫殿,他不半途而废才怪呢”(格里美尔斯豪森,2004:3)。把他阿爸的农事劳作比喻成犹如贵族、骑士的消遣式、尚武式生活:“在兵器和盔甲库里,各种犁耙、钉耙、锄头、斧子、铲子、粪叉、草杈塞得满满的,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我的阿爸每天都摆弄这些兵器。锄地、垦荒是他进行的军事演习,就像古罗马人在和平时期所干的那样。给牛套车是他作为司令员所下的命令, 运粪是他的防御加固措施,耕种土地是他进行的战役,劈木柴是他每天的体格锻炼。”(4)在文学本体上既把一种流浪汉小说典型的广场吆喝式语言带入了叙事,在人物描写上又表明“我”是个智力低下、不明事理的“傻角”。“30年战争”来了,养父母农庄被毁,“我”逃进森林,遇一隐士,被其收留。隐士见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便管他叫“痴儿西木”,教他识字和写字,还教他祈祷、基督教教义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两年后隐士辞世,西木独自在森林里生活了半年,被乱兵洗劫了窝棚,没了粮食和衣物,只得去外面世界寻找果腹之物。在哈瑙,西木被瑞典士兵抓住,带到了司令官那里。司令官见西木呆头呆脑,不谙世事,了无心机,还会识字,便留下他当侍童。西木离开森林后的流浪经历由此开始,小说故事主线便是西木的流浪。
同样是流浪汉经历,作者可以写流浪者不同的命运,来自西班牙的那部《小癞子》讲述的就是一个穷苦流浪儿的故事。《痴儿西木传》中的西木流浪,很多是以作者格里美尔斯豪森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研究表明,西木的流浪遭遇在小说“第四卷之前几乎与作者经历一致”(格里美尔斯豪森,2004:译本序2),说明格里美尔斯豪森在用文学解他的人生之惑,或疏他的心中郁积。格里美尔斯豪森把自己人生经历作为小说最核心的写作资源,不是出于一个作家要表达自我的本能动机,而是因为战争是西木流浪的原因,格里美尔斯豪森起笔写这部小说就是拜战争的兽性所赐。《痴儿西木传》故事的起点就是战争,叙事从“30年战争”这个历史关口切入,叙事的开头就散发着兵燹气息。小说开篇不久,叙事讲述西木被一队骑兵围住,西木感觉这些人就是他阿爸时刻在告诫他一定要避而远之的“四条腿的流氓和强盗”(11),但是天真幼稚的他还是将这些骑兵带到了他阿爸的庄园。随即就发生了那些兵匪搜掠抢劫、毁灭村庄、奸淫妇女、施虐雇工之事:
这帮骑兵在我阿爸四壁乌黑的屋子里开始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们的马牵进马厩;然后,他们各干各的勾当,桩桩件件无一不是肆意破坏和糟蹋。……我家的使女在牲口棚里给他们折磨得那样厉害,她再也走不出来了,她被糟蹋了!那雇工,他们把他捆倒在地,往他嘴里塞进一块木头,灌了他满满一大桶臭粪水;他们把这叫作瑞典饮料……(12-14)
“30年战争”期间德国人惨遭荼毒,在第一人称叙事者那善于观察的视角和善于细致的讲述中重构,呈现在读者眼前。“我”的讲述将读者带进猝然降临的兵灾,“我”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的直白语言大大加强了士兵暴行的凶狠残暴维度。“我”还特地申明,意愿上他“并不想把爱好和平的读者和这些兵痞暴徒一起带进我阿爸的庄园——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简直是糟糕透顶,然而我这部故事的发展却要求我这样做。为了让亲爱的后代知道,在我们德国这一次战争中,常常发生了一些多么恐怖而骇人听闻的事情”(12)。将战争的动乱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们了解和记住“30年战争”使德国遭受的灾难,很显然就是格里美尔斯豪森为他的这部小说确定的一个基本叙事观。
接下来的叙事中,战争的罪恶在叠加,平民百姓遭到的战乱蹂躏在加剧。战争叙事的下一个画面,是残暴的士兵残忍地折磨和杀戮农民,子弹没有打中的就把他们的鼻子和耳朵割下来,“用短刀把农民从头顶到牙齿劈成两半”(44),暴行和戕害的动作刺激着读者感观,那浓浓的血腥气似乎仍在强烈嗅出。再次遭遇凶狠士兵的西木于饥寒交迫中昏昏睡去,进入一个梦境:
好像我家周围的树一下子都变了样,外表和原来的完全不同了。每棵树的顶上都坐着一个骑士,树枝上长的不是树叶,而是装饰着各式各样的士兵:他们或持长矛、或拿火枪、或短铳、或短刀、或小旗、或鼓、或号、或笛。都那么井井有条地渐次分列两边,煞是好看有趣。树根周围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像手工业者、雇工,大半是农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尽管地位低贱,却给大树增添了力量。当大树欲枯欲倾时,他们便再竭已而输,注以生气,用消耗自己来补足大树因落叶而造成的空乏,致使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害。他们朝着坐在树上的人叹息,实在并非无病呻吟,因为大树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口袋里的钱,甚至连七道锁锁着的钱都压出来了。谁要是不交出钱来,那么司令官就用毛刷去刷他们,这叫作军法处置。他们只能从心底里发出叹息,从眼睛里滴出泪水,从指甲里渗出鲜血,从骨头里流出骨髓……(45-46)
这个梦是小说叙事的一个机关,西木梦见的“战争之树”既是意象也是象征。梦境中的“战争之树”在构建一个情势框架,其树上、树下与四周参差交错的关系结构将骑士与士兵、城市与农村、手工业者与农民、雇工与小丑、社会下层的人、底层的人与社会上层的人网罗到一起。这个意象看上去比较荒诞,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表达了对战乱年代社会情形和生活命运的认知,格里美尔斯豪森用荒诞的笔触挑开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图像:动荡年代地方武装风涌,各种势力拉锯,“草头王”横行,到处是毁灭别人和被别人毁灭的雇佣兵现象。
小说第五卷里,格里美尔斯豪森写了一段话:西木成了香客,跟着朋友去朝圣,到达一个村庄,看到的安然生活情形让他产生了仿佛置身于“巴西或中国”的感觉。“我看到百姓们安居乐业, 厩舍里满是牲畜, 场院里鸡鸭成群, 街市上游人熙攘, 酒店里宾客满座,尽在寻欢作乐。这儿完全不存在对敌人的恐惧和对抢劫的担忧,根本不必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牵肠挂肚;人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下生活得无忧无虑。与其他德语国家相比,这里是一片欢乐和愉快的景象,以至于我把这块国土看作是人间的天堂。”(389-390)西木的这段感言,与混乱年代人们无比盼望和平的内心期冀不无关系。格里美尔斯豪森这样“美化”中国,不是在对中国投以敬意,而是在以对中国的理想想象寄托战乱年代人们祈望太平的内心诉求。
3 生存处境的升降沉浮
“战争之树”梦境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上又是格里美尔斯豪森抛给读者的一段预示,西木那时一会儿是宠侍, 一会儿是跟班,一会儿是命运的宠儿,一会儿又立即变成倒霉鬼的后来际遇,就在这个梦境叙事里已经被预示。西木被战争推出生活正常轨道拽入流浪命运后,小说情节在向世道野蛮和荒谬方向发展,讲述西木的生存处境被推向了变幻无常的升降沉浮。流浪已是叙事的枢纽,西木生存处境的升降沉浮又是枢纽的枢纽。流浪中西木的生存处境不时经历着变幻无常的升降沉浮,表面上看是因为西木作为一个下人的粗俗与所谓“正派人”的雅致大相径庭而遭殃,或是因为西木的天真单纯而被人当作是可以任意作弄的蠢货,背后则是在没有是非、没有法制、没有公理、没有人权的动乱年代,弱者只能是赔着笑脸接受强者欺辱,人们灵魂深处充满荒唐的写照。
被抓进军队后,西木生存处境的沉浮便又一次次地开启。战争罪恶画面描述退到后面,格里美尔斯豪森的叙事策略着意挖掘流浪汉小说叙述模式的“低品”审美,以通俗趣味的讲述让读者去体验西木生存处境的升降沉浮,达到的效果越是通俗趣味,西木生存处境的无可奈何就越是彰显。通俗趣味与无可奈何两者配合,又生成出第三层意思来。小说第一卷第27章中,西木正对一件让他感到很是好笑的事开心说笑,于无意中放了个臭屁,顿遭书记官谩骂,把他赶进猪圈,要他从此同猪睡在一起,他原来在写字间干活的好差事也由此“一下子给断送了”(85)。臭屁在这里制造了一种让人预料不到的“笑”,似乎亵渎了生活的斯文,但真正让斯文扫地的则是自称“正派人”的书记官瞬间变成了恶人。“正派人”表面上的恂恂文明和高贵优雅在这里通过臭屁引发的“笑”遭到了民间狂欢式颠覆。
那件让西木感到非常可笑的事,是一本记载官衔的名称簿落到了他的手中。在西木看来,“这本名册里所写的尽是荒谬绝伦的东西,简直是我至今从未见过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任何人是从水里冒出来的,也没有任何人是像白菜那样从地里长出来的。为什么只有至尊老八、至贵老八、至高老八、至大老八,而没有老九呢?或者说那老五、老六、老七在哪儿呢?”,“倘若高贵这个字眼本身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指极高的德行,那么为什么当这个字眼被授予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们,即公爵或伯爵时,反而会降低这些爵位的等级呢?出身高贵这个字眼完全是无稽之谈,每个男爵的母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有人问她在生她儿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话”(84)。仿佛是“傻话”连篇,实却充满了皮里阳秋、谏果回甘的滋味,邃使滑稽解构“高贵”的反讽的“笑”又在此产生。尤其是“如果有人问她在生她儿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话”这句时,把小说的“低品”形态写到了粗俗鄙下的程度,也把对贵族“高贵”的“笑”推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高度。
小说第二卷几个篇章,写西木还是司令官身边侍童,因单纯无知,对一对男女偷情之事说了真话,“她把裙子撩起来,冲着他……要拉屎”(108),便被司令官决定剥夺他的全部智力,要他去当小丑,是西木生存处境在瞬间升降沉浮的又一次写照。格里美尔斯豪森善用西木的粗话脏话,也善用流浪汉小说夸张、怪狂、畸形的表现形式,将西木被送去当小丑的情节写得乖僻和暴戾,讲述西木被人装神弄鬼和毒打折磨,为的是要将他本就显得愚钝的智力扫荡干净,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傻呵呵的痴儿。毒打折磨后西木被穿上新鲜的牛皮,戴上牛角,要他装扮成一头会说人话的牛犊供人取乐。一句看似开导西木的话道出:“如今的世界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牲畜和人之间的区别已经很小了;难道你就不愿意跟着一起干吗?”(118)或许是最早在德国小说中道出这样的信息:时代混乱,万事颠倒,人已沦为非人。西木自己也宽慰了自己一句,“我先前曾亲眼看见,有些人怎样比猪更肮脏,比狮子更凶残,比羊更淫荡,比狗更下贱,比马更放浪,比驴更粗鲁,比牛更贪饮,比狐狸更狡猾,比狼更贪婪,比猴更愚蠢,比蛇蝎更狠毒,他们却全都享受着人的饮食,只不过在外表上区别于野兽而已,而在清白方面还远远不如一头牛犊呢!”(118)逼真地道出混乱年代的世相荒谬和冷酷。
4 流浪汉小说的社会讽喻
对战乱年代洞若观火,流浪汉小说模式的社会嘲讽也充分到位。不论是对周围人的一个个幽默嘲讽,还是发生在吝啬房东与机智寄宿者段落中的暴露不健康心理的自嘲,还是西木被当作一个姑娘遭遇危险时的调情,还是与教士讨论信仰问题而把教士玩弄于股掌之中……审丑或激恶,都是对混乱时代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颓败流弊的一种指陈。先前,西木那未谙世事的纯洁禀性的瞳孔看不懂他周围人的举止。他周围的人在他这个“痴儿”面前也毫不掩饰,将他们行为上的种种轻浮、色欲、物欲、反常、颠倒统统表现出来让他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我目睹这些宾客的盛宴,其声像猪,其饮如牛,其状像驴,到最后呕吐起来就像癞皮狗。他们用圆桶般的杯子往肚子里灌下那霍赫哈埃姆、巴赫拉赫和克林根贝尔格产的名酒,这些酒也就立即在他们的头脑里施展出自己的威力。于是我看到了叫人目瞪口呆的情形。”(89)后来,西木已从一个淳朴的“傻瓜”变成了一个聪明的“傻瓜”,发现自己被人当作傻子而因此获得了“傻子的自由”,有把天然的保护伞, 可以嬉笑怒骂放言无忌,以看似傻了吧唧的荒腔走板将那些涂脂抹粉的假正经、假正派、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真正傻瓜一一卸装。“从现在起,人人都管我叫小牛。我也对每一个人报之以特殊的讽刺性的绰号……人家把我当作一个不开窍的蠢货,我则把人家视为自作聪明的傻瓜……干脆说吧:到处都是蠢人!”(117)“到处都是蠢人”的断言留给读者一个回味的观察空间,小说很多笔墨描述西木装得傻里傻气,尽情扮演他的让人取乐角色已不是闲笔。如下面对话中,西木就以他不懂时髦的“傻”讽刺了上层社会以来自法国的时尚为追逐对象的虚浮颓靡风气:
“什么?”主人表示惊讶,“难道你以为,这些夫人都是猴子吗?”我回答:“如果她们现在不是,那么她们很快就会变成猴子的。谁知道事情会怎样呢?事先也没料到,我会变成一头牛犊,可现在不是变了吗?”主人问我,何以见得,这些夫人会变成猴子。我答道:“猴子的屁股都是光光的,这些夫人也袒露着胸脯,而其他姑娘总是把胸脯遮盖着的。”“你这个劣种,”主人骂道,“你真是一头蠢牛,像你这样的家伙也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些夫人是让人欣赏她们身上值得欣赏的部位,而猴子是因为没有衣裳才赤身露体的。赶紧弥补你犯下的过错吧,否则你就要挨揍了,让狗再把你赶回到鹅圈里去,就像我们对付不知好歹的牛犊那样。听着,你究竟还懂不懂赞美一位理应受到赞美的夫人?”……“这位小姐头发黄黄的,如同小孩子的粪便;她的头路又白又直,好像用猪毛刷子在皮肤上刷过一般;当然,她头发卷得很漂亮,看起来好像空心的笛子,或者说好像两旁挂了几磅蜡烛,或者一打烤肠。啊,你看,她那鼓鼓的额头多么漂亮,多么光滑啊,难道它不比一个肥胖的屁股更好看,比一个风干多年的死人面孔更白吗?十分遗憾的是,她细嫩的皮肤被发粉弄得太脏了,如果让不知道发粉的人看到,一定会以为这位小姐得了疥癣病了,头上才有那么多的头皮屑呢!”(123-124)
符合西木“傻瓜”标签的民间语言,不雅不洁、粗鄙放诞,形成与流浪汉故事文本吻合的本色感。粗俗粗糙的“傻瓜”语言营造的粗话、怪话、脏话、滑调和油腔,张猛淋漓,上下位移,藏着玄机,意味深长,在小说中写得浩浩荡荡,酣恣笔端,足见格里美尔斯豪森在修辞方面的功力。它们一词一句褒贬相依,抑扬互换,明褒实贬,一石二鸟,读起来不疲劳,想起来有味道,尤觉新颖别致,深得流浪汉小说语言运用上活泼恣肆、不拘粗鄙的精髓,小说由此很有流浪汉小说独有的气味和魅力。诙谐机敏又毫不留情的“笑”是《痴儿西木传》的一种标志性建构。通过建构这种讽刺性的“笑”,格里美尔斯豪森在上面那段西木与他伺候的主人的对话里狠狠地讽刺了上层社会对外国摩登的趋之若鹜习气,不仅是因为在其中看到内在的俗气和本质的轻浮,更因为看到如此“崇洋媚外”、分裂而弱小的德意志帝国将有丧失其政治上的主体性或者说独立性的危险,故而忧虑而调笑。
5 德意志民族心态
格里美尔斯豪森为何要让他笔下的这部小说涵纳他自己,但同时也包含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愿望表达,小说第三卷第三至六章中出现的那个高谈阔论的尤韦,就承担着这个表达愿望。这个尤韦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要“唤醒一位德国英雄”,对这位德国英雄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期待:品质高尚,身体力行,将不惜南征北战,“用锐利的剑锋来完成一切事业;处死所有的恶人,保存并提拔那些虔诚的人们”,将使得“所有的大城市都将在他面前颤抖”,将让“任何坚不可摧的要塞都将在顷刻之间俯首帖耳地听从他的支配;最后他将支配世界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并且对海洋和陆地进行令人叹服的治理,使神和人两方面都能称心如意”(224),将攘夺王公贵族的权利,推行民主体制,“从全德国的每一座城市里挑选出两名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由他们组成议会,使各个城市之间永远和好联合;农奴制连同一切关税、税收、地租、债据、捐税在全德国都要废除;要使百姓们不再遭受苦役、哨役、战时特别税、捐款、战争,或者其他负担的痛苦”(225),还将统一宇内,征服整个世界,由他来对附属国、臣服国的帝王加冕头冠,分封土地,“然后就将像奥古斯都大帝时代那样,在全世界各族人民当中出现永恒持久的和平”(227)。在外族入侵国事日蹇,战争和战乱就在德国土地上发生的时代,格里美尔斯豪森却借善说者尤韦之口想象着一个强大起来的德国如何重塑世界秩序,这里面除了祈盼太平的乌托邦精神,大德意志民族心态和愿望也起着相当的作用(2)由于“30年战争”展露无遗地使德国人看到了长期分裂的德国之弱小和无力,激发了社会上一波又一波的爱国主义强烈愿望,致使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色彩的思想在当时非常流行。格里美尔斯豪森显然也是受此裹挟。。
6 时代混乱的反映
当然,“唤醒一位德国英雄”只是小说的一个叙事点,整体上,格里美尔斯豪森十分稳定地把握着要反映混乱时代的小说底色。小说世界里,西木被安排重新恢复他的智力,不让他再做小丑。这时,他被克罗地亚人掳走。为隐瞒过去保护自己,西木不得不时时撒谎,可谓练就一种自保的本领,能够泰然处之或玩世不恭地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方面以自由姿态营造小说的流浪汉模式艺术空间,一方面铺展编排西木在时代的动乱漩涡里身不由己,漂浮动荡。格里美尔斯豪写西木又再操小丑旧业,写他从一方军队转到另一方军队,写他当了马童,写他成了苏斯特猎兵,写他立了战功荣誉加身……。叙事文本此时呈现给读者的是西木在步入社会、宗教、政界、军界时,眼见和经历种种堕落和颓败的一个个开始。小说表现出来“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贵族特权和教会腐败的倾向”(格里美尔斯豪森,2004:译本序3), 也在这一个个开始中成为小说题旨的重要导向。
如同流浪汉小说里主人公先后在伺候过不少主人的“主仆”关系模式,西木在他漂浮动荡的生存处境中先后跟随了好几个军官和其他人,还遇到了各种身份的各色人物,包括与无赖流氓为伍。不论是作为敌人还是朋友,这些人物都为次要,他们的出现只是把小说情节导入不同的情境和场域,使得叙事更进一步触及到流浪汉小说的社会批判意涵。或以他们与西木之间形成的关系,或借西木对他们行为的观察,小说叙事里格里美尔斯豪森讲述的不是流浪汉命运的波谲云诡,而是在展开对世相肮脏、人心善恶的暴露和嘲讽窗口。
小说第三和第四卷叙事提供的一幅幅画面,场景多变、事件繁复,描述西木的个人生活和活动空间在持续变化,表现西木一路不停混迹于世,化身“魔鬼”偷窃食物,通过犯罪攫取财富,从一个底层人上升为一个春风得意的声名显赫者,授男爵头衔,获女性青睐,间涉风流,韵事不断,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被迫与军官女儿结婚,为挽救财产不得不去科隆,命运将他带到巴黎,以婉转歌喉和英俊面孔一举成名,领略上层社会放荡,人生艳福达到高潮,又命运多蹇,及至返回途中,得了天花,脸面变丑,钱也耗尽,再度穷困潦倒,沦为兵痞、骗子、冒充医生的人和强盗团伙。叙事将西木的这些故事一个个连缀,持续给读者提供打量那个时代社会的新的视点。一个原来淳朴单纯、天真未凿的“痴儿”,现在变得虚荣、堕落、罪孽、无耻、无道德和善于弄虚作假,既可唾可鄙,也复可悲可怜。格里美尔斯豪森以流浪汉小说同一审美模式的跳跃性叙事片段将这个如今变得“毫不弃恶从善,而是越变越坏了”(340)的西木置于读者观察之下,让读者看到乱世生活对西木来说既是一所使他成长的学堂,也是一个让他“近墨者黑”的染缸。西木越是为非作歹,就越是让读者感到群魔乱舞的混乱社会和野蛮世道改变了他。社会揭示虽然构成了《痴儿西木传》一个精神标识,但应当说它对社会伸出的褒贬时弊触角多少有些失于浅尝辄止,这又应当说流浪汉小说首先要的就是那份通俗性意识膨胀。
7 并非表现精神的救赎
虽然结交了对宗教信仰虔诚的海尔茨布鲁德,但是西木也只不过是出于去一个新地方看看的心理跟着海尔茨布鲁德去瑞士隐居,实际上他对自己放纵的生活尚无真正的省思。他也只是表面上皈依了天主教,内心里却并未放下世俗,也难耐身体寂寞。海尔茨布鲁德去世,西木便再次结婚,有了儿子,岂料妻子实际并不爱他,婚姻成了莫大的欺骗。与养父母重逢,西木得知自己本是贵族家庭出身,当年在森林里遇到的那个隐士原来就是他的生父。与魔鬼湖王子交谈,生活上已摒弃了信仰的西木听到了对人生在世的一种认识:世界和人生是上帝对人的考验,是上帝对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试金石。西木似乎又有皈依宗教的念头,但外国军队来了,西木再次当兵,流落到了莫斯科,被鞑靼人俘虏,流浪至朝鲜、日本、东印度、埃及等地。叙事只是三言两语简单讲述了西木的这些颠沛,更多是空间变换在构成故事。回到家乡黑森林,西木对这个“对于你无可信任,也无所期望”(469)的世界发出一番诅咒,决意重新去过隐居者生活。
小说第五卷有几章,远离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经验,进入神话色彩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想象。叙事讲述西木的魔鬼湖及水下旅行,把一些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包罗其中,同时也使得一些“修身文学”(Erbauungsliteratur)(3)“修身文学”是一种宗教文学,广义指所有的宗教修身读物,狭义指旨在增强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对信仰虔诚度的作品。参见张威廉主编:《德语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767页。气息在段落中弥漫。格里美尔斯豪森这样写小说的结尾部分,既是对那个时代巴洛克小说中迷信、巫术、鬼怪、魔幻这类故事的美学视角再现,也与那个时候的人们面对乱世社会需要灵魂安置的需求相适应。小说开头处留下的情节断线,在西木重逢养父母时被回照,形成完整的故事链条。小说开头写的是西木被从童年时代的无忧乐园生生拽出,小说第五卷第23章写的是西木省思自己,为他在小说最后的第24章里决定回归隐士生活作了铺垫,全书首尾相应的整体结构得到完成。
我观察人生和时机,不是为了我灵魂的拯救,而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得到享受。我曾经多次拿自己的生命进行冒险,却从未热心于使我这一生改邪从善,好使我死后能心安理得地进入天堂。我只看到眼前的一切和我短暂的利益,却从未想到未来,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面对上帝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交代!(468)
西木“由浊变清”,在忏悔以前的生活,先前的一个罪孽者在用上帝的灯火照破晦暗而精神升华,有“过来人现身说法”的启示意味。不过,流浪汉小说并不一定要表现精神的救赎。西木的语言虽然在直接传递基督教的救世思想,但这有可能只是小说对那个时代宗教信仰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态的一个简单应和,并不一定是西木背后的小说作者格里美尔斯豪森立足于他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困境的终极思考。(4)格里美尔斯豪森后来还写了一卷《痴儿西木传》“续集”,在“续集”中写了主人公依据所经历的生活沧桑而拒绝皈依宗教。小说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记载了“30年战争”的罪行、社会的病态和人们经受的苦难(5)到了今天,德国文学对“30年战争”面貌和状况的描写,也大都是根据格里美尔斯豪森小说中的描述。,在于格里美尔斯豪森将他对失衡乱世的见多识广和感慨诸多注入西木的流浪汉生活,在于它同时高蹈流浪汉小说的通俗艺术,把那个时代的战争和社会、人世和人生、兵燹和创残,混乱和欺凌、恶习和愚顽、乌烟和瘴气、乖杵和反常、落后和失路、皈依和危机……写得过目难忘,写得充满奇特的幽默和粗俗的生气,写得极富丑恶与俏皮同存的特色。德国学者认定它是德国文学第一部近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中文译者李淑老师评价它是17世纪德国文学的巅峰,无任何其他作品堪与轩轾,是“德国巴洛克文学的丰碑”,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