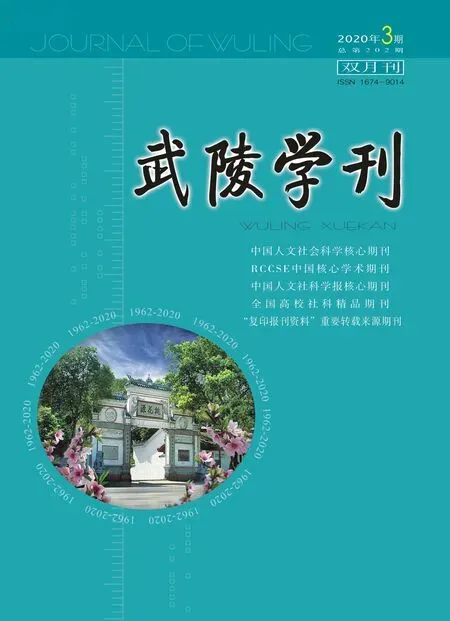“左联”领导文艺发展的局限性之原因探析
2020-01-02付甜甜
付甜甜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09)
“左联”的成立是中共正式在实践上领导文艺战线、与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在中国发展的组织方式来看,“左联”一改社团时期①文学社团各自为战的局面,吸纳了一大批党内外深谙文艺的作家,并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左翼文艺工作者在国民政府的封锁中接连创办刊物、坚持译介国外理论成果、参与各种文艺论争,为粉碎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初步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左联”在开展文艺活动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组织成员流动性大、文艺活动开展困难重重,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严重,组织内部沟通不畅以及内部思想分歧、冲突频发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最终导致了“左联”后期“两个口号”的论争及“左联”的解散。而探究造成“左联”文艺局限性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历史,也对我们当下开展文艺运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民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共的军事围剿
“左联”是中共主导下成立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群众文艺组织。“左联”之“左”,本身就是政治立场的划分,即激进的、革命的。因此,这一激进的、革命的、与国民政府对抗的组织存在于国统区的事实,决定了“左联”与国民政府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从而使“左联”各种活动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来自国民政府的文化统治,另一方面来自国民政府对“左联”的实际领导者——中共的政治高压与军事围剿。前者是对“左联”文艺活动以及文艺工作者的直接破坏与迫害;后者则间接影响“左联”的文艺活动。
从文化统治方面来看。1928年以来,南京政府就开始大力宣传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左联”成立后,有关文化出版业的文件更是密集出台:1930年12月的《出版法》、1931年10月的《出版实施细则》、1932年11月的《宣传品审查标准》、1934年6月的《图书审查办法》、1935年修正通过的《出版法》等。审查的内容从规定不得破坏国民党或三民主义政策、不得颠覆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到明文规定宣传共产主义者为反动、一律禁止批评国民党、对国民党不满等。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制定了《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开列出了564种查禁文艺书籍,同年8月制定了《取缔反动社会科学书刊一览》,“又开列社科书刊676种”[1]。在这种情况下,茅盾曾回忆说,到1931年春,“左联”的阵容就“已经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2]。此外,国民党还用暴力手段破坏左翼文艺团体,甚至对倾向左翼的文化界人士不惜采用暗杀、拘捕、绑架等手段②。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3]。为了与“无产阶级文学”相抗衡,国民政府还积极培育自己的文学力量,相继提出三民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并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它标志着政党意识形态将从此有意识、有目的地全面介入到文学领域,从而使文学演变成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另一片战场”[4]。
国民政府对中共的军事围剿也间接影响了“左联”的正常运转。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革命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震动。从1930年到1934年,国民党就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军事“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了漫漫长征。毛泽东曾说,这种白色恐怖,使得“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5]。而在国民党统治区,1931年后,由于国民党特务情报机关羽翼丰满,上海的中共机关不断遭到破坏③。“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属机构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6]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残酷镇压、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共产党上海领导机关,要想始终和“左联”的主要领导成员保持联系并就文艺问题从容地交换意见,是极为困难的:
第一,从政策层面看,由于整个“左联”期间,中共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无暇顾及到文艺战线,因而中共中央几乎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左联”文艺发展的具体指导方针与政策。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中央高层缺失了对文艺工作的具体指导,“左联”文艺工作的开展很大部分是靠“左联”党团及其上属的“文总”、“文委”通过对中央政治文件的解读来进行。这就难免出现因受到政治层面上“左”的影响,而使文艺实践与上层文艺工作要求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说,从组织的活动方式上来,“左联”的成立,是中共由过去秘密开展文艺宣传到借助“左联”这一群众组织,公开、合法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所采取的重要文艺策略。但由于受到党内外“左”的影响,“左联”前期创办的刊物政治色彩浓厚,很多刊物一经出版旋即被封,很多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又如,中共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左联”成立的初衷之一便是在最广的范围内团结文艺界人士,然而这一点在具体落实上却存在很大的问题。萧三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授意下所写的解散“左联”的来信中,便提到“左联”的这种状况,即“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7],但实际上门却关得很紧,很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在共同战线之外。再加上那时在上海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团成员都是一些年轻的党员,“都是一些不仅很少政治斗争的经验,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也都非常薄弱和幼稚的人”[8]31,这就导致“左联”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中与党中央的要求是存在距离的。
第二,从时间层面来看,位于上海的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艺团体甚至一度与党组织失联。“到了1935年春天,田汉、阳翰笙等同志被捕了。其他‘文总’负责同志也一时找不着,‘左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9]。直到1935年10月,周扬才重新组织“文委”,恢复“左联”的正常运转。林淡秋回忆说,他在1935年冬由“社联”转入“左联”时,“因领导各联盟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左联’内部又不团结,处境非常困难,组织机构很不健全……”[10]。而这既影响了中共对“左联”的指导,也使得“左联”在内部沟通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制约了“左联”文艺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左联”对外公布的组织架构是常委集体领导,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左联”的高压,“左联”成员行动困难,无法召开常规会议,因此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左联”党团实际在“左联”中起到了核心领导的作用。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个体,虽然只是在“左联”中担任常委一职,却因其在文艺上的造诣与影响力,而被视为“左联”的盟主、旗手及统帅。这就造成“左联”具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个是党团,一个是鲁迅。党团核心地位的确认,是组织赋予的,是有党、有组织、有制度保证的,是有形的。而鲁迅这一核心地位,是无形的,没有制度上的保证,主要靠自身的影响力去实现,但又极为重要。冯雪峰就曾多次由衷地褒扬鲁迅对“左联”的意义与贡献,“名誉、地位及不胫而走的辉煌文章”[8]31,使得鲁迅吸引了许多左翼青年,使“左联”能够冲破国民党封锁。“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只要鲁迅先生不退出‘左联’,不放弃领导,‘左联’的组织和它的活动与斗争就能够坚持。”[8]33而在一个组织内出现两个“核心”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平衡与沟通这两个核心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左联”在组织结构上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对此,“左联”在政策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按照“左联”在筹备期就有的惯例,解决方法是在鲁迅与党团之间指派一个联络人。“左联”成立之前以及“左联”前期,鲁迅与党团之间的联络人主要由冯雪峰担任。但由于“联络人”这一角色并不在“左联”正式的组织结构内,对于如何指派“联络人”、指派什么样的“联络人”、“联络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这些都不甚明确。“左联”前期,由于冯雪峰的积极有效沟通、瞿秋白对鲁迅的支持以及两人的密切协作,“左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内部也有摩擦,但是由于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而在整体上保持了“左联”的团结。
然而,继1933年底冯雪峰与瞿秋白相继奔赴苏区后,“联络人”在党团与鲁迅之间的沟通上便出现了一些问题。1933年12月至1934年10月,胡风成为“左联”党团与鲁迅之间的“联络人”。胡风与鲁迅私人关系很好,但从其作为“联络人”的身份来看,却并不能说是合格。因为“联络人”作为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难免会“根据‘听者’的不同或者根据‘信息发出者’的意思对信息进行增加或者删减”[11],这便造成了传播中的问题甚至矛盾。事实上,自从1934年开始,以胡风“中山馆”④事件为契机,鲁迅与部分“左联”领导人关系越来越差。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风“性格独立不羁,不甘居于人后,又心直口快,在日常与人交往时常常处理不好与人的关系。在‘左联’工作时,除了鲁迅的意见,别人无论是谁,他都敢于争论,对于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观点是相当淡薄的”[12]。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核心之间很难做到有效沟通。
徐懋庸一度作为鲁迅与党团之间的“联络人”,但是他作为“联络人”显然也是不够称职的。一方面,他缺少冯雪峰那样的团结艺术,另一方面他在“左联”中的位置也决定了他无法像瞿秋白与冯雪峰一样及时获取准确、全面的党的相关政策、信息,再加上传播过程中信息的过滤,这就使得他与鲁迅的之间的沟通质量不高。徐懋庸曾在“两个口号”论争时期写给鲁迅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提到,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13]。细究起来,这种“不了解”恰恰反映了徐懋庸作为“联络人”的失职。无法及时得到准确的信息,鲁迅在某些事情的判断上更多是基于自身过往的经验。可以说,徐懋庸在鲁迅与“左联”党团之间,只做到了“沟”,但并没有真正的“通”。鲁迅甚至并不承认徐懋庸作为“联络人”的身份。
除了因“联络人”问题导致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外,两个核心之间的交往方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左联”后期⑤主要是由周扬代表党组织领导“左联”工作。由于“左联”人士经常遭到国民政府的迫害、暗杀,周扬作为当时“左联”的实际领导,不宜经常外出,具体的工作主要由徐懋庸、任白戈等人与鲁迅联系。正是这种深居简出,造成了这两个核心之间缺少面对面的沟通。这与冯雪峰、瞿秋白时的交往模式完全不同。冯雪峰、鲁迅、瞿秋白之间由于密切交往而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是在正式组织⑥中产生的,“由一定数量的个人(通常规模比较小)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团体”[14]176。在工作中,经常接触的人,有可能基于相互的同情、钦佩、兴趣等,而在他们的正式关系之外形成某些非正式的行为模式。非正式群体既可以成为“组织产生的真实基础,并且维持着正式关系”[15],也有可能对正式组织的发展构成威胁。由鲁迅、冯雪峰以及瞿秋白所组成的非正式群体,在内部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冯雪峰与瞿秋白尊重与倚靠鲁迅,在鲁迅与党团之间,形成了很好的沟通。不仅党的政策、方针能够及时地被鲁迅了解,而且冯雪峰与瞿秋白作为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一心为民的人格魅力也深深感染着鲁迅。瞿秋白在险恶的环境中,三次避难于鲁迅家,这种患难之情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使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御敌,带领“左联”成员共同前进。冯雪峰对鲁迅的思想和行动则有着直接的影响。他曾住鲁迅隔壁,与鲁迅每天见面交流。许广平曾回忆冯雪峰和鲁迅在一起的情形:“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16]
而心理学研究表明,“面对面直接交往的时间与人际关系融洽程度成正比例关系。长时间的面对面交往使成员之间容易形成相似的价值系统,使群体成员有可能在超出群体本身目标之外的广泛事务上形成共同的情感。共同价值系统和共同情感又是群体凝聚力的主要源泉。交往时间短,则成员之间的关系就会冷漠、生疏、有隔阂”[14]162。瞿秋白作为当时“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冯雪峰作为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联络人”,他们与鲁迅之间的沟通是面对面的,是互动的,并在互动中最终达成一致。而周扬却一直处于“隐身”的状态,虽然这种“深居简出”也是身不由己。但客观上确实会造成很多的误解。因此才会出现“左联”后期,鲁迅称周扬为“工头”、“元帅”、“奴隶总管”。1936 年4月,冯雪峰从瓦窑堡回上海,鲁迅与雪峰握手后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8]33,可见双方隔阂之深。
三、“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虽然“左联”是中共主导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并非政党组织,其基本定位依然是群众组织、左翼文学统一战线。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报导)》中,有关于“左联”主要工作方针的描述。这些论述既涵盖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又涵盖了著作出版、学习外国文学以及组织内部的发展。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左联”成立的基础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艺术剧社以及左翼的“南国社”,另有小部分没有任何社团背景的盟员。从这一视角来看,“左联”与之前的文学社团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社团基本上都是同人社团,是作家个体间的联合,社团成员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趣味基本一致,或者说同人社团成立本身就是因为同人之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学趣味。而“左联”内既有作家个体间的联合也有社团间的联合。它以政治立场的号召为核心,兼顾文学立场,是政治立场基本相同但文艺思想不尽相同的群体组合。这是“左联”作为文学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的最大特点。
这一特点使“左联”的文艺活动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左联”依然保有并延续传统文学社团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当“左联”作为一个文学组织整体存在时,他们能暂时搁置分歧、一致对外,如与右翼的新月派,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以及与自由人的论争等;另一方面,“左联”以文学社团为基本单位的联合方式也使“左联”从成立开始,内部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和思想的碰撞,小论争不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隔阂和内耗,不利于文艺活动的开展。“左联”如鲁迅所说,“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17]。
首先,“革命文学”论争所造成的对左翼文坛的撕裂,影响深远。虽然冯乃超一再强调“左联”的成立“并非某一个或几个团体所能左右”,“左联”也并非“只是几个小团体的组合”[18],但不可否认,人事关系的亲近,使他们对原来所为之并肩战斗的社团有天然的归属感。“左联”成立之前文艺界曾发生过长达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论争中鲁迅遭到了创造社、太阳社的联合“围剿”。创造社和太阳社在论战中“采取强词夺理的策略,不是从学理上加以批判和辩论,而主要是对被批判者进行理论宣判,甚至有时包含着人身攻击……”[19]。而这种大批判造成的左翼内部的撕裂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左联”成立以后,论争各方在“集团的文化形式”作用下,集中精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学和理论,各种情绪暂时得到压抑。但此前积累起来的鲁迅对于革命文学内部某些人与现象的反感其实一直都没有冰释与消除。钱杏邨就说过,“我们对鲁迅检讨过,承认在论争中不应该用那种态度对待他,鲁迅也说了些团结的话。谈话时我们对鲁迅是尊重的,但思想上双方并未彻底解决问题”[20]。
其次,“左联”作为社团的联合体,虽然各社团在政治立场上都是“左”的、革命的,但是他们在文艺思想上是有分歧的。与此同时,社团时期的文学论争基本上都发生在社团之间,同人社团内部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但是基本上不会公开论争,更不会公开激烈论争,多控制在社团内部范围。“左联”则不同。“左联”中存在着“非左翼”甚至“反左翼”的文学创作甚至理论批评,思想之间既有碰撞也有制约。这是历史的事实。“第三种人”论战的发起人苏汶,以及之后支持苏汶的杨邨人、韩侍桁、杜衡等,本身是“左联”的盟员,但是在鲁迅、瞿秋白批判胡秋原“文艺自由论”之时,他们表面上宣称自己是除了以胡秋原为代表的“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翼文人之外的“第三种人”,但实际上却站在了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进行攻击。1935年春,杜衡、杨邨人、韩侍桁等人还组织了星火社,创办了“第三种人”的同人刊物《星火》,继续攻击左翼文坛和鲁迅。可见,一部分人与“左联”渐行渐远,并在无声无息中退出了“左联”。虽然对于一个文学团体来说,因文学观点的不同,组织成员分道扬镳,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鲜见,但还是在客观上削弱了“左联”的力量。
“左联”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冲突为《汉奸的供状》事件。1932年,“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上,发表署名“芸生”的文章《汉奸的供状》,以辱骂的手法攻击胡秋原,出现严重的极左偏向。冯雪峰作为当时中共文委的书记,认为这是“违背党的策略的”[21]。鲁迅也认为这篇文章不应该拿胡秋原的姓氏开玩笑,也不应该在无产者的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因此在冯雪峰的授意下,鲁迅撰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告诫左翼作家不要因袭中国历来文坛上那种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的手法。战斗的作者应该重于论争而止于嘲笑与热骂。这篇文章言辞恳切、有理有据,对当时流行的“左”倾幼稚病是有力的针砭,对左翼文学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当时几个自认为受到批评的“左联”内的年轻人却联名发表公开信反驳鲁迅,并给鲁迅按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虽然瞿秋白相继撰文《慈善家的妈妈》以及《鬼脸的辩护》支持鲁迅,但同道中人向鲁迅射来的冷箭还是对鲁迅造成很大的伤害。
作为一种新型的文艺组织,“左联”在中共领导文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共领导文艺运动从社团时期到延安时期的过渡。它在中共的主导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文艺宣传活动。但是“左联”与生俱来的政治色彩及其所处的险恶的外在环境,“左联”内部的沟通机制以及“左联”作为新型文艺组织所呈现出来的薄弱的组织基础都对“左联”的正常运转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因素如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等影响到了延安早期文艺。而这些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得到部分解决。“左联”作为过渡时期的文艺组织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功不可没。
注 释:
①社团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主要依托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进行发展传播的时期。参见泓峻著《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载于《文史哲》2019年第2期。
②1931年2月,国民政府逮捕了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并把他们秘密枪杀;1933年3月,艾芜被捕;1933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因拒捕而牺牲,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1933年7月,英文版《中国论坛》上公布的《钩命单》上,鲁迅、茅盾赫然在列,这使鲁迅多次搬家并到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处避难。1935年2月,田汉、“文委”书记阳翰笙、“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等三十多人同时被捕。
③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被迫转移撤离(王明于10月去莫斯科,周恩来12月到达瑞金),上海成立由博古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使得国统区的工作更加困难而难以立足,因此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根据地;此后,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但是该中央局依然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因此,从1934年开始,它遭到连续的破坏。1935年7月后,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参见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1934年,胡风本来在孙科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当编译,后来韩侍桁故意在教育馆里公开了胡风是“左联”成员这一身份,说他又拿国民党的钱,又拿共产党的钱,胡风被迫辞去了教育馆的工作。本次事件中,周扬等人怀疑胡风的身份,而鲁迅则支持胡风。
⑤主要指1933年下半年以后,周扬继任“左联”党团书记,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之一。1933年底,瞿秋白和冯雪峰相继离开上海,周扬等人与鲁迅的关系开始恶化。
⑥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正式组织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参见于显洋著《组织社会学》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