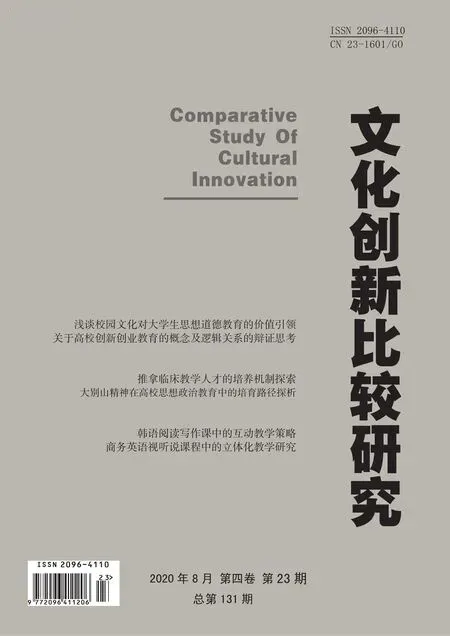现代设计中的功能异化及其发展
2020-01-01邢川
邢川
(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00)
在艺术尚未使我们养成这种作风和教会我们说一种雕琢的语言以前,我们的风俗虽很粗犷,但确是很自然的。言谈举止的差别,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出性格上的差别。 人的天性并不是过去比现在更好;但是,人们只有在互相都能很容易看透对方的内心时,才会感到安全。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好处了,而在过去,它却使人们少做了许多坏事。
——让-雅克·卢梭
1 设计中功能异化的表现
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于1938—1958年间任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 (IIT)建筑系主任一职,在此期间曾参与设计与规划诸多项目,如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校园规划(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以及芝加哥大会堂(Convention Hall)等,但这些作品相较1958年建成的纽约西格拉姆大厦,不论从投入来看还是历史地位均逊色许多。西格拉姆大厦,作为密斯终生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作为现代建筑的丰碑,其设计上的成功不仅将其本人推向了荣誉的另一高峰,也开启了其在美国事业的新的篇章。这座矗立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商业中心且耗资巨大的现代主义雕塑,自建成始便带有极致属性加持,由钢筋混凝土支撑呈现几何对称的形态的建筑整体; 内部开放式结构与通体琥珀色玻璃幕墙的应用,配合强迫症般的三段式的窗帘,种种这些淋漓演绎了设计师“少即是多”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但这在一些批评家眼中却是非法的禁锢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密斯为追求完美而失去的理性正是现代主义所主张的,这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以至于其设计动机是如此可疑,批评家汤姆·沃尔夫曾经对此发表评论:“他的思想就是把普通工人住宅与毫无装饰的严酷和优雅细致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最少主义”[1]。如果“少即是多”的出发点是功能而非形式的话,那么由此将现代主义(或是国际主义)精神与功能主义和非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被调侃为一种“讽刺的关联”也是无可厚非的。
詹克思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中将密斯的现代建筑风格称作最单一的建筑艺术形式或是形式的高度贫困化:“它只应用有数的几种材料,简单的直角几何图形。从特征上讲,这一简略的形式已证明似乎是有理性的(同时是不经济的),是通用的(同时只满足极少的功能)……在密斯和他的弟子们手中这一贫困化的体系已变成迷信,这种迷信压倒了其他所有关系。 ”[2]虽然诸多评论家均借此对现代主义混淆和困扰公众视听的阴谋口诛笔伐并大做文章,但实际上问题并非仅出现在现代主义那里,从西格拉姆大厦的个案来看,其优美而足以自豪的外表实则被那些重复抄袭的建筑损害了,那些布满世界各地的同质化的建筑具有迷惑性的样貌却不具有实际功能或具有“迷惑性”的功能,如西格拉姆大厦外部贴有定制的宽缘铜梁以“表现”藏在混凝土中的真实构造;以及广为诟病的三段式窗帘等。 (这并非没有先例,虽然密斯不仅一次地以其行动践行其“God is in the details”的理念,但同样的抱怨却出自“如同被展览的动物般”的范斯沃斯女士)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步入“后工业社会”的现代主义在设计领域其内在功能已被其符号性所超越,曾在欧洲忧国忧民的现代主义设计已被美国的富裕所腐化,并从此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 这直接导致人们对于现代主义那崇高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表示怀疑,它那以牺牲形式多样性为代价的单调风格也因此受到挑战。 象征性替换掉了之前的属性,使设计中广义的气氛价值成为众相追捧的目标,所谓的功能,也异化为了由资本编织的美好幻象。 如果说这种符号价值开始是被动的由时间与空间所赋予物自身的话,那么进入后现代以来的设计便是主动的迎合了这种符号物的建构,并立足于此进而渗透至全部设计体系。 进而,我们也由设计物的符号性步入了立足于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异化的功能性问题。
2 功能异化的演变
鲍德里亚通过对古物(或古董)这一典型的非功能物的分析,认为人们对物品精神需求(符号价值),已经超越了对其自身具备的实际功能,符号的加入使得物品成了符号物,从而主导了物的存在方式。在上述情况下,“纯粹的对象[物],被剥除了功能,或是从它的用途中被抽象出来,则完全只拥有主观上的身份:它变成了收藏品。”[3]这种情况就像波普艺术在创作中广泛运用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当代现成品以及那些符号堆叠的集合艺术,这种符号的集合随着传播媒介而快速发展,象征性的设计通过大众传媒确立了消费社会对于人的统治。 这种设计象征性的异化并非是进入后工业社会才产生的,而是全程隐匿于现代设计发展之中,虽然其自身蔽而不显,但却借由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无处不在。 这种象征性在现代设计的发展中曾经化身为装饰、 功能元件,直至现当代逐渐沦为纯粹的符号。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性是在平庸琐碎的日复一日中被异化的生活,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要批判这种日常性[4]。消费社会的发展与批量化的工业复制加速着设计异化的进程,而资本的推波助澜也使得符号化的商品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并刺激着消费者为其买单。在各种符号物争相成为目光的焦点、消费的明星时,物的使用价值自然也被人们严重忽略了。 马歇·布劳耶(Marcel Breuer)早在包豪斯期间便已成功地设计出多件划时代的家具作品,虽然其提出的功能性主张得到了建筑界同仁的支持,而亲自设计的“植入式厨房”如今也成为整体厨房的前身。但实际上在其诸多设计中,绝大多数产品从未在一个合理的价位进行批量生产。 这种境况似乎同样出现在勒·柯布西耶身上,其与夏洛特·佩里安(Charlotte Perriand)和皮埃尔·詹内特(Pierre Jeanneret)约于20 世纪20年代共同设计的钢管家具,在由Thonet代工生产后同样奢侈昂贵,后期经由Cassina 生产至今的LC 系列也俨然成为家具设计的业界翘楚,吸引着无数的中产阶级为其不菲的价格买单。
鲍德里亚指出,包豪斯以被他称为“物”的状态,宣告了一场“符号的”革命。 这场革命在意义上等同于之前的工业革命。物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制造、交换和分配(一种产品),现在,它自动被生产为了一种“符号”。所谓符号,鲍德里亚的意思并不是一种图标或再现的形象,而是指某些物体能够“意指”社会地位、规范性权力,或者文化身份[5]。 如家具品牌Knoll(诺尔)那种对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商业化运作,也可视作功能走向异化的旁证,现代设计史学者维基耐利在他的专著《诺尔的设计》一书中写道:“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讲,包豪斯的胜利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完成的”[6]。正是在诺尔那里,现代设计的功能主义被描述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它描绘了一幅成功的中产阶级景观,标榜了一种消费主义价值观。正如当代对设计趋之若鹜的现象,设计的符号被视作行之有效的卖点,仿佛镀金一般吸引着消费者为之买单,设计产品与设计者也成为在商品社会中的宠儿,沉溺于流行文化的先行者和文化明星,由此而来的功能异化也就不可避免。 可以说现代主义的先驱虽然有着正确的政治理想,但是由于其失败的生产结构,导致虽然设计者完成了大众家具的创造,但却只为了精英阶层所享用,所谓“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也从未达成。随着进入后工业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从而使商品具备了更强大的象征性。
由进入后现代而引发的设计革命也多采用的诸多符号性(或象征性)手法,如雕塑一般的沙发、艺术造型的座椅等,诸如此类十分有限的使用功能与反之倍增的符号价值形成强烈对比,使物成为营造氛围的存在。这种介于古物与功能物之间的,艺术与设计之间的新门类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这场不断持续的无意义发明的实验中,符号现代性不断推动着生产出诸如当下所谓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m),中古风格(Mid-Century Modern)等概念。那些有着先锋精神的现代主义先驱此刻摇身一变成为了消费社会的明星,接受着中产阶级的膜拜。 对此,面对异化的商品市场以及虚无主义双重威胁的设计者,对于以无意义的发明,无理性的复杂化,伪功能性,空虚的功能主义等为具体表现的设计异化,可以说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3 异化的设计者
以“功能失调”[7]为表现的异化状态的加剧不仅意味着物的象征的投射对自身使用价值的超越,并在人逐渐失去对真实判断力的同时,预示着人也逐渐成为物投射符号的载体,物在超越其功能的条件下成为凌驾于人的存在。 各种因符号的生产导致的设计异化,价值与功能的非正常分离以及设计者与商品之间的异化的关系,不断引发着我们对于设计本质的思考,以及提醒着我们重新确立设计责任,即设计者与设计物之间,设计者与设计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的重要性。
我们一方面不能够否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以及客观世界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和经验来源; 另一方面我们的知识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之上这一点也不容置疑; 既然设计者并非具有先天的设计实践能力,而作为经验者,其自身对于经验对象的认识便构成了其设计的重要前提,这造成其自身认识的先天局限性。除此之外,设计者所运用的符号学的思维方式也难脱其咎,对当代设计来说,普遍运用的符号学思维方式,以经验到的物的符号性为根据进行的设计实践,以及经由部分符号、指号和信号构成的一系列符号系统也同样有其弊病,当人们在通过各种中介和象征意谓与“他人”和“他物”建立多样的关系时,对于中介符号的真实性和其意义的不假思索的接受便成为一种对于强权政治的默许。 相较于设计者自身所客观经验之物更加具有虚无主义倾向。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缸中之脑”的假设,对这种方法论的机械应用,导致了设计相当程度的同质化,并为功能异化提供了条件,语义的可复制性使得凌驾于当代人的符号物快速扩散至所有领域,使得设计行为已然变成对于那些“虚幻又切实的东西”的批量复制。
当1981年瑞典设计师乔纳斯·博赫林(Jonas Bohlin)以混凝土与铁为材料制作了一把椅子时,这并不表示其自身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或是审美价值,事实上恰恰相反,由两块混凝土制作的板面构成靠背和椅面,笨重的材质以及受刑般地坐感都意味着其实用价值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混合在混凝土之中的并非是这些特征,而是一种先锋精神和一种开拓性的尝试,此后在瑞典掀起的创造性浪潮也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于责任的划分以及对于真正创造的划界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理所应当的为那些先锋们脱帽致敬,而并不是那些随波逐流的人和伪装者。我们面对着设计增值的时代,诚实可以视作一种符号而非美德,设计本身作为目的而非手段,当所有产品统一口径地向消费者讲述着设计的故事的时候,同样也是先锋精神消失殆尽之时。
碍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超验的知识这种符号性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否如同鲍德里亚预测那样带来灾难性后果。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符号生产的速度已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发展与演变如今已实在地脱离了控制,景观社会的理论虽然将研究引向了社会学的范畴,但事实上留给设计者的问题依旧存在,这依旧是关于认识的问题,真实的问题以及存在的问题。虽然设计物让自己看上去微不足道,清楚明白,实际上却又如此复杂,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诡谲。 究其原因,是缺乏被物所奴役之下的批判,当我们越是处于这种异化当中,越是需要对其自身进行反思、重新认识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