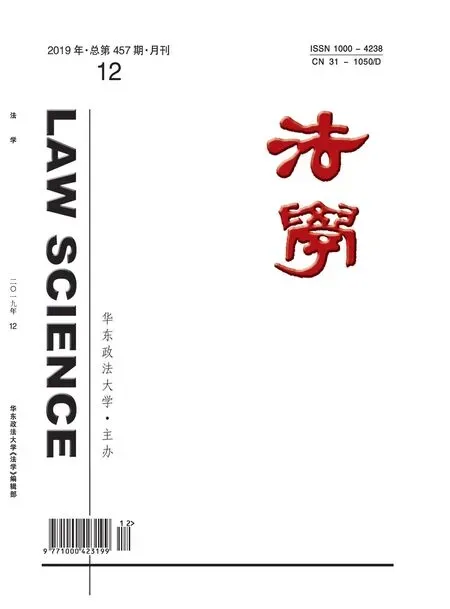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的实证研究
2019-12-31叶小琴
●叶小琴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回顾
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研究集中于“网络容留吸毒”与明星容留他人吸毒案件的讨论。2011年10月公安部破获“8·31”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视频交友平台进行的特大吸贩毒案件,大量涉案人员在网站设立的虚拟“十人房”“百人房”内表演吸毒行为并交流吸毒感受。对这些“房主”能否适用容留他人吸毒罪的讨论中,产生了容留场所是否必须为物理空间的讨论。学者们普遍持否定观点,并提出立法修改建议。一种观点认为“房主”从开设“房间”时起即具有组织类犯罪特征,建议增设“组织吸毒罪”;〔1〕参见刘仁文、刘瑞平:《“网络吸毒”行为的刑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2期。另一种建议将本罪改为“聚众吸毒罪”,处罚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2〕参见陈恳:《以聚众吸毒罪取代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立法思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比例原则与目的解释的限制性规则,主张对开设网络“烟馆”聚众吸毒行为用道德或行政手段调整。〔3〕参见莫洪宪、周天泓:《论开设网络“烟馆”聚众吸毒行为的定性》,《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6期。也有检察官针对物理空间的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建议增设单位犯罪,认为现在多数娱乐场所容留他人吸毒通常经过单位的集体决定,但被处罚的只是具体执行者。〔4〕参见张宇:《认定容留他人吸毒罪应向三方面扩展》,《检察日报》2011年10月17 日第3版 。此后2014年开始,房祖名等明星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件的连续曝光,引发了对限制容留他人吸毒罪处罚范围的关注。有学者建议该罪主观方面改为有明显“恶意”或以牟利为目的,客观方面则以主动提供场所或开设专门吸毒场所,造成严重后果为限。〔5〕参见莫关耀、杜敏菊:《容留他人吸毒罪的重构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6期。还有观点主张通过“以营利为目的”提高的入罪门槛。〔6〕参见黄瑛琦、张洪成:《容留他人吸毒罪主观限缩之合理性研究》,《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总之,对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研究呈现阶段性、集中性及表层化特点。多数研究基于单一司法现象从扩张或限制角度提出立法与司法建议,对此如何取舍应进行实证研究。
面对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多年持续爆发式增长的犯罪趋势,应当对该罪定罪规则进行实证研究。中国裁判文书网一审刑事判决书数据显示,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量每年持续增长且总量已达147 058件,跃居全部罪名第8位,与位居第7位的寻衅滋事罪159 264件仅相差12 206件。一定时空范围内某类刑事案件增长率显著超过人口时意味着犯罪率的增长,但犯罪率的大幅度增长是否一定解读为现实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数量的猛增?美国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提出对官方犯罪率的两种应用路径,一种认为犯罪率是人群中真实犯罪现象的测量指标,另一种则将犯罪率视为社会控制机制的指标,由此聚焦于调查研究真实的社会控制机制。〔7〕See Donald J.Black, Production of Crime R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5,No.4.(Aug.,1970), p.733.在我国,面对某类刑事案件的增长态势,必须考虑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扩大解释定罪规则的可能性,容留他人吸毒罪也不例外。例如刑事法官的代表性观点认为,“面对毒品犯罪特别是容留他人吸毒罪如此大幅增长的严峻形势,为有效治理毒品犯罪,有必要加大对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打击力度,对容留他人吸毒罪中‘容留’的含义作扩大解释”。〔8〕杨子良:《如何理解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容留”》,《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3日第6版。因此,不能将容留他人吸毒罪刑事案件的增长片面理解为毒品犯罪形势的严峻。由此应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以下问题: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是否存在扩大解释的趋势?如果存在前述趋势,这种趋势是否与容留他人罪刑事案件的增长相关?定罪规则厘定的处罚范围与该罪规范目的是否一致?
从刑事政策角度对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进行实证研究应综合三组概念作为理论基础。第一是司法的刑事政策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也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指在刑法中贯彻刑事政策的内容,从而使刑法成为落实与实现刑事政策的工具,可以区分为立法和司法的刑事政策化,后者指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刑事政策的精神,使刑事政策成为司法活动的指针。〔9〕参见陈兴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二种是司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犯罪化指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对象,非犯罪化则与之相反;犯罪化包括立法上的犯罪化和法律适用解释上的犯罪化,后者指在解释适用刑罚法规之际将本刑罚法规适用于迄今为止没有被作为犯罪予以取缔的事实。〔10〕参见〔日〕大谷实:《刑事政策》,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9页。我国学者认可前述界定并将概念表述为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提出罪刑“法”定并非“立法者”定,只要司法上的犯罪化不背离刑法条文可能具有的含义,即使违背了所谓立法原意,也应认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11〕参见张明楷:《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法学家》2008年第4期。第三种是刑事立法与法律规则的司法重构。对正当防卫裁判规则的经验研究表明,司法裁判规则是司法重构的产物,应将关注点扩展至包括立法、司法及社会生活在内的“多元主体互动、互构的去中心化视角”,才能促成法律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12〕参见赵军:《正当防卫法律规则司法重构的经验研究》,《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本研究的理论逻辑在于司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刑法适用的指导,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定罪规则反映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导向,这种导向体现为对某类行为以司法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方式实现的定罪规则司法重构。
二、方法检讨及研究设计
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对裁判文书的定量研究。已有研究包括大样本与抽样样本。机器学习模型普遍存在“算法黑箱”,缺乏可解释性,对刑事裁判文书的大样本分析目前只能应用于分析量刑或者程序性事项。当前的研究主要包括分析交通肇事罪量刑情节并建立量刑模型、〔13〕参见白建军:《基于法官集体经验的量刑预测研究》,《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采用捕后实刑率等指标评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效果、〔14〕参见王禄生:《论刑事诉讼的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基于 303万判决书大数据的自然语义挖掘》,《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辩护率的差异及其经济因素相关分析、〔15〕参见左为民、张潋瀚:《刑事辩护率:差异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以四川省2015—2016年一审判决书为样本》,《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交通肇事罪中赔偿与判处缓刑或实刑的相关性。〔16〕See Yanyu Xin,Tianji Cai,Paying Money for Freedom:Effects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on Sentencing for Criminal Traffic Offenses in China,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Feb.2019, pp.1-28),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40-019-09409-w.仅仅对裁判文书通过机器学习方式进行自然语义挖掘,很难对定罪规则得出具有信度与效度的结论,因为这需要对证据、查明事实、法律与判决结果之间进行系统的法律逻辑分析,只能通过专家人工阅读裁判文书才能达到一定研究深度。而且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绝大多数裁判文书中证据、查明事实与判决结果非常简单,文本提供的信息不多。当前的大样本研究方法不适合定罪规则,对容留他人吸毒罪裁判文书的分析采用抽样样本即可。
目前基于刑事裁判文书抽样样本的单一数据研究成果比较多,本研究在组合运用数据方面进行改进。实证研究分为定量与定性研究两类,两种研究形成的定量与定性数据并无高低之分,定量数据更加标准化、精确化,但数值化过程可能损失裁判背景、过程等丰富含义;定性数据的代表性和普适性较差,但能够深入现象内部,一项理想的实证研究应当综合运用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集二者之所长。〔17〕参见何挺:《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运用为中心的探讨》,《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本研究在改进组合运用裁判文书抽样数据和访谈资料研究方法基础上,采取多阶段混合研究模式,每个阶段均采取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同时使用多个数据库对裁判文书数据进行测试与补充,并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分别采用Spss与Stata软件进行模型测试与数据分析。刑法实证研究根据不同目的划分为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评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四种类型,本研究将探索性研究列为第一个阶段,后三种列为第二个阶段。探索性研究属于验证文献回顾所得观点的准备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归纳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共性与差异性定罪规则,评估性研究分析共性定罪规则形成的实际处罚范围与差异性定罪规则形成的处罚差异,解释性研究则分析定罪规则的形成机制。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2017年11月至2019年8月的探索性研究阶段采用对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概率抽样方法,以及跟踪式自由访谈收集数据。由于缺乏可供参照的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实证研究成果,本阶段旨在初步描述定罪规则的特点及相关因素范围。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1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纪要》与2016年4月1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毒品解释》)均有容留他人吸毒罪规定,为保证不同时期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于2017年11月12日以北大法宝为来源数据库,〔18〕选择北大法宝数据库是因为当时中国裁判文书网存在每日访问量和下载量限制,不利于人工进行数据清洗。同时对容留他人吸毒罪裁判文书数量的对比测试表明,两个数据库的文书数量基本持平。检索得到容留他人吸毒罪裁判时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12日的全部一审刑事判决书共4744份作为抽样框。再采取分层抽样方法,根据裁判时间将样本分为2015年、2016年、2017年三组,以10%抽样率确定各组抽样数量,在各组中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得到474份裁判文书样本,经人工数据清洗后得到有效样本470个案例(以下简称抽样案例数据)。基于对抽样案例的人工分析,设置次数、人数等变量形成定量数据,也初步筛选了有关场所范围、容留行为、容留主体与容留对象定罪规则的代表性案例17个。
探索性研究阶段在不同时点分别与3名公安机关从事毒品犯罪侦查、强制隔离戒毒业务的警察、3名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强制隔离戒毒业务的警察、4名从事批捕和公诉业务的检察官、3名刑事法官、4名因容留他人吸毒罪服刑的罪犯、4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进行了两至五轮的跟踪式自由访谈。自由式访谈以面谈或电话访谈方式展开,围绕容留他人吸毒罪乃至毒品犯罪、强制隔离戒毒等进行非正式聊天。访谈贯穿全部研究阶段,其中约三分之二的访谈在探索性研究阶段完成(以下简称访谈资料)。
第二,2019年9月至11月的描述性、解释性研究与评估性阶段收集面板数据、五组案例数据与少量访谈资料。本研究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无讼案例的容留他人吸毒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总量,以及各年度数据经过为期三天的对比测试,选定数据量最多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主要来源数据库,于2019年10月3日收集重要毒品犯罪面板数据与容留他人吸毒罪微观数据。考虑到2014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4条首次规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本研究以裁判日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裁判文书作为数据来源。面板数据指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三个罪名分年度及裁判法院(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数量(以下简称重要毒品犯罪面板数据)。
本阶段收集的微观数据包括容留他人吸毒罪无罪案例、重要案例、补充完整的代表性案例以及容留他人卖淫罪的无罪案例。经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共得到容留他人吸毒罪无罪的裁判文书17份(涉及13个案例,其中终审无罪的12个,1个二审改判有罪;相关数据以下简称无罪案例数据)。访谈资料显示各类典型案例对裁判规则形成有重要影响,故以北大法宝、北大法意数据库的全样本重要案例为数据来源,〔19〕重要案例包括两高指导性案例、两高公报案例、各省参阅案例、最高法及各省高院发布的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报》等出版物刊登的典型案例。北大法宝与北大法意的典型案例不完全相同,主要是收录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等其他出版物案例不同。经人工合并、清洗数据后得到有效样本17个(以下简称重要案例数据)。同时为补充探索性研究阶段收集的代表性案例,以“网络聊天室”“草地”“多次”“共同控制”“相互容留”“嗨场”(还包括“嗨包”“嗨房”“烟馆”)“强制隔离戒毒期间自首”为关键词在该罪判决书中全文检索,在线阅读裁判文书230份并从中筛选体现共性与差异性定罪规则的代表性案例,包括探索性研究阶段的17个样本,最终获得代表性案例122个(以下简称代表性案例数据)。为了对照分析容留行为的定罪标准,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与北大法意网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3日期间的容留他人卖淫罪无罪裁判文书,采取以月份为裁判时间检索范围的分阶段检索方式,经人工筛选获得容留他人卖淫罪无罪的裁判文书9份(案例也是9个,以下简称容留他人卖淫罪无罪案例数据)。
综上,本研究旨在对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共性及差异性定罪规则进行描述性研究,对定罪规则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性研究,并对定罪规则建构的处罚范围进行评估性研究。研究采用多阶段综合研究模式,组合运用10个月期间对21人跟踪式自由访谈形成的资料、三种毒品犯罪6年期间32个省级裁判法院的面板数据以及631个刑事案例数据。刑事案例数据系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意、北大法宝作为来源数据库,经分层抽样、立意抽样或全样本形成的五组案例数据:容留他人吸毒罪的470个抽样案例、13个无罪案例、17个重要案例、122个代表性案例与容留他人卖淫罪9个无罪案例。
三、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共性定罪规则
刑事司法机关先后根据2012年5月16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三)》)第11条及《毒品解释》第12条确定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定罪规则。根据《追诉标准(三)》,容留他人吸毒罪是指提供场所,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
(一)定罪条件的数量化
《毒品解释》的实质性变化是将容留次数的定罪条件从两次提高为三次。如表1所示的抽样案例数据显示,《毒品解释》实施前后容留次数均为最常用的定罪条件,分别占比72%与62%,其次是容留人数。这两类数量化定罪条件适用比例合计分别达到94%与84%。《毒品解释》实施后,容留未成年人定罪条件适用比例升高,这可能与未成年吸毒人数上升有关。

表1 容留他人吸毒罪定罪条件频数分布表(单位:份)
行政处罚与严重后果这两项定罪条件适用频率极低。行政处罚适用少,因为犯罪嫌疑人中存在大量因吸毒被行政处罚或者强制隔离戒毒的情形,但没有因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受行政处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1条至74条对涉毒违法行为的条文中并不包括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的行为,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对容留吸毒行为的行政处罚书。于是,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不能证明行为人“二年内曾因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受过行政处罚的”,就无法适用该项定罪条件。适用严重后果的仅有1例,被告人容留李某注射毒品海洛因并造成李某中毒死亡,〔20〕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2016)浙0326刑初1078号判决书。表明这项定罪条件主要考虑容留吸毒行为对被容留人健康或生命造成的影响。不过法院对于适用该定罪条件的因果关系证据要求非常高。无罪案例数据显示,公诉机关未提供现场勘查笔录及死者尸检报告这两项关键证据佐证死者生前吸食毒品,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人无罪。〔21〕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2017)湘0202刑初424号判决书。严重后果的定罪条件适用频率低,是因为容留他人吸毒造成其重伤或死亡的情形比较少。
牟利目的定罪条件独立适用极少。有些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认定被告人具备牟利的目的,不过此类案件中场所长期容留他人吸毒,往往现场查获多人吸毒,有的案件高达30余名吸毒人员,判决书实际适用的定罪条件还是容留多人以及容留多次,此类判决书均归入表1的容留次数或者容留人数类别。无论哪类案件,大多数判决书均未具体描述牟利事实,重点关注行为人提供场所的行为认定。通常,具有牟利目的影响量刑。代表性案例证实,法院认为在本人家中容留比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毒的主观恶性更小。〔22〕法院认为行为人并非开设地下烟馆,只是在其家中容留他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4刑初112号判决书。换言之,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毒的,主观恶性更大,量刑应从重。
(二)容留次数认定标准的简单化
代表性案例数据显示,司法机关根据吸毒次数的简单化标准认定容留次数,通常不考虑场所与吸毒人员的同一性以及时间的连续性。容留行为人往往与“他人”系共同吸毒的人员之一,由于吸毒的频率较高,因此以吸毒次数确定容留次数的定罪规则导致“多次”定罪条件非常容易达到,《毒品解释》将容留次数定罪条件从两次提高为三次,实际上对定罪影响极小,也并没有缩小打击范围。适用《追诉标准(三)》的案件如2015年11月16日下午,葛某在宾馆房间与蒋某共同吸毒一次,11月17日凌晨葛某又在同一房间与蒋某共同吸毒一次,法院以容留他人吸毒两次判决葛某有罪。〔23〕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3刑初55号判决书。该案件中被认定为不同容留次数的时间在24小时之内。《毒品解释》后的认定的3次容留也以吸毒次数认定容留次数。例如,被告人的三次容留均发生在同一宾馆房间,每次吸毒行为中的“他人”均为相同的两人,时间分别为4月6日晚7时许、4月7日晚12时许、4月8日下午1时许。〔24〕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赣0103刑初637号刑事判决书。当然,次数的定罪条件从两次提高到三次,显著的影响体现在无罪案例数据中。《毒品解释》实施前行为但实施后判决的8个旧案中,被告人被指控两次容留他人吸毒的,法院均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判决无罪。〔25〕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2016)黑1202刑初94号判决书等。以吸毒次数认定容留次数的定罪规则表明,刑事司法工作人员以形式量化标准最大程度简化定罪规则的倾向。同一行为人在同一场所容留他人吸毒的情形,如果进一步考虑吸毒时间的连续性、人员的变动性,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不采取吸毒次数的简化标准,就需要考虑“他人”相同或不相同对容留次数的影响、吸毒次数与容留次数的关系。代表性案例显示,被认定为不同次数容留行为的情形中,“他人”有的是不同人员,如2015年5月5日22时与5月6日7时,邓某某在某公寓房内容留陈某某、杨某某各吸毒1次;〔26〕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刑初字第1522号判决书。也有的部分人员相同,如2014年11月6日下午王某在宾馆房间容留尚某吸毒一次,11月7日下午王某又在同一房间容留尚某与刘某某吸毒1次。〔27〕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5)黄刑初字第326号判决书。
(三)提供行为的扩大化
刑事司法机关普遍采取提供行为指任何形式收容留置的扩大化广义概念,提供行为既包括明知他人准备吸食、注射毒品而主动安排场所的作为方式,也包括明知他人在本人控制的场所内吸食、注射毒品而不制止的不作为方式;还包括采用各种手段招徕不特定吸毒人员到本人控制场所内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同时容留主体认定也被适用广义标准。行为人只需对场所具有某种排他权利而不一定必须是场所的所有人,娱乐场所负责人主动招揽吸毒人员是提供,服务员给吸毒人员开房间也是提供。〔28〕参见郑伟:《毒品罪三疏两议》,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重要案例的定罪规则对提供行为与容留主体有非常明确的扩张倾向。如娱乐场所的管理者明知有顾客要在其会所包房内吸食毒品,但其为了增加营业收入,仍为他人提供吸食毒品场所的属于容留行为。又如,孟某将谢某、郭某约至吴某某住所共同吸食甲基苯丙胺,被告人吴某某当日虽未吸毒,但明知上述三人在其住所吸毒未予制止,仍然被认定成立本罪。法院普遍认为,容留他人吸毒罪是指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或者允许他人在自己管理的场所内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29〕高锋容留他人吸毒案,孟某、吴某某容留他人吸毒、吴某某盗窃案,卫薇等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可以是主动实施的,也可以是被动实施的,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许的。由此,场所的共同居住人也被认定为共犯。
代表性案例数据显示,招徕不特定吸毒人员的提供行为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经营专门供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场所即“嗨场”的行为。这种场所的毒品通常是顾客自带,“嗨场”提供吸毒工具,有的判决书将此类行为表述为聚众吸毒。第二类是吸引包括吸毒人员在内的“顾客”到经营场所内消费的行为。这类场所主要是赌场,毒品与吸毒工具通常由场所经营者免费提供。〔30〕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7刑初322号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刑初字第1131号判决书。对于前述行为,判决书通常认定为以牟利为目的的容留行为,认为应予严惩,量刑普遍较重,通常为1至2年有期徒刑。而且,经营性场所的消费者也往往被认定为场所控制人从而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对于宾馆等需要身份证件登记的场所,多数法院往往将提供身份证件的行为人认定为容留主体,对其他经营性场所则将支付场所费用的人员认定为容留主体。
(四)场所范围的宽泛化
定罪规则采取物理隔离性标准,认为场所包括一切与公共空间具有隔离性的物理空间,最大限度扩张了场所范围。代表性案例显示,定罪规则将网络空间排除在场所范围之外,不过物理空间范围广泛,既包括住宅、办公室、公共厕所休息室等固定场所,也包括机动车与船舶等移动交通工具。对于场所的权属不限制,无论是自有、租赁还是借用均不影响定罪。场所的永久性或临时性也不影响定罪,帐篷也包括在内。有些案件中认定的场所是正在营业的临街商铺、渔船、果园或者苗圃地帐篷,与公共空间并非完全隔绝。又如,被告人李某在河边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容留多人吸毒也被判有罪。〔31〕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0803刑初110号判决书。因此,定罪规则对于场所的认定标准是与公共空间的物理隔离性而非场所的封闭性或人员的隔绝性。
有检察官建议对场所的空间范围扩展至荒山林地等开放空间。〔32〕参见张宇:《容留他人吸毒罪的认定宜适当扩展》,《检察日报》2011年8月17日第3版。这种建议没有得到定罪规则支持,不过在行为人驾车到偏僻公共场所共同吸食毒品的案件中,有关吸毒地点的事实认定往往采取了模糊的证据标准。例如,王某某被指控在停放的机动车内2次容留他人吸毒,被告人辩解车停放在河边之后,大家在河边的草地上共同吸毒,法院没有采纳该辩解。〔33〕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2015)阳西法刑初字第71号判决书。该类案件显示,场所的范围扩大到移动交通工具与半封闭场所之后,所谓行为人提供的“场所”与开放的公共空间之间界限非常模糊。通过证明标准的“软化”,实质上对某些公共空间的所谓“容留”行为也实现了司法犯罪化。
四、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差异性定罪规则
(一)容留多人与多次界限的模糊化:吸毒次数?
共性定罪规则将容留次数简化为吸毒次数标准,结果在同一场所连续时间内的人数与次数两种定罪条件边界模糊,同时在次数没有达到但人数达到定罪条件时,这种吸毒次数等于容留次数的定罪规则又被“软化”。例如,在高某开设的麻将馆内,2015年10月19日下午6时,许某吸食毒品,下午8时潘某与荣某吸食毒品,公安机关认定的容留行为是两次,检察机关认定的则是一次容留多人,追加起诉容留他人吸毒罪,法院也予以认可。该案行为时间是《毒品解释》之前,生效判决时间在《毒品解释》之后,次数的认定标准直接决定容留他人吸毒罪能否成立。
实际上,《毒品解释》实施后,对于同一行为人在同一场所比较接近的时间内连续容留相同或部分相同“他人”吸毒的行为,是认定为一次还是不同次数容留行为,不同判决之间仍有差异。例如,11月9日22时,周某、尚某、刘某在周某车上吸毒;次日2时,周某驾驶同一辆车到另一处空地上,周某与尚某、闵某、刘某在车上吸食毒品;同年10月,闵某驾驶朋友的汽车,搭载尚某,两人一起在车上吸食毒品三次。〔34〕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赣0191刑初70号判决书。前述案例中,法院将被告人周某4小时之内在同一辆车内的两次共同吸毒行为认定为一次容留行为,从而适用“容留多人”定罪条件;不过对于闵某同一个月内的容留行为,则认定为三次容留行为,从而适用“容留多次”定罪条件。其他认定为不同次数容留吸毒行为的案例中,也有人员与场所具有同一性、吸毒行为具有连续性的情况。如2019年6月15日晚,高某在酒店房间与郭某共同吸毒一次,6月17日凌晨在前述房间与郭某吸毒一次,7月8日晚在前述宾馆不同房间与郭某共同吸毒一次。〔35〕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5刑初199号判决书。前述这类案件中,吸毒行为连续,吸毒时间接近,场所的同一性是否会影响容留次数或人数的认定,判决书没有给出更多的事实以及法律适用标准。而且相当多判决书在事实认定部分往往以某月期间“多次容留”这种概括性语言认定法律事实,具体次数的认定标准不清晰。
总之,定罪规则中容留多人与多次的“可转化性”体现了明显的选择性司法定罪导向。如果案件中没有任何一次共同吸毒行为符合“容留多人”的定罪条件且吸毒次数超过3次的,或者至少有一次共同吸毒行为符合“容留多人”的定罪条件,则案件通常适用以吸毒次数认定容留次数的共性规则,从而认定被告人符合“容留多次”,或者同时符合“容留多人”与“容留多次”的定罪条件。如果共同吸毒行为仅为1次或2次,且任何一次吸毒行为中的“他人”均为1人或2人,则通常不按照吸毒次数认定容留次数,而将时间接近的不同次吸毒行为合并认定为同一次容留行为,从而合并计算“他人”,以适用“容留多人”的定罪条件。但是,同一场所内时间相近的不同次吸毒行为何时被认定为同一次容留行为?判决并没有阐述清晰的法律事实认定与法律逻辑论证标准,无论是共性还是差异定罪规则,容留多人与容留多次的界限体现了明显为定罪目的服务的选择性司法倾向。
(二)经营性场所容留主体的选择化:出资者、经营者、管理者、消费者或共犯?
场所为KTV与餐厅等经营性场所时,可能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的行为人包括场所的出资者、全面负责场所日常管理的经营者、行使某方面管理职能的管理人员、从事具体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吸毒人员消费者。如何认定前述行为人容留他人吸毒的故意和容留行为,以及多位行为人明知场所内有吸毒行为的情况下,何者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或者何时构成共同犯罪,尚缺乏统一的定罪标准。绝大部分判决书在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往往简单描述为“被告人在某处容留某人吸毒”,并没有就何谓“提供场所”给出清晰的法律论证标准。
第一,重要案例表明了追究场所出资者与经营者刑事责任的导向。陈壵东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认定共同出资者陈某以及共同出资者、经营者文某对于娱乐城内发生的吸毒行负刑事责任,但并未认定文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认为文某与陈某只是共同出资开设娱乐城,属于经济合作关系。利惠青等容留他人吸毒案中,利惠青等三人共同出资租赁某KTV2间包房用于容留他人吸毒并共同负责日常经营管理,三人被认定为共同犯罪。黄林贵等容留他人吸毒案中,被告人黄林贵、陈某均系某娱乐广场股东,且分别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因为明知他人在娱乐广场吸食摇头丸且提供便利,被认定本罪。前述案件中追究的均是场所出资者与经营者刑事责任,场所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作人员以及吸毒人员消费者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实际上,利惠青这类租赁场所经营“嗨场”的案件中,场所出租人也应成为容留他人吸毒犯罪的打击重点。代表性案例显示,“嗨场”经营者通常负责场所卫生并提供吸管等吸毒工具。〔36〕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8)湘0406刑初128号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7刑初322号判决书。因此,“嗨场”内长期吸毒,毒品及其气味、吸毒工具的痕迹非常明显,通常并不缺乏认定场所出租人明知的证据。
第二,代表性案例显示,经营性场所发生的容留他人吸毒案件中容留主体呈现多元性,不同法院分别采取全面定罪、部分定罪及个别定罪原则,处罚范围涉及场所的出资者、经营者、管理人员、普通工作人员以及被现场查获的吸毒人员消费者。有的案件采取全面定罪原则,如胡某甲出资租赁某农庄并将两个房间装修为“嗨场”,胡某甲及其安排的“嗨场”管理人员雷某、王某等4名普通工作人员均被认定本罪,同时某日支付6800元在“嗨场”包下一间房间邀请10余位朋友庆祝生日并共同吸食毒品的刘某也构成本罪。〔37〕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4刑初68号判决书。有的案件采取部分定罪原则,处罚经营者、管理人员和部分普通工作人员。如徐某是某山庄经营者,山庄业务之一是经营“嗨场”,孙某负责管理“嗨场”,订房并收取服务费用,梅某等人打扫“嗨房”卫生,为客人送酒水饮料、吸毒用吸管、“嗨服”等服务。本案中,梅某之外的普通工作人员,以及案发当日支付“嗨场”费用邀约朋友共同吸毒的杜某等人并没有被认定本罪。〔38〕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7刑初322号判决书。还有的案件采取个别定罪原则,不过定罪的人员范围不一致、定罪标准不清晰。有的只处罚经营者。如何某出资在某村租赁一间平房后装修成“嗨场”并收取一定服务费,负责开门、做卫生、提供水果和吸食K粉吸管的朱某以及结伙到此消费并支付费用的吸毒人员,均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39〕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8)湘0406刑初128号判决书。有的案件处罚普通工作人员,如贾某系某网吧网络管理员,因3次在网吧二楼一包间内容留李某吸毒构成本罪。〔40〕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5)庄刑初字第112号判决书。该案中,网吧经营者是否明知网吧包间内经常发生吸毒行为,贾某的容留他人吸毒是何种“提供场所”行为形态,李某是否支付网吧包间的费用,均不清楚。另外有案件处罚吸毒人员消费者,消费者往往以支付场所费用为标准。如林某某、谢某某、林某甲、苏某某等人在KTV包厢唱歌,费用AA制,每人出资200元,林某某与谢某某被认定本罪。〔41〕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2014)湛麻法刑初字第80号判决书。但是该案件中,出资的并非仅仅两位被告人,二被告人成立犯罪的关键事实可能在于林某某叫谢某某购买200元的毒品供大家吸食。但是,容留他人吸毒罪处罚的是提供场所行为,而非提供毒品或者吸毒工具。如果贯彻本案的裁判逻辑,那么所有出资并参与决定将KTV包间用于吸毒的行为人均为容留行为人。但是,将KTV房间费用的支付者都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就会陷入没有“他人”的境地,因为本案中费用是共同吸毒人员分担的。这类案件实际属于场所共同控制人的相互容留行为,认定为无罪更为妥当。如果有证据证明KTV经营者或管理者明知客人吸毒仍然继续出租包间,则应追究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的刑事责任。
第三,无罪案例数据显示,有的法院认为到合法经营性场所正常消费的人员在该场所内不具有制止他人吸毒的义务,也不能认定其提供场所的主观故意。如法院认定,对娱乐场所发生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经营管理人员发现后有向公安机关报告的义务,到该场所正常消费的人员在该场所内并无制止他人吸食毒品的义务,在其所开包厢内发现他人吸食毒品不予制止,其不作为不符合本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因为行为人开包厢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宴请他人饮酒娱乐,而非为吸毒提供场所,不符合本罪主观方面构成要件。〔42〕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4刑终59号判决书。认定容留他人吸毒的故意应考察行为人提供场所时的目的这一点非常有价值。这项定罪规则倾向于认定在经营性场所预订房间而没有与“他人”共同吸食毒品的人员无罪,当提供场所的行为人也共同吸毒时,判决通常认定行为人有罪。如宋某邀约3位“他人”到其弟弟的住宅打扑克,打牌期间四人共同吸食毒品,宋某被认定有罪。〔43〕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3刑初34号判决书。另外处置娱乐场所人员的案例同样认定经营性场所经营者的不作为可以构成本罪,不过在主观故意认定方面严格坚持了证明确实、充分的标准。如,王某租赁某酒店两层楼开设KTV,本人不亲自管理,聘请王某为经营者负责管理日常工作,某日公安机关在KTV某包厢内查获吸食K粉的12名吸毒人员,检察院指控王某为了牟利,明知有人在其经营的KTV包厢内吸毒并不阻止;法院认定王某虽然是涉案KTV的经营者,但证据仅能证实KTV内有他人吸毒的客观事实,不能证实被告人王某有明知他人吸毒而给予默许的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判决被告人王某无罪。〔44〕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8刑初551号判决书。总之,经营性场所内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主体认定在审判环节呈现多元性,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及侦查策略有关,也与公安、检察与审判机关对于容留故意与容留行为认定标准存在巨大分歧有关。无罪案例数据显示,对经营场所内发生的吸毒行为,能否根据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存在不同作法。个别法院根据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第三十条解释》),有限制地扩大了经营性场所承担刑事责任人员的范围。如某餐饮城系个体工商户,法定代表人为韦某,艾某系受韦某委托全权打理餐饮城的经营者,陶某系担任总经理助理的管理人员。本案没有追诉韦某,一审认定本案既没有证据证实案发当晚陶某看见有客人在包厢内吸食毒品,也没有证据证实有服务员向其报告有客人在包厢内吸食毒品,更没有证据证实其为吸毒者提供了帮助,判决陶某无罪;但二审法院根据《人大第三十条解释》认定本案具有单位犯罪性质,陶某作为案发期间现场值班的主要行政领导,曾经到发生吸毒行为的某个包厢应酬,应负领导责任,改判陶某成立本罪。〔45〕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4)鱼刑初字第254号判决书(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柳市刑一终字第173号判决书(二审)。已经存在“单位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司法犯罪化的做法。
(三)特定关系人容留行为的差别化:共同控制、一方容留一方他人、相互容留无罪?
1.特定关系人共同犯罪的差异性定罪规则
案例显示,对于特定关系人,包括共同居住的男女朋友、合租人、场所的所有人与借用人等人员与其他吸毒人员共同吸毒的案件,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处置方式。第一种是特定关系人构成本罪的共同犯罪,第二种是认定一方是容留主体,另一方属于“他人”。
首先,认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共同犯罪的定罪判决,通常认为共同居住于同一场所的人员对场所形成共同控制关系。即使“他人”系一方邀约到场所内共同吸毒的,只要另一方不制止吸毒行为,就构成共同犯罪。判决书对于共同控制关系的认定标准比较单一,同居关系本身即成立共同控制关系,一方是否系房屋的所有人、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或者分担租金或其他费用这类事实基本不影响认定。如覃某和韦某一起在某出租房合租,租金由某KTV管理人员支付,水电费由覃某、韦某均摊,到出租房吸食毒品的人员系覃某邀请,不过两人被认定为共同犯罪。〔46〕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2刑初121号判决书。该案件中,虽然覃某、韦某不是房屋的承租人,但法院认定两人分担水电费的事实,强调两人共同居住期间对出租房形成的共同控制关系。另外如,刘某和周某系情侣关系,共同租住在某出租房,法院认定共同构成本罪。〔47〕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辽0902刑初67号判决书。其次,但是与前述案例类似的案件中,特定关系人之间没有构成共同犯罪,一方被认定为容留主体,另一方被认定为“他人”。如熊某系被告人程某男友,且二人共同控制程某父母购买的房屋,但是熊某被认定为“他人”。〔48〕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刑初19号判决书。再如,邱某和刘某系情侣关系,共同居住于某住宅,同居期间两人共同贩卖毒品,所得毒资共同挥霍,邱某与刘某等人在家中、宾馆、日租房都有过共同吸毒行为。但是法院只对邱某、刘某的贩卖毒品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同时认定邱某成立容留他人吸毒罪,反而将刘某认定为“他人”。〔49〕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16)黑0604刑初76号判决书。显然,法院在追求定罪的结果导向指导下,场所共同控制人是否共同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被适用了不同的裁判逻辑。
2.特定关系人相互容留无罪的裁判趋势
第一,无罪案例数据显示,部分法院对特定关系人之间相互容留行为的定罪进行限制,认为特定关系人属于场所共同控制人,其相互容留行为不成立本罪,容留“他人”吸毒时才涉嫌本罪。如闫某和蔡某、张某在参加朋友的宴会后到本市某酒店以闫某的身份证开房,在房间内打扑克牌并用从每局赢家处提的钱支付房费和购买香烟,后蔡某提议吸食毒品并打电话向杨某购买毒品,并与张某、杨某在房间内共同吸食毒品。法院认为,虽然房间是用闫某的身份证登记,但房费是用三人打牌提成的钱支付,不能仅仅因使用了闫某的身份证就认定该房间为闫某一人控制,该房间是被告人闫某及证人蔡某、张某共同控制。〔50〕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刑初958号判决书。前述案例反映了对经营性场所中消费者层面的共同控制人以及共同控制人之间是否能成立容留吸毒罪的差异性规则。
第二,访谈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特定关系人相互容留无罪的裁判趋势。法院倾向于在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将预定场所、提供身份证件进行场所登记、共同支付场所费用的人员认定为共同控制人,共同控制人之间相互容留不构成本罪,不过其共同容留“他人”吸毒则涉嫌本罪。这种特定关系人之间相互容留无罪的定罪规则,在共同居住的男女朋友案件中最为明显。一方租房,另一方与之同居,然后双方在出租房内共同多次吸毒的案件,租房一方往往被以容留他人多次吸毒定罪。但陆续有地区出现一审判决无罪或者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之后,当地的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逐渐就不再立案或者起诉这类案件。
但是各地法院在认定特定关系人范围方面并未形成一致性标准。这类特定关系人相互容留不被认为是犯罪的情形,除了恋爱同居关系的,通常还包括近亲属关系、房主与借住人关系、合租关系。当然,合租人员,理论来说,在客厅等公共空间相互容留,不构成犯罪;在本人可以独立控制的卧室内相互容留,理论上可以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不过当前的案例中,没有考虑那么细致,通常不再考虑合租住宅之内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区分。
五、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的形成机制
定罪规则是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与被害方(被害人及其家属)、被告方(被告人及其家属、辩护人)实施诉讼行为时互动形成的。容留他人吸毒罪属于“无被害人的犯罪”,司法机关普遍认为本罪犯罪客体是国家对于毒品的管制秩序,从而最大限度扩张处罚范围,该罪定罪规则是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异化为严刑禁毒政策的结果。
(一)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与司法犯罪化
刑事司法机关普遍认为,为有效治理毒品犯罪,有必要加大对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打击力度,因此基于立法原意以及惩治毒品犯罪的实践需要,对“容留”含义理应扩大解释。〔51〕参见杨子良:《如何理解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容留”》,《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3日第6版。从规范层面分析,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应该与查处的吸毒人员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新收戒人员具有同步上升或下降的正相关关系。因为,吸毒行政案件通常伴生强制隔离戒毒、容留他人吸毒刑事案件的线索。虽然2014年至 2017年查处吸毒人员的人数分别为 887 000、1 062 000、1 006 000、870 000 人,呈现上升趋势。〔52〕吸毒人员相关数据来源: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15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6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spss软件的相关性检验表明,每年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与新发现登记吸毒人员、查处吸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新收戒人员及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新报到人员数量之间的显著性均大于0.05,不具有相关性。前述变量可能共同由其他的变量影响,对该变量的合理假设是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结合数据分析发现,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背景下,毒品犯罪刑事案件数量不仅是毒品犯罪处于高发期的标志,也成为治理毒品问题并实现良好社会控制的核心指标。统计分析表明(如图1,分析工具为spss软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与非法持有他人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数量位居前三的案件,2014年至2016年期间呈现先大幅度上升后下降趋势,峰值均为2015年,2016年后下降趋势明显。前述趋势与对毒品问题的治理政策导向有关。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公安部组织全国29个省份公安机关在109个重点城市集中开展百城禁毒会战。〔53〕参见张年亮、田海军:《百城禁毒会战:一场影响深远的禁毒人民战争》,《人民公安报》2015年4月16日第3版。2015年以来容留他人吸毒罪等重要毒品犯罪案件数量迅猛增长固然与我国禁毒斗争形势严峻相关,也与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导向下的禁毒专项斗争在时间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相关性。

图1 三种毒品犯罪刑事案件趋势图
可进一步提出的假设为,三种毒品犯罪数量之间具有相关性,整体是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体现。重要毒品犯罪面板数据显示,〔54〕面板模型的原始数据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标准划分司法辖区,分别赋值如下: 1=北京市,2=天津市,3=河北省,4=山西省,5=内蒙古自治区,6=辽宁省,7=吉林省,8=黑龙江省,9=上海市,10=江苏省,11=浙江省,12=安徽省,13=福建省,14=江西省,15=山东省, 16=河南省,17=湖北省,18=湖南省,19=广东省,20=广西壮族自治区,21=海南省,22=重庆市,23=四川省,24=贵州省,25=云南省,26=西藏自治区,27=陕西省,28=甘肃省,29=青海省,30=宁夏回族自治区,3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容留他人吸毒罪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犯罪在不同省份相同时间点内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具有一致性。这种趋势究竟是巧合还是具有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将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根据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实证计量基准模型设定如下:Crime1i,t =α+βCrime2i,t +γCrime3i,t +εi,t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度,Crime1i,t 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i个省第t年的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决书数量;Crime2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决书数量,Crime3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决书数量,α和ε分别为截距项与随机误差项。经检验,个体效应明显,应选取面板模型中的随机效应模型(如图2,分析工具为stata软件)。

图2 容留他人吸毒罪随机效应模型
根据随机效应模型得到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之间的回归方程为:Crime1i,t =134+1.89Crime2i,t +0.12Crime3i,t +εi,t 。其中,P=0.0000 小于 5%,因此模型具有整体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模型拟合优度是衡量随机效应模型优劣的重要标准,拟合优度R方≈0.52,说明该模型整体上具有较强的预测性。
根据容留他人吸毒罪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方程可以发现,非法持有毒品罪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89和0.12,表明这两种毒品犯罪数量与容留他人吸毒罪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与图1的观测结果一致。而且,非法持有毒品罪案件数量每上升一个单位,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量上升1.89倍,因此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对容留他人吸毒罪影响力较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对容留他人吸毒罪定罪的影响程度较小。在毒品犯罪的现实样态中,毒品生产地、毒品过境地、毒品消费地并不完全一致。三种毒品犯罪刑事案件数量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三种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为主的毒品犯罪数量是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治理效能的衡量指标,并主导了毒品犯罪的从严打击力度,由此才在全国范围以及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呈现容留他人吸毒罪与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量的正相关关系。局部地区甚至出现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量超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数量的反常情况。如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位居全国第三的江苏省,2014年开始该罪数量每年均超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二)“以刑逃戒”与被告方对“相约吸毒”定罪规则的“认可”
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的强势运行背景下,被告方通常“认可”简单化与扩大化的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使得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异化为严刑禁毒政策。代表性案例数据显示,被告人在吸毒被行政拘留期间或强制隔离戒毒期间主动交代容留他人吸毒犯罪行为的,通常被认定坦白或者自首,量刑通常为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元,甚至是拘役4或5个月。访谈资料表明,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依法“减期”后实际执行21个月左右,吸毒人员因吸毒被行政拘留期间为了避免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强制隔离戒毒初期为了早日获得自由,往往主动交代“相约吸毒”事实,以通过“转刑拘”方式被判决容留他人吸毒罪,从而逃避更长期的强制隔离戒毒。按规定,〔55〕《戒毒条例》第三十六条:刑罚执行完毕时、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时或者释放时强制隔离戒毒尚未期满的,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刑罚执行完毕后,行为人应该被转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继续接受戒毒治疗。但是刑罚执行完毕后,即使强制隔离戒毒未期满,执行机关往往一放了之,而没有再次移送回原戒毒所。〔56〕参见吴加明、陈钢:《强制隔离戒毒与其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衔接》,《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访谈资料显示,直至2019年,强制隔离戒毒与刑罚执行的衔接仍普遍存在漏洞。
总之,容留他人吸毒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的比例特别高,辩护人通常仅进行量刑辩护,这种控辩双方的“无重大争议”状态催生了案件法律事实的“脚本化”,即某位吸毒人员提供场所,与他人多次或者一次与多人“相约吸毒”。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的简单化与扩大化成为吸毒人员“以刑逃戒”的“跳板”,被告人的“配合”又加剧了定罪规则的进一步扩大化。容留他人吸毒罪成为办案周期最短、成本与风险最低、定罪率与可复制性超高的毒品犯罪刑事案件,这与刑事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及其工作绩效目标非常契合。因此,刑事司法过程中形成了通过剥夺公民自由方式对毒品供给与消费两端并重实行高压管制的毒品问题治理模式,容留他人吸毒罪通过对“相约吸毒行为”的司法犯罪化实际成为严刑禁毒的工具。
六、容留他人吸毒罪处罚范围的评估与建议
(一)容留他人罪处罚范围的评估
司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司法刑事政策化的重要工具,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司法犯罪化倾向非常显著,绝大部分处罚范围是两位或多位吸毒人员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共同吸毒的“相约吸毒行为”,处罚对象是与提供场所有关联的行为人。共性定罪规则的处罚效果在于,通过追究提供场所人员刑事责任,将2人3次或者4人1次的“相约吸毒行为”司法犯罪化。抽样案例数据显示,42%的判决书记载被告人与“他人”共同吸毒的法律事实。访谈资料显示,被告人是否吸毒不影响定罪,因此判决书不一定记载被告人吸毒的事实,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容留他人吸毒案件是“相约吸毒行为”。
首先,共性定罪规则处罚的“相约吸毒行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零包贩卖+容留吸毒”型毒品犯罪。掌握上线资源的上层零包贩毒人员幕后操控吸毒人员租赁多处住宅或开多个宾馆房间,提供零包毒品、免费的吸毒场所与吸毒工具,形式上支付租金或者房费的吸毒人员被认定为本罪。根据证据情况不同,上层零包贩毒人员往往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或容留他人吸毒罪。大多数情况下,容留他人吸毒罪成为打击此类行为的兜底罪名。
第二类是特定吸毒人员之间的共同吸毒行为。场所往往是住宅、汽车,有时也在经营性场所,通常是互相认识的吸毒人员长期轮流到对方提供的场所共同吸毒。共同吸毒行为发生在经营性场所时,邀约吸毒人员、支付场所费用、支付毒资,提供吸毒工具以及购买毒品的行为人,有时相同,有时不同。通常被现场查获的某次吸毒行为中提供身份证件或支付场所费用的人员构成本罪,偶尔也有其中代购毒品的构成贩卖毒品罪,提供毒品的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情形。
第三类是多位吸毒人员与少数非吸毒人员之间共同庆祝生日或“狂欢”之类的聚会性吸毒行为。这类行为往往发生在经营性场所,涉及牟利型容留,应该属于打击重点。抽样案例以及代表性案件显示,2014至2019年全部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直接以牟利为目的经营“嗨场”的案件仅有281件,被告人涉嫌牟利目的的情形包括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牟利是行为人开设专门供吸毒人员吸毒的场所并收取服务费等,通常提供吸毒工具,个别场所还有零包贩卖毒品行为。判决书往往将场所冠之以“嗨场”“嗨包”“嗨房”“地下烟馆”之类的称谓。间接牟利是地下赌场、卖淫窝点或娱乐场所为招揽生意、增加营业收入而容留他人吸毒。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往往构成本罪,也有的行为人还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根据证据情况,行为人可能还构成贩卖毒品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抽样数据显示,本罪宣告刑很低,约27%的被告人被判处拘役,约57%的被告人被判处6至11个月有期徒刑。因而前述案件中行为人被数罪并罚时,该罪宣告刑在决定执行的刑期中实际上“消失”了。
其次,差异性定罪规则表明“相约吸毒行为”中普遍呈现处罚对象不均衡现象。本罪只处罚提供场所的行为人,当该行为人与邀约吸毒、提供毒品的人员不同时,实际上放纵了引诱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犯罪。例如,王某提供毒品,冯某容留王某及其邀约的覃某、赖某一同吸食。〔57〕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28刑初10-1号判决书。本案中冯某被以容留他人吸毒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实际上提供毒品以及邀约其他吸毒人员的王某社会危害性更大。而且经营性场所中的“相约吸毒行为”人员类型众多,消费者一方包括预定场所、提供身份证件办理场所登记、共同支付场所费用的人员,场所一方涉及出资股东、名义股东、经营者、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普通工作人员。当前定罪规则既没有明确消费者与场所经营方相关人员是分别还是共同构成容留他吸毒罪,也没有确定追究一方刑事责任时具体的人员定罪标准。
(二)容留他人罪处罚范围的建议
下面初步回应当前有关容留他人吸毒罪处罚范围的主要观点,并提出建议。
将本罪场所进一步扩大解释为包括偏僻的矿场、林场之类公共场所的观点不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从正当性层面分析,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必须具有可控制性,行为人不具有管理可能性的公共空间不属于本罪的场所。从必要性角度分析,当前定罪规则已经“虚化”场所的封闭性标准而代之以隔离性要求,同时适当模糊具体吸毒地点的证据标准,已经最大限度将在公共厕所休息室、帐篷、开车到所谓“偏僻场所”吸毒等公共空间发生的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纳入本罪处罚范围。对于场所,在概念层面理解为包括一切固定的或可移动的陆地或水上构筑物、船舶、航空器、空中漂浮物即可。
仅处罚牟利型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立法建议不具有现实基础。以牟利为目的作为定罪条件的独立适用频率很低。而且以牟利为目的的法律事实认定证据标准具有一定模糊性,对于间接方式牟利的能否认定为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毒,在法律适用层面也有一定争议。
增加单位作为本罪犯罪主体的立法建议有一定必要性但没有紧迫的立法需求。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经营性场所基于单位意志专门容留他人吸毒的案件很少,往往只能证明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场所经营其他合法或非法业务的同时容留他人吸毒行为。此时,根据《人大第三十条解释》,可以满足该罪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需要。
修改本罪为“聚众吸毒罪”或“组织吸毒罪”的立法建议不具有必要性。容留他人卖淫罪无罪数据显示,容留卖淫罪中的容留是单纯地为他人提供场所的行为,容留者与卖淫者没有控制与调度的关系;组织卖淫行为则是利用服务场所的便利条件,以招募、雇佣等手段,管理多人卖淫。〔58〕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4)辽阳白刑初字第129号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刑初770号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刑初951号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4刑初381号判决书。但是本研究发现,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处罚范围大部分属于“相约吸毒行为”,绝大部分情形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吸毒,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控制与调度的关系,第一个提出吸毒建议的人员很难被认定为组织者或首要分子,也很难进一步区分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实践中有计划的长期容留他人吸毒的情形包括开设专门吸毒场所即“嗨场”与“零包贩毒+容留吸毒”的情形,但这两种情形中均属于吸引吸毒人员到场所“消费”,场所提供者与吸毒人员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控制关系,目前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的定罪规则也可以处罚这两类人员。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参考性案例,明确共同控制人标准从而将特定关系人之间相互容留无罪的规则普遍适用,并将“相约吸毒行为”中特定吸毒人员之间的相互容留吸毒行为司法非犯罪化。代表性案例数据显示,司法机关多认为本罪为复杂犯罪客体,即“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公民的健康权利”,〔59〕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2015)莒刑初字第10号判决书。也有的认为属于单一犯罪客体,即“国家对于毒品的管制秩序”。〔60〕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刑初19号判决书。总之通常认为对毒品的管制秩序属于本罪保护法益。“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长期的社会工程,打击犯罪(减少供应)与治理吸毒(减少需求)是解决毒品问题的两大抓手,如果说打击毒品犯罪是‘治标’,治理吸毒问题就是‘治本’”。〔61〕胡云腾、方文君:《论毒品犯罪的惩治对策与措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根据《禁毒法》第3条与第31条规定,任何单位以及公民都应当依法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因此,普通公民有不为吸毒人员提供场所等便利的义务,吸毒人员有获得国家帮助戒除毒瘾的权利,容留他人吸毒罪保护法益是国家对毒品消费市场的治理措施。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在于行为妨碍了国家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之教育和治疗措施实施。
抽样案例数据显示,发生在3人之间的“相约吸毒行为”是定罪最多的案件,人数多的通常也不超过6人。如被告人臧某、余某二人分别三次容留对方在本人家中吸毒的行为,分别被法院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拘役4个月与5个月、罚金3000元。〔62〕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2019)湘0902刑初139号判决书。这类案件属于典型的特定吸毒人员“相约吸毒”、相互容留的行为,对这类行为的司法犯罪化欠缺正当性与必要性。从正当性层面分析,集体法益的保护不能轻易放弃相对明确性的要求,集体法益是为了保护个人法益而存在的,应通过嵌入个人法益因素并以此作为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门槛”。〔63〕参见孙国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一位公民吸毒不构成犯罪而应获得国家对其戒除毒瘾的帮助,“相约吸毒行为”仍然属于吸毒关联行为,并没有因为人数的增加而改变行为性质。对于行为人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决定行政拘留,或根据《禁毒法》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同时,对行为人处罚的必要性与被害人的保护必要性是相对存在的,在被害人能够自我保护却疏于自我保护的时候,刑罚权无发动的余地,对行为人也无处罚必要。〔64〕参见[美]道格拉斯·胡萨克:《过罪化及刑法的限制》,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绝大部分“相约吸毒行为”属于特定吸毒人员长期共同吸毒的情形,这是被害人能够对自身健康予以保护而放弃保护的情形,也没有造成吸毒人群的扩大与毒品的扩散,并不值得科以刑罚。总之,须进一步明确限制对“相约吸毒行为”的司法犯罪化,容留他人吸毒罪处罚范围应该是经营性场所直接或间接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毒的、贩毒毒品时容留他人吸毒的、非吸毒人员一次容留多人或多次容留他人吸毒的、多人共同吸毒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七、结语
定罪条件数量化及简单化的侵犯秩序类法益轻刑罪名,在我国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司法过程中,由于具有办案成本与风险低、办案模式可复制性强及定罪率超高的特点,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惩处方针指导下具有明显的司法犯罪化倾向。由此,定罪规则的最大程度扩张与案件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呈现同步。容留他人吸毒罪如此,危险驾驶罪也很可能如此。对此应通过多种方式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通过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与指导性或参考性案例,明确刑法条文涵摄的构成要件具体行为类型,预防及纠正过度司法犯罪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