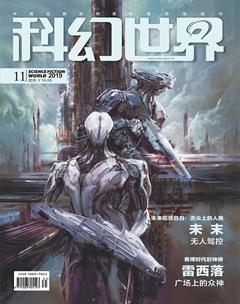我和《科幻世界》的“前世”与“今生”
2019-12-29张静
1985年秋,中国科幻小说在长期受极“左”思潮批判的低迷状态中有所好转,我收到天津新蕾出版社《智慧树》杂志的邀请,参加我国首次科幻小说笔会。
笔会在天津师范大学招待所举办,与会者有著名的科幻作家童恩正、刘兴诗和年轻的科幻新秀吴岩,以及科幻作家董仁威、吴显奎等人。另外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伊、《少年科学》沙孝惠、《智慧树》李群、《科学文艺》(《奇谈》、《科幻世界》的“前生”)的谭楷等资深编辑。笔会后期,肖建亨老师也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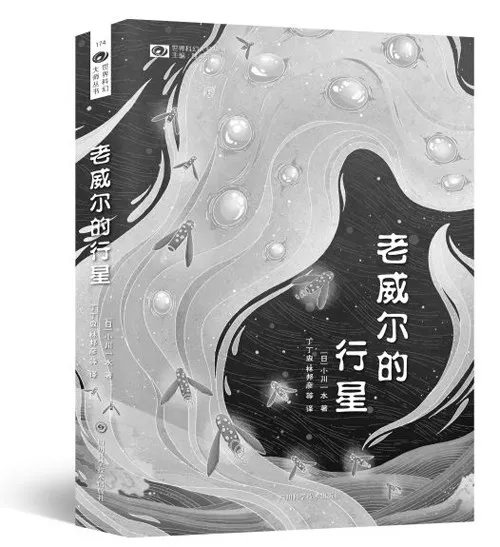
这次笔会之前,也就是从1979年至1983年前后,科幻小说受到过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的无端批判:有的科学家认为科幻小说是“伪科学”;有的文学家则认为科幻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另类”;更有甚者,把科幻小说当作“精神污染”和“毒草”进行打击批判。才华出众、写过《小灵通漫游未来》等脍炙人口作品的科幻作家叶永烈,在受到铺天盖地长期不公正的批判后“挂靴”科幻,改为纪实作家;写过著名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的郑文光则中风病倒。来参加这次科幻笔会的童恩正、刘兴诗、肖建亨可谓是“劫后余生”。
我是1982年应《科幻海洋》编辑部王仙民老师之约,试着写了一个中短篇科幻小说《神秘的声波》给《科幻海洋》的。谁知不久,《科幻海洋》因科幻小说屡受批判被迫停刊,我的那篇科幻小说处女作也如“泥牛入海”,没了音讯。多年后得知,《科幻海洋》停刊时,编辑叶冰如大姐十分认真地将这篇稿子转给了天津的《智慧树》。科幻写作大环境略有好转了,《智慧树》便邀请我参加笔会。
谭楷为人热情真挚,他在笔会上向我这个科幻界无名之辈约稿,我真有些诚惶诚恐,但还是答应了。那时候的《科学文艺》除了发表科幻小说,还发表报告文学、科学诗、科普文章。彼时《智慧树》即将停刊,除了少数少儿科普杂志,《科学文艺》成了国内唯一一家发表科幻小说的刊物。对于这样一本坚持发表科幻小说的刊物,我十分敬佩。
天津笔会结束后,我写了短篇科幻小说《最美的眼睛》,以“晶静”的笔名投寄到《科学文艺》,此后不久,此稿发表在1985年第6期的《科学文艺》上。谭楷在电话中说,他曾将这篇科幻小说稿给著名作家流沙河老师过目,流沙河老师认为小说的幻想虽不算高远,但故事写得很有感情。为此我深受鼓舞。
1986年1月,我的科幻小说《神秘的声波》也在《智慧树》发表,并获得全国首届科幻小说银河奖。为此,我应邀参加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首届银河奖颁奖大会。会议期间我和与会作者一同参观了《科学文艺》编辑部,很高兴又见到了忙碌的谭楷,还见到了办事干练的社长杨潇和沉稳雅静的资深编辑莫树青(莫愁)等人。整个编辑部人员不多,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个个吃苦耐劳,朝气勃勃。《智慧树》即将停刊,《科学文艺》这个人数不多的编辑部独自承载着中国科幻小说生死存亡的重任,虽然艰难,但是他们从容自信,我深受感动。
想象力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是文学艺术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前奏,科幻小说可以丰富人的想象,启迪智慧。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幻小说被更多的人喜爱。我过去没有接触过太多科幻小说,但童年时在上海阅读过许多童话,年轻时还接触过不少俄国和欧美文学作品,觉得科幻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有许多共同之处,于是利用业余时间“爬格子”(那时候我都是用手写稿)陆续在《科幻世界》和《少年科学》发表科幻小说。
1991年,我有幸参加了成都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这次由《科幻世界》主办,以“科幻、和平、友谊”为主旨的国际科幻大会办得红红火火,让我结识了一些科幻界的朋友,也开了眼界。大会期间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我的科幻小说《女娲恋》获三等奖。
从1985年开始到1997年,我先后在《科学文艺》《奇谈》《科幻世界》发表作品有:
1985年第6期《科学文艺》,《最美的眼睛》;
1987年第3期《科学文艺》,报告文学《冰海中国心》,内容写是我国为了在南极大陆建立中山站,一位年轻的中国船长只身一人随澳大利亚“冰鸟号”远航东南极,收集相关航海资料的故事。
1990年第1期,《科学文艺》已经改名为《奇谈》,发表了我的科幻小说《爱的工程》。
1991年《奇谈》更名为《科幻世界》。从更名为《科幻世界》开始,1991年第3期、1992年第3期、1993年第2期、1994第10期,连续发表了我由中国远古神话演绎的科幻小说《女娲恋》《织女恋》《夸父追日》《盘古》。1997年的增刊,发表了我的科幻小说《鸟人阿腾》。其中科幻小说《女娲恋》,获第三届银河奖。
这十多年,我和《科幻世界》的前生、今世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我又应邀参加了北京国际科幻大会,除了见到许多科幻界的老朋友外,还见到了刚调到《科幻世界》编辑部的姚海军,他高高瘦瘦的,但精神饱满。早就听说这个小伙子在东北某林场工作时,手刻蜡印,自费办科幻《星云》小报,受到不少科幻迷欢迎,被杨潇“慧眼识才”调到《科幻世界》。事实证明姚海军确实不负众望,此后为科幻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期间王晋康、吴岩、赵海虹、韩松、星河、凌晨等青年科幻作家也已经成长,他们学历高、视野开阔,作品符合时代的发展,更受年轻读者的欢迎。而这时的我即将“耳顺”之年,在为中国科幻文学后继有人感到无比欣慰的同时,自身深有紧迫感。
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前后,我把主要精力花在少儿科幻小说创作上,先后出版了《张静佳作选》《穿越时空访南极》《神秘的声波》三本科幻小说集,以及长篇少儿科幻小说《沛沛的小白船》《小活宝碧海探奇》《寻父探险记》。在科幻小说集里,收录了不少我在《科学文艺》和《科幻世界》上发表的作品。再后来,我又用六七年的时间出版了一本32万字的长篇小说《眷恋蓝土》,反映我国三代海洋人,为实现“查清中国海、挺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努力奋进的历程。
不知不觉,我已到了耄耋之年,心里依旧牵挂《科幻世界》。2017年第5期《科幻世界》少年版发表了我的科幻小说《隐形小英雄》,并于同年参加了成都国际科幻大会期间举办的《科幻世界》少儿版笔会,见到了编辑部黄蓝主任,以及于娟、柳彤等编辑,看到他们辛苦忙碌的样子,仿佛依稀又见到三十多年前《科学文艺》老编辑们的身影。他们继承了原先《科学文艺》和《科幻世界》的老传统:吃苦耐劳,朝气勃勃,使我感到十分亲切。2018年第10期《科幻世界》少年版,在编辑毛霏老师的帮助下,又发表了我经过整理的科幻小说《两个小祖宗》。这一年我八十岁了,哈,从中年到老年,我和《科幻世界》真的难解难分。
感恩《科幻世界》,她是我创作科幻文学起步、成长的园地,同时也让我见证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成长历程。祝福《科幻世界》越办越好。
——谨以此文敬贺《科幻世界》创刊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