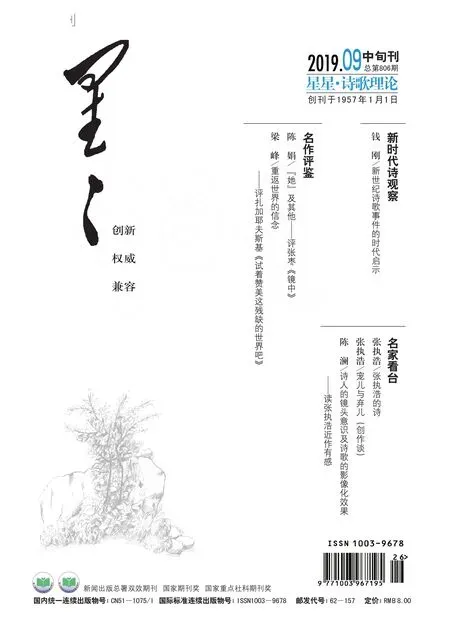桑多镇:一个不断自我繁殖的小世界
2019-12-29扎西才让
■ 扎西才让
窗外大雨滂沱,室内,却是一个相对静寂的世界。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看到我用不同文体表现过的桑多镇在暴雨之后渐渐安静下来,重新呈现出清晰的容貌。
现实中的桑多镇,有另外的名字。起初,我用诗歌来表现她时,她叫羚城。我用散文来呈现她时,她有一个藏族名字——黑措。后来,我用小说来完善她时,她是甘南这块土地上许多小镇(譬如拉卜楞镇、扎古录镇、柳林镇、城关镇)的综合,她的身上,有着其他小镇的影子、故事甚至灵魂。
二十年前,我就尝试用诗歌来呈现这个小镇。我在地方志里了解到:在建镇之前的可追溯的岁月里,她曾经是一片湿地,千百只羚羊和当地零星的土著在此繁衍生息。民间,则流传着一则更久远的传说:“情窦初开的罗刹女,在荒凉的高原行走,遇到了来自普陀山的猴子。他们结合了,把后代悄悄地生在蛮荒的雪域,从此,人面猴身的族人越来越多,形成了部落,再也不愿跟随父母离开故土。后来,因为兄弟之间的雠仇,祖先们走出山谷,牵着神骏,举着旌旗,背着羽箭和长矛,穿越了数不清的白昼和黑夜,步行了几千里的非常路,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土地,在宗师的指引下,休憩于桑多河畔。再后来,大德们晒在阳光下的经卷,被时间翻到第一百零八页,就被风给吹乱了,只剩下纸上的明晃晃的下午。河谷两岸肥沃土地上招惹禽兽的五谷,也在一茬又一茬的生长过程中,成为佳酿,引出了人世间数不清的欢愉。”
这样的传说,一经阅读,就让人陷于沉迷。由此,也生发了我用诗歌来还原桑多人的形貌、生活、灵魂与精神的愿望和勇气,以一腔热血,来勾勒、建造、装饰我桑多河畔的藏地小镇。
我坚持用诗性的文字,来抒写桑多镇的历史:桑多人的祖先们来了之后,桑多河畔的湿地渐渐变成干地。但这不影响先人们想发展的欲望。于是,羚羊们只好选择给人类让位,它们集体迁徙到了另外的地方。羚羊离去不久,祖先们还不曾在新的领地繁衍生息到三辈人,又一批更有破坏力和创造力的垦荒者也来了。他们是躲避战争的流亡者、商人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的骑着白马,有的扛着旗帜,有的什么也没带,只有着强壮而野蛮的躯体。他们与桑多人结婚生子,建造了寺院和民居。哦,天哪,小镇开始了自己的不得不记录的历史。除了伟大的文字担任起这个伟大的使命,小镇上空,蓝天也担任起书记官的角色,它像块巨大的幕布,总是在人类打瞌睡的时候,把时间老人录下来的场景悄悄播放。那宽大深邃的布景上,湖泊像星星那样闪烁。人,也成为神仙,出没于巍峨的宫殿,又集体消失在海市蜃楼里,那里仿佛就是另一个天界小镇。桑多镇的人们一边劳作,一边繁殖,有时也抬头打量深蓝色的天幕,就突然觉得人类的需求过于强势,想收敛收敛,但也明白那与生俱来的贪欲,总是无法消失殆尽。以至于在祖辈带领下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来苦苦追求理想的天堂——香巴拉,其实早就像传说中的魔镜,被神秘之手悄然打开了。但这美好的事实,却无人注意,也无人知晓。
显然易见,桑多镇的历史,就是桑多人的历史。个体的命运,必然组成一个族群的命运。我在抒写桑多镇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爱上这里的人:寻找神灵的患者,教训孩子的老人,尚未顿悟的高僧,失败的酒鬼,逃逸的画家,凋零的诗人……我沉浸在甘南文学版图上的桑多世界,很多时候,眼里、心里只有“他”“她”“你”“他们”“你们”和“我们”,而忘记了“我”才是抒情的主体。举个例子:我爱着笔下的一个清雅秀丽的女人——扎西吉的母亲,她在小屋里阅读,窗外是晴朗的春日,一座白塔被蓝天衬托得越发圣洁。阳光还没照进玻璃窗,就使精美的茶具,染上了温暖的色调。她的镶着黄色丝绸宽边的红色袍子,也层叠出难以言说的明与暗。旁边的铁皮炉子上,铜壶的鸟嘴里冒出缕缕热气。她的身后,一尊姺足袒胸的度母在画中静坐,那金色的线条有着柔和的气息。我以诗人扎西次力——扎西吉的未婚夫的身份,来写我对这个女人的热爱与崇敬:“另一个世界的光芒尚未溢出画面,佛国的慈悲和爱,就涌满了这间简陋的屋子。”
桑多镇的边界,就在这样的不断抒写中,加快了扩展的速度,形成一个不断自我繁殖的小世界。我一直以诗性的文字完善着我的文学根据地——桑多镇,并且以此为使命,不仅写出我对这片土地上的桑多人的爱与恨,也试图写出我对他们的理解、赞颂、同情与怜悯。
不注重我的小得失和小情绪,只关注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坚韧挺拔,唯有这样的写作才有意义。这样的抉择,使我想起一个与我有着相同追求的特立独行的甘南画家,他用铁丝般生硬而杂乱的笔触,一遍又一遍地勾画一个颓废的中年男子:奇怪的头型,模糊的面孔,还有那仿佛在接受审查时的敌意的姿势。这个画中的男子,肯定已经发现并暴露了人性的秘密,所以才眼神浑浊,鼻子塌陷,嘴唇干裂,嘴角下滑的弧线,也是那么软弱无力。当酒色财气蜂拥而至,这人接受诱惑并自甘沉沦。这沉沦到了怎样的境地?只要仔细观察,就能从其深渊般的眼眸里,捕捉到我入地狱的大势。当我们也从其深渊里挣脱出来,才清醒过来:大家不过是在桑多镇文化站里观看一幅油画,而创作出这幅作品的画家,早就离开了甘南。但很显然,他把痛苦在这幅肖像画里留了下来,等待着欣赏者来默默承受。一旦我们都深陷进他设置的地狱,就只能指望他的出现。当我们争先恐后祈祷之际,他或许就会来解脱我们。
只要诗人和作家存在,这藏地甘南的动人故事和美妙情感,还将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作为作者与读者,我们在回顾往昔之际,总是在不断的惊讶中无数次地被众多的故事所打动。这样一来,我们的写作,就真的有了长远的意义。
在被暴雨清洗过的桑多镇,在这样的雨后,倚窗而立的我,越来越觉得以诗性的文字来写桑多,对桑多人、作者本人和众多读者来说,都将是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事,当然也就值得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