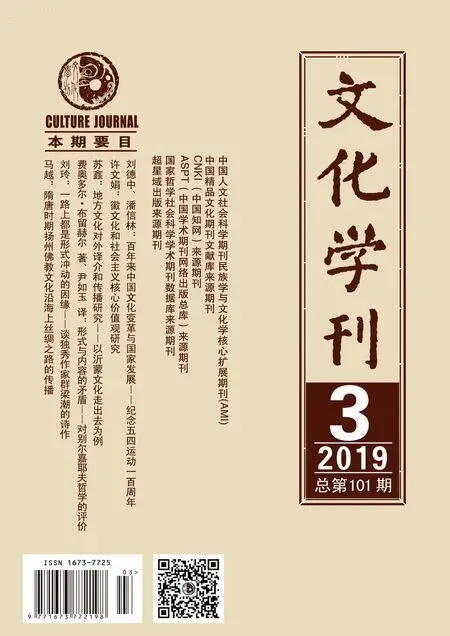隋唐时期扬州佛教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2019-12-28马越
马 越
中国古代有两条丝绸之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过世界,对全球文明和经贸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就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而言,古代多呈现在宗教领域。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公元前六世纪前后起源于印度。佛教从印度经陆路传入中国,而经海路到来的僧侣则使佛教在中国的地位更加牢固,并由此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南海北路的贯通,促生了一个佛教文化循环游历的大圆圈。当这个圆圈转动的速度骤然加快时,往来僧侣明显增多。在这个佛教文化共生的循环圈里,长江下游南北水运及海路交通大动脉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珠——扬州。这座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古港,不仅成为隋唐经济文化体系中的翘楚,更成为佛教发展的重镇,在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隋唐扬州佛教文化传播的经济与交通资本
7世纪以后,隋代的重新统一以及唐代的崛起,令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区,获得了比北方黄河流域更迅猛的发展,南方各天然港口推动的海外贸易重塑了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关系,商人们的注意力从横跨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自7世纪中叶起达到了中国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峰。当人口与技术、财富与智慧在扬州迅猛膨胀时,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物产推广等全方位的人类活动就此生根发芽。
(一)扬州古港的水运经济枢纽位置
扬州位于长江入海口北侧,兼有海、河港口的特质,为南北水运交通要冲,唐代成为发达的国家贸易港。除去先天地理条件,扬州港埠事业的开端于鲁哀公九年(前486)邗沟的开凿。隋代以前,受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扬州城的范围基本局限在蜀岗东南缘。随着隋代运河的大规模开凿,扬州迅速发展起来。《隋书》记载,开皇七年(587)夏四月,隋文帝为征伐南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1]。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东南经射阳湖接邗沟,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榖、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2]。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谷、洛水到黄河,又从板渚(河南汜县东北)引黄河水通淮河。大业六年(610)冬十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自此,南北水运干线大为缩短,扬州作为水运经济枢纽尽显优势。在这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上,扬州位居长江与江南、江北大运河的交汇点,也是南粮北运的重要中转站,为扬州城跃升为唐代仅次于两京的经济文化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国家幅员广大,东南临海,海岸线绵长。与海岸相关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和出发处。“唐时扬州东距海却只有五百里有奇,东南距海更近,才四百里挂零。当时海岸在盐城县东。唐代后期李承曾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置堰地方实在盐城县。北宋时范仲淹又踵其故绩,于泰州城东修捍海堰。可知唐代扬州距海确不甚远。”[4]因为距海口近,船舶可以直达城下,所以扬州能够成为对外贸易口岸。彼时苏南地区包括上海港尚未发育成熟,长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扬州。
民国二十九年(1940),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在其重要论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揭示出扬州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
第一,国内贸易发达。“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水运非常便利,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5]
第二,国际贸易发达。其一,由海外来华的船舶,可以直驶扬州;其二,由南海来华的外国商船,除驶往广州及福建外,又向北直驶扬州;其三,南洋各国的商船虽以驶往广州贸易为多,但这些外货之运销于北方各消费地,须先沿着北江、赣江及长江等水道北上,集中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扬州,然后才能利用运河的水路交通线,分配于北方各地。因此,扬州不但有南方盐、茶、药材各货,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于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扬州本地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相应而生。
第三,扬州地处江淮之间的长江三角洲上,北边比邻黄河下游的中原大平原,南边接壤吴、越平原。自然条件的优越性,行政区域的重要性,加之自身优越的地理交通位置,大量外来人口蜂拥而至。由海道来华的外国人,也常常把扬州当作海洋航运中点或者侨郡。隋代江都一郡共有十一万户,为这一地区人口最多者。后来的昇州(治所南京)、常州(治所常州)、苏州(治所苏州)当时的人户也就在两万上下[6]。在人口的刺激下,扬州经济快速发展,反过来更多地吸引了各地的能人巧匠前来,为建设扬州添砖加瓦。
(二)交通航道促进扬州佛教的发展
公元前1世纪,佛教自印度传入伊朗以及中亚各地,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晋以后,经由南洋群岛或中南半岛的交趾、扶南,抵达广州、扬州、徐州、青岛等地的海路传法通道也已经形成。隋唐时期,佛教在亚洲东部大陆上蓬勃发展起来。隋唐佛教以国家统一和空前富强为社会背景,无论在译经、著述、思想学说还是寺院规模方面,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此景象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统一社会在文化上的需要,更是南北运河经济发展后衍生出的结果。
建德六年(577),北周武帝以佛教“废财伤民”“悖逆不孝”为由,宣布毁法。隋代的统一,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战乱和分裂的同时,通过重新崇佛收拢人心。隋文帝在位二十年,共度僧尼23万人,立寺3 792所,写经46藏,13 286卷,治故经3 853部,造像106 560躯[7]。和父亲杨坚采取的策略一样,晋王杨广在扬州任职期间,除了息武兴文,汇编关于礼仪巨著《江都集礼》,团结江南文人,更以发展佛教的方式,加强南北文化的交流。据南宋天台宗僧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及僧士衡《天台九祖传》所记,高祖开皇十三年(593),杨广在扬州设千僧会,从天台宗的四祖智顗受菩萨戒。
此前近三个世纪里,隔江的建康(南京)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沿着丝绸之路来到的异国僧侣先后奔赴那里。随着南陈的覆灭,隋炀帝杨广着手另建一都替代原本的建康。最终他选择了长江北岸的扬州,这一选择直至终唐之世,都令扬州在淮南地区居于政治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显要位置,选择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交通航道的需要。
杨广执政后的第一年(605),便将扬州改名为江都郡,同时颁布了全面开凿运河的诏书。运河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政府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运河网络把长江流域与黄河及其北方地区连接起来,从而能够用南方的粮食和物资供养庞大的中央系统,并给北方汴京提供战略物资。至唐朝,政府继续在江北运河的整治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保证了南北大运河的全线沟通。安史之乱之后,大运河更从有益的补充手段变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命线。
运河畅通之后,运河带来的经济利益令生活在扬州的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上层人士愿意把大量土地和财富施舍给寺院,并经常把自己的宅院用于做佛事,宗教生活成了扬州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鉴真东渡弘法,圆仁跨海求经,都与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密切相关。佛教文化从扬州沿着两条线路向外传播出去 :一路是通过运河沿运河沿线传播,另一路是借助海路向海外传播。交通航道的开拓扩展了扬州佛教的发展与传播空间,交通航道带来的经济繁荣更令扬州成为新兴的东亚佛教世界的重镇。
二、扬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港口
扬州是佛教在中土传播较早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无论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就传播到了扬州地域,扎根成长。同时,扬州的文化氛围开放而兼容,这一点与扬州早年接受北人南下以及成为侨郡的经历有关。唐代开放的对外政策为扬州佛教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繁荣的经济文化令扬州佛教形成兼容并蓄、乐于交流的特质。扬州僧人可以西行北上拜师求法,还可以面向海外。同时,这里也不乏来自他乡异国的僧侣。唐代扬州不仅是连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更成为佛教东渐的起始港。
(一)隋唐僧侣海路求法的中转港
汉僧求法除了唐代的玄奘,更早广游西土的是东晋高僧法显。法显凭信风泛舶,求法东归,被视为海路求法的始祖。后秦弘始元年(399),法显一行4人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寻找佛法。十二年来,他的足迹穿越三十多个国家。为了确保来之不易的戒律和经本能顺利带回国内,踏上归途的法显放弃陆路而选择海路。义熙七年(411)秋,法显乘船经由印度半岛顶端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途经耶婆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次年夏抵达山东半岛的青州(青岛)长广郡牢山(崂山)南岸。而后法显往南到扬州,最后到达晋都建康(南京),在当时的佛教翻译中心道场寺同佛驮跋陀罗等共同翻译经律诸书。义熙十四年(418),法显在道场寺撰写完《佛国记》,记述了自己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史的重要文献。此事件对于扬州而言也是值得纪念的,扬州港的海外交通史因此事追溯到了东晋时期。
法显之后,许多僧人沿着他的足迹,陆上西行去印度取经,从海上东归回国,如西凉僧人智俨,高昌僧人道普,走的都是同样的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多了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的内容。
1921年,梁启超在《改造》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论文《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时改题名为《中国印度之交通》。文中整理出一张《西行求法古德表》,统计了从三国末年到唐代中叶约五百年间,通过陆路、海路前往印度求法的169位僧人的名单(佚名者82人)。梁启超对于中印间交通路线进行了整理。届时有六条路线通印度 :海路、西域渴槃陀路、西域于阗罽宾路、西域天山路、吐蕃尼波罗路及滇缅路。海路亦有三条路线 :从广州放洋,以及由安南或者青岛放洋。文中总结 :“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放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8]此语间接证明了隋唐以来,随着西域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广州专设市舶司,海路代替陆路成为中印之间僧侣往来的主要路线。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纪录,公元641—689年,共有60位高僧西行求法,其中从海路到印度者有38位,这个数字与梁启超整理的37人数字相差无几。在这37位海路西行求法僧中,长江以北从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河北和山东出发的有22位,长江以南从四川、越南、广西、湖南、广州出发的有15位。
长江以北的僧人要走海路,最佳捷径是走水运,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遵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9]如此一来,扬州便是南北交通最可能途经之地。史载,唐代求法译经僧义净与弟子善行自山东经扬州南下广州,搭乘波斯舶,西行取经。至于法显走海路在青岛上岸,南下也是先到扬州,再至建康。此外,海外僧海路求法也有过扬州北上的情况。唐龙朔二年(662),38岁的新罗僧义湘大师搭上唐使者的船舶,取海路入唐,“初止扬州,州将刘至仁请留衙内,供养丰瞻”[10]。离开扬州后,再乘商船北上至新罗僧人聚集的山东登州。唐贞元十九年(803),日本僧空海跟随桓武朝遣唐使舶第一舶漂流至福建长溪(今霞浦)赤岸登陆,经苏州、扬州北上,十二月到达长安。
(二)扬州沿海丝建立起的中日、中朝佛教关系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隋唐时期由北而南兴起了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沿海港口城市,往来海上丝绸之路求法弘法的僧侣从这里启程或登陆。作为新罗使节、日本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登陆、经停的主要城市,扬州与日、朝建立起独有而稳固的佛教关系。
1.鉴真东渡传播文化
佛学家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论及“隋唐佛教之传布”时写道 :“中国佛法传布,最重要者为日本。”[11]自隋至唐末,日本敕遣入华使十六次,两次直接在扬州登陆,随使求学巡礼的僧人非常多,日本国内的佛寺建筑,僧伽组织,均取法唐制。及至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法,日本僧侣的法制形态,从训练、教育到受戒得度才得以有了正式完整的体系。
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鉴真出生于扬州江阳县。《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江阳,贞观十八年分江都县置,在郭下,与江都分理”。可知唐时江阳县是扬州的附郭。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扬州大云寺从律宗高僧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中宗景龙元年(707)至玄宗开元元年(713),鉴真前往洛阳、长安学习佛法,学成后回家乡扬州,在江淮一带弘扬佛法,取得了极大的声誉与成就。在扬期间,“前后度人、授戒,略计过四万有余”,“讲授之闲,造立寺舍,供养十方众僧,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12]。因此,在日本僧荣叡、普照来到扬州发出邀请之前,鉴真在江淮一带的佛教界已经成为戒律学高僧以及佛界领袖人物。
接受日本僧人祈请的鉴真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其中,两次失败是由于自然的险阻,三次失败是由于人为的阻扰。虽然五次东渡漫长而悲壮,却让鉴真在七年里沿海岸线游历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海南七省,水路往返一万余里,“所经州县,立坛授戒,无空过着”[13],成就了扬州佛教文化向南的传布。尤其当鉴真到达唐代四大都督府之一的广州,不仅受到都督卢奂亲率僧俗的欢迎,更接触到大量循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婆罗门、波斯、昆仑、师子国和大石国等僧侣。据传,昆仑国人军法力就在广州加入鉴真东渡的僧侣队伍,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之一。
鉴真第六次东渡搭乘了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归国航船。唐天宝十二载(753)十二月二十日,鉴真一行所乘的第二舟驶达冲绳(今日本阿儿奈波岛)。此后,航船又北航到达萨摩川边郡的秋目(今日本阿多郡秋妻屋浦),登陆上岸。十二月二十六日,僧人延庆将鉴真一行人引入太宰府(今日本福冈)。太上皇圣武和天皇孝谦女帝专门为鉴真颁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14],更颁授“传灯大法师”名位。鉴真带去了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工匠一起,按唐寺院法式,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作为佛教中国化后的此次东传,传播的不仅是佛、法、僧,还包括建筑、绘画、雕刻、翻译、音乐、舞蹈及日常生活习俗,鉴真大和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隋唐时期的中国,就佛教而言,输出的力度远远大过传入,其中,扬州佛教领袖人物鉴真功不可没。鉴真东渡弘法成为佛教中国本土化后二次输出的典范。
2.日僧圆仁跨海求经
鉴真东渡之后,跨海求经的学问僧众多,最为著名的有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和宗叡,被称为“入唐八大家”。仁和天皇承和元年(834)正月,日本任命了以藤原常嗣为大使、小野篁为副使的遣唐使团,随行请益僧圆仁“携带延历寺未决的疑义三十条入唐,请求唐朝高僧给予解释”[15]。此次遣唐使中的学问僧人才济济,圆行、圆仁、常晓、义澄、真济等都在其中。唐开成三年(838)七月初二,船队抵达扬州海陵县,再向西,经江阳县禅智寺前桥进入扬州罗城,寄住开元寺。
在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奏报朝廷后,只准大使等少数人入长安,其他人原地待命。留在扬州的常晓进入栖灵寺学习密宗,次年又谒华林寺大德问学三论宗义。圆仁则在开元寺求法,跟随宗叡学习梵书,又跟从全雅受灌顶礼及金刚界等诸尊仪轨等大法。可是,他要求巡礼天台山的申请却未被批准,只得于开成四年(839)二月和常晓一道随遣唐使从扬州踏上归途。
圆仁不甘心就此回国,途中伺机逃脱,常晓则携带典籍31部36卷回到日本。开成五年(840),滞留中国的圆仁又向官府申请巡礼五台圣地,终获批准。同年四月,圆仁率弟子从登州出发,经山东青州、河北德州等地,抵达五台山。他们巡礼了五台山各名刹灵迹,参谒大华严寺志远和尚等名僧,抄录了天台典籍34部。八月,一行人抵唐都长安,居资兴寺,又向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义真等高僧学习密法,跟从青龙寺法润和尚学习金刚戒。
圆仁在唐期间恰逢唐武宗实行排佛,毁寺驱僧的政策。唐会昌五年(845),圆仁被命还俗,离开长安。宣宗大中元年(847)六月廿八日,圆仁再到扬州。在扬州停留三四天,最终携佛教经疏、仪轨559卷(包括在扬州求得的128部198卷[16])以及法物多种(包括在扬州求得的胎藏金刚两部、曼荼罗诸尊坛样、高僧真影及舍利二十一种[17])自山东登州赤山浦渡海回国。日齐衡元年(854),圆仁受封为第三代天台座主,撰写了《苏悉地经略疏》《显扬大戒论》等著述近百部。日贞观六年(864),71岁的圆仁在京都延历寺圆寂。两年后,日本清和天皇赐圆仁“慈觉大师”谥号。
圆仁之所以在中日佛教史上名垂不朽,也因为他留下了一本游历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史料。此书卷一记载了圆仁入唐的第一站扬州,书中生动描述了扬州城的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寺院法会、出产饮食、经济交通及民间习俗等,不仅成为研究唐代扬州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成为扬州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3.新罗崔致远佛学化
隋唐时期也是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而后新罗统一的时期。彼时作为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受到了近邻各国的学习和仿效。前文提到,新罗僧义湘大师入唐学法,事实上三国末年以及新罗统一后,入华僧人数比其他各个历史时期的入华僧人数的总和还多。不仅仅是僧侣,前来学习的留唐学生更是不绝于途,被称为“东国儒宗”的崔致远就是之中的佼佼者。
崔致远12岁随商船自新罗入唐,在东都洛阳国子监接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得中“宾贡进士”。广明元年(880),崔致远来到扬州,投入高骈淮南幕府,先后被委以书记、都统巡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职。中和四年(884)秋,以淮南入新罗兼送诏书国信等使身份回国。崔致远自称“儒门末学”,归国后积极传播汉文化,完成了记载有扬州文化大量珍贵史料的二十卷《桂苑笔耕集》,献给新罗宪康王。《桂苑笔耕集》带有浓郁的扬州地方色彩,共收入崔致远在淮南幕府时候的公私应酬文章310篇、诗篇60首。
崔致远在扬州为官四年,不仅所写《檄黄巢书》天下传颂,更参与乾符六年(879)前后在扬州修筑唐罗城、羊马城的工程。此时的唐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而扬州却商贸活跃,生活富足,佛音悦耳,僧侣云集。《桂苑笔耕集》里使用了“十地”“火宅”“演迦叶之真宗”等佛教用语,集内涉及佛教的有七篇,数量虽不多,却能够反映出崔致远在扬州接触到了各种佛教宗派,并对于佛教有了初步认识的思想。如在《天王院斋词》中,崔致远代高骈表达出希翼借助佛的引领与庇佑,在乱世之中护持统治、教化众生的思想。在《求化修大云寺疏》里,崔致远借重修鉴真和尚出家祖庭,分析了佛教的功用 :“其如妙旨则暗裨玄化,微言则广谕凡流,开张劝善之门,解摘执迷之网……”[18]文中更留下了扬州名刹大云寺、禅智寺的宝贵史料。
扬州是崔致远旅居唐朝十六年中成就最为辉煌的地方,在这个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和优越交通条件的城市,其佛教的发展对内扩散到整个江淮地区,覆盖中国东南,对外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当地更是寺院众多,海内外僧侣络绎。浸润在这种环境中的崔致远回国后以儒佛同根的观点精研佛法,广交高僧,为新罗王室、寺庙撰写了大量佛事文书,包括最著名的《四山碑铭》,最终“带家隐加耶山海印寺,与母兄浮图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偃仰以终老焉”[19]。作为正宗的儒者,崔致远的佛学化为扬州佛教东渐提供了另一种渠道。
三、结语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信仰实践,又是一种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扬州佛教文化的传播建立在这座城市经济繁荣与交通航道便利的基础上。作为隋唐时期最繁华的南北水运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枢纽,扬州财力的雄厚、物质的丰腴以及文化的发达,均是全国其他城市望尘莫及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才会产生,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单纯的贸易之路,它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交流之路,这种持续千年的交流对于沿岸各国各地的影响是至深的。仅扬州一地就留下了多种佛教史迹,如大明寺、鉴真纪念堂、惠照寺石塔,它们见证了经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也为世界宗教传播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