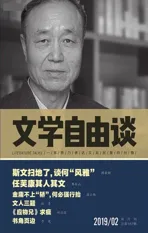对经典小说作品的期许
2019-12-27刘金祥
□刘金祥
在我国文学发展漫长而辉煌的历程中,诗、词、赋、曲、散文和小说,每一种文体都曾有其勃发时期和鼎盛年代,都曾显示出一种文体的优越性、不可替代性和无法超越性,但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些璀璨炫目的文体似乎风光不再、日渐式微。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文坛涌现出《尘埃落定》(阿来)、《长恨歌》(王安忆)、《历史的天空》(徐贵祥)、《暗算》(麦加)、《秦腔》(贾平凹)、《生命册》(李佩甫)、《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黄雀记》(苏童)、《沧浪之水》(阎真)、《江南三部曲》(格非)、《繁花》(金宇澄)、《花腔》(李洱)、《你在高原》(张炜)、《推拿》(毕飞宇)等一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但令人忧戚沮丧且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兴盛时代,正在凄楚地走向衰落甚至悲怆地趋于终结。与之相伴,葆有经典属性的小说作品越来越显得凤毛麟角,包括上述获奖作品在内的诸多长篇小说,并未进入多数国人的阅读视野,难以成为被读者接受且流布广泛的传世精品。鉴于小说精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创作现状堪忧、前景黯淡,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境地。由于近年来很多小说创作涉猎题材领域狭窄、跨越时空幅度仄小、状绘社会心理轻淡、触及人本人性浅薄、运用表现手法粗糙,以致于文艺理论界无法从审美角度尤其是从叙事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评判和言说。许多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不得不被迫借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语汇和范式(如文化、道德、启蒙、批判、民主、科学、权利、反抗……),将文艺理论这个原本规范而严肃的学科的身份,改造得十分模糊、可疑和乖谬。也就是说,文艺理论界所关注和谈论的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都无法以具体细微的“文学形式”加以切进和介入,而往往只能不顾逻辑地直奔主题。这显然是跨界越位地闯入了文化史范畴和思想史界域。在2014年召开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一些文艺理论专家学者呼吁,应对文学表现形式给予更多关注;正如会议纪要所指出:“文学把对于过去的纷乱的记忆塑造成某种特定的形式。文学形式是令人信服的,文学形式又是令人难以忘却的,文学之所以具有某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由于它不同于历史和新闻报道。”但是,面对迅疾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和加速进行的国内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这一时代大势,会议纪要中所表述的避重就轻式的观点,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整体研究而言,显然不合时宜。
在加速度与世界文化接轨融合、高频率向国外传播输送中国文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坦率地直言:在当代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继莫言的《蛙》《檀香刑》《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以及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等少数文学作品之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小说经典作品还比较匮乏,比较稀少!尽管文学发展史表明,一百年没有经典作品绝非怪事,尽管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饶有兴致的国人只能阅读传统经典作品。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小说界的表现的确差强人意:一方面是一些传统长篇小说的审美价值遭到强烈质疑甚至极大否定,另一方面则是新的审美标准迟迟没有诞生。这种现状,的确给广大读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带来深深忧虑。于是,一些业内人士面向故纸堆“翻箱倒柜”、寻经问史,深入到现代文学史中,寻找优秀长篇作品并藉此开掘和提炼经典成分:先是集中抉发沈从文、钱钟书、汪曾祺等人作品的美学价值,接着又细致梳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创作轨迹,随后又过分夸大和肆意抬高张爱玲、徐纡、无名氏等作家作品的艺术地位和审美品位。
今日中国小说界之所以陷入低俗、芜杂和迷乱的局面,与当代作家缺少小说精品意识乃至经典观念密不可分,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中国小说创作自身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滑坡、精神危机、价值迷失在当代文学中的表征。经典小说作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审美传统和道德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一位作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在断裂的过去和将来之间,依靠自己的社会判断力、历史洞察力和精神表达力,创作出展示社会风貌、修补文化裂痕、增强读者价值认知的小说作品,无论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抑或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些经典小说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人性的本质诉求,而且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心理和愿望,从而成为被中外读者争相传阅的旷世经典。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传世之作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创作主体苦心孤诣、充分释放内宇宙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小说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2018年以来,我国当代作家们推出了《考工记》(王安忆)、《重新生活》(张平)、《天黑得很慢》(周大新)、《云中记》(阿来)、《牵风记》(徐怀中)、《候鸟的勇敢》(迟子建)、《黄冈秘卷》(刘醒龙)、《幸存者》(陆天明)、《风声(2018版)》(麦家)、《主角》(陈彦)、《人世间》(梁晓声)、《修改过程》(韩少功)、《穹庐》(肖亦农)、《北归记》(宗璞)、《太阳升起》(彭荆风)、《刻骨铭心》(叶兆言)、《天上有太阳》(杜斌)等一批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作品在变动弗居、缤纷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通过题材的深度开掘与多种表现方式的运用,展现出日益丰富的时代样貌,彰显出当代作家认识时代与解读时代的能力有所提升。无论是艺术表现还是内容架构,都呈现了不同的文学特质,尤其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立体刻画,状摹出人民与时代的精神风貌,勾勒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人物的命运沉浮,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出人类精神世界深处的幽暗与光芒。但从人类精神层面与艺术自觉高度来衡量,这些小说与前文所提的个别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并无质的区别,即作品依然缺乏传达人文精神的自觉和彰显价值理性的自信,距离“代表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的经典作品,相去甚远。
也许正是由于经典小说作品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证明和文明符号,是文学创作的引擎与标杆,所以,现实中一些学者和读者仍旧在孜孜寻找小说精品、殷殷期盼经典小说,对经典小说作品依然怀揣着莫大期许和种种幻想。事实上,在西方后当代文学主流语境中,所有传统经典都被视作一种话语权力,成为被理论界所解构所颠覆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这颇像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一概加以否定和摒弃,但本质上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几千年来磨砺出来的“经典”,顷刻间瓦解损毁得体无完肤,但五四的先驱者们反传统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吃人的历史”“吃人的礼教”,意欲将没有人之地位的“沙聚之邦”变成“人国”(鲁迅语)。就在他们高擎并舞动着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时,西方反传统的非理性思潮也风起云涌,呈狂飙突进之势。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人对传统经典的破坏更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人的主体就是一种假象,创作主体一旦死亡,小说作品即失去确定的意义,读者阅读小说文本无非是创造出无限多的、没有同一客观标准的各种意义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解构思潮,对我国小说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种知识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的问题,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艺术消亡与否的问题。但从总体而言,现代西方社会是有经典小说而消解之否弃之,当代中国文学界是无经典而求经典却不得之,二者走势截然相反。更何况,当代西方文学与鲁迅先生当年“别求新声于异邦”时的情形,早已是南辕北辙了。
经典小说作品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统摄作用,正是那些彪炳史册、熠熠生辉的小说经典,引导着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走向。当代中国作家在强大的商业逻辑推动下,其文学创作几乎全部纳入市场机制,独立的精神空间基本陷落。当权力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省反思也被置换成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顾准等已作古之人。因此,看清当代部分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孱弱和文化信念的流失淡漠,也就找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缺少经典作品的内在因由。面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应从当代文学批评入手,强化两项工作:一是在树立小说创作正确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注重汉语文学批评中审美分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二是在维护市场经济中“文学场”的生成功能的基础上,对更加年轻一代作家进行正向引导与及时推介,努力培植小说经典作品生成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土壤。
《鲁迅新观察》
张映勤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这是一部研究鲁迅的学术随笔集。作者聚数年之功,在真实可信的史料上,力图以新的视角,平实的语言走近真实的鲁迅,为我们还原了一位真实丰满的鲁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