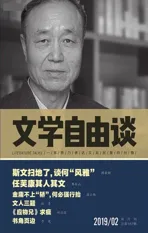书角页边
2019-12-27□李更
□李 更
一
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早期的文学储备,很多来自于“文革”时期的诗歌、小说,准确地说,来自于那个特殊时期的标志性作家——浩然。
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自我矮化?没有,我一直没有改口,到了今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我的文学营养非常完善、健康。
我现在还经常随手翻阅《艳阳天》《金光大道》。有不少人攻击路遥,就是说他的写作手法落伍,类同于浩然,甚至“文革”前十七年文学。我不这么看。现在再去看浩然,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是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是一个不容易超越的高峰。
首先,他创造了自鲁迅以来第二个系列性类型化文学人物。研究近当代文学多年,我发现,那么多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创造出什么类型化人物,也没有为中国民族语言的发展提供新的词汇——要知道,作家有义务创造,或者从民间口语中提炼语汇去丰富民族语言的宝库。而除了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华威先生》,从鲁迅到浩然,这方面几乎就是个空白,直到出现“弯弯绕”“滚刀肉”“马小辫”“高大泉”——这些不仅是一个个可以和实际生活对号入座的鲜活人物,还成为市井社会的流行词。
最近读浩然,发现他的小说居然大有深意,埋了地雷。两个农户在土改时分了地主家的骡马大车,一个拿了骡子,一个拿了大车,两家一直为此矛盾不断,他们必须合作,否则都不能用,但是合作又老是摆不平,都认为自己吃亏了。于是又来找地主评理,要求地主主持正义帮自己说话。是不是黑色幽默?先锋小说吧?浩然没有写地主的内心活动,却是写了村支书面对冲突,批斗地主挑拨离间,是阶级敌人又在搞破坏。按照今天网络上的说法,真是“活久见”。
我一边看,一边想,其实可以把浩然小说按照现在的观点重新写一遍。如果是我写,我可以把那些人物写得非常搞笑。
在国际美术界,改写与恶搞一直是波普艺术最时髦的追求,他们叫做“向大师致敬”。最近几年,国际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几乎都是这样的当代艺术作品创造的。在中国,其实也早就有了,比如黄宾虹之于“四王”,李可染之于黄宾虹,张大千之于石涛,齐白石之于吴昌硕,崔子范、李苦禅之于齐白石。
二
每次坐飞机,我会习惯性地翻阅那些精美的航空画册,上面有大量奢侈品广告,引导富人的消费。当然包括花园洋房和别墅,经常出现的广告词让人想到一个自杀了三十年的诗人海子——他在自己二十五岁生日过后两天卧轨山海关,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其实,那个时间我在广东一家报社做“民工记者”,也过得非常沮丧。当地新闻业很多人是不在编的临时工,和其他行业的农民工一样。那时没有同工同酬,临时工收入至少比有编制的正式工少一半,而且活儿还多一倍。我们的报纸是对开四版,经常是四个版面都有我写的消息、通讯、专访。
最近,有家刊物介绍我的字画,提到我的简历时,说我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章。这引起了别人的质疑。那个简历不是我写的(以前我也曾经热衷于编写自己的简历,总希望有朝一日用得上,后来却没有什么机会用,就不再写了。如果有地方跟我要简历,我甚至连几句话都懒得写,并且,一想到有的人能把简历写成文章,就羡慕不已,起码人家还有激情),是我在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一本小书时,编辑随便写的。书在出版过程中审查再三,二十万字删除了一半,我连送人都觉得拿不出手,所以连简历也没有看。现在看来确实不合适,虽然其中并没有多少夸张。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做记者、编辑,三十六年了,千万字绝对有,只是,大部分都是“本报讯”之类的。那时还没有电脑,都是用笔,写得我右手中指关节处磨出的老茧像石头一样坚硬。
我就这样干了三年“民工记者”。
所以我对海子的行为非常不理解。我也曾经在北京流浪,是最早的“北漂”,1984年就去了,工作了半年,住在白家庄北里,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招待所,还是个地下室,每天像老鼠一样钻进窜出。我在那里请客,叶文福、高伐林、陈松叶等都是我的座上客。如果当年我能够像海子那样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班,有寒暑假,应该比我现在已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要好得多,而且,在北京当农民工都比在南方当一个白领好。有一个湖南农民工,只是在武汉的一所大学旁听了一下,然后跑到北京想方设法呆下来,十几年后,就是京城的著名诗人了,可见平台决定命运。像海子那样年纪轻轻就在京城有了体面的工作,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自杀的资格,尤其是他出身于那么贫困的乡村(他的家乡现在仍然没有脱贫),他的抑郁完全是因为对现实的要求过高。
我是从当时我的顶头上司那听说海子自杀的事的。他是嘲笑的口吻:一个写诗的因为发表困难气死了,用这个办法做广告,出名成本太大。我知道他其实也在暗讽我这个文学青年。
事后我才去打探,得知这个诗人叫海子,北京大学毕业的神童,留在北京的大学就业。这样优越的条件,为什么这样?
我后来也因为编辑文学副刊,接触到不少有抑郁症的诗人,其中一个笔名叫“梧桐树”的也自杀了。他们的抑郁来自于他们的本身,就是现实离自己的梦想太远了。
三十年前的海子,应该是还没有今天这些诗人对物质享受的苦求。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但是海子似乎更加在乎精神。不过,看看海子的文集,也没有什么忧国忧民,他只是忧他自己。
新时期以来,中国诗人基本上是两个大类:“忧国忧民”与“私我”。改革开放四十年,诗人们经过短暂的忧国忧民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很快就“物质化”了,进入所谓“小时代”,然后就是充分甚至过分表现自我,诗人变成私人、私我,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看看一些诗歌学会、协会,实际上已变成商会。
忧国忧民的诗人,不少是口号诗人,其作品技术含量不高。私我的那些诗人,则打着人文旗帜,强调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有的还标榜自己的“公知”形象,结果又是一波“文化口红”。
海子应该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引导者。他的自绝,只是一种避世行为,极端化了。这种避世者,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比比皆是,《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就是一个典型。对他在瓦尔登湖独居两年,有两种说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自觉退回原始社会,直接回到农耕时代;拒绝工业文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梭罗是个低能儿。在日本,夏目漱石,一个标准的旁观者,在火热的明治维新中,虽然没有像梭罗那样去过乡下人的日子,也是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
改革开放,似乎与诗人海子无关。他只有一个小目标: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没有房子,他的感情生活都是空白。从他自杀当年的成名作来看,他只是想过一种清心寡欲的日子。
非常幽默的是,他当年的小目标,今天只有富人才可能实现,因为,还要面朝大海。
这个世界,就是让人如此感慨:房地产商用一个穷小子的诗句启发富人的遐想,而这个穷小子,卧在冰冷的铁轨上。
其实,海子的诗歌技术含量并不高,相比北岛、顾城、舒婷来说,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和这样的句子比较,海子的诗很朴素,很口水。如果在这个方面海子是中国诗歌的代表,那么相对应的,中国小说的代表就是路遥。路遥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先开始一直是退稿,但是却畅销到今天。为什么?就是因为朴素,接地气,打动了无数草根的心。
实际上,把海子的绝命诗——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他以前短暂的创作爆发期的作品相比,他以前的作品显得用力过猛,尤其是长诗,如语言瀑布,泥沙俱下。最后,他返璞归真,平淡如静水。没有了急功近利,没有了立竿见影,没有了弯道超车,没有了百尺竿头,他才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内心,却是那种脆弱的、神经质的、盲流般的,让一个淳朴孩子的小目标在诗歌中真实展现。
如果再把海子的名句拆开来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本来就是民间经常使用的句子,并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原创,只不过海子放大了其影响。这样一句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诗之所以流行,源自三十年前普通老百姓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当年贪腐现象已不鲜见,像海子这样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的知识分子,只能在贫困孤独中一面自怨自艾,一面自我澎湃;他甚至谈不好一次恋爱。
有人说,海子现象最大的受益者西川是借海子放大自己在诗坛的影响。其实,西川也在放大海子的影响,他们是彼此借势。
可笑的是,海子居然也成为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追捧的对象,成为他们恶补文化的低门槛,更成为房地产广告的文案,让银子变得文化一点而闪亮起来。这是黑色幽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