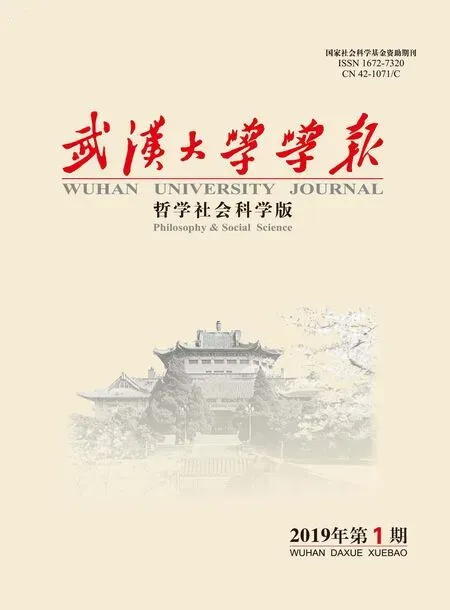《创业史》“新人”梁生宝考论
2019-12-22张均
张 均
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新人”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除主人公梁生宝外,其他人物如高增福、冯有万、任欢喜、徐改霞、刘淑良、赵素芳等,其实都有“新”的特征。这些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他(柳青)暗暗地列了名单,有的一、两个,有的三、五个,那个人的原型是谁谁,那个人的原型是谁谁,很清楚,我见过,家斌也见过”[1](P271),如梁生宝直接取材于王家斌,改霞则与“村上一个漂亮女子”[2](P116)有关,冯有万原型为董柄汉,高增福原型主要是刘远峰,等等。遗憾的是,由于左翼革命在20世纪末的“大失败”,学界出现了“今是而昨非的思想逆转”,“反映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小说也面临着被否定的命运”[3]。因此,以梁生宝为中心的《创业史》本事重塑问题就未能引起充分注意。
当然,存在于王家斌、梁生宝之间显而易见的裂隙--如小说未提及王家斌买地发家的念想--是被注意到了的。不过,这仅被用于证明梁生宝“被净化成了一个苍白无力的政治理念人物、艺术上的‘扁平人物’”[4]。对此类研究,柳青当年曾深表不满:“说不把王家斌同志曾想买地写在梁生宝身上,就是被‘不留痕迹地删去’了。‘删’字该当何讲?文学创作是不是改编生活?批评者这里所要求的又是一种什么艺术方法?”[5]柳青申诉的是文学应有的虚构权利,而在有权删改的背后,《创业史》怎样通过虚构完成有关“新社会、新历史与新文化的主体”[6]的召唤,却是柳青未充分言明而研究者却必须面对、深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与文化生产问题。
一、对梁生宝“前史”的重构
柳青选择王家斌作为《创业史》主人公原型,在偶然中含有必然。事实上,此前身为长安县委副书记的柳青更熟悉王莽村。该村党员蒲忠智精明强干,已经组织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后来还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县上有人把他的事迹写成书,柳青不断鼓励和帮助作者”[7](P117)。以常理度之,王莽村无疑是合适的“文学根据地”,但当有县委同志提议将王莽村作为落户地点时,柳青明确拒绝。他的理由是王莽村已是先进点,“我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显然那里不合适”[7](P118)。当然“还有一点他没有说,经验告诉他:‘工作的典型未必是艺术的典型,有个合适的人物原型非常重要。’”[7](P119)那么蒲忠智为何不能成为艺术的典型呢?董廷芝(区委书记卢明昌原型)道出了其中缘由:
(柳青)开始想以王莽村的互助组长蒲忠智为原型,以后了解到蒲忠智虽然出身好,人也好,但旧社会睹(赌)过钱,当过睹(赌)场的会计。他又改变了主意,经过一段考察,最后把生活基地选到了皇甫村。[1](P271)
赌场素来是三教九流混杂之地,出入其间的蒲忠智就不大符合“体制选民”的要求了:“‘选民’本是基督教术语,指被上帝选中的人。‘新人’作为‘体制选民’似具双重意味:一是组织近乎红色主宰;二是被组织遴选为接班基层党支部的‘新人’,也就被赋予权威性、神圣性”,因此,“体制选民”需要携带日后成长为“英雄”的基因,譬如,“根正苗红”[8]。这些偶然而又必然的因素,导致了柳青与王家斌的相遇、友谊以及《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的诞生。可见,柳青在选择“新人”原型时是有慎重考量的。《创业史》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记录历史巨变中的种种瞬间,而且也希望通过叙事为当代现实矛盾提供某种“想象性解决”,恰如柳青自述:“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9](P98)这意味着,《创业史》不可能如实“照搬”人物本事。那么,在其“改编生活”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的原理”呢?此种叙事复杂性,在梁生宝“前史”重构上体现得异常明显。
《创业史》“题叙”所述,是梁生宝“前史”。“题叙”有很强实录成分,与王家斌经历相仿,如 10岁时“随父母逃荒讨饭到皇甫村,后因父亲病逝,母亲改嫁皇甫村的王三(王明升),肖浩奇随继父姓,而名王家斌。”[10]这种叙写,源于柳青与王家斌父母的熟识,“柳青和她(注:王家斌母亲)一坐就是大半天,听她讲她辛酸的身世”,他们逃荒时,“先住在人家大门道,天不亮就赶快离开,以后找一个废砖窑,讨吃回来三个人就蜷曲在里面,家斌父亲就死在那里。以后老婆婆才带着王家斌要饭到皇甫,嫁给蟆河滩的王三”[7](P136)。柳青与王三(梁三老汉原型)往来也较多,但多有尴尬:
老汉说什么柳青都听着,老汉有时候说互助组怎么不好,看不惯这,看不惯那,他让老汉尽管说,听完了哈哈一笑,过几天再来,又和老汉说长道短。头年老汉还给柳青点面子,后来,柳青和他说话越来越困难,老汉一见他,满面怒气,脸一吊,顺手拿起个活计,屁股一拧,走了。柳青知道他嫌家斌黑明不在家,为了大伙的光景不顾自家的光景:“你不给屋里干活,成天往外跑,跟的啥人?看他不把你领到沟里去。”[7](P137)
《创业史》中梁生宝遭到的继父的怨怼几乎就是现实中王家斌家庭关系的实录。但纵观“前史”,柳青对原型王家斌的本事资料有实质性的删添和改写,如果不细勘,小说与史实的差异不容易被发现。
比较起来,对王家斌童年苦难之源的删改较为隐蔽。“题叙”这样记载梁生宝母子早年的逃荒经历:“娘家爹妈都是这回灾荒里饿翻的,哥嫂子都各顾逃生了。婆家这头,男人一死,贴近的人再没了。自己带着娃子,从渭北爬蜒到这南山根儿来。”[11](P6)小说将梁的童年苦难之源指认为灾荒,但实际情形却更加复杂。据载,“(王家斌母亲)原来嫁在长安县章村的萧家,穷得终年借贷度日。她的一个叔叔有钱,是他们的一大债主。王家斌七岁那年,唯一的财产一间破房,被叔父卖了,说是卖了二十五块还不够还他的债,从此一家人开始了要饭生活”[7](P136)。亲族欺凌才是王童年不幸的来源。对此家世柳青自然熟知,但小说毫不犹豫地剔除了这一本事资料,以“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作了置换。
但“题叙”对王家斌革命斗争史的彻底删除,则颇难理解。小说中,梁生宝与革命几无关系(仅1949年他突然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家了”,高呼“解放啦!”“世事成咱们的啦!”),但王家斌此前却有光荣的革命经历。董廷芝回忆:
我们闹一闹,慢慢心大了,大家说过去人家李自成起义,如今人家共产党的李先念也商洛起义,咱也起义,就一起开了会,商量谁杀哪个坏蛋。其中有一个长工,黑夜开会晚了跳墙回大地主郭林轩家,被郭发现了,骂他。他就对人家说:你还张狂哩,你的头就是我的,我都号了。郭问:怎号的?他说,俺都开会了,谁杀谁都定了,我杀你。地主当晚就向七分校告密了……我们一行动,就被人家捕了37人,当时打死了一个。所有这些行动,家斌都是参加的……家斌在狱中受过三次刑,打死喷活,夹手指头,皮都夹烂了,光剩下骨头。[1](P276)
但如此充实、可遇而不可求的革命本事竟被弃若敝屣。“题叙”呈现的梁生宝“前史”,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矻矻谋食而终不能摆脱贫困的经历。
《创业史》还将王家斌“减去七岁”。在小说开始,梁生宝27岁,未婚(有童养媳但已病故),正处于恋爱年龄,但究其原型并不如此。王家斌1919年生,1953年时34岁,虽然早年确有病故的童养媳,但此时已另有妻室子女。在资历上,王家斌不但不低于郭振山原型高梦生,实还高于高梦生,因为高梦生土改期间虽然积极,但此前只是麻河滩上的“大衫子客”,“喜欢在人前露脸,凡村里谁家给谁说媒、结婚,或者是埋葬死人,这些红白喜事的席面上总少不了他”[12](P254),这与王家斌参加暴动、遭受酷刑的经历不能相提并论,但《创业史》将王家斌“减去七岁”,直接将梁生宝变成了郭振山的下一代人。
那么,《创业史》如此“改编”王家斌早年生活,其后有着怎样的话语运作的考量呢?其实,亲族欺凌与压迫本是新文学习见题材,但在1950年代,批判宗法文化早就不再是“时代主题”,“新式好人”梁生宝的故事本身还要援借儒家,故王家斌遭受的残酷“亲情”就不宜进入“记忆”了。至于删除王的革命经历并“减去七岁”,则与两层话语调节有关。一是对“青年”隐喻力量的配置。当年互助合作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家庭拖累重或生产资料欠缺的贫苦农户,青年尚非主要。柳青将王家斌变为朝气蓬勃的青年,目的之一,应在于以“青年”为反对者众的合作化运动加持合法性力量。那么,“青年”何以有如此功效呢?究其原本,“青年”只是生理学概念,但自梁启超始,“青年者流”就被目为“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13](P464)。其后,“少年”(青年)与“中国”的相互投射就成为现代文化的基本“语法”:“因了‘少年’的支持,‘中国’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却又更多地指涉个人,本身也被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并形成强大的情感的或者道德的感召力量。”[14]将中年王家斌“减”为青年,无疑是在援用“青年政治”为合作化运动加注“自然”的道德力量和“面向未来”的合法性力量。二是“新人”叙述的结构性设置。有研究者曾批评“新人”梁生宝缺乏必要的成长过程,这应是以郭全海式的“新人”来要求梁生宝,而忽略了《创业史》之于“新人”的代际厘分。实则郭全海式“新人”对应的是郭振山,这些“新人”“在思想意识上与富农、地主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带有一种‘地主性’,都属于中国旧农民的范畴”。梁生宝则不甚相同,如果说《暴风骤雨》等早期文本“主要描述的是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地主是作为农民的他性而存在的,农民们则通过消灭地主而确立了自身,但到了《创业史》的时期,农民又成了无产阶级的他性,无产阶级需要通过与农民的斗争来确立自身。”[15](P131-132)《创业史》内在的话语性、“旧农民”与“新农民”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决定了柳青必须将王家斌从其同类中析离出来,安放在崭新的也是最后的“青年”位置上去,并使之成为真正的现代历史主体。
由此可见,“题叙”对梁生宝“前史”的删改,是民族国家文化生产内在要求的结果,而“理想人物”就成为这类要求最直接的体现,“作家把自认为最先进的世界观,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以及最高尚的道德伦理观念,都贯注进去了”[9](P98)。由此,柳青和《创业史》成为 20世纪这一所谓“极端的年代”“召唤、创造新文化与新人的尝试”[6]的有效部分。梁生宝背后的形象文化政治学要比梁三老汉、郭振山复杂得多。那么,这种“创造新文化与新人”的建构性,在“前史”之外的本事改写中有怎样进一步的表现呢?
二、“新人叙事学”中的利他主义
《创业史》“题叙”比较可读,但进入正文就渐成问题,因为梁生宝人品之好几乎到了可疑程度。比如,他自家劳力条件不差,但他不去和“三大能人”寻求“优势互补”,偏偏要和“穷棒子”们混在一起。不得不说,如此看待《创业史》真是十分冤屈,其实梁生宝多数故事都有据可查。据载,1951年“蛤蟆滩闹春荒,贫雇农三分之一缺粮,一半农户无耕畜”“村委会一些人,主张合约贷款,然而经过再三动员,却连一斤粮食也未借到。村委会主任王家斌响应党和政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带头成立一个五户互助组,用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办法解决了春荒口粮和耕畜使役问题”“1953年春王家斌在县农技干部曹彦信的帮助下,制定了互助组水稻丰产计划,亲自带上锅盔干粮去眉县为互助组买稻种,科学管理,育出壮秧”[10],甚至王家斌还有许多动人事迹柳青并未写入小说。
不过这仍不能充分释解读者之疑:即便是“善人”,也该有些许自私的意图吧?黑格尔以为,历史本质上是“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人类为了这类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16](P23)。依此观之,梁生宝的无私就更不可信。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据现存资料看,有两类本事被柳青列入了“影响不大的事实”:一是经济诉求。最为人熟知的当然是王家斌动念买地之事(被柳青劝阻),此外,统购统销在王家斌互助组里遭遇的困难也被“摈弃”。小说中,除几家富农、中农外,大部分贫农和普通中农都踊跃卖粮。现实情形却复杂许多,王家斌互助组最初也不愿将余粮低价卖给国家,经柳青反复做思想工作,王家斌等干部才答应卖粮。二是权力诉求。几乎在所有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革命与权力的互惠关系都属“不可叙述之事”,《创业史》亦不例外。据目前材料看,没有证据显示王家斌走互助合作之路意在谋求村庄权力,但有两条材料显示,身为领导的柳青是考虑到“做官”问题的。一是刚发现王家斌时,他就向冯继贤(皇甫乡党支书)推介培养,此后在柳青等领导支持下,王家斌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二是反复教育王家斌如何当主任:“当社主任大家都想当,但当社主任不是为了务人,坐汽车,指拨人。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为了给大家办事,而是为了坐官”“要全心全意为大家打算,一点也不能为自己打算。当主任除过社里的利益,再没有其它一点利益”[17](P232)。这种教育甚至琐细到无谓的程度:
你啥也不敢胡来,更不要说搞资本主义了……他在这,整天好象就有个圈圈在你头上圈着哩。社办起来后,我在油房里榨油,他来了,说,首先,在油房里吃饭,不能用筷子头在油瓮里蘸一点香油调到菜里头,要把这前提卡住哩。要不,吃一吃就会用油把提在瓮里舀,再吃一吃就会用油瓶子往回提。弄一弄就发生贪污现象了。俺的会计帐上差了五毛钱,柳青发现了都不依,要批评哩,要追究哩。[17](P235)
这说明,在互助合作中,革命与权力的互惠关系客观存在,甚至单向度利用革命追求权力进而以权谋私的现象也很可能发生。柳青对王家斌的教育意在防止后者,但对前者的存在其实是默认的。
但无论哪种权力诉求,在《创业史》中皆隐匿不见。梁生宝始终是纯洁的与权欲无涉的“新式好人”。就自然反映而言,无疑比较真实,因为现实中“王善人”的确不是赵炳(《古船》)或呼天成(《羊的门》)。但王家斌很大程度上是被柳青塑造而成,恐怕不宜作为农村干部典型,因为“整天好象就有个圈圈在你头上圈着”的权力监督在其他村庄着实不为普遍。以常情度之,合理的自私与不合理的自私在乡村皆为较大概率的存在。但柳青拒绝以此来刻画梁生宝,转而采取了剥离策略,如梁生禄入社想占便宜,白占魁入社想当官,郭振山则兼而有之,他们分担了梁生宝可能会有的“贪欲和权势欲”。经过剥离,就将梁生宝与权力、经济等诉求分割开来。在柳青看来,这无疑是成功策略,“在组织主要矛盾”和“对主人公性格进行细节描写时,就必须有意地排除某些同志所特别欣赏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盲动性,而把这些东西放在次要人物身上和次要情节里头”[18](P95)。遗憾的是,这在部分读者看来与虚假并无差异。
然而这背后的“新人叙事学”之于“新社会、新历史与新文化的主体”的召唤,却很值得探究。程凯以为,“‘新人’典型的背后对应着一套新的社会构成原理”“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意味着改造所有制形式,不仅是建立、巩固一套生产关系、生产制度或政治体制,它还需确立一套社会制度,一套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意识状态”[19]。此论涉及颇广,但就《创业史》隐匿革命与权力的互惠关系而言,梁生宝形象的建构,不仅有“王善人”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则是革命的利他主义的文化愿景。
何谓利他主义?丹尼尔·巴塔尔认为,“利他行为应包括以下特征:(1)必须使他人获利;(2)必须是自愿行为;(3)必须有行为目的;(4)他人所获利益必须是行为目的本身;(5)不期待任何物质和精神的回报。”[20]如果不把自我道德完善列入“精神回报”的范围,那么这个界定是可取的。应该说,传统儒家和革命文化皆有利他主义色彩,不过儒家“亲亲,泛爱众”是为尊卑有序的礼治秩序的完善,革命利他主义则是基于巨大同情心的反体制的平等诉求的反映。对后者有人并不认同,他们更习于以“仇恨”“狼奶”来描述革命文化。这多少是知表而不及里:革命之所以仇恨黄世仁,实在是对下层不幸感受得真切、“爱得深沉”。而此同情心则是中国精英传统中的稀缺资源。这种同情心构成了革命及其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以“耕者有其田”为旨的土地改革自不必说,就是《创业史》着力描写的农业合作化实亦如此。1948年,新华社曾专门解释过何以要在土改之后推进“农业社会主义”:
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完全相等,尤其不可能保持不变。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又努力生产,善于经营,他们的经济就可能发展,而逐渐地富裕起来,其中有小部分就可能进行剥削,而成为新的富农。而另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产,或者不善于经营,或者遇到不可抗拒的打击,他们的经济就不能发展,而逐渐地穷困下来,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剥削而变成新的贫农或雇农……(这种)竞争与分化,如果是在旧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那可以因为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垄断的无限制的发展,而一直分化下去,以至于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获得利益,化为乌有。[21](P405-406)
这种预判正是毛泽东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他认为,农村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用不了多久,甚至一年半载,农村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这样,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中国现代化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的环境。”[22]这类忧虑其实在土改结束未几就已渐成事实,在皇甫四村,陈恒山、陈家宽叔侄就在土改后沦落。全国性合作化运动其实包含着对竞争力不强的下层民众的巨大悲悯与保护。对此,或有人以“联产承包”为例,认为私有“单干”才是下层自救之途,但那毋宁缺乏历史眼光。黄宗智认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23](P445)。
全面评价合作化运动尤其是它的激进倾向及其对可能“先富起来”的群体的自由的抑制,无疑非常复杂,但以同情心为前提的革命利他主义,却实实在在构成了王家斌本事改写的策略。虽然王家斌原本即是“王善人”,但《创业史》仍剥离了他的合理的经济诉求与权力诉求,而放大了他的爱与同情,以至到了“多善而近伪”的程度。梁生宝几乎对一切人都充满了温暖的爱,对高增福、有万、欢喜皆是如此,甚至对名声不好的素芳,对前国民党兵痞白占魁,也都视同于兄弟姊妹,如对主动想与自己发展性关系的俊媳妇素芳,生宝想的却是“俺下河沿的众邻居,有办法叫栓栓和素芳变成恩爱夫妻”[11](P380)。这种“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深厚感情,这种对被摔出历史轨道者的温暖的爱,与其说是“王善人”实有之事,不如说是柳青对“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意识状态”的美好愿景的投射。遗憾的是,在以恶劣的情欲为规则的当下社会里,平等、同情心这类社会主义新文化原则逐渐成了不可理解的事物。
三、本事重构中的“经济的胜利”
相较于利他主义在王家斌本事改写中的功能性作用,经济优先亦成为《创业史》“新人叙事学”的重要原则。在这部以“贫困者要改变贫困状况”为motive[7](P399)的小说中,梁生宝竭力通过“经济的胜利”证明互助合作的制度优势。他之感叹亦由此而发:“啊呀!这形式上是种地、跑山,这实质上是革命嘛!”[11](P247)《创业史》也始终按如下逻辑叙述:互助合作具有必然经济优势,也必然会成为农民自发的潮流。那么,这种叙述是否有其本事根据呢?
考之事实,无疑比较确凿。柳青之所以选择王家斌为原型,就直接因于其互助组丰产,“试验的稻田,每亩平均九百九十七斤半,其余平均六百二十五斤,创全区纪录”[24]。而切实可见的经济效应更是互助可以进行的根本原因,如王家斌互助组此前甚为贫穷:“六户人家都是解放前在别处穷得断了活路才到此落脚的,在北岸的村里难以插足,便在这稻地间搭了草棚栖身”[7](P123),其中组员陈恒山(任老四原型)地少娃多,入组之前几乎就在绝境之中:
他给柳青讲他到秦岭深处去伐木,山里没路,走陡崖,爬立坡,回来背着一背柴,两手交替着拉树杈,一有不慎连人带柴滚下去,就只有等着喂狼了。说起进山,他脸色就变白,流露出恐惧和后怕。但是,没有办法,他不进山,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土改以后他还是一个到处欠债的穷汉,就像他自己说的,就差没有向滈河的石头借过钱了。年年春荒,他心最慌,他无路可走,只好参加互助组,对他,这是唯一有希望的路。[7](P123-124)
显然,陈恒山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并非因为它的政治性质。詹姆斯·斯科特认为:“穷人为获得工作、土地和收入而奋斗;他们的目标并未指向诸如社会主义等大的历史的抽象概念,更不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了。”[25](P424)农民的这种生存逻辑在王家斌互助组中极为明显:“这六户人家能组织起来,基本稳定,主要原因是都太穷。”[7](P123)亦因此故,王家斌互助组成功升级建社,《创业史》对此作了忠实记录。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创业史》中所有农民,如高增福、姚士杰、任老四、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郭世富、郭振山,都是经济的理性主义者,没有一人是因“社会主义等大的历史的抽象概念”而投身或反对互助合作。即便是能“将党的理论和政策转化成自身意识的内部构成”[26]的梁生宝,也奉行经济优先原则。尤为难得的是,同样出于对经济理性的尊重,《创业史》还借梁生禄、栓栓退组之事记录了当时部分农民抵制互助、合作的历史事实。其实柳青初到长安县时,多数互助组是难以维持的,“从高湾村到郭家十字,每个互助组柳青都去”“但他却没能把大多数互助组巩固住,勉强维持下来的,不久也散了”[7](P122)。
可以说,《创业史》不但将经济优先处理成了农民生存逻辑,也将之讲述成了合作化运动终获成功的保障。按照柳青设计,即便是郭振山,最终也会因为合作效益优势而积极投身其中。在小说中,以梁生宝为中心的“稻地革命”确实汇成了这种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不过究之本事,海登·怀特所言--“只有决定‘舍弃’一个或几个包括在历史记录中的事实领域,我们才能建构一个关于过去的完整的故事”[27](P173)--仍然是《创业史》无法绕过的叙事疑点。这主要包括两层。一者,现实中合作经济的成功,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扶助,但小说基本“舍弃”此层事实,改写为农民自发推动而政府予以协助。譬如,小说中梁生宝互助组的成功主要得力于郭县稻种和新法育秧,但在现实中,柳青帮王家斌“实现了升级换代”,“柳青的业绩,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化肥和进口种子的双重成果。现实中的梁生宝们只能到眉县买稻种,而柳青帮助胜利合作社买到了日本的进口稻种。这是一种粳稻,稻秆很硬,不怕风吹,结的谷粒溜圆饱满”,但新种子需要“调拨尿素上肥”,“可是那时候尿素只能调拨得来,高产的幸运,就难以落到每块田的头上”[28]。这也表明,若无特殊政策倾斜,互助合作未必胜过“单干”。对此,小说未作展开。二者,《创业史》彻底舍弃的是互助合作的发展并不完全得力于经济优势。小说中梁生宝完全以经济优势成功“说服”乡亲,但现实中思想教育却至关重要。如柳青对董廷芝父亲(梁大老汉原型)的教育:
(董父)家里原先贫苦,后来慢慢好了,土改时订了中农成分……他开始说啥也不入社,爱骂人,谁他都骂哩。把廷芝叫“董伟人”,骂入社的贫雇农是“拿干棉花在俺的油瓮里蘸哩!”柳青考虑区委书记的父亲都不入社,对群众的坏影响大。为此事把廷芝批评扎了,有一次批评得廷芝哭着从长宁宮由人扶着才走下来。有一段他停止了廷芝的工作,让他专门回去做他父亲的思想工作。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柳青给廷芝出了三个主意:一是把他父亲分开,全家其他人入社,派人给他父亲做饭。伙食费不够了由柳青自己的工资给补贴;二是全家人监视他爸,不让老汉出去随便乱骂人;三是干脆把黑马卖掉,逼老汉入社。[17](P234)
较此更甚的是,司法部门还介入其中:“在秋忙和第二次扩社前夕,为了下头的工作顺利,免得肖德新(注:白占魁原型)再闹事,县司法部门把他拘留一段,等他回来,社已经巩固,他也没有群众基础,跳腾不开了。”[7](P150-151)无论司法拘留还是柳青的教育,其实皆含权力压制性质。遗憾的是,《创业史》对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和经济扶持全部舍弃,改写为农民自己的觅求与成长。
那么,怎么评价“新人叙事学”对王家斌及其互助组本事的如此改写呢?这与其说是“历史都是以某个视角怀着某种特定的偏见来讲述”[29](P143)的又一见证,不如说是革命艰难与复杂的现场记录。从历史上看,具有资源优势的中国人更愿意选择“抛弃”而不是帮助缺乏利用价值的穷人,贫苦农民也更愿选择依附权势而非与同阶层人“弱弱联合”。这种貌似“自由”实则权势“通吃”的丛林规则,导致的是一个大规模的永久沉沦的下层社会。革命却要挑战此从来如此的规则,追求“不抛弃,不放弃”。然而无论是提倡弱弱联合,还是劝说资源优势者体恤贫弱乡亲“走大伙富足的道路”,革命都会在丛林法则前屡屡碰壁。无奈之下,外力干预就成为不合理但合情的选择。柳青深信合作化是“消灭一切贫困”“最后解放农民”[21](P408)的必经之途,所以在写作中删除这些“幕后因素”、将合作化运动相对“自然化”,就是合乎逻辑的行为。对于绝对不允许个人自由被干涉的读者来说,这种本事改写不可接受;但若对丛林法则下“沉默的大多数”有更多怜悯的话,读者或会认可此改写背后“不抛弃,不放弃”的“新文化”诉求。
与经济优先相关,《创业史》还着意凸显了“新人”梁生宝另一特征:热爱劳动,尤其倾心于集体劳动。前者是蛤蟆滩农民的普遍特点,后者则是梁生宝从被人目为“出身贫贱”的“讨饭娃子”[11](P273)到广受尊敬的原因。那么,现实是否如此呢?究之本事,几乎是实录。不过,小说却虚化了一层事实,即农民对王家斌的尊重,可能不仅因于集体劳动,或还有对他“活到了人面前了”[11](P23)的新精英身份的认可。但《创业史》删除此层,对其吃苦耐劳、倾心集体则有浓墨重彩之描绘。何以如此呢?当然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于“新人”的灵魂改造有关:“要拯救灵魂必须通过‘自赎’才能实现。‘破鞋’应当抑制情欲;知识分子应当克服名利观念;地主应当根除贪欲;农民应当力戒懒惰;干部应当时时刻刻消除‘教条主义作风’。”[30](P605)对于农民“新人”而言,与集体可以对接的劳动,就成为必要的主体价值。但在中国传统中,劳动仅是局限于下层社会私人道德评价的弱价值,缺乏与金钱、权力并重的广泛的社会认同。只善于劳动却积财无几的人,很难受到尊敬。梁三老汉在郭世富盖房现场被村人恶作剧地摸头、奚落即是证据。这多少是权贵文化逻辑宰制的结果。但自延安以来,革命“新文化”一直试图校正中国人从来如此的价值观,从而赋予革命主体(工农兵)以地位和尊严。在缺乏权力或财富资源的现实条件下,重塑劳动价值就是必然选择。这是梁生宝日常生活被集体“劳动”所充斥的原因。由此,集体劳动与经济优先原则一起,深度介入《创业史》对“可以叙述之事”与“不可叙述之事”的区分,而对“最大多数人”的温暖的爱、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希望,都兼具在内了。
四、革命、儒家与清教徒
《创业史》将劳动、经济优先、利他主义等列为“新人”叙述的必选项,不但与诸多读者从来如此的非正义价值观相抵触,更与其重暴力、喜情色、嗜权术的阅读趣味拉开了距离。距离之大,几乎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对此,柳青也自心知。故在将王家斌“减去七岁”加持“青年”价值时,也顺理成章地将他带入情恋纠葛之中。不过,恋爱年龄的梁生宝又表现出节欲、苦行的清教徒特征。对此学界历来批评甚多,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民,没有‘人性’,只有‘党性’……‘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值得那么吝惜的了。’这是何等可怕和恐惧?”[4]此说明显夸张,《创业史》在性叙述方面诚然保守,但并不意味着“新人”缺乏人性。何谓人性?人性是指人之异于动物的属性,“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1](P105)可见,人性兼涉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并非只有性欲才是人性。其实,梁生宝为人朴实、善良,对于遇人不淑的素芳他有命运的悲悯,对于意见固执的继父他有尊重和体贴,甚至对于非常鄙视自己的王二直杠,他也跳下墓坑替他踩土(依乡俗,非孝子替亡者踩土是不宜不利的)。不过,就性表现而言,《创业史》确实相当节制。虽然在刻画素芳被姚士杰诱奸的场景时不乏《白鹿原》式的笔法,但其“新人”确实近似于清教徒作风。
其实,现实中王家斌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干部,无贪财恋色之表现。钱财方面,柳青对他多有教导。如王家斌善饮,柳青即对他言:“不能用公家的钱,一分钱也不能用,那都是社员的血汗,经济上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7](P139)在女色方面王家斌更无不检之处,互助合作之时他已有家室,且无婚外性关系。柳青曾告诫他:“做一个干部,千万不能在男女关系上有问题。你当干部,进东家、走西家,人家男人上地了,你和人家女人胡来,你这人民的干部就成了人民的敌人。”[7](P139)故而小说中梁生宝与素芳的流言风语、与改霞、刘淑良等的或惆怅或平淡的恋爱,皆系虚构。虚构之因,当然与对读者趣味的适当考虑有关,但对读者情色趣味的考虑又予以极大限制。尤其梁生宝与改霞单独相处时的反应非常令读者不满,那种冷淡未必符合王家斌生活隐私,与农村实存的性真实更不相衔接。
那么,柳青为何要将“新人”梁生宝虚构成“清教徒”呢?不少学者归之为革命的影响。“革命设想的实现不得不依赖革命者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时,只有禁欲是持续革命的保证”“禁欲促使革命者放弃个人的享乐、放弃个人的趣味甚至放弃个人的生命而参与某种危险的事业”“如果革命的纵深遇到了愈来愈大的阻力,革命者必须凝聚为一个坚固的整体才能有所突破”,这时,性关系“这种私人空间可能对于政治纲领的长驱直入形成障碍”,于是,“禁欲是清理和纯洁革命组织的一个有力措施”[32]。这当然有其道理,整体的形成必须以对异质成分的辨认、区分和排除为前提。对此,邵荃麟在有关“正面的英雄人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里讲得颇为清楚:“当作家从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了各种各样英雄人物,进入到创作的过程时候,他一定要经过概括和集中。他凸出其人物的某些方面,而舍弃其另一些方面。他所凸出的东西,一定是属于最充分最尖锐地足以表现人物的社会本质的东西;他所舍弃的,一定是属于非本质的,和主题无关的不必要的东西。”[33]所谓非本质事物,性关系无疑首当其冲。这可从许多当代中国革命作品得到佐证。不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恐怕亦只是《创业史》着力舍弃性叙述的非主要成因。比较而言,苏联文学(如《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的性叙述还是较为自然的。其间差异,可能还有革命的叙事成规之外的传统或个人因素的介入。
这可从两个层面观察。一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英雄厌女症印象深刻,“对好汉更重要的考验是他必须不好色。梁山英雄大都是单身汉。至于已婚英雄,他们婚姻生活方面的事书中很少提及,除非他们因为妻子遇到什么麻烦”“与不贪女色的梁山泊英雄迥然不同,小说中别的造反头领如田虎、王庆、方腊以及其他许多不太知名的歹徒则被写成了淫棍色狼”[34](P88)。显然,如果把《创业史》置于古今演变脉络中看,梁生宝这类羞涩、矜持的男性角色,和鲁迅、巴金、老舍、孙犁等笔下的人物一样,都是儒家厌女症英雄的久远回响。他们对于妻室以外女性的性欲的克制,折射的是作家内心的儒教修养。与此相应,姚士杰的好色与《水浒传》中的淫棍色狼并无二致。故《创业史》“清教徒”式的“新人”叙述,受制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成分其实有甚于革命。二是柳青个人婚恋观的影响。柳青是一位严肃的事业主义者,视婚姻为事业之从属。他与马葳论婚时,“他要求‘忠厚老实’的信条没变,但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与他进行思想交流,对他工作有帮助”[7](P114)。可见,柳青仅视性与婚姻为事业之助,而非一见女性就不能自制。梁生宝在改霞面前的克制,就与两人的事业冲突有关。柳青曾对女儿刘可风说:“在我的书中英雄与美人没有结合,因为他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7](P410)两人既有矛盾,梁生宝在与改霞接触时止乎礼义,恐怕也不宜理解为“没有‘人性’”。可见,个人定见、儒教遗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成规,共同参与了《创业史》对王家斌私德的重新建构。尽管王家斌在现实中并无复杂男女情事,但柳青仍通过素芳、改霞、刘淑良等不同交往对象的设置,完整地投射了他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家斌并无情恋纠葛,但素芳、改霞、刘淑良等却皆非空穴来风之人物,而都有实在的人物原型。她们之存在,亦不仅是完成梁生宝的“新人”建构,她们自身亦在“新人”之列,同样被寄予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想象。董廷芝回忆:“改霞的模特是俺这一个姑娘,叫郭福娃。福娃人长的漂亮,上过小学,在西安戏曲剧院唱过戏,后来嗓子坏了,回到农村”“在各项运动中表现的都很积极,当村里的团支部委员,跟另一个团支委--复员军人王来运恋爱”“可是福娃她妈不同意,嫌来运穷,我和柳青都做过工作,说不通,还骂我们是把她娃娃往火坑里推哩”[1](P280)。显然,这桩爱情悲剧柳青并未写入小说,但改霞妈妈的择婿观与福娃妈非常接近,福娃性格更被发挥,最终将改霞推到哈蟆滩以外的国家空间,使“新人叙事学”与国家现代化发生建立深刻勾连。赵素芳、刘淑良亦皆有所本:“互助组扩组时还扩进了董同州一家,同州媳妇是姚淑芳,一九五四年加入共产党,以后是社里的妇女干部。待同州很好。”[1](P283)姚淑芳并无小说中素芳年少被诱奸、引诱梁生宝、与姚士杰通奸等实事,柳青虚构此类情节,既是为了“说明旧社会造成了这个女性的可悲命运”,也是为了在后续卷册中“让素芳当妇女队长”[7](P413)以展示女性与国家的互动成长。刘淑良则取材于小姜村某女性,后者当然不曾与王家斌恋爱,但小说安排离异妇女刘淑良与梁生宝进行一场违反现实性别秩序(在传统农村只有极度家贫或有残疾的男性未婚青年才会与离异妇女发生婚姻关系)的恋爱,显示新的性别关系之义。
这些女性“新人”的重构,与清教徒式的梁生宝一起,构成了《创业史》“新人叙事学”的深长意味,恰如1960年柳青的肺腑之言:“时代赋予现在中国的革命作家这样光荣的任务——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任务。”[35](P59)从私德重塑到劳动与经济优先,再到利他主义,《创业史》改造了主要人物原型王家斌的本事真实,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愿景加赋其中。兼之对其“前史”的重置,《创业史》最终将梁生宝塑造成了当代中国新的历史主体。这样的“新人”,也许在今天不再与读者新的历史认知发生共鸣,但在20世纪50-70年代,却承担着当代历史的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