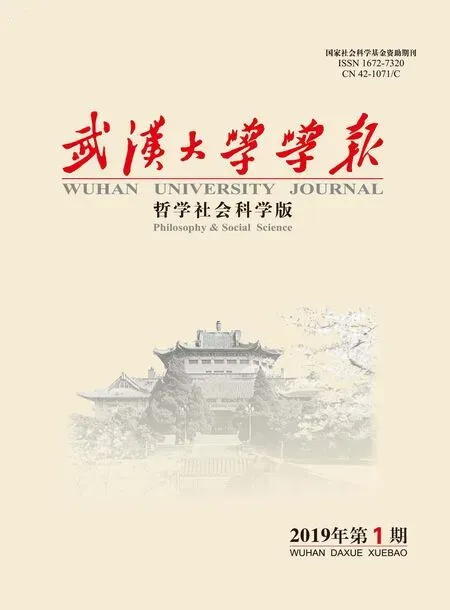对王维“诗中有画”的再讨论
2019-12-22蒋寅
蒋 寅
自拙文《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发表以来,学界给予了热烈的关注,发表多篇商榷性的或延伸性的研究论文[1–12],我一一拜读,收获不一。今重拾旧题,补足前论,以期做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一、“诗中有画”的“画”指什么?
《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立足于绘画的造型性,以此衡量王维诗歌的艺术特征,从而质疑“诗中有画”的命题是否适用于概括王维诗歌的主要成就,并进而思考“诗中有画”作为批评术语,其意义是不是被夸大了。关于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争论的双方都没有事先界定物质画与想象画,也混同了‘有画’与‘可画’的含义”[13]。这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看似具有学理上的反思色彩,实际上却未斟酌“有画”和“想象画”的概念是否能成立,或是否有意义。在我看来,“有画”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无法界定其内涵,历史上许多诗人包括杜甫的作品都被说成有画,但没有人关注那些作品的绘画性;而“想象画”只能勉强说是一种心理表象,恐怕不是讨论诗歌文本适用的概念。
浏览这些续出的论文可见,论争的焦点在于对“诗中有画”之“画”的理解。按常识说,这里的“画”应该指绘画的特征和意趣,即绘画性或者说造型性,但商榷者都不这么看。他们提出诗中有画的“画”乃是指中国画特有的意境[14](P151-152),认为我对“画”的理解太拘泥,不懂得中国画的美学本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画特有的意境又是什么呢?不就是中国画的象征意蕴么,或者说不就是诗意么?这么一来,“诗中有画”在他们的解释中就变成了“诗中有诗”,这样的循环命题显然是无助于讨论深入的。
我也反思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苏东坡的命题其实提供了两种讨论的角度:价值估量和话语分析。《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的讨论出于价值估量,观点已表达得很清楚。这里我想再尝试做一番话语分析。这一研究已有学者尝试,基本观点是东坡所谓“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判断,而是对王维个人诗、画特征相互渗透现象的直感[15]。这种话语分析的方法不是要考究东坡说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而是究明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要对王维诗和画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探讨的立足点已转变为对苏东坡艺术思想和见解的研究,这与对王维艺术特征的认识不是一码事。
由于宋代文学艺术总体上为“破体”--不同艺术门类、不同体裁的艺术特征相互交融、渗透的风气所笼罩[16](P67),诗画艺术的交融尤其是画家自觉地追求抒情性也是当时的流行思潮[14]。如李公麟“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说“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17](P131)。这就让人很自然地向诗画互相借重对方所长的方向去理解诗画关系,将“画中有诗”解释为画有诗意,“诗中有画”解释为诗有画趣。这绝不是我的穿凿理解,事实上宋人对于王维诗的确说过:“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已自有画意。”[17](P169)但这只是后人的感觉,王维的创作理念究竟如何,终不能起九原而叩之。法国画家瑟拉说过:“有些评论家抬举我,说在我的画作里看到一种诗意,但我是以自己的方法绘画的,并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18](P325)那么对于苏东坡的评论,王维会怎么说呢?既然我们无从断定苏东坡的说法是否符合王维本意,就只好据其所说作一番话语分析了。而话语分析的前提,是要求回到东坡命题的语境,关注他发言的艺术史和美学背景。研究者指出,诗歌和绘画创作在唐代都进入一个繁盛时期,两类艺术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也日渐突出。到北宋诗画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以苏东坡为代表,艺术家们在理论、实践两方面都有一些探索。随着文人画、写意画主体地位的确立,诗歌和绘画在表现作者人格精神的最终指向上趋于同一,由此产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19]。这一论断我总体上是认同的,但觉得具体思路还有展开的余地。
二、“诗中有画”的“画”作为王维画意
当我们将考察的中心由王维诗歌转移到苏东坡的艺术观念上时,问题马上就与艺术史上足以同文化史上的唐宋转型相媲美的观念变革联系起来。日本学者浅见洋二考究殷璠《河岳英灵集》所谓“着壁成绘”与六朝以来“雕绘”“雕画”“图缋”“画缋”等词的渊源,认为那是指一种人工色彩强烈的艺术美,并推想王维诗在当时就给人这种印象。他的研究着眼于中国文人如何读诗,在他看来,“所谓诗的绘画性,或所谓诗与绘画的接近、融合,最后仍与怎样读诗的问题有关”[20](P39-49),此言深得我心。
上文提道,宋人读王维诗,“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已自有画意”,说明他们从王维诗歌的画意中看到的是作者的高情逸致。这一方面体现了宋人尚意的美学旨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王维诗之画意的感受不是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绘画性,而是着眼于王维诗体现了他本人绘画的某些审美特征。这样,我们的讨论就重新回到学界早就涉足的思路上来--考察王维绘画的艺术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在诗中的表现,说明它们给王维诗带来了什么特色,然后评价其历史意义[21]。
东坡对王维诗的论断,相信与他对王维画的认识有关。苏东坡是非常推崇王维画的,他在《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诗中比论两家之长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评论两家的艺术特点更具体指出:“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22](P109-110)这不就是说,他在王维的壁画中看出王维诗既清又不失其厚的美学特征吗?这似乎也是古代艺术家惯常的思路。黄公望论钱选画,说“知诗者乃知其画”[23](P86),反过来也可以说知画者乃知其诗,即肯定钱选的诗歌表达了其绘画的境界,能懂得他的诗便能懂得他的画。为此清代画论家笪重光曾将诗画相通的原理概括为:“故点画清真,画法原通于书法;风神超逸,绘心复合于文心。”[24]而诗人乔亿更具体论述了王维诗具有与其画同样的美学风貌:
以画论诗,李、杜歌行,荆、关、董、巨之山水也;唐初四子歌行,思训父子之金碧山水也;摩诘之诗,即摩诘之画,意致萧散中自饶名贵。[25](P1088)
至于苏东坡,陶文鹏先生已指出,他对诗画的艺术界限是有清醒认识的[26](P14-21)。虽然学界考察东坡对绘画特性的认识,对他论画重传神已形成一致看法,但我们仍可以肯定,东坡对绘画的造型特征有着清楚的意识,他对诗歌“写物之功”的理解并不向绘画的造型性靠拢。这从《东坡志林》卷十的一段话就可以了解: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落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27](P88)
他明显将诗的写物之功限定在能够捕捉事物的形象特征、与特定环境的关系,而非概括性的一般说明。那么,他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理解是指这种写物之功吗?更进一步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论就是对王维诗、画具有共同的美学特征即乔亿所谓“摩诘之诗,即摩诘之画”的认识吗?
在考究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应该肯定,苏东坡对绘画的认识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刘石认为,东坡已“开始突破了仅仅以画家身份定义文人画的皮相之论,成为绘画史上较早系统提出文人画理论的学者”,他有关文人画的理论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在绘画原则上强调神理象外,不重形器;二是在绘画功能上强调达心适意;三是在绘画风格和意境上强调意气所到,清丽奇富,变态无穷。刘石进一步推断,“苏轼‘诗中有画’观念之发,正是其主张诗歌写物图貌的体现”,“用于评论王维就如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21对杜甫的评论:‘杜公善于摹写,工于体物,愚谓必力思此二事’”[28]。他的看法是,东坡评价王维的两个命题隐含着对王维画风的认知,即王维的画具有他诗的那种意境[25](P1088)。我赞同这种见解,虽然我们尚不能坐实这一点,但通过南宗画的传统间接地体认王维绘画的艺术特征,也能获得到一些验证。
三、王维画的写意倾向
作为画家的王维,在美术史上有多方面的贡献,但他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南宗画的鼻祖,二是开士人画风。
根据文献记载,王维绘画的成就主要是在山水画。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称“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29](P18),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称“王维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30](P47),荆浩《画山水录》称“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31](P5)。王维后来被尊为水墨山水之祖和开创“士人画”的不祧之宗,是因为他不仅是第一位以画著名的文士,还开创了一种文人画风。后人甚至将他与书圣王羲之相提并论,说:“画法自李师训父子而下,便称摩诘;书法自钟太傅以来,即数右军。摩诘画惟《避暑图》为奇绝,昔人谓其不餐烟火;右军书惟《内景经》为入神,昔人称其为飞天仙人、运腕太史。”[32](P308-309)这么看来,王维在绘画史上的地位比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还要更高。
“士人画”之名始见于苏东坡《王维吴道子画》,其《又跋汉杰画山》也提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33](P2216)为此前人或认为士人画的概念出自东坡(如邓椿《画继》卷三),这是不对的。谢赫评刘绍祖已有“伤于师工,乏其士体”的说法[34],只不过“士人画”的概念现在始见于东坡文字而已。明代以后,以“士气”称许文人画的精神已为老生常谈。屠隆《论元画》云:“赵松雪、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四大家及钱舜举、倪云林、赵仲穆辈,形神俱妙,绝无邪学,可乘久不磨,此真士气画也。”[35](P353)冯梦祯《忆姬人》云:“笔间常有拙意,画家所谓士气,不入匠作也。”[36](P245)董其昌也说:“士人作画,当以草粲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37](P40)王夫之评杜甫《哀王孙》曰:“世之为情事语者,苦于不肖,唯杜苦于逼肖。画家有工笔、士气之别,肖处大损士气。”[38](P25)王文治题骆绮兰画曰:“画贵士气,谓卷轴之华流露于笔墨间也。”[39](P18)这里所谓的士体、士气,与师工、匠作、画师、工笔对举,都指有别于画师、工匠之作的士大夫画或者称文人画特质。前人追溯这种特质的由来,王维之前更无古人。
王维的绘画成就原是极高的,作品传世也很丰富。《宣和画谱》记载北宋御府所收王维画多至126幅。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在世间流传,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载苏氏藏有王维《卧披图》,郑樵《夹漈遗稿》卷一有《夏日题王右丞冬山书屋图》诗,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李邦直家藏有唐蜡本《江干初雪图》真迹,世传为摩诘所作,末有元丰间王禹玉、蔡持正、韩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张邃明、安厚卿七人题诗。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可惜历经千载,兵燹之余,只剩下后人摹本《雪溪图》《山阴图》《江山雪霁图》《江岸雪意图》《奔湍图》及《长江积雪图》(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藏)等几幅流传于世。王维所传画作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辋川图》。明汪珂玉《珊瑚网》载:“王右丞维,工人物山水,笔意清润,画罗汉佛像甚佳。平生喜作雪景、剑阁栈道、骡纲晓行、捕鱼雪渡、村墟等图。其画《辋川图》,世之最著者也。盖其胸次潇洒,意之所至,落笔便与庸史不同。”[40]元代袁桷有《辋川图》诗,叙述图中景物道:“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余。山色无还有,云光卷复舒。前溪渔父宿,旧宅梵王居。千古风流在,披图俨起予。”[41](P474)图传到清代下落不明,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著录一个宋人摹本,约略可见其大概:
观其石用小斧劈皴,树叶多作夹笔,人物眉目分明,深得右丞遗意,当是宋时名手所临。[42](卷 1)
根据袁桷的记述,《辋川图》的意趣颇能与王维的诗歌相印证。所谓“画里见诗余”,具体表现为山色似有若无,云光卷而复舒。这种凭借水墨浓淡渲染出来的效果,不正是《汉江临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感觉么?王维所以被奉为南宗画的初祖,正因为他的水墨山水开创了文人画的新风。以王维为南宗画之祖师,其说发自董其昌。董氏《画旨》之说曰: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43](P36)
他认为王维的水墨山水,一变钩斫之法而为渲染,由张璪而递传至元四大家,遂形成南宗一派。其说甚为后人信从,清初恽寿平论南宗画源流,更补充以元明间的承传:
南宗以唐王摩诘维、荆洪谷浩为祖,开文人笔墨游戏法。后至董源,号北苑,南唐人,高逸沉古,元四大家皆宗之。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最近巨然。巨然北宋僧,亦师北苑者也,故今称董巨。但一峰用正锋长皴数笔,则得自北苑也。倪瓒元镇号云林,又号迂翁,学北苑,兼洪谷意,所以独逸在三家上。吴镇仲圭号梅花道人,独得北苑墨叶,兼巨公之长,最为沉郁。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初师北苑,后兼摩诘,细麻皮皴,极郁密浑厚,其用墨意不离北苑。要之,黄倪吴王四家总出北苑而各不相似,所以能高自立家。若如出北苑一手,纵极肖,已落第二乘矣,岂能与北苑并传不朽者乎?如近世王绂、杨基、张羽、徐贲皆以笔墨游戏,得元人意致,亦各成家;文征明、沈周、仇英、唐寅未尝相袭,而董宗伯其昌复宗北苑,绘苑风流赖以复振云。[44](P651)
历史地看,南宗画的艺术精神以写意为主,不重写实,强调文人画的士大夫气。乾隆间画家王学浩论文人画,尤其强调:“六法一道,只一‘写’字尽之。写者,意在笔先,直追所见。虽乱头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极工丽而气味古雅,所谓士大夫画也。否则与俗工何异?”[45]嘉、道间画家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也说:“吾家檀园老人笔墨清超,不事刻苦,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若实父仇英,譬作室者,瓴壁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筑起,及其成功,则又如齐云落星,缥缈在天际矣。此士气、作家之别也。”[37](P1)他们心目中的士大夫画,无非是以写意为核心,意在笔先,纵情笔墨,不事刻苦,不重写实,唯以意趣自足和气味古雅为尚。然则我们直接在写意与士气之间画上等号也不为过吧。
写意一方面意味着不拘泥于对象的真实,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所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如张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难与俗人论也。”①关于雪中芭蕉的真实性,后来引发持续的争论。朱熹《语类》卷 138以为王维误画,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王肯堂《郁冈斋笔麈》卷 2则认为实有其事,王渔洋《香祖笔记》卷十也以自己岭南游历的经验证实其说。[46]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不作写实性的描绘及忽略细节,如沈书同卷论董源画: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灿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然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46](卷17)
李修易概括南宗画用笔的特点,适可与沈括的说法相参照:
山无险境,树无节疤,皴无斧劈,人无眉目,由淡及浓,可改可救,赭石螺青,只稍轻用,枝尖而不劲,水平而不波,云渍而不钩,屋朴而不华,用笔贵藏不贵露。[37](P1)
正因为如此,沈颢《画麈》说:“今人见画之简洁高逸,曰士夫画也,以为无实诣也。”什么是实诣呢?他解释:“实诣,指行家法耳。”即工笔写实的细致刻画,这正是文人画所鄙弃的画法。
南宗画尚写意而不刻画,在用笔上就变线条而为渲染,不用骨法而以气韵胜。唐岱《绘事发微》说,“唐李思训、王维始分宗派。摩诘用渲淡开后世法门。至董北苑,则墨法全备。”[47](P17)董源的山水画技法,甚为后人宗尚,到元代画家黄公望甚至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48](P24)。詹景凤跋饶自然《山水家法》,称山水有二派,一为逸家,一为作家。逸家始自王维,作家始自李思训。“若文人学画,须以荆、关、董、巨为宗。如笔力不能到,即以元四大家为宗,虽落第二义,不失为正派也。若南宋画院诸人及吾朝戴进辈,虽有生动,而气韵索然,非文人所当师也。”[49](P191)在风格倾向上,南宗用笔疏简,出韵幽淡。如元四家之一的倪瓒自题《师子林图》,谓得荆、关遗意,然简淡有韵,所谓师法舍短是也[50](卷4)。明代师法王蒙的陆治,自跋山水立轴也云说:“山樵笔意古雅,多萧闲林壑之趣,非澄怀弄笔,罕臻其妙。”[51](P10)明末自称以“南为主,北为辅,笔墨之性往往闯入唐宋诸家”的沈颢[51](P17),在《画麈》“分宗”条说:“南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出韵幽淡,为文人开山……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王原祁自题山水立轴云:“云林设色秋山,不在工丽,全以冲夷恬澹之致出人意表。”[51](P29)这些论者对南宗画技法特征和艺术风貌的概括、描述,都旨在强调,洋溢着文人气息的南宗画,能以潇洒的写意性克服工笔刻画的繁缛琐细,独造一种气韵冲淡、神情幽远的意境,其画面之意境流动着天机,透露着逸趣,随处可见作者的人格和襟抱。这种不是强化而是抑制造型性,同时突出作者主体性的画法,的确有着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诗意,不妨称之为画中有诗,实质上就是中国画的抒情性亦即写意倾向。如此再看李修易的清言:“夜月梅花,最得诗人清迥之致,漫以无声赋此。”[37](P44)就知道画家的创作冲动,首先起于感受到物色景象的诗意,而且是特定的诗意境界,然后以画笔赋形,于是成就古人所谓的“无声诗”。这便是“画中有诗”的原理。如果我们将它视为中国画的特质,说王维诗中有画的“画”即指这种特质,那就不啻是在演绎一个“诗中有诗”的循环逻辑;而如果将苏东坡说王维“画中有诗”理解为可从王维的画中感受到他诗歌的意境,即那种清空澹远、隽永灵动的诗趣,则不能不说是过人的深刻感悟。同理,若将东坡的“诗中有画”解释为王维诗有着绘画的造型性,那就不仅在学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同时也大大遮蔽了王维诗歌夐绝的艺术造诣。因此,只有将“诗中有画”解释为王维诗中含有他自己绘画的意趣,才可以将王维诗歌的艺术表现与其画风对应起来考察。
四、王维诗的写意特征
王维画因负当世盛名,论者往往先入为主地设定其诗与画同出一源,而从绘画的各种要素入手,寻找它们在诗中的种种表现,以见王维诗歌总是不经意地露出画家本色。按这种思路来评论王维诗歌的论文已发表很多,这种批评方式虽然不失为认识王维诗歌的一个途径,但不可避免地也带有流于主观化的危险。如果我们同意说苏东坡的“诗中有画”是指王维诗中可见其南宗画风的某些特征,那么就应该从他描绘景物的写意特征来印证这一点,因为南宗画风首先是以写意而非刻画见长。我们一旦从写意特征来看王维诗对外部世界的描写,就会从艺术表现到风格层次都得到一些异于往昔的判断。
我们先要转变一下习惯的反映论思维方式。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表现取决于观察,而是观察取决于表现。意大利美学家冈布里奇的研究告诉我们:
画家只是被那些能用他的语言所表现的母题所吸引。当他扫视风景时,那些能够成功地和他学会运用的预成图式相匹配的景象会跳入他的注意中心。样式像媒式一样,创作一种心理定向--它使艺术家去寻找周围风景中那些他所能表现的方面。画画是一种主动的活动,因此艺术家倾向于去看他所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见的东西。[52](P80)
绘画所展现的并不是观察的结果,而恰恰是选择的结果,以往被视为素材的形象其实是写意的符号。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最大程度地强化了这种写意特征。从王维诗歌对景物的处理中也明显可以看出写意化的倾向,这在许多侧重于视觉要素来分析王维作品的论文中都被忽略了。
在《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一文中,我已分析、说明王维诗习惯将空间存在转化为时间过程的动态表现模式,尽量避免静态描写的效果,用诗学的语言说就是去赋笔化。去赋笔化意味着脱弃单纯的白描、形容、比喻等呈示性要素,而采取以景叙事、离形取神、淡化线条轮廓、忽略细节等方式来造成整体上的写意特征。以下试分述之。
先应该确认的一点是,王维那些被论者目为山水田园诗的作品,大体是沿袭谢灵运游览纪行诗的写法,以叙事为主调,风景描写其实着力不多。像《晓行巴峡》《宿郑州》《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游化感寺》《赠裴十迪》《蓝田山石门精舍》《渭川田家》《田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①唯独一首铺陈景物的五排《东溪玩月》,一作王昌龄诗,陈铁民先生《王维诗集校注》认为作者难以遽定,并且它明显是试帖赋题之作,也不适宜作为写景诗来讨论。[53]。许多貌似写景的句子实际是叙事。最典型的如《敕借歧王九成宫避暑应教》中两联:
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
黄生评道:“右丞诗中有画。如此一诗,更不逊李将军仙山楼阁也。‘衣上’字,‘镜中’字,‘喧笑’字,更画出景中人来,尤非俗笔所办。”[53](P26)但是我们只消参看《题友人云母障子》“君家云母障,时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画来”四句,就知道这是纯粹的叙事,说明暑热中九成宫特有的凉爽。除了“岩间树色隐房栊”一句,上三句完全是说明的而不是描绘的笔法,将对象的位置和动作关系作了细致的说明。《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一首被明顾可久评为“写景如画”[53](P366),而实际上此诗从头到尾都是叙述:“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青山尽是朱旗绕,碧涧翻从玉殿来。新丰树里行人度,小苑城边猎骑回。闻道甘泉能献赋,悬知独有子云才。”这哪里又是在写景呢?即便我们姑且承认“青山尽是朱旗绕”是写景,它的描述意义也太有限了吧?更不要说“新丰树里行人度,小苑城边猎骑回”一联了。这就像《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明明是写人的行动,刘辰翁偏说“带字画意”[53](P28)。前人在这些地方确实常有不加细考、大而化之的判断。《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两联,沈德潜也视为“纯乎写景”[54](P539),可后联恰恰是为避免纯粹写景而变换的叙事,与《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一样,都是一组蒙太奇镜头,也是王维笔下最具特色的表现手法。还有像《酬张少府》的“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归嵩山作》的“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从歧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的“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也是类似的例子。这种蒙太奇式的笔法,以不事刻画而重传神写意为基本特征,可与“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春园即事》)之类突出瞬间呈现的有限例证截然区别。古代批评家中只有王夫之注意到王维诗的写意特征,曾指出《送梓州李使君》“明明两截,幸其不作折合。五六一似景语故也”。他看出诗的颈联貌似写景,其实是叙事,只因为主导动机是写意,以致写景和叙事的界限不太分明。因此他肯定“右丞工于用意,尤工于达意。景亦意,事亦意”[38](P101)。评《终南山》指出:“结语亦以形其阔大,妙在脱缷,勿但作诗中画观也。此正是画中有诗。”[38](P98)诗从不同角度叙说了终南山的广袤高峻之后,以游览者与樵夫的问对结束全诗,“隔水问樵夫”仍然表现了空间的阔大,所以王夫之提醒读者不要错认为山水画里点缀的人物,即诗中有画,而正须看作是画中寄寓的诗意。
由于写景承担着叙事的功能,王维笔下的景物大多是粗略点染,不事刻画。《春中田园作》的“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是交代时令,引出下文“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的农事活动;《齐州送祖三》的“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系即目所见,为下文“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埋下伏笔;《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的“眇眇孤烟起,芊芊远树齐。青山万井外,落日五陵西”,以由近及远的景色表现了清晰的视觉,从而由“眼界今无染”引申出“心空安可迷”的禅理。诗的重心不在铺陈景物,写景除了突出视觉感受和景物的远近层次外,就没有着意细描的必要。由是这种写意笔法,非但不刻意于细节,甚至连景象的轮廓也很模糊。《汉江临泛》中两联著名的景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上联是以轮廓线不分明的写法来展现水天混茫的感觉,下一联同样不作清晰的勾勒,只用“浮”“动”两字形容江流奔涌的动感,造成奇警的效果。其艺术魅力与其说来自视觉的直观,还不如说是身体感受到的声压①声压是大气压受到声波扰动后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大气压强的余压,相当于在大气压强上叠加一个声波扰动引起的压强变化。我们在聆听低频量大的音乐时感受到的物理震撼,就是声压的作用。。的确,即使研究者们能从王维诗作中撷取一串串写景如画的句子,其中又有多少是以形似取胜的呢?最为古今论者推许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绝非以刻画形似见长吧。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四个物象,并没有关于颜色、状态的描写,尤其是大漠、长河、落日,都近于固定词组,定语大、长、落只有概括性的一般化说明而没什么具体的描写意义。两句真正出彩之处只在直、圆二字,虽是形容词而含有动词属性,如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含有升腾和沉坠的动态。所以,这一联写景与其说是形似而不如说是神似。王维另有《送韦评事》写道:“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送人赴边,只是悬想边塞景致;自身亲历此境,方才深刻地体会边地的辽远和苍凉。王夫之评《使至塞上》“盖用景写意,景显意微,作者之极致也”[38](P100),可谓深得作者之心。
中国画的写意特征是,无论风景或人物都仅抓住主要特征,而不作细节刻画,这使形象的表现机能带有强烈的程式化亦即符号化倾向。具有写意倾向的王维诗歌同样如此。《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一联,向来被推许为描绘朝堂气象的名句。乍读之下,我们也会觉得朝拜景象历历如绘;但细加品味,却发现两句是典型的写意而非工笔--宫殿聚焦于门扇,君王和使臣被代以衣冠和冕旒,这种文学修辞的借代手法,在绘画中就是传为王维《山水论》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远水无波的写意笔法,实质上是一种象征化的表现,以“九天阊阖”和“万国衣冠”来夸饰朝仪的规模盛大,以寄托长安收复后人们渴望再见汉官威仪的中兴幻觉和苟安心态。在“阊阖”“衣冠”和“冕旒”作为代表性的符号被突出时②《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也同样是符号化的表现。,更多写实的内容却被省略了。明代画论家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阐述绘画表现的三重景象,曾论及用笔的省略,即所谓“忽”:
凡画有三次第:一曰身之所容,凡置身处,非邃密,即旷朗,水边林下,多景所凑处是也。二曰目之所瞩,或奇胜,或渺迷,泉落云生,帆移鸟去是也。三曰意之所游,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处是也。然又有意所忽处,如写一树一石,必有草草点染取态处。写长景,必有意到笔不到,为神气所吞处。是非有心于忽,盖不得不忽也。[55](P287)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王维诗中的景句,一定是浑融疏略的写法占主导地位。像《归嵩山作》“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的例子,很能代表王维写景的特征,取疏而不取密、取神而不取形、取浑沦而不取刻画是其大旨。这其实也是整个盛唐诗风景描写的主导倾向,不只王维如此,同时代的大家、名家莫不如此。明代格调派诗论家谢榛将这种审美倾向概括为:“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56](P1184)王渔洋论诗鄙薄温庭筠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独赏其“古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一首,许为“晚唐而有初唐气格者,最为高调”[57](P4912),也无非喜其浑闳不切、无迹可求而已。由此可以间接地理解,盛唐诗歌风景描写的基本倾向就是浑闳不切,不拘泥于细节刻画。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断然否定王维诗中存在细腻的景物描写。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王维放弃写意化的表现而致力于细腻的刻画,他就往往用非常突出的意象来构成场景,使景物成为渲染氛围的媒介。如《秋夜对雨》“寒灯坐高馆,秋雨闻疏钟”一联,张谦宜评为“写意画,令人想出妙景”[58](P845),其实妙景之外还有孤寂的况味;《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一联,上句写山泉遇峻石阻挡而流声微弱,下句写阳光透过茂密的松林失去热度,传达出山寺幽深冷寂的氛围;《奉寄韦太守陟》“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一联,以孤馆草木的衰落映衬作者的境况,引出结联“故人不可见,寂寞平陵东”的心境;《归辋川作》“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一联,也是以草木象征身不由己、无法摆脱仕宦羁束的命运,为结句“惆怅掩柴扉”定下情感基调。这种意象化的表达可以说是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方式的先声。我的看法,情景交融的意象化抒情模式是在大历诗中定型的,王维诗中这种意象化的苗头,涉及唐诗写作范式演进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专文讨论,这里姑不展开。
以景叙事、离形取神、淡化线条轮廓、忽略细节,这些特征的交集,就造成王维诗出韵幽淡的意趣。尽管有许多为人称道的写景名句,却少有以刻画见长的例子。王鏊《震泽长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59](P1690)王维诗中风景所留给人的印象,就像他的水墨画一样,无非是一个“淡”字,它是艺术家从胸襟之淡到笔墨之淡的全程体现。
五、结论
如果前文对王维绘画特征的概括大致不错,那么就可以肯定,苏东坡能从王维诗中看出这些特征,是很有眼光的。问题是这些特征是否为诗歌中前所未有,纯属画家王维移借了绘画的艺术精神呢?
回顾诗歌表现的历史,从南朝到初唐这个阶段是形似的追求走向极致的过程。虽然它对于唐诗艺术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资源积累,但在后人眼中,“其时脍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等诗,本色无奇,亦何足艳称也?”[60](P351)确实,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来说,这类名句绝不是诗歌最上乘的境界,就像黄生《诗麈》所说:
写景之句,以雕琢致工为妙品,真境凑泊为神品,平淡真率为逸品。如“芳草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沈佺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皆逸品也。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维),“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皆神品也。[61](P320)
以此标准来衡量,王维诗歌的写景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超越了以雕琢求工的妙品,而臻真境湊泊的神品、平淡真率的逸品境界。这与他绘画的写意精神正相一致,具有反造型、平面等一般意义上的绘画性的倾向。这种写意化倾向融入诗境,强化了超越绘画性的动态特征,不仅实现了诗性对“形似”的超越,同时也使诗歌中的风景由自在之景向意中之景过渡。中国古典诗歌最核心的审美特质--情景交融的意象化表现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正式开启了它日益占据诗歌美学主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