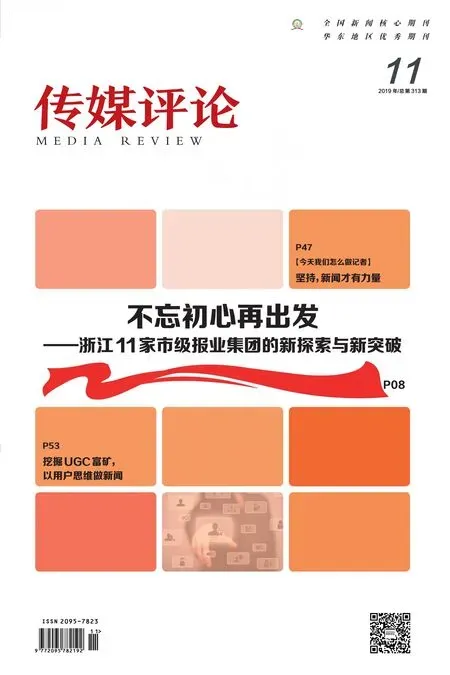专业化、精细化、社区化:UGC内容在传统媒体中的三种应用
2019-12-17文_刘征
文_刘 征
从上世纪60年代控制论风靡欧美开始,维纳的《控制论》就对现代社会有着诸多的积极影响。在他的理论里,人在技术体系中是相当重要的。随后,麦克卢汉也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当中提到了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乃是人的延伸。既是思想的延伸,又是身体的延伸。至于凯文·凯利,更是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把技术看成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进化的一部分。
倘若这些乐观的技术理论是真的,那么依靠大规模集成效应获得关注度的传统媒体将有理由充分利用新技术来反映一种复杂社会体系的表象。在它的专业机构支撑下,它所具有的一种拟社会属性会让我们通过信息书写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感知到社会的全貌。并且,这种趋势正在被证明。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Chinese Academy of Cyberspace Studies)披露的数据,《纽约时报》网站月访问量达到3.881亿次,并不比4.992亿次的谷歌新闻访问量小多少。[1]即便是在YouTube这样的聚合类媒体上,专业生成内容(PGC)也比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增长速度更快。连聚合类媒体也在这种趋势下变得越来越制度化。[2]
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复苏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完整地发挥一直以来传统媒体引以为傲的拟社会属性吗?它所要传递的一种有体系的信息生态是否会因为来自于民众自发的碎片化信息而受到冲击?或者,在互联网的业态下,传统媒体的采编发过程中针对主题的策划、采访、编辑到销售的流程是否将完全让位于未经加工的原始信息的互联网呈现?
本文将通过传统媒体利用UGC内容的一些策略,来讨论一种新信息体系建立的可能性。在这种尝试里,我们假设传统媒体以往的体系性优势依然可以起到主导作用,而新的UGC内容的加入,不是削弱和冲击了传统媒体当中信息的系统性,而是增加了新闻媒体在以往曾期待成真,却一直限于各种原因未能成真的一种新闻理想。在这种新闻理想里,新闻既可以系统地呈现社会样貌,又不至因为内容过于庞杂而显得不够专业化,同时,由时效性带来的不全面真实也可以被弥补。
信息专业化过程中的UGC
所谓专业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表现为内容的专门化生产。并且,这种专门化生产体现在媒体的整个机制设置当中,并受其保护。比如,每个传统媒体都会将所属人员分成时政部、经济部、法制部、文娱部、社会新闻部等等。每一个部门都在该媒体拥有一块专版,且随着记者进入到每一个分部,记者将会进入到这个分部所对应的社会领域,并对此领域进行深耕,以获得只有业内人士才能知晓的内容。这种机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专业记者采集到的新闻无论从数量和深度,都是异于常人的。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优势正在被打破。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普通民众借助互联网平台发布了一系列信息。这些信息既不专业,也缺乏制度性制约,但却渲染性极强。正如布迪厄在《区隔》当中对大众趣味的总结,普罗大众天然喜欢那些感性的、或者貌似有理,实则新奇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带有强烈情感和戏剧性的文字都天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的传统媒体试图激发用户的创造能力,以增加自身的专业度。据《国外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引入UGC的现实图景》[3]一文的回顾,早在2003年,《达拉斯晨报》和美国航天航空局就曾联合呼吁该报读者提供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目击性文字或图片素材,以期获取有利于揭开事故原因的宝贵线索。随后,伊拉克战争等轰动事件也常寻求来自社会各界的信息。
至于英国,根据Alfred Hermida和Neil Thur-man针对114位编辑和英国主要新闻网站的执行编辑的半结构化采访,结果显示,英国早在2006年就已经通过“投票”“留言板”“评论”“Q&A ”“博客”“你的媒体”和“你的故事”等各种不同板块来增加与受众的互动。同时,这种互动作为鼓励用户生产内容的开端,最早使用户生产内容由评论这种简短的内容形式变成了博客这样颇具规模的内容生产模式。在这些尝试当中,用户自然以主题被区隔开来,讨论都是围绕媒体设置的主题而展开。这就使传统的、仅限于编辑部内部运作的一种封闭的采编系统获得了继续纵深下去的可能。媒体的专业度获得了明显的提升。
而且从一开始,用户参与的积极性就很高。每日邮报公司的民意调查,在英国一次可以获得1万张选票。读者博客更是受到了大众的追捧。也是在2006年,英国最畅销的日报《太阳报》率先创办了读者博客。尽管这种博客因其在技术上托管在新闻媒体的Web服务器上,使媒体面临很多法律及道德的麻烦,但是大多数媒体依然采用比较宽松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依靠注册流程提升责任感,或者采用反应性审核。在各家媒体的不懈努力下,英国全境的媒体博客从2005年4月开始投入使用,并在其后的18个月里,博客的数量从7个增加到118个。[4]这种做法的直接好处就在于媒体收编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精英以及专业人士,并利用这些业余写手的文章补充记者采访的不足。
国家性大报开设博客做法在法国也十分兴盛。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就专门在显著位置开发了下属博客。邀请写手发表各类观感、业界观察以及个人生活体验。在这些人士当中,学者、教师及各行各业的发烧友是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博客类似于纸媒时期的专栏。因为博客没有篇幅的限制,因此比专栏更丰富。媒体也着力展示这些博客的内容,其中最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即在一篇新闻当中,通过字典关联的方式,用网络爬虫将相关博客的内容标题嵌入新闻文本的段落之间。涉及到该段的信息一旦有了其他文章的支持,就显得十分复杂。非但背景被还原了,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新闻于是具有了明显的互文性特征,变得既有体系,内容也十分丰富。用户生产内容于是成为纸媒内容专业化的一个助益。并且,媒体邀请各种专业人士进驻本媒体,也获得了更多的、源源不断的高品质素材。
但是,随着博客维护费用日益剧增,加上上文提到的博客内容无法被有效掌控,现在,很多媒体已经开始关闭旗下的博客。法国《世界报》就是其中一家,它自从2019年5月宣布于2019年6月5日关闭下属博客以后,这家报纸就再也没有了下属博客。发文者则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下载收藏自己的文章。当然,虽然这种做法在《世界报》遇挫,但是它依然是一些媒体最常见的用户生产内容方式。尤其在一些互联网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UGC对信息细节的填充
上述方式都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早期与UGC内容的结合。在当前,这些内容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操作。目前,以细致化作为目标的UGC内容手法朝向社交化的方向发展。比如,Annie Schugart曾在《The Best i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Journalism 2017:Pushing the Limits of Storytelling》[5]一文中详细列举了美国在2017年最受欢迎的几款交互新闻,包括《The Pessim ist’s Guide to 2028(悲观主义者的2028年指南)》(彭博新闻)、《Trump Prom ise Tracker(特朗普承诺跟踪)》(华盛顿邮报)、《Emmy Awards Analysis:Live Chat(艾美奖分析:现场聊天)》(纽约时报)等均成为大众参与交互新闻的方式。这种新闻的特点在于既能够收集到全国各地的民众的意愿,并且还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方法,让这则新闻在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保持热度,并且,因其十分形象,阅读门槛很低。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信息填充式的交互新闻来自于以往读者调查、读者评论和图片等形式,是一种读者参与新闻的旧方式的新变种。它的要义就在于需要媒体设计出一个大的主题框架,用户只需要将自己与此新闻有关的活动信息加诸其上,就可以成为新闻信息的提供者。比如,纽约时报为《权力的游戏》创建的《Good,Evil,Ugly,Beautiful:Help Us Make a“Game of Thrones”Chart》新闻游戏,就吸引了无数网民参加。而类似在全国征集日全食照片及故事的可视化新闻产品更是调动了来自全美各地网民的积极参与。
当然,在用户参与到媒体新闻的过程中,这些新闻之所以变得出乎意料的好看,并非仅仅是因为交互新闻设计得好,多数时候,是因为受众的参与创造出了新的鲜活的内容。这些产品虽然不及传统的PGC内容专业,却更受欢迎。Lister等人比较了YouTube和电视上的节目类型。发现这些用户自制的视频节目其实与我们所看的电视节目十分相似,但是同时它们又完全出乎意料和不可预测,拥有新鲜的活生生的个人印记,而不像专业化产品那样过于流畅,反倒产生了距离感。[6]
Ahva曾在2017年写了一篇《新闻业的“中间人”是如何参与实践的》(How is Participation by“In-betw eeners”of Journalism)[7]的论文。试图在文中勾勒参与新闻创作的个人是什么形象。在文中,Lahva先是确定了各种各样的大众贡献者:活动人士、志愿者、艺术家、学生和当地人,并把这些人统统称之为“中间人”。即他们不是全职专业人士,但是都参与过至少一次新闻工作。最后,Ahva发现,这些非专业人士参与新闻时,并非都是为了公开辩论,很多人对社会和睦、文化生活或他们的个人职业发展都有表达的意愿。因此,经由这些业余人士的加入,新闻的细节都被填充,甚至连新闻的面向也都丰富了。
社区对UGC的吸引力
无论是为了增加新闻专业度而鼓励UGC内容,还是为了精细度增加用户对新闻的参与程度,其根本的关键就是要激发起用户参与和生产内容的欲望。是否能够激发起用户的行动,一个关健问题就是了解用户参与创作的心理。有研究发现,之所以用户愿意参与到新闻创作当中,主要是希望获得声誉。他们对内容质量和同理心的感知影响着自己对控制、包容和情感的期望。而在自己所身处的虚拟社区,人们参与的欲望更强。
所以,媒体生产内容投放的平台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自然》杂志,他们认为了解自己的视频应该嵌入到哪些网站,比知道观看者和订阅者的数量更重要。作为以科学家、博士生和科学文献的读者为主要受众的媒体,它要激发起受众的创作和参与,就需要到适合的平台发布内容。
至于BBC地球频道(Earth Unp lugged)发现他们的观众年龄在16到34岁之间,所以他们决定通过YouTube频道创作原创内容。它有一套精确得多的风格指导方针,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他们的YouTube内容具有特定的个性:他们认为视频是与社区的对话,并试图与该社区的用户建立亲密关系。所以他们录制的视频,演讲者都是看着摄像机,镜头多为特写,新闻以一个问题开始,答案处于中间,清晰的启示放在最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回应受众,BBC甚至专门在团队中指定了一个特定的“社区管理者”角色,该角色的职责是密切监视对话,并直接参与形成的社区。有时候,受众反馈将在下一期的内容里被回应,或者干脆成为下一期的内容。
除了上述的虚拟社区,服务型内容的生产将使媒体的内容直接对应到实际的社区生活。David Harte、Andy W illiam s和Jerom e Turner通过采访和分析新闻网站内容的方式,评估了英国超本地新闻媒体培养参与形式的方式。研究表明,当业余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参与新闻活动时,如果这种参与涉及到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受众/业余新闻参与者之间的互惠或关系交换形式时,他们的参与将是最成功的。[8]
这种互惠交流既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也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除了需要基本的信任以外,这些关系还要以改善社区为关键。事实上,这篇文章认为,参与互惠关系的超本地新闻媒体不仅仅提供了参与创造新闻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为社区内其他团体或个人发起一些项目,以做出贡献。比如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以改善社区成员生活的方式帮助他们建立联系。
这种在英国进行的服务型内容,以媒体专业记者作为主导,但是却显示了社区服务的特点。当然,这种方式在国内也已经有了很多。一些儿童频道经常为儿童举办暑期或寒假活动,一些医药板块的记者会依靠在该领域的人脉组织挂专家号等活动,这些都拥有便民惠民的性质。当然,除了传统媒体以外,类似于穷游网或者小红书一类专门化的新媒体,主要内容就是依靠用户的参与。比如,小红书主要就是依靠用户分享全世界各地的好用之物给其他用户起到参考作用,它的本质是口碑效应。至于穷游网,则是依靠大量的旅行者发布旅行攻略来给其他用户做出参考。这些专门化的新媒体所采用的主题社区化运营都值得我们去关注。
总之,在互联网成为用户使用常态的今天,网络媒体体现了开放式情景沟通、参与性与反馈性沟通、层次性沟通、社会性互动沟通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传统媒体更好地利用用户生产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又不能仅仅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需要激发用户创造的欲望。这就需要媒体发挥以往策划主题的优势,并且,始终秉持传统媒体的优势,依靠UGC内容使新闻成为一种复杂的信息群,以强化自己的拟社会体系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