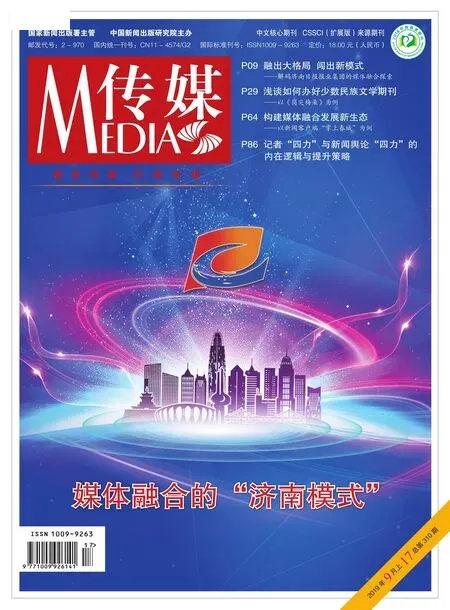“西安年”节庆活动的空间叙事与文化传播
2019-12-17闫月英
文/闫月英
从2018年12月31日开始至2019年3月6日结束的历时66天,“西安年”节庆活动策划推出了包括开幕式和闭幕式两项主会场活动在内的251场活动。此外,活动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媒体联动的方式,展开全方位互动式营销,利用信息流、新媒体等网络平台开展主题活动宣传推广,进一步提升了“西安年·最中国”的品牌影响力。
“西安年”不仅是一种新型的节庆活动,在空间生产理论的视野中,显然是一种在多种力量交织下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再度谋划。通过这种谋划,城市的街道成为一种景观,一种具有展演性质的特殊媒介。在参与者与观看者的狂欢中,叙述城市故事、建构城市价值、创造商业机会等各种诉求相互交织、相互利用,使得“西安年”活动成为具有多项收益可能的文化产业。
一、作为空间媒介的“西安年”
1.“西安年”活动以“主会场+分会场”的形式呈现。“西安年”活动空间的规划与选择,充分体现了主办方的精心设计,贯彻了主办方的意图。活动承载地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沉淀着历史文化记忆的古代建筑,如西安城墙、书院门街区;第二类是近年来新建的拟古建筑与园林,如大唐芙蓉园;第三类是体现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现代空间,如曲江书城与创客街区。通过对城市道路和景观的精选和组合,主办者生产出一个独特的、最能体现城市面貌与特色的空间。当热情的观众汇聚到这里,观看高度组织化、仪式化的展演,通过游客们在这些空间进入、感受、观看、体验、回味、传播,西安城市景观的空间叙事文本便被生产出来了。
2.城市的空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是一种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存在。长久以来,空间被视为一种物质构成的环境和背景性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索亚等人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阐释,促成了一种崭新的空间意识的诞生,由此开启了思想界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空间学者索亚提出,空间概念可包含三个层次,即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其中,第三空间特别强调了城市作为一个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存在,更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是一种观念,是人们的想象,是一个“既真实又想象化”的世界。
3.空间通过在时间中的展开,处处暗示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位于曲江核心区域的现代唐人街是“西安年”的中心承载区。春节期间,这条1500米长的步行街一到夜晚便火树银花,流光溢彩,游客摩肩接踵,万头攒动。徜徉其间,仿若时空穿梭般梦回长安古城。在这条街道上,不管是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等文化地标,还是民生百货、银泰商城等高档购物中心,外观设计都体现着汉唐建筑风格的诸多元素:刚劲有力的斗拱,宽展明快的檐角,错落有致的鸱吻,大小屋脊组合的建筑群落。陕西大剧院主体建筑采用重檐庑殿和单檐歇山的建筑形式,将观演建筑的大空间用唐风大屋顶覆盖,放置高台之上。除此以外,引人注目的还有矗立于街道中央高大生动的系列主题群雕,以贞观之治、大唐群英等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由北向南呈现在空间场所的边界、节点、路径之间。它们的出现就像文本叙事中的闪现、插叙、并置的方式,对整个街区进行着空间渗透与主题强化。
诚然,规模庞大的仿古建筑群并不承载真正的历史信息,但它是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通过对景观符号的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展示的一个“拟态环境”。这个“拟态环境”不是对历史的再现,而是对历史的表现,是一种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呈现的“象征性的环境”。来此游览的游客欣然徜徉其间,在“拟态环境”中建构着自以为真实的历史感。如果说这样的街道与景观提供了整个空间叙事的框架,那么,更为丰富的内容则来自其内部空间中的文化展演。
二、空间中的“身体在场”
1.空间内部的各项文化展演活动是“西安年”空间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达66天的时间里,主办方借助“年”这一凝聚着中华精神信仰的节日主旨,策划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展演,并突出强化了游客的身体体验。文化立足于传统,如果未经现代解读、传播与实践,就无法在现代发挥作用。在“西安年”的空间中,无论是大唐不夜城,还是明城墙,亦或是现代唐人街,都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完美的展演空间与场所。“年”文化与建筑景观相互渗透,相互强化,使整个空间叙事血肉丰满。以大唐不夜城为例,新年狂欢主题活动包括正月初一的新春大拜年及大唐文化体验活动;正月初五的巡游活动以及全民迎财神活动;正月十五的灯谜类、表演类、民俗游戏类活动等。在现代唐人街南端的开元广场,每晚七点举行一场由东方歌舞团带来的盛大演出,节目从舞蹈到歌曲无所不包。传统文化通过表演者的肢体表达、语言传达呈现在空间中,通过转喻、象征等视觉修辞,用以制造故事与幻象,挟带着特定偏好、价值立场,使现代社会的观众沉浸其间。空间中的身体在场,具有认知情感建构的特征,使空间具有了更明显的形而上属性。传媒对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空间文本进行进一步的编辑、加工、呈现,二者在互动中创造了新的意义空间。
2.体验式文化游戏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完成“最中国”的心理体验。美国传播学者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强调,在同一空间内,受众经由身体在场、共同参与、情感共鸣等以唤起或塑造、强化仪式共同体的价值与文化记忆。他认为,传播本身作为一种仪式媒介,可以唤醒受众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吸引他们参与到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之中,以形成民族等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寻根之旅。在“西安年”所呈现的空间中,颜色、光线、造型、材料、语言、动作等种种符号构成了一个乌托邦的精神世界,无处不在地强化着某种信仰与精神体验。每到夜晚,人们或漫步现代唐人街,穿梭在唐朝特色的茶道、酒肆间品尝美食,观看古代诗歌、礼仪、服装表演,欣赏专业艺术团带来的精彩演出;或游玩于步行街上,亲自体验一把童年游戏跳皮筋,亲手触摸活人扮演的兵马俑雕塑。人们眼睛所视,肢体所触,口舌所尝,唤醒的是共同的民族情感与记忆,确认着文化共同体的身份。“最中国”自然而然达成了观者对西安的心理认同。
三、社会化媒体对空间的意义再生产
1.传媒的介入,瞬间将囿于狭窄之地的空间转化为超时空的传播文本。电视传媒的影像呈现、社交媒体的实时讨论,以及短视频APP等新兴表现形式的使用,都是当今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具有话语生产与社会动员能力的信息互动平台。截至2019年2月15日,“西安年”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亿,相关话题在抖音上的播放量达2.9亿次。但我们也应看到,媒介内容让城市外部的人快速了解城市的同时,空间符号选取的同质化却又强化了受众对城市空间的刻板印象,其导致的结果是对整体空间的认知偏差。在社交媒体上,节目生产者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大雁塔、灯光秀、大唐不夜城等几个标志性的象征物,而忽略了不具有炫目效果的场景,也自动忽略了在这一空间中流动的人群。随着“西安年”视觉符号的不断强化与渲染,西安城市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真实,成为一个随时可以反复复制粘贴的社会化表征。
2.空间叙事借助图像与视觉创造了新的意义空间。在新媒体平台上,“西安年”的多个瞬间被捕捉为一张张图片或一个个短视频。网友惊叹镜头里“西安年”的迷人与繁华,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分享、评论、转发。借助关注、分享、评论等功能,这些媒介内容在社交平台上体现出四两拨千斤的议题设置力量,产生了类似于核聚变的传播效果。其中,图像与视频是最吸引眼球、传播力最强的符号形式,它们善于制造令人目眩神迷的光影效果,表现出“西安年”恢宏阔大的气势,令人印象深刻,观之难忘。在抖音上,播放量最高的几个短视频均是以航拍机摄取的光影瞬间,通过航拍这一俯瞰视角,观众所看到的是一个被精心建构而成的“西安年”:仿唐建筑群上空穿梭不停的激光灯柱,悬挂空中一望无际的莲花灯,大明宫公园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秀。制作者还会给这一个个15秒的小视频配以特定的音乐、滤镜、特效,进行重新演绎,营造出梦回大唐的感觉。在微博上,映衬在仿唐建筑群下的火树银花,被璀璨夜色包围的高耸的大雁塔,被一张张图片定格。制作者对媒介内容进行再加工,实现了对空间叙事的重新解释与二次传播。
3.空间叙事实现了从“身体在场”到“身体缺席”的意义建构。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有充分的成本和机会进入到空间内部亲眼观看或亲身感受,传媒满足了这部分身体不在场者的参与欲望。微博、抖音等平台的主要特征就是能即时将空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空间场。在电脑或者移动终端的后面,当他们集体观看并对视频评论、转发时,就形成了类似于聊天室群聊的氛围,营造了超时空的集体观看体验。这部分观众虽然身体缺席,但可以在媒介精心编辑的文本中共享信仰与精神体验。文字、图片、视频等媒介符号将抽象隐喻的精神能量传递给观众,通过观众与媒介内容的身心互动,意识形态立场得以表达、体验、强化和传承。弹幕评论作为网络视频的新场景,不仅让物理空间与视频空间的界限消除,同时也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连接起来,使得观众在异时空之下居于同一视频中,打破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实现了不同时空的混杂。这样,“西安年”所造就的空间不仅仅是面对在场者的意义建构,也完成了不在现场受众的意义建构。
四、结语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透视城市空间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如前所述,空间叙事是一种包含了特定偏好、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实践活动。“西安年”以凝聚着中国集体记忆的年文化为契机,开启了一种力量交织的空间叙事与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空间谋划案例,对“西安年”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探究与分析,不仅有助于对传播学理论的研讨,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辩证地审视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
不可否认,“西安年”的空间谋划给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良机,但我们在肯定成功的同时,也不得不冷静思考这场空间叙事的风险。
其一,城市在匆忙中花费巨资创建了一个与内在要素有所联系、但也有所取舍的“想象的共同体”。这座全面重建的空间,被认作是对“过去”的真实记载,但这种“过去”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伪造的。它向人们植入一段关于过去的“错误记忆”,其实质是对个人和集体的“历史记忆”实施强制性的再造。
其二,传统文化挟带着商业欲望的呈现,是否会替代与消解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与现实的冲突,但并不能消解或带走这种冲突,反而把传统文化导引到一条简单化的道路上。长此以往,“年”文化将日益丧失其丰富深刻的内涵而成为简单的存在,独特的文化记忆可能会逐渐被遮蔽、甚至被剥夺。
其三,组织这样一场丰富复杂的城市节庆活动,背后所要调动的市政资源超乎想象。回顾近十年来西安的城市空间拓展,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曲江新区,曲江模式一路风光,而最大的获利者则是曲江系房地产开发企业。趋利是资本的唯一目标,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逻辑是商业利益,是资本增殖。通过“西安年”对城市空间的谋划、招募、征用,同时也实现了商业资本与政府意志对空间性质的全面渗透。空间本身的性质与结构不过是特定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一个注解。资本基于利益的驱动开展城市建设,在这种趋利的行为当中,各种拆迁风波也夹杂其中。西安2011年法门寺景区上市和随后的兴教寺拆迁申遗事件,曾将曲江模式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证明,资本的增殖欲望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对传统的极大破坏,这一教训值得所有城市管理者铭记。